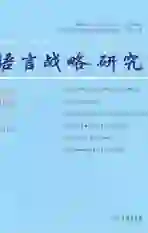澳门的语言运用与澳门青年对不同语言的认同差异
2016-05-30覃业位徐杰
覃业位 徐杰
提 要 澳门通行着多种语言和方言,极为复杂的多语生态和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为研究语言认同和多语竞争提供了语言社区样本。语言认同是指语言使用者就自身与某种语言或方言之间关系的心理定位。调查显示,语言使用者对不同语言的认同程度和功能定位差异直接影响其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语言认同还跟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密切相关。绝大多数澳门青年对粤语的认同度最高。而对其他三种语言的认同度相对较低,且功能明显分化。多数澳门青年认为葡语是官方语言和第二外语,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英语是第一外语。澳门大、中学生对不同语言的不同心理距离,决定了其对不同语言的不同言语态度和不同言语行为,而其在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上的表现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语言认同差异。
关键词 语言认同;语言态度;语言运用;澳门
一、引 言
随着科技的日益进步、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工作空间迅速扩大。在这个潮流中,我们的语言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个人或社会的多言多语模式逐渐取代以往的单言单语模式,成为语言生活的一种常态。在此环境下,语言之间的竞争势必变得异常激烈,不同的语言认同必定会影响同一社区中语言使用者所做出的语言选择。因此,语言认同研究既有现实的实践意义,也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然而,目前关于语言认同的概念和性质并没有理清。本文在进一步梳理语言认同概念的前提下,结合澳门青年尤其是大、中学生的语言认同的案例进行阐述。
众所周知,澳门虽小,但澳门社会使用的语言种类相对较多,语言运用情况极其复杂,素有“语言博物馆”之称(黄翊、龙裕琛、邵朝阳 1998:3)。复杂的多语环境和较为封闭的地域环境恰巧能很好地为研究各种语言的地位和功能变化提供得天独厚的条件,而这些正是在较大社区难以进行的。本文将首先梳理与语言认同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献,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这个重要概念进行重新定义。随后简单概述当今澳门社会的语言运用状况,结合我们的实地问卷调查结果,讨论与澳门青年语言认同相关的种种问题。
二、语言认同的性质
(一)以往有关“语言认同”的定性论述及其存在的问题
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焦点问题之一,“语言与认同”这一议题已经受到了语言学家的充分关注。近些年来,部分学者开始聚焦于对语言本身认同(即“语言认同”,linguistic identity)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一系列很有意义的话题,如语言认同与语言变化(孙德平 2011)、语言认同与方言濒危(杨荣华 2010)、语言认同与语言教育(Zhou 2012;周明朗 2014)等。这些研究对语言认同的内容及其作用做出了十分有益的探讨,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对语言认同理论的认识还较为有限。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关于语言认同本身的性质目前尚不明晰,不少文献是模棱两可,甚至是避而不谈。①
明确讨论语言认同性质的文献也是观点不一。有的学者界定得比较宽泛,如韦达(2002:116)认为语言认同既可以表现为言语兼用互融,也可以是不同语言间的互相承认、不相排斥。有的学者则将语言认同与民族认同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等相联系,如姜瑾(2006:37)认为语言认同是通过使用某种语言来表示民族或种族归属的身份认同,杨荣华(2010)认为语言认同是讲话人对某一语言的本体特征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价值的认同,同时还涉及讲话人的身份重构问题。也有学者提出语言认同是用语言区分我群与他群的心理和实践(张军 2008:70)。我们认为,以上这些对语言认同性质的探讨较少涉及其最核心的内容(具体分析见下节)。
语言认同的内容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定性有差异,各家对语言认同的内容也稍有不同,但基本都在语言态度、语言行为以及语言意识之间做排列组合。②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讨论均将语言态度视作语言认同最核心的内容,比如“通过对语言态度的研究可以发现社区成员语言认同的情况”(王玲 2009)。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做深一层的分析,就会发现对语言态度的界定与以上语言认同所涵盖的内容基本是重合的。一般认为,语言态度是指对某种语言或方言的感情(feelings)(Crystal 2008:266)。持语言态度是多元结构观点的学者基本上都赞同语言态度包括认知的(cognitive)、情感的(affective)和意欲的(conative)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分别与知识(knowledge)、评价(evaluation)和行为(action)相对应(Agheyisi & Fishman 1970)。显而易见,这三方面与上述语言认同的三个内容整体上大体一致:知识对应语言意识、评价对应语言态度、行为对应语言使用。③ 可以说,以往对语言认同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基于语言态度的或宽泛或狭窄的讨论:要么综合了语言态度、语言行为和语言意识,要么就只讨论语言态度的情况。
(二)本文对语言认同的定义
一般认为,认同就是进行定位(positioning),就是确定自我和他物之间的关系(如Bucholtz & Hall 2005:586)。比如,文化认同就是定位个人或者群体与某种文化之间的关系,民族认同可以理解为是个人或群体定位与某一族群的关系。由于语言具有社会属性,它与社会、文化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语言认同状况也能反映个体或族群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状况。但这些都属于语言认同的外延而非其内涵,亦即前人对语言认同性质的探讨都只涉及外延部分而未能触及其根本。我们认为,语言认同指的是语言使用者就自身与某种语言(方言)之间关系的心理定位。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多语社会的大趋势不可逆转,直接的影响就是个人语言模式的转变:从单言单语模式演变为多言多语模式。在多语模式中,使用者所持有的各语言不可能是平等的,它们都具有不同的地位和功能。这些功能甚至会因语言习得者的不同而不同。如果从多语习得者的认知角度来说,语言的功能大致可以分为第一语言/
第二语言、母语/外语、工作语言/生活语言、国家通用语/方言、民族语言、官方语言等。此时,语言认同就具体表现为联系自身来给语言定位功能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语言使用者将语言的这些功能与(自己所使用的)某一语言相配对的心理过程就是语言认同。
由于语言认同是一种心理层次上的认知,它无疑会影响具有现实性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比如语言认同上的差异可能会投射到对该语言的态度上来。一般来说,语言使用者对第一语言比第二语言具有更积极的态度,母语比外语亲切度更高,生活语言可能给人更友善的感觉,而工作语言或官方语言则可能更权威,往往象征着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另一方面,语言认同的差异可能会更直接地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行为。比如说,通常情况下会使用母语而不是外语来跟自己的父母或子女交流,与朋友聊天会使用生活语言,在国外遇到同胞一般都会使用民族语或者国家通用语,如果遇到的是同乡则甚至会使用方言。
语言认同与地域认同、文化认同、民族(国家)认同等也密切相关。按照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语言具有社会性,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因此可以作为观察认同的窗口。如果语言认同能够影响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那么就有理由相信语言认同也会与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等认同的其他方面密切相关。比如多元文化、多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如果母语有所差异,那么他的文化认同或民族认同与别的孩子应该也有不同。而对于同一语言的语言认同不同,那么这些多语使用者在其他认同上也会不尽一致。
三、澳门语言运用的现状
要深入认识澳门的语言认同现状,不能不了解澳门多种语言分工并存、相互竞争的现状。
“特殊的历史原因,特殊的地理位置,特殊的经济生活以及特殊的政治历程决定了澳门特殊的语言状况。”(程祥徽 2005:21)澳门虽然仅有30平方公里的面积,但语言种类较多,最显著的就是标签式特征的“三文四语”:“三文”为中文、英文和葡文,“四语”是粤语、英语、葡语和普通话。④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少数群体使用的语言或方言,如菲律宾语、越南语、闽南语、客家话等。因是之故,澳门往往也被学者称为是“语言的拼盘”(刘羡冰 1995)、“语言的博物馆”(黄翊、龙裕琛、邵朝阳 1998)。
丰富多样的语言资源无疑会使得澳门语言运用的具体情形显得异常复杂。根据最新的调查数据⑤,在澳门常住人口使用较多的语言中,粤语占据绝对优势,所占比例高达83.3%,在澳门通行无阻。同时,普通话(5%)、英语(5.7%)、葡语(0.7%)和其他语言或方言(5.3%)也很活跃。
在澳门的语言景观(即公共空间的书面语,如招牌、广告牌上的文字使用)方面,其总体特点也显示出澳门是一个多语言并存的社区(张媛媛 2015)。一方面,澳门语言景观涉及的语言种类多,涵盖中文、葡文、英文、日文、韩文和法文等。另一方面,同一样本中又以多语并列的情况为主,所占比例高达53.6%,亦即体现出多语并存、多言并用的局面。
多语社区可以提升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其成员用来交际的语言在数量上不止一种。根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调查,九成的澳门常住人口会说粤语, 41.4%的人会使用普通话,还有21.1% 的人能够用英语进行交流。由此可以推测,很大一部分澳门常住居民和本地居民都具有双语甚至是多语的能力。苏金智等(2014:52,73—75)的调查也显示,澳门大、中学生和普通居民一般都能使用二至四种语言或方言,部分人能使用的语言数目甚至高达五种。
同处于澳门这样一个狭小地域空间和微型语言社区中,“三文四语”之间客观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根据邹嘉彦、游汝杰(2001:209—210),决定语言综合竞争力的是五项要素:政治、文化、经济、人口和文字。照此看来,葡文与中文(包括粤语和普通话)一样,在政治(主要指官方的语言政策)这项要素上享有明显的竞争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条明确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语文。”所以即使葡文、葡语在使用人口这项要素上处于明显的劣势,它仍然能与其他三种语言(方言)并列。在经济竞争力上,普通话显然是首屈一指的。每年到澳门观光旅游的游客大多数都来自中国内地,普通话自然而然就成为商家吸引内地游客的首选语言。而粤语则具有最大的人口优势,九成以上本地居民的第一母语就是粤语。英语在澳门虽然没有法定地位,但是由于英语是事实上的世界通用语,外加澳门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和高度国际化特点,所以英语在澳门一直享有“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或“半官方语言”(de facto and semi-official status)的特殊地位(Moody 2008)。就“文字”(亦即书写系统)来看,“三文四语”中“三文”均有完整规范且广为通行的体系。此外,几种语言背后所分别依托的中华文化、英美文化和葡语文化也都是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所以它们在文字和文化两项要素方面其竞争力难分高下。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澳门的语言数量众多,既有标签式的“三文四语”,还有不少其他语言或方言,同时澳门的语言运用情形也非常复杂。具体来说,粤语在澳门的语言运用中占据着绝对优势,可以说是澳门流通最为广泛的语言,其他语言则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内保持一定的竞争力。
澳门复杂的多语生态为研究语言的地位和功能变化提供了几近完美的环境。针对澳门语言文字的运用状况,除了澳门官方粗略性的统计和普查外,还有不少学者做过一些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术性调查(可参考Yan & Moody 2010),内容主要涉及澳门人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取得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成果。其中规模最大的为苏金智等(2014),他们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调查了澳门大、中学生和公众场所民众的语言使用和语言态度。但到目前为止,有关澳门人的语言认同问题尚未见到直接或间接涉及的文献。
四、澳门青年对不同语言的认同差异
澳门是一个青年化的城市。澳门统计暨普查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12月31日,13至29 岁的人口为163 500人,超过澳门整体人口的四分之一。⑥ 这一群体的构成也相对单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们的想法在最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今以及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典型澳门人的状况。而中老年组澳门人的构成则比较复杂,其中外地尤其是在中国内地出生、在不同年龄阶段移居澳门者众多,而且成人移民虽然人已移居,但其思想意识、语言认同等可能并未随其居住地的改变而发生巨大改变。就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中老年组难以作为当代澳门人的典型代表。
根据第二节语言认同性质的观点,我们以问卷形式随机抽样调查了澳门的一所大学和两所中学的学生,考察他们对“三文四语”中“四语”的认同状况。⑦ 其中本地大学生(平均年龄19岁)和本地中学生(平均年龄14岁)各120人,回收的有效样本大学生为105份,中学生为108份。以下分别展示大、中学生对粤语、英语、葡语和普通话的认同情况。
(一)粤语:功能多样,认同度普遍较高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都一致认为粤语扮演着第一母语(92%)、生活语言(95.8%)、工作语言(89.7%)的角色, 同时还是澳门的官方语言(88.7%)以及自己的民族语(84.5%),说明粤语不仅功能多样,而且还得到本地青年极高的认可。具体而言,粤语在母语和生活语言这两方面的认可度最高,而最低的为外语, 只有1.4% 的学生认为粤语是他们的(第一)外语。另外,还有51.6%的学生认为粤语是一种方言。
(二)英语:功能层级分化,组际差异明显
英语的工作语言身份和第一外语身份最为明显,分别受到了72.3%和65.3%的学生的认可,而在民族语、国家通用语和方言上认可度最低,均没有超过10%,说明学生对英语的认同呈两极分化。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英语的母语(21.6%)、生活语言(19.7%)和澳门官方语言(18.8%)功能并不十分突出,但也达到了一定的比例,表明英语在大、中学生心中除了是典型的外语和工作语言外,还有上述三种次要功能。同时,大学生组与中学生组在工作语言、生活语言、官方语言、外语这四种语言功能上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差异(相差10个百分点以上):大学生更认同英语的工作性(82.9%)、官方性(25.7%),也更认同其第一外语功能(70.5%),而更多中学生则赞同英语是自己的生活语言(27.8%)。
(三)葡语:功能认定比较单纯
对葡语的认同最明显的是官方语言(58.7%)和第二外语(43.4%),其他方面大都低于10%⑧,说明葡语在大、中学生中功能单一且认同度较低。需要注意的是,葡文与中文在法律意义上同为澳门的官方语言,然而认同粤语(88.7%)是官方语言的学生要远高于认同葡语(58.7%)的。这也进一步佐证了葡语在大、中学生中的认可度不高。
(四)普通话:功能认定多样,但占比均偏低
普通话几乎在所有方面的认可度均达到了两位数,但其所占比例却并不算高,说明它在学生中影响较广但不深刻,体现出普通话在澳门青年中所面临的复杂境地。具体而言,普通话最显著的功能是其国家通用语身份,得到了超过九成学生的认可。其次是它的第二母语(58.5%)和工作语言(46.5%)角色。值得注意的是,有13.8%的学生认为普通话是一门外语,而只有24.4%的人同意普通话是自己的民族语。
(五)讨论
1. 对“四语”认同具体情况的分析
综上所述,澳门本地大、中学生对四种语言在语言认同上的总体特征为:绝大多数澳门青年对粤语的认同度最高,认为粤语既是母语,又是生活语言、工作语言、民族语言和官方语言。而对其他三种语言的认同度较低,且功能明显分化,多数澳门青年认为葡语是官方语言和第二外语,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英语是第一外语。这一情况反映出语言认同在澳门相对复杂的一面,与其“三文四语”的语情是相符合的。
具体来说,澳门青年对英语的认同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尽管普遍认为英语是一门外语,但其工作语言认同也非常突出(72.3%),远高于普通话和葡语,仅比粤语低17.4%。这种实用性还体现在对下一代的语言期望上,有44.3%的人希望自己孩子第一位或第二位要掌握的语言为英语,而做出这一选择的主要原因均为英语“最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四种语言中对普通话的认同是最复杂的。一方面,普通话所有功能的认同占比都超过了10%,表明它在大、中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种影响力并不深刻,只有在国家通用语和第二母语上占据相当的优势。⑨ 另一方面,对普通话认同的复杂性也与大、中学生对它的态度保持一致:调查显示,虽然不少学生对会说普通话感到(非常)高兴(38%)和(非常)自豪(61.5%),但也有17.8%的学生表示对普通话没有感觉,为四种语言中最高。
澳门青年对葡语认同的局面相当微妙。一方面,高达92%的大、中学生认为葡语是一门外语⑩,这一比例在“四语”的外语认同以及葡语自身所有功能中都为最高,同时它在母语和第一外语上的认同却非常低,甚至连第二外语的占比都只有微弱优势,足以说明葡语对于澳门大、中学生来说是一门典型的外语,在心理上处于最为疏远的位置。另一方面,葡文与中文同为法定的官方语言,理论上应该是处于同等地位,然而,大、中学生对它的认同度只有58.7%,远远低于粤语的88.7%。葡语在外语和官方语言上的认同情况能明显反映出它的尴尬境地:至少在大、中学生看来,澳门是在用一门外语来充当官方语言。
2. 几个问题
从语言的功能视角来看,四种语言在工作语言认同方面整体上最高,其他功能上则呈现明显的分化状态。大多数学生将自己的第一母语认同为粤语,第二母语为普通话;在外语认同上,英语是大、中学生作为第一外语的首选,而葡语则在第二外语上表现出一定优势;在生活语言、方言以及民族语和官方语言上,粤语依旧体现了其认同广泛且认同度极高的特点。
只有一半的学生认同粤语是一种方言。按照现行的语言学观点,粤语应该是现代汉语的方言之一。然而澳门青年在方言认同上却表现出一定的分歧。认为粤语是方言的占比在所有的粤语认同中为最低,只有51.6%,同时还有22.4%的学生认为粤语并非方言。我们认为,粤语在方言认同上的这一表现与澳门的特殊现状相关。澳门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的特别行政区地位又明显区别于中国的其他省份。这种双重地位反映到语言上,便为粤语既是汉语的一分子,是汉语的一种方言,又应该要能体现出与特区相对应的独立语言身份,即认为粤语不是一种方言。
绝大部分澳门青年的民族语是粤语而非普通话。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在国际上往往代表中国、代表中华民族。澳门青年虽然也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详见第五节),但普通话却并非其民族语的首选语言,排在第二位(24.4%),与第一位的粤语(84.5%)相差悬殊。这一现象应该是与粤语和普通话在澳门的特殊功能有关。对于澳门本地的大、中学生来说,粤语不仅是典型的生活语言,同时也是主要的教学语言。而普通话是后来才进入港澳地区的,并非本土方言,所以有些学校甚至把普通话当作外语来教,每周只有几节课。在这种氛围下,一般学生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粤语的民族语认同感。
作为法定官方语言的中文,其口语形式是粤语而不是普通话。中文和葡文是澳门的法定官方语文,这一规定是从书面语做出的,它并没有限定口语的官方形式。根据黄翊(2007:164)的研究,澳门通行的书面语称为“语文体”(也有学者称作“澳式中文”,如雷曦(2015)),实质上就是普通话的书面形式,不过掺杂着许多方言、古汉语和外语的成分。因此,理论上中文的口语形式应该是普通话(或是国语)。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大、中学生认同的澳门官方语言最高的为粤语(88.7%)和葡语(58.7%),对普通话(13.6%)的官方语言认同甚至还排在英语(18.8%)之后,处于最末位置。我们认为,这与澳门特殊的语言运用现状有关。由于历史原因,澳门的通行书面语与通行口语一直处于脱节状态:书面语是文言色彩较重、非常正式的“语文体”,而口语则为大众日常使用的粤语。因此,这种言、文不一致的情形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普通民众(包括大、中学生)一般都认为是粤语而非普通话与中文这一官方书面语相对应。
需要指出的是,按照Moody(2008)的调查,澳门的许多官方机构除了使用中文和葡文两种法定官方语言外,一般都会再添加英语辅助对外交流,亦即英语在语言使用上具有半官方语言的地位(de facto and semi-official status)。但是根据我们的调查,这一现实情形想要得到大、中学生的认同暂且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只有不到两成的学生认为英语在澳门是官方语言。
3. 语言认同对语言态度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分析结果,四种语言在澳门青年的母语和外语认同上总体情况是:粤语(第一母语)—普通话(第二母语)—英语(第一外语)—葡语(第二外语)。
我们上文认为,语言认同会影响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一般地,第一语言比第二语言态度上会更积极,母语比外语亲切度更高更友善,亦即其积极态度也会表现得更加明显。根据这一原则,上述四种语言中,大、中学生的语言态度优先次序应该是:粤语>普通话>英语>葡语(“A>B”表示语言态度上A优于B)。我们的这一推论印证了苏金智等(2014)的调查。
苏金智等(2014:53—58,155)曾大范围调查过澳门大、中学生的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认为澳门“三文四语”中“四语”的排序大致上是“粤语>普通话>英语>葡语”,亦即我们的上述推论与苏金智等的调查结果是吻合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普通话在第二母语上的认同度并不是特别明显(58.5%),比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65.3%)的认同度要低,所以二者在语言态度上存在竞争的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的调查报告(阎喜 2014)显示出“四语”的排序是“粤语> 英语>普通话>葡语”。
五、语言认同与澳门青年的
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
(一)澳门青年的地域认同与语言认同
根据调查数据,总体上看,认可澳门人身份的比例(85%)和认可中国人身份的比例(65.3%)都比较高,同时认同澳门人和中国人身份的学生比例也有55.4%,说明澳门的大、中学生对澳门和对祖国的态度均积极向上。尽管如此,76%的学生都非常突出自己的澳门人身份(即澳门身份排第一),只有24% 的人认为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比较显著。
澳门大、中学生在地域认同上的表现与语言认同中的母语认同、民族语认同关系密切。突出自己澳门人身份的学生第一母语是粤语的比例高达96.9%,认为粤语是其民族语的比例占到89.5%,均比认为中国人身份优先的学生的比例(分别为78.4%和68.6%)高出不少。与此相反,突出自己中国人身份的学生则在认同普通话为第二母语(56.9%)和民族语(39.2%)方面比认为澳门人身份排第一位的(分别为37%和20.4%)高很多。这表明,大、中学生的地域认同与其母语和民族语是有关联的:更认可粤语为第一母语和民族语的学生倾向强调其澳门人身份,而更认可普通话为第二母语和民族语的学生则更突出其中国人身份。
(二)澳门青年的文化认同与语言认同
数据显示,中国文化?(34.3%)、澳门本地文化(55.9%)和西方文化(70.9%)在澳门青年中均得到了较高的认可,说明澳门的大、中学生呈现出多元文化认同的态势。而数据上的递增则说明了这三种文化内部又体现出不平衡性。具体而言,大、中学生对西方文化认同的人数最多(分别为64.8%和78.7%),其次是澳门本地文化(分别为61%和50.9%),而中国文化则排在最后(分别为42.9%和25.9%)。同时,大学生组和中学生组又体现出明显差异:大学生上述三种文化的变化幅度显然远远低于中学生。以上分析表明,西方文化对本地青年, 尤其是对中学生更具有影响力。
根据我们的调查,本地青年在文化认同上的表现与母语(第一母语和第二母语)以及生活语言也具有密切的关系。? 认同中国文化的学生,其普通话的母语认同和生活语言认同在三种文化认同中最高,分别是59.5%和18.5%;而认同澳门本地文化的大、中学生,其粤语的母语认同(98.8%)和生活语言认同(97.1%)在三种文化认同中为最高;同样地,认同西方文化的学生的母语认同和生活语言认同在英语上的表现也最为突出,分别为24.5%和20.3%。这表明,澳门青年的文化认同与其相关的语言认同有关联:在中国文化、澳门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认同哪一种文化就预示着与此相应的语言在三种文化中有最高的母语和生活语言的认同度。
六、结 论
以往对语言认同性质的界定,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与语言态度难以清晰切割,纠结之处甚多。本文认为,认同就是进行心理定位,就是在心理上确定自我和他者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语言认同就是指语言使用者就自身与某种语言或方言之间关系的心理定位,而这种定位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如何联系自身来确定某种语言或方言在自己心理上和语言生活中的功能。语言认同度的差异会直接影响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态度和语言行为,语言认同与地域认同、文化认同,乃至国家和民族认同等密切相关。
澳门是一个典型的多语社区,其语言运用情况非常复杂。它不仅拥有标签式的“三文四语”,还有多种少数群体使用的语言或方言。在这个多语社区中,粤语在日常使用方面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地位,其他语言或方言则在特定领域内保持着一定的活力。这种复杂的语言运用状况也影响着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差异。
根据我们对澳门“三文四语”中“四语”的调查,发现本地青年对粤语的认同度最高,而对其他三种语言的认同度较低,且功能明显分化,其中最弱的是葡语,普通话和英语次之。具体而言,粤语和英语分别在第一母语和第一外语上占比最高,第二母语认同最显著的为普通话,而葡语则在第二外语上表现出一定的优势。“四语”在工作语言上普遍都得到了很高的认可,而其生活语言功能则只有粤语比较突出。多数大、中学生都认为粤语和葡语是澳门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也认为粤语是自己的方言和民族语言。这一情况反映出语言认同在澳门相对复杂的一面,与其“三文四语”的现实语情是一致的。
语言认同与地域认同、文化认同具有密切的关联。调查发现,更认可粤语为第一母语和民族语言的澳门本地学生更倾向强调其澳门人身份,而更认可普通话为第二母语和民族语言的学生则更突出其中国人身份。同时,在中国文化、澳门本地文化和西方文化中,认同哪一种文化就预示着与此相应的语言在三种文化中有最高的母语和生活语言的认同度。
本文只是举例性选取澳门大、中学生这一群体作为一个案例讨论澳门人的语言认同问题,主旨在于建立一个研究此类问题的方向和框架,存在的局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希望,将来能在调查对象上扩大覆盖范围,在将多重复杂因素考虑进去的基础上将少年组、中年组、老年组、土生本地人和新移民都包括进去,甚至将澳门人的语言认同跟其他地区人士的语言认同进行比较,同时进一步改进统计手段和统计方法,以期最终将此问题的讨论提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注 释
① 确实有很多文献都谈论过“language indentity”,如Jenkins(2007)、Edward(2009)等,但他们谈论的都是“语言与认同”,与我们这里的“语言认同”(linguistic identity)并不是一回事。
② 语言意识(language awareness)指对语言本体特征的认知(微观层面)或者对语言所承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认知(宏观层面)(Kroskrity et al. 2000:5)。
③ 或者说此二者存在大部分的重叠:根据定义,语言态度的知识对应语言认同中的语言意识以及语言态度的理性部分,语言态度的评价则对应语言认同中语言态度的情感内容。还有的学者甚至对语言态度和语言意识的界定也大致相同,比如杨荣华(2010)将语言意识视作“语言本体特征的认知和对其情感、功能方面的评价”,而其语言态度的内容则是“情感、认知和功能上的评价”。
④ 理论上,粤语是汉语的方言之一,因此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与作为一种语言概念的英语、葡语并列的。为简便起见,本文不做语言和方言的区分。
⑤ 资料来源为《2011人口普查详细结果》(澳门统计暨普查局 2012),http://www.dsec.gov.mo/Statistic.aspx?NodeGuid=8d4d5779-c0d3-42f0-ae71-8b747bdc8d88。
⑥ 数据转引自圣公会澳门社会服务处的《“澳门青年研究回顾及发展2013”报告》(2014:3),http://portal.dsej.gov.mo/webdsejspace/internet/Inter_main_page.jsp?id=8493。
⑦ 受限于调查的可行性,本文没有考虑学业完成后就业的青年这个群体。
⑧ 尽管有32.4%的学生认同葡语是工作语言,但这一数据还是远低于其他三种语言。
⑨ 普通话的工作语言认同虽然达到46.5%,但跟粤语和英语相比,还是落后许多,可以看作是不明显的。
⑩ 这里的“外语”指在调查问卷所给选项中认为是外语的语言,与“第一/第二外语”中的“外语”(在调查对象已掌握的语言中认为是外语的语言)不同。
? 出于学术讨论目的,本文的“中国文化”指不包括澳门的中国大陆文化,以便于与“澳门本地文化”进行对照。
? 然而,澳门青年的语言认同并不是与其文化认同呈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即澳门青年最认同的文化(西方文化)并不与认可最广泛、认同度最高的语言(粤语)相对,而是呈现如文中所述的面貌。至于为何表现出这样一种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程祥徽 2005 《中文变迁在澳门》,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
黄 翊 2007 《澳门语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黄 翊、龙裕琛、邵朝阳 1998 《澳门:语言博物馆》,香港:香港和平图书·海峰出版社。
姜 瑾 2006 《语言·社会·生态:社会语言学动态应用研究》,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雷 曦 2015 《澳门中文与大陆中文的语法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刘羡冰 1995 《双语精英与文化交流》,澳门:澳门基金会。
苏金智、朴美玉、王 立、谢俊英、陈 茜、刘明建、郭龙生、张瀛月 2014 《澳门普通话使用情况调查》,澳门:澳门理工学院出版社。
孙德平 2011 《语言认同与语言变化:江汉油田语言调查》,《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王 玲 2009 《言语社区内的语言认同与语言使用——以厦门、南京、阜阳三个“言语社区”为例》,《南京社会科学》第2期。
韦 达 2002 《壮话与白、客、闽话的共同特征及其文化意蕴》,《云南民族学院学报》第6期。
阎 喜 2014 《澳门大学生语言态度研究》,《澳门语言学刊》第1期。
杨荣华 2010 《语言认同与方言濒危:以辰州话方言岛为例》,《语言科学》第4期。
张 军 2008 《蒙元时期语言认同建构之经历与经验》,《新疆社会科学》第1期。
张媛媛 2015 《语言景观中的澳门多语状况》,“第六届东亚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5月17—19日),澳门大学。
周明朗 2014 《语言认同与华语传承语教育》,《华文教学与研究》第1期。
邹嘉彦、游汝杰 2001 《汉语与华人社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Agheyisi, R. and J. A. Fishman. 1970. Language Attitude Studies: A Brief Survey of Methodological Approache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12(5), 137-157.
Bucholtz, Mary and Kira Hall. 2005.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 A Sociocultural Linguistic Approach. Discourse Studies 7(4-5), 585-614.
Crystal, D. 2008.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 and Phonetics (Sixth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Edward, J. 2009. Language and Identities: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nkins, J. 2007.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Attitude and Identit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roskrity, P. V., B. B. Schieffelin, and K. A. Woolard. 2000. Regimes of Language: Ideologies, Politics, and Identities. Santa Fe, New Mexico: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Press.
Moody, A. 2008. Macau English: Status, Functions and Forms. English Today 24(3), 3-15.
Yan, X. and A. Moody. 2010.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Macao: A Review of Sociolinguistic Studies on Macao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Chinese Language & Discourse 1(2), 293-324.
Zhou Minglang. 2012. Language Identity as a Process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Chan, W. M., K. N. Chin, S. K. Bhatt, and I. Walker (eds.), Perspectives o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Boston/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55-272.
责任编辑:王丽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