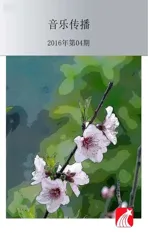中国流行歌曲中的性别隐喻与“错位”
2016-04-03肖婵
■肖婵
(广西艺术学院,南宁,530022)
中国流行歌曲中的性别隐喻与“错位”
■肖婵
(广西艺术学院,南宁,530022)
中国流行歌曲作品在表现内容、表演者、声音与音乐风格等方面皆表现出了性别隐喻,且这三者之间有时会形成性别的“错位”,这种“错位”意味着在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当代流行音乐界的性别文化已开始慢慢被人们重新建构。
流行歌曲 性别隐喻 社会性别 心理性别 生理性别
中国近现代流行音乐发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当时,西方人带来的流行音乐开始传入中国。1927年,黎锦晖创作了我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还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歌舞剧团“中华歌舞团”——从剧团演职人员的分工中可以看出,唱歌表演的主要为女性,乐器伴奏以及作曲为男性,这和中国古代音乐传统中的分工情况一样,似乎已形成了一种社会性别的标签。这或许是因为受众主要为男性,在传统观念上,他们习惯将歌女视作尤物来欣赏。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女性受众越来越多(女性也可以主动欣赏男性,但在言语和举动上依旧需要保持庄重),男歌手也开始出现,改变了以往歌坛的社会性别形态。现今,男女歌手比例持衡,歌手不再只是女性的社会标签了,而词曲作者的男女比例依旧严重失衡。
笔者通过分析作品表现内容、表演者以及声音/音乐风格的历史演变,以及三者之间的“错位”关系来探讨流行歌曲具有的性别特征。其中,主要是对黎明晖、周璇、李香兰、邓丽君、罗琦、李宇春、周笔畅等各个阶段较有代表性的创作者/表演者的相关情况做了观察梳理,通过“点—线—面”式的勾勒,建立起对研究对象的认识。
一、作品的表现内容的性别隐喻
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体现了女性的初步解放意识,不再只是被动者。从《毛毛雨》的“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哎哟哟!你的心”及《桃花江》的“(男唱)我也不爱瘦那我也不爱肥,(女唱)我要爱一位像你这样美,(男唱)哎哟不瘦也不肥百年成匹配,(女唱)好桃花江是美人窝,你不爱旁人就只爱了我,(男唱)好桃花江是美人窝,比那旁人美得多”等歌词中,体现了当时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上有了自由选择意识,同时也可以看出男女青年在选择配偶时的侧重点——“不要金不要银只要心”体现了女性对男性内在精神的注重,而“不爱瘦不爱肥只爱这样的美”则体现了男性注重的是外貌特征,忽略了女性的精神品质。《毛毛雨》的“雨息风停你要来”、“心难耐等等也不来”等词中,体现了女性主动无怨无悔等待的思想,这也正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社会性别的塑造。
20世纪20、30年代,歌词的表达通常较为优美含蓄,此时期,民间小调歌曲被周璇首先带上舞台,如湖南民歌《采槟榔》、东北民歌《对花》和安徽民歌《凤阳花鼓》等。此后,歌词有引用古诗词之风,更加具有古韵,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70、80年代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歌星演唱的歌曲,如《但愿人长久》、《独上西楼》、《在水一方》等等。但从其内容隐喻的社会性别上来看,并没有太多改变。纵观我国流行歌曲历史,大多数歌曲都不外乎如此,并在无形中形成了一种社会性别规范,流传和影响着一代代人。
受西方摇滚乐的影响,国内在1987年刮起一阵“西北风”,歌词具有深刻的反思、回归情绪及现实批判意味,以民间的审美情趣重新体味处于剧烈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现实生活。①参见黄燎原等编著《十年:1986~1996中国流行音乐记事》,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被称为“中国摇滚乐之父”的崔健的《一无所有》的歌词“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表面上看似情歌,实质上具有其深层的文化内涵。但即便从情歌的角度出发来看,歌词也没有了以往常见的那种纸醉金迷式的浮沉感。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出现了第一批女性摇滚歌手——以“眼镜蛇”乐队与“指南针”乐队为代表,摇滚的反叛精神在我国女性身上得到体现。指南针乐队的主唱罗琦在1994年发表了专辑《选择坚强》,其中同名歌曲的歌词“选择坚强,我不想再倒下,赤裸灵魂,我已经没有害怕”,已经摆脱了女性的阴柔气质,具有一种男性的阳刚之气。
2005年,热门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中参赛者的翻唱歌曲很多都是具有男性特质的歌曲,如李宇春翻唱张宇的《大女人》,周笔畅翻唱陶喆的《你爱我还是他》、《普通朋友》等。
二、表演者的性别意识
《毛毛雨》由黎锦晖的女儿黎明晖首唱。“20年代上海妇女的发型,大都是发簪加刘海,穿着一般为旗袍或长裙,而黎明晖却是短发短衣又短裙,并且爱好游泳、驾车和骑马。遗老遗少认为这是伤风败俗,而具有新思想的青年观众则把她当作崇拜的偶像。”②赵士荟《中国第一位女歌星黎明晖》,载《世纪》1996年第5期,第28页。在此之前,留短发以及游泳、驾车和骑马等活动一向都是男性的社会标志,由此可以看出,黎明晖突破了传统社会女性的形象。但在舞台表演上,黎明晖浓妆艳抹、短衣短袖等特质依旧还是由男性来决定的。此后的周璇、李香兰再到后来的邓丽君等的形象,仍然是主要由父权决定的。
之后,摇滚歌手罗琦一身黑皮衣、文身、嘴唇穿钉的打扮,打破了传统的女子温柔贤惠的刻板形象。另,自“超女”李宇春、周笔畅以及“快男”刘著以来,中性风格开始盛行。李宇春一头清爽富有朝气的短发搭配衬衣牛仔裤,让人难以想象其生理性别为女性;而相对地,长发飘飘的刘著穿上短裙、丝袜与高跟鞋,也让不明情况的人难以相信其生理性别为男性。
三、声音与音乐风格的性别特质
《毛毛雨》是以民间旋律配上西洋节奏的作品,具有典型的民间小调特质,在唱法上,也是传统的民族唱法,嗓音直白、尖而细。20世纪30年代,受周璇风格的影响,女性歌手的嗓音通常甜美圆润、轻柔曼妙。50、60年代起,受李香兰的影响,歌手们在演唱方法与技巧上学习西洋。邓丽君则融合了中国、日本与西洋的唱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声唱法”,声音依旧是甜美婉转。
“西北风”类型的流行歌曲总体特点是一反之前流行歌曲的特色,以陕西、甘肃等地的民歌素材为基本音乐语素,旋律昂扬,演唱风格刚劲豪迈。③同①。女性歌手遇上西北摇滚乐后,嗓音变得铿锵有力,甚至带着嘶吼。而李宇春的歌声清新平淡,周笔畅喜欢唱R&B风格的歌曲,在音色上比较偏男性。在近年的《中国好声音》中,女歌手林燕用粗粝狂野的男声演唱了黑豹乐队的摇滚歌曲《别来纠缠我》,而男性歌手童予硕却以非常妩媚的声音和慵懒的爵士乐风格翻唱杨宗纬的《对爱渴望》。
四、各要素之间的性别“错位”
性别并不是理所当然存在的,而是被人们赋予的,可以被重新建构与改造。按照传统的二分法则,人们将性别(不管是生理性别、心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简单地划分为男性和女性,并根据生理性别建构了社会性别——这就像一种约定俗成,如果谁破坏了条约,就会被认为是“不正常”。而纵观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则可见歌词、表演者以及声音与音乐风格之间有时会形成某种“异常”的性别“错位”。
(一)作品表现内容与表演者性别的“错位”
如今翻唱已成风,一些早期的歌曲早已被翻唱无数次,其中那些具有性别隐喻的歌,有两种歌词处理方式:一种是微改歌词,使歌词性别变得中性或与歌者性别统一;另一种是不改动歌词,使其在心理性别或社会性别上具有异性的特征。
如歌曲《烛光里的妈妈》,原唱歌手的性别与歌词“妈妈呀,女儿已长大,不愿牵着您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噢妈妈相信我,女儿自有女儿的报答”所表达的一致。当男歌手姜育恒翻唱此歌时,将歌词改成了“妈妈呀,孩儿已长大,不愿牵着你的衣襟,走过春秋冬夏”,巧妙地将原词的女性视角,改成了中性。同时代由崔健创作演唱的《花房姑娘》更具性别特征——“你带我走进你的花房,我无法逃脱花的迷香,我不知不觉忘记了,噢……方向,你说我世上最坚强,我说你世上最善良。”按照传统的思维观念不难看出,“我”是男性,“你”是女性,“花房”、“花”及“善良”通常是女性的社会性别符号,“坚强”是男性的社会性别符号。当女歌手程璧翻唱此歌时,将“你”“我”对换——“我带你走进我的花房,你无法逃脱花的迷香,你不知不觉忘记了,噢……方向,我说你世上最坚强,你说我世上最善良。”此时的“我”是女性,“你”是男性,歌词微改后,其视角依旧与表演者的性别一致。由此可以看出,微改歌词后,便没有形成性别错位。
有些表演者并没有改变原有的歌词,而形成了一种跨性别的演绎。同样是女歌手翻唱《花房姑娘》,魏语诺在《我是歌手》舞台上的表演并没有改变歌词;李宇春、周笔畅等人也在舞台上表演过跨性别的演唱。此类现象让人可产生五种设想:一是表演者在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上皆为女性,但在表演此歌时临时站在男性的角度上歌唱;二是表演者具有男性社会性别特质,同时也爱慕女性;三是表演者具有男性社会性别特质,爱慕具有女性社会性别特质的男子;四是表演者自我认同的心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男性,不仅在心理上以男性社会性别为标准,而且在穿着打扮上也以男性社会性别为标准;五是表演者的自我心理性别认同为女性,社会性别为男性,以男性的标准穿着打扮(也就是所谓的“异装癖”),在舞台上理所当然地扮演男性。
除了这些翻唱歌曲之外,在原唱歌曲当中亦有性别“错位”的现象。如“二手玫瑰”乐队的《征婚启事》:“那天我心情实在不高兴啊!找了个大师我算了一卦,他说我的婚姻只有三年长啊!我那颗爱她的心有点慌啊……我做个艺术家,我娶个艺术家,我嫁个艺术家,我毁你个艺术家……这时我惊奇地发现我是否怀孕了……”而在表演上,乐队的男歌手经常穿着女性服装,甚至头戴大红花,将自己的装扮过分突出女性化——①参见陆正兰著《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201页。“雌雄同体”,性别完全“错乱”。
(二)声音、音乐风格与表演者的“错位”
从音乐风格上来讲,摇滚乐是最具有性别特征的。“摇滚本身几乎和战争同样,都带着明显的男性荷尔蒙倾向,正是这个特征,使摇滚和战争一样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一样具有男性思考模式的传统,而这些几乎都和传统女性所具有的一切特征相悖离。”②季德方《论当代中国摇滚歌词的文化维度》,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31页。可见,人们通常认为,摇滚是属于男性的,女性“玩摇滚”就会与传统女性特征相背离——所以,当年“眼镜蛇”乐队与“指南针”乐队的出道,表现出了风格与性别的“错位”。
在声音方面,中国传统女性的嗓音直白、尖细或圆润、甜美,这是中国女性社会性别的符号。摇滚乐出现后,中国女性的声音中也出现了粗犷、铿锵有力,甚至有些嘶吼的特征,极具男性社会性别特征;相反,男性的嗓音由浑厚、粗犷、铿锵有力,逐渐走向“尖细腻”。这种情况在选秀节目上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是一种个性的追求与展现,由此形成了性别“错位”,而观众也愿意为这种“错位”买单,然后此种现象不断循环,直至愈演愈烈。
(三)声音、音乐风格与作品表现内容的“错位”
1995年,“唐朝”、“黑豹”、“1989”、“轮回”四支摇滚乐队以及郑钧、臧天朔等摇滚歌手一起为纪念邓丽君而发表了翻唱专辑《告别的摇滚》。歌手们用西北摇滚风翻唱了包括《在水一方》、《船歌》、《再见!我的爱人》等在内的十首邓丽君原唱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内容表达的都是一些“小情小爱”,适合采用中国民间小调、爵士、拉丁等曲风,但在此专辑中,歌手们用西北摇滚风重新演绎,摇滚的批判反思精神与“小情小爱”形成“错位”;在声音上,阳刚粗粝的男性嗓音与阴柔细腻的女性嗓音形成“错乱”。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作品表现内容、表演者和声音/音乐风格的历史演变,以及三者之间的“错位”关系来探讨了流行歌曲具有的性别特征。从中可以看出,男女性别看似“错位”了,实质上是性别二元对立论似已经无法立足于社会。人非生来就有社会性别,而是后天形成的。在文化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性别文化开始慢慢被人们重新建构,这也体现在了流行音乐世界中。
(责任编辑:韦 杰)
肖婵,广西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为音乐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