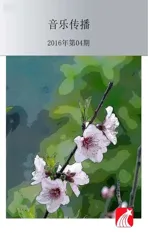《声无哀乐论》的典型命题及其音乐社会学意义
2016-04-03刘元平
■刘元平
(韩山师范学院,潮州,521041)
《声无哀乐论》的典型命题及其音乐社会学意义
■刘元平
(韩山师范学院,潮州,521041)
作为音乐思想家的嵇康,在全面遵从名教礼法的时代,推尚道家自然,倡导玄学新风,以《声无哀乐论》尝试探讨音乐的本质、“声”与“情”的关系、人听赏音乐时情感的由来等问题,并从社会政治环境的视角出发,将音乐分为抽象的“至乐”和具体的“音声”,由此阐发了他那附着有强烈的政治理想色彩和社会文化建设意味的音乐观。嵇康的音乐观与汉斯立克的相近,与儒家的则针锋相对且存在概念定义上的不一致,但无论如何也可以为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当今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的责任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嵇康 古代音乐思想 音乐情感 音乐接受 至乐 音声
嵇康①嵇康(公元224—263年,一说223—262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是三国曹魏时著名的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他工于诗文,其作品风格清峻。他也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身上集合了政治人物、文化人物等多重属性,后世学者对他的解读也逐渐趋于多元化。是三国魏末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竹林七贤”的领衔人物。他幼年丧父,励志勤学成才,娶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女)长乐亭主为妻,是曹魏宗室的女婿。曹氏当权之时,他曾做过中散大夫(七品文官),因此世称嵇中散。后来家道中落,常与向秀以打铁谋生。司马昭掌权后,提倡“人伦有理、朝廷有法”,他却推尚道家“自然”,反儒反政,桀骜不驯,坚持不苟合于统治者的言论,并率另外六位名士栖居竹林,弹琴咏诗,酣歌纵酒,自得其乐,且轻肆直言,抨击虚伪的礼法与趋炎附势之士,“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因此遭杀身之祸,享年四十岁。
一、嵇康“乐论”的思想基础
才性和独立,是汉魏之际仁人志士普遍的精神追求。“才”即外在才能,“性”即内在性情,于是“才性之学”成为一种名理之学,直接影响了魏晋玄学。正始末年,“竹林名士”在栖居中清谈,正是共倡玄学新风的举动。“清谈”原是“清议、谈辩、雅谈、正论”的意思,来源于先秦以来的“谈辩”风气和东汉的“清议”。魏晋时期,社会上盛行“清谈”之风:士族名流相遇,不谈国事、民事、家事、俗事,专谈老庄、周易,寻找“玄”的道理,被称为“清言”。而“玄学”即玄虚之学,以抽象的“无”作为思想核心,强调“以无为本”,认为万事万物皆产生于“无”,在现实世界以外自然有一个纯粹抽象的“玄”的世界。简言之,清谈玄学就是以清谈的方式畅谈以老庄、周易为核心的特殊思想。
嵇康从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出发,提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认为万物皆禀受元气而生。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一个人应该不受清规戒律的约束和褒贬赞辱的羁绊,按其本性,顺乎自然,这样就可以“心无措乎是非”。
而在个人与宇宙的关系上,嵇康认为物情顺通,大道无为,主张“审贵贱而通物情”、“情不系于所欲”,即不拘泥于世间利欲,这仍是顺应本性、超脱自然的用意。这种不尊圣贤、不按儒教、毁弃礼法、恣意而为的思想,以及遁世逍遥、借酒浇愁、酒后狂言的行径,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典型的文人志士那种强烈的反儒、反政思想。
同时,嵇康也是一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见解的音乐家。音乐对他来说不仅是提升“才性”的手段,还是隐世避俗、寻求寄托的途径。他也正是在清谈玄学、反儒反政思想的基础上,撰写理论著作《琴赋》的。他阐述音乐之功用说:“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他也是一个古琴演奏家,如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在创作上有琴曲《嵇氏四弄》,即“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与蔡邕所作的“蔡氏五弄”被合称“九弄”。他临刑前从容不迫,索琴而抚《广陵散》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
他的《声无哀乐论》则是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自律论音乐美学文献。鲁迅曾有这样的评价:“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①《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1页。这个评价不仅肯定了嵇康的学术观点和政治立场,也概括了嵇康锋芒外现、桀骜不驯的鲜明个性,可以说相当精辟。
二、《声无哀乐论》中的命题与音乐社会学视点
《声无哀乐论》设立两个论辩主体“秦客”和“东野主人”,以对话、答难的方式阐述其理论观点。文中的“秦客”其实代表儒家礼教思想,而“东野主人”则是嵇康自己的化身,代表着道家和玄学思想。通过八次答难,文章不仅充分讨论了“声无哀乐”这一形式自律论的元命题,还就一些相关问题做了美学或社会学视角的思考。
(一)乐的本质
嵇康接受和延续老子的音乐思想,认为音乐的本质是“音声有自然之和,而无系于人情”,指出音乐不能表现具体的情感,也不涉伦理,要求音乐以平和为体。“和”是“有声”和“无声”的对立与统一,即“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音声相和”。“无”才是天下之“道”、万物之本。
这种“和”的观念使得他把音乐与政治密切关联起来,作为他音乐观点的核心立场。他指出音乐是客观存在着的音响,是一连串运动着的纯粹声音的组合,音乐的意义在于自身,所以“声无哀乐”。他进一步明确“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者“殊涂异轨,不相经纬”。他认为心之哀乐是人的情感范畴和一种主观宣泄,音乐只是乐音的运动形式,所以其本身并不传示什么感情。二者彼此外在,但又各自独立。
“万殊之声”、“音声无常”,是说相同的情感可以发出或表现为万般不同的声音,同一种声音也可表达不同的情感,二者于是没有固定匹配、对应的可能。于是,哀乐非音声之哀乐,音声非哀乐之音声。由此,嵇康指出音乐与情感是“名”与“号”的关系:“因事与名,物有其号……玉帛非礼敬之实,歌哭非哀乐之主也!”哀乐是人的情感反应,体现的是内心本身;歌哭是外显形式,只是“名号”标识,并不代表人内心的哀乐。因为哭未必是哀,歌未必是乐,所以“歌哭”者并非“哀乐”本身,哀乐之名未必音声之实,这就是为何“歌哭”之声与“哀乐”之情并无恒常的对应关系。
(二)“声”与“情”的关系
嵇康认为“和”是音乐的本质,主要体现为音声形态和运行特征,即“大小、单复、高埤、猛静、舒疾”等,除此之外,它本身不具有思想、道德和哀乐之情。但是,嵇康也指出,“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也就是说,“乐”虽无“情”,但它作为媒介可以诱导和引发人的哀乐之情。理解嵇康这一思想的关键在于,情绪和情感在他看来并非一回事。他指出听者对音乐的反应仅限于“躁静”、“专散”,即音乐只能使人感觉兴奋或恬静,让人精力集中或分散。很明显,“躁静”、“专散”是人的情绪特征,而非情感。情绪体现为生理上短暂的态度体验,情感体现为心理上持续的态度体验。关于情绪和情感的关系,通常认为情绪往往是情感的先兆,而情感是情绪的后续。人在某种外界作用的刺激下,先是发生情绪反应,然后才可能通过引发情感动机并借助联感、想象而产生具体的情感。嵇康说“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这里所谓“俟”(意为“等待”)应该是指潜藏于内的情感动机,因有了音声,感应而生发情感。他在文中举例:人在“会宾盈堂,酒酣奏琴”之际会出现“或忻然而欢,或惨尔而泣”的情形。显然,“忻然而欢”属情绪范畴,“惨尔而泣”属情感范畴。所以,我们应该对嵇康乐论中的情绪与情感做好理论界定和分辨,不要把“躁静”、“专散”以及“忻然而欢”所带来的冲动误认为是情感。
(三)“情”从何来
音乐是被感之物,人是主体的存在,这就是嵇康说的“乐之为体,以心为主”。他也对哀、乐做了界定——“哭谓之哀,歌谓之乐”。音乐本无哀乐之分,那么哀乐之心究竟从何而来呢?首先,各人有不同的情感经历和生命诉求,当音乐触动人的情绪引发情感动机后,人就会在自我的世界中产生一连串的情感联想与伸展。嵇康一再强调,“和声无象”但“哀心有主”。“哀心”在嵇康乐论中就是指人的情感。人的情感在听乐主体的世界里独立地发生和伸展,纯属主观意识。嵇康对此的阐述是“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惟哀而已,岂复知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哉?”虽然“和声”本身无所谓哀乐,但它具有情感的诱导和催化作用,音乐作为媒介,发挥了诱导、引发情感的作用。这就是听乐时的情感发生机制。
关于听乐中产生的“哀乐之心”即情感的内容,嵇康说“哀乐自以事会,先遘(相遇)于心,但因和声以自显发”。他所说的“事”,缘自人所生存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人情不同,各师其解,则发其所怀”。每个人对社会现实的态度和情感反应不同,所以音乐引发的情感也因人而异。这种将音乐中的情感归结为“政治现实环境”的做法的唯一结果,是忽视了人在听乐过程中个人的性格取向、文化养成及其生命情感等因素对情感构成的影响。这种疏失,可能与嵇康放旷不羁、纵意所如的“竹林”精神,以及他不尊圣贤、对抗朝廷的思想密切关联,同时也是我们必须体察的。
(四)“至乐”与“音声”
嵇康从社会政治环境的视角出发,将音乐分为抽象的“至乐”和具体的“音声”。
至乐嵇康认为凡和于心者则为“至乐”,其本性具有“和”的内涵,即“至和”、“太和”。嵇康说音虽“无变于昔”,但“以平和为体”。他强调“和必足于内,和气见于外”,即人的内心之情志与外发之和气符合自然之理,两者相协应、一致。当这一切都“和”了,人所感受到的音乐也就是“和”的,所以“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音乐才能“感人之最深者也”。可以说,嵇康是为了同儒家学说截然对立,才将合乎道的“无声之乐”奉为“至乐”的。他认为,音乐无论怎样感人,也不会对人的习性产生改变作用,即“至八音会谐,人之所说,亦总谓之乐,然风俗移易,本不在此也”,这体现了他的玄学思考与追求。
在嵇康看来,政治环境、哀乐之情和“至乐”三者的统一与一致,是体现宇宙之“和”的重要标志。一方面,良好的政治环境促就人心之和,人心“和”了,乐也就变“和”了。他认为,只有古代理想社会才存在至乐,如古代的“咸池”、“六茎”、“大章”、“韶”、“夏”等,都是“先王之至乐”,这是因为在他眼中上古之世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百姓和睦,风俗纯朴,人民幸福,一切都体现着“和”的标准。另一方面,凡“至乐”者能使人生发“和”的情感,这种情感可以“动天地感鬼神”,可以诱使整个社会关系和谐统一,政治环境趋向“至和”或“太和”。嵇康关于“和”的这些理论,不仅体现了他对乐之“和”的观点,还体现了他对社会、政治乃至生存环境的终极关怀。
音声凡当世之乐,嵇康均认为属于“音声”。嵇康认为他生活的时代的一切都不具有“和”的标准。如果统治残暴,政局混乱,社会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听到的只能是混杂着甚至充满着浊气的“音声”。嵇康特别强调,音乐中缺失“和”的根源和关键,其实不在于音乐本身,而在于政治环境。他认为,那些被称为“淫邪”的音乐,必然是“上失其道,国丧其纪”即统治风气不良的结果,所以只有改良政治,让国家安泰,民心和谐,让社会处于和的状态,才能产生“和”的音乐。据此,他强烈批判那种本末倒置、不顾政治环境这一根本因素、将音乐作为孤立的存在、随便给音乐加上“乱世之音”或“亡国之音”罪名的,所谓“儒家正统”的主流音乐思想。
嵇康也批评民间音乐,这倒不全是此类音乐被“儒家正统”定性为“淫邪”之故,而是因为此类音乐确有不与社会现实相一致的因素。他虽然并不主张对民间音乐予以强行禁止,但也认为对这些音乐必须加以控制或矫正,所谓“具其八音,不渎其声,绝其大和,不穷其变,损窈窕之声,使乐而不淫”。这就是说,民间音乐因为不尽符合社会现实而必须进行改良。他觉得既然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如此残酷恶劣,如此限制人的自由,就不可能会有真正美妙而且使人向“和”的音乐,所以必须对那些看似美妙的声音加以修改,让它们更好地反映真正的现实,即便是蕴含愉悦快乐的音乐,也绝不能让人感到有放纵之意。
三、余论
嵇康的音乐思想附着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立场,他对音乐的看法充满了“阶级意识”和“阶级标准”。《声无哀乐论》这篇“玄学”乐论在将矛头指向儒家“礼乐治天下”的功利主义音乐观,并探索音乐本质及其社会环境、情感内容的同时,是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和反叛精神的,也深远地影响了后世不少学者。例如《世说新语·文学》载:“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南齐书》载王僧虔《诫子书》云:“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晋书·嵇康传》末云:“复作《声无哀乐论》,甚有条理。”这些是对嵇康的“声无哀乐”逻辑观点的肯定,此外当然也不乏批判的声音。例如明代黄道周作《声无哀乐辩》,对“声无哀乐”提出疑问。①孙永岷《论嵇康“声无哀乐”的哲学美学思想》,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无论如何,《声无哀乐论》与一千多年后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虽处在不同的民族地域和文化时空,但思考的是同一个问题,他们在对音乐形式这一根本性问题的讨论上,以及音乐形式论美学的确立上,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嵇康与汉斯立克的相通之处,是都主张音乐的意义和美在于乐音运动的形式自身:嵇康认为音乐的本质是自然之和,其本身不具情感,只显于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大小、单复、高埤、猛静、舒疾”,是与人的情感无关,特别是与当下的社会风尚、政治现实无关的声音自然之和;汉斯立克认为音乐的内容只是乐音运动的形式,音乐的美在于形式自身,人们通过其“幻想力”而产生的情感无关音乐本身,应该视为病灶加以驱除。他们二人的区别则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对音乐“形式—自律论”的认识上,立论的角度和哲学基础不同,嵇康不仅有学术性还有突出的现实针对性,而汉斯立克仅立于纯粹的学术角度;二是在音乐与情感的关系问题上,嵇康认为音乐是“无常”的,即具有非确定性的,认为音乐虽能引发人的情感但其内容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的,汉斯立克则认为音乐使人产生生理快感和审美情感,这种反应机制统归于人的“幻想力”。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嵇康的“声”与儒家思想中的“声”在概念上不尽一致。儒家传统乐论《礼记·乐记》中有一段广为音乐学界所知的话:“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里,可以看出“声”、“音”、“乐”是三个不同的概念,处于不同的层次。在儒家思想看来,音乐的产生,包含了由自然的“声”到审美的“音”的转化过程。当代美学家叶朗先生从美学角度就《乐记》中的“声”、“音”、“乐”做过这样的阐述:“不是任何情感的表现都是音乐。你激动了,大喊大叫。你悲痛了,大哭一场。这是‘声’,是自然之声,并不是艺术,不能给人美感,别人不会来欣赏你大哭大叫。‘声’必须有节奏的变化,要合乎旋律,要和谐,才能成为审美的对象,才叫做‘音’。所以说‘声成文,谓之音’。‘成文’就是合乎形式美的规律。这种审美的‘音’,加以舞蹈动作的表演,就成为‘乐’。”②叶朗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4-155页。而嵇康《声无哀乐论》中的“声”,诸如“声无哀乐”、“心之与声”、“音声无常”等语中的“声”并非指自然万物之声,而是指作为人的情感意识表达的“乐”。
(责任编辑:魏晓凡)
刘元平,广东韩山师范学院音乐学系主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音乐美学、音乐史、音乐人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