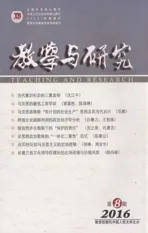规范性外交框架下的“保护的责任”
2016-02-04贺之杲巩潇泫
贺之杲,巩潇泫
规范性外交框架下的“保护的责任”
贺之杲,巩潇泫
规范性外交;“保护的责任”;欧盟;美国;新兴国家
保护的责任作为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中逐渐达成共识。在全球各行为体开始关注规范性外交的背景下,“保护的责任”被纳入到规范性外交框架中,规范性外交主体由此获得相关话语权,进而影响其他国际行为体,实现其目标。规范性外交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国际行为体为实现其规范目标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其二是国际行为体为实现其外交目标而进行的规范性外交。通过梳理“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显示出该规范已经在国际社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接受与认可。考虑到规范主导国家的地位作用,国际社会主要力量对“保护的责任”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这就为各行为体将“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纳入到规范性外交的框架提供了可能性。在规范性外交框架下,主要全球行为体,包括欧盟、美国及新兴国家群体,对“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的理解与实践也在影响着这一规范本身的发展。
国际体系中人权与主权的内在冲突是国际关系中首当其冲的问题。考虑到全球相互依赖与不稳定的态势,维护国际社会责任与国家主权平衡的需要,“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被提出并试图调和传统主权概念(排他性与至高性)与保护本国居民责任之间的关系。“保护的责任”作为均衡人道主义干涉与维护主权完整的新规范,已经被国际共同体部分内化。尽管在不同行为体的内化程度不一致,但国际社会主要力量*国际社会主要力量指的是大国,在笔者看来,大国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既包括内部的物质能力及目标追求,也涉及外部对其的期望与恐惧。也就是说,大国既是全球秩序的产物,也是施动者塑造的结果。详见巴里·布赞:《美国和诸大国:21世纪的世界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已接受这一规范,并将其纳入到它们的外交政策中。这也为“保护的责任”纳入到规范性外交框架打开了机会之窗,一方面各行为体利用规范性外交来充实与改进“保护的责任”内涵和实践,另一方面各行为体利用“保护的责任”来获得国际规范的话语权。
国际规范的更替与发展的动力来源,一是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二是来自国际行为体的努力。对于国际规范生命周期的研究已诸多*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887-917; Thomas Risse, Stephen C. Ropp and Kathryn Sikkink, The Power of Human Rights: International Norms and Domes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但是对于主要国际行为体对规范的态度及政策研究并不多*陈拯,朱宇轩:《中国政府与“保护的责任”辩论:基于安理会相关辩论发言的分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曾向红,霍杰:《西方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选择性适用:影响因素与案例分析》,《欧洲研究》,2014年第5期,第14-32页。该类研究仅限于单一类型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及影响,并未从主要大国规范性外交框架下来解读。。“保护的责任”的规范背景因其塑造行动的利益而得到重视。但是不同的视角有不同解读,比如说现实主义认为是基于地缘战略或政治利益而行动,自由主义认为是基于经济或贸易优势来引导其行动,康德的视角是强调促进民主与自由价值是行动的动力。人道主义行为作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源自多种原因的加总。国家往往利用正当理由去掩盖自我利益诉求的动机,正当理由是“国家联结行动的合理公正标准与可接受行为的尝试”,[1](P4)正当理由往往与动机合并,但两者并非一致。“保护的责任”包含着一种道义诉求,不管是源自何种动机。国际行为体既强调为本国民众负责的主要责任,也关注其他生活在风险中民众的次要责任。本文强调主要国际行为体在“保护的责任”规范发展中的作用,即在规范性外交框架下如何内化与发展“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
一、规范变迁与“保护的责任”的发展
规范是指“行为体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1](P4)按照规范的生命周期理论[2](P887-917)理解,规范发展处于一个生命发展周期,从规范产生到规范扩散再到规范内化,不同的机制(强制、理性计算、社会化、劝说等)[3]与行为体(比如规范倡导国、规范主导国、规范追随国等)[4]在规范发展阶段也不尽相同。“保护的责任”由一个概念演变为一个国际规范,同时内涵得到不断丰富的过程,正是一个规范演进过程的体现。在规范演进过程中,一种规范在国际社会中逐渐达成共识,虽然被视为国际社会接受的稳固政治规范,但对这一规范的理解和解释仍处于变动中。这是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对于“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认同—干涉实践”话语逻辑[5]的不同理解,也涉及对于规范具体性、一致性与附着性的建构主义解读[6](P31-63)以及倡议联盟的政策过程解读,[7]同时主体间理解的深度(即具体性和持续性),以及劝说和社会化的力量或合法性(包括国内的显突性、国际政治和结构的相合性、规范争论的程度),[8](P2)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一种规范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认识。
由于“人道主义干涉”往往被认为是有选择性的(selective)、伪善的(hypocritical),受到国家利益影响*人道主义干涉始于二战之后普世人权的西方自由概念,追溯到文艺复兴哲学。联合国作为一个基于服从而非强制的集合体,促使各成员国遵守联合国人权宪章(UNDHR),以避免二战的浩劫,人道主义干涉概念在二战之后在西方得以盛行。但是人道主义干涉并未得到成功,如科索沃战争、卢旺达屠杀案,因此被国际社会指责。再加上当前国际社会的最大危险并非大国间战争,而是国家内部战争及其外溢效应,所以亟需新的国际规范来应对此类威胁。,对于人道主义干涉也存在广泛的争论,其中主要集中在实施强制的程度上,通过提供技术、经济和政治援助等实施的软性的干涉,相较于政治制约、制裁或直接开展军事行动等硬性的干涉更容易被接受。进入21世纪,“保护的责任”渐渐取代“人道主义干涉”,并逐渐被接受。“保护的责任”概念本身指当一国当局无力在本国避免大屠杀、战争罪行、种族清洗以及反人类罪行时,国际社会可以行使保护的责任,对该国内政进行干涉。该概念被写入2005年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公报中,以代替充满争议的人道主义干涉概念。[9]该概念始于2001年加拿大“干涉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CISS)向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交的《保护的责任》报告,经过多次谈判协商,该原则以宣言形式进入政治议程,得到2005年联合国全球峰会的肯定。2009年第63届联合国大会讨论并通过《履行保护的责任》,为“保护的责任”提出三大支柱的建议*“保护的责任”的三个支柱包括:主权国家有责任保护其本国居民;国际社会有责任协助保护公民并协助进行冲突后的和平建设;在联合国安理会命令下,通过军事力量对国际社会的责任做出反应,以停止大规模暴行。前两个支柱属于预防性的,第三个支柱属于干涉性的。。2011年联合国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实施对利比亚军事打击,被认为是西方首次实践“保护的责任”。由巴西在2012年提出的“保护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这一概念可以被视为对“保护的责任”的修正和新发展,强调了对国家在行使保护责任时的程序、手段等方面加强规范。尽管“保护的责任”概念已经发展10余年,经由概念演变为规范,但该规范仍存在不同国际行为体的不同理解与实践,这也促使世界政治规范构架趋于多元化和竞争性。
“保护的责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道主义干涉”并获得发展,一是因为“保护的责任”(特别是“保护的责任”的第一支柱内容)被认为是国家主权的同盟;二是因为“保护的责任”将宽泛的大规模人口死亡缩小为四个具体罪行: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三是因为涉及使用强力或武力实现的“保护的责任”需要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四是因为本国政府对本国公民负首要的保护责任。总之,“保护的责任”缓解了不干涉规范与人的安全原则,强调人的安全是一种责任而非权利,从而修正国际关系中的主体间意义。本文并非分析“保护的责任”作为一种规范本身的发展逻辑,而是分析规范主导国家在规范演进中发挥的作用,即规范主导国家如何将其纳入到规范性外交维度,即规范在规范主导国家中的政策体现。考虑到每个外交行为体在特定背景与时空中都有不同的规范性外交诉求,因此,本文力求将关键行为体纳入到规范演进与发展的框架中,探析其规范性外交的历史、制度和文化背景,分析其对“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及政策,以及对全球秩序的影响。
二、规范性外交与“保护的责任”
规范作为一种共享的理解与价值,塑造了行为体的偏好与认同,并合法化了其行为。随着国际社会规范性层面重要性的提升及外交政策领域的多层化,规范和价值在外交政策的解释因素中也日益凸显,[10]任何外交行为体都会有对规范性外交的追求,只不过在不同时空背景下有所侧重。那么规范性外交是什么或者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总体来看,规范性外交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国际行为体为实现其规范诉求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即以外交为手段,为其谋求话语权;其二是国际行为体为实现其外交目标而进行的规范性外交,即以规范性倡议为手段,实现其利益诉求。
对规范性外交的一般理解是基于对规范性力量的解读,即国际行为体对他国或国际事务在道德规范或道义观念上的影响力。规范性外交的衡量指标包括目标、方式和影响。[11]从目标来看,规范性外交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物质利益,还包括维护外部环境的和平、推广规范性原则;从方式来看,规范性外交既包括经济、文化等规范性手段,也包括政治接触、技术援助等使用方式;从影响来看,规范性外交的影响需要追踪国际行为体直接或间接的行为,主要涉及是否有效建立以国际法为基石的外部环境的路径。总体而言,规范性外交不仅仅基于某个规范性原则,而且是以一种规范性的方式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12]
但仅仅基于规范性特征或非规范性特征来描述规范性外交政策很可能没有解释力,因为国际行为体会在不同区域不同领域采用不同的外交政策,根本出发点还是在于对国家利益需要的认知。规范性外交的制定也需要做出如下考量:(1)从国际行为体实际出发,考虑其内部政治环境,即不同的宪政结构(比如政党,利益集团,市民社会,媒体,公益和商业)以及官方机构的角色;还需要考虑其内部权能,即不同的能力构成,比如军事实力、经济能力以及相对权力对比,比如依赖与相互依赖程度。这关系到行为体如何定义、诠释、操作其外交政策目标。比如强调制度构架,比如说多层次权威限制其追求现实政治;比如国际行为体的制度设计过滤各层级利益,继而塑造其对外政策;(2)从国际行为体如何看待世界出发,比如康德理念投射到欧盟外交政策,中国义利观投射到外交政策;比如欧盟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行为体,影响欧盟追求规范性外交。(3)从国际体系层面出发,外交政策是该行为体在国际结构位置的结果。考虑外部环境对行为体如何在国际体系(或国际社会中)展开外交政策的影响,涉及如何与第三国的国内动态互动,如何与第三国或特定议题领域的其他国际行为体的政策互动,如何在更大国际背景下与第三国互动。
规范性并非一个非黑即白的概念,存在着灰色区域,不同行为体在不同情境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这既表明规范性外交与非规范性外交不是截然相反的,又说明外交行为体的规范性外交并非完全互相排斥。“保护的责任”在对外关系中就构成了规范性外交的维度,不同行为体对“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对全球秩序的认识都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行为体针对某一特定规范有不同的态度,或者同类行为体针对不同规范有不同的态度,这属于两个不同的问题提出方式,需要提供的分析框架也不相同。。全球秩序变迁与其内在规范的变迁密切相关,规范主导国一方面通过规范内化,促进其他国家变成规范追随国,并实现规范普及,另一方面根据其自身特点,对规范予以修正,开展有利于自身的规范框架。大国在塑造全球规范过程中是否合法与恰当对全球规范的演进有着重要影响。本文所讨论的是欧盟、美国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是否以相似方式行动这一问题,具体的通过“保护的责任”这一议题,描述了不同外交行为体在该规范范畴中的外交政策,其中涉及它们之间权力竞争、不平等与合法性的冲突,以及对全球秩序的影响。
三、欧盟与“保护的责任”
在伊恩·迈纳斯(Ian Manners)提出“规范性欧洲”(Normative Power Europe)[13](P235-258)这一观点之后,对欧盟规范性外交以及其作为一个规范性力量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何种作用的讨论就层出不穷。在官方文件中,欧盟也力图将自己定位成一个规范性力量,[14]在对外交往中积极推广自身的规范性原则,强调通过规范性的手段并借助“榜样的力量”来对其他行为体施加影响。“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本身与欧盟一直以来追求的自由、民主、良好治理、法治等原则息息相关,因此,欧盟(包括欧盟机构、欧盟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内的公民社会)一直以来也被认为是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作为国际社会上明确支持这一理念的关键行为体,欧盟认为政府有责任保护其人民来抵抗那些大规模的、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侵害,但同时也需要一个辅助性的国际责任来支持这种保护的努力。欧盟基本上将这一概念理解为新兴的法律规范,并通过多边论坛将“保护的责任”引入讲话、声明和决议中,以一种“规范塑造”的方式来传播这一概念。在2005年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欧盟联合其盟友努力寻求将“保护的责任”涵盖在会议的成果文件中,并最终获得了实现。
然而欧盟规范性外交在实践中经常被诟病的一点在于理念与实际之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在处理规范性诉求和利益诉求之间的分歧时尤为明显。这也与欧盟自身组织结构的特性密切相关,欧盟与其成员国在外交政策决策上的协调势必会对欧盟政策实施造成影响。在处理“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及其相关问题时,对于欧盟来说期望通过在外交事务中以“一个声音说话”来将自身规范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广,而对于成员国来说自身的利益考量占了更大比重,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除了保持对这一原则基本支持的立场,欧盟内部在具体的政策执行方面依旧难以达成一个共识。
在欧盟内部,北欧国家、荷兰以及斯洛文尼亚都是“保护的责任”的积极支持者,但是它们的政策偏好在欧盟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力与欧盟成员国中的三驾马车——英国、法国和德国相比还是有限的。这三个国家与欧盟机构之间在一些基本观念上是保持一致的,即认为“保护的责任”的实施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长期的、多边性质的规范建设,同时致力于将这一理念向全球范围推广。在2005年的联合国首脑会议上,英法两国表达了对于”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大力支持,而德国由于受到安全理事会改革事务的牵制,并没有过于深入地参与其中。然而,在具体认识方面三国仍存有分歧:德国强调的是军事约束(military restraint)以及民事危机防御(civilian crisis prevention),[15]在2011年利比亚的干预行动的触动下,德国政府对”保护的责任”这一概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并将其解释为一个道德原则,需要政策辅助实施来实现;而法国和英国则继续坚持其一直以来的人道主义干涉原则,将“保护的责任”作为与之相匹配的修辞手段(rhetorical tool)和一种政治工具,这既不限制它们在安全理事会的自由行动,也不排除它们在缺少安理会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军事干预。[16](P11-30)欧盟内部的分歧主要来自于成员国对其历史上运用武力的经验或教训的总结,反映在实际中就是成员国内部在具体战略文化以及对“人道主义干涉”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差异,这些差异也阻碍了欧盟塑造一个共同观念和政策的努力,影响了欧盟作为一个共同体在国际社会中外交关系的开展,这在欧盟处理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的讨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处理利比亚问题时,欧盟明确表示了对“保护的责任”原则的肯定和支持,欧洲议会强调,“欧盟及其成员国必须尊重‘保护的责任’以将利比亚平民从大规模的武装袭击中解救出来”。[17]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武器禁运的1970号决议之后,欧盟随即表示对利比亚实施军备禁运,同时还禁止与利比亚进行可能的贸易。欧盟还对卡扎菲等人也实施签证禁令和资产冻结。但在讨论到以军事干预防止班加西的流血事件上,欧盟则彻底分裂,其中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法国和英国都坚决支持在“保护的责任”原则下进行干预,但并没有获得所有成员国的支持,比如德国就以存在操作风险和大规模人员伤亡的可能性为由投了弃权票。欧盟在“保护的责任”的实施中仍受制于成员国(尤其是主要国家)间的分歧。
在叙利亚问题上,欧盟内部的分歧依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对阿萨德(Bashar al-Assad)暴力镇压人民的行为进行了一致谴责,并倡导国际社会对此有所反应,进行经济制裁,但是2011年10月,一个以法国、德国、葡萄牙、英国等欧洲国家提出的决议在安理会并未获得成功。随着冲突加剧,欧盟在保护叙利亚平民的必要性以及对叙利亚制裁的共识依然坚挺,但对于是否进行干预行动分歧开始凸显,比如在2013年9月叙利亚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后,法国表示坚定支持采取干预行动;与利比亚问题不同的是,成员国普遍并不倾向于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干预行动,其他成员国或者如西班牙一样持观望态度,或者如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典等国一样,表示只有在国际审查确认叙利亚政权的罪责并得到联合国认可情况下才会支持一个干预行动;另外,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欧盟成员国,除了表示应当必须等待检查结果、尊重国际法外,还明确表达了对实施干预行动的政治愿望的怀疑,并指出最好的优先选择还是应当以外交途径来解决;德国为了表达自己的态度甚至推迟了对于G20声明的支持,因为在声明中涵盖了呼吁国际社会对叙利亚做出反应的内容。
从这两次危机的处理中不难看出,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口头上认可并支持“保护的责任”的一般原则。2008年发布的关于欧盟安全战略实施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主权政府必须为它们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同时共享保护人类免受由种族灭绝、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等带来侵害的责任”;[18]当“保护的责任”的第二个支柱不能有效解决问题时,欧盟应支持“保护的责任”的第三支柱,以停止大规模暴行。但是在具体操作中,由于成员国之间在利益和认识上的分歧使得欧盟与成员国之间难以达成共识,尤其是无法为阻止大规模暴行而实施国际干预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也没有就危机出现时应如何应对、采取怎样的行动达成协议。欧盟内部的分裂意味着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实施支持人道主义干预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只能在联合国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实现。
四、美国与“保护的责任”
与欧盟相比,美国对于“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表现出的态度更加含糊其辞,美国政府将其视为指导而非约束国际共同体的一种道德原则。在美国看来,“保护的责任”第一支柱与第三支柱的性质不同,前者更强调一种职责,后者更多的是一种权利。也就是说,美国不认可针对第三支柱的一般性的行为准则,而认为干涉是基于逐项给予的(Case-by-Case)。尽管美国被认为是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能力与意愿支持与发展“保护的责任”,但是美国政府仍未完全在规范性外交框架下实践该规范,而是将其服务于现有的美国政策体系,表现为其一,将“保护的责任”纳入到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文件中,比如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到,“美国及联合国所有成员均应支持‘保护的责任’”;[19](P48)其二,美国政府为迎合国内的怀疑态度而避免“保护的责任”塑造美国外交政策;其三,“保护的责任”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开展依赖于选举周期的官僚过程,而非立法过程。
一直以来美国政府都致力于通过实用主义原则来保证政策的一致性,但不同党派政府也存在不同。布什政府对多边行动持更多的迟疑态度,2001年美国开展的全球反恐战争就是一例。布什政府驳斥“保护的责任”是国际共同体的法律职责,并在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的修改过程中淡化“保护的责任”的规范内容,还试图阻扰该峰会的谈判,布什政府希望以此保留自由行动的可能性、不至于丧失美国单边行动的合法性。在新保守主义者看来,美国国家利益是决定干涉合法性的唯一衡量标准。[20](P71)考虑到总统在美国外交事务中发挥主要角色,奥巴马对干涉行动所持的怀疑态度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对“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及政策。2011年8月,奥巴马政府通过总统研究指令-10(PSD-10)建立防暴委员会(APB),并指出阻止大规模种族灭绝既是美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是主要道德责任。[21]行政部门之间、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三权分立为审议与控制(deliberation and control)提供足够空间,[22][23](P430)当三者能达成一致时,美国更能快速在外交事务中采取行动。一般而言,国会可以通过立法程序、听证会或委员会调查和大众评议等来影响总统的行为,其中最主要的工具是预算权力和发动战争的权力。这涉及总统是否能够依赖其政党处于多数状态,或者总统和美国议会中的多数由不同政党所掌握。也就是说,政党支持能够在军事行动中给予总统诸多灵活性。
在利比亚危机中,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受到国内掣肘尤其是民众压力而不愿采取军事干预,另一方面也受到鲍威尔、克林顿等人的影响,[24][25](P217)美国最后才同意支持英国和法国的干涉联盟,不仅支持禁飞区,还实施全方位的军事干预。国际支持、卡扎菲的行为、美国内部的推力促使奥巴马在利比亚问题上实施“保护的责任”第三条原则。但是奥巴马声称该行为是个例,不表明美国基于人道主义采取军事干预。在叙利亚危机中,大国间存在的争议约束了美国在多边关系中的影响力及“保护的责任”的实践能力。由于叙利亚局势不够明晰,同时伊拉克泥潭的阴影仍存在,“保护的责任”在美国民众中依然不是一个优先考虑。2012年,美国曾两次提出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但均被俄罗斯与中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分别于2012年2月4日、2012年7月19日讨论由美欧国家提出的关于叙利亚危机的决议草案。。这也预示着“保护的责任”在叙利亚危机中陷入困境。
通过两次危机中的美国表现,显示了三个特征,其一,“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性原则逐渐进入美国外交政策文件中,并予以实施;其二,美国为迎合国内民众避免通过“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来塑造主要政策;其三,“保护的责任”的实施需要经过一个官僚而非立法过程。从理念维度看,“保护的责任”范畴下的美国规范性外交掺杂着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趋向,以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动机。从实际政策来看,“保护的责任”范畴下的美国规范性外交受到诸如对国家安全的狭隘定义,三权分立政治体系的复杂性,国内政治和与媒体的极化争论传统[26]等影响。
五、新兴大国与“保护的责任”
“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提出伊始往往被视为一个西方的概念,[27](P383-386)除去西方思想家为这一概念做出的努力,也反映出“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在全球范围内存在普及程度和认识上的差异,比如对于一些国家来说,“保护的责任”原则本身是西方国家寻求通过人权的意识形态观念强加给贫穷国家的,[28]这也造成了有学者指出的一些新兴国家对于”保护的责任”原则进行批评,在某些情况下还试图破坏其发展成一个全球标准。[29](P453)但是随着国际社会交往的深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崛起,它们在融入适应现有国际秩序的同时,也在寻求对现有规范原则进行丰富和扩展,从而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诉求。
作为一个整体,金砖国家对于“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的理解也是在不断深入和发展中的*金砖国家并非是规范接受者。金砖国家扮演着规范主导国家的角色,与欧盟、美国一并影响着“保护的责任”规范的演进过程。只不过金砖国家立场复杂,难以用一个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但是金砖国家在基本倾向方面有相似之处。陈拯:《金砖国家与“保护的责任”》,《外交评论》,2015年第1期。。“保护的责任”本身内涵了主权与人权关系的内容,由于历史经历等因素,欧美与新兴国家存在决策主权与领土主权的分野。在2001年国际干预与国家主权委员会的报告发布之前,金砖国家对“有条件的主权”(contingent sovereignty)原则普遍持有怀疑态度,因为这一原则意味着一个国家的主权取决于其保护其公民的意愿和能力。[30](P11-24)虽然“主权作为责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本身并不是一个西方概念,[31]但是在“南方国家”中倡导这一概念的也只有非洲联盟成员。因此,除了南非之外,其余金砖国家成员在这一概念提出伊始并没有发挥积极的参与和推动作用。在2005年联合国世界峰会之前,印度常驻代表还公开质疑“保护的责任”的法律和道德基础;[31](P23)在会议讨论过程中,巴西也频繁地表达了对这一概念所持的反对态度。在“保护的责任”作为一揽子计划中的一部分被纳入到会议成果性文件后,金砖国家的态度依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2007年,伯克利大学人权中心的一份报告中列举了一份所谓的“倒退国家”名单,针对那些转变了对2005年同意通过的“保护的责任”基本原则态度的国家,其中就包括了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同时报告中列出的推动“保护的责任”原则的非政府组织中无一例外全部来自西方国家,报告还指出,“在亚洲,无论是政府还是非政府组织出于‘保护的责任’原则将危及国家主权的考量都多少表现出了对这一原则的不欢迎”。[32]因此,在“保护的责任”原则获得承认的首个四年中,金砖国家基本持怀疑和谨慎*Chris Keeler, The End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12 October 2011, http://www .foreignpolicyjournal.com/2011/10/12/the-end-of-the-responsibility-to-protect, IBSA refers to the trilateral grouping of India, Brazil and South Africa.的态度。实际上,金砖国家的这种态度以及与西方国家在理解上的区别并不基于这一规范本身的存在是否有必要,而在于何时以及如何去实施这一规范。2009年联合国秘书长的报告就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并对“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的前两个支柱进行了重点解释。之后,2011年金砖国家共同投票支持了通过“保护的责任”来应对在中非共和国、几内亚比绍、苏丹和科特迪瓦的冲突。[33](P401)
利比亚危机和叙利亚危机同样是检验金砖国家对“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态度、加深彼此理解的机会。2011年,南非作为联合国1970号决议的共同提案人,甚至被认为是解决利比亚问题时的领导者之一,明确表示支持对利比亚实施严厉制裁并谴责卡扎菲政权(the Gaddafi regime)对本国公民使用暴力。在随后关于处理利比亚问题的1973号决议中,南非投赞成票,其余金砖国家均投弃权票,决议获得通过,这也意味着金砖国家支持或者并不反对在一些特定事例中采取干预行动,但是中国等国也表达了执行中对于武力使用的强烈反对。作为传统上主权原则最为坚定的捍卫者之一,印度投票表示支持S-2012-77号决议草案以谴责叙利亚政府。[34]从根本上来说,金砖国家对“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是持支持态度的,尤其是这一规范的前两个支柱方面,但是金砖国家内部在“保护的责任”这一问题的理解上也并非完全一致的,同时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金砖国家在处理这一问题时的实施力也不同。
与此同时,“保护的责任”作为一项发展中的国际规范与新兴大国的融入密不可分。在“保护的责任”原则及其实践中,部分西方学者将这些新兴国家描绘成“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或“逃兵”(shirkers)[35](P44-53)[36](P285-297)完全是一种误读,实际上新兴国家积极贡献了自己的解读,丰富了这一概念的内涵,使其向更加全球化的规范发展。在2009年联合国大会的辩论中,印度代表作为“保护的责任”这一问题的特别顾问提出了“殖民主义和干涉主义运用保护的责任”这一观点。[37](P43)一直以来,南非都充当着地区内“保护的责任”原则推动者的角色。南非作为金砖国家中最为积极的一份子,在从“不干涉”(non-intervention)向“非冷漠”(non-indifference)谈判的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8](P436-457)与“保护的责任”原则相对应的,2012年巴西常驻联合国代表瓦尔蒂提出新的概念“保护中的责任”(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指出基于“保护的责任”原则下开展的干预行动在一些时候非但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加剧了既有冲突,军事行动也造成了人员和物力的巨大损失,而且还存在“保护的责任”原则被滥用的现象和可能性。因此,应当对国家在行使保护责任时的程序、手段进一步规范,并明确武力只能作为行使保护责任的最后手段。以上这些新观念的提出都展现了新兴国家积极参与新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塑造的抱负。
另外,“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也被新兴国家用来服务于本国外交政策。目前,“保护的责任”已经成为印度政府在开展对外关系时经常使用的概念,比如以此来呼吁斯里兰卡政府对平民进行保护。俄罗斯通常被认为是金砖国家中对“保护的责任”原则最积极的批判者,但往往俄罗斯阻碍或反对这一原则实施的情况只出现在其核心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在2008年8月对格鲁吉亚进行干预时也采用了这一原则,虽然国际社会对在这一问题中俄罗斯政府所持的理解存在争论,但俄罗斯政府以此来捍卫自己的行动,也显示出俄罗斯在原则上是认同以侵犯另一个国家主权的方式来避免该国公民受到大规模暴行的。[39]以“保护的责任”原则来合法化自身行动,也是国家认识到规范性外交重要性的体现。巴西对于主权原则的看法也是在发生变化的,对于干预行动的立场也是在变动中的。[40]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虽然传统的思维仍然强劲,但很多巴西政治家和学者已经认识到在一些时候政府缺少或无力去保护本国公民。中国也已经开始对之前无条件的主权原则进行反思。[41]这一方面是由国内政治环境决定的,也是出于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另一方面也是表达了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中国政府在支持保护责任理念的同时,更多关注其实施过程,并表现了四个主要特点,即审慎的态度、尊重联合国权威、强调和平手段和尊重当事国人民以及该地区的国际组织。[42]
总之,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国内政治结构以及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等原因,金砖国家在对“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的理解上自然会存在与西方国家不同的认识,金砖国家内部也会存在不同的理解与实践。但这并不意味着金砖国家就是“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的对立者,事实上金砖国家一直在努力寻求通过合法途径将自身诉求表达出来,这无论是对于丰富“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的内涵,还是对于国际实践的开展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同时,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对于“保护的责任”这一原则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并逐渐反映到其外交政策中,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它们外交政策的开展,也有助于这一原则本身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
六、结 语
伴随着权力转移,国际规范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竞争与冲突的一个议题领域。对于“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的争论就是表现之一,它涉及主权和责任、普世主义与例外主义的争论。对于国际规范(“保护的责任”)演进变迁趋势和扩散动力的研究也成为规范研究的重点议题之一。国际规范与国家行为(外交政策)的关系涵盖规范变迁与行为遵照两个议题,社会化过程穿插其中。但是社会化“结构—行为主体”关系并非是单一顺从模式,而是规范竞争与规范顺从的合体。规范主导国的规范性外交政策成为影响规范变迁的主要渠道。“保护的责任”更多地被接受为一种正在制定中的政治规范,但在具体实施方法上仍需要个案的实践来不断丰富,因此行为体对于危机处理的方式也影响甚至决定了这一规范在全球范围的可接受程度。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的实践中,行为体内部和行为体之间对于危机处理中“保护的责任”原则的实践存在分歧,不同行为体之间围绕如何有效应对大规模暴行展开了讨论,也推进了一个全球规范的发展。
规范性外交既可以作为行为体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的工具,也可以被视为行为体追求的目标。但是由于各行为体对“保护的责任”的理解不一致,欧盟、美国与金砖国家在“保护的责任”的态度及规范性外交实践上有所差别。欧盟作为“保护的责任”规范最早、最积极的倡导者,以其内在的规范架构外溢到对外关系层面,以“保护的责任”的外交实践来实现其自身价值规范;美国作为传统“人道主义干涉”的倡导者,呈现出规范性与霸权结合的方式,通过“保护的责任”的外交实践为其霸权地位提供合法性基础,以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金砖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新兴行为体,在接受“保护的责任”这一规范的基础之上,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并寻求为其增添新的内涵,将这一原本带有“西方色彩”的概念向全球化的层面推广。
考虑到每个国际行为体对“规范(性)”有不同的认知,以及不同国际行为体之间存在不一致的关系,如友好与敌对、合作与竞争。中国应积极利用国际社会变动的时间窗口,并且利用国际社会规范竞争的特点,积极塑造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崛起,在全球规范层面也发挥了作用,即体现在和平与发展两个价值规范的崛起。[43]中国应积极开展规范性外交,以充实中国外交实践,一方面为中国提供在国际社会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为中国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
[1] Martha Finnemore. Constructing Norms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A].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s.).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2] 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 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3] 贺之杲.欧盟的合法性问题及其合法化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2).
[4] 曾向红,王慧婷.不同国家在“保护的责任”适用问题上的立场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1).
[5] 陈小鼎,王亚琪.从“干涉的权利”到保护的责任—话语权视角下的戏份人道主义干涉[J].当代亚太,2014,(3).
[6] Noha Shawki.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he Evolu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Norm[J].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3, No.2, 2011.
[7] 黄超.框定战略与“保护的责任”:规范扩散的动力[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9).
[8] Jessica Port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 Normative Analysis[EB/OL].http://www.polsis.uq.edu.au/OCIS/Porter.pdf.
[9]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 UN Doc.A/RES/60/1[R]. 16 October 2005,http://www.worldlii.org/int/other/UNGA/2005/47.pdf.
[10] Karen E. Smith, Margot Light. Ethics and Fore-ign Polic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 Nathalie Tocci, Daniel S. Hamilton, Radha Ku-mar. Who Is Normative Foreign Policy Actor? The European Union And Its Global Partners[J].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2008.
[12] 贺之杲,巩潇泫.规范性外交与欧盟气候变化外交政策[J].教学与研究,2015,(5).
[13] Ian Manners. Normative Power Europe: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J].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20, No.2, 2002.
[14] European Council.Treaty of Lisbon amending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R].13 December 2007,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OJ:C:2007:306:FULL&from=EN.
[15] Alister Miskimm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Libya Crisis[J]. German Politics, Vol.21, No.4, 2012.
[16] Nicole Koenig. The EU and the Libya Crisis: in Quest of Coherence?[J].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46, No.4, 2011.
[17] Europe Parliament[EB/OL]. No 305/2011, 9 March, 2011, http://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32011R0305&from=EN.
[18] European Council.Report on the lmplementation of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Providing Security in a Changing World[R].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EN?reports/104630.pdf.2008.
[19]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R]. Washington, DC.The White House,May 2010.
[20] Theresa Reino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mpediment, Bystander, or Norm Leader?[J].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3, No.1, 2011.
[21]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ial Study Directive on Mass Atrocities[R]. PSD-10, August 4, 2011.
[22] Douglas L.Kriner. After the Rubicon: Congress, President, and the Politics of Waging War[M].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10.
[23] Eugen R. Witttkopf, Christopher M. Jones, Charles W. Kegle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attern and Process[M]. Belmont:Thomson Wadsworth, 2008.
[24] Michael Hastings. Inside Obama’s War Room[J].Rolling Stone,13 October 2011.
[25] Tom J. Farer, Claudia FuentesJulio. Flesh on Doctrinal Bones? The United States and R2P[A]. in Monica Serrano and Thomas G. Weiss,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Human Rights-Rallying to the R2P Cause[C]. New York: Routlegde.
[26] Samantha Power.A Problem from Hell-American and the Age of Genocide[M]. New York:HarperCollins, 2003.
[27] Serena K. Sharma.R to P at Ten Years[J].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3, No.4, 2011.
[28] 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In Respon-ses of Government and Agencies to the Report of the UN Special Representative for Internally Displaced Persons[R]. E-CN-4, SR.40, 1993.
[29] Rama Mani and Thomas G. Weiss. R2P’s Miss-ing Link, Culture[J].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3, No.4,2001.
[30] Stewart Patrick. The Role of the US Government in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Stuart Elden, Contingent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and the Sanctity of Borders[J]. SAIS Review, Vol.26, No.1, 2006.
[31] Alex J. Bellamy.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Words to Deeds[M]. London: Routledge, 2011.
[32] Human Rights Cent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Moving the Campaign Forward[EB/OL]. 2007, http://www.responsibilitytoprotect.org/files/UNA%20Canada%20Report%20on%20R2P.pdf.
[33] Anne Orford. From Promise to Practice? The Legal Significance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Concept[J].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3, No.4, 2011.
[34] Security Council. S/PV.6711[R].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PV.6771.15.May 2012.
[35] Stewart Patrick. Irresponsible Stakeholders? The Difficulty of Integrating Rising Powers[J]. Foreign Affairs, Vol.89, No.6, 2010.
[36] Randall Schweller. Emerging Powers in an Age of Disorder[J]. Global Governance, Vol.17, No.3, 2011.
[37] Alex J. Bellamy.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From Words to Deeds[M]. London: Routledge, 2011.
[38] Cris Landsberg. Pax South Africana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J].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Vol.2, No.4, 2010.
[39] Elena Jurado. A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EB/OL]. 15 August 2008, http://www. newstatesman.com/asia/2008/08/russia-international-georgia-2.
[40] Kai Michael Kenkel. Brazil and R2P:Does Taking Responsibility Mean Using Force?[J].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Vol.4,No.1,2012.
[41] China’s Svolving Foreign Policy: The Libyan Di-lemma[EB/OL].The Economist, 10 September 2011,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28664.
[42] 罗艳华.“保护的责任”的发展历程与中国的立场[J].国际政治研究,2014,(3).
[43] 王正绪.中国崛起的规范性力量[EB/OL].2015-02-07,http://www.guancha.cn/Wang-Zhengxu/2015_02_07_308843.shtml.
[责任编辑 刘蔚然]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ormative Diplomacy
He Zhigao1, Gong Xiaoxuan2
(1.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2.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normative diplomacy;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emerging countri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as a norm has gradually become a consens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context that all the actors in the world begin to pay attention to normative diplomacy,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framework of normative diplomacy. There are two forms of normative diplomacy. One is the diplomatic activ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actors aiming at the realization of their normative objectives. The other is the normative diplomacy of international actors aiming at achieving their diplomatic goals. The main forc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which provides the possibility for th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into the framework of normative diplomacy.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ormative diplomacy,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tection” of the main global actors, including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merging powers, i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ms.
贺之杲,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732);巩潇泫,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 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