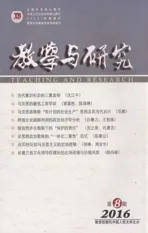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
2016-02-04谢富胜陈瑞琳
谢富胜,陈瑞琳
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
谢富胜,陈瑞琳
生存工资;工资; 最低工资
学术界针对马克思的工资理论长期存在争论和误解。从不同时期的文本来看,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经历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发展过程。受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的影响,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并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工资与最低工资等关键概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建立起自己成熟的工资理论,并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最低工资学说,从而彻底与古典经济学及其代表性的“工资等于最低(生存)工资”的说法划清界限。与工作日理论一脉相承,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从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出发,为法定最低工资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中,工资问题无疑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868年1月,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其中之一就是“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1](P12)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工资理论有待于在《雇佣劳动》册中予以阐述。[2](P52)罗斯多尔斯基认为马克思后来放弃了六册计划,关于雇佣劳动的部分被并入了《资本论》第1卷中。[3](P59)但是,罗桑批评罗斯多尔斯基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阐述只是摘抄了其成熟作品中广为人知的片段,而未能指明马克思观点的演变过程和其中存在的重要理论难题。[4](P182)罗桑的评论实际上阐明了一个事实,也就是在马克思广博的著作文本中,马克思对工资的论述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这也是为什么国际学术界在马克思有关工资问题上的丰富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文本基础上长期存在着争论的根源。不仅非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对此展开猛烈攻击,[5](P237-257)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内部针对具体问题也存在理论上的分野。例如,大卫·哈维强调资本积累的社会需要是影响和决定劳动力价值的主要力量,认为受到广泛关注的生存工资假说、供需平衡等多个视角都只是它的衍生理论;[6](P182)莱博维奇则主要关注阶级斗争对工资的影响。[7](P113-116)因此,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的文本中阐述的工资理论,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放置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去理解。
作为马克思工资理论一个组成部分的最低工资学说,在其早期文本中常常与平均工资一起出现。马克思早期有关工资的论述是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之上的,确实将平均工资看作是生理上最低限度的工资。尽管恩格斯在1885年德文版《哲学的贫困》的脚注中予以纠正,但是将平均工资视为最低工资的看法仍然存在。[8](P95-96)事实上,这一问题早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透过“最低限度的工资”到“工资的最低限度”这一术语的转变便得到初步回答。因此,只有基于马克思文本发展的脉络进行仔细的梳理,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以及包含其中的最低工资学说。孟氧细致地梳理了马克思早期工资理论的演变过程,并对“最低工资”这一概念进行了解读。[9]遗憾的是,他的解读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成熟的工资理论中的最低工资学说,而对这一点的理解正是区分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区分马克思的最低工资理论与拉萨尔工资铁律的关键。下面我们首先回顾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然后在第二部分梳理马克思早期文本中的工资理论,第三部分着重阐明马克思成熟的工资理论中的最低工资学说,最后是结论与启示。
一、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
第一部最低工资法颁布于1894年的新西兰,但最低工资政策及相关讨论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的英国。1348年突然爆发的黑死病使英国人口骤减三分之一,面对劳动力短缺和随之而来的工人议价能力增强,各地的庄园主开始积极游说议会,要求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工人罢工、遏制劳动力成本上涨。在此背景下于1349年颁布的《劳工条例》相当于规定了法定最高工资,这一制度直到1563年《学徒法令》的出台,才以“之前限定的工资水平在部分地区太低以至于给底层劳动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负担”为由正式废除,[10](P15)并迅速被1604年增设的最低工资条款所取代。受重商主义的影响,14-17世纪的英国议会为了巩固国家政权、维护传统工商业道德,采取了严格的劳动管制和工业管制,尤其在16-17世纪,政府实际上承担起保障工人阶级基本生存权利的责任。[11](P251)因此威廉·配第在1662年《赋税论》中写道,“我们一方面把限制贫民的工资,使其不能有一点积蓄以备应付失去工作能力或失业时的需要,看成是理所当然之事,另一方面又让他们饿死,那显然是极不合理的。”[12](P19)在他看来,工资既不能低到生理界限之下,也不能高到会使劳动者偷懒的程度。事实上,政府应该同时设定最低和最高工资,“使劳动者只能得到适当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你使劳动者有双倍的工资,那么劳动者实际所做的工作,就只等于他实际所能做和在工资不加倍时所做的一半。这对社会说来,就损失了同等数量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12](P85)
随着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政府权力逐渐削弱,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自由主义倾向开始受到关注。在此时期发展起来的重农学派更多的强调竞争关系,认为工资应是供求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但是工人在与资本的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只有双手和辛勤劳动的单纯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工资“不能完全由他本人来决定;这是他同那个购买他的劳动的人双方协议的结果。后者尽力压低这一价格;由于他有一大群工人可资挑选,他便优先选用那个讨价最低的工人”,因此工人内部的竞争使得“工资只限于为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13](P21)也就是说,平均而言工资将趋于生存工资。
亚当·斯密的工资理论大体上与重农学派的观点类似,既认同工资取决于劳资两方所订的契约,也认同“雇主常居于有利地位。”[14](P60-62)不过他还抽象出“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这一概念,将工资与劳动力的再生产联系起来,“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并将这一标准定性为“符合一般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在相当长的期间内,即使最低级劳动者的普通工资,似也不能减到这一定标准之下。”[14](P60-62)尽管斯密没有明确指出,但反映人道标准的最低工资本身就暗含了李嘉图和之后马克思反复提到的历史和道德的因素,因而与绝对生理学意义上的最低工资区分开。因此斯密口中的最低工资,更多地等价于生存工资,只是在它作为最低界限的工资的意义上,才表现为最低。此外,斯密还提到了工资与劳动力规模相互影响的机制,后来被马尔萨斯发展为著名的人口原理。斯密认为,工资的提高会鼓励劳动者结婚生子,其结果是造成市场上劳动供给的增加,从而反过来压低工资,回到社会正常水平,“像对其他商品的需求必然支配其他商品的生产一样,对人口的需求也必然支配人口的生产。”[14](P73)
大卫·李嘉图在斯密的基础上,将“让劳动者大体上能够生活下去并不增不减地延续其后裔所必需的价格”定义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正式把生存工资的内涵确定下来,并明确提出了平均工资趋于自然价格,即生存工资的观点。“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论能和其自然价格有多大的背离,它也还是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符合自然价格的倾向。”[15](P77-78)与斯密类似,在李嘉图的理论中,除了资本的转移之外,促使劳动的市场价格围绕着其自然价格上下波动的另一种机制也是抽象的人口规律:“当高额工资刺激人口增加,使劳动者的人数增加时,工资又会降到其自然价格上去……当劳动的市场价格低于其自然价格时……只有在贫困已经使劳动者的人数减少,或劳动的需求已经增加之后,劳动的市场价格才会再提高到自然价格上。”[15](P78)此外,李嘉图还特意分析了习惯的影响,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不能理解为绝对固定和恒常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必需品价值也是如此。它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中是有变化的,在不同的国家差别就十分大。这一点基本上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15](P78-80)从而将劳动的自然价格与生理必需品价值区分开来。
然而,穆勒在总结李嘉图的工资理论时,仍然将李嘉图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替换成“最低工资率”,认为“这或是从物质上使人口得以维持的最低工资率,或是人民借以维持人口的最低工资率。”[16](P384)虽然他也提到这一最低限度本身是可以变动的,“特别是在其为可以称作道德的最低限度的这种限度,而不是物质的最低限度的时候”,但是他却坚持认为“在现在的社会情况下,竞争是工资的主要调节者,习惯和个人的性格只起修正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也比较小。”[16](P380-385)正因如此,穆勒以会增加失业为由强烈反对以任何法律形式设定工资下限。[16](P402-403)
马尔萨斯分析英国的“济贫法”时提到,“不能用货币提高一个穷人的地位,不能用货币使他的生活境况大为好转,而不相应地降低其他穷人的生活。”[17](P32)他将低工资看作是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不仅可以鼓励储蓄、惩罚堕落和挥霍,还能阻碍不能养家糊口的男子结婚成家,“与其鼓励人口增长,然后让匮乏和疾病对其加以抑制,还不如从一开始就让预见与担忧来抑制人口。”[17](P35)在他看来,底层劳动者之所以生活困苦,是由于他们“漫不经心和大手大脚的习气”,所有助长这种风气又不能增加生活资料的法律都只会产生更多的穷人,因此消除贫困的第一步应是放开所有限制,使劳动市场处于绝对自由的状态。[17](P37)这一理论根源无疑可以一直追溯到斯密,只不过前人简略提及的影响工资的其中一种方式在这里被放大成了最主要的工资决定机制。
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与抽象的人口规律相结合,最终被彻底庸俗化为拉萨尔的工资铁律,其最直接的结论是平均工资只能趋于绝对最低工资。习惯和道德等因素被彻底抛弃,只剩下“劳动人民所以贫困,只是因为他们数量众多”这一劳动者间的尖锐对立。[18](P267)当前主流经济学对最低工资就业效应的关注,也不过是这一系列理论模型化后的现代版本。
二、马克思早期的工资理论:异化劳动与生存工资的结合
马克思最初关于工资的阐述直接建立在古典经济学的生存工资理论之上,但即使是在那个时候,其理论也表现出极强的批判性*针对马克思早期工资理论究竟来源于亚当·斯密还是大卫·李嘉图,目前学术界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孟氧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资的最初表述只借鉴了斯密的最低工资概念,因此他的早期工资理论应主要来源于斯密。但罗桑强调马克思在1844-1847年对政治经济学的潜心钻研以及恩格斯的影响,使他的观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罗桑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的早期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了李嘉图的影子,尤其是在《哲学的贫困》中。他认为在那里最低工资被表述为“劳动的自然价格”,反映出早期马克思对李嘉图工资理论的认同和参考。。从定义来看,二者并无实质性区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低工资”被定义为“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活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19](P49)而在《哲学的贫困》中,最低工资被抽象为“劳动的自然价格”,[8](P94)这里马克思不仅完全借用了李嘉图提出的术语,甚至也默认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工资等价于最低工资”的说法。
尽管马克思几乎完全借用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然而,正如孟氧所指出的,他围绕着这些概念所展开的论述已经显示出与前者明确的理论分野,这首先表现为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运用与古典经济学完全相同的逻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一开始便从资本家的联合、生产劳动的专用性和工人的生存压力这三个方面论证了工人相对于资本家的弱势地位,但他并没有停在这里,而是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分析了市场竞争和分工如何在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使工人永久地陷入贫困。在他看来,工资平均而言表现为生存工资并以此为限,恰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值得质疑的地方。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其获得的却越少。劳动产品成为与劳动者本身相对立的异己力量,反过来统治和奴役工人。这种异化关系,是由工人作为出卖劳动的无产者加入生产过程所决定的,而后者又与私有财产直接相连,反映的正是两大阶级之间的持续对立。在阶级对立下,工资作为异化劳动的一个结果,从长期来看无疑只能趋于其绝对最低值。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工资变动的表象而不分析其背后的阶级冲突,是将工人退化成“劳动的动物”、“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需要彻底的革新。[19](P57)事实上,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概念的沿用从一开始就带有批判的色彩。在“异化劳动”这一章的开头,马克思这样写道:“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我们从国民经济学本身出发,用它自己的话指出,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是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正比;竞争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来,也就是垄断的更可怕的恢复;最后,资本家和靠地租生活的人之间、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别消失了,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9](P89)可见,这里对原有框架的继承本身就是一种策略性的选择,是为了突出其中的逻辑漏洞。如果因此就认为马克思此时对工资问题的认识与古典经济学完全一致,则是舍本逐末了。
早期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另一个视角是以马尔萨斯为主要代表的绝对人口过剩理论。它首先由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在那里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周期性,他认为是相对于有效需求而言的生产的周期性过剩带来了经济危机,造成了失业和贫困,并不是生产力水平绝对不能满足工人的需要。他讽刺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意味着,“人口总是威胁着生活资料……当地球上还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人口过剩了。”[20](P617-618)恩格斯还在其经济周期理论中最早提出了“产业后备军”这一概念。[21](P369)但同时他也认同斯密的观点,认为工资与生育率和死亡率相互决定,“这种情形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情形完全一样:如果工人不够,他们的价格(即他们的工资)就上涨,他们就生活得比较好些,结婚的人多起来,出生率逐渐提高,养活的孩子也多起来,直到有了足够的工人为止;如果工人太多,价格就下跌,失业、贫困、饥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疾病就都出现了,而疾病就会消灭‘过剩人口’。”[21](P365)1847年12月,马克思写了一个名为“工资”的手稿,作为《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补充。在这个手稿中,马克思将工资变动主要归之于分工和机器生产的发展,他认为这会使劳动过程日益简单化,从而使儿童、女工都成为潜在劳动力,加剧工人之间的竞争。正因如此,“提高工资的主要条件是生产资本的增加和尽快增长”,而不是人口减少。[22(P649)[23](P378)这一规律最终在《资本论》中取得了科学的形式,成为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与古典经济学的绝对过剩人口理论针锋相对。不过,马克思也没有完全否认劳动力规模与工资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只不过他反对将其看成最重要的机制,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写道,工资提高会“缓和那些使工人后代减少和绝灭的影响,使结婚变得容易,由此使工人人口逐渐增加”,但这同时也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机器的采用和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人为的相对过剩人口。”[24](P243)资本的和自然的人口规律同时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工资水平,也被工资水平所影响。
不可否认的是,在马克思早期的工资理论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他还没有区分劳动与劳动力,错误地把劳动看成是一种商品,而把工资理解为劳动的价格。[8](P359)尽管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将工资重新表述为“劳动能力的平均价格”,但是直到1865年,他仍在公开演讲中使用“劳动的市场价格”这样的说法。[25](P164)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马克思确实没有认识到只有劳动能力可以作为商品出卖,劳动本身必须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意义。这一点要等到《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才被彻底地阐明。
其次,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对价值理论的阐释也是很不充分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以及货币作为价值的表现,体现的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些基本问题在《哲学的贫困》中都有初步涉及,但是只有建立在完整的资本积累、循环和周转理论之上的价值理论才能清楚地解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关系而存在的内涵。直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资本章”的最后,马克思才阐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内容,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是对资本本质的掩盖,同样要等到《资本论》第一卷完成之后。
最后,工资与最低工资这两个概念在其早期写作中始终未做明确区分。1847年12月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做了一系列关于工资的演说,以此为基础的演说内容在19世纪80年代又被正式整理成以《雇佣劳动与资本》为名的小册子,在工人间流传。1891年恩格斯对它进行了修订,成为马恩著作中第一本系统性地讨论工资问题的作品。在这本小册子里,马克思清楚地写道“这种维持生存和延续后代的费用的价格就是工资。这样决定的工资就叫做最低工资。”[22](P485)在《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原理》中,也有很多类似的表述。[22](P481,P359)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甚至还严厉批评了提高工资的努力,认为它们“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分和尊严”,[19](P101)不过是给奴隶更多酬劳而已。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有意识地剔除工资理论中的古典色彩,将工资重新定义为“劳动能力的平均价格”,但是它仍然与最低工资概念没有区别开来。[26](P52)
然而,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并非始终秉持“工资必须趋于其绝对界限”的观点,这以马克思对工会问题转变看法为突破口。1853-1856年,受克里米亚战争的影响,欧洲的粮食价格不断攀升,而工人的工资却持续下降,工人阶级忍无可忍开始频繁罢工。也正是在分析当时的社会问题时,马克思才逐渐意识到雇佣劳动作为商品的特殊性,它的价格决定不能完全依据供求规律来解释,而必须考虑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在同一个工业部门里一再罢工,同一些‘干活的’一次又一次要求再增加工资充分说明,按照供求规律,工人们早已有权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更高的工资,只是由于企业主们钻了工人们不熟悉劳动市场状况的空子罢了。”[27](P377)这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工资不再必须等于其绝对最低水平,而是也取决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工会存在的意义,第一次被明确确立了。
1857-1858年,作为《资本论》的准备工作,马克思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继续强调工会的重要性,但是涉及工资决定的却只有只言片语。他在“资本章”中反复提到未写成的“工资学说”,并强调为了更好地研究资本,此处必须对工资问题进行简化。[23](P241、247、414)在马克思1858年写给恩格斯的信里,他解释到自己因病痛而无法按计划完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并给出了自己的“六册计划”,其中在第一篇“资本一般”中,需要“假定工资总是等于它的最低额。工资本身的运动,工资最低额的降低或提高放在论雇佣劳动的那一部分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在研究每一个别关系时不致老是牵涉到一切问题。”[28](P299)由此可见,此时的马克思已经认识到工资运动的复杂性,他之所以仍然坚持让工资等于最低工资,只是暂时把它当成一个可以简化资本理论的技术性假设*莱博维奇也强调过这个问题,“通常被人们当作马克思的观点的有关真实工资不变的结论,实际上不过是方法论上为了分析方便所作的假设。”参见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43页,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
三、马克思成熟的工资理论中的最低工资学说
马克思的工资理论直到1865年《工资、价格和利润》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才最终走向成熟。马克思的成熟工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理论和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二重性学说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完全科学的价值理论;马克思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使其透过现象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的本质。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马克思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相对过剩人口规律。“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29](P737)尽管对劳动的需求可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总资本的不断扩大而绝对提高,但是相对于总资本的增速而言,“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29](P726)因此,工资的变动由资本积累规律和社会与自然人口规律共同决定,也受阶级斗争的影响*马克思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阶级斗争对工资的影响,却都没有做详细的分析。莱博维奇认为这是因为《资本论》中有关工资的讨论都是围绕着资本展开的。如果从雇佣劳动的视角出发,阶级斗争将成为工资决定的一个关键性环节。。
随着劳动力价值工资理论的完善,马克思还阐明了相对独立的最低工资学说。关于最低工资的说法不再使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出现的“最低限度的工资(minimum wage)”,转而修正为“工资的最低限度”(wage minimum)*值得注意的是,“工资的最低限度”这一说法早在1844-1845年就由恩格斯提出了。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生存所必需的工资”、“工资的最低限度”和“最低工资”这几种表述都被用来描述满足工人基本生活需求的“这一点点聊胜于无的东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60-363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以及“工资的最低限度”即最低工资这四个概念之间开始有了明确的区分。劳动力的价值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9](P201)而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9](P199-201)劳动力价值存在一个下限本身就表明前者并不是绝对最低水平,它“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29](P199)”,并且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相应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表现形式的工资也不是固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弹性的最低界限”,[29](P705)即绝对意义上的最低工资。
为了与庸俗经济学划清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对拉萨尔和马尔萨斯进行了批判。针对工资基金理论,马克思从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出发,认为工资的规模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它取决于社会资本中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而这一比例会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而不断改变。他提出工人的规模只会相对于资本的需求而出现过剩,绝对意义上的人口过剩是不存在的。[29](P728)庸俗经济学家把工资的资本界限说成是工资的社会自然界限是偷换概念。[29](P705)这里,“工资的社会自然界限”和“工资的资本界限”对应的正是“工资的最低限度”和“最低限度的工资”这一组概念*恩格斯在1875年《给奥·倍倍尔的信》中也评价道,“我们的人已经让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强加在自己头上,这个规律的基础是一种陈腐不堪的经济学观点,即工人平均只能得到最低的工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6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也就是说,拉萨尔的工资铁律反映的正是“最低限度的工资”。。
工资的最低限度与最低限度的工资最显著的不同是:前者只界定了工资的一个评判标准,旨在提供一个可以考量劳动者是否仍保有其基本生存权利的经济指标,类似于“贫困线”的概念;而后者则直接与工资的波动挂钩,暗示着工资仿佛天然就受到约束。而事实却是,工资的变动从来都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下限,正如“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29](P271)一样。马克思用丰富的历史材料不止一次地阐明资本家如何利用各种手段将工人的工资压低到纯粹生理的最低界限以下,譬如英国反雅各宾战争时期的农场主、[25](P164-165)圈地运动中发起农业革命的资本家。[29](P834-835)此外,不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早期的论述,都用“最低限度的工资”来分析工资的平均趋势。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入“工资的最低限度”,主要是想说明劳动力作为商品的特殊属性。在他看来,工资之所以不能像其他商品的价格那样任意的波动,是因为雇佣劳动“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29](P201)劳动力的价值“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29](P199)而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是“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29](P196)价格降到它之下,“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29](P201)
尽管从资本的逻辑看,工资由供求决定;但从劳动的逻辑看,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29](P202)工资必须在其最低界限之上。一方面,最低工资直接反映身体的基本物质需求,低于它,劳动者会得饥饿病;另一方面,最低工资也与超时劳动紧密相连,小时工资率越低,工人为了挣得勉强糊口的收入就不得不工作更长的时间。因此,工资一旦突破其绝对最低限度,会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29](P307)要么因为忍饥挨饿而过早死亡,要么因为过度劳动而未老先衰。
在关于工作日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虽然单个资本有追求无限扩张的冲动,但是对剩余劳动的索取必须受到有效的遏制。因为私人资本通过突破劳动者的生理界限而攫取的剩余价值,是以整个工人阶级的劳动退化为代价,而这个代价将最终由所有资本共同承担。资本积累依赖于社会再生产的不断反复和更新,社会再生产的核心又在于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问题,尤其是劳动力的再生产问题,因此“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29](P659)*莱博维奇以此为突破口,认为雇佣劳动的循环与资本的循环是相互依赖但又相对独立的两个过程,只涉及自身总量运动的资本是片面的、不充分的,必须以劳动力和消费品之间的不断转化为前提。因此,“在资本循环本身中,已经存在着一个超越了这一循环的特性。”参见莱博维奇,《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62-66页。但是资本家的短视和贪欲,常常使他们无视这些前提,如果不对此进行约束,单个资本会毫不犹豫地为了私人利益铤而走险。马克思曾写道,“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弄到这种极端退化的绝境。”[25](P161)所以“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29](P349)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分析争取提高工资的具体方法时,除了提出限制工作日外,还提出当工人不能影响工作日时,可以采取提高工资的方法。[25](P161)他发现,“劳动价格越低……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29](P629-P630)可见,法定最低工资与限制工作日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两种社会保障制度,它们具有同样的理论基础。
四、结论与启示
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的梳理揭示了其工资理论发展的历程。马克思早期的工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的继承,随着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完善,马克思的工资理论已经彻底与古典经济学划清界限。工资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区别于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其运动主要由资本积累过程与产业后备军来调节。不同于古典经济学,马克思的最低工资学说只是其工资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工作日理论相辅相成,以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为出发点,论证了国家干预工资决定的必要性。
在其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明确区分了两组重要的概念,即劳动力价值与工资,以及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与工资的最低限度。尽管工人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弱势地位使得第一组概念不断在现实中趋近第二组概念,这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身具有什么内在的一致性。二者在理论内涵上是根本不同的,这并不受彼此在表现形式上相似性的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是一个伸缩性很大的可变量,既包含生理上的因素,也包含历史的道德的因素。相应地,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工资,更是处于不断的波动之中,甚至在市场中其他因素都不变时,也常常是一个变动的值。相比之下,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和工资的最低限度在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则往往是不变的,它们反映的都是生理意义上的绝对界限。低于这一界限,不仅社会再生产无法正常进行,还会带来劳动力的萎缩和种族退化。然而,正如劳动者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性一样,这一绝对界限也是针对全社会而言的。单个资本家在不断追逐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并不会天然地感受到它的强制力。这正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与“工资的最低限度”的根本不同。只要工人还没有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与资本相抗衡,只要关于工资的谈判还是以局部的、零散的形式进行,实际工资就有突破它的社会最低限度的可能。这一可能性的实现,不仅对于产业工人是毁灭性的,对整个资产阶级也是毁灭性的,由劳动力整体退化带来的社会成本将最终由所有资本家和劳动者共同承担。从这个意义上说,运用国家强制力以法律的形式对工资水平设限,也就是说,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资本和劳动而言都至关重要。
事实上,早在1691年约翰·洛克就对此进行过论述,强调政府应该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劳动者的工资,避免社会大灾难的发生。他说,“这种拉和抢一般发生在地主和商人之间,因为劳动者所得到的份额一般是仅足糊口,这使他们没有时间或机会来想这些事情,或(采取共同行动)与富人们争夺他们的一份;除非有某种共同的大灾难使他们在一种普遍的纷扰局面中联合在一起,使他们无所顾虑而鼓起胆量来用武力夺取自己的所需;在这种情形下他们有时会突然袭击富人,并且像洪水一样地把一切都冲掉。但是,除了在失职和不良的政府的错误管理下,这种事情是很少出现的。”[31](P69)
然而,只要浏览一下马克思引用的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历史资料就不难发现,马克思口中的“种族退化”和洛克口中的“共同的大灾难”曾多么经常地表现为现实。英国官方派去考察工人阶级贫困状况的斯密斯医生,不仅在1863年撰写的工业蓝皮书中详细讨论了“平均至少需要多少碳素和氮素,才刚好足够防止饥饿病”并发现,“这个数量大约与棉织工厂的工人在极度贫困压迫下实际上所能够得到的菲薄养料相等”;[25](P6)也在第二年公布的《第六号公共卫生报告书》内写道“在调查属于农业人口的家庭时发现,这些家庭有五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碳食物,有三分之一以上得不到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含氮食物,并且在三个郡里(伯克郡、牛津郡和索美塞特郡),缺乏含氮食物是通常的现象”。[25](P6-7)同样的,1863年公布的《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书》中也提到,“陶工这一类人,不论男女,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居民中最退化的部分;不健康的儿童,反过来又要成为不健康的父母;有增无已的人种退化是不可避免的;斯泰福郡的居民,若不是经常有邻近地区的居民流进来,若不是与比较健康的居民群通婚,他们的退化程度是还会更加厉害的。”[25](P8)
近20多年来,中国底层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同样堪忧。程连升分析1991—2005年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加班与就业困难的并存,提出这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资轻劳”的社会政策造成的;[32]朱玲对国内农村流动人口进行抽样,发现其中超时劳动的现象严重,近26%的工人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他们之所以选择加班主要是受生活所迫,“小时工资越低,迁移工人超时劳动概率越高”,“挣钱全凭加班”的现象对工人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危害。[33]李钟瑾等也发现中国私有企业工人的工资长期低于生存工资的水平,“工资过低和劳动超时成为私有经济发展模式的双生儿”,中国私营经济在过去三十多年获得的高额利润主要的来源不是技术创新,而是不断压低劳动报酬强行拉开的私人生产成本与社会生产成本之间的差距。[34]在最新的研究中,潘毅等对富士康工人的调研表明低工资与超时劳动仍然广泛存在,为了维持日常生活消费,一线工人被迫长期加班,工资水平甚至成了制造业企业控制劳动者的手段之一。[35]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19世纪英国的经济发展:“英国工业的威力仅仅是靠野蛮地对待工人、靠破坏工人的健康、靠忽视整代整代的人在社会关系、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发展的办法来维持的。”[21](P462)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在于受经济水平的制约,其工会的发展程度受到严重限制,而针对底层劳动者的劳动保护、工作福利以及社会保障也长期缺位,这直接导致部分个体的基本劳动权益经常性地受到资本的侵犯。尽管最低工资制度本身存在局限,它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的短期行为,企业可以选择不遵守,也可以采取“打擦边球”、“钻空子”的方式使劳动者的收入明升暗降。事实上,在当前中国,最低工资已然日益演变成基本工资、平均工资。但是,毫无疑问,最低工资制度法律效力的不断增强,仍然能够对私营经济施加一定的限制,把社会工资水平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避免种族退化等极端情况的出现。在短期内工人话语权得不到显著改善的现状下,依托国家强制力对资本进行限制将是培育经济长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3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1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3]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M]. 魏埙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
[4] Rowthorn B.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M]. 1sted. London: Lawrence &Wishart, 1980.
[5] Lapides K. Marx’s Wage Theor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Interpretation[M]. 1sted. Westport: Praeger, 1998.
[6] Harvey D. The Limits to Capital[M]. 2nde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7] 莱博维奇. 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第2版)[M]. 崔秀红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7.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9] 孟氧.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拉萨尔的工资铁则[J]. 马克思主义研究, 1985, (3).
[10] Bland A., Brown P. & Tawney R.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Select Documents[M].New York: Macmillan, 1919.
[11] Lipson E.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M].2nd ed. London: A. & C. Black,1947.
[12]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 陈冬野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1.
[13] 杜尔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M].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说史教研组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14]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8.
[15] 大卫·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 郭大力,王亚南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6.
[16]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上)[M]. 胡企林,朱泱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17]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M]. 朱泱,胡企林,朱和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8] 埃德蒙·伯克.埃德蒙伯克读本[M]. 陈志瑞,石斌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6卷(上).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24] 马克思.资本论[M].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16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47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2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9] 马克思. 资本论[M].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 第19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1] 约翰·洛克. 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M]. 徐式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2] 程连升. 超时加班与就业困难——1991-2005 年中国经济就业弹性下降分析[J].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6, (4).
[33] 朱玲. 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时间和职业健康[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1).
[34] 李钟瑾, 陈瀛, 齐昊等. 生存工资、超时劳动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2,(3).
[35] Ngai, P., & Chan, J. Global capital, the state, and Chinese workers the Foxconn experience[J]. Modern China, 2012,38(4).
[责任编辑 陈翔云]
Marx’s Concept of Wage Minimum
Xie Fusheng,Chen Ruilin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subsistence wage; wage; wage minimum
Surrounding Marx’s Theory of Wage, there exists extensive debates and some deep-rooted misunderstanding in the academic arena. A review of Marx’s writings throughout his life has shown that his theory of wage undertook some substantial changes in his later works. Influenced by the Subsistence Theory of Wage proposed by classical economists, Marx failed to make coherent distinctions between several key concepts in his early writings, including labor versus labor power, and wage versus minimum wage. It was not until the first edition of Das Kapital did Marx manage to develop his own mature theory of wage and propose within the theory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concept of wage minimum. This fundamental change successfully distinguishes Marx’s theory of wage from his classical predecessors and helps to resolve the long-standing confusion raised by an indiscriminate treatment of wage and minimum/subsistent wage. In line with his Working Day theory, Marx’s concept of wage minimum is based upon the peculiarity of labor power as a commodity,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minimum wage policies.
*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号:11XNI012)的阶段性成果。
谢富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瑞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