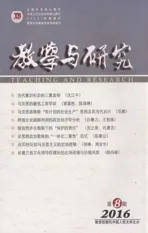当代意识形态的三重面相*
2016-02-04沈江平
沈江平
当代意识形态的三重面相*
沈江平
意识形态;哲学批判;话语体系;公共外交
“意识形态”一词曲折发展,被概念化、政治化、神化直至丑化、妖魔化,祛除学术包装和政治外衣,各种厘定粉墨登场。尤其在全球化、两种制度所谓“趋同化”的今天,有关“意识形态”的论调更是怪象迭出,文明取代论、终结论等不断混淆着人们的视听。哲学家往往对意识形态的至真旨趣怀有终极关切,人类学家则侧重意识形态的文化意蕴,政治学者似乎更愿意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功效即其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出现,经济全球化则赋予意识形态以国家利益的底色。哲学批判是理论的澄明,话语体系指向意识形态的国家治理层面,而公共外交则是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的话语呈现。如何把握意识形态在当下的真正面相,不仅是一个理论澄明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指导思想能否有效发挥其价值功能的实践问题。
英国学者迈克尔·弗里登曾指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意识形态概念成为最复杂、最可争辩的政治概念之一。”[1](P13)正因为意识形态用法多如魔方,人言人殊。学界对其理解和诠释侧重各异,考察的角度不同,其所强调的功效也就不一样。哲学家往往对意识形态的至真旨趣怀有终极关切,人类学家则侧重意识形态的文化意蕴,政治学者似乎更愿意从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功效即其作为一种话语体系出现。这意味着学界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多么五彩缤纷,多么兼容并蓄。意识形态不仅具有多面性,而且是块“白板”,学者们肆意地挥发其想象和创造力,给予其无穷色彩。但是,意识形态又不同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文化”等日常概念,它近乎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述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是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深层契合互动关系。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必须选取恰当的视角,一些研究者视意识形态为一种宣传机器和附着其上的思想言论,这往往是肤浅和欠考虑的。意识形态的研究必须拓宽视野,必须以总体的视角来考察。当然,无论意识形态这个术语如何“博大精深”,如何“变幻莫测”,从现实和理论的需要来看,我们可以从哲学批判、话语体系、公共外交政策的视角来审视、反思当代意识形态的多维内涵。
一、哲学批判
每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我们都会追问其时代的哲学主题是什么?俞吾金先生在《意识形态》一书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思考愈深入,就会愈自觉地汇聚到一个焦点上,这个焦点就是意识形态问题”。[2](P1)借用俞先生的话语,我们可以断言,21世纪的哲学主题依然离不开意识形态问题。当然,从哲学视角考量意识形态,并不等于只是对其一种哲学发展史的平铺直叙。哲学的视角将意识形态的源头搁置于哲学观念的变迁,但又离不开制度化意识形态的建设历程,其基本的道具是一种哲学式的审视和反思。
意识形态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联系密切,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必须承认。但“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个哲学概念……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讨论始终是从哲学的角度出发的,这既契合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本来含义,又便于从理论上作深入的探索和论述。”[2](P11)从哲学层面看,意识形态问题属于精神范畴。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精神现象是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的集合体和统一体。实际上,构成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东西,都深刻地镌刻在人们无意识的心理层面上,这种镌刻以一种现实和实践为基本尺度,承认与否,它都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哲学思考一旦进入到反思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它就不会是悬置于一些浮于表层的东西,而是深入到事物的本质中去了。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中的观念建筑,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看来,“经济方法”已经成为合理解释人类全部言行的关键点;同样,马克思也认为人们争取的一切都与自己的利益有着莫大的关系,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利益的衍生物,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意识形态因利益的出现而存在,因利益的发展而发展,它是利益的表征之一,脱离了利益,意识形态似乎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意识形态与利益密不可分,而利益又是人们对自身或他人行为以及事实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由此可以得出,意识形态能够借助利益这个中介来影响甚至支配人们的价值实现与评断。实践中,人们认同某种意识形态绝非依靠理论自身抽象的逻辑演绎,而是取决于意识形态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和牵引力上。因此,意识形态批判或对某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成为阶级社会中实践和理论塑造的重要一维,这种批判针对的是批判对象所承载的荒谬性、虚假性和反人民性;从学理逻辑视角颠覆批判对象,从而为在实践中击溃批判对象背后的阶级力量,推翻这个意识形态及其所庇护的社会制度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意识形态批判或对某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不必然意味着一种合理性或应当性,特别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当下,普世价值等西方意识形态理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从历史规律来说,这种批判就不具有必然性。
自我意识的主体地位随着近代以来认识论哲学的转向得以确立,但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过程中崇高价值的陨落,犬儒主义大肆盛行。原因不难分析,认识论哲学的转向使得人类桎梏于认识论的窠臼中来审视主客体关系,认知理性或逻辑理性取代整体理性狭隘化地把握客观的必然性,从而产生逻辑化的价值判断,现实的真理的目标遮蔽了价值的理想性,自我意识的迷恋不断膨胀,人的神圣性逐渐蜕化。哲学的泛逻辑化、实证化和科学化由此成为哲学认识论转向的现实产物,哲学走向思辨和科学化。哲学成为工具理性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认识论思维方式放弃了价值理性的追求,已经无法容纳和承担起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问题和意蕴的诠释,在认识论的框架内,人类对美好和价值的追求、抉择、创造、发展和实现已不再具有可操作性。随之而来的哲学人本学转向,人的生活世界成为关注的焦点,意识形态由此也开始转向生活世界,人类开始在生活世界中找寻生存与发展的价值和意义。这是因为,意识形态触及了世界的统一性和历史的规律性问题,这事关哲学的基本问题,有关一元世界观、历史观的合法性问题,当然也包括其所衍生的两大形而上学关系:理性与欲望、幻象与实在。[3](P14)意识形态蕴涵着虚假与科学因素,片面绝对地放大其否定面,忽略其科学理性的一面,必然导致意识形态所蕴涵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的迷失,从而导致对世界和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的可能性的抛弃,结果必然是由相对主义走向虚无主义和主观主义。从个体层面而言,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在于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和批判。意识形态的生存论视角分析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意义所在。生存论产生的主体——人,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始终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理论的产生离不开人的创造,意识形态自始至终围绕着人,它的发展也离不开人,意识形态作用的主体是人,脱离开人这个元素的意识形态是不存在。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产生于人类社会,并且对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始终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存在,它来源于人的意识,从意识中不断发展,慢慢地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从而起着影响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作用。人是意识形态的主体,离开这一主体,意识形态这个范畴将无从谈起。
意识形态的存在论转向造就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对一切旧的意识形态的虚假的总体性的破除,又是对现实存在的总体性的真实阐明。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马克思批判了包括德国意识形态在内的旧的意识形态批判,实现了对以往旧哲学的批判的扬弃。在过去,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世界支配着现实世界,一切存在物似乎都是意识形态的“副产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现实世界才是思想世界的真正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也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是其哲学批判内核所在。特拉西对意识形态在观念学意义上所作的理性科学的断言,德国古典哲学在意识形态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认知,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实践对意识形态认识论的科学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生存论的生命思考,都努力去追求一种真善美的终极价值关怀。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人们开始重新、全面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也引发人们对意识形态符号学物化的社会关系考量,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存在论的实践转变。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理论的哲学批判,为当下纷繁复杂的各种意识形态思潮提供批判的理论武器和方法支撑。唯有如此,人类才能由抽象的本体论层面向生存论的本体论视角转换去探讨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意识形态问题,才能真正从认识论层面解决意识形态对人类思想世界的支配问题,从而实现马克思毕生所推崇的彰显人的价值理性诉求的实践精神;才能消解存在主义对意识形态终结的误读,进而深入探求人类的社会性存在的无意识领域的意识形态问题;才能祛除符号学的非历史的意识形态立场,在现实批判基础上创新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有着其本身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只有重新确认历史唯物主义在意识形态认知领域的应有地位,才能克服以往旧的意识形态与生活世界隔离的形而上学的弊端,从而在社会存在的现实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备“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功能的意识形态。这种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质的意识形态学说具有明晰的元批判导向,这也是真正理解哲学的真精神,领悟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批判和哲学变革之所在。
从哲学的理论高度和思维视角介入考察意识形态,既是意识形态范畴伊始就以观念论的科学面目出现的结果,更是特拉西意识形态观念化走向破碎的现实使然。尤其对于马克思哲学而言,这种哲学的实践特质无法接受意识形态范畴停留在观念论的窠臼里沾沾自喜,物质利益的困惑促使他走出书房,他的哲学也从抽象王国向现实王国行进。意识形态范畴从意识层面向道德层面直至利益层面的转变,表明了意识形态范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引导下与人类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在今天,我们同样需要马克思的这种哲学批判下的思维方式和考察视角,用它来对意识形态进行审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中被系统化为一种群众运动的学说,政治因素逐渐成为意识形态的主导性要素。随之而来的种种非议更是推波助澜,加剧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解的分化、迷惑和误解。诸如“意识形态终结论”、“非意识形态化”、“虚假意识”、“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观点逐一登上历史舞台。当曼海姆从马克思视角出发赋予意识形态以“利益集团的思想体系”的意蕴时,当列宁用“社会意识形式”来指称意识形态时,以上观点和行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拓展还是背离?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在马克思那里实现了命运的根本转向,但由此附着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诸多解读同样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就需要一种意识形态的哲学批判和自我批判的精神。正如德里达所言:“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吸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构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那就是一种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的步骤。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阐释的。”[4](P112)无论是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意识形态理论,哲学批判与自我批判不可或缺。
二、话语体系
诚然,作为哲学概念的意识形态,本质上而言是概念形态,但其现实利益的特殊属性使得意识形态充满了现实的因子,不仅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里,更是国家治理中无形力量的一种较量。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有这样一段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P591)很明显,马克思分析社会结构所依赖的方法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能够系统地、自觉地、直接地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制度,是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观念上层建筑的部分,其形式包括法律的、教育的、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艺术的或哲学在内的社会意识形式。马克思由此得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6](P550)马克思告诉我们,在生产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阶级,必然要求其对观念上层建筑的话语言说的主导性,无疑,意识形态成为其话语的主战场。
“话语”该当何解?话语是语言符号和价值观念的统一体,它既是一定的符号、概念、词句、语音、语法等要素构成的语言符号,同时又反映了特定的认知、情感、意志。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7](P15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话语关系直指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这种关系与一定的制度、时代所构建的总体组织起来的话语集群,它由某个处于支配、统治地位的集团、权威主体发出,在特定的话语关系体系中往往被披上真理性、全民性的陈述特征。依托话语,个人或社会组织能够获得某种认可和承认,从而确立起其社会存在中的地位。作为解释和理解世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现实世界中,话语实质上还充当着掌控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武器。话语中立则对社会有利,话语垄断则危害社会。所以,现代国家大多以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以限制霸权话语,使话语处于有序竞争状态。言说者的权威性和内容的可信性是话语体系得以建立的前提。一般情况下,一定社会中处于权威者和可信度较高的群体通常居于统治阶级内部或所谓精英阶层,这个群体的思想往往表现为社会的指导思想。正常情况下,统治阶级的思想或意识形态指导和支配着人们向着共同的目标前进和奋斗。
意识形态与话语体系有着天然的联系,话语体系的确立主要体现为意识形态的争夺。作为价值观念的理论载体,任何意识形态都具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虽然这种反映真假还有待确认,同时它还具有社会规范的功能。而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在生活实践中往往以话语体系为载体,对人们的生活经验和社会心理进行筛选,既有对外部的同化,又有对外部的顺应。任何阶级、集团都有代表其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的意识形态,为了实现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控制力,就必须主宰和支配话语体系,尤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集团,话语体系的确立和运用是其意识形态得以操控和掌握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前提。表象上,话语体系以话语为载体,但真正激发话语体系效能呈现并产生权力的密码在于话语背后所依赖和蕴藏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要素。作为阶级意志表征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还是非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它们都是最大限度、最为集中地凸显出特定阶级、集团利益主体的意志和利益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必然要对它们所处特定社会形态的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本质、规律、社会结构、权力架构及具体运行规律等问题进行探究、评判及扬弃,据此,实现对社会走向和理想形态的应然性价值追求和思想纲领的锻造。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往往力图借助与国家权力和统治阶级的契合来塑造出管理和统治社会的软实力,渗透和制约着其他文化形式的存在和发展,与其他文化形式一起形成总体合力,制约和规范着其他文化形式一起为主流意识形态管理社会提供智力和思想支撑。所以,现实社会中话语体系的确立常常与意识形态主导权争夺密不可分。
意识形态功效的发挥必须以话语体系为载体。意识形态对社会生活发生的直接作用,需要依靠话语体系的普及。一定的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必然在社会上形成相应的话语系统,用以解释、传播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者“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6](P537)意识形态功效的发挥并非柯林伍德所言的“自我——授权的”[8](P268-269)脱离自身以外的权威起作用,最终得依靠意识形态自身的权威性和可信性或科学性和真理性。意识形态的这些质的属性又必须借助一定的外在形式来表现和运行、生效,因此,话语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从常识看,话语体系除了借助语言的表达功能外,脱离不了运用语言的主体及其实践,脱离不了社会—历史的理解框架,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而必须搁置到一个更为广泛也更加深入的领域中去领会和探索,这个领域便是话语的实践、运行环境。话语是社会化了的语言,而语言本身在马克思看来就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6](P533)话语体系是整个建立在“现实生活的语言”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话语体系的生成与兴盛、持续与衰落,是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特定主体的实际生活过程及其语言现象的或者较为接近抑或较为遥远的结果。而这恰恰是意识形态最为贴切和最直观的依存载体,特定主体的实际生活过程及语言现象过程必然地蕴含着代表其利益和价值诉求的思想观念,当这种观念借助一定的模式表达出来时,就充当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可以看出,意识形态要运行和兑现其旨趣,话语体系是其必经之路。意识形态在当今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具隐蔽性,尤其是以西方价值理念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润物无声”,其语言平和,往往不再直接攻击与之对立的意识形态,相反借助现代性、进步性、时代精神等内容“传递自由世界信息”。可见,随着时代的变迁,意识形态借助话语体系的言说方式、内容等都要与时俱进。话语体系的任务是要不断对从属于社会存在主观意识对现实实践的反思进行最坚决的维护和推进,并从这种维护和推进中宣示其所处社会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随着以上进程的践行,意识形态赋予话语体系的光荣使命也随之告一段落。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成为与资产阶级对抗、直至最终取代其地位的话语体系,除了其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价值理念之外,最根本的是揭示了反映了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般性规律,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着人们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并最终走向共产主义。从全球视野看,马克思主义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同样,其意识形态功能的发挥也遭遇诸多理论思潮的冲击、围剿。应当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越来越趋向学院化,崇尚思辨和建构体系,其后果是逐渐远离生活而日益被生活疏远。因此,如何促进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关联,增强其关照现实的话语权,是一项亟待解决的任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彻底、崇尚实践的理论,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学术话语体系,承载着引领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即意识形态属性。由于国际共运事业曲折发展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攻击等原因,马克思主义面临巨大挑战。西方话语霸权挤压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空间,“西化”、“分化”、网络化的负面影响以及多样化社会思潮严重削弱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的功能。掌握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构其行之有效的话语体系,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必然要求和现实任务。显而易见,意识形态话语权问题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研究中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需要理论界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展开深入研究和进一步探讨。只要人类依存于阶级社会之中,意识形态领导权或话语权之争就不会停止,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三、公共外交
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面相在面临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时就表现为公共外交。翻开人类的历史,意识形态的魔咒一次次被打开,其踪迹若隐若现。自从国家出现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往往镌刻着意识形态的身影。尤其是近代社会,两次世界大战、民族解放运动、东西方漫长而冰冷的冷战、恐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多种形式的民族主义无处不显现着意识形态忙碌的影子。各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意识形态对界定国家利益有重大的影响。本质上而言,意识形态是看待世界的一种思想体系和系统化的观念,它是对现实世界的主观反映,有真实和虚假之说。或者它被认为“是指解释一个社会的系统方法,它或者为这个社会辩护,或者批判这个社会,成为维持、改造或摧毁这个社会而采取行动的依据。”[9](P9)据此来说,意识形态具备其他思想文化没有的信仰力和刚性的与生俱来的先天指引力,能够解释其他一切现象的出发点和旨趣缘由。除此之外,卡尔·曼海姆还认为意识形态的特殊含义可以作为一种策略和战术,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当意识形态“这一术语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那些观点和陈述被看作是对某一状况真实性的有意无意的伪装,而真正认识到其真实性并不符合论敌的利益。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10](P56-57)由此看来,意识形态在公共外交政策中的表现,主要是凝聚本国社会成员的向心力,保持同步性,给自己的政策披上一个神圣的光环的同时掩盖自己的真正政策意图。美国学者艾尔登认为,“就像在国内政治中一样,在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通过提供被广泛接受的价值观,不仅对决策起着约束作用,而且还发挥着创造性的作用。”[11](P23)
丘吉尔在论述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无论从历史经验还是现代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来看,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政府所作所为的思想价值基础或对此做出的解释,国家内政及公共外交都脱离不了意识形态的干预。在道德和法律等层面,意识形态能够对对外政策进行包装和粉饰,统治阶层正是青睐于此,通过意识形态来使国家对外政策显得合理和正义,公共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意识形态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和具体展开。就像迈克尔·亨特所说,“忽略了意识形态,想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可能遗漏关键性的一步。……只要试图对美国如何进入国际政治的密林,或者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进行深入的探讨,意识形态都占据着显著地位。”[12](P5)从他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与意识形态的密切联系来看,毫无疑问,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亦是如此,在制定公共外交政策时,意识形态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但是,重视意识形态对公共外交政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时刻都决定和支配外交政策,正如丘吉尔所言,现实利益才是外交的价值追求。事实也证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暂时搁置差异,共同处理面临的世界性难题。意识形态特有的政治性、利益性、立场性、价值性对国家之间公共外交的影响是微妙而复杂的。意识形态给国家行为制造了必须参照的精神坐标和行为准则,并依靠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诠释,维护国家公共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合理性、神圣性的价值存在,以求国家或国际社会的认同。意识形态已成为国家外交的一种“低代价、高收益”的软资源,约瑟夫·奈称之为“一种无需要投入过多,相当有价值的软文化力量资源。”[13](P16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已成为影响国家对外关系性质与走向的重要因素,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予以重视成为各国政府的普遍共识。冷战期间,“两种意识形态都为双方宣传的使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相互攻击信奉不同意识形态对方的意图。”[14](P242)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成为“外交中的第四手段”,意识形态外交继续着冷战思维,“人权外交”、“民主外交”、“新干涉主义”等外交模式无一不充斥着意识形态的背影。
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态势趋于稳定,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思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日益抛弃了原有的存在方式和表现态势。全球化使人类的共同精神文化财富和共同的价值观念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多,同时,民族间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也越来越突出。文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受到重视,文化的输出方式和表现形式由于交流的不断扩大和传播媒介的技术化也显现出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意识形态在当今人类社会也日益表现出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存在样态和显现方式。目前,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处于相互承认但又相互竞争、斗争的状态,制度上的对立和意识形态的对抗一直存在。这种对立和对抗不会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而消失,虽说两制关系“共处——对抗”模式已被“共处——竞争”模式所取代,但西方凭借其“强势”地位,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条件”的援助,相反强度愈发加深,只是方式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围剿浪潮源源不断,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帜在世界各地推广其意识形态,宣扬其价值普世性,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所谓民主革命不断出现。
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及其“游戏规则”主导和操控下进行的,这就表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表征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张、传播的过程,即“资产阶级国内意识形态阶级性的国际化”进程。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性是个不争的事实。当然,判断国家对外政策的实质“不应仅仅在意识形态的性质中去找,而应在一国对外政策的各种决定因素的总和中去寻找”。[15](P137)而“各种决定因素的总和”正是存在于现实的历史关系之中,这应当是明确了解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之间联系的核心。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6](P29)意识形态这个范畴也不例外,“用意识形态作为对外关系准则,其实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它经常会用来掩盖其实并非意识形态的意图”。[17](P11)意识形态作用于公共外交政策除了必须与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结合外,还必须充分考虑本国与他国国情。也就是说,没有超越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可以有灵活的作用方式。一个政府国家意识形态确立后,必然要求有与国家意志相对应的外交政策。但是,在不同时期,外交政策可以随现实实践不同而改变。意识形态可以是恒定的,但外交政策无须不变。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延伸,更是现实利益的转换。在现实利益面前,实用主义往往大行其道。美国从来都是实用主义的先驱和坚定执行者,因为美国明白“实用主义帮助政策的制定者有可能保持最大的灵活性,避免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诺而超过限度,把外交努力集中在特定的利益上,承认严酷的现实。”[18](P113)邓小平认为,“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19](P353)现实也表明,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坚持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扩大了我国的外交空间,从而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
斗争除了军事手段外,思想的手段往往走在舞台的荧光灯下。这样,意识形态问题就理所当然地展现在人类面前,并一直伴随人类自身。当下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对抗处于次要地位,但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不重要或不需要。从现实来看,某些国家和局部地区,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依然存在,某些时候甚至强化和突出。两种社会制度的存在也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斗争还在继续,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斗争方式日益变得隐蔽化、多样化。无论一国政府其外交政策如何,人们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时,可以搁置意识形态差异,但不等于抛弃意识形态、放弃原则。事实证明,对外交往中,我们只有坚持国家利益,充分考虑别国实际,抵御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防止西化、和平演变。因为两种制度对立的局面并没有改变,某些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依存,只有在坚持国家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尊重差异,积极扩大交往,最大限度地为我国和平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实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发展,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
结 语
传统的以信仰、价值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受到各方的批评和质疑,但不能因此附和甚至宣扬意识形态的缺场。漂浮在意识形态矩阵中的人以及他们的意志由于无法依据个人理性对各种意识形态内容的真伪做出准确分析而容易在意识形态的迷雾中迷失,并最终对现实做出错误的判断。意识形态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新问题。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和划分肯定不止于此,对于这样一个概念,从任何一个视角来界定言说意识形态都不为过。传统的意识形态理解可能更多的是纠结于科学与虚假之分,事实上,现实的发展迫使我们用更为开阔的视野来考量这个概念。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论证下成为现实利益的表现,从根本上扭转了以往从纯观念的视角来解读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倾向。从此,意识形态观念不再不食人间烟火,从神圣王国回归世俗世界,实践、现实、利益成为支撑其存在的根本。在构建中国精神家园和以期实现中国梦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多方面的功能,它既可能是反动阶级落后的虚假的意识,也可能是先进阶级动员民众的号角和与敌人斗争的锐利武器。我们必须以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眼光加强和推进当下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和创新,建立一种自我完善、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机制,积极整合意识形态和民族意志的对接,凝聚民族力量,这些都是全球化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亟待解决的课题。
[1] Michael Freeden.Ideolog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6.
[2] 俞吾金.意识形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 侯惠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与当代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4] 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王治河.福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8]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9] 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M].杨祖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10]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1] Edward H.Alden & Franz Schurmann.Why We Need Ideologies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Democratic Politics and World Order(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1990)[J].Policy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Number 37,1990.
[12] 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M].褚律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13] 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14] 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5]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M].时殷弘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18] Joseph Frankel.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45—1973[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19]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孔 伟]
Three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Ideology
Shen Jiangp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ideology; philosophical criticism; discourse system; public diplomacy
The word “ideology” has experienced tortuous development. It is conceptualized, politicized deified and even demonized. In the globalization in which the two systems are converging today, the argument of “ideology” is constantly confusing people’s minds. Philosophers tend to have the ultimate concern for the true meaning of ide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focus on the cultural implication of ideology. Political scholars are more willing to study the effect of social mobilization of ideology. The critique of philosophy is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theory, while the public diplomacy is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ideology in the foreign policy. How to grasp the real face of ideology in the present is not only a theoretical clarification of the problem, but also is related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the guiding ideology can effectively play its value functions in practice.
*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思想史视域中的意识形态研究”(项目号:15ZXC018)和北京市社科联青年人才资助项目“微时代意识形态认同研究”(项目号:QNRC201609)的阶段性成果。
沈江平,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