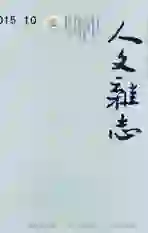空间下沉的隐喻与逻各斯的重建
2015-05-30李红章
李红章
内容提要在马克思的哲学叙述中,存在一种空间性的隐喻,它与古希腊哲学、甚至基督神学保持着叙事上的张力。马克思以空间的下沉指明了无产阶级的现实遭遇,也透显了后者在社会历史上的载体、根基品质,暗示了一种新唯物主义的叙事可能。在这种叙事中,马克思以对社会阶级锁链的批判,回应着古希腊哲学中存在巨链的隐喻,重新演绎了宿命论和生成论的辩证法;而对于基督神学的巴别塔隐喻,马克思重新解读了革命叛乱与语言混乱的现实意蕴,展开了对意识逻各斯(即意识形态)之普遍语法的解构与重建,开始了新的哲学叙事。马克思的这种逻各斯革命是在新的救赎叙事形式下完成的,无产阶级以复数的形式成为了英雄整体。充满张力的叙事使得马克思文本呈现出令人困惑的属性,这正是在思想的逻各斯革命阶段展开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的。
关键词空间隐喻逻各斯存在巨链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5)10-0021-06
在马克思的哲学叙述当中,始终能够感受到一种空间性的隐喻。这种空间隐喻不仅体现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构建中,还弥漫在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之使命的整体论述中。在这种空间下,马克思的哲学还与古希腊哲学、甚至基督神学保持着一种叙事上的张力。其笔下的无产阶级,在新的空间转换中,解构以往的意识形态话语,以新一轮的意识逻各斯重建,接续着落寞与归来的新哲学叙事。
无论如何,把无产阶级对照于神话、传奇的人物,总不免引起警惕,甚或有“谋取支持”的嫌疑,但以本雅明将弥赛亚精神与马克思哲学相对应为肇端,比较哲学在为理解马克思哲学文本开辟了新的途径。无论如何,他者的文本总是透视文本本文的一面镜子,不管这面镜子自身是否拥有绝对的忠实,但其提供的视角总是重要的。
一、空间的下沉与存在的巨链
如同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观念,即原子的“下落”构成了现实的世界,马克思哲学的文本在其叙事策略上也有一种“空间下沉”。这种下沉指明了无产阶级的“下落”状态,也呈现了其遭遇的历史现实。除此之外,居于空间之底层,还透显出一种回归根基的哲学隐喻——无论是作为生存第一要务的“物质生产”,还是革命手段的“物质武器”力量,无产阶级以其“底层回归”回应了那种“基质(Substratum)是本体”的哲学论断。在日后被称作新唯物主义的哲学文本中,马克思以“物质生产”震荡了“物”的概念内涵,以新的载体、基质或根基的隐喻,构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
“空间下沉”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在古希腊的空间观念里,如学者吴国盛的考证,“万物皆在处所中,不在处所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因此,处所具有先在性。”吴國盛:《希腊人的空间概念》,《哲学研究》1992年第2期。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空间的先在性同样存在。与近代科学的与物无关的绝对空间不同,这种空间恰恰总是与无产阶级发生内在的关联,它既不是抽象的也非空洞的。无产阶级必须在一个被重新认知的空间世界找到自己的位置,空间不是外在于它的无干的媒介,而是身份的隐喻。
在古希腊原子世界的空间中,“一旦原子转入了现实界,它就下降为物质的基础”,而无产阶级一旦进入了社会现实界,同样也“下降为物质的基础”。这暗示了一种新唯物主义的叙事可能。无产阶级与原子有一种隐喻的“互映”,并且一如后者,无产阶级也是“充满多种多样关系的世界的承担者”。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33页。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指出原子的这种“空间下沉”并非独立性的运动,他称赞伊壁鸠鲁“以原子的直线运动表述了原子的物质性,又以脱离直线的偏斜实现了原子的形式规定”,并援引卢克莱修的话,认为“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③马克思这种看似抽象的评价,在日后的新唯物主义叙事中越发透显出明确的现实意蕴。
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有两项隐喻式的空间处理,一个是下沉,一个是颠倒。无产阶级身份的空间下沉,对于马克思来说更主要的是一个状况的“承认”,而不是对地位的“承诺”。之所以不承诺在于,空间的“下沉”总是呼应于空间世界的“颠倒”,后者不具有合理性,因而不值得承诺。当德国已经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接下来的哲学任务,马克思认为当像费尔巴哈一样,“从思辨的天国下降到人类贫困的深渊”,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64、3、4、16页。这种下沉在于“谬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之后 ,新的任务就必须回到“人间”。而处于上层的宗教已经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映像,如同镜子一般,是“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 ⑤
不管是面对神圣天国的颠倒影像,还是“底层回归”的空间下沉,“先在”的“空间”总是显示了一种判若云泥的境况差异:相对于统治阶级的“高高在上”,无产阶级总是占据着“下降”的政治地位和“下降”的经济状况,无论如何,工人阶级总是处于“最底层”,甚至在文化意识形态上,它都处于一种低劣的位置。
2015年第10期
空间下沉的隐喻与逻各斯的重建
因此,“下沉”具备了两重的意味,一重是作为现实根基、载体的“可能性”;另一重是身份低劣的“现实性”。然而被统治阶级的遭遇总是由意识形态话语笼罩,结果恰恰是第二重的意味被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希腊传统的空间哲学就为每一种物质要素安排了合理的位置(Topos),不但如此,物质要素还分别按照层级的区分以梯度的形式在空间上排列。其中有如阿那克西米尼的气本原说,认为一切事物都由于气在量上的差别而导致;气的浓厚与稀薄的性质差异,决定了其形成各种不同的东西,各自都拥有各自合理的处所。亚里士多德构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存在之链(Great Chain of Being)。存在于世界之中的生物,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序列或者自然阶梯(Scala Naturae);而在后来的阿奎那笔下,宇宙也被描述成一个由事物构成的完备等级序列。
存在之链的精神奥秘体现在现实的政治中,无产阶级的空间下降总被套上一层宿命论的隐喻,于是马克思从自然的“阶梯”转向了社会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位置或处所被指认为合理的现实,这种现实被一种叙事话语系统笼罩,透显出“本质先于存在”的思维框架。正因此,在马克思的叙事策略中,这种话语系统被其反指认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正是这种颠倒的世界所产生的幻相。
“存在之链”在政治上表现为“阶级之链”,这种链条既是现存秩序的合理性链条,也是使被统治阶级陷于困顿的枷锁,于是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撕碎锁链上那些虚幻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⑥马克思在空间上做出了新的指认,“如果不是由于自己的直接地位、由于物质需要、由于自己的锁链本身的强迫,是不会有普遍解放的需要和能力的。”⑦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处在一个最低级的空间,才有可能有打破这一困境的欲望和能力,正如赫拉克利特认为的一样,灵魂只有摆脱潮湿泥泞的底层,拥有“干燥的光辉”才能成为“最智慧,最优秀的灵魂”,[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9页。它浮升到干燥而光明的顶层,要成为“共同意识”或“逻各斯”。而占据这样领地的,自然是目前无产阶级遭遇的意识形态,马克思正是要击毁原来的“idea”和“logos”即意识形态(Ideology),使逻各斯成为“活火”,有死亡方有生命,有生命才有死亡,空间的下沉也正所谓“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既可以为保守势力做论证,也可以成为革命的基础,表现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则成为一种宿命论和生成论的张力并存现象。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方面事物本身拥有内在变化的动力,一切运动都有既定的目的归宿,甚至在这一切的制动背后,有一个更加终极的第一因。目的因被他看作一切生成变化的最高原则,任何事物都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生成或者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质料总是事物的原始载体,事物绝对地由其生成,并继续留存在事物之中。
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无疑拥有着物质载体的性质,基于这种物质力量的空间处所,马克思指出了这个存在之链上的阶级等级,而要以解构现有意识形态的方式,以新的生成论,去打破原有的宿命论,彰显新的历史前景。要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6~17、550页。在这个基础上,“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5页。
二、語言的混乱与逻各斯的重建
打破存在的等级,打破存在的锁链,任务是繁重的。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宿命论与生成论的张力,一直存续于后世的哲学之中。对存在之链的认可与论证,是哲学相当强大的传统,诚如马克思的老话,“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④《存在巨链》的作者诺夫乔伊在考察整个西方思想史时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关于终极价值的假设与关于世界之构成的同样的一些假说结合在一起,而又与别的同等流行的关于善的概念相冲突。”这暗示着似乎不止一条关于等级的秩序存在链。但也恰恰接下来,诺夫乔伊又继续评论道,“这种价值观念,和关于宇宙是‘存在之链这一术语所蕴含的东西的信念一起,为解决恶的问题以及揭示事物之图式是一个可以理解的和理性的图式的大部分较为严肃的企图,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美]诺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作者前言第5页。
无论如何,历史上总有打破这种等级之链的欲望与尝试,然而这种对等级的解构与超越,又总是困难的,诺思洛普·弗莱记录了一个印第安部落中的民间故事,显然是一个失败的案例:
从前“天上的人”与“地下的人”发生了一场战争,地下人显然是指动物。地上的禽兽,通常传说是一只鹪鹩,一箭射中了月亮;另一只鹪鹩射出第二支箭,恰好击中头一支箭的尾部槽口;这样一箭又一箭地,终于造起一个由地面通到天上的梯子。这时地上的动物纷纷往上爬去,后因灰熊的身体太重把梯子折断了。[加]诺思洛普·弗莱:《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吴持哲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
“地下的人”与马克思笔下“空间下沉”的无产阶级的情况有些类似,但是文风不同,采用了悲剧式的叙事形式。“沉重的肉身”把向上的力量抵消了,“人为”的弓箭构建的天梯,没有抵抗过“自然”存在的巨链。在两条对“善恶”的不同指认的巨链上,地上的动物失败地重新回到了宿命论式的空间场所。
宿命论隐含着对既有秩序的认可与保守,而哲学家常常在以个人的形式言说着这种世界秩序的合理性:比如在莱布尼茨看来,实质的世界总是有着充实性、连续性和线性等级的存在。他指认了世界的成分乃是单子,这些单子构成了庞大而有序的存在之链,从最低级的有生命感觉的层次,一直到达上帝的所在。没有完全相同,却总有高下之分,“一些等级的单子或多或少地统治着其他等级的单子。”[德]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在上面诺思洛普·弗莱的故事里,“地下的人”终没有能打破存在巨链,各自仍旧回归各自的场所,如果在莱布尼茨看来,当纯属预定的和谐所致。“实体全都是为完成上帝的计划而协作。”②④[德]莱布尼茨:《莱布尼茨自然哲学著作选》,祖庆年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83、84~85、8页。与“天上的人”发生战争注定是失败的,“在所有实体中都存在着力是千真万确的,但正确地说,这些力只存在于实体自身中,而在其他的实体中,跟随力而发生的只能依靠一个前定和谐。”②
与诺思洛普·弗莱的例子相仿,但有微妙的不同,德里达论述了一个“巴别塔”的概念,后者言说出了更多的东西:
巴别不仅指变乱一词的双重含义,也指父名,更准确更普遍地说,是作为父名的上帝之名。这座城市将采纳上帝圣父之名,和被称作变乱的城市的父亲之名。上帝,特有的上帝,将以父名标志一个公共空间,即那个城市,在那里,理解已经不再可能了。一旦只有专有名词,理解便不再可能;而一旦不再有专有名词,理解也不再可能。由于命了名,他所选择的名,所有的名,父就成为语言之源,那种权力应当归于圣父。圣父之名将是那个语言之源的名。但也正是上帝,在他愤怒的行为中(如伯姆或黑格尔的上帝一样,离开自身的、将自身限定在有限性之中、因而生產历史的上帝一样),取消了语言的才能,或至少使语言陷入混乱,在他的后代中播下了混乱的种子,毒害了当下(Gift-gift,毒品-才能)。[法]雅克·德里达:《巴别塔》,载《论瓦尔特·本雅明:现代性、寓言和语言的种子》,郭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9~40页。
在这里,德里达敏锐地看到了存在巨链上的悖论处境之实质问题,如果说“地下的人”打造“弓箭天梯”是一个从上到下构建“新秩序”的尝试,那么巴别塔则是一个从下到上的“建筑案例”。并且,前者是因为地下人的沉重的肉身(即革命者本身的问题)而不能完成革命,那么后者则侧重表现因为语言的冲突而导致的交往无效性。
德里达呈现了“地下的人”失败的真实原因,在于“巴别”概念的双重含义,即“叛乱”和“作为父名的上帝之名”,这里有着矛盾的张力。是遵循一种预定的和谐,依附于父亲般权威的存在巨链;还是解构这个存在巨链,打破和谐,完成革命的叛乱,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更重要的,德里达还指出了“父”“上帝”本身就是“语言之源”,一种关于等级的逻各斯,而当人们打算通达天庭的时候,“父-上帝”则使语言发生了混乱。
这种意象表现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关于意识形态(Ideology)的问题,即意识的逻各斯。来自地下的(即马克思意义上的下沉空间)的语言只能是混乱,而唯一神圣的语言只能是上帝的逻各斯,后者在现实社会的化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显现出了无产阶级的困难遭遇。早期的马克思展开了对语言或者逻各斯的批判,这表现为他投入了大量的笔墨展开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
语言或者逻各斯的批判当然不止于此,马克思后来转向了对资本的现实批判,而这同样延续着一脉相承的思路。资本的批判离不开数字的计算,马克思对于逻各斯的批判也因之进入了计算领域。传统上与此相照应的,则是莱布尼茨对“普遍文字”的追索,他把逻各斯归结为数学语言,认为“一旦我们占有了事物本身的真正的特征数字,一个证明是否实质上是确定的,就可以第一次得到判断,而没有任何困难,也没有陷入谬误的危险。”④数学似乎代表了一种普遍真理路径,一旦把对世界的理解上升到数学,那么就算是得到了真理性的确认。
于是,对于关于数字的普遍文字,一种真理化了关于意识的逻各斯(即意识形态),马克思表现出了强烈的对抗精神。在针对价值问题的数字计算问题方面,马克思证明了数字作为一种普遍文字之不能成立。他摈弃了传统的以工换酬的计算原则,将工人的劳动划分为有偿与无偿,“工人每天的劳动只有一部分是有偿的,另一部分是无偿的,这无偿的或剩余的劳动正是产生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基础,但是看起来就好像全部劳动都是有偿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页。马克思甚至重新设定了一种关于价值、利润的算法,展现了完全不同的核算结果。如其所言,“在我以后的说明中,我将使用利润一词来标明资本家所榨取的剩余价值总量,不管这剩余价值究竟如何分配给不同的人群;我在使用利润率一词时,则总是用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价值来测量利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数字的逻各斯批判只是一个案例而已,背后勾连的是马克思对资本的整体批判解读,马克思对意识形态之逻各斯的解构是全方位的。问题只是,与后现代哲学上对概念本身的解构不同,马克思恰恰是在继承了概念本身之后,对概念加以内涵的震荡。无论是哲学意义上的“物质”“存在”,抑或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利润”,甚至是单纯空间范畴上的“上”与“下”,马克思都在自己的文本里完成了接续,但是却彰显着不同的意蕴。这种变化不是外形上的,而是内在的,总之,如詹姆斯·法尔的观念:“语法的演进不只是一个狭义语言学或概念问题,而且也是个政治问题。因为概念与信仰、行动与实践齐头并进且共同变化。理解概念的变化主要是理解政治的变化,而理解政治的变化则主要是理解概念的变化。而且这样的理解具有历史必然性。”⑧[美]詹姆斯·法尔:《从政治上理解概念的变化》,《政治创新与概念变革》,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第20、30页。
三、空间的还原与世俗的救赎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内涵式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面对巴别塔式的语言混乱,马克思把任务聚焦于意识形态之逻各斯批判,以一种新的语言系统与之对抗。当洛维特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国民经济学语言的救赎史”⑦[德]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53、52页。的时候,他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文本的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救赎。只不过在于,前者是内涵式的革命,后者道出了形式上的接续。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品质对照于神话、传奇的救赎人格,并不仅是形式上的“谋取支持”,而在于“救赎”采取了新的语言:“下层的空间”对“顶层空间”的反叛,是在新的语言系统框架内,并以“颠倒”为语法意象来实现的,如马克思所言,“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8页。海登·怀特把这点表述为,他“试图做的是提供一种分析方法和一种表现策略,它们将允许他以一种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语态来写作历史。”[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50页。在空间颠倒和语法颠倒之后,“救赎”方成为可能,马克思指明——无产阶级将“知道自己是绝对自我意识的主体,就是神,绝对精神,就是知道自己并且实现自己的观念。”⑥
于是,洛维特的下一个表述也在这种语境下变得可以理解,他说道,“只有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意识中,全部历史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种观念背后的现实的推动力是显而易见的弥赛亚主义,它不自觉地植根于马克思自己的存在之中。”⑦马克思要接过并解构神学、宗教的语言,使现实世界的无产阶级完成自己的“救赎”。
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与“神”“绝对精神”进行了概念上的对接,更换了语言行为的主语,这由此造成了无产阶级在新的空间隐喻中的上升或还原。通过这种空间上的“起伏”,马克思试图瓦解原来来自上层力量造成的语言混乱,而以新的秩序语言重新对历史进行了表述。他改变了社会历史上存在的既定的概念,使新的社会问题以新的形式得到了“再逻各斯化”。不但要使原来的存在巨链走向瓦解,而且要在概念或思想语言的意识巨链也得到瓦解。之后,新的概念将展现出另一番空间景象,如詹姆斯·法尔所说的,“一旦被重新概念化,有些问题就引起新的理论,而新理论重新概念化那些问题,如此继续……它复兴了那使论证和问题相一致的古老概念,这些问题以这样的方式与论证相对立,这种方式既改变了论证也改变了论证的问题——通常也改变了言说者们自己。”⑧
等级与救赎的观念,来源于希腊—希伯来文化传统的情怀,它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内化在文化的传承里。对于西方文化传统来说,无论是神话体系,还是宗教,抑或英雄传奇,都是这种文化本身不可缺少、而且极具特色的思想模式,涤荡掉马克思哲学文本中这种古老的文化结构底蕴,将会丧失掉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必要性。任何的对神话、宗教和传奇,一方面自有其虚假的意识形态特性;另一方面又深深内化于西方文化的叙事结构传统之中,詹姆逊的评语不失公允,他认为将“马克思主义与传奇相联系并不怎么影响前者的声誉,因为它解释了后者的持续性活力,……后者是一切故事叙述的最终源泉和范式。”[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92页。
在新的历史叙事话语中,无产阶级进入了一种传奇性话语体系,使得自己成为自我成就的英雄。而更重要的,无产阶级不再是以往的作为个体人格的单数英雄,而是以复数的形式成为了英雄整体。在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既是一种革命者,又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继承者,如同马克思自己的感受,“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连自己都不清楚的神秘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还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那时就可以看出,世界早就在幻想一种只要它意识到便能真正掌握的东西了。那时就可以看出,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最后还会看到,人类不是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10页。
总之,形式的终归是形式,将其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检点出来,做出必要的疏离是政治上的实践话语策略使然,这一点在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中同样随处可见。问题只是不应就此忽略掉马克思对西方文化传统的深层接续。马克思哲学文本的结构,通过空间隐喻的展示,与这一西方传统因缘颇深,而作为时代之精神,马克思哲学文本“形式持续性有别于它为适应社会环境而产生的变化。”[加]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吴持哲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导言第3~4页。
到此为止,如果说在第一阶段的空间下沉中,无产阶级遭受的社会真实的苦难给其蒙罩了一层悲剧的色彩,那么后续的空间上升则带来了新的希望,马克思需要为无产阶级寻找一种新的写作语法,一种新型的逻各斯,这种新的写作带来了不同的文本风格,如同海登·怀特指出的,“当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历史当作一部悲剧情节化时,无产阶级的历史便被置于一个更大的喜劇结构内,其结果包括了一切阶级的消解,以及将人类转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美]海登·怀特:《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426页。
马克思呈现的革命所面临的对象是全方位的。不但用物质的武器去革命现实的生产结构,还要与笼罩其上的意识形态做斗争的批判。这又需要不断地解构既定的话语逻辑,解构存在的一切思想样态:马克思承认了空间的先在性,但又不安于稳定的存在;他承认了空间上下的分置,但以颠倒的形式完成了新的划分;他下沉到物质的根基,又打破了存在的巨链;他承认真正普遍的真理,又反对既定的和谐;马克思以数学展开了对经济学的思考,但又不承认数字作为一种普遍文字的合理性;马克思不承认一切来自宗教意识形态的救赎,又在形式上实现着无产阶级这种复数英雄的自我救赎。也正因如此,这也困扰着对马克思哲学文本性质的确认。马克思的文本诚然是一种哲学,但是他曾明确拒斥“哲学”本身;他曾热情赞扬并致力于“实证科学”,然而他又拒绝国民经济学这样的科学体系。马克思的文本显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属性,这正是在思想的逻各斯革命阶段展开叙事所不可避免地造成的,因为任何的“述谓词”都在切换的当下拥有着双重的意蕴。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