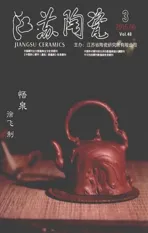浅谈用刀技法的丰富性和紫砂陶刻的艺术性
2015-04-11许沈紫
许沈紫
(宜兴 214221)
紫砂陶刻与中国的篆刻都有“以刀作笔”的共同特征。相比较而言,篆刻印章的可用面积较小,而紫砂用于陶刻的面积要大好几倍甚至十多倍。紫砂陶刻的刀与镌刻印章的刀有所不同,刻印章的刀为平口,刀杆宽、厚,它用“冲”或“切”的技法来刻印章,可以用转动印材的方法来实现刀的转换,而紫砂壶一般不适宜于转动位置的,它在刻的过程中必须用刀尖的转动来实现刀痕转侧的要求。所以,紫砂陶刻的用刀比篆刻刀要薄、要窄(一般刀宽 0.4~0.6 cm,刀厚 0.15~0.2 cm,刀长 16 cm左右),刀口为斜口,必须磨成45°角,可根据作者的陶刻习惯而定。由于紫砂陶刻需要在镌刻时转动刀,因此,必须把刀装入一竹制的刀管内,用狭长的纸片卷裹后装入刀杆固定。刻时手持竹管,用拇指与食指的配合捻动竹管,即可实现刀尖的转动,因而产生多变的陶刻技法。
紫砂陶刻从篆刻技法中学到很多东西,并有自己的创造。它的刀法与中国的书法艺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写毛笔书法讲究“起、行、转、收”,并有“欲横先竖,欲竖先横”的技法要求,紫砂陶刻的用刀也是这样,刻一横画必须在起刀时竖着下刀,再捻动刀管横向而行,收刀时必须像写书法一样竖向收刀,这样刻出的刀痕才有毛笔书法的意趣。
紫砂陶刻用刀的丰富性,给陶刻的书法、绘画带来各种形态的线、面构成的画面,增添了紫砂陶刻的可读性、可赏性。紫砂陶刻的线刻主要是用切刀法,切刀是按书法的顺向行刀,反之可称为推刀,是逆向行刀。从用刀的力度、速度来说,有轻、重、快、慢的区别。从下刀的角度来说,一种是刀杆接近直向下刀,形成一面毛、一面光的刀痕;另一种是刀杆 45°斜向下刀,正反各一刀,要求每刀的刀尖都在笔画的中心线上运行,形成一V形的凹槽,俗称三角底。从行刀的方向来说,有直行和曲行的区别,直行的刀痕接近于直线;曲行则刀痕产生曲的变化,一种为曲而有棱角;另一种曲而无棱角,又称为转刀,边行边转,刀痕为弧线。从清底的方法来说,除三角底外,还有平底及鲫鱼背,平底是用平口刀(刀口稍窄于笔画的宽度)铲成;鲫鱼背是用尖刀顺着光的一边的刀痕横向刮去笔画中的底子,须两刀完成,形成两边深、中间浅,状如鲫鱼背的刀痕。从用刀刮成的刀痕来说,有深、浅、光、毛的区别。从用刀的先后来说,分初刀和复刀,如刻一大片的荷叶,在用单刀刻出荷叶的边缘线后,须用刮的方法刮去叶面的底子,有的地方须刮,有的地方须留,留的地方就如中国画中的空白;有的地方须深,有的地方须浅;刮好后,须再刻叶筋,称为复刀。刀法的丰富性使紫砂陶刻的画面产生犹如中国画“墨分五色”的艺术效果。
一幅高水平的陶刻作品,可从作者用刀技法的丰富性和对各种刀法综合运用的娴熟程度来品读。欣赏陶刻大家任淦庭在一“牛盖洋桶壶”(见图 1)上刻的诗句“色到浓时方近苦,味从四处有余甘”上来理解。这幅草书刻得姿态飞动、神完气足,正如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述:“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艺术效果,与作者用刀的轻、重、快、慢、转的娴熟程度有关,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准”字,与书法相合,准确无误。在紫砂陶刻中,以草书的难度最大,也最能体现作者陶刻的艺术水平。“重若崩云”,可以从这幅作品的较粗、较深的笔画中来体味。“轻如蝉翼”可从其细笔及牵丝、萦带中见刀工。轻重的对比与和谐是书法艺术的要素之一。“导之则泉注”可见于“浓”字的三点水,草书则为一刀轻点再提刀后一刀直泻而下,如山泉倾注。“顿之则山安”,可见于“甘”字最后的收笔,下刀深重,刻出的笔痕如高山坠石,在厚重处见千钧之力。“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可以“回”字四侧的转角,环转流畅似月之初升,又如天上仙女舞动的彩带环绕飞动,毫无滞涩之处,非有极高的书法造诣及炉火纯青的用刀技巧者,不能得此神来之刀(笔)。“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可从这幅草书的整体章法上来欣赏。其正文三字一行与两字一行交错使用,与以后较小字体的六行落款相互呼应、错落分布,犹如天上的星辰自然排列,在看似不经意中见作者的匠心所在。

图1 牛盖洋桶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谭泉海曾经说过:“笔笔见刀,刀刀见笔”,才是功夫,才是紫砂陶刻的真谛。“刀刀见笔”,则要求我们的陶刻作者必须打下中国书画的扎实功夫。“笔笔见刀”,则要掌握复杂多变的用刀技巧,才能在陶刻实践中驾轻就熟,刻出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