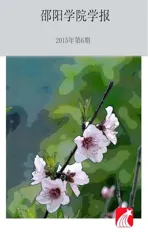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研究
2015-04-11杨利华李红辉
杨利华 李红辉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 100088)
商标法意义上的商标使用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100088)
摘要: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是经营者创造、维持、扩张无形资产——商誉的绿色渠道;是维持商标专用权、获得商标法保护的必要前提。鉴于商标取得制度、维持制度和保护制度的立法目的和制度价值不同,对于“商标性使用”的认定标准也有宽严之别。我国商标法尽管揭示了商标“区别商品来源”的本质,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商标制度不同阶段商标性使用的特定标准。文章立足于商标法中的商标保护制度,结合相关典型案例,针对“商标性使用”和非商标性使用(限于商标法上正当使用制度)的标准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商标性使用; 正当使用; 突出使用; 第一含义
李红辉(1990—),女,河北邯郸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知识产权法专业硕士生。 商标作为一种区别不同生产经营者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记,其本身是一种文化符号。各国法律之所以保护商标,其根源在于商标上承载了诚信的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通过持续经营、改善商品或服务质量等努力而形成的“商誉”。商誉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生产经营者长期、持续地将商标真实地使用在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之上,通过商标性使用,经营和保护商标,培育知名品牌,实现文化符号向企业无形资产“商标”的蜕变。此时,消费者看到的商业标识,不再是二维平面商标,或者立体商标,而是商品或者服务以及企业信息的载体。例如百雀羚商标象征着味道清新、包装精美的草本护肤产品,以及不断创新的企业理念。总之,商标性使用是商标法律制度产生的实践基础、理论基石。
如果说商标注册、商标维持、商标保护是商标制度中的不同节点,那么商标性使用必然是连接上述节点的一条相对隐蔽的纽带。倘若没有商标性使用,没有无形资产——商誉,即失去了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那么商标专有权的获得、维持和保护便无从谈起。在商标保护制度中也是如此。如果不存在商标的使用,混淆也就无从谈起,也就不存在商标侵权行为的前提和基础。[1](P22)本文主要以商标侵权典型案例中的商标性使用为视角,结合司法实践中商标保护的典型案件,试图进一步界定商标保护制度中商标性使用与非商标性使用理论标准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个案中商标性使用的判断标准,以期缩小理论探讨和司法应用之间的鸿沟,确立相对清晰的商标性使用判断标准。
一、商标性使用
中国古代素有“重招幌,轻商标”[2]的习俗,但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利用标记区别商品来源的历史由来已久。众所周知,北宋时期,我国就出现了图文并茂的纸质商标,即济南刘家功夫针铺的白兔商标[3]。因此,尽管我国的商标保护法律制度直至清朝才真正确立,但不容置疑的是,我国商标使用的历史源远流长。
(一)商标性使用的含义
商标性使用是以指示商品或者服务来源为直接目的,将商标用于商品或者服务及其衍生物之上,或为商业目的将商标用于宣传推广等其他活动中的一切行为。[4]商标性使用的本质在于商标标识具有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表彰商品的质量和产地等商品信息。通过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经营者可以创造知名品牌,吸引消费者,开拓消费市场,提高市场份额及企业经营利润;商标成为“无声的推销员”,形成商标、商品和经营者之间的固定联系,消费者可以认牌购物,节约搜索成本[5](P273)。
(二)商标性使用的法律规定
根据我国商标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商标的使用,是指将商标用于商品、商品包装或者容器以及商品交易文书上,或者将商标用于广告宣传、展览以及其他商业活动中,用于识别商品来源的行为。
200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Z].2005-02-18.对于商品商标和服务商标使用的具体方式的规定更加具体详实,如音像、电子媒体、网络等平面或立体媒介上使用商标标识;明确了单纯转让注册商标,而未发挥区别来源的功能,不属于商标性使用;界定了计算机软件商品商标的使用方式以及核准注册的商标与实际使用的商标有差异时,在未改变同一性的前提下,视为对注册商标的使用。尽管该《解答》并非司法解释,但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明确商标性使用的认定标准,以及适应互联网时代对于商标性使用的新发展,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三)认定标准
商标保护制度的设立目的,是保护经营者的商标专用权,防止竞争对手采取搭便车、混淆视听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攫取不当利益;避免消费者被附有假冒商标的产品所欺骗,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因此,经营者不仅对于在相同商品上使用相同商标的行为享有禁止权,而且对于在相同商品上使用近似商标,以及在类似商品上使用与之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行为享有禁止权,即商标专用权人的禁用权远大于其专有使用权。由此可知,侵权案件中对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相较于商标取得制度和商标维持制度而言,认定标准相对较宽。
商标侵权中,商标性使用的具体标准如下:
第一,为了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商标专用权是为了保护生产经营者的商誉所附带的利益。从商标权人的角度而言,只有在商业活动中使用注册商标,才能够建立商品或服务与来源的固定关系,从而提高商标知名度,获取消费者信任和“反射”的价值,扩展司法保护范围。从被诉侵权人的角度而言,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包括为了在商业活动中使用商标而制造、储存侵权产品等阶段,但是并非一切以在“商业活动”中使用为目的而生产、制造附有争议商标的产品均会构成侵权。
例如,在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案件中,经过多年司法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界的深入探讨,从平衡生产方、委托方和商标专有权人的利益出发,主流观点认为,涉外定牌加工的货物不是侵权货物,贴牌行为并未侵犯国内商标权。[6]即在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纠纷中,生产方或加工方在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义务后,受委托而使用商标的行为不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用”[7](P142)的结论。这种观念的转变、发展的关键,源于对于“商标性使用”的理解。
在涉外“定牌加工”商标侵权纠纷案中,首先,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决定了我国商标法旨在保护在我国获得商标专用权授权的权利人,保护我国管辖范围内的相关市场的正常秩序,以及相关地域范围内的消费者的利益。其次,定牌加工所生产的产品主要是销往国外,不在国内市场流通,因此,该商标不会在国内市场的相关公众中发挥识别作用,更不会造成混淆,因此定牌加工商标纠纷案件中对于争议商标的使用不构成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但是在立法价值迥然不同的商标维持制度中,对于涉外定牌加工中“商标性使用”的认定标准则另当别论。
第二,突出使用,且具有识别来源的功能。从理论的角度而言,只要被诉侵权人在相同或者类似的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且具有混淆可能性的,即构成商标侵权。即商标侵权的认定不以主观过错为要件,但被诉侵权人可以正当使用进行抗辩,如描述性使用、指示性使用。在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被诉侵权人往往以善意使用商品通用名称,表明商品或服务来源及特性等功能性使用进行抗辩。而“拨开迷雾”的利剑即判断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即于个案中判断被诉侵权人“是否在商品上或者广告宣传中突出使用争议商标,并发挥了识别来源的功能”。如辉瑞产品公司等诉江苏联环药业公司商标侵权案*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9)民申字第268号民事裁定书。中,由于涉诉侵权产品,即附有争议商标的药品,在商业活动中被包装在不透明的材料中,不能发挥商标的区别性作用,因此,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
第三,自主使用。对于未注册商标而言,当他人主张商标申请人的行为属于抢注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时,其未注册商标需要满足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且发挥了识别功能。此外,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原庭长孔祥俊法官认为,“权利人”就未注册商标主张权利的,其应当具有将该标识用作商标使用的意思和行为,即“被动的使用”不属于商标性使用。[8](P136-137)但是如果经营者能够将相关公众、生产者、销售者以及媒体公认的商标简称或者其他标识作为商标真实公开且持续的使用,符合自主使用的要求,即属于商标性使用。
如在索尼爱立信公司诉商标评审委员会、第三人刘建佳商标行政纠纷*参见最高级人民法院(2010)知行字第48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中,刘建佳于2003年申请注册“索爱”商标,于次年获得核准。2005年原告向商标评审委员会提出商标撤销申请。最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在涉诉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原告没有将涉诉商标实际应用在商业活动中,并且在2007年原告的负责人曾多次表示拒绝相关公众以及媒体将原告简称为“索爱”,认为该简称不能表示商品及服务的来源。因此,尽管从2002年网络媒体等就开始将“索尼爱立信”简称为“索爱”,且在消费者心中“索爱”和原告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一一对应关系,但是由于原告始终未在其商品中使用涉案商标,即“索爱”,因此原告的诉讼请求最终没有获得支持。
(四)除外情形
根据立法规定、判断标准以及司法实践,下列情形属于非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第一,在核定使用的商品以外的商品上使用注册商标,或者实际使用的商标与核准注册的商标不具有同一性。第二,如果商标权利人注册了联合商标,而对这类商标的从商标没有使用的,对主商标的使用不能视为对从商标的使用。就防御商标而言,该商标在某类别上使用,不能认定在其他类别的商品上进行了真诚使用[9]。第三,象征性使用注册商标,未持续性、真实使用注册商标,未发挥注册商标的识别作用。第四,未公开使用,如仅仅在公司员工内部流转带有注册商标的样品或者被许可人利用注册商标生产或输入商品后存入仓库,但一直未进行市场销售[10]。第五,单纯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被许可人或受让人未发挥商标的识别功能。第六,即使商标权人事后追认,无权使用者的使用也不属于注册商标的使用等。
二、非商标性使用
商标性使用的本质在于识别不同生产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来源。因此,商标性使用与非商标性使用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发挥了商标的识别功能。[11]在商标侵权案件中,商标性使用是认定构成商标侵权的前提,因此,原告需要承担证明被告使用争议商标的行为构成商标性使用,即被告利用涉诉商标发挥了表明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功能,具有混淆可能性。而被告在不享有商标先用权的情况下,可以非商标性使用进行抗辩。非商标性使用抗辩最典型的体现是正当使用抗辩,但是非商标性使用不等于正当使用。非商标性使用对应的是商标性使用,是从商标的区别来源的功能划分的,包括不正当竞争中虚假宣传等违法性行为。而正当使用是为了平衡商标专有权人、社会公众、相关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属于商标专用权的限制制度,正当使用商标的行为是法律所允许的。本文将仅仅在商标法意义上探讨非商标性使用,且仅仅限定于商标法的正当使用制度。
(一)正当使用的含义
商标正当使用是指生产经营者为了宣传自己的商品,可以以合理的方式正当使用自己的姓名、名称,或者使用其生产经营的商品的名称,或者使用标示商品形状、图形、型号、质量、主要原料、用途、功能、数量、重量、来源等特点的标识,而不受商标权人限制的一种法律制度。它通常包括叙述性合理使用、指示性合理使用和说明性合理使用三种。[13](P302)
商标正当使用作为一种商标专用权限制制度,是为了保证社会公众对于公共信息资源的共享和使用,平衡商标权人、具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经营者、社会公众等之间的利益,协调商标专用权与公共资源享有权的关系。
(二)正当使用的相关规定
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九条明确了叙述性使用对于商标权的限制,但是未规定商标指示性使用、平行使用等商标正当使用制度的构成要件。《解答》第二十六条则明确了商标正当使用的构成要件,第二十七条明确了商标正当使用的方式,将指示性使用纳入到正当使用制度。相较于商标法的规定,该《解答》对于商标正当使用制度的规定更加全面、完备,对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指导法律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解答》中规定,商标正当使用需要满足下列要件:(1)使用出于善意;(2)不是作为自己商品的商标使用;(3)使用只是为了说明或者描述自己的商品。
(三)正当使用要件
首先,商标正当使用制度要求使用人善意使用商标,即使用人不具有利用商标权利人的商誉获得非法利益、减少权利人的市场份额及利润等恶意竞争的目的。因此,尽管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被告的主观状态并非侵权认定的要件之一,但是在正当使用制度中,使用人善意使用是认定构成正当使用的要件之一。如使用人在描述性商标的第一含义范围内使用商标,发挥其功能性价值,如“嘀嘀打车”中的“嘀嘀”通过象声词表明了企业所提供的服务,又如奔驰汽车维修公司在服务宣传中使用“奔驰”的标识,说明为奔驰汽车提供维修等服务,发挥其指示作用等。
其次,从商标的使用方式来看,使用人未在相同或者相似的商品上突出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商标的使用方式是使用人主观意图的外在表现,是判断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的关键。是否属于“突出使用”需要进行综合考量,如对于文字商标,需要考虑使用的目的、字体、颜色、大小、位置等因素。
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满足“在相同或类似的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商标”的前提下,被诉商标侵权人一般会主张其对于争议商标的使用属于非商标意义的使用或属于正当使用。囿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法官需要根据被诉商标侵权人的主观意图、对于争议商标的使用方式等因素进行客观、中立的判断。
三、商标性使用与非商标性使用在司法中的认定
在纷繁复杂的商标专用权侵权纠纷中,商标性使用判断是法官裁判的前提和焦点。因为在商标专用权侵权案件中,商标权利人主张被诉侵权人的行为侵犯其商标专用权,需要证明被诉侵权人在相同或者相似的商品上使用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而被诉侵权人在不享有先用权的情况下,多以善意使用、正当使用抗辩。法官作为中立方,在被诉侵权人的主观状态无法辨明的情况下,只能够根据其对于涉案商标外在的使用方式判断是否属于商标性使用及其主观状态。如果被告对于争议商标构成突出使用,且发挥了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功能,那么无论其主张将该符号作为企业名称、商品系列名,还是作为商品颜色、服务来源等描述性使用,或是指示性使用,均可能会被认定构成商标侵权。
(一)商品名称与商标
具有吸引力与独创性的商品系列名称是画龙点睛之笔,可以给传统商品注入新的生命力,如宝洁旗下的“飘柔”“海飞丝”“潘婷”等。而有的经营者未给予二线品牌足够的重视,区别商品不同特征的系列名称多取材于中外传统文化。这些系列名称不具有独创性,显著性较弱,如在家具上使用“书香门第”。一旦该系列名称被同业竞争者模仿,且任何一方注册为商标,商标争议由此而生。
1.案例简介
尽管与最高级人民法院之前审理的“谊来陶瓷工业有限公司(沈阳)与上海福祥旧瓷有限公司、上海亚细亚陶瓷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一案”*参见最高级人民法院 (2004)民三终字第2号。非常相似,在格力公司诉美的公司侵权“五谷丰登”商标专用权案*参见(2011)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26号。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仍然作出了和最高人民法院截然不同的判决。不难发现,导致两案判决不同的关键在于法院对于商标性使用和非商标性使用的判断。
在谊来公司诉福祥公司等商标侵权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福祥公司在产品包装箱和宣传册上使用“维纳斯”文字时,突出自己的“亚细亚”图形及文字注册商标,并标明生产企业的名称,未突出使用“维纳斯”,而是将其作为“亚细亚”商标商品项下一种规格、款式名称。因此,最高人民法院根据被告使用争议商标的主观意图和客观使用方式,认定被告是在描述性商标的第一含义范围内使用涉案商标,属于正当使用,不属于商标意义上的使用。
相反,在格力公司诉美的公司侵权“五谷丰登”商标专用权案中,法院认为,是否属于商标使用应当从客观意义上进行判断,商品名称是否具有识别商品来源意义,不以使用人的主观认识或者称谓上的差异为转移,而是要根据其客观上是否具有识别商品来源意义进行判断。本案中,从美的公司使用被诉侵权标识的方式看,被诉侵权产品室内机面板正面左上方标有红色艺术字体的“五谷丰登”字样,且字体较大。该标识较为明显和突出,相关公众在购买空调器产品时,非常容易观察到被诉侵权标识,并将该标识与美的公司特定商品相联系,从而凭借该标识在市场上识别美的公司特定商品。因此美的公司使用“五谷丰登”标识的行为,属于突出使用,客观上起到了指示商品来源的作用,应认定为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尽管美的公司主张其属于善意使用,将“五谷丰登”标识作为产品系列名,用以表达丰收吉祥的含义,是叙述性使用,不属于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但是其实际使用方式和善意使用的表述相矛盾。
2.案例评析
对比谊来公司诉福祥公司等“维纳斯”商标侵权案以及格力公司诉美的公司侵权“五谷丰登”商标专用权案,不难发现,法院在判断商标性使用时,更加侧重于被告对于涉案商标的客观使用方式。因为被告的主观意图难以判断,但是从其是否在涉案商品或服务上突出使用争议商标,即可以表明其主观意图。因此,即使被告主张在描述性商标的第一含义上使用争议商标,但是在商品或者广告宣传单中使用特殊字体,或者颜色等在显著位置突出使用涉案商标,即可以认定属于商标性使用。从而商标性使用的判断标准更加客观、公正。
(二)字号与商标
从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的角度,企业字号和商标一致有利于广告宣传,防范法律风险。然而,理论和实践的鸿沟不可小觑,如实践中在市场利润的诱惑下,利用他人驰名商标或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字号来鱼目混珠,恶意竞争的行为比比皆是。针对此类与诚实信用原则相悖的行为,商标法明确规定将已注册商标或未注册驰名商标登记为企业字号的,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不过,法律规定具有抽象性和单纯性,实务中此类商标侵权案件相对复杂。因此,在涉及字号权的商标侵权诉讼案件中,要求法官在综合考量诚实信用原则、在先权利,以及商标性使用等因素的前提下,进行理性判断。
1.案例简介
在“好又多管理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诉张家港市好又多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刘念龙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参见广东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三“好又多管理咨询服务(上海)有限公司诉张家港市好又多连锁超市有限公司、刘念龙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原告购得内含“好又多”字样的图文商标(于2000年核准),核定服务项目是“推销(替他人)”。被告张家港好又多公司先于上海公司在企业名称中使用,2010年授权刘某在超市名称中使用“好又多”。法院认为,张家港公司以“好又多”作为其企业名称的字号具有正当性,可以整体使用。但张家港公司在公司成立9年后,在“好又多”已然在全国百货类具有显著影响后,仍授权他人使用“好又多”作为企业名称,简化、突出使用“好又多”字样,其行为造成了公众的视觉混淆与误认,其行为明显属于搭便车,遂判决张家港公司停止突出使用“好又多”三字,并赔偿经济损失15万元。
2.案例评析
本案中,尽管张家港公司有权在企业名称中使用“好又多”,但是在“好又多”商标已被上海公司注册取得的情况下,张家港公司和字号被许可使用人均不能突出使用“好又多”,将其作为商标使用。该案明确了字号在先权利人与商标专用权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字号在先权利人及其被许可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且仅仅在企业名称的范围内以整体的方式使用;如果其将已被他人注册为商标的“字号”突出使用,擅自僭越权利边界,那么,其行为将构成商标侵权。
(三)服务主体简称与商标
为了便于称呼、说明服务来源,具有合作关系的市场服务主体多采用简称的方式代替冗长的主体名称。当服务主体的简称与已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且服务种类相同或类似,应当如何平衡相关主体的利益关系?服务主体的简称具有区别服务提供者的作用,那么,此类主体简称的使用必然是商标性使用吗?
如前所述,对于非臆造性商标,同业竞争主体有权在第一性含义的范围内使用商业标记。同理,服务主体有权使用特定标识发挥表明服务主体、服务类别、服务特点等作用。因此,即使服务主体简称表明了服务的来源,发挥了识别作用,只要其使用方式合理,不存在突出使用的情形,仍然属于描述性使用、功能性使用。
1.案例简介
在“杨汉卿、北京新范文化有限公司与恒大足球学校、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参见(2013)粤高法民三终字第630号。中,杨汉卿是“皇马”商标专用权人,核定服务项目“组织体育比赛”等。后杨汉卿认为被告使用的“恒大皇马足球学校”侵害了其商标专有权。被告主张,“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是对足球学校办学主体真实、客观表述,即“皇马”是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的简称。该名称体现了学校的办学优势,属于描述性使用,而非商标性使用。对此,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观点存在分歧。一审法院认为,恒大足球学校对外使用的名称为“恒大皇马足球学校”,除了突出使用“皇马”二字,也突出使用了“恒大”二字,属于商标性使用;但考虑到恒大地产公司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在相关公众范围内的知名度,以及原告商标未实际使用,不具有较强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因此,一审法院认为不构成商标侵权。二审法院认为,恒大足球学校对“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使用,不属于突出使用,不是商标意义上的使用,两者商标非相同近似商标,更不构成反向混淆以及不正当竞争。
2.案例评析
本案中,尽管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被告使用的“恒大皇马足球学校”未侵犯原告的注册商标“皇马”,但是对于是否属于“突出使用”、商标性使用和非商标性使用有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虽然商标性使用需要法官根据个案进行具体判断,但是商标性使用判断标准的立法缺失,容易诱导法官肆意扩张的司法裁量权,从而加剧同案不同判、上下级法院观点矛盾的司法现状。因此,亟需确立相对具体、客观且统一的商标性使用认定标准。
(四)商品颜色与商标
在特定行业中,商品主体均会使用约定俗成的、行业内部公认的词语来表述商品的名称、质量、颜色、产地等特点。一旦该标识被注册为商标,如“金华”火腿、克里斯提·鲁布托的红色的高跟鞋鞋底,商标纠纷不可避免。鉴于这类描述性商标的显著性较弱,商标权保护的范围相对有限,商标权人不得限制他人在第一含义的范围内继续使用该词语,不得剥夺社会公众使用公有领域资源的权利。然而,判断是否属于描述性正当使用的关键,在于被诉侵权人使用争议商标的方式,是否属于突出使用,且发挥了识别商品来源的作用,而不是其主体是否存在不正当竞争的恶意。
1.案例简介
在“深圳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诉湖南德兴瓷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度十大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之二“深圳国瓷永丰源股份有限公司诉湖南德兴瓷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中,永丰源公司是“帝王黄”商标注册人,核定使用商品“日用瓷器”等。其认为德兴公司在其网页、产品宣传册、黄色瓷器商品、瓷器商品外包装上使用“帝王黄瓷”文字标识构成商标侵权。德兴公司以正当使用为由抗辩。一审法院支持了被告的抗辩。二审法院认为,在部分商品上,主观意图上,德兴公司是依据陶瓷行业的特点,使用“帝王黄”标记来区别瓷器商品的颜色,表明商品特征,没有攀附永丰源公司涉案商标名誉的恶意;使用方式上,德兴公司在醒目位置标注了自身商标及企业名称,用以指示商品来源,客观上不会导致相关公众混淆,不构成商标侵权。
在部分黄色瓷器商品,德兴公司的两种不当使用方式客观上决定了其非正当使用,属于商标性使用。第一,在包装盒醒目位置以显著字体标示“帝王黄瓷”文字标识,而自身注册商标较小;第二,在部分黄色瓷器商品的包装盒中心位置以显著字体标示“帝王黄瓷”及“KING HUANG PROCELAIN”标识,而未标示自身的商标或其他足以区分商品来源的标识,容易导致相关公众将使用该包装的商品误认为来源于永丰源公司。
2.案例评析
“帝王黄”是陶瓷工艺品行业非常流行的产品颜色,象征着权威、华丽与富贵,因此,许多陶瓷厂家将“帝王黄”作为陶瓷产品的系列名称。因此,即使“帝王黄”商标权利人享有商标专用权,或者通过商标性使用获得了“第二含义”,也不得限制其他竞争者使用“帝王黄”描述瓷器的颜色。这和“双十一”商标专用权人阿里巴巴无权限制其他电商或者其他实体企业继续在各种商品促销活动以标明时间使用“双十一”的情形,如出一辙。
本案中,终审法院综合考虑德兴公司使用“帝王黄”商业标记的主观意图、具体位置、字体,其自身商标、企业名称等因素,判断德兴公司的主观状态、以及是否属于突出使用。最终,根据德兴公司不同的使用方式,作出部分属于商标侵权,部分属于正当使用的裁决。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对于非臆造性商标而言,商标专用权人以外的市场主体有权在其原有含义的范围内使用商标,但是不得突出使用,否则将构成商标性使用,属于侵权行为。具体而言,无论是商品名称、企业名称,还是表示商品颜色或者服务主体等标明商品或服务来源或特点的文化符号,即使被注册为商标,其他竞争者或社会公众仍然有权在原有范围内使用公共领域信息资源,如描述性商标的第一含义。这类使用商标的行为属于正当使用。然而,任何权利都是有边界的。商标专用权人以外的市场主体不得滥用正当使用制度。如果其他竞争者以正当使用的名义,在其商品上、宣传页或广告中,突出使用该标记,则构成商标性使用。一旦权利人逾越了正当使用的权利边界,则有侵犯商标专用权的嫌疑。因此,无论是商标权人,还是其他竞争者或社会公众,均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尊重他人的应得利益,在合理的范围内以合理的方式行使权利。
四、结语
传统观点侧重于强调商标性使用对于商标权的取得、行使、维持和保护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商标侵权案件,商标法性使用的判断是法官不可避免的焦点问题、先决问题。而商标法对于商标性使用的规定比较概括、抽象,需要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认定,综合考虑争议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被告的主观意图、对于涉案商标的使用方式等因素。通过对商标性使用的理论阐释与案例分析,本文力图缩小商标性使用的立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之间的差距,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商标保护制度中商标性使用的标准。
此外,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大力推进实施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应当从商标战略的角度,强调商标性使用对于商标的取得、运营、管理、保护等各个阶段的重要价值。因为我国虽然属于注册取得主义的国家,但是通过商标性使用带来的商誉是商标法保护的标的和基石。如果仅仅着眼于商标权的取得、维持和保护,不利于商标权利人从战略的高度以商标性使用为途径,更有力地获得商标确权、保持商标权的有效性,以及获得更宽的保护范围,容易误导商标权人在发生纠纷时,措手不及地投机性、象征性地使用注册商标,而忽视商标的经营和品牌的培育。
参考文献:
[1]张今,郭斯伦.电子商标中的商标使用及侵权责任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2]郑成思.商标与商标保护的历史──商标制度的超源及发展(一)[J].中华商标,1997,(5):39.
[3]罗晓霞.商标法溯源:富有竞争政策内涵的历史演进[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2):106-110.
[4]张今,刘晗.商标使用相关问题探究[J]. 中华商标,2013,(9):61-64.
[5][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6]王莲峰.海关应慎重认定涉外定牌加工货物的商标侵权——基于对近年《中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分析[J].知识产权,2015,(1):31-36.
[7][8]孔祥俊.商标法适用的基本问题[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9]陈学.商标使用制度研究[D].上海:华东政法大学,2010.
[10]李扬.注册商标不使用撤销制度中的“商标使用”界定——中国与日本相关立法、司法之比较[J].法学,2009,(10):96-109.
[11]马荣.非商标性使用侵权的法律规制[J].中华商标,2015,(2):68-72.
Research on the Trademark Use in the Sense of Trademark Law
YANG Li-hua, LI Hong-hui
(Civil, Commercial and Economic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Trademark use is the green channel for operators to create, maintain, expand their intangible assets, or their business reputation and should be the necessary premise to maintain trademark, and obtain protection from the trademark law. Given that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and the value of system among the trademark obtained system, maintaining system and protection system are different, the standards of “trademark use” are also different. Although our trademark law reveals the essence of the trademark, which is to indicate different sources of goods and services,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ear specific standard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trademark system. Based on trademark protection system of trademark law, to analyze the standard of “use of trademark” and non trademark use (limited to the fair use system of the trademark law) with the typical cases involving trademark use, will be a useful research to solve such issue.
Key words:trademark use; fair use; prominently used; primary meaning
作者简介:杨利华(1966—),女,湖南长沙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知识产权理论体系研究”(11AZD047)
收稿日期:2015-10-10
中图分类号:D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012(2015)06—003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