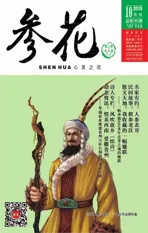我收藏的一幅楹联
——一幅承载600多年忠孝之魂的楹联
2015-02-18高笠鑫
◎高笠鑫
我收藏的一幅楹联
——一幅承载600多年忠孝之魂的楹联
◎高笠鑫

作者高笠鑫系长春市收藏家协会副主席
一九九一年腊月的一天早上,下了一夜的大雪缓慢下来,天空中却依然铅云低垂,细雪飞舞。雪后的城市银装素裹,行人寥寥,平时很热闹的古玩市场也分外冷清,没几家店铺开门。趁着市场人少,我就早来了一会儿,整理了一下前几天收的货物。我忙碌了一会儿,偶然一抬头,看到一个瘦高的人影在门口徘徊,想要进来又迟疑不敢进来的样子。我想,在这样的鬼天气里,来个顾客可不容易,我精神一振,连忙开门请他进来。
他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了,头发花白,穿着还算整洁,清癯的脸上流露出一股浓浓的书卷气。是因为衣衫单薄吧,他拱肩驼背,冻得瑟瑟发抖。在他的肩上斜背着一个黑色人造革兜子,兜子的肩带都磨损得发白了。
我几番相让他才肯坐下。我一边烧水一边问:“老大哥这么早就来古玩市场,是要买什么东西急用还是想出手转让什么宝物啊?”“没啥买的,也没啥值钱东西好转让的,就是看看。今天都这时候了,咋都没开门呢?”他边四处张望边问。“今天不是节假日也不是星期天,昨夜又下这么大的雪,就都来得晚。古玩市场不像大商场,到点开门。说到底这也算是个自由职业,有时赶上有事儿,几天不开门也是常态。”“现在古玩生意还行吧?人都说古玩行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他认真地说。我笑道:“这也得看你开多大的张,三年都吃什么。”听了这句话,他忧郁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笑,我们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起来。
不知啥时候,外边的雪又紧了起来,北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街上的行人更见稀落。店里炉火熊熊,屋子里暖融融的。我泡了两杯热茶,他再三谢让才接过茶,连着喝了几口,感叹着说:“真是好茶,很久没喝过这么好的茶了。”茶气蒸腾,小屋里弥漫着茉莉花的清香,逐渐地消融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陌生感,我们边喝边聊着,从社会现象谈到工作境遇,从这些年的生活变化又扯到了书画艺术。他原来是个很健谈的人,对书法及古文字颇有研究,对有些生僻词句的出处都能引经据典娓娓道来,言语间不乏古雅之气,让我由衷地产生了敬意,并引发了深深的好奇。这样一个谈吐不俗的老先生,跟他那寒酸的衣着打扮实在是不相配啊。我试探着问道:“先生高寿?祖上是什么地方的人?看谈吐是出身书香门第吧?”来人看着窗外的大雪,若有所思地说:“我今年76了,穷教书匠一个,终生坎坷,活到现在一事无成,愧对先人呐!”他站起来望着窗外沉默了。我默默地又为他续了茶,就安然地等待着他的下文。果然,停了一会儿他又坐了下来,说:“我们家在民国时家道就已衰落了。我这辈子没一技之长,又干不动力气活,只能当个‘孩子头’,在乡下小学教书,一个月工资50多块钱,就够混口饭吃。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好事儿摊不上,来运动就挨整,一直到40多岁才娶了个同样出身不好的农村媳妇。媳妇是个老实人,身体也不好,我挣得钱又少,连要个孩子都不敢。就这样与世无争吧,老天爷还是来找我的麻烦,这不,大难临头了……”他摇摇头,说不下去了,声音也有些哽咽。一时间屋里的气氛变得很沉重, 火炉上的开水壶噗噗地响着,不断冒出一股股的白气,我默默地冲茶,添火。过了好半天,他缓缓抬起了头,声音从压抑变得清朗,说:“我姓凌,祖籍安徽人。祖上明清时原是做官的,解放前一大家人纷纷离散,亲戚间很早就没有了来往。祖父带着我们这一支来到东北,就此定居下来。我曾祖父叫凌燮,是晚清著名的诗人,与祖父都写得一手好字。曾祖父手里有明成祖永乐皇帝御赐的‘赐砚堂’和‘忠臣孝子名宦乡贤之子孙’两颗大印。光绪年间《巨鹿县志》就是我曾祖父编修的。现在浙江乌镇西栅灵水居景点,灵水居大门两侧有一首诗,那就是我曾祖父写的诗:‘名园曲折水通流,水源来自霅溪头;清晖旁映洞壑宇,碧影倒浸楼台浮。’这首诗对仗工整,意境幽雅,写得好啊!不过听父亲说,我们家虽是名门望族,家境却不是很富有,没什么值钱的物件,就是藏书多。”
那时我还没去过乌镇,也不知道清代有个叫凌燮的诗人,更从没听过这首诗。一时不知道该和他说什么,就试探着问:“您祖上是个清官,又是大诗人大书法家,应该有些遗珍墨宝留下来吧?”他慢慢地拉开兜子,从里面拿出个布包,里头又是一层布包着的两个卷轴,他说这是曾祖父留给他们家的一副楹联,让我展开来看看。我仔细地打量这幅挂轴楹联,字是用上好的檀皮宣纸写的。签条上写着(某)友鹤(某)对,上、下两轴,(某处字已磨损看不清)平轴头用黑白两色寿字纹缂丝装裱,全绫二色镶边锦绫包首,原装原裱,装帧非常考究,内容是用钟鼎文书写的:“无疆福寿,明德封爵”八个大字。笔力苍劲,力透纸背,虽是用钟鼎文写的,可是骨子里又浓浓地透着石鼓文和金石之气,用中锋浓墨,使字体更显沉稳肃穆,内容深远博大,耐人深思,让人爱不释手。上联引首盖有5X8公分一个大印,篆书“赐砚堂”三个大字,字两边有龙虎纹图案,下盖有3.5X3.5公分一方大印“曲阳世家”四个大字。下联下方盖有5.5X5.5公分两方大印,“皖人凌燮”“忠臣孝子名宦乡贤之子孙”为小篆。下款书:乙未冬月初凌燮,印章字体隽秀清雅俊美,刀法娴熟老道,一看就知是出自大家之手。画面有少许水迹和保管不当造成的霉斑,虽不十分洁净,仍算完好,是一幅难得的上佳楹联,是有一定文化历史内涵和文物价值的收藏珍品。我不住点头,边鉴赏边随口说了句:“这幅楹联真不错,看它满身沧桑,一定也是经历过不少的沧桑磨难了。”

“哎,说起我们家的事可真是太多了,别的不说,就说这对楹联和上面几个印章的来历就够写本书的,你要愿意听,我就跟你说说。”他一直平和的声音终于激昂起来,隐隐透出骄矜。重新坐下后,我们之间的生分已经消除得差不多了。我又给他杯子里续上茶水,听他讲述。
“说这话长了,六百多年前我的先祖是木匠世家,远近闻名,当时大买卖家起楼盖房子雕梁画栋,富贵人家精美的雕花和做精细家具都是我们家做,县城最大的牌楼就是我们家三百年前做的,现在还有。听我爷爷说以前家里有一块知府大人题的‘巧夺天工’的金字大匾,这在当时还得了啊!那就叫名声,让多少人羡慕!每逢年节或祭祖时都要把金字大匾请出来放在大堂里供奉,谁到我家来都要先向这牌匾作揖。
明朝永乐四年,永乐皇帝朱棣迁都,在北京建造皇宫。全国征调各类能工巧匠,征来的人员都是由各县挑选举荐的,工期不完不能回家。我的祖上就是第一批被征调的木工。在那个朝代这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能被举荐去建造皇宫,一个手艺人几辈子才能赶上这样的大荣耀啊!这些人到了京城都憋足了劲儿要干出一番成就来,为国尽忠。我的先人因为有些文化,会看图纸又能干,解决了很多工程中的难题,没多久就提拔为‘掌线’,管了几百人(可能就是现在的工长加现场工程师),成了工程中极受重用的人。就在皇宫快建好时,突然家乡来人说,老父亲快不行了,要他赶快回去见最后一面,并料理后事。作为家里长子,按理应该回去,给老人尽孝送终,当时最重孝道,工程再忙也是能够给假的。可他却对来人说:‘我虽是家里长子,可现在工程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我离开了实在放心不下!既然忠孝不能两全,当以国事为大,只能请父亲谅解了。不过我虽然不能给老人尽孝送终,却应尽孝子之心。’说着话谁也没想到,他突然拿起刀来割股取肉,从自己的身上血淋淋地割下一块肉来,交给来人让他速速返回,转告父亲,儿子今天为国尽忠不能回去床前尽孝,就用儿的肉给父亲做碗汤喝,算做儿子最后的孝心吧!说罢向着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大叩响头,嚎啕大哭。大忠臣大孝子的事儿在整个建殿工地传开了,大家争相传颂。此事惊动了总监督察大人,并向朝廷禀报了此事,给木匠‘凌掌线’奏请“忠孝”功名,奖宣其亘古难寻的忠心孝行。说来也怪,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忠臣孝子的事迹感动了上苍,他老父亲的病体竟然奇迹般的康复了,后来活到了八十多岁。
大明皇宫建成,明成祖朱棣大宴群臣,诏告天下,奖赏有功人员,有的进爵封官,有的赏赐家庙,有的赐匾。又大赦天下,农民减赋三成,万民尽沐皇恩。我的先人舍小家为国家,识大体明大义,实为人臣人子之楷模,赐印两枚,一为‘赐砚堂’,二为‘忠臣孝子名宦乡贤之子孙’。并官封七品,夫人还封了诰命。后代的儿孙们因品学兼优,又承蒙祖上威德,都做了官,贤良辈出,勋业辉煌。在明代最大的官做到礼部侍郎,还立了状元牌楼。这就是我们家族过去的历史。”
“忠孝”二字,这个充满了陈旧气息的遥远而陌生的词汇,在关联到这个家族命运兴衰的时候却让我产生了深深的敬畏。我被带回到了礼教森严的封建时代拔不出来,一时间,两个人都陷入了沉思,只有炉火熊熊燃烧时发出的声响。
过了好一会儿,我轻声说:“凌大哥,今天怎么把这样珍贵的传家宝带出来了?”他像是被惊到了,蓦然抬头,又恢复了刚进屋时那种略带拘谨的神色,他轻轻抚摸着挂轴镶边的锦缎,目光里流露出深深的眷恋和哀伤,说:“我们这个家族,延续了六百多年的辉煌,在清末逐渐衰退,等到文革一来,就彻底结束了。房子、祠堂,都破了四旧,印章也不知下落,抄干净了,我偷偷保存下来这副楹联,想留给后人传承,让子孙后代知道,我们凌家,是有根的,只要这些东西还在,循着这些老物件,就能找着凌家的根啊。可是……两个月前,我老伴儿突然高烧咳嗽,到医院检查,大夫说是肺癌晚期,已经没有治疗价值了,让拉回家想吃啥买点啥。你说好好的,这人咋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她是个苦命人,自从嫁给我就没得着好,没享过一天福啊。这几天她高烧不退,总想吃口凉的。这大冬天的,西瓜、桃、冻柿子,我换着样给她买着吃,没断过。别看我没钱,临了我得对得起她,还能吃几天呀!”
他的眼里泛起了泪花,我默默递过去毛巾,他摆摆手,用袖子抹了一把眼睛,继续说:“不怕老弟见笑,现在家里,连给老伴儿打个止疼针都拿不出钱来。我没儿没女,亲戚也早都失散了。等老伴儿走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再一倒下,这东西就不定落哪儿了,要是落在不三不四的人手里,糟蹋了,我就更没脸见地下的先人了!所以吧,我现在就想给它找个好主家,别糟蹋了好东西。要能换俩钱儿,让老伴儿走之前尽量享点儿福,少受点罪,我也就没啥遗憾的了。”
我望着这位明代忠臣孝子乡贤名宦的后人,不由得感慨万千,说道:“凌大哥,这东西不应该卖,再说也没有比照价格。一般人不知凌燮是谁,不太好卖。”他不解地看着我,不知怎么应对。我又说道:“现在一对清代刘墉(石庵)干干净净的七字大联也不过5000元,你这能卖什么价?”我是说的实话,也的确是发自内心地不想让他卖,因为有点急躁,话一出口有些生硬。他却被打击到了,脸色瞬间胀得通红。“你的意思是……我这宝贝……不值钱?”因为失望,更是因为痛苦吧,他的脸都有些扭曲了。他的腿打着颤,扶着桌子缓慢地站了起来,看来是打算离开。我急忙伸手拦住他,问:“先别急大哥,你想卖多少钱?”“几百块……还不值吗?”希望似乎又抬了头,他的眼睛里又现出熠熠的光来,声音里却透出不自信。我的心里却一沉,这可是宝贝啊,怎么能几百就卖?他实在是太需要钱了!我又激动又难过,两只手在口袋里轮番掏摸,直到掏光了所有口袋,把一堆零的整的钞票一股脑堆在桌上拢到他的面前,说:“我这就800块钱了,大哥你先拿去用,等你宽裕了再还我,这幅楹联你带回去。这是你们凌家的传家宝,不该卖啊!”他惊呆了,面对着这一堆钱手足无措。我把钱硬塞进他的人造革兜子里,拉上拉链,说:“咱俩唠了半天,也算是有缘人了。你不是没啥亲戚朋友吗?你要不嫌弃,我就认下你这个大哥了!老嫂子的病也不见得就真的治不好,等病好点了就一块儿来我这儿坐坐,你再把祖上的事儿多给我说说,我也长长见识!”说到这儿,我看他还在发愣,就不由分说把他推出了屋子,关上门。
茶香还在,我回味着他刚才的讲述,心里实在难以平静。突然,门开了,那老大哥又回来了!他的眼神不再惶悚,一进来就把兜子放到桌上,大声说:“老弟,钱,大哥就不跟你客气了,不管我这宝贝值不值这么多!这楹联,从现在起就是你的了!大哥没有后人,它早晚也是要落在人手。大哥看准了,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好主家!这幅楹联跟你老弟有缘分!”他用力攥紧我的手,说:“啥也不说了,不说了!认识你高兴,老大哥真的高兴!为了我这宝贝找到了家,高兴!”
雪停了,乌云在逐渐散去,温度也稍稍上升了一些。他最后回过头看了包裹一眼,就推开了门决绝地走了出去。我追上去大声说:“大哥,楹联我给你保存着!只要你想了,随时可以把它接回家去!”他没有回头,一边继续前行一边回过手摆了几摆。他脚步坚实,背影也比来的时候挺直了许多。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二十多年转瞬即逝。这些年我辗转大江南北,也遇到过很多的人和事,心也早在波谲云诡的商场的磨砺下生出了老茧,可每当想起那个卖楹联的凌家后人,我的心仍会一阵阵悸动。我忠诚地履行着诺言,一直等着他回来找我,我知道这副楹联弥足珍贵,如果单纯以投资的角度去衡量,我没赚到钱。可我更清楚,这楹联只有回到他的手里才真正有价值,这上面承载着一个传承了六百余年的世代家族人的尊严和荣耀。更重要的,这是那个诗书官宦之家的“根”。
凌家大哥,如果你已经不在人世,我会信守承诺,替你好好保管这份传家之宝,让凌家的“根”在我的手里继续传承下去,永不消亡。
凌燮: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凌燮主修《巨鹿县志》。浙江乌镇西栅灵水居景点,在这灵水居大门的两侧,有许多明清时期的文人骚客对灵水居的描写。凌燮有诗云:“名园曲折水通流,水源来自霅溪头,清晖旁映洞壑宇,碧影倒浸楼台浮。”嘉德等拍卖书法作品,有落款凌燮的书法作品,或“友鹤凌燮”,或“友鹤弟凌燮”等。钤印:“赐砚堂”“皖人凌燮”“凌燮”“友鹤”“鼐臣”“老荒”“退叟”“皖北旧家子弟”“曲阳世家”“忠臣孝子名宦乡贤之子”等等。其书法作品多见于隶书、钟鼎文。
(责任编辑 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