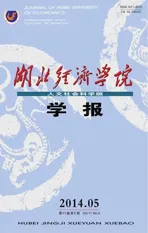从《游戏报》到《世界繁华报》:李伯元的“变”与“不变”
2014-04-07薛梅
薛 梅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春夏之交,李伯元将盛极一时的《游戏报》转手,另创《世界繁华报》。和《游戏报》一样,这也是一份小型报纸,初版时为长条形一张,半年后增至六版,其中四版为商业广告。版面采用大报分类设栏的形式,诸如引子、本馆论说、时事嘻谈、评林、讽林、艺文志、野史、官箴、北里志、鼓吹录、谭丛、小说、论著、花国要闻、梨园要闻、书场顾曲、艺苑杂刊、翻译新闻、滑稽新语等等,但栏名并不固定,随内容而变。体裁上,散文、诗词、寓言、谐语、俚言、书信等等,所在多有,而又“花样翻新,不名一格,逐日更换,层出不穷”。[1](P159)
关于李伯元为何放弃已经有固定读者群的《游戏报》,改创《世界繁华报》,有种种说法。或认为李伯元是因为同类小报日起林立,竞争激烈,不得已而为之。如张乙庐就说,继《游戏报》后,《寓言报》、《采风报》等报继起,各有佳作。这些小报,“名駸駸驾于《游戏》。氏惧,复创立《繁华报》”[2](P14)。或认为李伯元创办该报是基于“变”的需要,如吴趼人《李伯元传》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后,“踵起而效颦者,无虑数十家,均望尘不及也,君笑曰:一何步趣而不知变哉!又别为一格,创《繁华报》。 ”[3](P10)周桂笙亦有相同记载,说李伯元创办《游戏报》后,“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相接也。南亭乃喟然叹曰:何善步趣而不知变哉?遂设《繁华报》,别树一帜。一纸风行,千言日试。 ”[4](P12)
要在竞争中突出重围当然说出了部分事实,但张乙庐的说法并不准确,他所列举的两份报纸,《采风报》创刊于1897年7月10日,与《游戏报》可能有一定竞争,《寓言报》创刊于1901年3月5日,《世界繁华报》仅在一月之后,即当年4月16日已经在《同文消闲报》上已经布告《新出〈世界繁华报〉章程》,预告该报栏目,以《游戏报》所拥有的影响力,后一份报纸后来虽然颇有影响当时却仅创办了一个月,显然尚未对《游戏报》产生威胁。不过,尚未造成威胁不代表永远不造成威胁,李伯元创办《世界繁华报》,未必有吴趼人、周桂笙所言之笑傲报林的潇洒,却显然有着鲜明的“求变”动机。
这种“求变”意识并非突如其来。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敌入侵加剧,战争频仍,国家危在旦夕,民众的危亡意识逐渐觉醒,对于国家事务的关注变得迫切起来,这种关注体现在民众的日常阅读需求中,便是对“时事”的日渐关注。例如庚子事变中,全国上下震动,民众迫切想要了解这一事件,以至于“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5](P5)《游戏报》以“游戏”花间为旨归,在这样的时事下,虽然颓势未现,却显然已经渐渐不合时宜。
另一方面,从办报本身来说,求变是作为新生事物的小报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诉求。事实上,小报出现后,大报和小报之间呈现出某种相互学习和融合的过程,不仅小报学习大报,大报也在向小报学习,如《字林沪报》另创小报性质的《消闲报》随该报每日附送,以此作为吸引读者的手段就是一例。而小报对大报的学习,也是势所必然。
因此,无论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还是出于办报人身份对于报纸销量的现实考量,李伯元都必然要迈上一条“求变”之路。
一、“求变”体现为定位的拓展
《世界繁华报》对《游戏报》原本过于狭窄的定位进行了拓展。《游戏报》一如其名,“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以“游戏”为基本定位,它首开沪上妓女选美风气,更“逐期刊登妓女的姓名住址,俨然一副寻芳索引图”。连它登的新闻,也都是一些“妓女争风吃醋,嫖客拖欠嫖资”或诸如“二万钱败子完姻,四百金赌徒开局”、“难为小姨十三龄居然生子、妄充大少一百元何必担肩”等从标题上我们就可以充分领教其游戏性,甚至可以说是低级趣味的内容。[6](P91)这自然使得他容易吸引同好读者,但却也限制了它的范围与可能性。1896年年末,日俄战争爆发后,《游戏报》发布《本报论前增添逐日路透社电音及东省要电告白》,称“今海诹告警,宵旰焦劳,凡我臣民,同怀义愤,本馆亦不得不略更旧例,以示变通”。[7]并从该期开始,刊登日俄战争的相关新闻,以摘录翻译新闻为主,偶有评论。但是,《游戏报》作为花间同好的形象如此成功,也如此深入人心,这样的改变显然只能是不伦不类,既吸引不了新的读者,反而还有招致原有读者厌烦的可能。
相形之下,另起炉灶显然是更好的选择。《世界繁华报》一开始从名称上便表现出了它拓宽对象的企图心。它着眼于“世界”,这就大大拓宽了原本《游戏报》着眼于“花间”的狭隘,它也追求娱乐性,但这种娱乐以“繁华”笼统言之,也使得报纸在内容方面要更为从容开阔。事实正是如此,《世界繁华报》创办以后,一方面,它如常开办“花榜选举”,对花界新闻一如既往的热衷,且增设了梨园要闻、书场顾曲等栏目,扩展《游戏报》原有的消费和娱乐范围,另一方面,它表现出对“时事”的强烈兴趣。
二、“求变”体现为内容上对时事的强烈兴趣
在古代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了一个庞大的“华夏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但公众对于这个共同体上所发生的事情却并没有多少知晓权;即使官方有心将一些事务公之于众,地域辽阔、交通不便等因素,也使得传播也不能及时,因此,民众往往只能了解自己家族、乡里的情形,至于国家大事,则是一个十分遥远的概念。近代以来,随着印刷技术的发达和出版业的发展,以及交通的逐渐便利,地域等不再成为障碍,客观上使民众了解外界成为可能,事实上,《申报》等大报很早就开始刊登时事新闻。其它报刊也逐渐增大了时事在报刊中的比重。而新创立的《世界繁华报》,索性将时事作为其核心内容。
《世界繁华报》“体裁仿《中外日报》”[2](P14),分类设栏,但栏名并不完全固定,不过,“时事”还是明显占有不小的篇幅,既有“翻译新闻”、“最新电报”、“紧要新闻”直接刊载时事,又有“时事嘻谈”、“滑稽新语”以嬉笑怒骂的方式评论时人关心的事件,“新编时事新戏”则索性把当时轰动的新闻编成戏曲唱本连载,如《康有为说书》、《大阿哥出宫》、《陆兰芬归阴》、《经连珊哭狱》等等。
李伯元亲自操笔撰写的《庚子国变弹词》当然更是其中的典型例子。《庚子国变弹词》共四十回,自1901年10月至1902年10月排日连载于《世界繁华报》,它以刚刚发生的庚子事变为内容,从清平县武举与教民冲突、县官偏袒教民以致酿成武举复仇、率众杀死两民教民开始,直至辛丑条约签订、两宫返京止,其间如毓贤剿杀义和团、刚毅利用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逃、李鸿章议和,以及中俄战争等,均有反应,因此,阿英称赞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李伯元自己也非常强调《庚子国变弹词》内容的真实性,“是书取材于中西报纸者,十之四五;得诸朋辈传述者,十之三四;其于作书人思想所得,取资辅佐者,不过十之一二。”[8](P132-135)同时又一再叮嘱读者,“小说体裁,自应尔尔,阅者勿以杜撰目之”,要求读者不要将之当作杜撰的野史看待。这其中固然有王德威所说,“面对急遽变化的文化和历史情景”,“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迫切感,想要记录重大事件和当代人物,由此呈现国族当下的危机”[9](P140)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却也体现出了《世界繁华报》力图通过各种方式来展现“时事”,同时也是“消费”时事的努力。
三、“求变”的同时保留了娱乐化与通俗化的风格
不过,《游戏报》的成功是这样明显,拓宽内容、收敛风格之外,李伯元仍然有意识与大报拉开距离,使《世界繁华报》延续了《游戏报》重娱乐化与通俗化的特点。
首先,它保留了《游戏报》的经典栏目——“花榜选举”,此外,它还增设梨园要闻、书场顾曲等栏目,这多少有助于吸引部分原有读者。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它开始以连载弹词、小说等通俗文体的方式来招徕读者。
我们先看《庚子国变弹词》。对与庚子事变这样一个严肃事件,李伯元没有选用正统的诗词曲等文种,而采用了在中国传统文学结构中显然不够严肃的弹词。弹词是中国古代的民间艺术之一,严格意义上的弹词,是一种民间说唱曲艺,即伴着弹拨乐器(最初为琵琶、三弦,后来加入扬琴、击鼓、拍板等)可直接进行说唱的脚本。它起初由一些活跃在民间的具有创作能力的说唱的民间艺人创作,后来也逐渐有文人加入其中,出现了许多流传后世的杰作,如 《再生缘》、《笔生花》、《玉钏缘》、《天雨花》、《锦上花》、《再造天》、《玉连环》 等。 但无论如何,在传统文人看来,这种“不伦不类”的“乞儿谎语”显然相当“卑不足道”,只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游戏”文体。
“杞人忧天之语,托于俳优相戏之词”[10](P181)。 《庚子国变弹词》弃“正统”文种而选用弹词,显然有其多方面的考虑。首先,诗、词、曲都是主情而非主事的。对于这段腥风血雨的国难,若不仅仅满足于抒情感慨一番,而是欲生动、具体地反映,甚至达到“再现”某些历史史实、画面的目的,诗、词、曲显然都难以胜任。其次,弹词也自有其文学性的一面。阿英曾盛赞其文学性与艺术性:“其特有的音乐性和描写细腻,弹唱起来,或‘柔语如珠,绵绵不绝’,或雄浑浩荡,有若奔流,绘影绘声,竭尽委婉曲折之妙。”“其所具艺术性,是并不亚于所谓‘大文学’……其细腻雅韵,实臻‘大文学’所不能达到的境地”[11](P85)。 而李伯元出身书香门第,据说“从骈文到江南民间小调,从论说考订到诗词歌赋、戏曲弹词”[1](P1),他几乎“诸体兼擅”,雅俗全能。既然身负如此才华,以七言诗为主要构成,富有音乐性的弹词,自然能让其得心应手,一展所长,与此同时,也能满足一般文人读者的文学鉴赏要求。其三,如上所述,弹词传播面广,传播力度强,难以数计的民间艺人为生计、为乞食而奔走四方,日夜传唱,而它又对接受者的文化程度没有任何要求,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老人、儿童、妇女,也往往是其忠实听众,因此,弹词影响广大,拥有广泛的受众。“传播的广远,尤非‘大文学’所能望其项背。”[11](P85)这样,综合了时事的阅读期待、文学的鉴赏价值、文体的广泛传播性等多个方面的优势后,《庚子国变弹词》得以雅俗共赏,从而也在最大程度上吸引了读者。
早在《游戏报》时期,李伯元就已表示过“盛衰之感辄结郁勃于怀,而不能自已。欲为一家之言,或托之稗官野史,或摹写酣歌恒舞之大凡,魑魅鬼蜮之殊状,补《游戏报》之未备者。 ”[2](P134)《庚子国变弹词》可以说正是这种尝试的开始,李伯元在其中倾注的热情与社会责任感显然不容忽略,但同时,却也未尝没有报纸销量的考虑。
《庚子国变弹词》是一个成功的实验,它有力的完成了通俗化与关切当下的结合。对于李伯元来说,也完成了个人抱负与办报生涯的某种平衡。从此,仿佛一扇新的大门向李伯元敞开,他的第一部小说《官场现形记》①开始连载于《世界繁华报》,此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小说家的道路。
四、结语
《世界繁华报》创办时间不长,现存资料不多,专门的学术研究论文更是几乎没有。在李伯元的编辑生涯中,论成功和影响力,它比不上之前的《游戏报》,也比不上其后的《绣像小说》,但对于李伯元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从《世界繁华报》开始,李伯元开启了职业生涯中一个编辑家到一个小说家的转折,开启了人生中游戏花间模式到批判社会模式的转型。也是从这份并不起眼的报纸开始,李伯元正是迈向他作为谴责小说家的道路。
注 释:
① 长期以来,研究者一般认为1899年由游戏报馆分期印行的以吴语描写妓家生活的《海天鸿雪记》是李伯元最早的小说。但后来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该书并非李伯元所作,参见祝宇宙:《〈海天鸿雪记〉的作者并非李伯元》,《文学报》,1991年5月16日,第529期。本文采纳了这一观点。
[1]王学钧.李伯元年谱.李伯元全集(第5卷)[N].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2]张乙庐.李伯元逸事.李伯元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吴沃尧.李伯元传.李伯元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周桂笙.新庵笔记(卷三):书繁华报.李伯元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5]阿英.晚清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80
[6]薛梅.从《游戏报》看晚晴报纸的商业意识[J].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2,(2).
[7]李伯元.本报论前增添逐日路透社电音及东省要电告白[N].游戏报(第 160 期),1896-11-30.
[8]张乙庐.李伯元逸事.李伯元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郭道平.关于《庚子国变弹词》的资料来源[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4).
[10]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M].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李伯元.《庚子国变弹词》序.王学钧、李伯元年谱.薛正兴、李伯元全集(第5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2]阿英.弹词小话引.小说二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