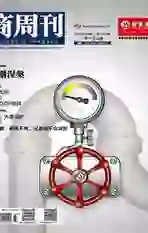青钢涅槃
2014-03-17宋鑫陶
宋鑫陶
策划前言
这将是一次钢铁业的集体迁徙——全国39家城市型钢厂。将在“十二五”期间搬离城市,迁向沿海、沿边区域。放眼世界,也鲜见如此大规模的产业搬迁。
水污染、大气污染、产能过剩。这都是催生城市钢厂搬迁的倒逼因素,而其背后则是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钢铁只是包括火电、石化、化工等在内的重污染行业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们的搬迁。是这个行业寻求新的生存之道的一种途径。也已然成为一种产业现象,被议论与探讨。
面对搬迁。很多行业的企业也都忧心忡忡。担心“不搬等死。搬迁找死。”其实不然,搬迁既然不是简单的位移和复制,就应该视其为一种再生发展的机遇,从而找寻到正确的生存路径。
“一座城市的发展路程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转型期的城市尚且如此,亟须转型的城市钢厂又何尝不是。
对于在城市已经无法辗转腾挪的钢厂来说,从城市退出,也许才真正意味着海阔天空。
在39家搬迁的城市钢厂中。青岛钢铁公司是首批纳入搬迁计划的5家钢厂之一,其余4家是重庆钢铁公司、杭州钢铁集团、石家庄钢铁公司和合肥钢铁公司。2011年。国务院也将山东作为国内唯一一个钢铁产业结构调整试点省。
对青钢而言,它的搬迁吸引着太多眼光,而它能否做好一个“循环经济的样本”,建成一个现代化绿色钢城。甚至能否成为钢铁行业搬迁的一个典型案例,都值得我们去了解和探究。
城市钢厂的前世今生
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的传记作者彼得·克拉斯曾说,“每一块钢铁里,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在中国,我们同样也可以对城市钢厂下一个类似的结论:每一家城市钢厂,都曾维系着一座城市经济的兴衰。
“很多钢铁企业都建在城市里面,有的还是先有了钢铁企业,才有了后来的城市。”青岛钢铁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钢”)党委书记、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王君庭说。这些钢铁企业的名称里往往带有城市的名字,因此也被习惯性地叫做城市钢厂,它们的出现是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诉求,亦带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在工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在乎的不是钢厂排放了多少污水和粉尘,而是它能生产多大的量,为国家贡献多大的产值,能不能手里也捧个“铁饭碗”。在计划经济时代,大而全的钢厂就是“铁饭碗”,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和招待所等,设施齐全。那时,人们“挤破头”地要进这样的国企,但没有“关系”往往是“挤”不进来的。
56岁的张占孝对此记忆犹新。他的父亲张腾芳在青钢干了16年的保卫科科长,直到退休。张占孝正是接了父亲的班,才得以进入青钢,从销售工作干到如今的青钢钢渣综合利用加工厂的厂长和青钢废钢管理部的部长,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钢二代”。
张占孝1958年出生,青钢也正是在这一年成立,最初的名字是“青岛第三钢铁厂”。他见证了青钢的起起伏伏,而青钢走过的历史也折射出我国钢铁工业发展的脉络。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时,我国几乎没有一家完整的钢铁联合企业。后来,在前苏联的援助下,才建设了鞍钢、武钢和包钢等钢铁厂,并逐步形成了“三大”、“五中”、“十八小”的发展格局;此后,在国家“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指导方针下,钢铁工业便开始了“大跃进”,走上了追求产值和产量增长速度为目标的粗放型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之后,面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机遇,国家对老的钢铁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和升级,并新建了上海宝钢、天津无缝钢管厂等一批现代化大型钢企;1996年,我国钢产量(粗钢)达到10124万吨,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产钢大国;2000年之后,我国钢铁业飞速发展;2005年,钢产量增长率曾一度达到30.42%;2006年,我国规模以上钢企实现销售收入25735亿元,仅次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排在我国39个工业行业的第二位。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曾给国内钢厂带来过不小的影响,青钢就曾因为产品单一,销售不出去,差点“关门”。但危机过后,钢企很快便又陶醉于追求“速度与激情”的产业氛围,而钢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也正是在2000年之后的这一飞速发展阶段开始显现出来。
这一阶段的钢铁企业并没有被“放任自流”。从“十五”开始,我国就相继出台了《关于制止钢铁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下调钢材出口退税率、《钢铁产业发展政策》、《钢铁工业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加快结构调整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国家的调控政策似乎收效甚微。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犹如“雪上加霜”,整个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终于“暴露无遗”。
人们似乎在一夜间发现,工厂的仓库里堆满了生产出来、销不出去的钢材,供大于求的市场正在一点点掐紧企业的脖子,让它们喘息艰难,整个行业的销售利润率在2012年已经低至可怜的0.04%。这一年,我国80家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下降98%。
“生存还是毁灭,这的确是个问题。”
“对本就步履维艰的钢企来说,去年重重落下的那根‘最后的稻草,叫环保!”越来越严重的城市污染和人们谈之色变的“雾霾”,让钢铁业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调查显示,2013年1月至5月,我国大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17个城市有钢铁企业。如果再佐以2010年的数据,钢铁工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和粉尘的排放量占了工业排放量的9.5%、6.3%、9.3%和20.7%。
如果说,在过去拥有一家钢厂曾经是一座城市的骄傲,如今,它正成为一个巨大的负担。
搬迁是这些城市钢厂最后的出路,而“环保搬迁”也似乎是它们想要完成脱胎换骨的最后救赎。
搬出一个“循环经济的样本”
2012年12月31日,人们像过去一样,沉浸在辞旧迎新的喜庆之中。
这一天像每一个新旧年交替的日子一样平凡,但对于王君庭和他领导下的青钢而言,这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也是注定将会被载入青钢历史的一天。因为,这一天,青钢搬迁获得了国家批复。所以,这不只是新旧年交替的一天,还是青钢要完成“新老交替”开始的一天。endprint
搬迁的批复一下来,张占孝就第一时间跑回家告知了父亲。这个退休多年,但总爱“打听”青钢新闻,看到关于青钢的新闻报道一字都不会漏掉的老人说出的第一句话是:“青岛市这个产业保住了,青钢有救了,青钢人有饭吃了。”尽管如今的青钢早已不再是1997年那次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命悬一线”,它也坚强地“挺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这样的语重心长,暗含的是几代青钢员工的企盼。
搬迁,既不是以搬迁之名对现有企业的简单复制,更不是污染搬家。在王君庭眼中,青钢的搬迁就是要搬出一个“循环经济的样本”。
“企业要减少污染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靠减量排放,而减量排放最重要的办法就是发展循环经济。”王君庭向记者描绘说,“搬迁到董家口之后,企业将不会有任何一根管道通向海里,做到了污水的零排放、零污染;水渣(炼铁的渣滓)不再像过去那样带着水拉出去,而是依靠先进的工艺,在车间内部完成,做到渣不出厂,再通过深加工,做成塑料、化工的中间体或添加物等产品,供给相关业态的企业;炼钢产生的尾气不会再排放到空气中,而是全部回收,用来发电,使自发电率由现在的13%提升至65%以上。”正是借助于污水处理中心、固体废物加工中心、热能供应中心、冷源综合利用中心等“四大中心”,青钢构建起了企业间的循环经济体系,并投资20.5亿元配套建设了15项重大节能环保工程。
传统经济模式是一种“资源一产品一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模式,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多。而循环经济所强调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则是以“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模式为导向,使工业建设与能源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和环境保护融为一体。
在记者看来,青钢要创造的是一个钢铁建设的新型模式。这个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要做到:主业突出,相关配套产业专业化。王君庭为这个目标所配套的方法是:不可控的绝对不做,可控的放开做。
“以前是我们(青钢)来运营和处理污水、脱硫、除尘等工作,环保部门来监督我们。现在我们的做法是,请国内粉尘或者脱硫最好的企业,找专业化的公司来运营,然后按照吨钢产量付钱给对方,所以就变成了他们来处理,我们来监督。”王君庭认为这既做到了专业化,又提高了效率。
在我国,青钢不是第一家这么运作的钢企,但却是最系统、最全面的。“我们主要是投资主流程,而辅助流程是为主流程服务的。主流程如果控制不了辅助流程,我们是不能做的。”王君庭并不担心企业双方在目标上的一致性,“他们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海水涨潮涨上来的,而是双方共同追求效益和利润。”除此之外,青钢发展循环经济还要借助于设备的大型化和装备的现代化,来提高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并通过采用先进的处理技术,加大硬件投资的力度。
事实上,作为一个总投资额高达164亿元的项目,青钢在环保上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
2013年10月10日,青钢与中冶赛迪、北京首钢国际、中治华天举行环保搬迁工程烧结、炼铁项目签约仪式;11月11日,与神雾集团签署了钒钛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合作框架协议;11月25日,北京利尔、青钢集团、青岛坤博签订城市钢厂环保搬迁石灰项目合作协议;12月17日,与中机国能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河北瞳鸣环保有限公司、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就能源综合利用热电项目、环保除尘系统BOT项目和2x240m2烧结机烟气脱硫BOT项目签约……
2013年最后几个月接连不断的签约合作,只是青钢近几年来在环保搬迁投入上的一个缩影。据悉,青钢搬迁项目环保的总投资额约为18亿元,占整个搬迁项目总投资的11%以上。
搬迁不是空间位移,而是产业转型升级
卖一吨钢的利润可以买到什么?这个问题放在如今的钢铁业多半带有自嘲的味道。
几年前,卖一吨钢的利润约是1000元,在当时可以买到一部平板手机;放到2013年前11个月来看,利润只有4.2元,差不多是现在一斤鸡蛋的价格;如果只算2013年上半年的吨钢利润,最低时只有0.43元,只够买一个鸡蛋。业内人士坦言,如今炼钢不如卖白菜。
一边是不断淘汰落后产能,一边是新项目不断上马,我国钢铁业陷入“越治理越过剩”的怪圈。钢铁价格一夜回到20年前,昔日的“高富帅”如今沦落为“矮穷挫”。
陷于严重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已经“积重难返”,既然搬迁不能只做空间上的简单位移,那么借助搬迁完成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了包括青钢在内的城市钢厂重生的机遇。
我国大规模的钢企集中搬迁发生在“十一五”后期,青钢的搬迁几乎是最晚的,之前有成功案例,亦有一些钢企不成功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国内一些靠几万亿元资金堆积的区域,当这些潮水般涌来的资金,又突然像潮水般退去的时候,原来的大产业构想和依靠集聚大型企业实现规模效应和影响力的想法也在瞬间土崩瓦解。除了大规模投资造成的高成本,这其中还有企业自身产品市场定位失误等方面的原因,而这都是“晚迁”的青钢应该吸取的。
青钢未来,路在何方?
“青钢将来的产品一定是要将我们的工艺和市场等结合起来,保留并升级原有的拳头产品系列,发挥多年来自身形成的优势。如果脱离了这个,那就相当于去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企业。青钢就不是搬家了,也失去了自身的优势。”所以,在王君庭的规划构想里,青钢要走“高端差异化”的产品战略,使高端产品比例由目前的10%提升到54%,产品出口比例提升到总产量的1/3,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并通过向产业链两端延伸和内部管理系统的完善,寻求盈利模式的改变。
与那些动辄千万吨产能的“大块头”钢企比起来,青钢显得身材“短小”了不少,产能只有400万吨,以优特钢为主。但“浓缩的才是精华”,青钢的焊接用盘条钢、钢帘线、胎圈钢丝的国内市场份额,都排在全国第一位。“未来,钢帘线、胎圈钢丝、弹簧扁钢等的传统优势要保留,并在现有产品基础上,增加弹簧钢、齿轮钢、轴承钢、耐蚀钢等制造业所需的高端、优质钢材,同时开发机械、汽车、造船、海洋工程、风电、核电等行业的高端特种用钢。搬迁之后,青钢400万吨的产能不变,但特种钢的比例将由现在的15%左右提升至55%。”王君庭介绍。因为主产品的新定位和变化,青钢也将更名为“青岛特殊钢铁有限公司”。endprint
“搬迁后青钢将实现三大转变:由传统的粗钢生产企业向专业化优特钢生产企业转变;由钢铁一业为主向以钢铁产业为核心、多元产业融合发展转变;由单一钢铁产品生产企业向多元钢铁深加工制成品企业转变,深加工比例力争达到总量的1/4。”青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刘铁牛认为,青钢要实现“三大转变”,实现成功搬迁和产业转型升级,离不开这几个目标:吨钢投资成本要低;新区新的钢铁运营成本要低;产品档次和竞争力要强;循环经济能源利用的水平要高;环保水平和履行社会职责的水平要高。
一个循环经济的样本,一个钢铁建设的新型模式,以及对发展思路、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的脱胎换骨的改变,加在一起便是青钢描摹的未来:打造一个“技术一流、产品一流、效益一流”的现代化绿色钢城。
最后的机会
受繁殖、觅食和气候变化等需要,动物界经常会出现大规模的集体迁徙。我国大量城市钢厂在“十一五”后期,开始了从城市市区向沿边、沿海等的城市郊区地带的大规模搬迁。约39个城市钢厂,近2.28亿吨的产能,这被认为是“自抗战时期以来,中国钢铁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它们的“迁徙”也跟动物界类似,是一种被动的生存需求。
事实上,早在2003年,青钢就有了搬迁的计划,只是一直没有得到相关批复,直到2012年2月才正式启动了环评。“2002年至2006年,其他钢厂的发展都比较快,很多年产100万吨的钢厂都借助这几年的发展,将生产规模提高到了千万吨,而青钢在这一时期一直发展得比较慢。”刘铁牛觉得,如果青钢早一步搬迁,“兴许还会多赚两年钱”。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青钢搬迁的时间是晚了一点,但似乎晚的正是时候。过早搬迁的企业,没有对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充分预估,如今反倒进退维艰。而青钢在钢铁行业充分暴露问题之际,启动搬迁,却恰可以在市场和现实面前,更清晰地决策未来的发展走向。刘铁牛认为,青钢抓住了这最后一个机会。
不搬迁,城市钢厂将会受困于狭小的城市空间,无法辗转腾挪。一旦搬迁,将需要巨大的投资成本,迁入地的选择也需要仔细考量。
我国钢铁工业“北重南轻”,东南沿海对钢材的需求量很大,而环渤海地区近4亿吨的钢铁产能中,50%以上的产品需要外销,便捷的物流将会降低钢企成本。因此,钢铁生产地与钢铁需求地应该有一个距离上的匹配。
董家口,这个有着千年琅琊文化,并与秦皇岛长城有关联的区域,如今已超脱文化的勾连,成为承接青岛东部城区和西海岸经济新区中心区传统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未来,董家口港区还将是国家大宗散货集散中心和重要的能源储运中心。据刘铁牛介绍,青钢也曾考虑过其他区域,但最终选择了董家口临港产业区,厂区离董家口港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只有4公里,并且已筹建了青钢专用矿石泊位和钢材发运泊位,而且有着更优化的销售半径。
工信部原材料司副司长骆铁军曾说,钢厂搬迁通常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城市发展让你搬,你在那儿根本呆不下去了;二是,要有钱搬;三是,要以人为本,不能搬得太远,不然人员问题解决不了。
青钢也正是为了解决人员安置问题,规划建设了“青钢小镇”项目。这个可以“背山面海望琅琊”的搬迁配套生活区,距离新厂区只有约15分钟的车程。它的建筑设计在结合“欧洲现代都市”与“欧洲古典小镇”的建筑语言的同时,传承着青岛传统的城市建筑文化。
这样的配套生活区搭配零污染、零排放的新厂区,人们也许很难想象未来青钢的全新景象。它不再会像过去的钢企一样留给人们“傻大黑粗”的刻板印象,也不再会让人们对“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怨声载道。没有了飞扬的粉尘和浓浓的白烟,变得洁净而绿色。紧邻碧海蓝天,掩映青山绿水,人们也许会感叹:这还是钢企吗?但这正是青钢未来的景象。
2014年的春天已经来了,但没有人敢断言这会是钢铁行业的“春天”。青钢真正的搬迁动作,也将在这一年开始实施,人们期待它的“凤凰涅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