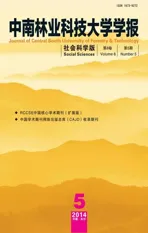力透纸背的苍凉
——《永别了,武器》的美学意蕴
2014-01-21张媛
张 媛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力透纸背的苍凉
——《永别了,武器》的美学意蕴
张 媛
(江苏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镇江 212003)
《永别了,武器》力透纸背的苍凉表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景物描写、人物描写,无论是战争与死亡描写,还是爱情与性描写,一切都冷静而客观,没有热度和温度,显示出一种切骨的苍凉。形成的原因当然很多,既与作者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也与作者写作时的心境有关,还与作者的艺术追求有关。苍凉比“迷惘的一代”、“虚无主义”等标签更贴近文本和作者写作时的实际情况,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美学内涵。
《永别了,武器》;苍凉;原因;美学意蕴
《永别了,武器》是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早期代表作,被誉为现代文学的经典名篇。中国大陆学界对于《永别了,武器》的研究,与对《老人与海》的研究一样,具有相当的热度。查“中国知网”,在“篇名”栏分别输入“永别了 武器” “老人与海”,检索到的论文分别是165篇、745篇①中国知网,截止时间为2014-06-17,http://epub.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 i x=CJFQ。。在这165篇研究论文中,对于《永别了,武器》的研究似乎方方面面都已经有所涉及,有对于主题的研究,有对于人物形象的研究,有对于叙事手法和文体修辞的研究,有对于翻译的研究,等等,不一而足。但从文本出发,对弥漫文中的苍凉展开研究的还未见到,笔者拟从此入手,探讨苍凉形成的原因,进而探讨苍凉在美学上的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一、力透纸背的苍凉
通常认为,《永别了,武器》的主题或者作者创作的主导思想是表现战争与爱情的悲剧,不少论者都由此立论。这并没有什么错,《永别了,武器》实质上就是两个告别:告别战争、告别爱情。问题是作者在告别战争、告别爱情时候的态度、主导思想是什么?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是迷惘,有人认为是虚无,有人认为是幻灭,有人认为是荒诞意识,等等。
笔者认为,如果从文本入手而不从观念入手,弥漫《永别了,武器》中的不是迷惘、虚无、幻灭、荒诞等等,而是力透纸背的苍凉。
苍凉的本意是荒芜悲凉,既指外在的环境,更指的是一种心境,一种美学意蕴。《永别了,武器》的苍凉表现在方方面面,无论是叙述方式,还是景物描写、人物描写,无论是战争与死亡描写,还是爱情与性描写,一切都是冷静而客观,没有热度和温度,显示出一种切骨的苍凉。
从叙述方式看,作者采用回望的姿势,本身就充满物是人非的苍凉与沧桑。《永别了,武器》是自传性色彩很浓的长篇小说,男主人公亨利中尉的战时经历与海明威的经历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很多论者已经形成的共识。这种作者和作品主人公经历的重叠,很容易造成作者主观情感因素介入小说的叙述中。因此,选择什么样的叙述角度是决定小说基调的关键。把叙述者定位在恰当的时间点,将造成不同的审美效果。美国海明威研究专家格莱布斯登(S.N.Grebsiein)曾敏锐地发现海明威《永别了,武器》的叙事特征:坚持采用过去式这种叙述时态,尽量拉长叙事时间距离,这样就可以在叙事中造成历史苍凉感与沧桑感。这种苍凉感与沧桑感在文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如第1章:“那年晚夏,我们住在乡村的一幢房子里。”[1]第18章:“那年夏天我们过得幸福快乐。”[1]第19章:“那年夏天就那么过去了。”[1]第22章:“那天夜里天气转冷。”[1]第38章:“那年秋天的雪下得很晚。”[1]简单看看每章的开头句,就能够给人惘然若失的沧桑感。这种叙事方式与“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苍凉与沧桑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描写方式看,无论是景物描写,还是人物描写,同样充满这种苍凉与沧桑。
在描写景物时,作者采用两两对照的方式,将赏心悦目的美景与战争背景巧妙地罗列在一起:“附近乡下,炮比从前多了好些,而春天也到了。田野青翠,葡萄藤上长出小青芽,路边的树木吐了叶子,海那边有微风吹来。我看见那小镇和小镇上边的小山和古堡,众山环绕仿佛是只杯子,背后便是褐色高峰,山坡上稍有青翠。小镇里炮更多。”[1]意大利旖旎的自然风光与战争带来的灰尘并列,形成鲜明的对照。“望见两道山脉呈一片翠绿和黛色,直至覆雪线处,而覆雪处则是洁白一色,在阳光下颇为赏心悦目。随着公路沿山脊向高处蜿蜒,我又看到了一道山脉,那是海拔更高的雪山山脉,呈白垩色,沟壑纵横,千姿百态,而在远方群山连绵,望上去亦真亦幻。这些高山峻岭都是奥地利人的,我们这边可没有。”[1]奥地利的美景与作者的调侃并列,增加了反讽的意味,表现了饱经世事的苍凉与沧桑。
在描写人物时,简洁的对话描写和心理描写结合。贯穿全篇的对话描写是一种实事求是、就事论事的基调:“找配件有什么困难吗?”我问那技工中士。“没有困难,中尉先生。”“现在油库在什么地方?”“还在老地方。”[1]整个对话干净利落,显得冷静、客观、冷漠。这种冷静、客观、冷漠在心理描写中表现得更为充分,突显了人物内心的荒凉:“夜间醒来,爱人依然旁卧,而非梦醒不见丽人眠。这才是真实的,其他的一切均为虚情幻境。……我们在一起时也有孤独感,而那是与外人不相容所产生的孤独感。”[1]海明威以冷静客观的笔触描绘出主人公孤独、冷漠、苍凉的心态。
对于《永别了,武器》的两大主题——战争与死亡、爱情与性的描写,同样充满这种冷静与冷漠、苍凉与沧桑。
在描写战争与死亡时,作者不动声色的冷漠与冷静更是让人惊异,这在描写自己喜欢的艾莫离开这个世界时表现得特别充分:“艾莫正在跨过铁轨,身子一晃,绊了一下,脸孔朝地跌了下去……皮安尼放下他的头,拿块急救纱布擦擦他的脸,也就由他去了。”[1]完全的零度写作,看不到丝毫情感因素,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有的只是漠然:“艾莫躺在泥土里,跟路堤成一个角度。他人相当小,两条胳膊贴在身边,裹着绑腿布的双腿和泥污的靴子连在一起,军帽掩盖在脸上。他的样子真像尸首了。天还在下雨,在我所认识的人们中,我算是喜欢他的了。”[1]这种冷漠的确让人震惊,背后显露的同样是疲惫、漠然、苍凉和沧桑。
在描写爱情与性时,作者没有茨威格、司汤达似的热情,保持着曾经沧海似的沧桑。如亨利和凯瑟琳第一次接吻的描写:“我亲一亲她那一对合拢的眼睛……我知道我并不爱凯瑟琳·巴克莱,也没有任何爱她的念头。这是场游戏,就像打桥牌一样,不过不是在玩牌,而是在说话。”[1]“天知道我本来不想爱她。我本来不想爱什么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可爱上她了。”[1]这里没有激情燃烧,只有心如止水、不动声色的冷漠与冷静。特别是小说结尾关于凯瑟琳去世的描写:“看来她是一次接连一次地出血。他们没法子止血,我走进房去,陪着凯瑟琳,直到她死去。她始终昏迷不醒,没拖多久就死了。”[1]没有撕心裂肺,没有痛不欲生,没有悲愤,没有热情,也没有激情,留下的是漫不经心的漠然与饱经忧患的苍凉。
综上所述,《永别了,武器》就文本的叙述方式、描写方式、战争与爱情两大主题的呈现看,弥漫文中的是力透纸背的苍凉。无论是回望的写作角度,还是两两对照的环境描写,无论是战争的生死考验,还是爱情的旖旎迷人,无论是反讽,还是象征,无不显示出时过境迁后的惆怅,世事沧桑的惘然,理想幻灭后的虚无,激情消失后的冷漠,看破红尘后的无奈,无不彰显着作者荒凉、沧桑、苍凉的心境与情感。
二、苍凉形成的原因
形成《永别了,武器》这种苍凉基调的原因当然很多,大致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展开分析。
首先,与作者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海明威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非正义性、残酷性、长期性,无疑是形成《永别了,武器》苍凉风格的最重要原因。
1918年,海明威费尽心力参加了红十字会救护队,后负伤住院,因作战勇敢荣获美国和意大利授予的勋章[2]1。这给创作《永别了,武器》提供了素材,也提供了反思。海明威满怀热情投入的这场战争,却是毫无意义的战争,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神圣或光荣的东西:“这是一条胡闹的战线。”[1]“人人都憎恨这战争。”[1]“抽象的名词,像光荣、荣誉、勇敢或神圣,倘若跟具体的名称放在一起,就简直令人厌恶。”[1]“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1]这场战争的无意义无疑是作者人生理想幻灭并形成苍凉之态的最重要原因。
战争的残酷、胶着更加重了这种苍凉。海明威亲身经历的意大利战场的战争胶着于在欧洲战场的南线——意大利和塞尔维亚对阵德奥,而“意大利军队的战斗力低到什么程度?一个连的德奥士兵挺着刺刀一冲锋,光意军战俘就抓了9000人。意大利的失败被称为雪崩,几十万大军上前线,一两天就完蛋了。”[3]历史学者袁腾飞虽然是调侃,但也多少反映了当时意大利战场的实际情况。血与火的洗礼,使海明威真正认识到战争是什么:战争是血泊,是地狱,是黑暗中痛苦的嚎叫,尸体上没有丝毫美感可言,炮弹休克的身上更没有丝毫尊严可言。战争的残酷无情,无疑改变了海明威对战争的梦幻:“是勇敢吗?……其实是一种冲动。”[2]“愤怒在河里被洗掉了,任何义务责任也一同洗掉了……我只是洗手不干了……但是这已经不是我的战争。”[1]
其次,与作者写作时的心境有关。《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于1922年,小说最后于1929年出版。作为自传性作品,距离此前的战争已经10年,而过去的10年,整个世界和海明威本人都发生了很多变化。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恐慌,百业凋敝,工人运动高涨,知识分子左倾,这种变化必然影响海明威的心境。自1922年到1929年,海明威亦因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他结了两次婚,他父亲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医治无效饮弹自尽。他本人由于战时受伤导致长期失眠,入睡后又常常被噩梦惊醒,旧病发作后常常陷入理性失去控制的状态。整个世界的巨大变化和海明威的这些遭遇,使他反复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将自己的感情和经历倾注于艺术创作中。由于经过了较长时间, 海明威可以更从容地反思投身战场的冲动,这是《永别了,武器》形成苍凉基调的又一原因。
第三,与作者的艺术追求有关。海明威运用自创的“冰山原则”,将简洁、凝练、朴实文风推向极致,写作时始终保持“冷静、超然和含蓄的态度”。这种“冷静、超然和含蓄的态度”在《永别了,武器》中达到了令常人难以理解的程度,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比如丁放鸣(1983)[4]、杨丽丽与张青(2003)[5]、吴静(2010)[6]都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不赘述。笔者想要强调的是,海明威自己坚持的冰山理论,是形成苍凉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三、苍凉在美学上的意义
对于《永别了,武器》中的苍凉,人们很少提及。一般的提法是所谓“迷惘”、“虚无”,要探讨《永别了,武器》的苍凉在海明威作品中的美学意义,首先应该厘清人们加在海明威头上的“迷惘”、虚无两个标签。
首先是所谓“迷惘”或者“迷惘的一代”。“迷惘”就其本义来说指“由于分辨不清而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迷惘的一代”则是一个专有名词,是由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于1921年提出的,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的题词就是“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从此“迷惘的一代”成为海明威及其作品的标签和称谓。人们常将《永别了,武器》誉为反映“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中国海明威研究者大致继承了这一说法,早在1988年,胡频就以《揭示迷惘 讴歌反战——从《永别了,武器》评介开去》为题展开评介[7],何小丽(1994)[8]、王云(1994)[9]、魏钟(2000)[10]、朱春燕(2005)[11]、张健稳与张晨虹(2005)[12]、王晓雁(2006)[13]、陈彦平(2007)[14]、霍卫国(2013)[15]等陆续发表了特有相似观点的论文。
将《永别了,武器》的基调定位为“迷惘”或者“迷惘的一代”,不能说一点道理都没有,但笔者感到多少有隔靴搔痒、乱贴标签的嫌疑。从主题上说,《永别了,武器》是明确的,谴责战争的种种罪恶和愚蠢,没有“分辨不清而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迷惘;从海明威的写作情况和文本说,作为自传性作品,他“身上的伤疤已经由紫变白,战争的遗患已经消失净尽”,他可以拉开距离从容、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回首往事时让人们感受到的是苍凉,而不是所谓迷惘;从海明威的个性说,他个性激烈、坚韧刚毅、勇敢正直、不怕挫折、永不言败,好胜心与虚荣心几乎是同等程度地并存于他的性格之中,与所谓 “迷惘”也不搭界。对于“迷惘”或者“迷惘的一代”的标签,海明威自己都不认可:“我没有迷失方向……我们是坚强的一代人”[2]。
综上,认为海明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是所谓“迷惘”或者“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还大致靠谱,有他的题词为证;认为《永别了,武器》反映的还是所谓迷惘,就多少有些脱离文本的嫌疑。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苍凉应该是《永别了,武器》整个作品的基调。
第二是所谓虚无主义。这也是评价海明威《永别了,武器》常用到的标签。中国海明威研究者李晓珍(2003)[16]、肖健与吴宇(2012)[17]等也发表了类似观点的论文。表面上看,海明威与虚无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库·辛格在《海明威传》中曾这样描写海明威:“意大利、西班牙、墨西哥和古巴等拉丁国家就像他自己的故乡。”[2]“西班牙信奉虚无……海明威成了天主教徒,同时又阐释虚无这个主题。虚无即有生之日的空虚,令人激动的荣誉的空虚,人生悲剧的空虚。”[2]“这种虚无同这位富于反叛精神而无意讲究美学的作家形影不离,他始终在奋力揭露一个虚伪怯懦的新世界,一个已经失去理想和不愿面对现实的世界。”[2]但严格地说,海明威并没有达到叔本华关于虚无的哲学高度。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之否定,亦即人们称为彻底的清心寡欲或神圣性的东西,经常总是从意志的清净剂中产生的;而这清净剂就是对于意志的内在矛盾及其本质上的虚无性的认识。(至于)这种矛盾和虚无,则是在一切有生之物的痛苦中表现出来的。”[18]“没有彻底的意志之否定,真正的得救,解脱生命和痛苦,都是不能想象的。在真正解脱之前,任何人都不是别的,而是这意志本身。这意志的现象却是一种在幻灭中的存在,是一种永远空无所有,永不遂意的挣扎努力,是上述充满痛苦的世界;而所有人都无可挽回地以同一方式属于这一世界。”[18]《永别了,武器》虽然与战争、爱情告白,但并没有达到“彻底的意志之否定”,在苍凉的背后,还是充满生的意志,爱的欲望。
因此,可以这样认为,《永别了,武器》的苍凉与《太阳照常升起》的“迷惘”、《老人与海》的坚强,构成了海明威不同阶段的不同创作风格。
实际上,苍凉这一概念与生气勃勃、历史短暂的美国渊源并不深,它与饱经忧患、历史悠久的中国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真正看透人生苍凉的中国文人当数苏轼,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论述“苏轼的意义”时曾对这种“苍凉”“空漠”有很好的表述:“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19]在苏轼词作中也有大量类似的表述,比如“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20]“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従此逝,江海寄余生。”[20]“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20]等等。《永别了,武器》里面的“苍凉”,类似于苏轼的“空漠”。由于文化传统、经历、时代、社会的原因,《永别了,武器》里面的“苍凉”不可能发展到苏轼“空漠”那样充分。
《永别了,武器》的苍凉与张爱玲更为接近,这当然有时代、社会的原因。
“苍凉“意识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底色和感情基调。张爱玲在《传奇·序》中曾说:“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中有这惘惘的威胁。”[21]张爱玲用浓重阴郁的色彩写尽人世的晦暗,在化不开的愁怨中表达对人生真相的质疑。《十八春》、《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作品在看似随意的轻描淡写中营造出一种苍凉的气氛,构成凄婉、哀怨、苍凉的悲剧美。
止庵先生在《张爱玲的苍凉和残酷》中,对张爱玲做如是评价:“张爱玲的一生跟温暖大概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张爱玲的苍凉味非常重。是后期的主要的基调……她的小说更多的是对于人生的这种不如意,人生的这种无奈。我觉得,张爱玲对于人生的看法是活着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得活下去。再往下说就是得找一个生存的理由,找一个立足之地。”[22]
因此,从深的角度说,《永别了,武器》里的苍凉,表现了苏轼似的“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表现了“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从浅的角度说,表现了张爱玲似的“活着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得活下去”。从这个角度展开分析,《永别了,武器》的“苍凉”就具有了与老生常谈的“迷惘的一代”“虚无”不同的美学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永别了,武器》的解读,其实是有多种不同答案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苍凉角度进行解读,对于丰富其内涵,多少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1] 海明威. 永别了,武器[M].林疑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2] 库·辛格.海明威传[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3] 袁腾飞.这个历史挺靠谱(袁腾飞讲世界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4] 丁放鸣.冰山的八分之七和八分之一——试论《永别了,武器》的思想、艺术含量[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3,(1):117-123.
[5] 杨丽丽,张 青.不着一字,尽显风流——也谈《永别了,武器》中的“冰山”风格[J].河西学院学报, 2003,(6):65-68.
[6] 吴 静.“冰山原则”在《永别了,武器》场景中的运用(英文)[J].海外英语,2010,(8):201-204.
[7] 胡 频.揭示迷惘 讴歌反战——从《永别了,武器》评介开去[J].电影评介,1988,(10):15.
[8] 何小丽.《永别了,武器》与海明威的迷惘主题[J].中文自学指导,1994,(6):30-31.
[9] 王 云.他属于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永别了,武器》中的亨利[J].外国文学研究,1994(1 ) :79-83.
[10] 魏钟.迷惘的硬汉子——试析《永别了,武器》中主人公亨利的形象[J].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4):37-39.
[11] 朱春燕.“迷惘”的主题——评析《永别了,武器》(英文) [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 (4): 62-65.
[12] 张健稳,张晨虹.迷惘的情绪,悲观的色彩——再评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5,(6):21-23.
[13] 王晓雁.“迷惘的一代”的心声——浅析海明威的小说《永别了,武器》[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06,(2):19-21.
[14] 陈彦平.《永别了,武器》中“迷惘一代”的精神特色[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11):33-34.
[15] 霍卫国.从《永别了,武器》的意象看“迷惘的一代”的悲剧必然性[J].文学界(理论版) ,2013,(1): 217-219.
[16] 李晓珍.存在·虚无·探求——再读海明威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4):25-27.
[17] 肖 健,吴 宇.战火之下的虚无印象——《永别了,武器》中的象征意义剖析[J].江淮论坛,2012,(4):184-187.
[18] 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9]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20]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1] 张爱玲. 流言·传奇序[M].上海:五洲书报社,1944.
[22] 止 庵.张爱玲的苍凉和残酷.[2014-06-18].http://culture.ifeng.com/renwu/special/zhangailing/ziliao/detail_2010_12/13/3486103_0.shtml.
Penetrating Desolation——Aesthetic Connotations of A Farewell to Arms
ZHANG Y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Jiangsu, China)
Penetrating desolation in A Farewell to Arms manifests itself in many ways. Whether in narrative mode or scenery description or characterization, or about war and death description or depiction of love and sex, everything is calm and objective, without heat and warmth, showing a deeply ingrained sense of desolation. There are of course a number of different reasons for this. The major factor contributing to desolation in the novel is the writer’s early experiences of war. This desolation is related to Hemingway’s mental state while writing as well. The writer’s artistic pursuit is also a relevant element. Desolation is much closer than labels such as ‘the lost generation’ and ‘nihilism’ to the text and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Hemingway creating this work, which contains extremely profound aesthetic connotations.
A Farewell to Arms; desolation; reasons; aesthetic connotations
I106.4
A
1673-9272(2014)05-0127-05
2014-06-27
张 媛(1973-),女,重庆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赛珍珠和英美文学。
[本文编校:罗 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