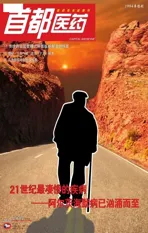走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世界
2013-10-19高军,纪玉英,侯玉岭等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已占到全世界患者的四分之一以上。在这样一个沉重的比例下,庞大的患者群体以及他们的家人子女都在如何生活?阿尔茨海默病给患者自身以及他们的家属,乃至整个社会都造成了哪些影响?为此,记者走访了相关医生、护士以及部分患者家属,希望在与他们的交流中,将一个更直观的阿尔茨海默病呈现给广大读者。
患者 令人心酸的“幸福”
在北京某知名三甲医院,一位从事阿尔茨海默病治疗多年的医生向记者简单描述了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内心世界。“患者一旦出现了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症状,他就不再有完整的自我了,随着病情的发展,患者会慢慢失去部分记忆和意识。阿尔茨海默病也可以说是一个逐渐的‘自我丧失’的过程,有点像我们常说的‘返老还童’。在某种意义上讲,患者本身是没有什么痛苦的,甚至可以说是‘幸福’的。”这位医生说道。“与阿尔茨海默病打了这么多年交道,眼看着病魔一点点‘抹去’患者的记忆,使他们或快或慢地走向木讷,与家人彼此陌生,而自己却全然不知,作为医生的我,也曾为此唏嘘不已……”
在谈及阿尔茨海默病对患者自身造成的影响时,这位医生说起了他的一些亲身经历和体会:“在我收治的患者当中,有些人见到异性就脱裤子,甚至当众手淫,这是一种本能的表现,与伦理道德无关。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把患者领到无人的场合,任由他去做吧,痴呆患者本来就没有什么生活乐趣了,对于他而言,这也许就是生命中的最后一点快乐了,我们又何必去剥夺它呢?只要不影响别人,就没必要横加干涉,更没必要以‘品德败坏’等言语刺激患者,这样做毫无意义。”
家属 撑着坚强的“无助”
“大概是从两年前开始,我爱人出现了健忘、抑郁、情绪不稳等一系列症状,最开始也没觉得不妥,以为只是更年期的问题,直到几个月前,她开始不认人了,我才发现问题的严重。”一位来自武汉的患者家属在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病房的走廊上与记者聊了起来。“听说北京治这个病效果好,我们就过来了。目前已经住院两个星期了,每天就是固定的打针吃药,也没见有什么好转。我也在网上查了,痴呆症只能通过药物尽量减缓病情的发展速度,并没有什么药可以有效治疗,如果还是这样,这周我可能就要办出院手续回武汉了。”这位家属说道。通过了解记者得知,患者刚满60 岁,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人群中算年龄偏低的。“我爱人出现轻微痴呆症状时,主要是变得不爱说话了,她常站在窗前望向大街发呆,像是在等着我和儿子回家,我们在家陪她时,她却总是发脾气。她以前是个非常开朗又要强的人,家务活从来都不让我们父子俩做,在工作单位也是业务骨干,没想到两年时间就彻底变了一个人……”说到这里,这位身材魁梧的湖北汉子把头转向了另一侧,避开了记者的目光。
在另外一位女性痴呆患者的床前,一位两鬓斑白的老者正在为平躺着的老伴按摩。当记者说明来意后,老人向记者不停地摇摆着手臂,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巧合的是,老两口的儿子正好走进了病房,在看了一眼表情呆滞的母亲后,他表示可以给记者五分钟时间。
在简短的采访中,记者得知小伙子一家是山西人,孤身一人在北京打拼,父母在老家务农。作为家中惟一的孩子,当得知母亲发病后,他就将父母一起接来北京,并为母亲联系医院治疗。今天也是下班后赶到医院,准备接替陪护了母亲一天一夜的父亲。“其实真没什么好说的。母亲得了病,我这当儿子的就是责无旁贷的事,赶上这么个治不好的病,我跟父亲只能坦然面对,积极治疗。”当被问及目前母亲的治疗情况时,小伙子有些动容地说道:“住院后,病情好像发展得更快了,刚住了一个星期,母亲就从一个还能有简单交流,生活基本能自理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无法交流且生活完全依赖别人的人,我觉得并不是医院的治疗有什么问题,而是当初不应该把母亲送到北京来。”小伙子接着说道:“突然换了环境,母亲恐怕很难适应,如果这样,还真不如我们父子回老家照顾她呢,老家的医疗条件比北京也差不了多少的,只是我的工作刚有些起色,就这样放弃,有些可惜了……”
说起家属与患者的关系,一位医生向记者讲起了她经历的故事:“记得几年前,我应患者家属要求,参加了一次‘家庭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是否要将痴呆多年的老母亲送到养老院’。患者家属之所以希望我参加,一是因为我作为老人的主治医生多年,对老人的病情非常了解;二是希望我从医学的角度提出一些专业的建议,综合评估一下老人目前的情况,送到养老院是否可行。本来是个挺好的事,可真到儿女们开始商量之时,这个会议就慢慢‘变了味’,大家从 ‘该不该送养老院’的讨论,演变成了‘孝顺与忤逆’的大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医生向记者介绍说,老人有三男一女,四个孩子,自从老人得了病,一直都是由小女儿照顾,其他兄弟三人按月交给妹妹一定数额的抚养费,直到半年前,长期腰疼的小妹查出了腰椎间盘突出,才找来哥哥们,提出轮流照顾老人的要求。当时,三兄弟还没有什么照顾痴呆老人的经验和思想准备,对于阿尔茨海默病须全天候看护,发病之后会打人骂人摔东西等情况始料不及,没过几个月,就开始叫苦连天,赶紧找来小妹和医生,商量送养老院的事情。“我记得当时小妹说‘妈妈她三儿一女,最后却被送进了养老院,你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这么多年我是怎么照顾过来的,怎么到你们那就不行了呢?!’说到此处,小妹泣不成声。三个哥哥则表示在家照顾多有不便,养老院照顾老人比家人更有经验等等,这事最后也没有达成共识,反而让兄妹之间伤了和气。”
“在我收治的患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曾受到过家庭暴力,老人身上都是一块块的淤青,非常可怜。”这位医生分析说:“之所以这种情况比较典型,是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在初期阶段的一些表象往往会被人所忽视,患者的种种反常行为会引发家庭矛盾,而作为家人,却还没有认识到这是病,导致与患者发生争执,甚至家庭暴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长期照料痴呆患者的家属或保姆,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往往得不到患者的认可与感激,反而会遭到猜忌甚至打骂,造成家庭气氛紧张,自身精神压力大,从而引发家庭暴力。”
“其实我认为,将痴呆病患者送到专门的治疗及养老机构,并非是件坏事。这样做不但可以让患者得到更科学的治疗,也同时拆除了家里的‘定时炸弹’,使家人的生活质量大幅提高,只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此外,中国人传统的‘孝道’也在其中起了反作用,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就是不孝吗?我觉得不尽然,久病床前无孝子,在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庭中不是个例,而是通病。与其这样,又何必苦守着所谓的‘孝’字不放呢?把老人‘囚’在家里,满身青紫,你们又是在‘孝’给谁看呢?”
社会 无法卸下的“负担”
关于痴呆患者对于社会的影响,在采访中,很多医生都认为是多方面的,而其中最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走失,一旦发现不及时,后果往往很严重。一位医生回忆道:“记得去年在贵州发生过一起老人离家走失事件,四个儿子找遍了老人可能去的任何地方,也发动了警察、亲友,甚至在网络上一起寻找。从他们调取的小区监控录像上看,老人是向郊区方向走的,录像也只记录到了老人进入郊区之前。在最后一处录下老人身影的地方及周边,大家苦苦寻找无果。三天后,老人被发现冻死在了离市区几十公里外的一处建筑工地的基坑内……”
天坛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也提到了患者容易走失的问题:“那天早上有个护士带着患者去做常规检查,护士就是去趟洗手间的工夫,患者就消失了。当时那个护士一再叮嘱患者站在原地别动,等她回来,前后最多两分钟,人就丢了。“当时我们找遍了医院,也看了监控录像,发现患者自行走出了医院大门,我们一路追下去,却没发现任何线索,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东单派出所的民警联系到了医院,才知道老人找到了。” 这位护士继续说道:“患者当天其实是穿着病号服的,走了那么远的路,也没人注意到他,要不是深夜被好奇的路人发现,又正好赶上当时是夏天,气温还不算低,恐怕就真出大事了。”
“如果按照业内普遍认同的我国60岁组老年期痴呆患病率约为5%,一个痴呆症患者平均每周的治疗及用药花费1000 元左右计算,每年全社会将为此增加4600 多亿元的负担。”一位医生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有‘医保’或工作单位,能报销的患者还好一些,对于一些外地来京治疗以及工薪收入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然,医保基金每年也在为这类患者及家庭分担着巨大的压力,占用着大量的医疗资源,政府还要投入大量的经费建设养老机构等等。这个病不同于其他疾病,虽不会直接危及生命,但却无法治愈。如果把病情的发展比作一条向下延伸的坡路,各种治疗手段也只是能将这个向下的坡度尽量减缓些而已。可是家属却往往不能理解,总认为花了那么多钱,结果还是看着老人每况愈下,感觉这钱花得冤啊。”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表示,痴呆患者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无法与家人沟通,生活需要有人照顾,家庭条件好些的可以请保姆,不然就要有人全天候陪在患者身边,更何况还有好多家庭信不过保姆,认为只有家人照顾才放心,这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拖一”甚至“一拖全家”的局面,为此,他也希望通过本刊呼吁尽快完善社会支持性服务体系,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更多专业机构,培养更多专业护理人才,在给患者提供专业照顾的同时,“解救”患者家属,让他们重返工作岗位,为家庭增加收入,为社会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