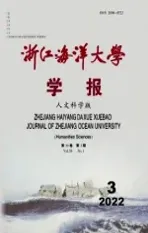《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
2011-08-15王守亮
王守亮
(山东轻工业学院文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3)
《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
——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
王守亮
(山东轻工业学院文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353)
南宋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并非刘向编撰,他只是做了编校订正工作。此说不确。全面解读《说苑叙录》、《汉书》刘向本传和《汉志》著录,可知三书为刘向编撰;《论衡·超奇篇》所说刘向“抽列古今,纪著行事……累积篇第”,以及三书收录西汉当代故事,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刘向三书是唐前规模最大的短篇历史故事集,开魏晋六朝志人小说先河,创立了魏晋六朝小说分门别类的编撰体例和模式。刘向为汉魏六朝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不应也不能忽略的小说家。
刘向;《新序》;《说苑》;《列女传》
在《新序》、《说苑》和《列女传》的研究中,一个向有争议但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是,三书是否刘向领校皇家藏书时“旧本有之”[1]762的前人成书?这不仅是一个刘向著作权判定和归属的问题,而且关系刘向与此三书文学史地位的评价,所以不应轻视,确有考辨的必要。
先说《新序》和《说苑》两书。
自南宋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新序》和《说苑》并非刘向编撰,他只是做了编校订正的工作。首倡此说者是宋人黄震,《黄氏日抄》云:“《说苑》者,刘向之所校雠,去其复重与凡已见《新序》者,而定为二十卷,名《说苑》。”[2]“校雠”之义,据刘向《七略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3]19故可知黄震之意乃谓《说苑》非刘向之作。后世遂不断有发挥此说者。清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七云:“此二书(按:《新序》、《说苑》)旧本有之,向重为订正,非创自其手也。”[1]762近人罗根泽《〈新序〉、〈说苑〉、〈列女传〉不作始于刘向考》一文认为三书乃当时之成书,已有定名,刘向只是“得读而校之”[4]228。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十认为:“当时本有《说苑》之书,向但除其与《新序》复重者,为之条别篇目,令以类相从耳。《新序》序录虽亡,度其体例,当亦与《说苑》相同。”[5]赵善诒《新序疏证·前言》亦谓《新序》和《说苑》“均非(刘向)自撰”[6]。如此等等,类似的看法尚多。
以上诸家之说所据主要为宋本《说苑》载刘向《叙录》,云: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後(按:当为“復”)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谨上)。[3]47
《叙录》所谓“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云云,容易使读者产生《说苑杂事》亦即《说苑》并非“臣向书”的认识,进而认为《新序》的作者亦非刘向。但如此理解却忽略了对《叙录》文意的整体把握。对于这段文字,徐复观曾分析提出三点意见:(一)“说苑杂事”乃刘向对许多积聚在一起的零星言论和故事所加的统一称呼,指藏于中秘的一堆材料,尚未勒为一书;(二)是刘向说对这一堆材料的整理。先从此中撰为《新序》,次将“浅薄不中义理”者编为《百家》;(三)是刘向说他编撰《说苑》的情形。即将编撰《新序》、《百家》后剩下的材料,再加上汉代的新材料,勒为《新苑》一书。徐先生还通过《新序》、《说苑》与韩婴《韩诗外传》有关故事的比较,认为“《新序》、《说苑》之作,盖承《韩传》之统绪而有所发展。其非先秦本有《新序》、《说苑》之书,更为明显。”[7]徐先生的分析全面而融通,说明《新序》、《说苑》乃为刘向编撰。
这从《汉志》也可以得到证明。《汉志》著录《新序》、《说苑》为“刘向所序”[8]1727。此所谓“序”若释为编订、次序之义,则两书均可视为非刘向之作。但我们认为,“序”解释为“叙述”、“叙写”也许更为妥当。《说文解字》段玉裁注:“次弟谓之叙。经传多假‘序’为‘叙’。”[9]“序”的这一意义见于汉魏六朝文献的使用。东汉王逸《离骚经序》云:“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10]梁萧统《文选序》云:“铭则序事清润。”[11]两例中,“序”即叙述、叙写之义。由此看“刘向所序”之“序”,也当如此理解。其次,紧接《新序》、《说苑》之后,《汉志》还著录:“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8]1727《太玄》和《法言》是扬雄编撰,这在长期以来是没有疑问的。既然如此,“刘向所序”的《新序》、《说苑》为何就不能属于刘向之作呢?第三,《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云:“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8]1958明确记载《新序》、《说苑》为刘向编撰。因此,《新序》、《说苑》并非“旧本有之”的前人成书,实为刘向之作。
较之《新序》、《说苑》,有更多学者倾向认为《列女传》是刘向所校而非编撰。这一看法所据为《七略别录》的一段佚文,云:
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3]48
这段文字最早见诸《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所引。因其谓《列女传》为刘向父子“所校”,故多有论者持该书“为当时所固有”[4]229的意见,认为刘向父子的工作主要是根据“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的意图进行了校订。
但此说亦不确。一则《汉志》著录《列女传》同《新序》、《说苑》一样,乃“刘向所序”。次则《汉书》卷三十六载,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8]1957可知《列女传》是刘向采择《诗》、《书》等经传典籍中列女故事,分类编撰而成。班固去向、歆时代未远,记载必有所据。因此,《列女传》一书可信为刘向之作。
在东汉人看来,《新序》、《说苑》和《列女传》确为刘向编撰。《汉书》的记载已自说明这一点。又,王充《论衡·超奇篇》云:“儒生……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12]这对司马迁、刘向颇有不以为然的意味,自非公允之论;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充指出两人均采用了相同的编撰方式,即“抽列古今,纪著行事”、“累积篇第”而成其书。采此编撰之法者,无非《史记》、《新序》、《说苑》、《列女传》等。这也就告诉我们,《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同《史记》一样,固然大量采录旧有史料,却并非“旧本有之”的前人成书。历代以来,谁也不否认《史记》是司马迁的发愤著述,那么,《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为何就不可属刘向之作呢?
《新序》、《说苑》和《列女传》所收有关故事也表明三书为刘向编撰。三书虽以收录先秦故事为主,但也有不少西汉当代故事。《新序·善谋》收录当代故事达十四则之多,记事最晚至汉武帝时期;其他篇章也有西汉人故事,如《节士》篇苏武故事;《杂事第四》“宋康王时有爵生鹯于城之陬”故事,时代虽为先秦,但“臣向愚以《鸿范传》推之,宋史之占非也”云云,则是刘向直接介入,发表议论。《说苑》的《君道》、《建本》、《贵德》、《复恩》、《正谏》、《善说》、《奉使》、《权谋》和《指武》诸篇,均收录西汉当代故事,记事最晚者至汉宣帝时,如《贵德》篇“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温舒上书”、《复恩》篇“邴吉有阴德于孝宣皇帝微时”、《权谋》篇“孝宣皇帝之时霍氏奢靡”等。《列女传》也收数则西汉人故事,如“陈寡孝妇”(《贞顺传》)、“京师节女”(《节义传》)、“齐太仓女”(《辩通传》)等,记事最晚者至汉文帝时。刘向生于昭帝末年,上距文帝、武帝时代不远,仕途始于宣帝时。而上述汉代故事如此接近刘向生活和领校皇家图书的时期,由此而言,《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也不可能创自前人之手而刘向仅为校订。
综上所论,《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乃刘向之作。三书均编撰于汉成帝时,缘起于刘向作为宗室老臣对朝政的关切和忧心。他目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故上三书“以戒天子”[8]1957。由于所处政治环境险恶,刘向不能恺切直言,只能运用讲述历史故事的形式讽谏成帝。其所借鉴的是先秦诸子常以寓言游说诸侯的方式,即通过讲述故事以说动人主。三书表现为短篇历史故事集的形式,类似《韩非子》内、外《储说》、《说林》等篇;至于《说苑》之名,显然脱胎于《说林》。但《韩非子》中故事的汇编没有明确的主题统领,故事的选择和收录尚缺乏系统性,与此不同,在《新序》、《说苑》和《列女传》中,刘向对故事精心归类,系以明确的主题统领,如“君道”、“臣术”、“建本”等,因而在编写体例方面,三书上承《韩非子》而有新的发展。
两汉是史传散文的辉煌时期。在《史记》、《汉书》等传记文学巨著的光辉之下,《新序》、《说苑》和《列女传》等短篇历史故事集相形见绌,自然难以引起研究者重视。而如果视其为“旧本有之”的刘向编校订正之作,它们的文学史定位则更为尴尬。①但是,从中国古代小说史的角度看,三书却自有重要价值,至少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三书是唐前规模最大的短篇历史故事集,开魏晋六朝志人小说的先河。三书纂辑先秦至西汉中期历史故事。故事多有同记一事而相互出入者,或与《左传》、《史记》等记载不合,因此历代招致不少非议。代表性的说法来自唐人刘知幾,指责三书“广陈虚事,多构伪辞”[13]。当然,也有持肯定意见的,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四云:“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亦不复计事实之舛误。”[14]两种意见虽相对立,立论角度却是相同的,均从史学角度出发。从文学角度看,无论“广陈虚事,多构伪辞”,还是“不复计事实之舛误”,都反映出小说文体虚构故事的特点,是三书跨入说部的明显特征。如当今论者指出的,刘向“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小说的创作手法,这使得其编撰过程成为一种文学再创作的过程,使得其文本显示出了鲜明的小说特征”。[15]《新序》、《说苑》和《列女传》收录记载人间言动的故事,在题材上开了魏晋六朝志人小说的先河。三书今存篇目900余则,系唐前规模最大的短篇历史故事集,在唐前小说研究中不应忽视。
其次,三书故事分类详尽具体,均以明确的主题统领,创立了唐前小说条别篇目、按主题分门别类编撰的体例和模式。三书编写体例上承《韩非子》而有变化和发展,将众多故事详尽分类,每类又以明确的主题统领。这创立了条别篇目、按照一定主题分类编撰故事的体例和模式,遂为先唐小说家所常用。如干宝《搜神记》,据《水经注》、《荆楚岁时记》、《法苑珠林》等书的引文,可知原书有《感应》、《神化》、《变化》、《妖怪》等篇,系根据各个主题分门别类编排志怪故事。再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每一门都是据该门主题系统记载名士言行,这一为后人所称道的“世说体”正是直接承自《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其他如志怪小说集荀氏《灵鬼志》,也是条别篇目、分类编排的。②
综上所述,《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自有其价值。也正因此,刘向为古代小说尤其是汉魏六朝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不应也不能忽略的小说家。
注释:
①郭预衡认为《新序》、《说苑》“都是辑录前代的传记,只是加以重新编排。其中虽有秦汉之文,但以先秦为多,可以说基本上是先秦传记等类作品的汇编。”置两书于先秦部分。见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聂石樵认为,《新序》、《说苑》和《列女传》“皆刘向类辑先秦至汉初之典籍及民间传说而成,……因为不是刘向所撰述,便不作具体阐释。”见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806页。
②如《水经注》卷二一《汝水》云:“王乔之为叶令也,……或云即古仙人王乔也,是以干氏书之于《神化》。”可知《搜神记》原有《神化》篇。《世说新语》刘注引荀氏《灵鬼志》,题作《灵鬼志·谣征篇》,说明原书依照主题分门别类编撰而成,惟其余篇题已不可详考。
[1]沈钦韩.汉书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8册[M].台北: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441.
[3]刘向,刘歆.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M].姚振宗辑录,邓骏捷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468.
[6]赵善诒.新序疏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7]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三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0-47.
[8]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9]许慎.说文解字[M].段玉裁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444.
[10]洪兴祖.楚辞补注[M].卞岐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2.
[11]萧统.文选[M].李善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2.
[12]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607—608.
[13]刘知幾.史通[M].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378.
[14]朱一新.无邪堂答问[M].吕鸿儒,张长法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161.
[15]周蔚.刘向小说的定位思考[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145-151.
Liu Xiang:the Writer of Xinxu,Shuoyuan and Biography of Women——the Value of Liu’s Three Boo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ovels
WANG Shou-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s,Shand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Jinan 250353,China)
Sinc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re has been an argument among many scholars that Liu Xiang was not the author of Xinxu,Shuoyuan and Biography of Women,but the editor,which is not correct.Studying the material recorded in the Xulu of Shuoyuan,Hanshu and Hanzhi,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three works were written by Liu Xiang.Material in Chaoqi of Lunheng and some stories in the three works also make it clear the author is Liu Xiang.Liu’s three works are the largest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efore the Tang Dynasty,and the beginning of fiction about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Wei,Jin and Six Dynasties and the first endeavor in editing and writing fiction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in Wei,Jin and Six Dynasties.Thus,Liu exert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novels in Han,Wei and Six Dynasties and deserves his position in Chinese classical novel history as a major writer of fiction.
Liu Xiang;Xinxu;Shuoyuan;Biography of Women
I207.419
A
1008-8318(2011)03-0012-03
2011-03-25
王守亮(1971-),男,山东昌乐人,副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