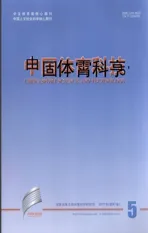论有音乐伴奏项目高水平运动员赛场的二次创作
2011-03-03樊莲香
樊莲香
赛前,无论编导和教练员投入多少精力编排成套作品,比赛一开始,成套作品的编排“档次”已成为不可控因素,赛场上可控因素主要表现在运动员完成成套作品阶段,即二次创作阶段。这个阶段将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结合在一起,最终体现了成套作品的编排“档次”并决定着“名次”。此阶段的成功与否,承载着成套作品参赛的全部意义。
1 运动员赛场的二次创作与艺术情感
运动员二次创作是指在赛场上运动员使用赛前创编的成套作品,并以创编的目的或主题为依据,明显地或刻意地赋予身体动作细腻的意蕴表现,在完成成套动作过程中展现出艺术情感的运动状态。
苏珊·朗格认为,在人身上,存在着极为广阔的情感(指广义的情感,亦即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领域[8]。有音乐伴奏下的成套作品中,运动员所表现出来的情感,隶属情感中的艺术情感。它是教练或编导在成套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作为艺术创作动力和表现对象的态度和体验。成套作品融入的形式和色彩、节奏和旋律、对比与和谐、运动员的身体动作设计和艺术表现是形成艺术感染力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为成套作品提供了可供观照的艺术情感。语言只能表达情感的概念,而情感的实际状况是具体的和丰富的、细腻的和复杂的[9]。凡是用语言难以呈现的情感活动的本质和结构都可以由艺术情感表现出来。若将情感呈现出来并激发人们的美感,也必须以情感的形式展示出来,并将情感转化为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体育赛场上的成套作品中的艺术情感同样如此传递。
运动员达成赛场上二次创作,首先要具有高水平的运动技术和竞技能力,拥有良好的本体感觉和内心的美感,特别是身体动作表达内心情感有了相当的基础,才能从动作的动力定型中,将成套作品的艺术情感细腻而深刻地表现出来。例如,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申雪/赵宏博双人滑(短节目)决赛的成套作品,选用皇后乐队的经典作品《渴望永生》(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为主题。申雪/赵宏博通过高超的动作技术,不但借用旋律和节奏表现了原音乐的艺术创作动力,也流露出他们俩人的内心期盼和忧怨,在画面的那一刻,我们所寻找的情感如此鲜明地被他们在运动状态中传递着、体现着,以至每个观者都被深深地吸引。他们不仅准确地把握了竞技难度、构成了一幅幅时空的画面,也让观者感受着人来自于自然,存在于自然,归属于自然,永生于自然的辨证法则。他们经典地表现出高水平运动员在赛场上的二次创作状态。这一状态呈现于他们的人生经历,专业训练历程和他们在训练赛场上,在生活中俩人的相濡以沫,这些因素都与他们赛场的二次创作状态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可以说,二次创作是竞技技术的真实与艺术情感完美融合的体现。

表1 影响运动员赛场二次创作主要因素的调查结果一览表(n=110)
2 影响运动员赛场二次创作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有音乐伴奏项目的国家队、省队教练员和运动员共110人进行调查,结果如表1所示。
结果显示,影响运动员赛场二次创作的主要因素可聚集为成套作品主题素材的选择、音乐选择、动作设计、空间的使用、运动员艺术表现力和文化素养等方面。这些因素属于赛前可控因素的创编阶段,如果运用的恰如其分,不但能够在赛前将失分降低到最少,更能够给赛场上的运动员二次创作预留艺术情感的发挥空间。
2.1 对抽象素材的理性提升与运动员赛场的二次创作
在成套作品创编时,教练或编导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将某种特殊的素材加以抽象地处理,使之以某种具体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动态中表现出主观经验、生命模式、情绪、情感、感知的复杂形式,还需理性地提升所选用的素材而不脱离具体的感性材料。
身体动作表现一般具有象征性,承载着社会方式在意识形态上的升华,构成现实世界的象征寓意,抽象素材的表达要使动作形象与主题内在意蕴相吻合,并引用身体表现形式去理性提升素材的深刻寓意,例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体操运动员程菲在自由体操成套作品中,使用了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名曲《黄河大合唱》中包括《东方红》的高潮部分,旋律雄浑壮阔、振奋人心,成套作品烘托出了浓烈的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氛围,尤其是开场时她选用“团身720°旋”强调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主题,最后一个出场的她不仅使在场观众为之群情激昂,更由此联想到北京奥运会确属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中国技巧队曾上演过《黄河》这一作品,通过一幅幅奔腾的黄河水流动的象征动作,在成套作品高潮时融入了运动员的“三连抛”动作,表现出“滴水汇成河,百川终归大海”的哲理性主题,让观众赞叹不已。编导们对抽象素材的把握与理性提升,把这个历史的形象素材创作成为实体并尽量简化,把情感转变成运动员的知觉感受,使人们的视觉、听觉和构造性想象在任何时候都能直接地把握它所渗透着的艺术情感,它之所以令人们难以忘怀,其一,是因为它的形式准确地表达了情感的本质;其二,是在创作上对抽象素材的理性提升;其三,是运动员在充满国家责任情感的提升中做到了赛场的二次创作。
萨尔瓦多·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永恒》,画中的时钟、蚂蚁、树枝、山水表现的是介乎于现实与臆想、具体与抽象之间的艺术境界。这个难以用语言来表现的素材,被西班牙花样游泳队在雅典奥运会上演绎,编导运用了抽象的方法从具体的油画中寻找到原画创作动力和被表现对象的态度体验,对运动员水中造型和队形的流动进行了具体形式的艺术点化,在成套作品中运动员运用身体动作构成的臆想却好似画中柔软的钟表挂在枝头,表现着时间在时空中的不可分割性、并不断地流动与流逝这一抽象主题[3]。这个创编过程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内在的抽象过程,即情感趋向与理智结合的过程,情感的感性因素与理性因素结合的过程。这种对抽象素材的理性提升,达到了创新创编的目的、形成了一种质的飞跃。苏珊·朗格认为:“每当情感由一种间接的表现方式传达出来的时候,就标志着艺术表现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8]。这种对抽象素材创编形式上的质的飞跃,结合西班牙花样游泳队运动员的二次创作,便成为体育赛场上成套作品创新创编的典范。
2.2 音乐与运动员赛场的二次创作
2.2.1 音乐有助于烘托动作节奏和艺术情感
赛场上,音乐的作用不是情感的刺激,而是情感的表现。在成套作品中音乐首先为运动员身体动作的表现服务;其次是渲染出成套主题所观照情感氛围;第三是满足视者欣赏多元化的需求。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音乐在竞技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也不能高估。音乐旋律使竞技动作更清晰,运动节奏在音乐节奏的烘托下更鲜明,它们之间不仅有动作节奏与音乐旋律内在效应的需要,完整的成套动作在完整的音乐助推下,能抒发艺术情感、更能增强艺术场景的表现。
2.2.2 音乐的特点决定动作编排的结构和特色
在艺术体操国际评分规则中规定:音乐伴奏的特点决定着动作编排的结构和特点;在健美操的国际评分规则中也同样规定:动作节奏与结构方式上的统一效应,表现在健美操动作的全套布局之中;花样游泳在音乐的选择,在内容的选择和顺序方面有严格的限制,必须体现自选音乐的特点,思想和编排方面的构思;在体育舞蹈项目中强调两个运动员的每一舞步的时间,正好与音乐合拍的“时值”和基本节奏是裁判打分的首要因素;花样滑冰项目在整套内容编排与音乐的和谐一致性方面,提出要充分表达音乐的风格和特点。
音乐对于运动员赛场的二次创作来说,只有感知音乐所蕴含的艺术情感,运动员才能将音乐所表达的主题融合于动作旋律和节奏之中,使“动”与“曲”合一,进而使身体动作焕发出新的活力和意义,如1994年体操运动员莫慧兰的自由体操“打字机”,音乐幽默诙谐,使用了打字机快速打字而敲击出来的声音点、其中不乏换行时候发出的“警告”铃声,以及打字者手动换行发出的“嘎嘎”声。场上莫慧兰灵动而富有动感节奏的形象化表现,高难度动作和着不断变化的音色和音效,淋漓尽致地描绘了繁忙而紧张的办公场面;又如程菲的自由操“黄河大合唱”中的连接动作多处加入了京剧锣鼓,在一个侧搬腿动作时通过绷脚、振臂、昂首挺胸这种典型的京剧造型来契合音乐内涵。可以说,音乐与成套作品编排结构的划分、难度串设计、高难度动作的转换、造型与构图等环节方面,首先要与音乐的情感相吻合,其次音乐的节奏、和声的性质、音量的强弱、乐器的色调需与主旋律协调统一。值得注意的是,音乐的情感不是主观随意附加上去的,而是已蕴含在旋律的本体之中。运动员可以通过自身的情感体验而对其有所感悟,甚至可以从自身情感材料中进行“移植”与“借用”,但借用过来的情感已是一种形式化了的情感,尽管还有某种“距离”,但高水平运动员也会用高超的动作技巧,灵敏的动作将其弥补,焕发出新的综合性的意蕴,要做到这点,运动员的艺术素养是前提。
2.2.3 音乐情感激发身体动作的艺术表达
在艺术体操国际评分规则中指出:成套动作必须强调音乐和动作之间的协调,在任何情况下,音乐必须与动作保持一致性,而不是几个无关联的音乐片断的组合,这一条文对音乐所要表达的统一主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健美操规则要求运动员在比赛中运用自身的音乐素养及身体动作表达音乐的意境;最具主题要求的花样游泳项目,则规定动作的连贯性以及动作要表达出音乐所表现的心境变化,必须通过动作技术与音乐配合,表现出运动员良好的艺术表现和抒发情感的动作能力等,条文中还提出花样旅游运动员还要具备音乐艺术鉴赏表达能力的基本功,包括对音乐节奏感、音乐内涵的理解能力;体育舞蹈明确地要求舞者在舞蹈中表现出对音乐的理解与情感表现;花样滑冰则严格要求运动员通过音乐的节奏感和对音乐段落的理解利用整个身体去提高音乐的艺术表达。
由此我们感知,无论成套形式怎样体现,其实质是在音乐的烘托下反映着一定的情感表达,成套作品必须具有的主题的渲染和动作的艺术表现。情感不仅仅是艺术创作的强大推动力,也是艺术的表现内容,只有使动作充满情感,才能完美表现动作内涵。英国国际舞蹈教师协会考官王子文先生曾谈到“当你要达到舞蹈最高境界,必须音乐与舞蹈结合一体,用感情去欣赏音乐产生不同的表情韵味,将音乐扩散到你身体周边,你已到达舞蹈最高峰”[1]。2.3 动作设计与运动员赛场的二次创作
2.3.1 动作设计要符合国际评分规则的发展趋势
顾拜旦认为:“如果现代奥运会要产生微妙期望的影响,它必须显示出美,唤起人们的尊严之心。体育应视为创造美的过程,展示美的机会[2]”。审视难美项群的发展方向及2009—2010年奥运周期评分规则的修改指向,各项目除了强调技术动作的完成和难度高标准外,更强调了对成套的稳定完成所显示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原国际女子体操技术委员会主席艾伦·伯格认为,“美比难度重要”。在本周期中,女子自由体操的发展方向便是朝着“高难度”、“高质量”、“多变化”、“重优美”的方向发展;技巧评分规则中的艺术性评分条文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不曾出现,到了2001—2004年奥运周期,国际技巧评分规则对于“艺术性”则从4个方面的30多个具体的条款进行表述。继而在2009—2010年这一奥运周期中,评分规则明确定位艺术性分值为5分[7],十分突出的创举是艺术性单独评分,在评定的力度以及评分因素的细化方面都是空前的。艺术体操项目从2009—2010年奥运周期开始,将身体动作难度列为D1难度、其从上周期的18个难度减至8~12个(最多不超过12个),增设了器械技术为D2难度,艺术分值也从1.5分到10分的特大幅度提高,并首次提出体现舞蹈编排的主题思想[音乐伴奏,艺术想象和表现力(舞蹈)],可以说,这为成套作品中的身体表现及艺术性创编带来了更大的突破。
难美项群诸项增加艺术美的内涵,并没有简单降低诸项目对身体动作难度的要求,反而使体育竞技的内涵得到升华,也给身体动作的文化与审美体现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在人们对身体的观赏欲望得到大面积实现的同时,也给人类文化带来了由身体动作多样性的表达,同时也为极限化的身体提供了艺术表达和文化展示的机会。这种表达和展示既满足了观众对运动员身体动作的观赏,同时又在对“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认同中,进一步促进了身体的文化印记[4]。
2.3.2 动作设计要符合运动员的本体感觉
本体感觉是人的大脑对整个躯体运动情况的认知与把握,包括着动觉和静觉(平衡觉)。对运动员来说,本体感觉一方面,体现在动作技术的完成,比如,艺术体操中难度动作的完成、花样游泳和花样滑冰的托举等;另一方面,体现于身体动作表现与音乐的协调配合;第三,是运动员对成套主题的理解与认知。可以说,赛场上运动员是在本体感觉的自导、调节和制约下,通过动作技术和技巧来表达艺术情感,在表达情感这个过程中,运动员美的感觉、艺术想象的产生与释放的基础,来自于运动员的动觉和静觉的自动化呈现,这也是运动员能否被激发出赛场的二次创作的核心动因。
国家队及大多数省队教练员认为,尽管训练施加的手段一致,每个运动员的本体感觉却不尽相同,呈现出来的动作风格、艺术情感迥然不同。对高水平运动员来说,从动作技术的条件反射到动力定型这个本体感觉训练阶段容易实现,但在动作的动力定型后将情感意蕴转化为身体动作表现,这个训练阶段就较为困难,达到赛场的二次创作则更难。当运动员动作技术达到了自动化阶段时,教练员便将更多的精力花在了艺术表现力、艺术想象和个人风格塑造上,如果运动员艺术底蕴不足,常常是收效甚微,这也是被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运动员难度动作往往领先,但艺术分值偏低的主要原因”。教练员们认为从小或从训练动作伊始就应同步注重身体动作美感和艺术情感的培养,坚持多年才能达到艺术情感表现的境界,一旦有了这样的功力,再追求动作的细腻和美感,运动员赛场的二次创作就有了相应的基础。
2.3.3 动作设计要有运动员的参与
成套动作设计不单是教练员或编导的事情,更应该有运动员的融入,这样在赛场上运动员才能细致地表现对象、被表现的对象才能更加生动与饱满。艺术体操的集体项目中的协作配合的设计,健美操、技巧、花游游泳的托举动作通常是教练员和运动员共同设计的结果,在教练员的引导下需要运动员无数次的体验与协调配合、才能印证动作设计在时间、空间以及抛接时机的环节上是否恰到好处,也就是说,只有在运动员的参与下动作设计才能不断地被完善。
运动员的二次创作是在教练员或编导者与运动员的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中实现的。要达成赛场上运动员二次创作能力的提高,达到身体动作准确表现成套设计的目的,就必须期唤起教练员及运动员对艺术素养和文化素养的重视,夯实身体动作艺术表现的美感功力。明确的目标,坚定的信心和不惧任何困难的勇气,是运动员提升运动竞技实力,实现赛场上二次创作的可靠保证。
2.4 动作构图与运动员赛场的二次创作
动作构图是指运动员在比赛场上,边做成套动作,边移动所构成的图案(队形)[6]。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有音乐伴奏下的集体项目,其观赏价值确实高于个人项目,这是因为集体项目的构图可形成错综复杂的线为复线;个人项目(艺术体操、健美操、花样滑冰)的构图是单线。构图的单线与复线、分散与密集、平衡与对称,是构成所有构图(队形)的基本状态。这些形式的转变可以递增出动与静、正与反、明与暗、增与减的对比画面,使成套构图呈现出多样化,流动快的效果,更重要的是,集体项目由于是多人合作表现,就为运动员进行二次创作提供了更大的时空条件,为充分的想象提供了可能展现的机会,也成为运动员在赛场上二次创作状态中艺术情感表现的重要视觉语汇。
就构图与情绪而言,构图在移动的过程中,采用不同的运动路线,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向和身体动作表现,就会形成不同的动态“延伸”。运动的“速度”,体现着动作频率的快慢与人的情绪和氛围的关系;身体动作的“反应”,体现着人的不同情绪及其倾向性的对应关系;可以说,运动员的二次创作过程中对构图与情绪这一细节的呈现,与运动员能否将主题表现出来密不可分。克莱夫·贝尔认为:“线条、色彩以某种特殊方式组成某种形式或形式间的关系,它能激起我们的审美感情”[5]。在北京奥运会上著名的乌克兰艺术体操运动员安娜·比索诺娃圈操的构图与其形式之美令人过目不忘。她着白衣手持白色圈入场、从开始的沉睡造型过渡到地面“视线外”半弧形滚圈接圈,接着一臂支撑旋转成圆形、另一肘关节做圈绕环,映射着白天鹅此时的幽怨和孤美;高抛圈后接着踹燕立踵从圈中通过、高潮迭起时抱腿旋转、连续反跨跳抛圈以及在阿拉贝斯转体中突然结束的造型动作,表现着天鹅高贵与挣扎。编导选择了高与低、正与反、明与暗、增与减的对比画面,根据不同种类的难度动作对应着对角线、大弧线、折线等线形变化作为衬托主题的基础,加上运动员完美的二次创作,经典地演绎了濒临死亡的天鹅所拥有的哀怨和渴望这一主题表现。
3 达成运动员赛场二次创作的关键阶段
在赛场上,成套作品最终是要通过运动员将创作意图展现出来。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我们均可认为,在世界大赛上,成功就既是标新立异、推进项目发展;失败便是一切努力付之东流。所谓吸取得失经验教训之说,绝对是自我宽慰之词。因为在竞技体育的赛场上,不可重复是其鲜明的特点,对于自己同一大赛的再亮相,就更不能有重复了。实现运动员的二次创作,是一个相当艰苦的消化及情感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划分是建立在教练员或编导者已确认了成套动作设计、成套主题中艺术情感的基础上的。
3.1 运动员接受动作设计,复制成套的动作设计
这一阶段主要是运动员要首先接受教练员的动作设计,熟悉和理解伴奏音乐的节奏、旋律与身体动作表现的关系,复制成套动作设计。
在实践中,教练员或编导需先把成套主题确定下来,如果在这一阶段,小有修改完全允许,但必须避免因运动员完成难度动作信心不足时的推倒重来;当教练员或编导者对成套动作设计经运动员初步体验并认为设计合理后,就要以不厌其烦地要求运动员重复练习;在逐步提高中达到动作技术的自动化阶段,在完成成套动作设计的复制后,分成段落地加入相应的音乐伴奏进行练习,同样,此时只强调合拍,达到形式的统一,逐步推进成套与音乐的配合,为运动员初步的二次创作做好准备。
3.2 演绎成套动作,阐述主题思想
当运动员实现了成套动作自动化表现,并与伴奏音乐达到契合的状态时,阐述成套动作主题思想就成为运动员完美表现成套动作的重点,教练员应结合成套动作的阶段进行主题思想体系的切割,把要表现的情感要求融入到每一动作之中,鼓励运动员把自己的体动与心动和情动有机结合起来,从内到外形成统一体,形成属于自己意识表达,当运动员在教练员的引导与指导下,基本达到了动作设计与音乐旋律的吻合时,成套动作主题思想即在身体动作不失误的状态下就实现了完整的表达。
3.3 完美表现成套动作,展示主题心声
运动员二次创作的真正意义,不是简单的复制成套设计,而是运动员对成套作品有自身艺术情感的表达。竞技中的身体动作有一个基本规律是熟能生巧,而所谓巧,是指对基本身体动作达到熟练状态时,表现者就会有所悟,而悟的结果是使动作在表现中又有了许多微妙的变化,这个变化并不是来自师承,而是个人体会、理解后的派生,此时表现在动作形式上仍是原设计动作,却并存着创新发展的可能与潜力。达到了这一阶段,教练员要向运动员提出更高的要求,激励运动员在音乐旋律的烘托下,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入主题表达之中。运动员有了这样的心理投射与转化便容易达到真正的二次创作状态。这种状态是运动员以肢体语言表达为主、辅以表情语言诉说;以器乐语言观照情感为主,辅以造型队形移动,逐渐超越自身一般样式的束缚,过渡到作品主题与内心艺术情感的表达层面上。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任何运动员都能做到赛场上的二次创作,这种感受与运动员的本体感觉、情趣性格、经历经验、文化素养、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有着密切的相关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成功的运动员演绎成套作品,对伴奏音乐中主题的情感理解程度也许只能达到80%~90%,能100%表现的伴奏音乐的主题程度几乎是没有的。这源于不同人的内心情感所表现出的形态是不确定的,是个变量,但原音乐创作动力中的情感表现性的形式本身却接近一个横量。我们认为,有音乐伴奏项目毕竟是主旨“难和美”的较量,加之对情感内容评判很难做到严格意义上的同步,回到竞技体育中依据各项目规则进行主观评判时,只要做到动作技术完美完成,难度动作种类齐全,运动员可以用身体动作将艺术情感细腻而深刻地表现出来,尽管不是天衣无缝,其实就是完美地表现了成套作品的主题,就接近了100%,同理,运动员就已实现了体育赛场上的二次创作。
[1]陈丹,任家良.对我国体育舞蹈选手表现力培养的探讨[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6,14(4):49.
[2]顾拜旦.奥林匹克与文学艺术[M].北京:奥林匹克出版社, 1993.
[3]樊莲香.难美项群中身体动作表现研究[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0.
[4]樊莲香.难美项群中身体动作的文化体现[J].体育学刊,2011, 18(4):49-53.
[5]克莱夫·贝尔.艺术[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5:4.
[6]江口隆哉.舞蹈创作法[M].金秋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
[7]梁海琼,史波萍,林群勋.从规则中艺术分的变化态势思考中国技巧运动的发展[J].体育科学研究,2003,7(3):73.
[8]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08-109.
[9]杨琪.艺术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