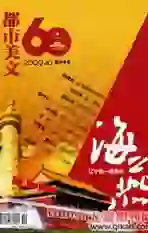广昌莲
2009-10-24任林举
任林举 一九六二年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作家》《长城》《青年文学》《诗刊》《星星》《文艺报》《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表诗歌、散文、文学评论近百万字,曾在《春风文艺》《新文化报》《城市晚报》等四家杂志、报纸上开设专栏,在鲁迅文学院第五期高级评论家班进修。获全国电力系统优秀著作奖、吉林文学奖、吉林省精品图书奖等。著有散文集《轻云起处》《说服命运》,长篇散文《玉米大地》。散文《岳桦》入选二〇〇九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阅读理解题。
在我的感觉里,莲是一种圣洁的花,它应该生在水里或天上,而不能生在田里或泥土里。
很久以前,我就在书本里看到过,有人说它,“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后来,又在阿弥陀佛经里看到,佛说它“微妙香洁”……种种佐证都已经明了莲的神异与不同凡响。就这样,不由得我在很少有蓮的北方,对莲,常常怀有倾慕与向往。
第一次到广昌去拍莲,差不多被那里铺天盖地的莲花惊呆了。只瞧那么一眼,收入视野里的莲花,就抵得上半生全部所见,岂止一个奢侈所能形容,简直就是奢靡。
一个搞摄影的人,总是要赶在太阳升起前到达某一个地方,这有一点像一种神秘的约会,有一点像某种仪式。如果想知道昨夜的黑暗里到底埋藏着什么,那么在光明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确定一个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否则,我们很有可能错过那个答案。往往,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许给我们的那个新娘已经上轿,她的脸是美丽还是丑陋,正被厚厚的盖头遮于暗处,我们要和阳光合作,一同用手指挑开那层蒙昧。对于一些心里常常怀有某种美好期待的人来说,这永远都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初,我才无怨无悔地爱上摄影这一行。
那一天,就是在太阳升起之前,我们抵达了预定的拍摄现场。当如水的光线一层层洗去附着在万事万物之上的夜色时,我们看到了一幅硕大无朋的照片正在大地上显影。
这就是广昌的莲了,举目遥望,我无从判断她们的队列从哪里起始,又到哪里终止。她们的声势浩大、她们的艳丽妖娆、她们的姿态纷呈,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自己的污浊、单薄与窘迫。作为一个来自于不同生存空间的异类,我找不到与莲并立、厮守的理由。面对这样的生命、这样的阵容,我久久地不敢抬起头来,不敢与那些怒放的花直直地对视。
我只能让眼睛躲到照相机的镜头后面,借着可虚可实的镜头来掩藏自己的羞怯。这羞怯,来自于我的生命深处,来自于我穷乡僻壤的童年。从很久以前直到今日,只要那些美好或美妙的事物映入我的眼帘,我都不由自主地想转身逃开。我从来也做不到无所顾及,勇敢地张开双臂去拥抱那些我认为圣洁的事物。这样的自警或自虐,并不是因为我害怕与那些美好事物将合未合之际,会把自己的卑污映衬得更加卑污,而是怕因为自己的卑污亵渎了那份圣洁。这世间美好的东西太稀缺了,不是我没有勇气,而是我总不能忍心,让一己快慰与满足无由地摧毁她们或改变了她们的性质。
隐于暗处的那只手,只是为我开启了发现美的窗口,却没有给我插上抵达美的翅膀。从遥远的少年时代开始,我就为那些美好的事物饱受磨难,所以我忧伤。当我面对眼前这些绚丽的莲花,当我躲在镜头后面的时候,我知道我贪婪的目光就再不能伤及她们了。于是我尽情地操作,把她们的脸放大、缩小,拉至眼前或推向遥远,定格或虚化,我一朵一朵地对她们进行着无言的叩问。我看到了,她们对着夏日的早晨,对着阳光,也对着我款款地微笑,而我却一点都搞不懂她们微笑的含义。
不知道那微笑里所蕴藏的是眷顾、是宽容,还是嘲讽。当我在相机显示屏上重放那些我以为千姿百态的莲花照片时,我看到的却差不多是同一张照片,因为每一朵莲花都似曾相识,每一张照片都大同小异。原来我以为我曾经看见,我以为曾经发现,而实际上我什么也没有抓住。在我的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荷田,却不再有莲,我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以怎样的方式一次次从我的镜头下逃走的。
最初的惊喜,在我的眼里已经渐渐消失,她们那千篇一律的面容与微笑已经让我分不出这一朵与那一朵到底有什么不同。如今,她们已经平凡而普遍得如同站在操场上翘首等待号令的中学生,或假日站台上找不到方向挤成一团的民工。一样的装束,一样的神情,一样的目光,如同一层坚硬的外壳,让我们无法进入她们的情感、个性、心灵和生命,无法了解她们的忧戚、快乐、梦想与身世。
当我看到那些面目模糊、衣着简陋的莲农随意地穿梭于那些花朵与子实之间,并信手捋下成熟的莲蓬或折断碍事的莲花时,我的心不由得一紧,虽有不甘,但却在心里狠狠地轻贱起她们。尽管,广昌的莲种本是从高远的太空而来,但面对她们没有个性没有选择的容颜和笑脸,我还是把她们等同于那些没日没夜守候在田里,只有面容而没有身份的农妇了。
或许,广昌的莲并不是为了开花,不是为了美丽而生,而是为了繁殖,为了结籽,为了让更多的莲蓬出生,为了经济而生。
然而,就在我路过一处遍撒浮萍的水塘时,一朵娇艳的红莲从浮萍的缝隙里映现出来,宛如夜色里的一个闪电,刹那间照亮我的心智。我的心,忽如明镜,透过那零星的浮萍和宁静而氤氲的水光,我看到了她五百年前的颜容与风姿,我看到了她五百年后从现实的某一个窗口向我透露的深长的意味,我也看到了她在岁月之河上荡开一圈圈涟漪的足迹。它不仅仅是一朵莲花在水中的倒影,而是我再度与莲花重逢的另一个空间另一个维度。
当我怀着虔敬的心情拍下这个影像的时候,我确认,那一刻我已经捕捉到了世间最美丽的精灵,触碰到了一种事物美丽的核心。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超越现实的视角,我拍下的莲花从此就不再雷同,有时就是拍同一株或同一束,所结出的影像仿佛也神情各异,姿态纷呈。
佛经里说,佛无定相却有万千法相。这时,我才有一点明白,那些站在荷田里的莲,定不是天生俗物,更不会是某种刻意的隐身。那个本真的莲,它从来就站在那里,只是我们不能够发现,只是我们从来没有从世俗的、现实的视角之外去参悟她们,所以才看不到她们真正的生命。而只有通过水,这与天同一形态、同一颜色的介质,我们才有可能走进莲的秘密、莲的真意。
《佛陀本生传》记,释迦佛生于二千多年前印度北边,出生时向十方各行七步,步步生莲花。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在广昌这片幸运的土地上遍布着佛访寒问苦的足迹,每一朵莲花,不啻一个深深的祝福。是所谓佛无定形,佛无定相,佛无定法。
在一处莲田的池埂上,我与一个朴实的莲农“狭路相逢”,就在错身的那一瞬,我问他,为什么莲心是苦的,他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说,那是因为它成熟了,嫩的时候莲心也是甜的。于是,他给了我一只嫩莲蓬。我细细咀嚼着那脆而甜的莲籽,和被一层甜甜的汁液包裹着的莲心,却感觉有一丝难以觉察的淡苦,如一抹心思,悠然飘过心头,那是莲与生俱来的秉赋。
后来,我查了很多关于莲的资料,才知道广昌的莲,不是产藕的藕莲,也不是专为观赏的花莲,而是专门产籽的籽莲。于是也知道了广昌县年种植太空莲十三万亩,年总产一千万公斤,产值达四亿多元的数据,意味着什么。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会养活多少人,让多少人过上好日子啊,广昌的莲让我们知道什么叫普渡众生。
广昌莲的莲,确实不单单是为了美丽,不单单是为了开花而生,而且还为了结出更多的莲蓬,拯救一方民众而生。
关于广昌莲,我下了一个让我自己满意的结论,但同样也是一个令很多人怀疑的结论。我知道,真正的美,往往是不承担什么重量的,承担了就会在某些领域或角度上存在着被摧毁或破碎的危险。就像我们自己的母亲,在我们的眼里总是那么无懈可击地美丽,哪怕她韵华已逝,哪怕她老态龙钟,但在那些不相干人的眼里她肯定会被以另外的尺度、另外的态度严厉地考量,在那些人眼里,她定然不再美丽。
庆幸的是,在我离开广昌时,一个意外的情景将我从一个尴尬的言说境界中解救出来。
在我们多次路过,却从没有留意过的荷田,我看见了一朵独立的莲花,那是我没到广昌就希望能够看到,但却一直没有出现的莲花。那是一朵开放得近于完美的白色莲花,硕大而又纯洁。就在那片无花也无蓬的莲池边缘,那朵莲悠然地显现出来,像昏暗的睡眠里突然降临的梦境一样,突兀而又新奇。一片芬芳的冰,从我的车窗边掠过,清晰复朦胧,随着车轮的远去,渐渐化开,如若浓若淡的情谊,如若远若近的召唤,如若隐若现的微笑……
广昌的七月,因此而香郁无边。
责任编辑︱孙俊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