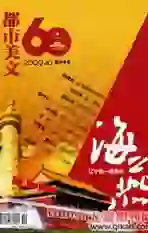1950年代的乡间生活
2009-10-24席星荃
席星荃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襄樊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学高级教师。迄今已在《光明日报》《散文》《长江文艺》《都市美文》等报刊及香港《大公报》发表散文两百余篇。在《写作》《名作欣赏》《语言教学与研究》《青年文学》等报刊发表教育、文学、写作学论文三十余篇。著有散文集《沧桑风景》《记忆与游走》等。曾获首届《长江文艺》散文随笔奖、第二届老舍散文奖优秀奖、第二届和第三届湖北文学奖提名奖等多种奖项。
代销店
代销店,大家都觉得这叫法有点正规了,就只叫商店,简简单单的,顺口。商店是借用一户人家的房屋,这户人家只有一个孤独的老人,就腾出两间房做代销店。也是草房,土墙,门前是土场,土场前是半荒的菜园子,长着些杂树,春上桃花开,夏天知了叫。草房右边是大路,也是土的,下雨天泥泞不堪,爬着蚯蚓。那大路是村子通往外界,主要是通往小乡政府所在地和本地小街大埠街的通道——原来是另有上街路的,是条弯弯拐拐的田间小路,在村西;现在这条路横贯三个自然村,是土改以后,又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农民们要开会,出工,集体活动多了,自然而然形成的。但也仍然在田间小路上拐来拐去。只是走的人多了,似乎就成了热闹的大路,其实也只是心理上的感觉。
商店离村初小有一点距离,双庙畈村是大队的中心村,在槐树畈北一里,坐北朝南,中间是一条大沟,终年流水。沟南沟北的人家之间很空旷,种些庄稼,也有隙地荒场和老坟包。商店在沟北的路边,小学在沟南的路边,只开到四年级,五年级便要到六里外去就读了。初小的学生们常常到商店去,买铅笔、毛笔、橡皮、黑墨块儿、算术本、语文本、大字本和小字本、蜡笔……但大多数时候什么也不买,单为的去看一看,闻闻那屋里特殊的气味。商店虽小,也算是一个经济中心吧。
两间草房,外间居中砌了一道长土台子,里面靠墙是极简陋的货架,摆放些最常用的日用货品:缝衣针、大底针、绣花针,顶针儿,以及各色丝线。丝线一缕一缕的卷成麻花状,拦腰拿纸扎了;妇女们仔细地挑,挑好了,付两分钱三分钱买一缕拿走。还卖火纸,这是为那些使用火镰的人家和吸旱烟的老汉们准备的。使用火镰的人家都备有火石,拿火镰斜着擦打火石,就冒出火星;火纸早就叠好,烧出了黑灰头,成了纸媒,紧贴了火石;火星迸溅,总有一两星落在纸媒上,那灰头点着了,变红,渐渐扩大,撮了嘴轻轻一吹,噗!升起了柔软的火苗。乡下人生火做饭,老汉们点烟袋,都使用火镰。这是悠久的传统了。所以,商店的柜台内堆放着一捆一捆的火纸。
还有煤油,装在一个洋铁方桶里,桶沿挂着两三个长柄的油吊子,有半斤的,有二两的,最小的一两。根据购买者的需求使用不同的吊子,有时候要交替使用几个吊子才能凑够一个顾客的数量。煤油气味不浓烈,但特别,很鲜明地刺激着鼻子,充满在草顶和土壁之内。煤油总是被人叫着洋油,的确,那只油桶上面就轧着两个浮出的字:“美孚”。想来这只桶是旧社会某个商号遗留的旧物吧。
称盐打油是人们的基本消费。那时多数人家点煤油灯。煤油灯是自家制作的,找一个墨水瓶,口上放一个剪成圆形的薄铁片,卷一根细铁皮管,正中插入,穿了棉线捻子当灯芯,一个简易煤油灯便成了。生产队有马灯,那是夜晚打场,或者风雨之夜抢场用的,私人绝不用那东西。小学的教师则用罩子灯,罩子灯全身是淡绿的玻璃体,圆脚,细腰,饱满的腹,洋铁灯头制作精细,有灯芯管、灯舌,旁边伸出个旋扭可以调节灯芯,四片花萼似的铁片卡着玻璃罩子。罩子灯特别明亮,它的光芒洁白素净,不生一丝黑烟,让人的心分外宁静。但也叫人联想到细腰的古代美人,遭了冷落,总是带几分寞落的忧伤。有许多人家仍然点原始的灯盏。灯盏是铁制的,圆形,不起沿,像短把的小圆勺,放了棉油或香油,油里放一根棉捻子,灯火很小,“一灯如豆”是忠实的比喻。
此外,最惹年轻人喜欢的是手电筒。电灯人们只在城里见过,电话只听说乡政府里有一部,手摇式。村北的田野里站着一排电线杆——高高的杉木杆子,下半截上了黑漆,上头装了瓷葫芦,手牵手地扯着两根电线,有风无风都呜呜地响。人们想像打电话的人的声音,顺着那细细的电线传过来传过去的情景。这些都与乡下人无关,乡下人跟电的接触就是手电筒。无月的夜晚,深黑的乡村如墨汁一样,远远的,一道耀眼的光芒划破夜空,如利剑,直直的,在夜空中晃闪,渐渐消失于看不见的高处。这便是快乐所在,乡村的年轻人,孩子,和一些爱新奇的中年男人或女人,都把夜晚揿亮手电在黑暗里乱晃当成无上的快乐。那时候,小小的草房商店里,手电和电池总是人们最热衷的话题和最心爱的商品。
孩子们,小小的初小学生,最爱的要数“十二色”了,十二色是我们形象的说法,就是蜡笔。因为那小小的火柴盒一样的盒子里装着十二种颜色的蜡笔。这种东西又硬又光滑,完全保有了蜡这种物质的特性,用它在粗糙的黄土纸上画画,因为不能主动调色,实际上只能选配颜色,就显得简洁,幼稚,拙朴而且原始。但买一盒蜡笔也不容易,两三角钱在那时乡下人手里并不是随便拿得出来的。有段时间我痴迷蜡笔画,最喜欢画马,而女孩子们则多喜欢画花朵,还有些男孩子喜欢画狗、猫和大刀、手枪之类,五花八门。课余画蜡笔画是一大娱乐。
但我始终对蜡笔有一点遗憾,或者也可以说是不满:它着色很淡,且不均匀,又呆板僵滞,不能表达出我心中想象出来的效果,所以,稍稍长大一些之后,就渐渐失去了对它的兴趣。不过,那时候孩子们又有了新的喜爱了,这是后话。
商店的柜台上放着两三个玻璃瓶,盖子顶端带一个圆球,像一顶透明的瓜皮帽。这是专门装糖果的。糖果分两种,水果糖和打食糖。打食糖呈宝塔形,上尘下圆,有淡淡的红绿相间的螺纹,微有药味,却以甜为主。乡下的孩子们饮食不注意卫生,肚里寄生虫多,哪个孩子黄瘦了,知道有了虫,最简便最便宜的法子就是到商店买几粒打食糖给他吃,过一夜,就会屙出许多的蛔虫。打食糖我是吃过多次的,也屙出过不止一回的蛔虫。水果糖一分钱一个,可是乡下孩子很少有吃到的机会。一块糖,常常是你吮几口,吐出来给我,我吮几口,再吐出来给你,在两个孩子的口里进进出出许多回。糖太好吃了,对我是极大的诱惑,那时候我暗下决心:等将来长大有钱了,一定买很多很多的水果糖,坐下来吃个够。可是真到长大了,却失去了吃水果糖的兴趣。
商店就这样跟孩子们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然而,还有更有趣的联系呢。
商店除了卖日用杂货还兼收购。不仅收购废品,还兼收土特产和药材。无论男女老幼都有可以拿到商店交换的东西:破布乱麻、锈铁丝、烂镰刀头,女人的头发,鸡内金(鸡的胃囊),黄鼠狼的皮,知了的壳。而最为孩子们喜欢的捉了土元和全虫到商店交换心爱之物。全虫是商店老罗的叫法,其实就是蝎子,而土元我们村里人叫团鱼。团鱼藏身旧墙根房旮旯,扒开陈土浮灰,腐朽气息正熏着人的鼻子,忽然见一个乌黑的硬币大小的虫子急急地爬走,這就是团鱼了。团鱼形扁而圆,正像一只微缩的鳖,外壳软软的,数不清的细足从壳沿下伸展出来。见的团鱼,赶紧捉了放进小瓶里,捉够四两半斤就到商店去。老罗瞅一瞅,个儿大的一个一分,小个儿两个一分。然后倒进专门装团鱼的篓子里,那篓子里已经有半篓子黑鸦鸦乌黢黢乱爬乱动的团鱼了。捉蝎子则必须到晚上,蝎子白天不出洞,晚上出来,翘着尾巴,张着两只大钳,静静地爬在墙面上等候食物,人们就揿亮手电,在老墙上下照来照去,发现了,拿夹子轻轻夹住,放入小瓶。蝎子比团鱼贵多了,一只大蝎可以卖五分钱,农家贫穷,捉住一只大蝎便会听到一声欢叫,有不少人就靠捉团鱼逮蝎子换个油盐钱。孩子们靠这来换本子纸笔,顺便也换几块水果糖和十二色,算是格外的奢侈和快乐。捉团鱼逮蝎子是乡村夏夜的一景,到了秋冬,虫豸入洞,人们就开始捉黄鼠狼了。
捉黄鼠狼一般用关子。关子是长约三尺的四方木筒,一头开着,一头封死,中间设了机关,机关后拴一只老鼠。黄鼠狼钻进来捉老鼠,踩了机关,咚,进口落下一块砖,关死了;老鼠隔着一层铁丝栅栏,见了黄鼠狼吓得吱吱直叫;殊不知其时的黄鼠狼已知大难临头,在关子里拼命地转圈子了。一只上好的黄鼠狼皮可以卖到三五块钱,那可是一笔大数目了。黄鼠狼的皮只有冬天才细密柔软,光泽闪闪;其它季节,黄鼠狼换了毛,商店就不收购了。
商店先后有过两个店员,先是老罗,后是老杜,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旧社会他们都是镇上的小商小贩,后来改造工商业,成立了供销联社,在乡下各村设了小商店,他们就被派到乡下来经营小商店。不知是自负盈亏,还是公家发工资。他们都一副沉默寡言的表情,跟村里人很少打交道,不知有没有家人,反正在乡下小店独自个生活,自己生火做饭,孤零零的。他们隔几天就到六七里外的大埠街进一回货,挑两只细竹篾箩筐,在乡下小路上慢慢地走。不进货的时候就守在草房小店里。老罗矮矮的个子,一双大眼睛像金鱼,除了沉默寡言,仿佛满怀心事。后来换了老杜,说一口外乡活,在这偏僻的乡村显得格外新鲜,仿佛代表着外部世界的文明。但他沉默时候多,开口时候少,惜话如金,仿佛不愿轻易展露自己的文明给乡下人。后来我想,老杜有自己的身世际遇,有自己闯荡世界的见识,却不一定有多少“文明”;或者,他也不是看不起乡下人,他只是有自己的苦衷和忧伤(这当然跟他的历史和现状有关),难以对陌生而朴实的乡下人诉说罢了。除了沉默少语,老杜多了些怪异,最使人惊奇的是吃炒蝎子。他选出最大的蝎子,炒得焦脆,一手端了碗,一手捏了蝎子一只只往嘴里送,嚼得脆绷绷的响。孩子们见了,惊异得不行,不懂蝎子的毒液一炒就不毒人。即使无毒了,难道成了世间的美味?呸呸!想起来就恶心。也有人问过老杜为什么吃蝎子,老杜却只笑一下,立即收住,照旧不答话。
老罗和老杜都不简单,他们不仅要懂得乡下人的日常需要,癖好,习惯和各种特点,进货合适;更要懂得收购——啥货啥讲究,如果收了次品而出了好价钱,他本人是要负责的;而亏了卖者也会背上坏名声。比如黄鼠狼皮,一张跟另一张,外行看起来没有差别,老罗和老杜却开出很悬殊的价格,原来毛色,大小,厚度,手感,都是有学问的,要眼看,手摸。我们常见老杜拎起一张黄鼠狼皮,吊在眼前看一眼,又吹一口气,那毛便翻卷開来,露出黄毛底下又细、又软、又密的灰色的茸毛,然后扔到柜台上,不容置疑地说:“三块五!”卖的人就只能拿到三块五,这就叫口无二价。有人怀疑老杜骗人,拿到镇上供销社收购部去,仍然是这个价,三回两回,大家就服了。
然而,老罗和老杜,身在乡下荒村,心却不能随乡入俗,跟村民们并无交往,仿佛一珠油浮在水上,永远不能融合。不过,村民与商店,倒也各行其是,相安无事。
就这样过了七八年吧,后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也就是“四清”运动开始了。不知与这运动有没有关系,总之,商店成了大队的商店,由大队自己安排店员,那是一个出身贫农家庭的陈姓青年,是大队长的亲戚。老罗和老杜从此消失了。姓陈的店员只管卖货,不再收购;而且物资紧张起来,开始实行计划供应,煤油、火柴、烟、酒、肥皂、布匹……一切凭票购买,小小代销店吃香了,小陈成了人们巴结的对象,有人为了多买一块肥皂、两包香烟、半斤酒,就请他吃饭,小陈常常喝得醉醺醺的,矮矮的个子,竟然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可关系不好,那美女总是哭着跑回娘家。
轧花机
本来是一个旧屋子,因为有了轧花机,就成了最热闹场所,吸引着大大小小的孩子,一些爱热闹的男人女人,有事没事也到这里闲呆着。破旧的屋子里人气就很旺。
不怨孩子们,也不怨那些男人女人,怨只怨那轧花机太奇妙了。轧花机转动起来,发出轧轧轧的响声,籽棉丢进去,吐出来就成了洁白的絮棉,而棉籽从机斗底下漏下来,下雨似的。这一切,多么神奇啊!小小的乡村里,这就是最高级的技术和最高级的机器了。
一个大队,三个村庄,八个生产小队,到了秋冬,大人小孩要换棉衣、添棉被,新棉絮都指望这架轧花机。一入秋,新棉花摘下来,轧花机就开动了,轧轧轧!一直响到冬月尾腊月头,赶完那些棉絮,响声才歇下来。
轧花机有庞大的结构,一半是木制,一半是铸铁。木制部分是动力系统:贴近地面是直径一丈五尺的木头大转盘,有撑木连着中间竖起的木轴。转盘装了木齿成为巨型齿轮。铁铸部分是工作系统:一个半人高的铁机械,四只脚,漏斗形状,上面是进料口,下面装了皮辊,外侧有大小两三个传动齿轮,跟转盘的木齿咬合。工作时,牛在转盘里走,拉动转盘,带动齿轮,再带动皮辊;籽棉通过皮辊,再出来就跟棉籽分离成为絮棉,也叫皮棉了。
在那时,轧花机是乡村最不能少的,它关联着全大队八百多户人家的吃穿呢。先说吃吧。槐树畈一带吃两种油,一种是芝麻油,俗称香油;一种是棉籽油,简称棉油。两种油各占一半。棉油是棉籽榨的,要吃棉油就必须开动轧花机,轧出棉籽来。大队有油坊,榨出棉油,挑回各小队仓库,等榨满一大缸了,会计一声喊:分棉油啊!各家各户忙不迭地抱了大罐子小坛子,在大油缸边排队。粮油是国家计划物资,生产队一年只分一回油,国家有定量,每人每年四斤半,这显然远远不够,炒菜只敢滴两滴辣个锅,不敢多一滴。家家都把这一罐子棉油看成命根子,分了油小心地抱回家,仔细藏了,只倒一点到小油壶里,放灶上炒菜用。然而,再小心也有出事的时候。有一回拗娃抱了一罐子棉油往回走,一路眼不敢斜视,嘴不敢跟人说话,一直走到门口,心想不会出事了,却不料被饿极了的母猪迎面猛地拱了一嘴,身子一晃,手不由松了,罐子摔成几瓣,棉油流了一地。拗娃也顾不得哭,慌忙用手捧,用碎瓷片刮……可是油渗得太快,眨眼被泥土吸干。拗娃一屁股坐地上,喊爹喊妈地嚎起来。可是生产队从来是不补发的。这一年,拗娃家可惨了。
这样,人们对轧花机的关注就理所当然了。
轧花机是传统农用机械,因为其动力是畜力。一头黄牛,蒙了双眼,套了轭头,在大转盘内走着圆圈儿,周而复始,永无尽头。黄牛啥也不想,只是走啊走,听着轧轧不息的声响,迈着悠缓的步子,以自己万年不变的节奏,走着,似乎要打瞌睡了,然而它始终没有机会睡着。那响声也悠缓,低沉,跟牛的节奏融合无间,浑然不分。牛的节奏也是传统的节奏,也是自然乡村的节奏。当然也是那个时代的节奏。
轧花机屋在我家老宅的西邻,隔着一个七尺宽的道子。这是道甫叔的四合头院子。正屋很高大整齐,木料也是上乘的;对面的西横屋也是全青砖瓦的,惟有这东横屋半坡瓦半坡草,后墙的砖也是半青半红。道甫叔对我说过,他的父亲,我的麻大爷——一个对晚辈极慈祥极和蔼的老人,一个很老实的“地主分子”——曾对他多次讲过,麻大爷的父母当年盖这座四合院时,因为亲自动手,搬砖抱瓦的,日夜辛苦,手指头磨得血珠直滴;而盖房的钱并不充足,东横屋盖了半坡瓦时,再也没钱买了,只好苫了山草。所以这座四合院就有些不伦不类。土改时,他家水旱田拢共只有二十五亩半,按政策规定根本不够打地主的,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们想分那大正屋,硬是给划了地主,把房子给分了,勒令他家搬迁到下庵村,搭两间草房住着。道甫叔对我说过,这院子原是内走廊,雨天在走廊走一圈可以不湿鞋。土改时西横屋分给了双喜,双喜把走廊砌成了前檐墙,而正屋和东横屋一直保持着走廊。正房和东横屋分给了贫农郑贺英,她没住几年就搬到樊家冈去了,这屋就成了公家的,平时开开会,东横屋放些杂物。后来,大队就在这东横屋安了轧花机。父亲说,他小的时候这东横屋是麻大爷家的牛屋和客房,有几年也做过私塾,附近几个村庄的孩子都到这里来发蒙,塾师姓岳,父亲也在这里上过两个冬学。算一算,已经有多少年了。四合院原有一个漂亮的大门楼,一直保持到六十年代初,后来就拆毁了。
记得我刚上学时,有一回父亲那辈人在这东横屋里开会,那时还没成立人民公社,“大跃进”也还没到,大概只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吧。抽烟的人很多,烟气缭绕,会还没开始,孩子们在屋里乱窜。狗爷给我出了一个字谜:一点一横杖,一撇到南阳,上十对下十,日头对月亮。狗爷从嘴里拔出旱烟袋,吐一口烟雾,笑问:“说说,是啥字?”我想也不想,回答说:“不是个‘廟吗?”狗爷大为惊奇,又出了几个字谜,都被我一一猜出了,从此,我成了村里小小的“能人”。
轧花有专人,叫李万林,是上村双庙畈人,因一只小腿有血丝虫变得很粗,人们就叫他“粗腿”。他像一只候鸟,每年收了新棉,他准时到来工作;两三个月后,冬天将尽,花轧完了,他就走了。到第二年秋天再准时到来。粗腿是好人,他一面坐在机子前,一点一点均匀地朝机斗里喂籽棉,一面跟闲看的人聊天,孩子们一进去他就喊,小心!不要摔到转盘里叫牛踩了!可是,哪个孩子也不在乎,照样跑来跑去。年底,空闲的轧花屋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园,大家站到大转盘上,轮番派一个孩子推动转盘,转得飞快的时候就像腾云驾雾,笑闹声要掀翻屋顶。有一年我不小心从飞转的转盘上掉下来,被转盘啃破了脚后跟,鲜血直流,跛了好久。
到我长成到大孩子与青年过渡的时期,电通到了村里,大队在双庙畈安了新式电动轧花机,速度快了,响声大了,味道变了。老式轧花机呢,自然是停了,后来就拆了,粗腿再不来一点一点地给轧花机喂籽棉。那一幅悠然古朴的画面和那悠然舒缓的轧轧声,从此消失;而孩子们也失去了一个绝好的冬天的乐园。
再后来,东横屋就拆了,只剩一堵残墙,在炎日雨雪里晒着,淋着,冻着。那已经是七十年代的情景了。
责任编辑︱曲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