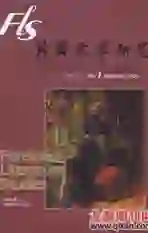不可言而言之
2009-06-24曾传芳
曾传芳
内容提要:威廉·斯泰伦的《苏菲的选择》被认为是“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作品以修辞性叙事和批评性元叙述,不仅重述了惨绝人寰的纳粹大屠杀事件,反思了人性之恶,还探讨了小说本身的构思与创作。本文认为,作品的叙述策略独出机杼,将修辞性叙事与批评性元叙述相互交融,建立了文本内部的对话关系。作家使用修辞性叙事,立足现实进行历史言说,从而使得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对话。同时,元叙述话语使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尖锐的批评性,不仅彰显了语言的力量,也肯定了文学的功能。
关键词:威廉·斯泰伦《苏菲的选择》修辞性叙事元叙述
《苏菲的选择》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威廉·斯泰伦(William Styron,1925-2006)的扛鼎之作,被蓝登书屋·现代文库评选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语小说之一,是美国大学课堂的必读书目,还被推荐为弗吉尼亚州全州公民的读物。斯泰伦深受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熏陶,具有南方作家特有的道德和历史意识。在作品中,他通过再现人类历史重要的历史时期和重大的历史事件,对人类历史、人性的善恶等问题进行人文主义的观照。《苏菲的选择》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立足现实进行历史言说,从而使得历史、现在和未来进行对话。小说以修饰性叙事重构、反思了难于言说的纳粹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件,以理论小说的元叙述探讨了小说本身的创作,赋予了小说思想性和批评性。
以纳粹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往往遭到无情的攻击。许多哲学家、史学家、学者和评论家都认为大屠杀这一事件不可言说,惟有沉默才能告慰千千万万的受害者。因为真实的大屠杀拒绝虚构。小说的“虚构”性与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相排斥,小说的再现功能受到质疑。
本雅明早在“讲故事的人”(“The Storyteller”,1936)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惨无人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作为一个文类、一种话语模式的“讲述故事”艺术(storytelling)衰落了,死亡了。从死尸遍野的战场归来,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人们已经无话可说。1940年,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中重申了这一观点,“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史学家们像故事讲述者一样,沉默无语”。德国哲学家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他说:“那些被枪托击倒的人们,受尽皮肉之苦,书写他们的经历就是从中攫取审美的愉悦……这样做对受害者不公”。欧文·豪进一步阐释了阿多诺的观点:“由于现有的审美成规与‘大屠杀真相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还由于不可能找到人类想象能接受的、可用作‘客观对应物的意象和象征,因此,大屠杀之后,作家的明智做法便是保持沉默,至少对大屠杀事件保持沉默”(Howe)。主张“沉默”的声音此起彼伏,斯坦纳也宣称:“除了诗之外,比诗更有力的是放弃,是选择沉默”(steiner)。也许没有人会否认,通过想象虚构的故事无权再现历史上那些真实的苦难。面对那些恶贯满盈的罪犯和深不可测的罪恶,诗难承其重。
与此同时,后结构主义关于历史的文本性的论断对历史再现的客观性和可靠性也提出了疑问。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罗兰·巴特、解构主义的始作俑者德里达都强调历史的文本性。这使得人们相信,我们惟有通过文本才能了解历史。同样,美国学者海登·怀特将历史编撰(或历史叙述)界定为一种文学与修辞的建构,一种由叙述对历史事件的再造。由此,人们生发了重述历史的冲动。不少当代作家开始思考重写历史和讲述他者的故事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斯泰伦通过讲述波兰女子苏菲的故事来接近、了解已成为历史的奥斯维辛,以期从新的视角重构关于纳粹大屠杀事件的无法言说的历史,并以此来探讨人性之恶。书写奥斯威辛的人们不仅需要思考“写还是不写”,还需要思考“如何书写”、“如何言说”。否则,很容易走向廉价的感伤主义。《苏菲的选择》使用了独特的叙述策略,不仅言说历史,而且着眼于现实,成为一部大屠杀文学的经典之作。
《苏菲的选择》最令人称道的是小说以修辞性叙述技巧将各个叙事层严丝合缝地融为一体。小说叙事的修辞性维度体现在诸多方面,比如,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叙述者的回顾性叙事视角和经验视角交替出现,赋予整个叙事文本以张力和反讽的基调。而同心圆的叙事结构让小说悬念迭出,使之具有强烈的哥特小说特征。在修辞的意义上,费伦把叙事定义为某人“出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在一个特定的场合给一个特定的听(读)者讲的一个特定的故事”。本文依据费伦的分析模式和方法,在宏观的修辞维度上可以发现围绕《苏菲的选择》的诸多平行关系。
《苏菲的选择》具有三个相关的叙事层面。第一个是内部层面,由苏菲讲述她自己的故事;第二个是中间层面,由叙述者斯汀戈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第三个是外部层面,由叙述者斯汀戈通过回顾性视角,或者说是斯泰伦作为隐含作者所建构的叙事层面——我们称之为作者的故事,也就是叙述者所讲的关于苏菲的故事的故事。
小说叙述者斯汀戈立志成为福克纳那样的大作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所租住的公寓里的另一房客苏菲。于是苏菲的故事与叙事者的故事开始相互交织,平行展开。很多时候,苏菲以第一人称向叙述者讲述自己的过去,包括二战前在家乡的生活、二战期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以及战后在美国的生活。此时叙述者的故事退居背景,苏菲的故事被置于前景,得以凸现。这种叙事技巧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苏菲的故事的恐怖和纳粹大屠杀事件的野蛮。本文认为,小说将纳粹受害者苏菲的故事放在叙述者的故事之中并不牵强,叙述者的故事并非多余。换句话说,如果只有苏菲的故事,那么小说只会是一部平庸的再现纳粹大屠杀事件的文学作品。在谈到《苏菲的选择》的创作时,斯泰伦曾说:
让人烦恼的事情是,以往我所读到的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作品都是些个人化的叙事,诚实、富有感染力,但是它们几乎是太有感染力了。作者不遗余力地描述集中营的囚禁生活图景:囚犯一天到晚不停地被鞭打、或陆陆续续地死去、或源源不断地被送往焚尸炉。我想避免这一切……我不想直接呈现恐怖,用另一种方式,我仍然可以达到富有感染力的效果。(qtd.in Cologne-Brookes 215-6)
可以说,斯泰伦是使用提喻的手法,用苏菲的故事来体现纳粹的罪行,然后将苏菲的故事置放于一个美国青年的成长故事之中。那么叙述者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的动机是什么?换言之,叙述者斯汀戈的叙述服务于怎样的修辞目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两个故事层面的并列与比较之中。
比如,叙述者斯汀戈与苏菲形成了对照。斯汀戈生活在社会相对安宁的美国,他未经历爱情,更不知死亡为何物,整天为赋新诗强说愁,其言行是唯典籍是从。苏菲则生活在波兰,后来被关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她时时面临死亡的威胁,并被迫亲手将女儿送进焚尸炉,身心受到巨大的创伤。但是,斯汀戈和苏菲二人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自私、冷漠、逃避现实。苏菲在被纳粹分子关进集中营之前,对她父亲超前的排犹屠犹思想保持缄默;在集中
营时,她试图藉此获得纳粹司令官的关照。她还拒绝加入和帮助当时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斯汀戈生活的全部则是性、文学和美国南方的历史。最初,他尽量回避与苏菲及其男友内森接近,认为与他们交往是浪费时间,自己是干大事业的,是进行文学创作的。后来,他倾心于苏菲主要出于两个原因,其一,他垂涎苏菲的美貌;其二,苏菲给予他创作灵感,因而想进一步了解她的过去。除此之外,他一概漠不关心。
此外,奥斯威辛集中营与战后美国社会也形成了对照。小说中凡此种种的对比不胜枚举。而这些并置都是由小说的时空双重叙事结构所体现。在空间上,美国战后生活情景是现实主义摹写的真实存在;奥斯威辛是一个虚幻的叙述空间,只存在于苏菲的回忆里,由一些被分割得零乱的情感碎片组成。在时间上,讲述美国的生活使用了现在时,并按线性时间顺序展开;讲述奥斯威辛经历时使用了过去时,时间流得快与慢、停顿与倒流,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层面不断变化与交替,构成了纷乱的时间形态。这是小说的深层时间。深层叙事被分割、穿插在用现在时叙述的表层叙事中,从而使得历史的与现实的、政治的与私人生活的、生存哲理的与琐细生活的场景平行并置;日常生活被上升到哲理层面来思考,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成了可视可感的东西。而在这些并置中,我们可以找到主题上的关联。通过苏菲与斯汀戈的对照,人性之恶的普遍性得以凸现。正如克罗根一布鲁克斯所说,受害者的悲剧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人们的不作为造成的,是人们对邪恶采取逃避和漠视的态度造成的(cologne-Bmokes)。
可以说,作者安排两个叙述层面的并置,是要观照战后美国社会的生存状况,并引导读者探讨人之本性。叙述者在倾听苏菲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目睹她在美国的生活之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巨变。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思考苏菲的悲剧命运,并打算通过书写苏菲的生与死来接近奥斯威辛,了解奥斯威辛。由此,读者在叙事的进程中也实现了与作者的交流:当斯汀戈从一个不谙世事、醉心于文学艺术的青年成长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成熟的作家,开始关注社会、人性乃至人类生存的终极意义时,我们欣喜不已。在苏菲的故事中,情况就复杂得多。对于苏菲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但同时,对她间接“参与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帮凶”角色,我们又持批判态度。
斯泰伦将纳粹大屠杀历史事件的再现置放在对日常生活的描述中的这种叙事策略,打破了政治话语与私人生活话语之间的界限,体现了一种新的撰史观。这种撰史观是盛行于欧美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物。虽然斯泰伦对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所呈现出的自恋倾向、文字游戏等十分不以为然,但他作品中所展示的具有自我意识的元叙述与冯尼古特、多克特罗等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殊途同归。
马克·柯里认为,“虚构作品与批评彼此吸收了对方的见解,产生出一种更富创造力的批评和一种新的具有思想性的小说”,这种小说就是所谓理论小说(theoretical fic-tion)。在这种理论小说中,叙述者(作者代理)常常打断叙事结构的连续性,直接对叙述本身进行评论;叙事性话语同批评性话语交融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换言之,这种小说在创造艺术形象世界的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抽象的批评世界。一部理论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一场作者(批评家)和文本(形象世界)之间的对话。在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中,这种批评性话语被称作为“元叙述”,其主要功能在于将读者的注意力引向关于小说叙述行为、叙述方式的评论。
在《苏菲的选择》中,作者不仅使用修辞性叙事,借助虚构人物苏菲讲述她无人理解也无人可以倾诉的隐衷,还原一段无法还原的历史,并实现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对话;而且借助叙述者回顾性视角,自由地穿梭于虚构的故事世界和现实的写作世界,对叙述方式、小说人物的塑造以及整部小说创作的构思等进行评论。也就是说,作家使用元叙述文本策略建立了一个批评世界。
在《苏菲的选择》中的元叙述呈现出两种范式。第一种是话语层面的元叙述。这种元叙述在文本中随处可见。比如,“如果真如当时所想,我在下一站下车,匆忙回到耶塔公寓,取出行李一走了之,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了,或是说根本没有故事可讲了”(斯泰龙)。又如,“让我们……先来看看霍斯这个人吧。他将在我们以后的故事里出现。但此时讨论一下这个反面人物,或许对了解这个畸形人物的背景有一些帮助”。这些话语层面的元叙述是叙述者关于自身叙述方法的评论,是为了达到某种叙述效果所采用的叙述方法。普林斯指出,从性质上讲,这些“元叙述评论”仅仅是叙事的“符码”,而不是“交流的成分”(Prince)。
第二种元叙述对文本的理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苏菲的选择》中,它被用来讨论小说创作的构思和叙事结构。首先,斯泰伦直接引用了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Lan-guage and Silence:Essays)中的观点作为自己小说整个构架的依据。斯坦纳说:
梅林和兰纳(两名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犹太人)被处死时,许许多多的人们正在两英里外的波兰农场,或5000英里外的纽约,酣睡,饱食,或看电影,或做爱,或为是否看牙医而焦虑不安。……同时发生的两种秩序截然不同,与人类的任何一种价值准则相悖。它们同时存在,完全是触目惊心的矛盾。……在同一世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时间种类,与“好时光”如影随形的,必定是如同撒旦之网的野蛮时期吗?(转引自斯泰龙)
这便是斯坦纳著名的“同一时间的不同秩序”的观点。如前文所述,整部小说的结构是将苏菲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经历同斯汀戈在美国的生活并置。这不仅是斯泰伦借叙述者之口对小说叙述方式的评论,更是对斯坦纳“同一时间的不同秩序”的观点的回应。斯泰伦进而说明了他为何要写苏菲的故事。他不同意犹太作家兼评论家埃里·韦塞尔的观点,即“小说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随意地把‘大屠杀取作题材……不仅削弱了它的意义,也使它的价值大打折扣”(262)。斯泰伦还说:“我不能接受斯坦纳‘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为无法言说的事情增加文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琐碎无益的争论的观点。我不认为‘在某些现实面前,艺术的再现是不切实际和微不足道的。……确实,正如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奥斯维辛的罪恶长时间保持一种无法理解的状态,我们没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远不可理解……我一直在想,也许了解苏菲,就可能对奥斯维辛有一丝了解”。斯泰伦拒绝沉默,表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以实际行动捍卫了文学。他坚信:“艺术无所不能!它可以探讨人类的任何经历——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还是未来的”(West)。
除了与韦塞尔和斯坦纳进行对话之外,在小说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的表达方面,斯泰伦还参考和援引了鲁道夫·霍斯的自传、汉娜·阿伦特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Eichmann in Jerusalem: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理查德·卢本斯坦的《历史的狡黠》(The Cunning of History:mass Death and the American Future)等著作。阿伦
特在60年代发表的《艾克曼在耶路撒冷》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平庸之恶。艾克曼是个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阿伦特将恶魔艾希曼平庸化。在她的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而是第三帝国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只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忠诚履行职责而已。在阿伦特看来,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官僚体制的杀人者”,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别正邪能力的人。阿伦特指出,艾克曼的行为正是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一种恶。这种恶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却默认并实践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虽然有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冷漠行为提供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但是,这种平庸之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苏菲的选择》中,斯泰伦在塑造历史人物奥斯威辛集中营司令官鲁道夫·霍斯和虚构的纳粹医生冯·聂蒙德时,明确地参考了阿伦特对“平庸之恶”思想的论述,还直接引用了霍斯的自传来证实该思想。霍斯和冯·聂蒙德被塑造成艾克曼式的人物。可以说,《苏菲的选择》论述了小说形式的“平庸之恶”,对人们提出了警示。
由此,小说元叙述部分为读者提供了解读小说故事世界的更广阔的视野。元叙述话语将《苏菲的选择》与其它相关文献建立了联系,与其他大屠杀评论者进行了对话。用克罗根,布鲁克斯的话说,在《苏菲的选择》中,奥斯威辛不仅通过幸存者的言说,还通过评论者的评述得以再现(Cologne-Bmokes)。
其实,斯泰伦在一定程度上也赞同大屠杀是无法言说的观点。小说中,作为青年作家的斯汀戈费尽心机地唤起苏菲的记忆。当讲述完自己在奥斯威辛的经历之后,苏菲走向了死亡。叙述或言说成为了苏菲的地狱之路。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以史为镜,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就是火中取栗,冒着灼伤双手的危险取出记忆之栗。奥斯威辛之后我们无路可逃,只能选择诗。尽管诗有可能毁灭诗人,却可以慰藉全世界。
欧文·豪说,精明的作家在处理大屠杀这个题材时,采用了珀尔修斯对付美杜莎的办法,即用光亮的盾牌作镜子找出美杜莎并砍下了她的首级,从而避免正面看见她而变成石头的命运(Howe)。斯泰伦是欧文·豪所指的精明作家。他用修辞性叙事着力表现奥斯威辛经历对幸存者的影响,从而间接地述说那段苦难的历史;又以理论小说的元叙述点评此叙事文本,使小说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尖锐的批评性。
责任编辑:桑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