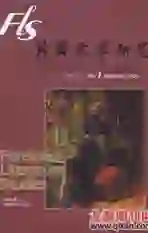克罗德·罗阿与中国的文化对话
2009-06-24刘阳
刘 阳
内容提要:克罗德·罗阿是当代法国的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他的文学生涯伴随着与中国的文化对话。他阅读中国古籍,到中国实地旅行,与来自中国的朋友密切交往,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写了几部著作专门论述中国和中国文化,表现出他对中国的热情关注。此外,罗阿还将其诗歌理论应用于中国古诗的改写之中。中国题材成为罗阿作品的一个重要部分,使之具有了几分中国文化的色彩。罗阿以其经历和文学创作证明了中外文化的交融和互补。
关键词:克罗德·罗阿诗歌中国文化
克罗德·罗阿(1915-1997年)是法国当代著名诗人、小说家、评论家,曾经长期担任法国加利玛出版社的文学顾问。他在小说、戏剧、传记、文学评论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诗歌领域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罗阿1985年获龚古尔学院诗歌大奖,1988年获法国诗人之家大奖。他的诗作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并被收入法国中小学教科书,受到中小学生的欢迎。罗阿出版的主要诗集有:《学艺的童年》(L'Enfance de l'Art,1942)、《亮如白晷》(Clair comme le Jour,1943)、《未成年的诗人》(Le Podte Mineur,1949)、《完美的爱》(LeParfait Amour,1952)、《诗歌集》(Pogsies,1970)、《在时间的边缘上》(A ln Lisiere du Temps,1984)、《秋天的旅行》(Le Voyage d'automne,1987)等。
克罗德·罗阿是一个具有特色的作家。他不属于当代的主要文学流派,与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和新小说派作家不同,他是一个遵循法国现实主义传统,不断探索文学奥秘的作家。在近70年的文学生涯中,罗阿笔耕不辍,以题材丰富的作品、清新流畅的风格,在法国文坛独树一帜。目前,罗阿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刚刚起步。少数研究者独具慧眼,对罗阿作了初步评价。江伙生翻译了罗阿的几首诗并且对诗人作了简要介绍。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一书中,分析了罗阿关于中国小说《聊斋志异》和《红楼梦》的评论。他们在中国率先进行了罗阿研究。本文认为,罗阿是20世纪的见证人,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法文化交流中也有杰出贡献。因此,必须对罗阿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探讨罗阿是如何与中国文化结缘,探索和弘扬中国文化,他的作品是如何表现中国题材和中国文化色彩的。
从耳闻到目睹:罗阿对中国的初识与理解
克罗德·罗阿与中国的接触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实现的,一是阅读中国古籍以及有关中国的著作,二是在中国的实地旅行,三是与中国人和西方的“中国通”接触。
青少年时代,克罗德·罗阿就想象着遥远的中国。他读了儒勒·凡尔纳的《一个中国绅士的遭遇》,感到自己与书中的人物金福和王哲颇为接近。后来,他又先后读了庄子、老子和列子,深受触动。罗阿不但阅读有关古籍,进行着想象的旅行,他还希望到中国实地旅行。1952年,罗阿作为进步作家应邀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纪念大会”。他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考察中国,并记下他的所见所闻。这些文章收入《中国入门》一书,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中国历史、政治、地理、文化等各个方面。
罗阿回忆他于50年代初在中国的旅行,他承认,他一下子就喜欢上了金福和王哲所代表的国家。罗阿在中国期间每天都能发现热爱中国的新理由。他的精神导师司汤达曾把“爱”区分为“心里的爱”和“头脑里的爱”。前者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后者是理性思考后的表现。而罗阿把这两种爱献给了同一个对象——中国。显而易见,罗阿对中国的热情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种真切的情感。
这次旅行的重大的收获之一是罗阿与老舍、茅盾、梅兰芳等文艺家建立了“幸运的友谊”。回到法国之后,他与这些朋友们保持着书信往来,此后他继续深切地关注着中国。70年代,罗阿第二次访问中国。他在此前20多年中写的有关文章,被收笔《关于中国》一书。罗阿在书中向人们介绍中国文化,与“欧洲中心论”作斗争。他以亲身经历介绍中国的现实,表达了自己的真切感受。
在罗阿的中国朋友中,定居法国的赵无极与他的联系最为紧密。两人的友谊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在罗阿去世时,赵无极写了纪念文章“我的朋友克罗德,罗阿”,回忆了他与罗阿的兄弟般的情谊。他说:“我与克罗德·罗阿的关系是友谊的关系,如同人们儿时发现炽烈的情感时所幻想的那样。……他对我的画作的理解是立刻实现的,他的书每一次出版我都是最先读到”。
赵无极和克罗德·罗阿的友谊首先源于他们对中国艺术的同样爱好。如罗阿所说,“艺术往往会导致友谊,我与赵无极的友谊就是这样”。诗人罗阿和画家赵无极的相识相知也体现了诗画同源的中国传统。正如赵无极所说的那样,诗与绘画二者都表达了生命的气息,笔在画布上的运动与手在纸张上的运动一致。它们揭示了其中隐藏的意义、宇宙的意义。罗阿与赵无极一样,从事“一种自我研究、一种内在运动”,“一种精神锻炼”,因为,激发着赵无极的“不是外部影响、环境,更不是时尚,他自我探询的是内心”。
赵无极遵循中国和法国的文化传统,将法国人的情感与东方人的意识结合起来。在西方人眼中,他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他的画作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用西方技巧表达了中国智慧,从而构成绘画中的抒情抽象派。罗阿对他的赞赏源于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对罗阿来说,赵无极的作品给了他一种“奇特的安慰”,这是一种“愉快的奇妙情感”。奇妙,这是因为赵无极是可资参照的“他者”,他的绘画作品深受中国思想的熏陶。安慰,这是因为罗阿觉得遇到了他期待已久的相遇。的确,罗阿把赵无极看作一个追求东西方和谐的榜样。而且,在赵无极看来,罗阿始终追求在个人和世界之间建立一种中国智慧所启发的和谐。
克罗德·罗阿和赵无极的友谊实际上是中外艺术家互相影响、相互获益的关系。对赵无极来说,克罗德·罗阿和亨利·米修是他在法国的两大支柱,这是他永远难忘的。他说:“尽管时光流逝,我仍然要将克罗德·罗阿和亨利·米修的友谊与我到法国最初几年的环境联系起来。他们的友谊是一种象征,使我扎下根来,因为他们一直陪伴着我,将我保持在亲密家庭和思想共同体中”。法国出版的第一部赵无极研究专著就是罗阿所著。同样,赵无极为罗阿的作品画了插图。此外,罗阿1967年与赵无极合作出版了一本《汉代石印画》。罗阿在赵无极的绘画中获得了平和与宁静。他在1956年夏天写给赵无极的一封信中说:“三个月来我与你的绘画和雕刻生活在一起,它们使我越来越愉快……”在罗阿心情郁闷的时候,正是赵无极的画缓解了他的痛苦,帮助他度过了生命中的艰难岁月。
罗阿与赵无极以其文艺实践进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他们相互交往,彼此欣赏,共同合作,各自受到对方的影响,同时也从对方那里获益。他们的交往是中西文化交汇中艺术家相交相知的例证。他们在互相交往中获得了各自思想和艺术的提升。
从观察到行动:罗阿对现代中国的体验与探索
与中国结缘是罗阿文学生涯中的浓墨重彩。罗阿与不少同代人一样,初次到中国旅行就意识到了中国的重要性。但罗阿与大部分当代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独立思考当代社会的现实,不受流行的“欧洲中心论”的束缚,对中国的感情一以贯之。罗阿在20世纪50年代到中国访问,他关注中国的各种复杂问题,对中国大地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奇。他利用一切机会来满足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好奇心。中国的幅员辽阔和巨大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细观察、记录他的所见所闻。他融入茫茫人海,力图透过人们的表情来领悟中国。他拜访参加抗美援朝的士兵和参加土地改革的农民,探索中国文学、历史,走访村镇、寺庙、博物馆,拜访郭沫若、茅盾、梅兰芳、齐白石等作家、艺术家,走访工人、农民、职员和学生。此外,他阅读了不少英文、法文书籍和中文出版物。由此,他对中国的理解更加深刻。
《中国入门》就是他辛勤耕耘的重要成果,其中汇集了他的游记、报告和访谈。罗阿对新中国表现了极大的热忱,他要通过这本书来介绍他亲临的中国,介绍中国的自然地理、古代中国的历史事件、当代中国的生活故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中国的哲学和宗教、中国古代诗歌和中国现代文学,等等。罗阿回欧洲之后继续关注中国的局势和各种事件。他经常拜访法国汉学家,关注他们对于中国的反应和态度。出于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热爱,他揭露一些人对中国的无理偏见,反驳他们没有事实根据的言论,表现了深刻的理性批评精神。同时,他也坚定地支持那些真实地表现中国现实的汉学家。罗阿的另一部书《关于中国》集中了作家1953年到1979年间曾发表于报刊的十多篇文章,于1979年由加利玛出版社出版。在这些文章中,罗阿对西方读者讲述了他心目中的真实中国。书中有对中国文学名著的评论,对中国诗歌翻译的看法,以及对中国现实的介绍。
按西方人的传统观点,中国地理位置遥远、社会习俗奇特、神秘而不可理解,中国人在体格和心理上不同于西方人,东方思想无法深入理解,甚至有人惧怕东方的存在。这些观点的具体体现就是“不可知论”和“黄祸论”。针对“不可知论”,罗阿指出,人们的视角不可避免地由他的生活环境所决定,他的判断力经常被隐藏利益所左右。西方人想表明自己了解中国,其实只是想表明自己的愿望。当他们以为描写了真实的中国时,其实只是纪录了他们希望看到的形象。对于“黄祸论”,罗阿认为,任何虚构都使得西方人离中国越来越远,任何神话都使得人们远离中国的现实。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以为接触了事物的本质,但只不过发现了表面的差异。在罗阿看来,“马可·波罗比19世纪的旅行家知道得更多,而19世纪的旅行家又比20世纪的士兵知道得更多”。因为他们曾经身临中国,有实地考察经验。因此,从不可知论到黄祸论,都不过是西方人在中国面前所表现出的无知。
罗阿不仅批判了西方的偏见,而且提出了纠偏的方法。他说,为了理解真实的中国,应该以深刻持久的兴趣来代替对异国情调的研究,应该用人类色彩来代替当地色彩,用真实来代替虚幻。所有这些工作有利于揭开表相,了解真实,还中国以真实的面貌。
如何看待东方,人们的出发点和视角通常不同,对于同一事物可能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重要的是保持独立思考,经过理性分析而得出结论。在这方面,罗阿表现了独特的眼光。在20世纪以前,有不少西方人即使到过中国,也仅仅对古代中国感兴趣,追求异国情调。他们并不想认识现代中国,他们的兴趣更多的是在中国瓷器、古玩、建筑和诗歌上。而罗阿认为,现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要深入了解中国,就必须了解现代中国。这不仅因为它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而且因为认识现代中国有助于理解古代中国,有助于以更深刻、更完整的方式理解中国。在罗阿看来,人类历史包括东西方历史,但西方教育体系把儿童关在犹太一希伯来一基督教圈子里。中国表现的则是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要认识中国文化,首先就要学习汉语。汉语的书写生动地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正是罗阿强调法国年轻人应该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理由。
罗阿不但撰文呼吁学习汉语,还具体提出了法国中学里开设汉语课的主张。他很早看到了儿童学习中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1969年,有人就减少语言学时而向罗阿咨询时,罗阿说他想发起一场战役来捍卫语言教育,在中学教育中尤其必须开设汉语和中国文化课程。罗阿第一个提倡在中等教育中把汉语作为必修课,并为此感到自豪。
罗阿鼓励法国人进一步深入了解汉语和中国人,不是为了以中国方式生活,而是学会更幸福地生活。他说:“生活在别处,这对于寻找比此处更幸福的人来说是可行的。”“这是一种朴实的智慧,虽不抱远大抱负,但很美好,这种智慧可以使那么不同又那么相似的人重新认识生存的权利。
罗阿在西方流行“不可知论”和“黄祸论”的时候,呼吁人们要认识中国,尤其要认识现代中国,而且很早就积极提出要把汉语和汉文化课程作为中学必修课,表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远见卓识。
从理解到实践:罗阿的中国诗歌翻译及其创作
罗阿不仅宣传中国文学,编了《中国诗歌精选》,还身体力行,以汉诗为蓝本,进行再创作。罗阿青年时代读到埃尔韦一圣一德尼翻译的唐诗集,对中国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50年代初,他在短期访华期间着手翻译中国诗歌。作为一个批评家和汉学家,罗阿对法国的中国诗歌翻译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自己也进行这项花费心血但意义深远的工作。
罗阿深知,将汉语翻译成法语的困难之处首先在于汉法两种语言之间的变化,即从一种单音节字到多音节字,从一种意符书写到一种拼音书写的变化。此外,还有散文规则、音乐效果等方面的不同。另外,中国诗歌包含隐喻联想、充满前期的文学回忆、暗示和历史寓意,一字一句都可以引申出多种含义,因此,罗阿认为汉诗不易翻译。
在罗阿看来,一个好的译者应该是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圣-德尼侯爵和程抱一都翻译了汉诗。罗阿赞扬圣一德尼是首次揭开和启发世界上最美的诗的人之一。“时间没有削减其光辉,也没有妨碍其精确”。程抱一翻译了不少唐诗,表明“对于一种处于隐喻层次的这个意义系统的符号学分析”。罗阿高度评价程抱一在其著作中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和丰富性,尤其向法国读者推荐他的中国古诗翻译。
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文化长期维系,绵延不绝,与其说因为受到长城保护,不如说因为受到语言保护。由于汉语结构极为奇特,所以人们一直认为中国几乎没有语法:名词无词型变化、动词无变位、很少用人称代词……对此,罗阿指出,因动词的无人称、无时态、代词潜隐而产生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并不是汉语的缺陷,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在天地万物间的一种态度。
罗阿看得很清楚:在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不可转达的成分,翻译家的工作是复杂而艰苦的,要求人们的勇气和智慧,博学和才能。他认为在翻译时要保持着谦恭的态度,最好保持
一首诗的原味。因为人们不能翻译出诗的全部美感。在这种情况下,读者借助于他的汉语知识,将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而对全诗有完整的概念。罗阿赞扬翻译家的工作,出于他的自身经验,他非常理解翻译是另一种形式的文学创造。
另外,罗阿还指明了翻译汉语诗歌的常见问题。西方翻译家通常想精确地抓住含义,谁在湖畔或者山中倾听飞雁的呼唤,哪只手在拨动古琴的琴弦。他想知道这在什么时候发生,是昔日、昨天还是今天?他要掌握各种成分,以便能确定诗歌的感情色彩,作者的思想状态(作者通常是看不见的、隐藏的)是乡思、愉悦,还是忧伤、悲痛呢?因此,在罗阿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比较忠实地翻译出来,还是彻底背叛了原意。因为进行这种尝试的作者忘记了一点,这就是西方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汉语表达方式,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人在世界面前的沉思方式和态度。比如人称代词的省略通常消除了汉诗中主体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对立。中国诗人不会把自己限制于单一的角色。罗阿举例说明汉诗法译中的误解。比如,汉代古诗和唐代著作在法文版中通常变成了充满“白霜”和“微风”的田园诗,“水”总是被翻译为onde(波浪),女子的脸被翻译为minois(脸蛋),春耕被翻译为ebats printaniers(春天的嬉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诗到法国人那里就显不出活力了”。
罗阿学过汉语,但没有坚持下去。由于几乎不可逾越的语言和文字、文化和传统的障碍,翻译中国诗歌对他来说是一件艰难的事。罗阿坦陈他所遭遇的语言障碍:“我也很不走运,没能到达学汉语的彼岸”。作为文艺批评家,罗阿指明了翻译中国诗歌的困难。但是,罗阿喜爱汉诗,努力掌握中国诗歌的特点,并加以推广。多亏不少中国朋友和汉学家的帮助和建议,罗阿努力掌握中国诗的精微涵义,终于实现自己的愿望,出版了他的中国诗歌改写集《盗诗者》(1991年)。
在《盗诗者》一书中,罗阿介绍了一批著名的中国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另外还有陶渊明、李煜和苏轼等。他还收入了一些民歌,主题往往是:时光流逝、人生如梦、生死爱恨、日常生活,等等。罗阿认为,中国文人倾听人民的呼声,追问人生的终极意义。面对人世沧桑,他们寻求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世界的和谐。而当个人理想不能实现的时候,他们试图排遣人世的忧愁,构建一个安宁的内心世界。罗阿介绍的大部分诗人通常具有共同的特点:他们在乡间和大自然中度过大部分时光,写了大量自然诗,大自然与他们的生活与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于是,罗阿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发现了一个新天地。对此,罗阿写道:“进入中国诗歌,就是进入了自然”。
罗阿认为,在形式和内容方面,不能百分之百地再现中国诗歌。因此,翻译的重要任务就在于使古代中国诗歌简洁明快的风格鲜活起来。但是,罗阿选的诗一般说来缺少隐喻或象征,偶尔采用,他也以自己的方式重写。比如王维的诗《欹湖》,“吹萧临极浦,日暮送夫君。湖上一回首,青山卷白云。”罗阿改写为:“吹着笛子穿越过湖/太阳落山。朋友分离。/独自回返。山色青蓝。/一朵白云山上飘散。”王维的原诗描写妻子送丈夫的场景,但在罗阿的两种文本中都改成送朋友。原诗中“青山卷白云”一句既可理解为山卷着云,也可理解为云被山卷着,体现了中国人的思想及其艺术表现,令人回味。在罗阿的改写诗中,原诗的意蕴就表现不出来了。
罗阿所选的大部分汉诗通常用大众化语言写成,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诗就是如此。由于风格上的接近,罗阿擅长于掌握这种类型的汉诗再创作。罗阿按照自己的诗歌取向选择了中国诗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加以改写,充实了他的作品宝库,使他的作品具有了更丰富的思想内涵。
罗阿从儿童时代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20世纪上半期,罗阿感受到了战争所造成的社会动荡。他在对人类社会悲观失望的时候,把目光投向中国,在中国思想和文化中找到了安慰和乐趣。经过阅读中国古籍和实地旅行,他对中国的了解逐步深入。他与赵无极等人的相遇使他更加熟悉中国文化的内涵。因此,罗阿不仅比他的前辈具有更多的实地体验,也比他的同辈作家更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意蕴。
在罗阿看来,发现中国就是发现另一个自我。他对中国的真情实感发自内心。20世纪下半期,在东方之光的照耀下,罗阿的诗歌创作达到新的高度。他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改写了中国古诗,成为法国诗歌宝库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中国题材成为他创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思想使其作品具有更深广的东方文化内涵。他的创作成就是与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同步发展的。
在罗阿看来,法国文化和中国文化相遇,能够实现两种文化的共存和发展,达到他所望的“和谐”。罗阿虽然在西方文化环境中生活,但他以中国文化为参照,与中国文化对话,以亲身体验证明了东西方文化沟通的可能。罗阿以他的著作和行动,向我们具体地证明:人类文明的价值是普世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有助于实现两种文化的互补,促进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外部世界的和谐。
责任编辑:桑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