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扼杀同人刊物《探求者》
2009-03-26于继增
于继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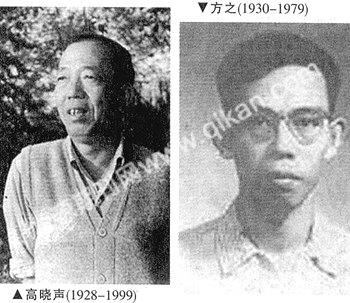
《探求者》是产生于1957年江苏省的一个文学社团的同人刊物,它刚具雏形一个来月便在“反右”风暴中被康生所扼杀。其发起人陆文夫、高晓声等作家也遭到了灭顶之灾。
那么,当初这样一个短命的刊物是如何“出笼”的呢?
周扬表态“同人刊物也可以办”
当时的国内情况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文人学者进行“鸣放”。这年11月,中宣部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研究和部署如何贯彻“双百”方针问题。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等积极主张文学期刊应当“多样化”,不赞成清一色“机关刊物”的倾向。大家畅所欲言,讨论得很热烈。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会议总结报告时也明确提出了“同人刊物也可以办”,这是“为了有利于提倡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自由竞争。”
所谓“同人刊物”,就是一批因信仰、志趣、文艺观相近的文人自愿结合办起来的非官方出版物,这种刊物容易形成各自的风格和特点。在早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类刊物很多,如郭沫若的《创造月刊》、林语堂的《论语》、叶圣陶的《开明少年》、黎烈文的《中流》等等。另外,同人刊物不需要“编制”,不需要政府拨款,办刊经费完全自筹,编辑和作者大都是尽义务。茅盾在1937年8月创刊的同人刊物《呐喊》(后易名《烽火》)启事中声明:“本刊排印纸张等经费皆同人自筹,编辑写稿,咸尽义务。对于外来投稿,除赠本刊外,概不致酬,尚祈谅鉴。”同人刊物成为那时编创人员自主交流、自由创作的一个重要平台。但建国后此类刊物几乎绝迹了。周扬这次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上的这个讲话,重新燃起一些作家、编辑尝试办同人刊物的欲望。
中宣部召开的这次会议期间,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组长陈椿年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4期文学讲习班,他和全体学员也列席旁听了中宣部的这次会议。“周扬的总结报告肯定将作为文件传达下去,但我却按捺不住喜悦之情,立即写信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在南京的朋友高晓声和叶至诚。当时并没有想到,更没有提出‘咱们也来办它一个,我只是以为今后的创作环境必将更加宽松自由了,为此感到由衷的兴奋,忍不住想和朋友们分享……”(陈椿年:《关于“探求者”、林希翎及其他》,载2002年第11期《书屋》)。据也是参加中宣部这次会议的《江苏文艺》主编、江苏省文联副秘书长章品镇证实:“在周扬的报告里听到中宣部已委托巴金、靳以创办一个《文学季刊》型的大型同人刊物。这个内容不待我的传达,已在江苏许多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中盛传……”(《三幅字给我的悲喜》,载2004年第5期《苏州杂志》)
总之,高晓声、叶至诚等得知允许办同人刊物的消息后深受鼓舞。
据已故原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时任江苏省文联《雨花》杂志小说组专业作家的陆文夫回忆:
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这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一番热烈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1957年6月6日……(载陆文夫《又送高晓声》,1999年第5期《收获》)
一个尝试办同人刊物,然而却为他们日后厄运埋下伏笔的计划就这样形成了。
巴金劝阻“不要办同人杂志”
为了实现办《探求者》的愿望,陆文夫等人按照组织程序,首先请示了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艾煊表示支持,说这些青年挺有积极性的嘛!他们又找省文联党组书记、文化局副局长钱静人,钱的意见是不要搞正儿八经的文学杂志,提议在《江苏文化报》上辟出整版篇幅,一周一期地发表同人作品。省文联专业作家高晓声认为这个主张不符合他们想办独立刊物的初衷,南京市作家方之说,要解决问题,只有找省委。于是他们找到省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谈,这位书记答复“同人刊物是可以搞的,但怎么搞还要再商量。”
不久,周扬的那个讲话作为文件下发后影响很大,四川、北京等地也出现了办同人刊物的势头。于是陆文夫他们便联名在7月号的《雨花》杂志上写了一篇《意见与希望》,反映他们想办同人刊物的愿望;还公推陆文夫、高晓声分别起草了《探求者文学月刊社章程》和《探求者文学月刊社启事》(这两份文件在筹备过程中没有来得及正式发表,后来是被《雨花》作为批判材料拿出来公布的。)。
由陆文夫起草的《章程》明确提出:“本月刊系同人合办之刊物,用以宣扬我们的政治见解与艺术主张。”“刊物不发表空洞的理论文章,不发表粉饰现实的作品。大胆干预生活,对当前的文艺现状发表自己的见解,创作方法也应该多种多样。不崇拜权威,也不故意反对权威,不赶浪头,不作谩骂式批评,从封面到编排应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本刊系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之刊物,不合本刊宗旨之作品概不发表。”“同人必须参加刊物的编辑、发行、联络友人、向刊物推荐稿件等工作,并不取任何报酬。”
高晓声起草的《启事》说:“我们是一群年轻的文艺工作者。我们的政治、艺术观点都是一致的。现在,我们结集起来,企求在统一的目标下,在文学战线发挥更大的力量。”“对于目前有一些文艺杂志的办法,我们很不满意,编辑部缺乏独立见解,显示不出探讨人生的精神,特别在艺术问题上,没有明确的目标,看不出他们的艺术倾向。这是用行政方式办杂志的必然结果。文学不应该只唱赞歌,要写人;不应当写政策、写运动。”“我们是同人刊物,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艺术倾向;我们把编辑和作者混同一起,稿件的来源就靠同人,我们将在杂志上鲜明地表现出我们的艺术风貌……就像打仗可以用各样的兵器一样,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各种创作方法都可以运用。我们不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更不承认这是唯一的方法。我们将勉力运用文学这一战斗武器,打破教条束缚,大胆干预生活,严肃探讨人生,促进社会主义。”
他们将这个章程的打印稿立即直呈北京,不久就到了康生的手里,康生看后对身边工作人员阴阳怪气地说:“听说这叶至诚是叶圣陶的儿子,嗯,嗯,嗯……”
陆文夫他们当然不知道康生到底想些什么。他们接下来的任务便是筹措经费和发展同人。由于陆文夫和方之是华东作家协会的会员,他们就带着一批印好的“章程”和“启事”跑到上海华东作家协会,先后拜访了巴金、叶以群、阿章、唐克新、姚文元等,希望他们能够作为同人参加。华东作协大多数人听了都表示赞同,尤其是《萌芽》杂志的编辑姚文元态度更加积极,不仅乐意“帮忙”,还留下了他们带去的材料,说“好好研究”。出乎意料的是,当他们和巴金交谈的时候却遇到了阻力。巴金毕竟是“过来人”,他此时已预感到政治气候在发生变化,于是明确表态自己不参加,并劝他们也不要搞了。巴金后来在《悼方之同志》一文中回忆说:
我只记得他(方之)和陆文夫同志一起来找我,谈他们组织“探求者”的打算。……他们想在创作上多下功夫,约几个志同道合的业余作者“探求”。他们说已找某某人谈过,得到那位同志的鼓励。我了解他们的心情,三十年代我们也曾这样想过,这样做过。这两位年轻人在创作上似乎有所追求,有理想,也有抱负。我同情他们,但是我替他们担心,我觉得他们太单纯,因为我已感觉到气候在变化,我劝他们不要搞“探求者”,不要办“同人杂志”,放弃他们“探求”的打算。……他们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也说不清我的意思,他们当然不会照我的意思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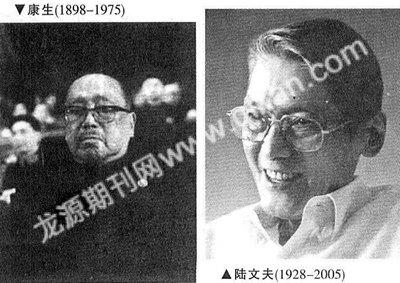
被巴金婉言拒绝后,血气方刚的青年小说家方之很是失望,说:巴金不是党员,我们别去听他。陆文夫虽然有些沮丧,但当时也没有表示什么。从上海回来,陆文夫顺便回了一趟苏州的家。他想,巴金的的意见恐怕有道理,于是写了一封信给南京市文联,信中说:“同人杂志,总觉得有小集团嫌疑,与提倡的集体主义思想有抵触,我想来想去,还是退出,不参加的好。”——这封信救了陆文夫一条命,后来追查时,他虽然受到处分,但没有被打成右派。“巴金的觉悟比我高,也许他已经听到了些风声,但不能明白表示出来。”陆文夫说。
方之从上海回到南京后,对他的妻子说,嘿,他(巴金)怕什么,他怕,我们又怕什么?意思是他们是小青年,是党员,不怕。他们觉得巴金不参加“探求”是出于“怕”,根本没有理解这是对他们的提醒和保护。所以他们很快就尝到了苦头。
康生批示“《探求者》是反党集团”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社论《这是为什么?》,由“整风”迅速转为全国“反右”。“探求者”在劫难逃。7月20日,江苏省作协党组召集全体“探求者”开会,要各人说清情况。8月12日省文联召开首次反右批斗大会,又召开文联委员扩大会,批判“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相继被隔离审查。不过,起初“探求者”们并不承认自己搞刊物是“反党”,只说是这做法“不合时宜”。——实际上,当时陆文夫他们已经看到了《这是为什么?》打出的信号,但出于对文学的天真和痴迷,使他们忽略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竟不顾劝阻,依然“逆流而上”,这就注定了悲剧的发生。
此时,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具体指导江苏文艺界的反右斗争。在北京时他已获知江苏搞了个《探求者》,那时他就认为这里面“有问题”。他胸有成竹,坐镇苏州,听取汇报,查办反右所获的“成果”,是揪出了一个名曰“探求者”的团体。康生说它是“有组织、有纲领、大摇大摆公开活动”,他在一个材料上批示:“江苏《探求者》这样的集团,如还不算右派反党集团,那还有谁算反党集团,谁算右派呢?”遂下令严查。
而当时中共江苏省委对反右并不积极,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还为此受到过上边批评。据长期担任省长的惠裕宇回忆,当时省委召开常委会专门研究对《探求者》这批人的处理问题时,所有的常委没有一个不想保他们的,省委宣传部部长俞名璜甚至“说着说着眼泪汪汪的”。于是组织上对有些人采取了“边戴帽子边摘帽子继续留在党内”的保护性做法,这是中共江苏省委在反右运动中的“发明”。尽管“探求者”们都作了深刻检查,但由于康生施加压力,开始了对《探求者》的公开批判。
1957年10月9日的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探求者〉探求什么?》,指出:“他们所谓‘打破教条束缚,就是打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所谓‘大胆干预生活,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所谓‘严肃探讨人生,就是否认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就是他们所谓‘探求的实质。至于所谓‘促进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促进到他们所‘探求的那些方向和目标去。”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江苏省的大型文学杂志《雨花》在这年的第9、10、11、12期上连续刊载多篇批判《探求者》的文章。上海的姚文元也闻风而动,他在1957年第12期的上海《文艺月报》发表《论“探求者”集团的反社会主义纲领》,文中说:“‘探求者的启事和章程是一个在文艺领域中的反社会主义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反动性是露骨的、不加掩盖的,他们也的确把自己的这种主张‘公之于世了。这个纲领是这样的荒谬,他们想‘探索一条资本主义的道路……”陆文夫不成想,他们不辞辛苦到上海送上门的“章程”和“启事”,竟成为“姚棍子”揭发批判“探求者”的第一手材料。这场由江苏发轫、北京推动、上海呼应的批判,连篇累牍,“探求者”一时间竟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大案。
由于康生的直接干预,“探求者”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名是“取消党的领导”,“搞同人刊物”。此时的“同人刊物”已等同于“反党刊物”,不仅是“不合时宜”,而且变成了敌我性质的问题了。康生的“批示”,直接导致了批判《探求者》的升级和定性。
“探求者”的最后归宿
从《探求者》发起到被勒令检查仅有一个来月的时间,其“生存期”之短令人惊讶!事实上,《探求者》作为一个“刊物”并没有出版,只能算是“胎死腹中”。然而这个“胚胎”尚未露面就已经成了“反党集团”的罪证。当时四川、北京等地的一些同人刊物也被取缔,但没有哪一个像《探求者》那样受到如此的系统批判和严重处理。这个“功劳”应当归功于坐镇江苏指挥反右斗争的康生。
后来陆文夫回忆说:“审查开始时首先要查清《探求者》发起的始末,谁是发起人?起初我们是好汉做事一人当,都把责任拉到自己身上,不讲谁先谁后。不行,一定要把首犯找出来,以便于分清主次。”时任省委宣传部文艺处指导员兼省文联创作室副主任的叶至诚和南京市团市委宣传部长方之是中共党员,在一次受批判之后,两人回到宿舍都哭了,他们商量好:“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然而这只是他们的良好心愿。“车轮战”使所有“探求者”成员无一幸免。“探求者”一案由于康生插手,最终一网打尽,难逃厄运。
至1957年12月,除叶至诚、陆文夫没戴右派帽子,叶至诚被留党察看和降职处分下放劳动外,其余“探求者”的成员们无一幸免地都被打成右派。作家曾华受迫害屈死,方之、梅汝恺送去劳改。首先想起办同人刊物的省文联专业创作员高晓声成为“主谋”,被发回原籍武进务农编筐。陆文夫降两级去苏州机床厂当学徒工。翻译家陈椿年降两级被发配到青海。对“探求者”表过态的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艾煊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宜兴太华山劳动……文革中又重新将这批人拉出来批斗。他们的家庭和亲人也纷纷遭殃,处境凄凉。
“探求者”们为了某些文学的“探求”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探求者》的冤案终于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们的政治名誉。沉寂20余年的高晓声、陆文夫、方之等东山再起,铁树一样开了花。他们拉动时代的引线,掷出的《陈奂生上城》、《美食家》、《内奸》等极具特色的小说在全国频频爆响,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道奇异的风景线。还有的“探求者”在写作的同时担任了全国和省的作协领导、文学杂志主编等职务。如今,这些同志大都已作古,但他们当初的“探求”毕竟如火花般划过历史的天空,他们对文学事业的执著精神留下令人难忘的一笔。
责任编辑 齐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