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与小天地
2023-11-01师力斌
师力斌

从我个人的经历看,诗意是生长出来的,与地理有关,与故乡有关。
我想赞美的地方,都是哺育过我的。现在的爱诗,都源于这些地方,源于这些地方的山川草木、花卉果实。我越来越热爱乡村,近于偏执,对高楼大厦、汽车霓虹完全无感。如果简单划分我的诗歌,热爱都出自山川草木、花卉果实,烦恼都源于高楼大厦、汽车霓虹。这或许是我先乡村后城市的后遗症。时常外出散步归来,遥看小区多窗的群楼中住了多年的住宅,仿佛异地,陌生而可疑:小小的水泥格子就是自己的家吗?城市住久了,心越不在城市,越往故乡跑,往自然风景区跑,往公园跑,往京郊的山水间神游。路边的一棵草、一株树触发的美的安慰,远胜于剧院、美食和聚会。每当神游,诗便成了宝马良驹,带我前往精神上的昆仑瑶池。2023 年,我去川西高原,见到贡嘎雪山的刹那,我便臣服了。它不断在上升、上升,仿佛在引领,气场远大于高楼大厦,远大于一座城市。那种无以名状的庄严神圣,不容置疑。人家靠的是亿万年的大修炼,一座城才多少年?细思好笑,乡野出身、童年记忆、亲近草木的历史,决定了我的爱诗,主宰了我的精神世界。对人生来说,童年太重要了,多草木、多田园闲适、多山水清旷,培育了我内心的草木、闲适、清旷与诗。
从小到大,尽管生活百般艰难,但在住地上总是与美景为伍,真是独特的“天赋”。2 岁至6 岁,我住在位于山西上党盆地的小山村姬家岭,南北两庄,中间一沟,全村二十户人家分住南北,独我家在沟里。记忆中的姬家岭像桃花源。一般的黄土高坡都是光秃秃的,这里四布的黄土崖上却生出众多柏树,凌空盘曲,远看像笔墨点染的国画。北庄庙院里一棵两围多粗的老柏,高耸入云,小时候和伙伴们比赛仰望它,望得脖子疼。柏籽能吃,有奇香。柏的香味、松的香味、祖母烧火做饭的柴火味、院中海棠的花味,是我幼时记忆深刻的故乡味道。后来,读杜甫《古柏行》尤有感觉:“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崔嵬枝干郊原古,窈窕丹青户牖空。”正合我的儿时记忆,我们的庙院小学本就在高台上,四望山峦起伏,可不就是“孔明庙前有老柏”“崔嵬枝干郊原古”,加之四时之景变幻,与杜诗如出一辙。我小学一年级在这里上课。
姬家岭的树哺育了我人生最初的诗意。生产队的梨园秋收后开放,大部分梨子摘去分给各家各户后,就成了孩子的天下。我们整天攀在树上,寻觅剩梨。若能摘到一个,便惊呼同伴前来共享。秋天阳光明媚,梨叶幻化出各种颜色,从黄到橘到红,启蒙了我对“五彩缤纷”一词的认识。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一章写果园采摘,情景与姬家岭相似。我家屋前有一棵海棠,粗可合抱,花开时节,满院飘香,蜜蜂飞舞,一团团粉白的花瓣把小院撑满了。近秋果熟,我常在树上待着,现摘现吃,像在蟠桃园里的美猴王。父亲请了木匠师傅打家具,我和一帮小朋友在院子里疯玩,阳光照耀下,木匠们身影晃动,刨花香味弥散满院。中午,祖母做好工饭,一般有肉,木匠们端碗蹲着,谈天说地,给我留下蒸蒸日上、日子红火的记忆。90 年代,那棵树被砍了。后来,我在北京郭沫若故居看到两树西府海棠,树影婆娑,风姿绰约,睹树思乡,倍觉伤怀。我们总是留不住树。姬家岭院子西边有一棵桃树,也是我的伙伴。每年秋收,玉米棒运回,堆在院子里晾晒,大人剥玉米皮,小孩子就把玉米皮挽起来,西连桃树,东接海棠,扯成一条几十米长的绳子,做打电话游戏。这巨大的工程,十分令我自豪。还有香椿、红枣、花椒、烟台梨等树,多是父亲从城里农场带回种下的。屋后还有一棵君迁子,土语叫“软枣”,果实状如羊粪蛋,在手里捏搓,软绵可心,吃起来沙甜,是我们村的唯一。
还有放羊。羊圈在村外一里多的崖洞里,牧羊人早饭以后开洞门,羊群如学生放学般涌出,黑山羊、白绵羊,“咩咩”叫着,在黄土坡撒欢。小屁孩甘当跟屁虫,我拿一个小羊铲,铲一块土坷垃扔向跑到庄稼地的羊,意不在护庄稼,在于看扔得准不准,嘴里学着他们的吆喝,“达咯嘶,达咯嘶”。最快乐的是骑羊,没坐稳便摔下来,躺在地上一身骚味,哈哈大笑,乐此不疲。那时当骑士游四方的理想,就是跟着牧羊人漫山遍野疯跑。
田野是儿童永远的乐园。秋收时节,夜里农忙,各家在地里点了火堆烧玉米吃,香甜的味道四下弥漫,比现在城里的烤玉米馋人得多。在夜幕鼓动下,我和小朋友们在各家的玉米堆前追打嬉戏,不亦乐乎。真是无忧无虑的日子。我对田野的浑厚感情就是在儿童时代产生的,与时俱长。实际上,那时的母亲正不得志,郁郁寡欢,我却根本领会不到。
小桥流水的最初经验也在姬家岭。房后二十米有一个小河沟,上有小桥通往南庄。秋雨过后,水沟涌溢,浸过石头,激出潺潺水声。可以洗菜,还可以拿了蓖麻杆做水枪,就地取水射击,比现在玩手机打游戏过瘾多了。小溪上溯,直至自留地。每年秋收,都能在地边玩水,这个乐趣一直持续到1987年我到长治上高中。
6 岁至17 岁,我到父亲工作的石哲镇上学,距姬家岭三四里。暑假和国庆节常回姬家岭玩。石哲也是个很美的地方,名字独特,地处小盆地,浊漳河上游,西为发鸠山,此山相传是神话精卫填海的诞生地,是精卫鸟的故乡。东临申村水库,建于1958 年。老人们说,当时王八多得像秋收之后地里的玉米茬子,想吃的人,到河边拿脚一踹,它便翻了身,用脸盆装起来就走。水库宽阔,水光接天。两岸绿树萦绕,远处青山脉脉,空气里散发着河草的香味。河面水鸟飞鸣,渔人隐映,像极了江南。河上往来木船,载各色行人,红黄蓝绿的衣服、自行车、包袱、孩子,说说笑笑,水声荡漾。岸边铺垫着松软的玉米秆,方便船客踩踏避水。这里是我人生最初体验到风光无限的地方。我家“文革”结束后到石哲,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开始。我那时对大历史没有任何觉察,该上课上课,该玩耍玩耍,沉浸在石哲的美景中。80 年代上高中以后患上神经衰弱,每年利用暑假回到石哲的水库边钓鱼休养,效果奇好,对故乡的精神依赖从此更甚。后来,我带父亲来北京,逛了颐和园等地,问他怎样,他说哪儿也不如石哲好。这可能正是国人常见的故乡“偏见”,现在进城打工的一些年轻人好像恰恰相反。
我家在石哲租了多次房,在村里转了一圈,最后定居在村子最西头,院子大,周围全部是田野。父亲把院子当田园侍弄。没有院墙,就用玉米秆编篱笆。80 年代,盖了院墙,种了百十来棵杨树,形成了一片小树林。早晚在树林里跑步,空气新鲜,十分惬意。父亲在院子里开辟了一个大菜园,再用一道篱笆围起来,以防鸡们偷吃。父亲不爱交际,菜地便是他的社交圈。搭架、捉虫、剪枝、固秧、修渠,自得其乐。菜园是父亲的最爱,他潜心经营,蔬菜口味纯正,植下了我对于绿色食品和农家乐的深刻记忆。夏天成熟季节,我家成了对面中学食堂的蔬菜供应地,品质好,比集市便宜。打水浇菜是又一个乐趣。院子里挖了一口深井,每次可以打二十来桶水,我星期天和放暑假帮父亲摇辘轳打水,累得气喘吁吁,乐此不疲。浇完,夕阳西下,金色的光从西院墙上洒到院子里,我就搬个方桌,放在院子中间,做暑假作业。如果是雨后,空气清新,泥土潮湿,廊檐下的青砖略带绿苔,倍觉恬静。母亲则一趟趟进出菜园,把快要熟了的蔬菜摘到一个塑料篮子里。她在秧苗间穿行,神情怡然,那种田园的满足令我终生难忘。
另一项农家乐是养鸡,找蛋。二十来只鸡田野里散养,吃得羽毛丰满、体态臃肿。每天产蛋一斤多。母亲在每颗鸡蛋上标上序号,以区别新旧,旧蛋先吃或先卖。母亲每天都要把母鸡抱在怀里摸蛋,说,黄鸡有蛋,白鸡有蛋,大黄鸡没有,肯定又下在什么角落里了。我就四处寻找大黄鸡下的野蛋,某一天会豁然发现,在某个角落的草垛子里边,或在一蓬荒草里,好多蛋。春天孵小鸡令我和弟弟着迷,孵十七八天,把蛋放在一个水盆里,晃动的鸡蛋可以出鸡,一动不动的,则可能没有希望。我们挤在母亲的旁边,东抓一下,西弄一次,充当养鸡小专家。到二十一天小绒毛球们出壳,刚出来便可直立在砖地上,叽叽叫着,或躲在母鸡肚子底下,第二天便欢叫着跑到院子里找虫子。当时没有感觉,似乎生活就应该这样,现在住到大城市回头看,这样的生活实在奢侈。后来我住在太原、北京,常常做白日梦:一个大院子,菜园、鸡鸭、树林、水井,一家人围坐院中,岁月静好。这才是我心目中现代化幸福生活的图景。进了城,失了地,没了院,才知道土地对于人生多么重要,才明白自己种的菜多么香甜,才明白人的幸福想象,其实就是童年想象。未来的孩子年老时,记起的是不是只有手机?
石哲和姬家岭给我留下印象的远不止这些。记得最多的是13 岁以前的事,14 岁上高中以后记得少了。在长治、在太原,近年来在北京的生活,都恍惚朦胧,姬家岭和石哲的生活却像一部老电影,清晰的影像经常浮现。我知道这叫作怀旧,是衰老的征兆,但我无法排除,它们牢固构成我的乡村记忆。
我的高中是在长治市太行中学,另名晋东南师专附中,同样也美。太行中学名字好听,气魄宏大,声韵感强,让我想起太行山,那里是我离乡进城的第一站。1984 年秋开学,到八一广场下车,往东经煤炭电影院,再往北捉马村方向,已近郊区,亦城亦乡的景象,正合我的审美。路两旁有高大的杨树,让我觉得人家城市里的杨树也比农村气派。柏油马路在阳光下闪亮平整,车辆来往,喇叭鸣叫,一派繁忙。那一段路成为我记忆中最早的城市印象。太行中学比老家对门的石哲中学地盘大、楼高、树多,靠东墙附近也有一片杨树林,亲切得让我想起家乡院子里的那一片。
我最早接触当代文学是在太行中学。冬天雪后,平房宿舍生煤炉,挺温暖,适合待着看小说。我借阅了好几本小说集,大概是1981、1982年左右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集,对铁凝的《哦,香雪》,何士光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都有印象。那位老人在玉米地里干活的情景,感觉非常亲切。我才知道,玉米还有包谷的别名。这是当时让我陶醉的文学作品。那时青春萌动,还有另外的读物。上英语课时偷看一种叫《多棱镜》的小报,令人脸红心跳。对女同学的感受也启动了。同桌是城里女生,声音清纯,普通话极纯正。我总是被她清晰标准柔和的说话声吸引。人家的话讲得多动听!桌上还有三八线,相互很少说话,但心里早就越线了。每天早操时,播放苏红的歌曲《小小的我》和邓丽君的《千言万语》,勾起一种特别的忧伤:“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我关注的不是最后一句,而是前四句,青春萌动的典型症状。更可笑的是,我把“那天起”理解为“那天气”,不深究,也没有和别人交流过,一直错到后来。毕业时,班里一位漂亮女生,用她的大眼睛望着我说:“师力斌,你知道吗,我还是你的半个老乡。”她给我的留言簿留言,曾跟着下放的父母在石哲读书,提到“上学路上的小桥、晨雾、鸡鸣,以及石哲中学她家门前的核桃树”。这是我高中时代难忘的一次奇遇,体验到莫名的情愫,美、害羞、朦胧……她美丽的大眼睛是我最早的启蒙。
中学时代的爱好,是一生重要的爱好。中学时代如饥似渴,不被此项占领,就被彼事迷惑,总需要什么来填充强烈的求知欲。要么旅游种地,要么画画写字,要么游泳打拳,中学教育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人陪着,把孩子引导到一项入迷的事业中来。直到现在,我的地理知识仍然很牢固,那都是初中和高中的底子。很多人犯愁的外国地名,比如山脉阿拉巴契亚、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国家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等,我都可以随口说出,不打磕巴。
文学黄金的80 年代,我在山西大学政治学系读书。山西大学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综合性百年老校,历史悠久,实力雄厚,但之前多年一直没有进入重点大学行列,在山西还不如太原理工大学,让人非常纳闷,近几年好像有所扭转。山西大学的校园仍然美丽。在那里,我第一次闻到丁香,沁人心脾。我发奋读书,各个门类的书,如手抄张贤亮的《习惯死亡》,其语言令我着迷。我热衷学生社团活动,参加学通社,结识了一大群记者校友。我还参加了学生书法社团,听过姚奠中、杨其群诸先生的书法讲授。姚先生曾经是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班的弟子,与鲁迅同门;杨先生专攻唐代诗人李贺。但那时的我仍是乱读书,乱作为,毫无章法,一事无成。大学毕业21 岁,我进入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工作,属于核工业系统,地点还在太原。
我这半生,两句话可以概括,即做人还算成功,做男人很失败。前者是说,近三十年,基本按自己的内心生活,喜欢文学,从事文学,人生大幸;后者是说,三十不立,拖家带口,无房无车无工作,实在失败。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工作以后的十年,才知道自己是典型的乡村型菜鸟。以文学为业,才是内心所向,且不断遇到文学界的贵人相助,这也促使我现在尽可能地帮助别人。1998年,改行的想法达到高潮。在单位工会和核工业神剑文学艺术学会的资助下,我自印了第一个诗歌散文小册子《心灵散步》,视为珍宝。28岁,还算年轻。同事段瑞忠是一位诗人,常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向我推荐余光中、北岛、聂鲁达等诗人,深深吸引了我。我迅速迷上了新诗,写诗在段瑞忠编的院刊《辐射防护》副刊上发表,还有一点稿费。1993年以后,我的诗作在《太原日报》连续发表,受到编辑黄海波和编辑部主任陈建祖先生的鼓励。1994 年,我参加诗刊社与《太原日报》举办的首届全国新田园诗歌大赛,获二等奖,受到李小雨等诗人老师的抬爱。在《诗刊》发表诗作后,得到了周所同老师的关注,文学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对文学的想法也日渐膨胀,萌生了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念头。2001 年,我第四次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成功。当拿到印有博雅塔的录取通知书,真想亲吻姬家岭和漳河水。去世两年的母亲老人家若是在世该有多高兴啊!母亲从小教我写毛笔字,督促我念书,寄望于我。此时,距大学毕业整整十年。我已经31 岁,但依旧信心百倍,梦想着此后新的生活,痛痛快快创作,弄出一点成绩来。
北大七年,使我脱胎换骨,终身受益。一方面,张颐武先生等许多名师传道授业,《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诸位学友共商学术,未名湖畔的师友情谊终生难忘,详情记于《我在北大的修炼》一文;另一方面,大龄已婚男的求学生活相当痛苦。在食堂打饭,厨师喊我老师。在三角地修自行车,有女生喊我师傅。我骑自行车带幼儿园的女儿出没燕园的情景,进入许多同学的记忆。高处不胜寒,高手如云,学无止境。北大求学的第一感受是不再盲目自信。高人太多,文学太大;第二感受是文学作为谋生手段,实在不宜。文学梦想是之前的黄金时代留下来的,而自己必须在市场背景下文学走低的现实中挣扎。到毕业时,我方看清了文学梦的真面目,才体会到要坐十年冷板凳,才晓得文学是一个绝对寂寞的事业,才知道“百无一用是书生”,才知道北大不培养作家是一个多么正确而无情的概念。越来越明白自己是一个领悟力迟钝的人,总要事情过后,才能认识其中奥妙。
毕业不等于结束,仅仅是个开始。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甚至是针尖对麦芒的两回事。方法上冲突,思维上冲突,时间上冲突,情感上冲突,某些方面更南辕北辙。要靠学术研究吃饭,必须在大学谋教职;而靠创作吃饭,则必须有作品,必须有时间创作。几个选项,我两不靠。学的是文学理论,从事的是文学编辑,心中喜爱的仍然是文学创作。三张皮怎么能粘到一起呢?
2008 年到《北京文学》编辑部工作后,我才看清了此前的人生道路。那是一条弯路,十年弯路。假如早十年到北大读书该是何等样子呢?哪怕早三年、五年?人生无法假设,路只能走过才知道。回顾以往38 年,学识庞杂,无一精专,一无所成,而人生已过天命之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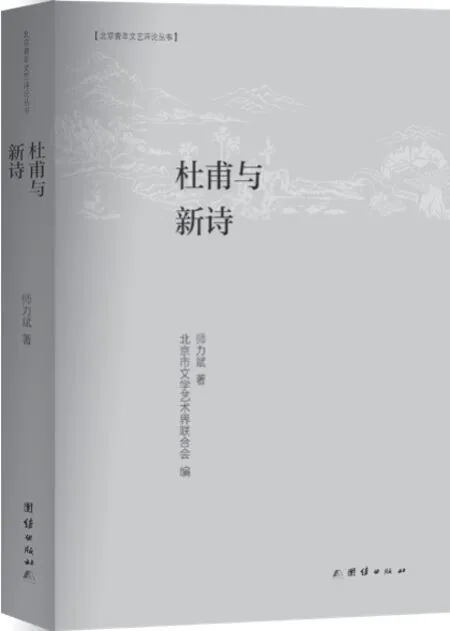
师力斌:《杜甫与新诗》
曲折乃人生本义。北大使我明白了学术之大、思想之富、自我之小,《北京文学》使我明白文学之美、之深、之古老。在《北京文学》的15 年是我在一个地方待得最长的15 年。故乡待了14 年,长治3 年、太原14 年、北大7 年。《北京文学》的15 年是我全身心服务文学事业的15 年,也是逐渐领悟人生妙理的15年。15年来,我遇见了多种风格的作家、各种写法的作品、五花八门的人生。有的作者从自然来稿相识,到他们成名成家,备感人生充实;有的我倾慕的作者已经仙逝,又觉人生如梦。跟作家打交道就是跟千百个自己的人生打交道,其间曲折进退,百感交集。幸运的是,在此又遇见了体己的领导和善良的同事。最重要的领悟是:文学是生命的结晶,值得投入,值得热爱。文学并非权宜之计、生财之道、扬名立万之物,它实在太可爱、太深奥、太有魅力,无法抵抗。
15 年来,我最意外的收获是遇见了杜甫,写了一本《杜甫与新诗》,将这位唐诗先贤与现代新诗勾连起来,踏上文学写作的新路。一开始,我仅仅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对新诗和古诗关系的一点体会,表明新诗可以而且必须学习杜甫的想法,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遂成一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这本书较为完整地阐述了我几十年来关于汉语诗歌的看法,过瘾。这本书得到了许多师友的指点、关爱和回应,他们提出修改建议,撰写评论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相关章节。该书还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的重点扶持和北京文艺评论家协会的奖励扶持。以上种种,都使我备受鼓励,鞭策我继续探讨杜甫与新诗。
回想来路,诗歌是命运对我的馈赠,来自故乡的馈赠。激动、兴奋、充实,是我投身诗歌常有的情绪,是从喝酒、看戏、刷屏、逛公园等娱乐中没有得到过的。在《北京文学》做编辑,与诗人安琪合编《北漂诗篇》,独自写作《杜甫与新诗》,种种诗歌的劳作都是如此。三十年过去了,我对诗歌的兴趣越来越浓,领悟越来越深,我在世俗世界得不到的,在诗歌这里都得到了。诗的小天地,虽然不大,足够容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