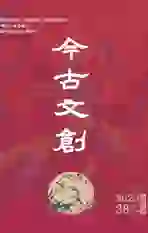本能冲动视角下的《彷徨》人物形象研究
2023-10-27夏惺怡
【摘要】本文以本能冲动为视角,将《彷徨》中的人物形象与各自的孤独气质、行走方式相沟通,分为退却、失去、挣扎、反抗、突围五种类型。依据相关心理學理论,品读人物在不同生存状态下的内心退却与异者疏离,归纳人物在本能中生成的认知偏差与失去,解码看与被看下被迫、无意、主动三种悖论式的反复推拉与挣扎,剖析莫比乌斯环叙述结构中至死不渝和以退为进的绝望抗战,浅评突围路上的独立意识、革命精神和宣战思维,从而在人物形象上丰富鲁迅小说中由孤独情结与孤独意蕴建构出的孤独体系。
【关键词】本能;孤独;《彷徨》;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8-003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8.012
基金资助:“本能冲动下的孤独世界:鲁迅《彷徨》中的人物群像研究”,校级一般项目(项目编号:S202210347058)。
《彷徨》是鲁迅向内审视和求索的小说,蕴含着“一组以孤独情感为中心内容的复合情绪”[1],其中的人物“变成某种类别化身而传达一些具体的社会诉求”[2]。汪晖认为小说创作中的孤独意识反映鲁迅的先锋性,是将“个人、个人的主观性、自由本质、反叛与选择置于思考的中心”[3]。故以“本能冲动下的孤独”为切口,探讨小说中的社会文化与孤独内在。
薛毅认为,“鲁迅的小说创作中有一个孤独者谱系:狂人——夏瑜—— N 先生——疯子——魏连殳。魏连殳形象是鲁迅对孤独者谱系的最后总结。”[4]但细读《彷徨》,会发现人物群像均有孤独气质,并受各自秉性的影响做出了不同的人生行走方式。因此,本文将孤独回归最初的“我”的构建,从内心追溯。在梳理孤独脉络时,将个人内部心理与集体中的个体并置,在解读中增加纯文本量去推究文章背后隐含的可能。
一、个体退却者与异类疏离者
小说《彷徨》中,个人和群体异类的自我退却与疏离对人物孤独精神谱系填充具有首要启发的作用。从本能冲动出发,这是个体在压抑、消极、极度渴求的状态下对先天认知的承载与发展,集中表现为在生死、自我闭塞、自卑心理影响下的退却与疏离。
首先,生死本能的冲动激化了内心欲望,使部分个体对自我、他人、社会的诉求以非理性的行动表现出来,与理想的自我、社会的认同背向而行。如封建旧知识分子四铭,反复强调孝女与光棍,“学学那个孝女罢,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将来只好像那光棍……”[5]难抑住自身对孝女的在乎,用自身的赘述企图在他人的语境领域中占有和控制孝女。在四铭太太的指责“你们男人不是骂十八九岁的女学生,就是称赞十八九岁的女讨饭……‘咯支咯支’,简直是不要脸”[6]中,可见四铭难抑性欲,精神出轨孝女不自知,拒绝承认,陷入孤立。其对性欲的渴望是弗洛伊德的生的本能的例证。魏连殳,作为一个处处碰壁的知识分子,以“自戕式”复仇,即“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7],甚至发出“但是现在忘记我罢;我现在已经‘好’了”[8]的病态诉求。他的行为蕴含着非理智的破坏性力量,体现相对的死的本能。
其次,部分个体撕裂“本我”“自我”“超我”,跌入自我闭塞的空间,走向对自我的极端拷问,使得人格统一失衡,自我向后退步。《在酒楼上》“我”与吕纬甫之间的内在对话关系呈现的即是“本我”和“自我”之间博弈引导的自我反思、自我审问与自我否定。吕反思回来的意义,“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不过绕了一点小圈子”[9],本能地归乡避免痛苦,以无聊来求得本心的舒适,在“敷敷衍衍,模模胡胡”[10]的状态上审视自己“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11],却又下意识地否定自我价值,自厌自弃;以一种约束性的“自我”活成一个局外人,即“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12]
再次,本能性自卑导致部分个体面对凝视时,内心深层生成优越,与他人保持距离,主动摆脱不安的环境。作为村中、友中“异类”,魏连殳骨子里与祖母进行绑定,认定或许会承祖母运命,在无人理解下主动逃离这种无助无望的境地,自觉不能让乡人发现自己落魄,厌弃“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13],在后期便坦然面对本能支配,“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14],以“自戕式”的“复仇”与先前志同道合者划界,成为庸众中的优越人士。子君则代表了部分的“五四”新女性在新式小家庭中的自我疏离,她在同居生活破落后,舍弃养的叭儿狗和油鸡,关系破裂后又不留一字地强硬出走,以期凸显身为家庭女性应有的立场和地位。这与阿德勒提出的“自卑感会让一个人感到焦虑,因此他就会寻找优越感来补偿自己的情绪”[15]相呼应。作为原始的决定力量或推动意志向上的基本动力,人的本能性自卑和由此导致的本能性疏离使得个体的孤独成为本能冲动下的必然,象征着作为“独异个体”的艰难生存状态。
生死本能、自我闭塞、本能性自卑使个体不论是面对自我还是他人都显著地保持了一定距离,尤其是在找寻伦理德行、苦乐共通感时,将内心直觉放大化,伴随着强烈的情绪,看似靠近“理想”却转向了退却与疏离。然而这样的退却与疏离并非全是消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不同个性特质对某种社会诉求的反馈,传达出在生死之间的某些行为语言的原动力。
二、失己者与失语者
小说中的部分人物在无意识的推动下于某些时刻生成认知偏差,或随波逐流,或丧失自我话语权,落入孤独牢笼,如以夸耀学问自欺的高老夫子、凭不切实话术寻求现实幸福的青年作者、被涓生剥夺发声权的子君、被四铭以“肥皂”贬损女性尊严的孝女和四铭太太。
把顺应潮流当归属的个体,轻视缺陷,在与世俗合流中失真、失心。打着“整理国史之义务”的旗号的高老夫子,改名换姓,发文迎合,与万瑶圃打着“X翁,久仰久仰”的恭维,却不审视自身学术;自认女学堂是为彰显虚荣,不从根源看自身思想的陈旧,却在与黄三等牌友玩牌凑成“清一色”时,觉“世风也终究好了起来”[16]。在撰写《幸福的家庭》时,青年作者以一碗龙虎斗、一部《理想之良人》为一个家庭幸福的标志,本能地对资产阶级某些生活方式残存幻想;采用中国菜作为幸福的原因不是出于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而是根据西洋人的话术“中国菜最进步、最好吃、最合于卫生”[17],忽视、抗拒、割裂其与茶米油盐现实的差距,误解世风与自身的不对等性;将笔下的A地与六株白菜堆叠成的A字含混,使自己的话语同手中的格纸沦为“用力的掷在纸篓里”[18]的纸团,不可说,不想说。这样的个体不审问自身、不丰盈自我、不明确目标,改换信仰只为扮好他人眼中的样子,面对社会的转型却急于在名利的虚无中谋求发展,对民族的不自信最终成为对自己的不自信,无形中磨平自我棱角、模糊本真面目,从而丢失自己。
丧失个体话语权的个体,以女性居多,她们身处封建旧家庭中,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涓生用男性话语权控制子君,却以启蒙者的姿态自居,认定“现在忍受着这生活压迫的苦痛,大半倒是为她”[19],在小家落魄时,用带有轻视语调的话“人是多么容易改变呵”[20],随意概括伴随他一起奋斗的子君的付出,使子君成为“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21]的孤独的话语缺席者。《肥皂》中,四铭对两块肥皂给孝女洗身的话语印象深刻,反复提及,掌握其描述权。而小说结尾处,四铭太太的“身上便总带着些似橄榄非橄榄的说不清的香味;几乎小半年,这才忽而换了样,凡有闻到的都说那可似乎是檀香”[22]。身染檀香的舍取与之前的性子对比,为她的出路创造一种可能:即对丈夫失望,出走世俗,将个人的虔诚奉献给神灵。
无意识挤压着个体的生存状态,让个体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缺失。在社会潮流中失己,选择和行为偏轨的个体逐步迟钝、异化;在封建思想中失语,被选择和支配的个体逐步失望、失落。从失己者与失语者身上看,认知的错位让本真步步遗失,归属只是短暂的依靠。
三、看与被看下的挣扎者
“在集体的心理中……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特性品质占据了上风。”[23]当独立个体陷入社会、集体的交替影响,极易在自我情感、道德等方面的独立性泯灭,迷失自我,表现为三类:
第一类人被迫加入集体,逐渐被集体同化而酿成自我命运的悲剧。他们在群体的无意识迫害下一步步逼近精神裂变,如祥林嫂。一个被他人冠以夫权色彩名称的劳动妇女,本意通过干活赢得地位,在不受重视后,受暗示本能影响,以重复讲述自身经历的方式向众人找寻归属感、安全感,却不料婚丧的被迫与无奈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自身沦为“弃在塵芥堆中、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玩物”[24]。
第二类人无意加入集体,在集体的推动下,放大自我消极因素而至沉沦。他们本是懂苦楚的不幸者,却要在观赏他人痛苦中宣泄情感,忘却自我痛苦,不死不活地存在。《示众》中的看客们,从被抱在怀里的孩童到拄着拐杖的老年人,都被注入了漠然的基因,关注的重点是看“白背心”的人的奇特,甚至当着巡警和犯人的面,出现“忽有几个人同声喝采”[25],喝彩的内容也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亦成为迫害知识分子的“刽子手”。他们的聚集日常化,无深刻目的,陷入几乎无事的本能冲动与偏执,是一种缺乏灵魂的孤独。这些于群体中的习惯性淡漠成为代代相传的本能传承,成为“沉淀于人类心灵底层的、普遍共同的人类本能和经验遗存”[26]。
第三类人在与社会、集体进行激烈地反抗后,个体信念遭到崩塌,从而再次主动回归集体,甚至近乎“归隐”。这种近乎“狂人”的群体中大多是觉醒的新知识分子,如吕纬甫,激情澎湃地参与革命,在革命失败的分岔路口,信念崩塌,在徘徊与彷徨中“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27]。
这些人在集体既定规范的无意识带领下,否定人的主体性,继而扩散和递承,在潜移默化中,对个体的自由意识进行群体既定规范的向导。他们在社会中找寻自我价值的突破口,却一次次地在集体的无意识规范导引下通向期望的对立面。这是个体在自我瓦解、自我拼凑的挣扎中的悖论。不管对集体态度是被迫、无意,还是主动,悖论的反复推拉造就了个体最终没入群体,由面对面的对话走向背对背的孤独。但这种递承和扩散可被环境改造和选择,在后世隐匿或消失。因此个体的挣扎往往烙有某个时代、某个地域的特色印记。
四、拓荒者与突围者
当小说《彷徨》的底层人物作为社会缩影,陷入相似情境的循环,挣扎等多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无意识往往推动着本能行为发起冲击,用独有方式开拓反抗。
有至死不渝式的反抗者。祥林嫂面对封建枷锁带来的精神折磨,不是自沉,而是反抗至死。在绝境中,一方面,她一次次逃脱,逃到鲁镇,逃离夫权和家长权的控制,这些逃成为她“生”的精神源泉;另一方面,她将“生”的希望寄托于鬼神,通过捐门槛自我救赎,但鲁镇风气使她通往死亡。对绝望反抗的态度赋予了孤独个体以意义,个体命运的悲剧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祥林嫂成为封建家庭影响下抗争妇女的缩影,化为后世的符号。反抗绝望的力量和个体命运的悲剧成为唤醒群体意识的钥匙。
另有以退为进式的反抗者。他们颠覆式壮举,铁血式革命,一腔热血冷然后,被迫开始自毁反抗,向内回溯。投靠旧军阀的魏连殳将部分人的仇恨、艳羡与虚荣化为自己的路,以本能的自沉“水似的化钱”[28]、不以好话为意、用物质买儿童的尊严等方式来摧毁这条道路,嘲讽社会的黑暗,用“含着冰冷的微笑”[29]打破人本能中的骄傲性,让更多人清醒地看到这头“受伤的孤狼”,清醒地退步、质疑。吕韦甫采用颓唐消沉的缄默反抗周遭一切,因回来迁空坟骗母亲安心,对孝的内涵进行重新叩问;模模糊糊地教学生“子曰诗云”,除他们父亲要求,或许希冀学生在不甚清晰的传统与转型的社会对冲中产生可能的自我个性。
孤独和绝望的反抗使个体在无尽的痛苦中超越时空限制,走向了时代的另一面,让时空扭曲成一个“莫比乌斯环”,一种扩大封闭范围的扭曲的圆形叙述。而由于本能受社会环境影响的不成熟,人物在孤独中绝望抗战未能打破此环,从而不得不实现历史性的轮回与重复,生成一种宿命。但扭曲、错位的时空,诱导本能撕扯、毁灭,开辟了巨大空间,让人生有了不一样的可能,有了引导他们找寻悲剧处境之根的动力,从而使得一大批具有不同意义的自由选择生命价值的拓荒者产生。
在拓荒者的困境反抗行为之上,部分个体在某些时刻冲破了时空困境的限制,溢发自我突破与革命:一类是有念头与勇气,却只能迈出一步或几步;一类是迈出了几步,在怀疑和惶惑萌生出新兴态势,将小范围的挣扎上升到大世界的抗争。
前者表现出独立的意识。他们拒绝不平等的合作、渴望社会文化给予认同,渴望婚姻对象给予恰如其分的合作目标,但由于时代局限性未能走远。在同居前呐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0]的子君,由于经济破落和涓生的失责,在家庭经济出现裂痕时,率先发声指出涓生“近来很两样了”[31],看到他逃避后不留一字地回家。靠着“简直抵得过一个男子”[32]的力气在鲁四老爷家做工的祥林嫂,面对被发卖的婚姻一路嚎骂,直到“喉咙已经全哑了”[33]“一头撞在香案角上”[34]。看到丈夫出轨、坚持斗争了三年的爱姑,找“七大人”评理,称若事情无法解决“就拼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35]。从“时间的标志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实践来理解和衡量”[36]来看,三人本能的时间性孤独以“家”的形式被呈现出来。祥林嫂曾不自主地步入两次婚姻,歸属感断裂后,不断从性欲和物欲中逃离。子君与涓生共建小家,忙着同甘共苦,在涓生误解她的果决、在言语中不放弃占据道德制高点后,陪涓生走过难熬的冬天后,就离开“家”的牢笼。爱姑看到丈夫出轨后,不愿受夫权控制,不断打架、控诉、分家,向外寻求帮助,不避外人对传统女性的看法。
后者在突围的路上,萌发了革命精神和宣战思维、“永远向前走”和革故鼎新的理念,打破“革新一保持一复古的历史循环”[37],用含垢忍辱的孤独本能推进着社会改造和文化变革。如《长明灯》的疯子于本能中不信禁忌,一心灭灯,“我知道的,熄了也还在”[38],并牢牢把持住多数认可的“不祥”、寥寥肯定的“真理”,认定“我就要吹熄他,自己熄!”[39]他表面上向空间意义上的村民宣战,实则向时间意义上村民精神内核中依赖的虚无寄托和侥幸心理宣战。他近乎入魔般跳脱、颠覆,将“放火”告诉孩童,流传“我放火!哈哈哈!”[40]的歌谣,生出对全村更顽强、更有韧性的不被认可的战斗精神及摧毁带有腐朽气息和无实质内涵的古物的质变思维。非正常心理表现出一种遗传的本能骄傲与不把任何后果放在眼里的执着、不羁,更迸发出了孤傲的风骨、孤寂的忧患意识。
拓荒者和突围者在本能冲动下总体展现出个性进步的一面。他们的孤独是虽败犹荣或清醒迈步,是面对带有挑战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的大胆与狂傲。“我”之为“我”,不被拘束,独立平等,自在自为。拓荒者和突围者虽命运坎坷,但在某种气质上却愈发立体、坚韧。
五、结语
显然,就本能性孤独,小说《彷徨》中的人物形象可归为退却、失去、挣扎、反抗、突围五类,并构建衍生出“我”的存在与发展、孤独精神的游弋与对撞。根据马大康《行为语言·无意识结构·文学活动》中本能依附于行为语言、行为语言非对象化、人的个性即行为语言的思想,本能视角让《彷徨》中的人物形象向深层意识追溯,通过追溯此意识引导的行动(行为语言)来表达人物特殊的个性,同时简化了人物行为的复杂性,使小说叙述更为整体,从而使“我”更加丰富与深刻。而孤独作为人精神建构的某一面,不仅是某种本能的外显、生命欲望的原点,是《彷徨》人物的气质、行动、命运的相生相伴,还是鲁迅创作心理的冷峻外延,是现代思维引起警戒、打破限定的治愈力量。故本能视角对于感受人物形象特征的共性规律、承载小说孤独内涵的疗救作用而言,有重要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敖行维.试论鲁迅的孤独情结[J].贵州社会科学,1996,(05):48-53.
[2]阎晶明.孤独者的命运吟唱——鲁迅小说里的孤独精神[J].名作欣赏(鉴赏版),2011,(07):27-32.
[3][37]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27,134.
[4]薛毅,钱理群.《孤独者》细读[J].鲁迅研究月刊,1994,(07).
[5][6][7][8][9][10][11][12][13][14][16][17][18][19][20][21][22][24][25][27][28][29][30][31][32][33][34][35][38][39][40]鲁迅.彷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48,50,100,101,23,25,25,29,97,100,82,34,39,120,119,120,53,6,71,30,106,107,112,123,7,10,10,151,60,60,65.
[15](奥)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自卑与超越[M].徐珊译.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6:44.
[23](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亦言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9:20.
[26](瑞士)荣格.荣格性格哲学[M].李德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3.
[36](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3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75.
作者简介:
夏惺怡,女,汉族,浙江舟山人,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2020级本科,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指导教师:杜瑞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