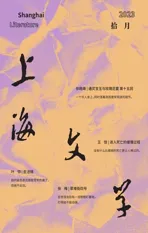草堆街四号
2023-09-20张梅
张 梅
冯老爷在草堆街是赫赫有名的。
草堆街在澳门也是赫赫有名的,它位于半岛中部,西启十月初五日街,东至大三巴街口紧邻卖草地街,长三百二十米,历来被视作当地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与十月初五日街、营地大街、新马路一道组成了澳门最为兴盛热闹的商业街区。
光绪八年。
连续几天早上,人们都看见穿着寿衣的冯老爷在草堆街来来回回地走着,低着头,专注地用脚量着尺寸。所有的人都被吓坏了,赶紧闭了店门,从门板的隙缝里露出一只只惊恐的眼睛,看到他边走边数着地上那些从葡萄牙运来的彩色石头,嘴里念念有词:“三百二十二,三百二十三,三百二十四……”冯老爷对脚下的黑布鞋特别不满意,像他这样有身份的人,平时穿的皮鞋都是从里斯本订制的。当家里人哭哭啼啼地把他放进棺材的时候,他愤怒地想抬起脚去踢他那个躲在棺木后面披麻戴孝一脸茫然的儿子。“一饭咁!居然让我穿着农民的鞋子入土。他们不知道我是在澳门第一个有资格葬进西洋坟场的绅士吗?”
这场葬礼声势浩大,澳门总督亲自为他担幡抬水,几个洋人亲自为他扶棺。草堆街两旁站满了观礼的市民,他满意地在棺材里面哼哼。

他的灵魂早已飞在草堆街上空游荡,他恋恋不舍地注视着白马行街一号,也就是他的大宅。这座大宅是他发家之后,从王禄手中买下的。连丁围数幢旧宅,拆建成一座类似广州西关大屋的唐楼院落,时人称为“冯家大宅”。设计师是葡萄牙人,为了让他对唐楼有感觉,冯老爷请他在省城广州的西关一带连住了三个月。那个葡萄牙人很爱吃鱼翅,他在当地觅得一家专做鱼翅的饭店,并且用各种借口拖延回澳门。
白马行街古称医院街,西接板樟堂街,东至水坑尾街,是澳门第一条水泥马路。由于其东端有一所圣辣非(H.S.B.)医院,故起初称为医院街。那时,路面还是传统的石子路,水泥路建好后,以冯老爷为首的华人认为“医院街”这个名称不吉利,刚好此街道上的渣甸洋行专营一种叫“白马行牌”的威士忌,还在洋行的门口竖起一面画着白马的旗子,于是居民把街更名为“白马行街”。一八六九年七月,官方正式宣布此街为白马行街。其后到一九四二年,议事公局为纪念曾任局长的伯多禄(Pedro Nolasco da Silva)诞辰一百周年,将街名更为伯多禄局长街。当然,卖酒洋行也搬离了,街上再也没有了那面白马旗子。旗子撤的当天,居民的心里一下子空空荡荡,他们已经习惯了白马在澳门的蓝天下飞驰。第二天,又有人把旗子挂了上去,旗子上面画了一条巨型石斑鱼,又称“龙趸” ,这条青色的龙趸,配有红色的胡须。
冯凤韶出生在广东南海沙头。沙头是一个富裕的地方,是所有爱吃鱼生者的天堂。百年间潮起潮落,但沙头公社第一招待所仍然是全世界“鱼生迷”渴望朝拜的圣地。
沙头河涌遍布,桑基鱼塘。冯老爷小的时候,就亲眼看到过“鱼生迷”们各种颠倒众生的怪异举动。每年八九月间,秋风既起,菊花上市,这些人不动声色地从四面八方涌来。当白花花的生鱼片摆上桌的时候,一声号令,装着炒花生、柠檬叶丝、切成薄片的酸荞头、蒜片和姜丝,还有炸香白芝麻、油炸鬼薄脆、花生油,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色佐品纷纷上桌,老饕们眼露精光,嘴角流着口水。他甚至见过这样的场面:人们在生鱼片前跪下,顶礼膜拜,用普洱茶来净手,然后再往身上洒柠檬水,口中称念,最后将生鱼片拨进自己面前的碟子中。路途近的,就立马大饱口福,喝了当地产的九江米酒,唱着咸水歌坐着龙头船趁着明晃晃的月色回家:“月光光,照地堂,年三十晚,食槟榔。槟榔香,食子姜……”路途远的,就等把晚餐的鱼生消化了,再进行另外一场鱼的盛宴。鱼生要做得好,讲究的是肉质细腻且血放得干净。晚清词人汪兆铨云:“冬至鱼生处处同,鲜鱼脔切玉玲珑。一杯热酒聊消冷,犹是前朝食鲙风。”
南海位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当时中国有两样西方列强垂涎的宝贝,一是茶叶,二是蚕丝。南海一带当年就是靠出口蚕丝兴旺发达起来的。冯凤韶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叔伯兄弟担着一卷卷蚕丝去澳门跑码头。他年纪小,皮肤黑,眼睛小,常常在脸上找不到他的眼睛,所以经常给人嘲笑他是“一云”(粤语,意为糊涂),或者是“一饭”(粤语,意为蠢蛋)。
冯老爷停留在草堆街四号上空,久久不愿意离开。这是他第一次开番摊档的地方,也是他淘得第一桶金的地方。番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赌场。那时的番摊档很简陋,草棚一样的东西。用“东西”形容是最准确的,就是一张桌子,桌上有几颗肮脏的骰子。人就围在桌子旁很激动地喊着,一看就是下等人,从草堆街的码头搬完东西就来到这里搏杀。那天,他刚刚跟随父亲在码头把蚕丝放下,父亲看看天色,说今晚要在澳门住了,赶不回去了。这时,他们走过一间番摊档,父亲一脸不屑地对他说:“千万不要像他们,这些衰神都想着不劳而获,而且肯定失败。”他听了没有反驳,一双小眼睛在黑皮肤里闪了开来,亮晶晶的,像澳门夜空的两颗星星。很快他就开了第一间番摊档,发了疯地想挣钱。他看见在草堆街码头下船的葡国先生和太太亲热地挽着手,身上都香喷喷的,冯凤韶也想自己的身上香喷喷的。
他的身体也迅速地成长,天空伸出一只手把他拔起来,肩膀也宽了许多。他的一个拍档陈六有葡国血统,他穿上陈六的西装,靓得不得了,陈六就把西装送给了他。“一云咁”,其实冯凤韶喜欢得不得了,但嘴上还要表示些什么。
几个合伙人趁着年轻,勇往直前。只是冯凤韶自己,就在草堆街有四间番摊档。他早年因往返澳门做丝茶生意而接触天主教,定居澳门后加入了葡籍也信了教,教名为方济各·沙勿略。很快就有人叫他“大佬”了,“大佬”就意味着冯先生可以穿着木屐迈着八字在草堆街横行。
冯老爷的突然离世好像和那条龙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澳门这个地方,做刺身基本用的都是龙虾或者象拔蚌之类的海产,因为没有河,所以也没有河鱼做鱼生。
这天,冯老爷醒来,突然十分想念家乡的鱼生,想起白花花的生鱼片配着柠檬丝、酸荞头、花生油的美味,突然觉得今天如果不吃一碟就了无生趣。在这个念头的驱使下,他穿起木屐,心事重重地走到十月初五日街头的六国饭店。在那里他看到一条刚刚打捞上来的巨型石斑鱼。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石斑鱼,它躺在那里,心有不甘地闭上眼睛,这鱼比他人还长。石斑鱼身上是青色的,闪闪发光,它刚刚饶有兴致地游走在五彩缤纷的珊瑚间,转眼间成了刀俎上的肉。冯老爷马上把它买下,不让饭店按常规的做法——用冬菜蒸,而是吩咐他们做生鱼片,既而满怀兴奋地坐进包间。他甚至没有叫任何人来一起享用。这个中午,他想独自把这条巨大的石斑鱼吃进肚子里。
过了很久,饭店的人都认为冯老爷应该把这条鱼吃完了,但也没有看见他出来。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敲门,再进去,看到冯老爷坐在圆桌旁,桌子上白花花的生鱼片已经一扫而光。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身体已经僵硬了。
子时刚过,有越来越多的人趁着黑夜走向草堆街四号。清一色的青壮年,长褂子,长辫子。冯老爷的灵柩要在那里停十天。所有人都听说在草堆街四号的地底下藏着冯老爷巨大的宝藏。
季如踏进白马行街一号冯家大宅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命运了。她不仅是一部被期待的生育机器,而且还要担负为老爷冲喜的重担。她进门没几天,已经病入膏肓的老爷就驾鹤西去了。“头七”那天,她居然还在花园里见过冯老爷,季如并没有害怕,上前问好。冯老爷对她竖起大姆指,再指了指他脚下的鞋子。不久,她就怀孕了。冯少爷对太太是百依百顺,对季如也是彬彬有礼,脾气出奇地好。季如也争气,随着肚子越来越大,冯家上上下下喜气洋洋,对季如、连如两姐妹也更加热络起来。冯家的房子在白马行街,中西合壁的建筑,大门是中式的,黑漆金扣,非常厚重。三进的房子,一进是老爷的书房、客厅和卧室,二进是两位少爷和一位小姐的房间,三进有两层楼,楼下是佣人的宿舍,二楼则是客房。开始,两姐妹都住在三进的客房里,季如的肚子大了,就搬到二进的院子里去了,连如还是在客房里住着。除了陪伴姐姐,连如经常和佣人们打闹在一起。不久,姐姐就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九斤儿子,把冯家奶奶高兴坏了,给了季如好几样贵重的首饰,也给连如置了几件新衣裳。连如趁着大奶奶高兴,就提出了重新上学堂的要求。大奶奶正抱着孙子,嘴角都咧到耳朵旁了,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连如吓得都快哭出来了,但还是下定决心地说:“我要上学。”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天上正好飞过一群麻雀,灰溜溜的,突然就齐齐整整地停在了二楼的屋榉上。大奶奶抬头看看那群整齐的麻雀,自言自语地说:“麻雀要变凤凰了。”
连如突然鼓起勇气,也不管姐姐在旁边哀求的眼神,大声地背诵起李清照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偌大的冯宅一下子安静下来,这种寂静像乌云一般笼罩着四周,挽着少奶奶的手臂正准备上茶楼喝茶的冯家少爷也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茫然地看着连如。
赵连如这时十三四岁的光景,样子其实是蛮漂亮的,但总是透着一股男孩子气,愣头愣脑,不像姐姐季如那样秀气。
从后院走进来一个中年人,是冯家长期的食客,基本就躲在房间里,不大出来,经常是佣人把饭拿进去,他就把吃完的碗筷放到门口, 由佣人收拾。连如问过送饭的佣人,那里住了什么人?他们都摇头,只说是老爷的客人。有一天,连如壮着胆子,轻手轻脚地趴在那人的房门上往缝里看,看到那人正埋头写书。哦,连如心想,原来是个写书的先生。老爷竟然白白养着一个书生,她心里不由得钦佩起来。
那天晚上,少女赵连如睡在散发着松木香味的床上,听到了黑夜中来自各处的声音。各种喃喃细语从不同的方向传进来,她居然听到了在大三巴的方向,舢板停靠在沙滩上的声音,船上有个皮肤黝黑的少年,少年也在喃喃细语。她很想听清他在说什么,终于在细语和黑暗中沉沉入睡。入睡之前,她记起了那个埋头写作的书生的脸。
当连如大声呤诵李易安的诗时,那个相貌丑陋的食客兼书生从后院走了进来,对着所有人说:“她应该去读书。”话音刚落,门口走进两个少年,一男一女,年纪相仿,后来连如才知道,这是一对姐弟,姐姐叫碧玉,弟弟叫雪秋,都是连如姐夫的堂姐弟,家住香山,经常来往。姐弟俩都有黑葡萄般的眼珠,特别是弟弟,长得像“番鬼仔”。
姐姐拍着手说:“好啊,好啊,我最钟意女仔读书了。这样我上学也有个伴。”她一溜烟跑到连如身边,拍着她的肩膀亲热地说:“就上我去的那家培基学校。那是澳门最好的学校。”
冯大奶奶皱起眉头喝斥她:“你收声,细路仔唔识野!”
碧玉垂下眼睛,不再说话。
冯大奶奶把手上的孙子交给佣人。“无规距。”她扔下一句话,扬长而去。
赵连如看着这个开朗阳光的少女,一缕阳光也照进了她的心里。
过了几天,季如生的儿子一百天,这是个喜庆的日子了。按照澳门、香山一带的风俗,这天是一定要大摆宴席,食烧猪的。
冯大奶奶原来准备是在十月初五日街头的六国饭店摆酒,这是当地最好的饭店。但她又想在家里摆,不去酒楼,因为她自己想看戏。为了这件事情她纠结了,于是把少奶奶和季如都叫到自己的房间商量。
大奶奶说:“六国饭店的烧猪做得最好。”少奶奶说:“甜点一定要上葡挞,还有主食就食猪仔包。”季如低声说:“甜点可以加一道黑糯米芒果布丁。”大奶奶手中折着糖纸,她有个喜好,就是把各种各样的糖纸折成元宝,给妹妹送到庙里,或者叫连如送到澳门的小庙。
大奶奶放下手中五颜六色的元宝,瞪大眼睛看着两人:“你们真的不知道我想什么吗?”少奶奶笑起来,说:“当然知道你就是想看戏。”三个人都笑了起来。大奶奶拿起桌上摆的糖莲子,叫她们:“吃一点,吃一点。”季如拿了一颗放进嘴巴里。大奶奶又说:“你们的死鬼老爷最钟意睇大戏了。听到我们要请戏班,估计要从棺材里爬出来看了。”季如想起老爷“头七”在花园里见到他,忍不住说:“‘头七’个日我在花园里见到过老爷。”两个奶奶一起好奇地问:“真的吗?他有说什么?”季如摇摇头,说:“没有,他只是指了指脚,不知是什么意思。”大奶奶一下子好像醒悟过来:“指着脚?”她想了一会儿,说:“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哎呀!”她一下子就把六国饭店忘记了,大声叫着儿子:“亚仔,亚仔,你爸爸最钟意的个对皮鞋呢?”一边叫一边开门出去。少爷已经站在门口,愕然地说:“早就烧给他啦。”
几个人一下子安静下来,只听到门外有人卖糖水的声音:“绿豆沙,绿豆沙!好靓陈皮臭草绿豆沙……”
冯家准备请当时在粤、港、澳三地都十分红火的“扎脚胜”来演粤剧《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扎脚胜”姓林,是广东新会双水楼墎乡人。扎脚(即缠足,四邑人称为“扎脚”)就是把两足的脚跟用薄板夹附于小腿上,用缠带捆扎紧固,动作时只用脚尖站地,类似今天的芭蕾舞。
“扎脚胜”演出前,连如和冯家的佣人一起在天井摆好给客人看戏时坐的小凳子和小桌子,摆上茶点水果。今天的茶是英式红茶,水果是荔枝,刚从东莞运过来的,叶子和枝干都是绿的。荔枝这种水果十分娇贵,一定要吃当天摘的,不然有“一夜干,两夜黑,三夜烂”之说。除了荔枝,还有大马运过来的榴莲和泰国的芒果。这两种水果连如从来没有吃过。每桌还配有一小束新鲜的茉莉花,散发着清香。连如忙着每桌派水果,很快把读书未成的不快淡忘了。
客人陆陆续续到齐,吃水果,喝茶,寒喧。
突然锣鼓喧天。锣鼓声中,一个大老倌背上插着八面锦旗,头戴着色彩鲜艳的雉尾,身上穿着百折战裙,在“策马”“趟马”“走圆台”时露出“三寸金莲”,踮起脚在戏台上不断地旋转,一时战裙飘飘,令人眼花缭乱。
所有台下的人都站立起来,鼓掌、喝采声不绝于耳。
“太美丽了。”一位被冯大奶奶请来的葡萄牙太太眼含热泪说。她是冯大奶奶的教友,住在东望洋山上,东南亚风味的房子有着面朝大海的宽大门廊。她兴奋地叫住连如,拿起一束准备好的鲜花交给她:“你替我到后台送给台上的这位先生。”
连如看看冯大奶奶。她点了点头。
连如恭恭敬敬地捧着鲜花,走到戏班的后台。她拨开帘子走进去,看到所有人都在紧张地化妆,描眉的描眉,打粉的打粉。每张脸都是一样的。她很茫然,不知哪位才是刚才在台上大放光彩的大老倌。她很想问,但看到所有人都在忙,没有人顾得上搭理她。她捧着鲜花,闻到玫瑰和百合发出的幽香,一时有点恍惚。身后传来一声娇嘀嘀的声音:“亚姐,我们又见面了。”
连如转过身去,看到一张和其他人一样画得红红绿绿的脸,身上穿着一件看上去有点脏的戏服。连如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她。这时,有人探头进来,大声地叫:“佩儿,佩儿,到你了。”
女孩子转过身去,走了两步,又转回头,调皮地眨了眨眼睛。
就这样,连如见了佩儿第二面。
连如读书的事情,少爷和少奶奶都帮她说话。少爷说:“读书是所有人的权利。”冯大奶奶只听儿子的,这样,连如就如愿进了澳门培基学校。这所学校有学生一百多人,是港澳两地唯一获得清政府核准立案的学校。连如冰雪聪明,成绩常为年级之冠,多次享受全免学费之优。
一九〇五年的夏天,刚刚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澳门的街头还是很凉快的。雨水冲洗过的石板路干干净净,碧玉和赵连如手拉着手,小心地走在路上。两边的铺子刚刚开张,她们一边走一边听到木板被抽起来的声音。一听到这种声音,她们就知道店铺要开门了。她们正在走的这条街是碧玉家里的,用连如母亲的话来说“好架势”,就是说,很有势力的意思。那时的冯家还真的“好架势”,冯凤韶把钱财捐出来,建了一间镜湖医院,这是澳门第一间平民医院。
冯碧玉是连如姐夫的堂妹,老家在香山石岐,在澳门也有产业,她父亲新派,就把儿女送到澳门读书,间中回石岐。每次回来,都带烧好的石岐乳鸽给堂哥吃。她比雪秋大两岁,生性活泼,性格刚烈,是雪秋的主心骨。那时还没有女校,培基学校还是男女同校,赵连如和比她大两岁的碧玉、同年的雪秋就同是校友。
此时,同盟会刚刚在日本成立,香港很快就发展为同盟会的重要据点之一。而在澳门,康、梁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政治主张尚占统治地位,培基学校的老师多半也信服康、梁的学说。学校每逢星期六下午都要举行演说会,开始是一些学术性质的讲演辩论,后来逐渐由性善性恶之争,又发展为尊孔反孔之争。连如和碧玉都是参与演说辩论的积极分子,她们还组织了一个“非儒会”,后来发展到十几人。与另一派主张尊孔的同学展开论战。
某个星期六下午,赵连如正在和“非儒会”的几个同学在一起讨论一会儿就要展开的辩论会,看到冯碧玉站在课室门口向她招手。连如走到门口,看到碧玉眼波流动,两颊绯红,神秘地伏在她的耳旁小声说,我明天就要去香港了。连如没反应过来,问,回香山吗?碧玉脸色一沉说,没听见我说的话吗?去香港。赵连如问她,到香港做什么?她也不答,转身就走。她的背影在一条柱子后面一闪就消失了。赵连如惆怅地站在门口,突然想起故乡那片长满荷花的池塘,也快到中秋节了,这是莲藕最肥的时候。
她刚想走进课室,雪秋就急急忙忙地走过来,问:“见到我姐了吗?”连如说,看到了,她说要去香港。雪秋急忙问她说了去香港做什么没有,连如摇摇头。雪秋那时也是“非儒会”的积极分子,口才了得,样貌英俊,好多女生都暗恋他。
雪秋急急忙忙地说:“出大事了。”
连如大声问:“出什么事了?”
雪秋顿足道:“一言半语也说不清。她回不了家了。”说罢一阵风似的走了。
连如住的这个客房,二楼的走廊是相通的,平时过道摆了些海棠、米仔兰之类的盆栽。这时,姐姐季如已经怀上二胎,连如除了上学读书,就帮母亲做些家里的杂活,或者是陪伴姐姐。少爷平时也很少过来季如的房间,老是和少奶奶去各式的茶楼或者教堂,但还是常带回些点心,叫佣人送到姐姐的房间。少奶奶有葡国人的血统,鼻梁很高,黑发,眼窝很深。时间长了,连如也是慢慢对她有所了解。少奶奶虽然傲慢,却没有一点小女子之气,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比连如走得还快。她将季如生的孩子视如己出,呵护有加,也经常送些时髦的首饰给她们姐妹,对连如的母亲也非常客气。冯家上下都说少奶奶好,虽然没有孩子,但人人都很尊敬她。连如觉得自己来到这个家里,简直是上辈子修了不知多大的福。
到了晚上,连如帮姐姐洗好了身子,铺好了床,自己拿本书看着,等姐姐睡着了,就吹熄了油灯,轻手轻脚走出房间,在走廊上看风景。有时就看见那个埋头疾书的人的灯光。连如就想,老爷对他那么好,也不知他在写什么大作。连如有时候会在走廊上待很久,看着远处的海面上太阳落下去,再看月亮升起来。
这天她下了课,一溜烟地跑进姐姐的房间,就看见大奶奶、少爷和少奶奶都在房间里,正脸色沉重地说着什么。看见她进来,大奶奶就问:“你见到碧玉了?”
连如吞吞吐吐地,大奶奶就不耐烦地问:“快说,急死人了。”连如知道大家都知道她和碧玉好,只好说,她是见我了,说是要去香港,但没说为什么。
少奶奶快人快语地说:“她偷偷把家里的地契卖了,拿着钱去戏班赎了个戏子,一齐跑到香港。”
少爷着急地说:“现在石岐的人都过来澳门了,要抓她回去浸猪笼呢。”少爷着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连如就说:“那她都去香港了,来澳门也找不到她呀。”
少爷说:“她来澳门读书,是托我们照看的。你说出了这种事情,怎么交代?”
大奶奶盯着连如:“她就没有跟你漏过一句?”
连如突然口干舌燥:“真的没有。”
有过这么几次,在下午没课的时候,碧玉都拉着连如说要去听戏。但连如不喜欢听戏,她一听到粤剧的锣鼓声心里就烦。“声音又大,又急。”她对碧玉说。但碧玉只要一看到那些穿红着绿、环佩叮当的主角上场,就兴奋得两眼放光。“哎,你真是乡下人。”她毫不掩饰对连如的嫌弃。这是她对连如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但连如是不服气的,因为在家乡,每到冬至的时候,地主陈四眼都要请上九台大戏给所有的乡亲看,就在收割后的稻田搭上戏台。通常陈家都是请九个戏班,先是把庙里的神仙请出来,八抬大挢抬着罩着红布的龙王爷在乡里游走一番,然后大摆宴席,请乡亲吃“龙王饭”,一摆就是几十桌。戏种很丰富,有粤剧,有潮剧,也有木偶戏。经常是看木偶戏的人最少,但还是每年都请。陈四眼说,龙王爱看木偶戏。连如也爱看木偶戏。有一年冬至,一台木偶戏就连如一个人傻呆呆地看着,虽然说是龙王爱看,但因为看的人少,戏台也没搭在田上,就搭在街角的拐弯处。远远听到稻野上锣鼓喧天,听到小孩子们打闹的尖叫声,甚至还有人燃放烟火。她是喜欢看烟火的,忍不住回头去看。她心里痒痒的,但总觉得身后有一双眼睛盯着她,盯得她动弹不能。转过头去看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连如就想,这大概是龙王的眼睛吧。
但是碧玉就不一样,她爱戏爱得不得了,说自己在香山的时候,就是全靠去看戏打发日子。她还曾想过去戏班学戏,给家里管住了。所以听到碧玉拿了家里的田契去赎了戏子一同去了香港时,连如马上就想到肯定是佩儿。当时佩儿跟着“人寿年班”戏班住在福隆新街内巷。有时下了课,碧玉就拉她到那里去,没让她进去,只是让她站在街口等。她说要到里面的一间饼铺拿包杏仁饼。连如当时忧心忡忡地站在街口等她,每每有男人经过,用不怀好意的眼光打量她,她就愤怒地大声咳嗽。好半天碧玉才出来,也不听埋怨,拽着她就走。连如依稀听过她说佩儿身世悲凉但戏唱得有多好,连如当时没有在意,因为只要听到“唱戏”这两个字,她就听到锣鼓喧天,精神注意力都没法集中,只想逃避。于是少奶奶问连如的时候,她就一直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发出“啊啊”的声音。她看到少奶奶疑惑地看着自己,感到非常地惭愧。
窗外下起雨来。从姐姐房间可以看到楼下院子里的芭蕉叶在雨水的洗涤下碧绿碧绿的,散发着勃勃生机。三年抱俩之后,姐姐又怀上第三胎了。第二胎生的是个女儿,冯家上下都喜不自胜,少奶奶还送了一对足金的镯子给小千金。大奶奶已经放出话来,如果第三胎是个儿子,那就给季如一家在珠海置房置地,让亲家后半生收收租子过清闲日子。
看着姐姐母凭子贵,连如也由衷地高兴,她越来越喜欢这家人了。一会儿雪秋哥也来了,大家就在商量碧玉去哪儿了。少奶奶说,会不会躲在哪个庙里了?但香港也没有什么名寺,都是一些敬龙王敬猫的小庙,住持也不会留她们俩这样的人。雪秋哥想了想,说,姐姐可能去了省城。其实连如早就想到了,碧玉应该是去了广州。
冯碧玉曾经跟连如讲过,她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在香港的富贵人家,认识了革命党人后,结婚并把自己的家产都卖了,双双去了日本留学搞革命。碧玉说,那样的生活才有意思。当时香港有一间“实践女校”,里面全是像佩儿这样的女性,逃婚的,从良的,只是冯碧玉这样的清白女子,连婚都没订,不知为什么对妇女解放一事如此着迷。她曾对连如说,我是不愿意结婚的,你看看你姐姐,不就是生育机器嘛。连如给她说得脸红耳赤,不知道怎么回答她。她心里倒不是这样认为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要是叫姐姐去闹革命,连如都觉得是个笑话了。碧玉在广州认识一个姓宋的女子,在广州的一家学堂里当刺绣老师。那个学堂也有点像香港的那家实践女校。碧玉好像在香港并不认识什么人,她肯定是去广州投靠了这个姓宋的女教师。
大奶奶还是吩咐众人在家附近的山头寻找一番。附近有座牛头山,山的样子长得真的像牛头一样,左右两块突出的石头在远处的海面上看过去,就如牛角一般,加上海边石头的颜色都是乌黑乌黑的,远处看过去,那些低矮的灌木好像是贴了一层黑色的短毛。正值酷暑,连如和雪秋一身汗淋淋地站在一棵巨大的橄榄树下,阳光从树枝中照射下来。雪秋觉得很累,看看连如,连如正仰着头兴致勃勃地看着树上。雪秋心乱如麻地问她:“你在看什么呢?碧玉也不会在树上啊。”
这时他们已经在山上找了几个小时,雪秋感觉自己都要迷路了。日光依旧猛烈,他心里安静下来,还好,他们上山的时候早。其实他当时并不主张到山上找姐姐,姐姐并没有到这座山上,他和连如都感觉到碧玉肯定是到了广州或者香港。但大奶奶很奇怪,就是坚定地认为碧玉是躲到这座山上去了。他们早上在家里吃了点简单的早餐就出来了,现在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
连如问他:“你饿吗?”他点点头。
山下面的海滩,白玉一样的沙子尽头有一湾湛蓝湛蓝的海水。海水在他的注视下,居然呈现出彩虹一样的色调。他都看呆了。这时,他听到隐隐约约、时断时续的歌声。
“好像有人唱歌?”
俩人互看了一眼,马上手拉着手往有歌声传出的地方跑去。但是没跑几步,他们就被一排锋利的栅栏挡住。那些栅栏很粗糙,高低不一,上面还缠着铁丝。俩人往里看,看到不远处有几间土墙筑的黄色房子,墙上有一个大大的记号。“麻风院?”冯雪秋小声道,他是学医的。这时他们看到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女人从房子里走出来,穿着一件黑色的香云纱的裙子,但肩膀处已经有了几个破洞。那个女人也看见他们了,毫不犹豫地向他们走来。雪秋第一个念头就是往回跑,但自己的手却被连如紧紧地拉住。
女人慢慢地走近他们,在离栅栏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住了,用非常平静的眼光看着他们。连如看到她有一张天使一样的脸。
连如大胆地说:“我们在找一个人,是我们的亲戚,一个女孩子。”
美丽的麻风女笑了一笑,说:“你们找错地方了吧?”
下山的时候两个人都有点心不在焉。连如被脚下的野草绊了几下,差点就滚下山了,幸亏给雪秋拉住。盛夏时节,两个人都穿着短袖的衣服,连如还穿着校服,胳膊都给划出了道道红色的伤痕,幸亏还没有出血。俩人惊魂未定地坐在一棵岗稔树下,树上结满了饱满的紫色果实。雪秋摘了一颗放在嘴里,二人默默地看着前方湛蓝的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