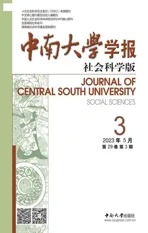以情为本:《大学》“絜矩”之儒家治道
2023-08-07宁静贤于述胜
宁静贤,于述胜
以情为本:《大学》“絜矩”之儒家治道
宁静贤,于述胜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大学》“絜矩”之道是在审慎而周密的度量中形成并持守治国、平天下的法度。本质上,“絜矩”之道乃情感体证之学。其基本精神,是强调治国之人要以自身的真实好恶为基本出发点,通过一己之情与家人、国人、天下人之情的相通相合,生成修己治人的理性行为法则,并以此理性法则感化百姓、推施政教。“絜矩”之道下的治道由此获得了纯粹的主体自由性、公正性与平等性。这一理论指出了政治治理的根本所在,并能与西方技术性思维下的治道两相补足,为现代政治治理提供反思与补益之法。
《大学》;“絜矩”;情感;好恶之情;通情;感化;儒家治道
“絜矩”乃《大学》独有的理论话语,其思想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治道精神。本质上,“絜矩”之道乃情感体证之学[1](21),而非技术层面的治政之学。但自古以来,以技术性思维解说“絜矩”之道者层出不穷。如朱熹便裂上行下效之化与“絜矩”之道为二,认为“絜矩”之道重于政术,是“就政事上言”[2](556),是“只言措置之理”[2](562),是“处置功用处”[2](557),将其思想意图指向为百姓提供维持生存的制度、政策保障,即“授之以可以尽孝弟慈之具”[3](341);王夫之在朱熹之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絜矩”之道的技术性特点,直指“絜矩”之道乃“有规矩制度,使各守其分”[3](340),即运用规矩制度规范百姓言行。近代以来,受西方政治伦理影响,这一诠释思路更加流行,晚清思想界即普遍将“絜矩”之道与西方权利之说相比附[4](22)。虽然技术手段在政治治理中同样不可或缺,但其并非“絜矩”之道的确切解释,以技术性思维作解是对“絜矩”之道莫大的误解。本文从《大学》的文本出发,试图说明“絜矩”之道的基本内涵是以情为本的儒家治道,在此基础上揭示“絜矩”之道的政治智慧。
《大学》末章中有两段话,为我们弄清“絜矩”之道的根本内涵提供了线索。其一是“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其二是“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第一段主要讲的是为何要有“絜矩”之道,第二段讲的是如何行使“絜矩”之道,而其中的“老老”“长长”“恤孤”“所恶”等语,都突出地表明,“絜矩”之道的产生和施行均与一“情”字密切相关。以下笔者的论述,将以《大学》尤其是其末章为基础,同时参之以先秦儒家典籍。
一、好恶之情:“絜矩”之道政治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大学》末章用六个“所恶”句阐发“絜矩”之道的作用机制,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其一,“絜矩”之道以好恶之情为论述对象。句中虽只明确提到“恶”这一情感,但人对有关对象的情感态度非好即恶。尤其在道德情感层面,“所好”与“所恶”具有直接而明确的关联性,故只言“所恶”而“所好”已含于其中。在下文对“絜矩”之道的申述中,便处处不离好恶之情,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爱即好);“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其二,“所恶”即我之所恶,表明“絜矩”之道是以我之所恶而非他人之所恶为主体的。其三,本“所恶”之情而“毋施”,暗示主体的行动是基于其真实的好恶展开的,中间没有丝毫截留或违逆。如此为文,意在提示治国者要以自身真实的好恶之情作为开展政治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何为好恶之情?与通常情况下杂糅着认知、情感与意向笼统谈论好恶之情的情况不同,儒者尤其是先秦儒者所言“好恶之情”,首先指向自然而尚未对象化的原发之情,如孟子所谓“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不忍人之心即是,它在物感我应的过程中自然生成,具有“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性质。“好”与“恶”乃原发之情的两种基本形态,具体而言即人在与外物发生感应之时所产生的或迎(亲近)、或拒(拒斥)的 直接心理反应,故《礼运》以“心之大端”(《礼记·礼运》①)状之。贯穿《大学》始终的好恶之情皆以此为指向。如“物格而后知至”即谓物我 感应而生好恶之情,故章太炎以“外有所触,内有所受”[5](48)为释,意谓好恶之情(“知”)乃 主体的直接心理感受;“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见好色自然好之,闻恶臭自然恶之,“恶恶臭”“好好色”就是感于物而自然生成的直接心理反应;文末又以“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作结,“好恶”与“性”对言,内含好恶乃人性之直接呈现之意,故凌廷堪以“终于拂人之性,然则人性初不外乎好恶也”[6](141)释之。
虽然好恶之情感于物而自然到来,不可预期、无从修习,但却是人之生活的起点。如此论断并非臆测,而是征诸事实之言。作为物感我应之时乍然间的情感涌现,好恶之情是人对有关接触对象当下且直接的感受。身为经验中的人,其行为的选择、人生目的的追求、认知的形成、思想的产生,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当下、直接的感受开始的[7](86)。就事实而言,因有好好色之情,才产生了亲近好色的行动意向,形成了“好色是美好的”这一认知;因有恶恶臭之情,才产生了远避恶臭的行动意向,形成了“恶臭是糟糕的”这一认知。思想由此形成,行为由此驱动,生活亦由此而展开。故黄玉顺称之以“本源性的生活感触”②,并说:“在‘感触’当中,你才能够‘动’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动’当中,我们作为主体性的人,这才得以诞生。”[7](87)总而言之,若无好恶之情,生活便失去了本源,政治也无从产生。故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公孙丑上》)他言政治治理须以原发的恻隐爱人之情为本,否则便丧失了本源性的驱动力而难至平和、隆盛的至善之境。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絜矩”之道才本好恶之情展开论述,以此强调政治实践的开展要从好恶之情出发。
不过,从好恶之情出发开展政治实践还只是相对笼统的逻辑性观点,如何才能把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呢?那就是遵从自身的真实好恶,根据“所恶”而“毋施”的作用机制:一方面,“所恶”之言以“我”为主体,意在强调治国者自身之好恶才是开展政治实践的基本出发点。若不从自身好恶出发,而以他人之好恶为准,便会压抑政治实践中的自主性,削弱其政策法令的内驱力,而且易流于伪饰和谄媚(譬如被孔孟批之为“德之贼”而“阉然媚于世”的乡原)。另一方面,听从“所恶”之情的召唤而“毋施”之,中间没有丝毫截留或违逆,提示治国者须从自身的真实好恶出发开展政治实践。这是因为,作为本源性的生活感受,原发之情本身便是真且实的,违逆此情行事则不真、不实,如“假装爱你”本质上是虚情伪意,若本此行事,便丧失了构建道德之善的根基。因而《大学》论修身的第一要义就在于“诚其意”:顺从自身真实的好恶之情行事。
总而言之,“絜矩”之道借“所恶”说明确指出,治国者自身的真实好恶才是开展政治实践的基本出发点。
二、通情:“絜矩”之道构建理性行为法则的基本方法
从字义上看,“矩”即法度,也就是公平、普遍而客观的理性行为法则③。生成理性行为法则,这是“絜矩”之道的核心目标之一。一己之好恶虽然是开展政治实践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若不加节制地一味顺从,便会使其在过度的发用中丧失正当性。此尤以生理性情感(如耳、目、口、鼻之欲)为著,荀子基于此提出节情制性说,并非全无根据。不只生理性情感,道德情感(如仁、义、孝、悌之情)若不加节制,同样容易发用失当。《大学》原文便明确指出,“意诚”之后,好恶之情仍难免有滞、偏、私之弊。所谓“滞”,即为对象化情绪所左右,“有所忿懥”;“偏”乃情感流于偏颇,即好而不知其恶、恶而不知其美;“私”即个人主观意见过重,“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所以,一己之好恶本身还不足以构成公平、普遍而客观的理性行为法则[8]。要想生成理性法则,仍须化解一己好恶中的滞、偏、私之弊,而诸弊得以化解的同时,普遍有效的理性法则也随之形成。
如何化解一己好恶中的滞、偏、私之弊?“絜矩”之道提供的方法是:通情。《大学》以“絜矩”组词便内含此意,“絜”乃量度,言在情感的量度中生成理性行为法则。上引:“所恶”一段话,即言己居中位,通过“所恶”而“毋施”贯上通下、承前启后、旁通左右,使“上—我—下”“前—我—后”“左—我—右”之人各尽其情,从而达成总体的和谐与平衡,以此化解自身好恶中的滞、偏、私之弊,生成普遍有效的理性行为法则。
从本质上看,“絜矩”之道所提出的“所恶”而“毋施”的通情之法就是推己及人的恕道。因而,“恕”道的操作机制同时也是“絜矩”之道的基本作用机制。儒家经典中关于“恕”道的论说颇多,如《论语》中便记载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中庸》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此以“好”论;《论语》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中庸》所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以“恶”论。从中可以发现,通情的作用机制在于,主体从自身的真实好恶出发,在换位思考中与他人之好恶相通相合,俗语“将心比心”[2](557)、“以情絜情”[9](2)讲的就是通情的道理。戴震以“反躬”为说,可谓得其精意。其言曰:“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之情也。”[8](2)即凡有所施于人,反躬自问,若人以此施于我,我在情感上能否接受,若不能(“恶之”),则我亦不施于人。在反躬式的换位思考中,人己之情达成了内在的平衡。所谓“人己之情的内在平衡”,即人己之情各有所尽。套用朱熹的话说,就是不只我能如此,他人也能如此④,我之好恶的展开不会侵犯他人之好恶的正常发挥。因而,在达成人己情感平衡之日,便是一己好恶中的滞、偏、私之弊得以化解之时,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行为法则形成之时。
“絜矩”之道与恕道虽然具备本质上的一致性,但是《大学》不言“恕”而复造新语,明显是考虑到二者存在的差别。这种差别源于“絜矩”之道的特殊应用背景,即它是应用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当中的。在复杂的政治实践中,想要最大限度地通达民情,并非易事。这就使得“絜矩”之道不能仅止步于基本作用机制层面的操作,而需要在具体操作上进行更具针对性的设计,这种设计主要从纵横两方面体现出来:
第一,纵向上把握三人关系的相互贯通。与展开于“人—己”二人对举中的“恕”道不同,“絜矩”之道是在三人关系的相互贯通中展开的。之所以如此,乃因三人结构才能构成最简明的政治关系。
第二,横向上进行以“位置”为基础的通情。为最大限度地降低政治环境中因民情的复杂性与疏离性导致的通情困难,确保治国者以相对简单的操作实现整体的社会面通情,“絜矩”之道对政治生活中的基本人事关系进行了基于位置的梳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国与天下之中,虽人数众多、人事复杂,但皆可统于上下、前后、左右这三对有限的位置关系当中。其中,上下以品级言、前后以时序言、左右以职事言。在通情时,只需兼顾这三对位置关系,便足以把握政治生活中的所有人事关系。另一方面,相比于因个人经验、外在环境的差异所造成的个体情感的多样性与不稳定性,位置传递出的情感更加明确且固定,如上位者无不好下属勤奋、恭敬,而恶下属怠惰、傲慢。
以形成“上—中(我)—下”之法则的过程为例。在社会关系网络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级和下级,“我”既不偏于上位,也不偏于下位,而独以中位自处,感通上下:我绝不以我所厌恶的上级行为领导我的下级,也绝不以我所厌恶的下级行为服务我的上级。就这样,“上”“我”“下”各得其所,“使”与“事”皆得其宜,一种公平、普遍、有效而客观的理性法则便形成了。
言及于此,不得不探讨一个重要问题:好恶之情是否可通?这一问题是讨论通情的根本前提,若好恶之情不可通,通情就成为一句空话。而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楚个体好恶之情的生发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西方哲学普遍认为情感是私人的、主观的,从而认定好恶之情存在个体差异。当代中国学者中持此观念者亦不乏其人,或谓“每个人皆有各自的好恶,就像生理上的喜好与恶心各有各的不同对象一样”[10](79),并据此否定好恶之情的可通约性;或作骑墙之论,认为有些可通,有些不可通⑤。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人性的直接呈现,好恶之情虽然随感而发,但并非变化无常、随意发挥,人在成为人的那一刻,其好恶之情就已经被人性所规定。故《逸周书》曰:“凡民之所好恶,生物是好,死物是恶。”(《逸周书·度训》)言凡为人者,莫不好致生之物而恶致死之物,这是人之为人的必然。从这个角度看,好恶之情既是私人的,又是普遍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简言之,生而为人,其好恶莫非人之好恶。这就决定了人在面对相同或类似的境况时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致的情感体验,故孟子言“四心”与“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⑥,即只要是人,便无一例外地会在面对特定情境时产生这样的原发之情。征诸事实亦然,如人乍见孺子入井皆生怵惕恻隐之情,危则恐、病则忧、丧则哀、娱则乐,见路有冻馁则生矜怜,遭人欺凌则生忿恨,如何不通?
不过,虽然好恶之情出自天性、触物自生,却并非机械的程序设定,它是以主体对客观环境的主观感知为基础的。这种感知能力源于人的生活阅历,从而造成不同阅历的人在同一情境中所感知到的东西与感知程度存在差异。譬如同样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成人感知到的是孺子之危,故生怵惕恻隐之情;而懵懂孺子感知到的却是欢乐刺激,故生奇趣之情。虽然整体而言,感他人之危而生怵惕恻隐、感欢乐刺激而生奇趣,仍是人情相通之例,但这不能抹除人情的个体复杂性。为减轻这种复杂性带来的影响,儒家经典中专门且明确探讨通情之道处,多以“恶”而非“好”为论,如《论语》“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不欲”即恶;《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不愿”亦“恶”;《大学》“所恶于上,毋以使下”,亦如此。因为比起“所好”而“施之”,“所恶”而“毋施”在道德实践中更具普遍性与可行性,显而易见的是,我之喜好不一定人尽皆好,但恶事悖行则往往人所同忿。
三、感化:“絜矩”之道持守理性法则的作用机制
“絜”有二义,除“量度”之外,还有“持守”之义。因而在生成理性法则之后,便涉及如何持守以便更好地施政治人的问题。整体而言,儒家很少从技术层面(看重政令制度的外在规范和保障作用)而多从情感导化层面探讨治人之事。如《孝经》便提到:“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强调治国者要以自身的爱亲、敬亲之情感发百姓的爱敬之心。再如儒家所重之乐教,也是要以本于中和之情制作的“乐”来感动人心、陶冶人情。所谓的“情感导化”,浅白言之即用情感兴引情感、用行为带动行为、用生命感发生命。为称述之便,本文以“感化”说之。
作为儒家治道,“絜矩”之道亦本感化机制来探讨理性法则的持守问题。换言之,即用理性法则去感化百姓。因而《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章开头便言“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直接拈出上行下效的感化之理。朱熹即释之以:“上行下效,捷于影响。”[2](554)那么,用理性法则感化百姓是如何落实的呢?在政治实践中,理性法则的精神主要通过治国者之行与治国者之政体现出来,因而其感化机能的发挥也主要依托治国者之行与政展开。故所谓“老老”本兼有老老之行与老老之政二义,意谓治国者是用自身的老老之行与老老之政来感化百姓的(“长长”“恤孤”亦然)。
所谓“以行化人”,即首先把理性法则的要求指向治国者自己。其基本内涵是,治国者通过把自身锻造成道德尺度来兴引百姓的修身立德之心、带动百姓的修身立德之行。《大学》以“所恶于上,毋以使下”而非“我之所恶,上毋使之”来阐述“絜矩”之道,其思想意图恰恰在于,使治国者在以我之所恶节制我之所行的过程中,将自身行为锻造成活生生的道德尺度,以此作为施政治人的根基。这一观点非《大学》所独有,而是儒家谈论治人问题一贯的宗旨,如《中庸》之“修身则道立”,《论语》之“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孟子》之“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莫不以此为旨。《大学》则明言“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强调以修身带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功。因为在儒家看来,相对于言教政令等外在的技术类手段,治国者自身的言行给百姓造成的影响更为直接且有力。故《大学》曰:“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更何况,治国者身处高位,其一言一行天然地就会成为百姓争相效仿的模板,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明儒杨慎认为:“《大学》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责自修也。”[11](294)
以行化人,这只是最基本的感化之道。作为政治实体,国与天下地广人众,无法尽人亲见、亲接于上位者之言行,因而需要借助政令法度开展治化。这就涉及“以政化人”的问题。这些用以治政的政令法度,本质上是理性法则逻辑化、形式化、系统化的产物,它当然有外在规范之效,但主要功能仍在于感化。详言之,即让政令法度充满道德情义,从而发挥价值导向作用。举例喻之,若想要百姓“老老”,就要让国家的各项政令措施体现出“老老”之义,譬如对乡里教化具有重要意义的乡饮酒礼,便是以其尊老养老的基本精神⑦感发乡人尊老养老之心,而非以礼法责求子女从事老老之行。故《礼记》曰:“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至而日见之也,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礼记·乡饮酒义》)若想要百姓亲贤远佞,就要让国家的各项政令体现出亲贤远佞之义,如《大学》引《秦誓》论用人之法曰:“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便是以容贤人、退小人的基本精神,感发百姓亲贤远佞之心,而非以政令强人相从。
总而言之,“絜矩”之道本感化机制持守理性法则,并从治国者之行与政两个方面落实其感化机能。
四、情感与理智之权衡与情感的根本性
在以情为本的基础上解读“絜矩”之道以区别于技术层面的治政之道,必然会涉及一个重要的议题:情感与理智的关系问题。二者孰以为本,这是两种治道观同时也是儒家与西方的治道观产生分歧的本源所在。因而,欲通达“絜矩”之道的政治智慧,须先理清二者之关系。
理论源于生活,经过实际的生活体验,可以发现:一方面,情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样态⑧。人不是机器,而是活泼泼的生命实体,所以人首先是情感的存在,也应该在情感的体验和关怀中实现作为“人”的生命价值。因而,治国之政若能以情感为本,便能在对现实生活的关照中、在对生命意义的珍视中维持社会的和谐运转。另一方面,情感对人类活动具有内在直接的支配作用。人之行为在本源上是由情感驱动的,蒙培元说:“(情感)在人的一生中起某种潜在的支配性作用……情感需要决定了人生的目的追求。”[12](23)故《大学》曰:“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情真则不患无术,若治国者真心爱民,自然会想方设法为百姓创造最佳的生存条件,由此生成的治国之法即便不完美,也绝不会失了大格。是以明儒吕坤曰:“有纯王之心,方有纯王之政。”[13](228)正因如此,清代通儒刘咸炘断言“知不能尽天下之事,情能达天下之心”[14](884),言唯有真情能够通达天下人心。
这并不是说,情感是唯一的,理智毫无意义,而是说,人之为人,首先是情感的存在,且二者相较,情感才是支配人之行为的原动力。刘咸炘曾以“主—役”总结情感与理智的关系[14](881−883),意谓情感与理智之间乃是“发动—从属”“目的—手段”的关系,此说精确。所谓“发动—从属”关系,即理智上的对错观念根源于情感上的认同、拒斥感受。因为在情感上认同此事,故而觉得此事合宜,此即王阳明所谓:“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15](111)所谓“目的—手段”关系,即理智是为了落实情感需求才产生的,理智思考不到位,往往是因为情感需求不迫切,故明儒吕坤曰:“只有不容己之真心,自有不可易之良法。其处之未必当者,必其思之不精者也。其思之不精者,必其心之不切者也。”[13](228)
综而言之,在人之价值世界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理智固然不可或缺,但情感更具根本性。西方从技术层面着力的治道观恰恰本理智而成。他们认定经验性的情感不具备形成价值准则的普遍性、客观性与必然性,主张摆脱情感的参与,以求得普遍、客观的价值准则。诚然,在现实发用中,情感确有沦于伪(不诚)、过(滞、偏、私)的可能性,但这些不能代表人类情感的常态,西人由此拒斥情感,有因噎废食之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摆脱了情感的价值准则只能是超验的、形式的、逻辑化的,因而缺乏可操作性和可实现性;另一方面,以这样的价值准则施政治人,容易在以理制情的政治氛围中形成“人为理役”⑨的理性压迫。而“絜矩”之道则认识到情感在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性,明示治国者以自身的真实好恶为基本出发点(情之“伪”由此化解),继而在通情中化解情感的滞、偏、私之弊,以生成修己治人的理性法则,并以此理性法则感化百姓,推施政教。
五、本情之“絜矩”的政治优势与相关反思
以情为本的“絜矩”之道具备独特而优越的政治特色,下文便在与以理智为本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对比中,详论“絜矩”之道的政治优势。
第一,“絜矩”之道具有纯粹的主体自由性。本理智而成的西方治道因弃情举智,而使修己治人之事沦为以理智调节甚至压抑情感、以外在之律令威权规范人己言行的他律主义。与此不同,“絜矩”之道用以我为主体建构的理性法则修己、化人,具有纯粹的主体自由性。所谓“主体自由”即行为自主,这里指主体在身行的修养上具备完全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絜矩”之道是通过以我之好恶节制我之所行来生成修己化人的理性法则。这意味着,其理性法则从本质上讲,是主体在情感生发、调适与沟通过程中自觉认识、自主选择、自我约束的产物。另一方面,“絜矩”之道用理性法则感化百姓,实质上是通过兴发百姓的道德心使百姓主动投入道德修养活动中开展自查、自责的过程。
第二,“絜矩”之道构建的理性法则乃大公之矩。何为“公”?因重理智而忽内发,西人之“公”不得不以众为准⑩,但这样的公是通过牺牲少数人之私得来的。除此之外,法家还有背私为公之说。两者大同小异,皆对立公私,主张损私以成公。但问题在于,在损私的情况下,公又何以获得普遍有效性而成其为公?追根究底,其最后所得仍为私而非为公,故废私以求公最终反致无公。由此可见,公与私具有根本上的一致性,欲成其公,须全众私。如何为之?儒家提供的基本方法便是推己及人,即在人己一体相联的事实下,以己情通合他人之情。果能如此,一己之意见便能代表他人之意见,推言之,己意便是公意。经由“絜矩”所生成的理性法则,正是在一己之情与家人、国人、天下人之情相通相合的过程中,在集私遂私的基础上获得了普遍有效性,成为修己治人的大公之矩。
第三,“絜矩”之道体现了真正的平等精神。重情感则思想长于合,重理智则思想长于分。西人往往以分析、区别态度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个体为抽象的孤立存在。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形成的平等观关注形式上的合理性,故而西人以权利为前提追求绝对的平等,但这样的平等终究难以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黎朋便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人类之不平等,固有基于天性者。此自然之不平等也。”[16](8)与之相对,“絜矩”之道则以人性为立论前提,言人无二性:人之为人,其性质无有不同,虽有智愚、强弱之参差,但只是程度之别,而非类似人与禽、人与物这般的性质差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平等的。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絜矩”之道更为关注实质上的合理性,即通过人己之间的情感交通洞察其人之实质,包括资质之别、伦位之异等,其根基就在于情通理得、心平气和。由此实现的平等也不是削平一切的“平均”“均一”,而是 在情得其平的基础上,使人人各得其所、咸协其宜,从而达成同中有异、异中存同的总体和谐与平衡。
由上可见,以情为本的《大学》“絜矩”之道,具有主体自由、公正、平等诸般特点,是儒家为为政者提供的最为平易可行的修己治人之道。这一理论能够为化解现代政治治理中情感与理性、自由与限制、公与私、人性与权利的冲突提供重要思路。果能循之,必能为现代政治治理增添助力。
虽然以情为本的“絜矩”之道拥有诸般优势,但若据此全面否定技术层面的治政之道,认为单凭以情为本的“絜矩”之道就足够实现社会治理,同样是失之偏颇的。因为情感与理智皆属人之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二者一主一从、一向内一向外,情感向内发展出了体证式的治道,理智向外发展出了技术性的治道,因着人之心理中情与智的主从关系,两种治道亦产生了本末之别,即前者为本、后者为末。由此可知,以情为本的“絜矩”之道意在点明政治治理的根本所在,反对舍本逐末,并非拒斥技术性手段。在政治治理中,技术性手段同样不可或缺。以树根与枝叶为譬,根固方能叶茂,把握了以情为本的“絜矩”之道就抓住了政治治理的根本;但根固后仍需剪枝,因而在此之外,治政的技术性手段也是必要的。只是这一领域并非“絜矩”之道的探讨重点。与此互补,西方治道观更为关注技术层面,重视对制度、政体等治政技术的探讨。若能两相结合,将技术性手段融于以情感为本的“絜矩”之道当中,便能互相补足,使“絜矩”之道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并为社会“带来更多的协商调解,更多的人际互助,更多的自治自理,减少法庭裁决,和缓理性竞争,削弱残酷争夺”[16](102)。
① 本文参考古籍包括《大学》《孟子》《论语》《中庸》《礼记》《逸周书》《孝经》,书名、篇名皆随文标注。
② 今人黄玉顺对此颇为关注,其所谓“感触”本质上就是原发的好恶之情。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86页。
③ 此处所言“理性法则”之“理性”,非谓概念化、形式化、逻辑化,而是指普遍性、必然性、客观性。
④ 朱熹说:“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则是不平矣。”参见朱熹:《朱子语类》,《朱子全书》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55页。
⑤ 亚当•斯密便是如此。他认为并非所有的情感都能引起同情,能否以及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同他人之情,会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参见亚当•斯密著,许丽芹,饶凯宾等译:《道德情操论》,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20年。
⑥ 《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⑦ 《礼记•乡饮酒义》:“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
⑧ 对此,蒙培元、李泽厚皆曾做过重点讨论,蒙培元强调情感是人最首要、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参见蒙培元:《漫谈情感哲学》(上),《新视野》2001年第1期,第47—49页。李泽厚则以情感作为人生的最终实在和根本。参见李泽厚:《关于情本体》,《伦理学纲要•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第52页。
⑨ 此即李泽厚所谓:“以伦理作为人的最高目的和最高境地,经常使人为神役,与‘人为物役’相对应,都造成人的异化。”参见李泽厚:《关于情本体》,《伦理学 纲要•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66页。
⑩ 社会契约论便是典型代表,它强调让私得公,即签订契约的人必须转让自己的自然权利,以形成社会的公 权力。
[1] 华军. 传统儒家情论的理路、特质及其当代价值[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1): 21−30.
[2] 朱熹. 朱子语类[M]//朱子全书: 第14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3] 王夫之. 读四书大全说[M]//续修四库全书: 第164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4] 黄克武. 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M].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6.
[5] 章太炎. 太炎文录续编[M]//章太炎全集: 第1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6] 凌廷堪. 校礼堂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7] 黄玉顺. 爱与思: 生活儒学的观念[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8] 李海超. 中国哲学现代性转型中的情感论进路及其发展逻辑[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4): 9−17.
[9] 戴震. 孟子字义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20.
[10] 刘悦笛. 作为“心之大端”的好恶本情—— 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情感禀赋论[J]. 人文杂志, 2020(7): 78−86.
[11] 王文才, 万光治. 杨升庵丛书: 第一册[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2.
[12] 蒙培元. 情感与理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13] 吕坤. 呻吟语[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6.
[14] 黄曙辉. 刘咸炘学术论集: 哲学编[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5] 王阳明. 传习录注疏[M]//王阳明全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16] 黎朋. 革命心理•下[M]. 杜师业重译, 吴福同增订.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7.
[17] 李泽厚. 己卯五说[M].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9.
Emotion-oriented: Confucian governance of the doctrine of Xie-Ju in
NING Jingxian,YU shusheng
(Faculty of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The essence of the doctrine of Xie-Ju (the measurement of Confucian moral rule) is the legal measurement formed after cautious and thoughtful measuring and maintained in governing the state and ruling the people. Its fundamental spirit is that the one who governs the state must take his own authentic likes and dislikes as the basic starting point, connect his personal natural emotions with those of his families, country people and global citizens to form rational principles for conduct, and hence move the populace and implement politics and beliefs accordingly. As a result, the governance by the doctrine of Xie-Ju acquires such properties as subjective autonomy, impartiality and overall concordance. This theory points out the essence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makes up for the deficiency of western governance model based on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provides reflections and remedy for modern political governance.
; the doctrine of Xie-Ju (the measurement of Confucian moral rule); human emotions; natural likes and dislikes; empathy; move; the Confucian governance
10.11817/j.issn. 1672-3104. 2023.03.004
B222.3
A
1672-3104(2023)03−0031−08
2022−10−25;
2023−01−1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先秦儒家‘意义—感通’的教化哲学研究”(15AZX009)
宁静贤,女,河北保定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思想史,联系邮箱:m18733820501@163.com;于述胜,男,山东烟台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教育史、教育思想史
[编辑: 胡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