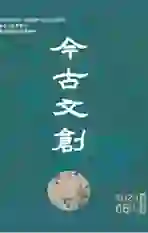娜拉在一九九〇年代
2023-05-31周文宁
【摘要】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小镇头铺街上的女孩妙妙以“出走”的姿态成为继现代文学“娜拉”热之后的新时期“娜拉”的代表。不同于现代文学“娜拉”们的“群体”性存在,妙妙展现了处于20世纪九十年代“娜拉”的孤独存在状态:主动背离群体的身份的孤独,历史与未来选择之间存在的孤独以及现代形态与价值的困惑造成的情感的孤独。“孤独”的背后,是“娜拉”们美丽的“现代想象”,是对不甘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和命运的反抗。
【关键词】“娜拉”;王安忆;《妙妙》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05-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5.006
20世纪90年代王安忆的小说创作“涉及女性的性犯罪问题” [1],有论者称她此时期的创作是“从抽象的观念性写作转向具体的历史性写作。”[2]作者将目光直接聚焦在社会转型时期女性的生存状况的改变上。其中《妙妙》讲述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头铺街上的女孩妙妙在追逐走出“现代青年的独特道路”的过程中,一步步走向迷失的故事。妙妙作为头铺街上一名普通的乡村女孩,不仅从心里瞧不起她所生活的头铺镇,“也瞧不起县城,省城这样的地方,或还能将就将就,她只崇拜中国的三个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她热烈地追逐三个城市,热烈地追逐成为独特的现代青年,热烈地想要离开脚下这片属于小镇的土地,在这场热烈中,与这场热烈相矛盾的是她呈现出来的孤独的姿态:社会上身份的孤独、伦理上存在的孤独和思维上情感的孤独。她是20世纪九十代追逐“现代想象”的“娜拉”们的代言人。
一、身份的孤独:主动背离群体的姿态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登出胡适的评论《易卜生主义》,胡适、罗家伦合译的《娜拉》,淘履恭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译的《小爱之夫》等,由此开端的‘娜拉旋风在中国文学界越刮越猛。”[3]“娜拉”创作成为风尚,乃至“中国版‘娜拉小说竟占去五四文学的大半舞台。”[4]五四时代的女性由此也掀起了“娜拉”热,这个时期的她们尽管逃离了家庭,但她们并不孤独,她们始终在人群之中,是社会政治运动的联合对象。她们的解放更多是为了服务于政治需要,服务于社会解放这宏大目标,服务于“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做个人”[5]的解放目标,这使她们更容易且必须向人群靠拢,在人群之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她们必须学会人群中的话语,并将这些话语作为自己的宣言,进一步得到人群的认同,发出以子君为代表的“我是我自己的”[6]呐喊,这些呐喊使她们不得不拥有相同的思维模式,并在彼此的呐喊声中获得情感的共鸣。她们这个群体,于社会之中是有着“正义”理论的强大支撑的合法性存在,并且呈现出“理论上”的目标一致的特征,是真正的群体。
“一九九〇年代初王安忆还在大写八十年代的‘娜拉小说《妙妙》”[7],甚至同时期的作品《米尼》《我爱比尔》中也有“娜拉”的痕迹:逃离家庭并与家庭断绝关系的米尼;家庭“失踪”,面对“积满灰尘和蛛网”[8]的房子,“不得不逃离出去”[9]的阿三。逃离、出走似乎成了这一时期作家书写的潜在意识,形成了王安忆笔下独属于20世纪九十年代的“娜拉”。20世纪九十年代“娜拉”为何重新走进作家的视野,她们与五四时代的“娜拉”又有何不同呢?
“她要走一条现代青年的独特道路,和头铺街上的所有道路都不同”是以妙妙为代表的20世纪九十年代“娜拉”们的宣言。这是一场追逐“现代”的出走,是一场自觉地走向孤独,以孤独彰显自己“独特”的出走。妙妙走向孤独的第一步,从服装开始。如果她坚持真正的时尚(大城市的流行风尚),那么她便只能做小镇的落伍者,如果她选择做小镇的时代领袖,那么对于大城市来说,她妙妙就成了一个落伍者。小镇与大城市之间似乎存在着“时间差”,在真实的生活上,小镇总是慢了大城市一步,这个时间差,是妙妙“孤独”的现实根源。妙妙在这个时间差上,在代表着“现在”与“未来”的两个方向上徘徊,最终选择了“未来”,即相对于小镇来说的未来。这就造成妙妙本人在小镇上的“格格不入”。本来这种格格不入是客观现实造成的结果,可是她却最终成为妙妙主观情感的错位,“人们都理解了她,她还凭什么孤独呢?她要是不孤独了,和头铺街上的女孩还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和头铺街上的女孩没了区别,她妙妙还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呢?”她将这种错位,这种差别,这种孤独看成是“现代”。她着意远离与头铺街上任何的相同,远离街上的女孩,远离街上的潮流,讨厌街上的方言,她在心理上走出了她生活的社会——头铺街。
20世纪九十年代“娜拉”的出走,是自身内部“解放”的需求,是追逐“现代”的必然选择。“不仅仅是做个人,还要做个女人”是以妙妙为代表的“娜拉”们的目标。五四时期的“娜拉”的目标是使自己成为“人”,社会化的“人”,而对于妙妙们而言,她们在成为社会人的同时,更强调自身的“女人”属性,她们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五四时代身为人的共性,而是身为女人的独特性,且是20世纪九十年代社会转型时期作为“现代青年”的独特性。这独特性决定了她们必然地要处于人群之外,无法形成属于她们的群体,因为在群体中,她将是她们。她们呈现出更多的反叛性、不合法性和单打独斗的自觉背离群体的姿态。由此,她们的出走是孤独的,是处在社会之中的身份的孤独。
二、存在的孤独:历史与未来的抉择
妙妙走向孤独,追求独特“现代”的第二步,是她与家庭的决裂。她像所有五四时代的“娜拉”们一样,毅然离开了家,“离了家,身体就解放了一半,思想可以更自由了”。社会向家庭施压,使得妙妙的妈妈和哥哥不得不出手阻止妙妙在头铺街越来越“荒诞”的行为。对此,妙妙的反应是“我是万万不回家的”。她将家庭看成是比头铺街更严重的地阻碍她走向“现代”的障碍。如果说头铺街代表的是妙妙的“现在”的话,那么“家”代表了她的“过去”,她的“历史”,离开了家庭,就是离开了过去的自己,是对自己的“历史”的彻底告别。“女性是在不断逃离中成长起来的,她们逃离男性,逃离社会,逃离爱情与婚姻,甚至逃离自己的灵魂,整天生活在镜像与幻想之中,逐渐陷入空虚、孤独与绝望的境地,这是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10]妙妙要逃离的“历史处境”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与命运”[11],要追求的“镜像”就是美丽的“现代想象”,而“不甘于处于社会底层的状况和命运”[12],是她们决绝反抗的根本原因。
现代媒体成为构筑妙妙“现代想象”的实体,作为一个小镇的女孩,“妙妙对头铺外面世界的了解主要是通过电影电视,还有部分报刊杂志。”妙妙现代想象的来源就是现代媒体展现出来的现代形象。这些现代“形象”形成了妙妙们心目中的现代,同时这些形象组成了现代“幸福,先进,富裕”的概念。“华而不实的时装、弄虚作假的‘致富信息、五花八门的室内剧、气派不俗的度假村、徒有其名的大奖赛、煽情刺激的末流通俗小说。”[13] 这些现代媒体构成的现代图景使妙妙们深信不疑。
妙妙将现代传媒中的“潮流”当成是现代,而潮流是什么呢?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妙妙而言,这场极端的表现就是反抗“历史”的我,追逐“未来”的我,在“历史”与“未来”中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选择的结果是自身存在的孤独。妙妙将与北京来的演员的性爱看成是她与北京的联系,她认为自己成了他们之中的一员,成了一个“不同寻常”姑娘,一个“头铺街上是没有像她这样不同寻常的姑娘”。这种不同寻常使她产生了“骄傲”的情绪,不仅如此,北京演员“亲妙妙的动作,就好像那些外国电影上的男人呢,妙妙就成了电影里的女人,而他的北京口音则使他断断续续的话像是电影里的台词”则使妙妙真切地成了梦想中的“他我”。妙妙的现代想象没有因为与北京男人发生关系而得以实现,反而从北京男人的北京,到孙团的省城,再到何志华的县城,她能“出走”的距离离她的头铺街越来越近,不管是北京,还是省城乃至县城,都没能带她离开头铺街,她本人的“孤独”情绪在一次次“离经叛道”的出走中也逐渐加深。
“中国现代作家塑造了大量出走的‘新女性形象,她们把‘离家视为‘个性解放的先决条件。把‘出走视为‘现代意识的必然结果。”[14]如果说五四时代的女性解放停留在了出走层面,那么20世纪九十年代的女性解放则停留在了欲望层面,错把欲望当成个性,当成独立思想,当成现代青年的特征。20世纪九十年代,女性追求“现代性”的最大的敌人是消费文化(在这里指现代媒体塑造出的美丽的现代想象)带来的欲望的喷薄,她们最大的障碍是自己,最大的难题时如何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因此,出走,不再是解放的结果,而成了一种姿态,一种宣言、一种途径和手段,其目的是反抗“自我”。
相比于五四“娜拉”“父亲的家门与丈夫的家门。在这两道门之间的徘徊彷徨、犹疑不决与进进出出”[15],王安忆笔下的妙妙在家庭、小镇和省城、北京之间,决绝地抛弃了代表“历史”与“现在”的家庭与小镇,奔向现代,她们身上已经不再是“五四”时代的横向的空间性的徘徊与抉择,而是纵向时间性地过去与未来的抉择。
三、情感的孤独:现代形态与价值的困惑
王安忆“她有广泛深厚的宗教的爱的情怀,所以更能发现‘孤独与‘激情”[16]。妙妙 “成了头铺街上最孤独的人”,她的孤独是“自我”(本来的我)与“他我”(梦想的我)之间角逐的结果,本质是我与“现代”的冲突。
客观上妙妙的“孤独”,是头铺街与妙妙双方对现代有着不同的理解的结果。妙妙所展现出来的姿态不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现代”性,不被人们看作是“时髦”,而被人们看作是“别扭”。“人们在注意妙妙的同时,终于注意到了妙妙与众不同的服饰,人们说:看她多奇怪,人家穿这个,她偏穿那个;人家兴这个,她偏兴这个,样样和人家拗着来,多么别扭。人家不说她时髦,直说她别扭,这更加深了妙妙的孤独。” 这种双方对时髦的“现代”理解的偏差,使得妙妙成了人们眼中孤独的客观存在。
主观上妙妙也没有从这代表自己是“现代青年”的孤独姿态中得到心灵的满足。她主动选择“孤独”姿态,主动脱离人群(头铺街),但她却并没有得到“现代”的认同,没有获得走向“现代”的“满足感”,她反而从这“姿态”中感受到了迷茫、孤独的情绪。“孙团是怎么看她的。是看她作头铺街上的女孩,没见没识的,所以哄来玩玩;还是将她看作和他一样的有现代意识的青年,才与她交这朋友。”妙妙开始对“本我”与“他我”哪个是真正的“我”产生了困惑,对自我究竟是否是“现代青年”产生了怀疑。
孙团在给妙妙的信中说“妙妙是一个可以和她谈性的女孩”,于家庭(历史),头铺街(现在),现代(未来)而言,这句话分别意味着妙妙是一个叛逆的女孩,妙妙是一个堕落的女孩还是妙妙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女孩?对于站在三者交缠中的妙妙而言,当她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会认为是对她的赞美还是对她的侮辱呢?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化“摧毁了旧文化帝制而未又建立新的文化制度的新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是无主导秩序、无主导话语的文化,它带有某种多中心的‘自由特点,虽然不免有些杂乱。”[17]那么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不仅要面对自身内部文化的拨乱反正、市场经济文化的兴起,还要吸收外部输入文化,其文化多元与多样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的多变与“不稳定”,从而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另一种“无主导秩序、无主导话语”的特点。从而呈现出现代形态与价值的困惑。五四时期,“中国‘新女性仅从《娜拉》剧中学到了离‘出走而没有从易卜生那里学到人格独立的现代意识,所以她们‘到末了还不是从一个‘家钻到另一个‘家里去了[18]”[19]。20世纪九十年代的妙妙用出走的方式表示与“旧”的“落后的生活”的决裂,去追求“新”的“先进”的生活方式,即追求成为现代青年,但她对现代青年的理解僅仅停留在现代青年的衣着上,现代青年在爱情中对身体的态度上,她用“身体”去追求这种“现代”,此时“现代”反而还给她的堕落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撑,即她的这种行为是现代青年的“新型的性爱观念”。“现代性”这个梦想存在,使得她们的堕落,呈现出符合“现代性”行为的“正义”的“先进”的自我价值判断,她们并不把这种堕落看成是堕落,反而看成是“现代性”的表现。因此妙妙所追求的不过也是从一个破旧的房子走向一个明亮的房子而已。房子里面的女人,从未具备真正的人格独立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思想。
小说的最后,头铺街上的“人们渐渐习惯了妙妙的行事,觉得头铺街有这样一个人物也算不上什么,也许每一条街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妙妙最终还是融入了头铺街,或者说头铺街最终还是接纳了妙妙。象征着“现在”的头铺街,也在时间的线性流动中不断走向代表未来的“现代”,包容和接纳着所有挣扎着飞向未来的孤雁的孤独。
参考文献:
[1][2]杨庆祥.阿三考——由《我爱比尔》兼及王安忆的写作症候[J].文艺研究,2015,(04):27,26.
[3][4][7]程光炜.小镇的娜拉——读王安忆《妙妙》[J].当代作家评论,2001,(05):175,175,176.
[5]卢隐著,肖凤,孙可主编.今后妇女的出路·卢隐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408.
[6]鲁迅.彷徨·伤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8.
[8][9]王安忆.王安忆精选集[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312,312.
[10]蒋海霞.当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女性意识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4:37.
[11][12]郑昕.中西方文学中女性解放主题的比较[D].辽宁大学,2013:12,12.
[13]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
[14][19]宋剑华.错位的对话:论“娜拉”现象的中国言说[J].文学评论,2011,(1):122,127.
[15]唐娒嘉.众生喧哗背后——五四女作家的娜拉书写[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2):127.
[16]徐德明,王安忆.历史与个人之间的“众生话语”[J].文学评论,2001,(1):35.
[17]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6.
[18]沈予复译.玩偶夫人·后记[M].上海:上海永祥印书馆,1948.
作者简介:
周文宁,女,河南长垣人,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