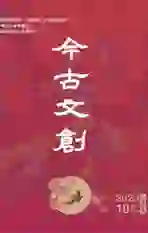《京华烟云》的哲学思想探微
2023-05-30宫净晨
【摘要】 本文是对《京华烟云》中所含哲学思想的研究,该书以道家哲学为主要内容进行叙述,因为这本书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人”,林语堂的思想也比较丰富,所以,儒、道、释、基督皆可在书中寻到踪迹。虽然不同的思想主张之间的内容不同,但对人世间的一些看法也有相同之处。本文将从书中所含的人生哲学落笔,再对书中的“道”进行阐述。
【关键词】林语堂;《京华烟云》;人生哲学;婚姻哲学;“道”的哲学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10-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010.003
一、顺乎自然的人生哲学
老子讲:“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 《中庸》里也有如是论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故君子慎其独也。”道家庄子最大的关切是让动物及人各遂其生,或让他们“安其性命之情”,亦可说是直面“现实”。因此,不论是“道”“常”还是“中庸”,他们都强调要顺应一种“法”,一种“自然”,一种从未变化的存在,一个一直运行在这天地宇宙间的一种“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的规律,是不可须臾离的。
在《京华烟云》中,姚木兰是懂道,知道顺势的典型人物。无论是自己的婚姻还是家庭,每一件事情出现,她都懂得如何自处,或顺从,或顺势而为。她有些像《红楼梦》中的薛宝钗,但比薛宝钗多了一些活气与恣意。她是林语堂笔下最理想完美的人物,是道家思想的代表。而姚家丫鬟银屏,她一生的所做所为则为“道”和“顺其自然”的反面,不合世俗,结局是被世俗淘汰。
在《京华烟云》中,银屏的角色很特别,也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她来自南方,自身带有南方宁波的粗野劲儿,长得漂亮,聪明能干,因为是家中丫鬟里唯一的南方人,平时很受欺负,孤身一人应对所有困难和处境,也称得上是十分勇敢的人。她无法回南方。既因为过惯了姚家的安稳日子,也因为在南方已经无依无靠,所以当体仁投给她温暖的怀抱时,她便毫不犹豫地迎了过去。综合考虑银屏最后自杀的悲剧,首当其冲的一个原因要考虑体仁于当时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的男人。
林语堂曾在《吾国与吾民》中说:“女人的受苦,多是出于男人的粗鲁过于男人的不够公民投票资格。倘男人而天生的讲情理,脾气好,慎思虑,女人便不致受苦。”
体仁是姚家的长子,姚父对儿子不如对女儿亲近,因而体仁从小就在姚母的手下成长,加上姚母因其是长子而对其过于骄纵,所以体仁并不是一个拥有好的习惯和修养的人。彼时十七岁的年纪,暴躁易怒,正如姚思安评价他,说其野性还没耗尽,遇事不会仔细思考谨慎执行。而银屏也不识大体,顺着体仁。在银屏自杀的前夕,文中写道:“体仁看见银屏那个样子,当然心里难过,自己隐入这种麻烦困难又怒气难消。他现在也许觉得不管天下什么女人,若要是忍受这么多的苦恼才能占有,那真不值得。”这足以表明体仁是银屏悲剧中最后且沉重的一个砝码。
从银屏的角度来讲,其自身的行事态度和处世习惯对其命运悲剧也拥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银屏的悲剧是命运悲剧,这个无置可否,但细看更是其性格的悲剧。无论是和家里其他丫鬟的关系上,还是同姚母与体仁,她都显现其刚烈和恃骄,也因此将自己推入困境中。如书中开始的描写,一大家子人逃难,“在纷乱当中,木兰听见母亲责骂丫鬟银屏,那时银屏在另外一辆车里,缘由是银屏浓施脂粉,衣服穿得太鲜艳。在大家面前,银屏自然觉得太难为情。青霞是一个十九岁的丫鬟,扶着太太上了车,正暗中微笑,暗喜听了主人的话,此行没敢打扮得花枝招展。”即透露出银屏的个性和与他人的关系。因为同是南方人,银屏有时就同太太用南方话交谈,而家中的其他丫鬟都是北方人,听不懂谈话,这也是引起其他人不快的一个方面。文中描写的话语也透露了银屏的个性和想法,在体仁要出国的前夕,和银屏的对话中有一段银屏回答说:“在聪明上,人比狗强;在忠诚上,人比狗差。并不是我不信任你。你既然有机会出去,你自然应当出去。我没有权利干涉你的前途。但是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现在我已经成人了。即使我愿等着你,可是也许情形有变,也由不得我。我若不嫁,變成个黄脸婆,人会笑我说:‘你还等什么呀?我拿什么话回答呢?我若任凭别人摆弄,你回来的时候儿,我的身子不是别人的了吗?哼!为人莫作女儿身,一生苦乐由他人。”短短几句,就可看出银屏的泼辣、大胆。银屏的角色似《红楼梦》中的晴雯,骄纵、任性,弄小性子,耍小脾气,同是性格占重要原因,导致其各自的人生悲剧。林语堂在书中对银屏的悲剧是这样评价的:“银屏算不算是一个好女人呢?不错,天下有坏女人吗?只要环境地位变动一丁点儿,银屏在人生所占的地位也就和木兰的母亲一样了——是财产万贯之家的女主人,能干的主妇,热爱子女的母亲,儿女心目中的完人。”
二、婚姻家庭哲学
谈到这世间的世俗生活,当然不能不提到婚姻,守着阴阳中和之道的婚姻,既调适了人事,又是这世间延续的存在之道,这也是大多数人不可避免要思考的问题。一个世间的人可以说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刻是脱离家庭的,婚姻家庭的重要不言而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都是在家庭制度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这个制度决定并润色了整个中国式生活的模型。《大学》中写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京华烟云》相仿于《红楼梦》,都是以一个家庭为中心,以姻亲或亲属关系相连,分别讲述几个家庭的时迁兴衰。所不同的是《红楼梦》中描写的大家族牵扯的人口众多,上到主子下到丫鬟,洋洋洒洒几百个人物,描写“社会”的意味多过描写家庭的意味;而《京华烟云》则是在实际上更接近于中国“小家庭”伦理人事和道德的描写阐释与介绍。所谓“修身”然后能“齐家”,家之组成,人也,家和之成,人也。像《弟子规》《三字经》,其目的即在于从小就要培养可以修其身,然后可以治其家,最后能够有能力再为其他人的人。而这其中除了学文从师外,父与母对其孩子的教育可谓重之又重。如人们耳熟能详的孟母三迁、岳母刺字、窦燕三教子的故事。首先,母亲在一个家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中国的孝亲文化传统,认为“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更在于女人不但是使一个家族香火延续成为可能者,“家族中各个支派的盛衰也是以所娶来的媳妇的体质心性为依归”“孙子体格的强弱,性情的优劣,完全以媳妇的体格性情为依归”。所以当曾文璞为其三子荪亚定下姚家这门亲事时是非常满意的,除了姚家与曾家门当户对外,更是因为姚木兰天生聪慧,定会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好妻子,孝顺的好媳妇;他叫太太等女人去逛庙会,是为了让她们看孔庙和石碑上刻着的前几代高中的人名,他以为,女人如若能重视这个,就容易把孩子教成儒生,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儒家的狂热爱好者。至于姚家的太太,体仁的结局与她的教育失败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而牛家,在书中的第十章就有专门的描写,对于牛太太,林语堂评价道:“牛太太并不是好讥笑别人的女人,只是一个野心勃勃、实际而又能干的女人,凭对现实环境的真正了解而获取利益。她不仅是已经训练了丈夫,而且推动他去获得了权力地位,官上加官,步步高升了”,可是在情势失败后,牛太太还是依旧如往常,不思悔改,且其子牛怀瑜在以后的情形上是比其母做得更过分的,为了追求利益,全然不顾及,娶了交际花,在暗中做无耻的事。
此外,夫妻两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也非常重要,对于这方面的看法,林语堂将其观点通过对木兰和荪亚夫妻间相处的叙述表达得很清楚。木兰与荪亚都是顺从且懂得符合世俗的人,他们之间的相处没有理想中的浪漫和惊心动魄,但却是符合情理,和谐且温馨的,这便可以说是林语堂的态度。
三、“道”的哲学
《京华烟云》分为三卷,分别是上卷“道家儿女”、中卷“庭院悲剧”和下卷“秋季歌声”,三卷每卷开篇都引了庄子的一句话作为总的题目。而这三句话也是整部小说的骨架。
(一)“道家儿女”
庄子《大宗师》语:“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如木兰的婚姻,事件的发端,人事的走向即体现了庄子所语。小说开篇描绘了人生无可言说的道家之意,“在人的一生,有些细微之事,本身毫无意义可言,却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事过境迁之后,回顾其因果关系,却发现其影响之大,殊可惊人,这个年轻车夫若头上不生有疮疖,而木兰不坐另外那辆套着小骡子的轿车,途中发生的事情就会不一样,而木兰一生也不同了。”只因一个无聊的小事,推至而出后来的走失,获救,然后理所当然的婚约,犹如多米诺骨牌,一个接着一个,指引着木兰最终走进曾家,与荪亚结为夫妻。所有的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人们顺着给出的方向朝着远方走,不问目的,也不回头。当她和孔立夫交谈并有些相知时,心中泛起了前所未有过的涟漪,恰巧碰上曾家上门来提亲,她才对自己的这门婚事产生些略微不安。但她最终还是遵从了婚约,因为她相信个人的婚姻大事都是命中注定的。
在《道家儿女》中,着重笔墨的还有孙曼娘,细细捋顺曼娘的人生脉络,其中的“道”不言而明。曼娘是曾家的表親,是曾家老太太内侄的女儿,小镇里朴实的女孩子,父亲是一个学究似的人物,因而便受了一套旧式女子教育。曾家老太太喜爱她美丽漂亮,且又聪明解事,便早有意将其许给平亚。后来的事情也就顺其自然。虽是平亚染疾,有考虑到让曼娘来行冲喜之事时,家人会有些犹豫,怕万一出了意外,曼娘会有不幸的结局,且此时如果曼娘不答应,不同意的话,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对于曼娘来说,她虽没有嫁到曾家,可是从小到大,曼娘是平亚妻子的事情早已经成了两家人认定了的事。无论是从曼娘对平亚的情感上来说,还是从一直以来曾家对她们家的照顾来讲,这件事情都不应该否了,况且在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依然认为“冲喜”是有可能将人从疾病中解救出来的力量的。曼娘也相信,虽然不知道成功的概率,但无论多少,她都是要去试一试的。尤其是当平亚为曼娘的父亲守完灵堂之后两个人的感情也自那以后更加深厚,从儿童时候的些许朦胧变得愈加不同往常那般了。在小说中的描写里,有多次描绘不详,暗示亚平的离去,如文中多次描写曼娘的梦和观音菩萨的佛像,为曼娘的悲凉命运埋下伏笔。曼娘的故事,表现了古老中国人的生活观,顺情理,顺命运,顺人事难言的情感。曼娘没有纠结过,她顺从命运的安排,走了她在人世的道路。
(二)“庭院悲剧”
庄子《齐物论》中说:“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但而田猎……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事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幕遇之也。”世事人生犹如一场大梦,转瞬,即所有都将化为云烟消散,到此时,无论是姚家、曾家还是牛家,都呈现了颓落之势。首先是牛家,牛家太太鼓励儿子们仗势欺人,任意妄为,不允许别人批评她的儿子,即便儿子公然犯法、违警,她也绝不说什么,且认为那是她在北京城赫赫威名马祖婆神通应有的体现,而这的后果也必将于日后显现。牛东瑜因自己的骄纵欺负了一个富家女,也惹怒了那女子的父亲,被设计弄了个亵渎尼姑庵、诱拐尼姑的罪名,加之其从前不善,被糟害的人借此都发动了攻击,以致牛家无论在金钱上还是在政治方面都面临了崩溃。牛东瑜也在这次风波中没了性命。曾经的牛家也因此而无法于北京立足。曾家的曾老爷退居在家,家中还算殷实,足够能安稳地度过往后的日子,曾老爷不愿接受新近涌进来的东西,依旧守着过去的礼过去的节,推掉了袁世凯给的官职,心里默默地为这逝去的“老旧的传统”而悲哀伤心着,家中的大媳妇曼娘生性软弱,无法管理家中的各事,而二媳妇素云只关心自己一房的事情,其他一概推个干净。所幸还有三媳妇木兰能将家管理得井井有条,但家中依然还是在走下坡路。尤其是素云的歧路行为,不仅使得经亚也曾为此做了错事,最后还使整个曾家有了不好的影响,以致最后的离婚都给曾家带来了不小的动荡。姚家更是遭受着接二连三的人事的变更,先是姚家大少爷的意外死亡,然后是红玉投水自杀,接着姚母病逝,姚老爷也将家里安排妥当进行他的进山修道,期限遥遥,走之前也立了遗嘱。
总之,戏已经过半,酒过三巡,物非,人亦非,是梦醒,亦是又梦。
(三)秋季歌声
庄子《知北游》里讲,“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
曲终落幕,人终散。几经沉浮的牛素云,虽靠着蝇营狗苟之事赚取了许多钱财,最终孤立无援,人事凄惨,不过事之将终,还是人悔归善,还报了自己所做的一些恶事。修道归来的姚先生安然度过了自己最后的人生时光,木兰虽遭丧女之痛但收留了许多的流散孤儿,也延续了更多的希望。国家处于战乱,但就像文中所记述的:“木兰问:‘爸,您想中国能作战吗?老父回答说:‘你的问题问错了。不管中国能不能打,日本会逼着中国打。他停了一下儿,又慢慢说:‘你问曼娘。曼娘若说中国非打不可,中国就会赢的。曼娘若说中国千万不要打,中国就会输。”而曼娘是坚定地肯定的。
四、结语
《京华烟云》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它将中国社会的人事情状,符合逻辑情理清楚地展现出来,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符合世俗生存规范的,他们懂得顺势而行,辨析得清周围事情的发生与自身的厉害,懂得如何在这人世间,各个环境中要以何种方式自处,活得守“道”,知道如何谋事,且懂得听从事情的自然发展走向,他们不是理想中的人物,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色彩。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想着自己的事情,同时也想着要将自己的周围也变得符合自己的理想,从某种方面讲,他们更像是个人主义者。诚如林语堂本人在序言中所说:“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参考文献:
[1]林语堂.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林语堂.老子的智慧[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林语堂.孔子的智慧[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5]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6]林语堂.京华烟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宫净晨,女,满族,辽宁本溪人,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