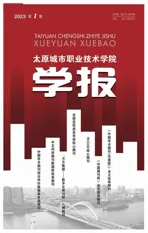论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
2023-04-05谢鑫娟阿依加马丽苏皮
■ 谢鑫娟,阿依加马丽·苏皮
(新疆财经大学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随着商品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发展,商业宣传中使用公众人物或明星的肖像来推广自身产品和服务的情形,已随处可见。在我国,学者关于死者肖像保护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肖像的精神利益,对于实际案例中出现的肖像财产利益纠纷的关注度不足。《民法典》第993条和第994条分别规定了肖像许可使用制度和死者肖像保护制度,侵害死者肖像,死者近亲属具有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权利,但此种请求权的性质并不确定,死者的肖像是否具有财产利益以及死者近亲属是否享有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请求权?《民法典》第994条对死者肖像保护的规定比较模糊,而司法实务中利用死者肖像获取商业利益的案例屡见不鲜,如“鲁迅肖像权案”“邓丽君肖像权案”。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从死者肖像精神利益角度出发,而应在司法实践中发现问题,从现实的侵权类型出发,明确保护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对于维护社会公平具有重大意义,然后结合司法实践的需求展开理论层面的反思与构建。因此,本文重点按以下思路进行讨论:首先在总结司法实践的基础上,阐述了我国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的现状;其次对比较法上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制度进行分析;最后针对我国具体的法律规定,论证用财产权模式来保护死者肖像财产利益,提出了司法适用的具体途径,即明确死者肖像具有财产利益并可以被继承、受到侵害时请求权主体以及保护期限。
一、我国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
我国死者人格财产利益保护是通过司法实践一步一步确立的。1988年,在“荷花女案”①中,一审法院判决被告魏锡林、今晚报社各赔偿原告400元,但法院没有解释该赔偿是精神损害赔偿,还是侵权损害赔偿;1996年,在“鲁迅肖像权案”中,被告未经鲁迅之子周海婴许可,出售镶有鲁迅肖像的笔筒,后原被告在法院达成和解协议:被告向原告补偿1.5万元,但仍无从知晓该补偿属于精神损害赔偿还是肖像的许可使用费。张红教授[1]认为这是肖像的许可使用费,该行为既没有使鲁迅的名望降低,也没有给其继承人产生精神痛苦,被告通过利用鲁迅肖像来推销自己的服务和产品,从而进行获利,也说明,死者肖像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1999年,王某等诉中国老年基金会北京崇文松堂关怀医院等侵犯肖像使用权案中,被告医院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死者孙某肖像的行为侵害了其亲属的合法权益,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②。该判决认为死者没有肖像权,但死者肖像具有财产利益,可以由其近亲属继承,商业化利用死者肖像,侵害了近亲属的合法权益。
理论上,学者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方式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人格权扩张模式,即传统人格权只具有精神利益,将人格权的内涵扩张后,人格权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并且财产利益依附于精神利益。学者王利明认为:“承认人格权中包含财产利益和精神利益两部分,财产利益可以进行商业利用并作为交易的对象。”[2]人格权其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可以被承受,该承受不等于继承,因为人格权不可以转让、继承。死者近亲属可以对死者肖像进行商业化利用得到相应的财产价值,但是该财产利益不具有财产属性,不能被继承;第二种是公开权模式,即死者的肖像财产利益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可以继承、转让。死者肖像上的财产利益并不随着自然人的消亡而消失,其背后承载的价值来自于本人生前的努力,该财产利益受到法律保护。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并不是保护作为人身识别符号的肖像,而是作为商业利益承载着的一项财产,将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类比为一种可以由近亲属继承的无形财产权。张红[1]认为:“人格上财产利益应予保护,利用死者生前人格特征获利之权利为死者生前人格上之无形财产权,应由继承人继承取得。”
《民法典》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和学理讨论的基础上通过第994条正式规定保护死者人格,相比《精神损害赔偿》中对肖像的精神利益赔偿,《民法典》赋予死者近亲属相应的请求权,但是该条款对死者人格财产利益的保护作了模糊处理。民事责任包括财产责任,请求权人既可以要求赔偿经济损失,也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而法律法规的模糊性会引起司法实践中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存有争议,同时法官在应对相关案件时会遭遇一些困境。
二、比较法上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格权中经济价值逐步受到法律保护,目前比较法上大多认为,人格权中同时包含精神利益与财产价值[3]。《民法典》第994条没有明确规定保护死者肖像财产利益,通过了解比较法上的制度,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美国和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德国为参考,可以在我国死者肖像保护规定的基础上设想对其财产利益的保护。美国和德国较早就开始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给予关注,并且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法律保护制度,通过梳理两国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的脉络,比较两国的保护制度,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可以更精准对我国死者肖像财产利益法律保护模式提出设想。
(一)美国——公开权
美国用隐私权(the right to privacy)来保护姓名、肖像等人身专属性质的精神利益,用公开权(the right to publicity)来保护姓名、肖像等人格财产利益。1953年,Haelan案的判决宣告了公开权理论的诞生[4]。1954年Nimmer教授在《当代法律问题》上发表了《公开权》一文[5]。公开权可以被继承是美国法院保护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前提。1975年的“普莱斯案”中,法官明确公开权与隐私权不同,隐私权不可继承、转让,而公开权可以继承、转让,属于一种财产权[6]。“马丁·路德·金案”是第一个涉及公众人物的公开权案件,佐治亚州最高法院明确表明公开权的可继承性。美国有16个州在州法律中明确规定了公开权,例如1985年的《名人权利法案》,该法规定继承人在被继承人去世后70年内可以继承其公开权,而纽约州则规定,公开权不能继承,只能由死者在死前行使。死者肖像上的财产利益可以继承,具有一定的保护期限。给予死者的保护期限因州而异,对死者公开权的最长承认在印第安纳州为100年,在田纳西州为10年。除明确决定保护死者公开权的国家外,也有些国家对死者的公开权给予有条件保护,例如,死者死后的公开权,只有具有商业使用公开权的人才会受到保护。
(二)德国——一般人格权
德国法上,对于死者人格利益保护是通过判例和立法确立的。较早涉及死者肖像保护的第一个案例是“俾斯麦遗体偷拍案”③,但帝国法院没有正面回答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问题,而是通过不当得利制度,判决照片的所有权属于俾斯麦家属并没收照片底片和禁止公开这些照片,因此该案被学者称为“鸵鸟政策”。随后,德国于1907年制定《关于肖像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突出对死者肖像的保护,其中第22条规定,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为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对死者肖像的利用,必须经其亲属同意。在1956年“Paul Dalhke案”④中,法院承认了肖像权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本案被告未经原告同意将其照片用作商业使用,一审法院判决被告赔偿原告一定的经济损失,二审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改判被告胜诉,终审法院恢复了一审法院判决结果,并认定原告的肖像具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在1999年“迪特里希案”中,德国联邦法院判决表明,死者的肖像财产利益可以由其继承人继承⑤。继承人继承此项财产利益,应符合死者明知或推知的意思。
无论是以英美法系为代表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都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给予了保护,尽管保护的模式不一样,美国通过“公开权”的方式保护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德国通过扩张人格权的内涵来保护,将人格利益解释为包括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但两国都没有通过立法的形式直接规定,而是以司法判例的形式来确认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公开权具有财产权、可得让与、得为继承三个性质[7]。虽然美国各州均在确认死者人格财产利益应当受到保护的同时也对存续期限进行了限制,但对公开权存续期限的规定并不相同,10年、100年均有规定者,多数州认为公开权类似于著作财产权,故规定了50年存续期限。在德国,对死者肖像保护规定在艺术著作权法中,死者死后10年内,其肖像依然受到法律保护,但必须征得所有亲属的同意才能获得许可使用死者的肖像,同时任何亲属都可以对他人非法侵犯采取保护行动权利。亲属指尚存的配偶、子女,若无配偶、子女,则由其父母。两国不同制度的规定是经过本土实践案例中一步一步确定并适用的模式,无论是美国的公开权保护还是德国的人格权扩张保护,都也认可肖像具有经济价值。美国创设公开权来保护死者人格财产利益在于其没有一般人格权的概念,对于侵犯姓名、肖像等人格精神利益案件,其通过隐私权来保护其精神利益。德国采用的是扩大人格权的内涵,将财产利益包含在内,但侧重于保护死者肖像的精神利益。认可死者肖像具有财产价值,并不是否认肖像背后的人格尊严,更不是将其物化,而恰恰是通过保护死者肖像背后的价值来保护人的尊严。
三、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的司法适用具体途径
在实践中,司法往往最先接触社会变迁中相关权利的需求,没有立法的指引,实务中法官造法式的“法律续造”并不能完全适应我国重视制定法的传统。《民法典》第994条确认了死者人格利益受法律保护,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妥之处:第一,该条没有区分保护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而是进行了统一规定;第二,该条将请求权主体限定在近亲属范围内,那么当死者没有近亲属或者近亲属不愿行使权利时,则死者利益不能得到保护;第三,该条没有确定保护期限,而是间接将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作为保护期限,但财产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不依赖死者与近亲属密切的情感利益而存在,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不能完整地保护死者的财产利益。本文结合司法实践,探索适应我国司法适用的具体模式,提出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条款进行详细化解释。
我国应该采取公开权模式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给予保护,采用人格权扩张模式保护死者肖像财产利益,无法解释为什么死者还具有人格权,与我国现有的关于民事权利能力的制度相冲突。自然人死亡之后,人格权消灭,人格利益也就随之消灭,无论是人格上的精神利益还是财产利益,都归于消灭。人格权扩张模式强调人格财产利益依附于精神利益,精神利益不存在,而财产利益也将不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公开权制度下,可以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进行完全保护,财产权可以继承、转让,使其价值最大化地在社会流通。个人劳动的商业产品应受到法律保护,因为这种法律保护会强烈激励个人投入必要的时间和资源来提高其价值。在财产理论下,公开权得到更好的承认,该理论将为未经授权的剥削提供报酬,当自然人奉献了一生来获得一定的地位之后,让一个商业企业从其劳动中获得意外之财将是不公平的,考虑到基本的公平性,确保了继续防止不当得利,同时作为个人一生中额外的职业激励,将有价值的财产利益留给其继承人或受让人的能力也应该得到法律保护。自然人对自己的宣传权进行了更多的投资,同样也应该对这些宣传权享有更大的利益。因此,法律保护并鼓励花费时间和资源来发展这些先决条件的技能,同时也向个人保证,他将能够从这些努力的成果中获益。自然人死亡后,肖像上的精神利益随之消亡,还剩下财产价值,故德国法上人格权扩张保护方式对我国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不适用。
(一)确定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具有财产属性并可以被继承
《民法典》第994条开放性立法为死者肖像利益留下了解释的空间,而肖像具有财产属性是解释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法律保护机制的理论依据。《民法典》第993条规定了肖像的许可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肖像的经济价值。就肖像的许可使用而言,除本人肖像外,基于肖像权所包含的财产价值的可继承性,死者肖像可以由继承人许可他人使用来获取经济利益[8]。根据人格自主理论,自然人可以支配自己的肖像,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具有财产属性,且可以被继承,理由如下。
第一,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具有财产属性。《民法典》第993条规定,民事主体可以将自己的肖像许可他人使用,并因此取得财产利益。如果允许自然人死后,其肖像可以随意被他人商业化利用,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生者,生前努力所创造的形象价值不能留存给后代,而只能是在社会中消亡。自然人的民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肖像权在死后并不存在,但肖像客观存在,死者肖像中的财产利益依然存在,该财产利益具有财产属性,可以继承。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支持死者肖像具有经济价值,在王金荣诉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一案中,法院明确承认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肖像享有特定的经济利益;在“邓丽君肖像权案”⑥中,法院酌定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判赔的理论依据是邓丽君的肖像具有财产价值,并由近亲属继承,公司擅自使用,损害了这一财产性权益,因此应当赔偿,在此后的鲁迅肖像案中,尽管以调解解决,但都是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赔偿。由此可以看出,司法实务中,法院支持死者肖像具有经济价值。
第二,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由继承人继承,以获利为目的使用死者肖像,必须征得继承人的同意,未经其同意,继承人可以提出损害赔偿。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可以继承,并明确死者继承人继承的是一项财产权,更能保障自然人对其人格上财产利益自主决定的权利,也是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继承人是继承的是死者去世前对死者人格肖像进行商业利用的权利,还是商业化的经济利益?《民法典》第994条对死者肖像的保护比较模糊,但我们仍然可以从实务判例中找到依据。在湖北汉家刘氏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与GUAN-VEN KANDARELI(中文名光文·堪达雷里)肖像权纠纷一案中,一审和二审法院都支持原告请求被告停止使用死者的肖像⑦。试想一下,如果继承人继承的仅是一项商业利用后的获益,那么继承人是没有请求权基础去要求被告停止使用死者肖像,法院也不可能支持原告对被告享有的停止侵害请求权,显然继承人继承的是一项权利,并能够对死者肖像进行处分。根据《民法典》第992条,人格权不可放弃、转让和继承。我国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自然人死后无肖像权,因此继承人继承的是死者肖像的处分权,例如许可使用权,具有可支配性和独占性。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可以被继承,当死者肖像被商业利用时,继承者继承的是死者肖像财产利益,即对肖像的处分权(如许可使用、转让),但同时仍负有维护死者人格尊严和保护死者肖像精神利益的义务。此义务的履行可以按照德国对于死者肖像保护的约束,即“继承人利用死者肖像不得违背死者生前明示或暗示的意思表示”。因此,实务中法院在继承人作为原告的判决中承认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
(二)确定请求权主体
根据《民法典》第994条的规定,在死者肖像受到侵害时,请求权主体要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有一定的顺位限制,第一顺位是配偶、子女和父母,第二顺位是其他近亲属。但此处的顺位规定主要是保护死者肖像所承载的精神利益,在财产利益受到侵犯的情况下,继承人可以在内部协商要求赔偿,法律不需要规定每个索赔人行使权利的顺序。死者肖像所承载的财产利益由死者的继承人继承,当有多个继承人时,无论请求是由一个继承人还是由多个继承人同时提出,都属于当事人私法自治的范围,法律无须加以限制。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25条的规定,侵害英雄烈士肖像所承载的人格利益,如果涉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起诉主体除了近亲属外,还可以是人民检察院。成立公益诉讼主体,不仅为了保护死者肖像承载的个人利益,更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民族尊严。权利人生前签订了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被授权人在权利人死后是否可以基于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而继续使用其肖像利益呢?根据合同的全面履行原则,被授权方可以在肖像许可使用合同范围内继续履行。如果被授权方超出合同内容,继承人可以提出防御保护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主体在继承顺序上,应先按照死者生前的意思表示,通过遗嘱或者遗赠的方式,继承主体可以是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死者生前无意思表示,可以按照法定继承顺序。
(三)确定保护期限
法律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并不是无期限的。首先,随着时间的流逝,死者肖像价值会逐渐减少,进行过长的保护将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有效利用;其次,死者肖像的财产价值,不仅来自个人的生前努力,也离不开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的参与,过长的保护不利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后,继承人持续对死者肖像独断使用,也不利于社会的创新发展。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学理上有两种观点。第一,应类推适用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即死者财产利益保护期限为死后50年[9]。第二种观点认为,参照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期限,即死者近亲属的生存期限[10];《民法典》第994条赋予近亲属相应的请求权,该条文显然是以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为死者肖像的保护期限,这会产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死者没有近亲属,法律是否对其肖像就不予保护?第二,近亲属的生存期限不一致,就导致法律予以保护的期限也不一致,违背了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学者杨巍[11]认为,死者人格的财产权益是可继承的,对死者人格的侵犯实际是侵害继承人的利益,对于该利益的保护,不是继承人的生前期,而是取决于立法政策对这种财产权益的存续期。因此,应该设定一个固定期限,有利于平等保护死者肖像利益。这种无形财产权与著作财产权的性质类似,故参考著作财产权的保护期限为死后50年,将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设定为50年。
四、结语
当然对死者肖像的保护也不是没有边界的,其同样应当受到《民法典》第1020条关于肖像合理使用的限制,特别是在第三人使用肖像是基于公共利益且使用行为在必要范围内的情形下,不应当认为相关行为侵犯了死者近亲属或继承人就死者肖像所享有的权益。在“鲁迅肖像传案”中,鲁迅作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去世后所留下的照片不仅为家人所拥有,更因其史料价值而为社会所拥有,进入社会公共领域,让公众了解和研究鲁迅文化的公共资源。在“溥仪肖像权纠纷案”中,原告以溥仪的近亲属名义向法院起诉,认为被告未经许可将溥仪的照片用在展览中,侵犯了溥仪的肖像利益,请求停止侵权并赔偿相关损失;被告认为溥仪作为历史公众人物,其肖像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成为社会公共资源,公民对此享有知情权,自己的行为是报道活动和传播历史,属于在合理适用范围之内,不构成侵权,最终法院采纳了被告的抗辩理由。
《民法典》第994条规定了对死者肖像的保护,但没有明确对死者肖像财产利益的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实际侵权类型中,多是行为人未经许可对死者肖像进行商业化利用,从而推销自己的商品和服务来赚取经济利益;司法实践中,法院更多偏向于对死者肖像精神利益的保护。立法解释的缺失引发法院在解决纠纷时出现一系列的困境,而当事人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为了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判,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为法官公正裁判民事案件提供重要的裁判依据和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发布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创设死者肖像财产利益保护的具体裁判规则。
注释:
①原告陈某是已故曲艺演员吉某(艺名荷花女)的母亲,吉病故后,被告魏某以吉为原型,创作小说《荷花女》,于《今晚》报社发表,小说虚构了有损吉名誉的一些情节,其母亲起起诉讼,请求被告魏某和《今晚》报社承担民事责任。
②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1999)崇民初字第1189号民事判决书。
③享有“铁血宰相”之称的政治家俾斯麦,于1898年病世,两名记者在夜晚偷偷潜入其家中,为追求最佳摆拍效果,随意摆动俾斯麦的遗体,甚至将墙上的指针拨动至死亡的时间。随后,在各大报纸上宣称,有大量独家遗照,可以通过高价购买。俾斯麦的家人得知消息后,立即起诉了两名狗仔,要求归还照片的底片,禁止泄露。
④VGL.BGHZ 20,345.
⑤BGHZ 143,214-Marlene Dietrich.
⑥被告在演出的地铁海报、售票广告、灯箱广告等众多位置商业使用邓丽君肖像。邓丽君的哥哥邓长富向北京东城区法院起诉,认为被告侵犯了邓丽君的姓名、肖像等人身权益,请求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⑦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3民终1465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