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社会中的音乐及其解放
——以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为中心
2023-03-21李雨轩
□李雨轩
【导 读】 阿达利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对音乐的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属性做了较为深刻的说明。它采用历史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模式,将音乐的发展概括为牺牲、再现和重复三个阶段。其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重复阶段音乐的一致性这一根本属性,并提出了重复社会理论。重复社会除表现为集体的无差异性,还借由众声喧哗达到沉寂状态。最后,阿达利提出了作为破局之道的“作曲”。然而,《噪音》在研究范式方面有其局限,它没有实现音乐的形式—本体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的有机结合。

雅克·阿达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Bruits:Essaisurl’économiepolitiquedelamusique,1977)一书(以下简称《噪音》),力图在对音乐的历史分析中展现整体的时代变迁,其提出的重复社会理论对理解当代文化生态尤有价值。重复社会及其音乐具有何种特点,面临何种问题?能否构想出可能的解放路径?本文拟以《噪音》为中心,对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一、牺牲与再现:前重复阶段的音乐符码
阿达利在“噪音”(bruit)与“音乐”之间建立了一种辩证关系:音乐也是一种“噪音”,一种“有组织的噪音”[1]13。法语词bruit 有两层含义,一是指普遍的声音,二是特指噪音。而本书中bruit 也兼有这两层含义。这样一来,噪音和音乐便形成了一种复杂关系:一方面是本体同源论,即承认噪音和音乐在本体上是同源的声音形式,“所有的音乐均可定义为依据某种符码(换言之,依据排列的规则和次序的法则,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声音的空间)所组合的噪音”[1]58;另一方面是功能差异论,即强调音乐是对噪音的导引和升华,是将各种噪音加以秩序化的结果。
噪音和音乐这种既同源又别异的关系影响了全书的定位。廖炳惠在中译本“导言”中认为,本书可被视为一部“噪音如何被接纳、转化、调谐,进而传播、制造出新社会秩序的政治经济史”[1]3;但另一方面,阿达利表明“本书在追溯音乐的政治经济学时,将其视为一系列秩序(也即差异)被噪音(也即对差异的质疑)侵犯的过程,这些噪音是预言性的,因为它们创造新的秩序”[2]19。阿达利在信息论和控制论的理论框架下,将噪音视为对信息的干扰和中断,但它亦可能产生新的信息秩序。上述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解,前者暗示噪音是被动的,后者表明噪音是主动的,而这种矛盾正是由阿达利本人对噪音和音乐的复杂态度所决定的。噪音和音乐不断相互转化,其情感色彩也随之变化。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便在英译本“序言”中察觉出阿达利理论中“音乐”的双重性:“现在的音乐既是一种新的、解放的生产模式的预兆,又是一种具有反乌托邦(dystopian)可能性的威胁。”[2]xi因此,我们可在不区分情感色彩的前提下,将“噪音”视为一种还未被“音乐”征服、驯化的原始声音状态。
《噪音》采用历史性与建构性相结合的模式,将音乐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牺牲(sacrificing)、再现(representing)和重复(repeating),并以作曲(composing)作为解放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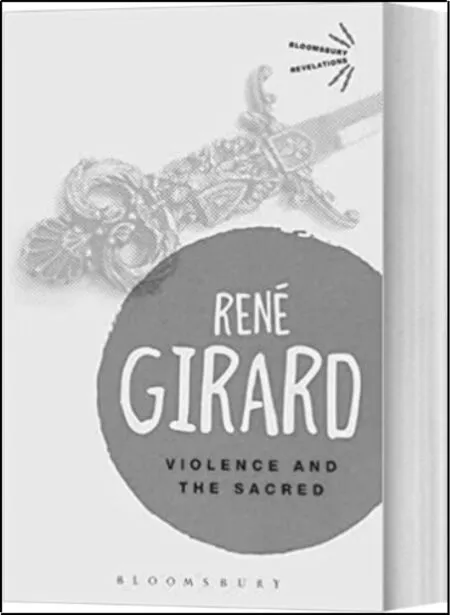
阿达利认为商业化之前的音乐在社会中充当“牺牲”的符码功能。阿达利对牺牲的理解受到吉拉尔(Réne Girard)《暴力与神圣》(La ViolenceetleSacré,1972)的影响。吉拉尔认为,“牺牲的目的是恢复共同体的和谐,强化社会的结构(fabric)”,牺牲的功能是“将暴力重新导引至‘适宜的’轨道”[3]。吉拉尔的基本观点是,牺牲是用以导引暴力、恢复和谐的。阿达利将这套理论运用到音乐上,认为“噪音就是暴力:它造成干扰。制造噪音就是中断信息传递,是切断,是扼杀。它是杀戮的一种拟像”;而“音乐乃噪音的一种导引(canalisation),所以也是牺牲的一种拟像”。[2]26可以看出,阿达利基本继承了吉拉尔的框架,将噪音与暴力、杀戮相对应,又将音乐与牺牲相对应,揭示了噪音和音乐对共同体的不同功能。但其理论迁移有三个缺陷:其一,虽然引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但未能提供多少早期材料,致使论证不够有力;其二,由于这一阶段时间跨度过大,牺牲的功能在后期被窄化为歌颂宫廷,巩固统治;其三,阿达利过分重视音乐与权力的关联,更关注官方对音乐的制作、利用而忽视了音乐在民间的情况。
阿达利将音乐开始商品化的阶段命名为“再现”,大致始于17世纪末。阿达利将音乐家从牺牲末期到再现阶段的地位变化概括为从“仆从音乐家”到“企业音乐家”。再现阶段的音乐的商业表现主要有两个:一是音乐会或现场演唱;二是在印刷术的支持下,出版商发明了作为商品的乐谱。乐谱主要由音乐家购买、演奏,最终与音乐会合流。这一时期音乐的主要受众也由封建贵族变为中产阶级,“新的观众希望音乐能反映他们的现实”[1]128,音乐家只有写出中产阶级熟悉的作品才能获得听众。
这部分最重要的是借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符号政治经济学对音乐的讨论。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力才是具有生产性的(productive)。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认为,生产劳动者“不仅把包含在工资中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而且把这个价值‘连同利润一起’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具体到文艺作品,“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或者说,因为他是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4]。以这种观点来看,最初以版税为收入的作曲者是不具有生产性的,其收入本质上是一种租金(rente),他们本身是食利者(rentier),“汲取工资工人在商品的循环中以其劳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1]91。这是阿达利依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早期音乐的产业状况的分析,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但在当下,很多文艺工作者已经以其产品成为资本增殖的重要一环,他们是具有生产性的。
为了描述音乐的特殊盈利模式,阿达利提出了一个原创概念——“制模者”(matriceur/molder):“他的收入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无关。反之,他的收入系于对该劳动的需求量。他生产的是一种模子(mold)。”[1]91也即模子的交换价值与生产本身脱节。提出这一点,首先是因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无法有效解决作为商品的音乐的价值问题:“音乐是无法衡量的、无法被化约成花费在生产该音乐上的时间。以作曲者和演奏者的劳动为基础来比较两种交换价值的不可能,不仅显示出对音乐的差别定价的不可能,也显示出不可能将再现中的符号生产降级(relegate)为劳动价值。”[2]58-59如果将范围扩大,则一切作为商品的文艺的价值都是难以简单用劳动价值论来解释和确定的。因为一般的商品只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作为商品的文艺还具有艺术价值。艺术价值究竟对应于商品的价值还是使用价值?这种三元的价值结构正是当下艺术生产论中的隐含问题,并且还未得到恰切的解决。
其次,阿达利提出这一问题还受到符号价值理论的影响。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消费社会》和《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分别问世于1970年和1972年,应该说符号价值理论已经形成。阿达利受其影响,看到了商品的符号性对交换价值的巨大影响。作为商品的文艺本身就能极大地体现出价值与符号价值的区别。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劳动及其时间为价值的基础,其基底逻辑是将人视为均质化的、抽象的人,其关注的是商品的客观价值;但符号价值理论则关涉具体的、现实的人,比如明星,其关注更多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主观价值。因此,在音乐的商品化问题上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劳动价值论难以适用,二是符号价值论表现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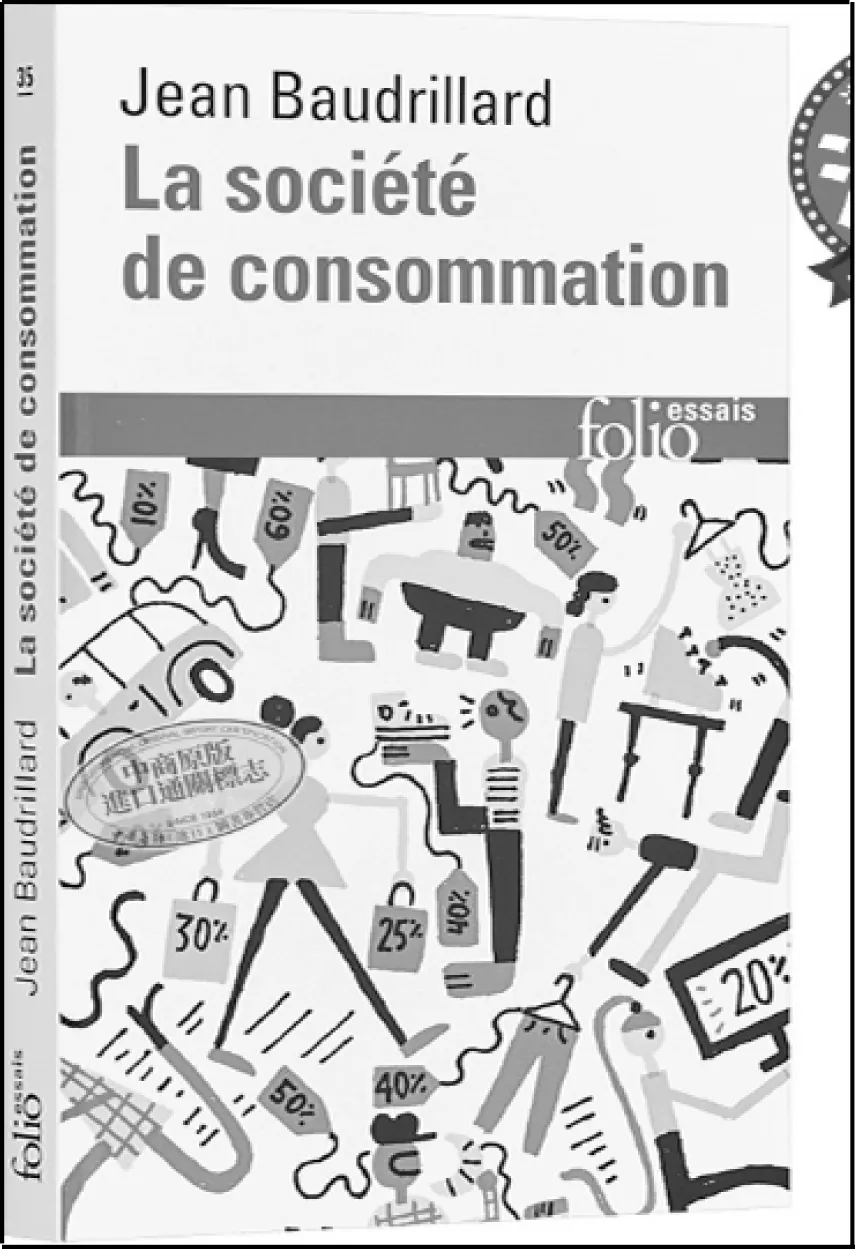
二、从重复音乐到重复社会
对音乐的重复阶段的描摹是阿达利理论的重点,故在此设专节加以讨论。音乐的重复阶段大致始于19世纪末。从再现阶段到重复阶段,背后以资本的逐利作为动力。这表现在三方面:第一,生产成本的提高使演出的获利空间缩小;第二,聆听音乐的消费需求日益增长;第三,广播、电视等的出现使音乐再现可以免费获得。而后随着录音技术的发明,音乐的盈利便聚焦于唱片。在重复阶段,音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音乐真正变成了一个产业。其次,音乐中出现了新内容:爵士和摇滚相继出现,成为流行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被收编;同时,对需求的制造手段——畅销排行榜也出现了。最后,音乐消费出现了私人化、非集体化倾向。
与再现阶段一样,阿达利继续用符号价值理论来分析重复阶段。以唱片为例,一方面,他揭示出唱片的价格与唱片的造价、录音的品质没有直接关联,确证了符号价值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音乐的交换价值已与其使用价值完全脱节,“使用价值在大量生产之中消失”[1]185。符号价值理论的确对分析音乐的价值问题有较强适用性,但亦非完全贴合,因为阿达利对音乐的“使用价值”的理解过于狭窄,仅将其理解为唱片、录音本身的硬件品质,而没有看到听众在聆听音乐时获得的满足,而后者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少数人会因为纯粹的符号价值而囤积海量唱片,却毫不聆听。
阿达利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重复阶段音乐的根本属性,即一致性(identity)。在重复阶段,音乐不再建构差异而是陷于一致性之中。这首先是从音乐的生产和消费角度理解的:其一,流行音乐不再根据阶级来进行层级组织;其二,严肃音乐仅限于前往音乐会的精英阶级,不再在中产阶级之间流传。这种音乐消费状况“造成个别消费者之间的同一性(sameness)。人们消费是为了与他人相似,因而不能再像再现中一样突出自己的不同”[1]240。阿达利甚至认为重复阶段音乐的特征是“将一切平等化”[1]258,正如周志强所论,这是“一种抹平个性、去除差异而拒绝承认阶层矛盾和经济差别的声音”[5],但它并未在社会层面造成实质的平等化影响,这里的“平等化”只不过意味着消费的一致性。其次,这种一致性还表现为制模者和模子的同化。在重复阶段,表演者的功能“是作为复制的一个模范(model),再生产与重复都在这个模子下成型”[1]257。在这个过程中,制模者本身也成了模子。这里的复制表现为两方面:一是自身的复制,也即风格的形成,预示了当代所谓的“人设”,表演者只有坚持这个模子才能获得稳定的粉丝支持,一旦突破既有风格,则有可能造成颠覆性后果;二是他者的复制,也即风格的引领,创新性的模子一旦产生,就会被投入批量生产、大量移植。
其实,从上述音乐研究中已能觉察出更大范围的社会状况。而阿达利本就不想局限于研究音乐本身,还试图以此来展现整个时代的变迁。他认为音乐不仅是一个研究对象,还是体认、理解世界的一种途径和工具,其真正目的是“借由音乐来论述”[1]13。因此,阿达利试图将重复作为一个根本特点推衍为整个时代的特征,也即重复社会(repetitive society)的诞生。
重复社会的第一个特点便是重复性和一致性,差异被集体性地抹除。这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和消费领域。从生产角度看,创造模子的制模者可以同时制造出无数的复制品,“生产所需之劳动不再内在于物品的本质”;从消费角度看,物品也“失去了其个性化的、区分的意义”。[2]128重复社会中的生产和消费正是鲍德里亚所界定的“物体系”,任何商品都存在于一个系列中,比如盲盒,看似彼此之间存在细微区别,但总体上是高度同质性的。比照“重复”和“体系”这两个不同指称,“重复”正显示了“体系”的本质,即“重复必须要试着维持多样性,为需求制造意义”[1]277。重复社会的矛盾便在于“焦虑地追寻失落的差异,所依循的却是弃绝差异的逻辑”[1]15。因为这种多样性只是表层的,在深层上仍是同质性的。
阿达利的重复社会理论还受到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启发,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以原真性(Echtheit)和灵晕的消逝来描述原作和复制品之间的差异。[6]但在机械复制时代,区分原作和复制品不再必要,因为每一原作在诞生之初便已存在于体系之中,早已做好批量复制的准备。阿达利凭借“模子”这个概念,使原作和复制品之间的区分变得模糊。而这与再现阶段产生了质的区别:“在再现阶段(手工工场或早期资本主义)中,每一物品都是独特的,模子只用一次。相反,在重复的经济中模子可以使用多次。”[2]40再现发展自单一的行动,重复则是数量的堆积。而当符号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时,消费就成为对物品的占有而非使用,阿达利将其概括为“囤积”(stockpile),可谓切中肯綮。大量囤积的物品不再被“使用”,却被“虚造使用价值”。[1]97
重复社会的第二个特点是声音与沉寂之间的辩证关系。阿达利深刻地指出,如果全社会“喧闹地自我表达”,那是因为“它不再拥有有意义的论述”。控制噪音不是要求噤声,而是创造“一种置身于声音中的沉寂,一种置身于可复原的喊叫中的无伤大雅的饶舌”[2]122-124。表面上大家众声喧哗,实际上只不过是“对空”言说。并且,在这些声音的另一边是一个自主的权力中心,不单单是统治阶层、国家机器,更是一个综合了镇压、法律、治理、技术的复杂体系,它应对、操纵这些声音。以此观照西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就能发现,不论一个话语是否符合真相,都埋没在众声喧哗之中:真理受到非真理的反制,非真理亦试图夺取真理之形,双方难以辨认。这种嘈杂、喧闹却无力的状态被阿达利指认为“沉寂”。从这个角度看,麦克白的经典台词——人生“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着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7],正是对阿达利观点的最佳注释。重复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可能沦为“愚人”。
除了上述两点,重复还有更多面向。比如,克隆便成为重复社会的一个极端表现。阿达利认为,“对生命复制条件的研究已经导引出一个新的科学典范(paradigm),直指西方科技从再现演变到重复的问题的核心”[1]193。从对产品、模子的复制到对肉身、生命的复制,这是重复最具伦理深度的面向。此外,重复还以其极致与死亡相联系。阿达利所欲批判的是科技滥用和军事扩张,他认为“核子强权已经囤积了足以摧毁这个星球许多次的工具。唯有将之诠释为囤积死亡,我们才能解释这种现象”[1]273。这种认知有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影子,两者都关注到了消耗的集体性,但又有所不同:在巴塔耶那里,积累和消耗是对立的,积累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消耗;而在阿达利这里,积累本身就是消耗,是一种“囤积式的消耗”。可以说,阿达利也为当今世界提出了警醒。
三、“作曲”与可能的解放之路
面对音乐的重复阶段,阿达利试图寻找可能性的解决方案。他关注到一种新的音乐创作状态,即“纯粹为作曲而作曲”“纯粹为了一己之享乐”“在存在(être)而非拥有中找到乐趣”。他将这种状态命名为“作曲”,在其中,“音乐家主要为自己演奏,不管任何功能、景观或价值的累积;而音乐从牺牲、再现与重复的符码解脱出来后”[1]287-289,它以自身作为目的。阿达利拒绝音乐的旧有符码,强调作曲的娱乐性和自主性;而其背后有一种普遍的本体论观点,即以存在取代占有。
那么,什么音乐能承载这样的理想?阿达利提及了凯奇(John Cage)的《4 分33 秒》,但认为它只有否定既有秩序而没有创造新秩序的价值。阿达利认为真正有示范意义的是自由爵士(free jazz)。自由爵士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一批先锋派乐手一反爵士乐的传统,舍弃和弦结构,采用自由调性。从乐队编制上看,自由爵士和以往的爵士乐没有太大区别,但其演奏形式更为自由,常常伴以即兴演奏。
这种音乐与另两种音乐形式相区别。其一是管弦乐团(orchestra),阿达利认为管弦乐团的组织形式是集中权力的象征,“管弦乐团的指挥是以一位合法且理性的组织者的形象出现,统御一个大规模、需要协调者的生产过程”[1]147。这亦可从语言角度予以验证,管弦乐团所必需的总谱,其法语partition 还有分配、配置区位之意,它本身就是一个权力隐喻。其二是“伪—即兴演奏”,阿达利认为对大多数即兴演奏(improvisation)而言,“在一个令人联想到自主与偶然的体系之下,隐藏的是一种最具有形式的秩序与最精准的指挥”,比如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的创作看似是即兴的,但实际上演奏者只能组合事先设定好的乐章,其行动均“源于作曲者对偶然的操控”[1]248。阿达利的判断是准确的,正如奥奈特·科尔曼(Ornette Coleman)在与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访谈中所论,“尽管叫作‘即兴音乐’,但令人震惊的是在这种音乐中大部分音乐家都用一个框架结构(trame)来作为即兴演奏的基础”[8]。这亦构成了重复社会中的权力表征:个体无论做什么,都“只不过是一个数据法则中的一个随机因素”,“即使表面上任何事对他都有可能发生,但平均而言,他的行为遵循明确的、抽象的而无法逃避的法则”。[1]249
阿达利认为在理想的作曲状态下,“创造性的劳动是集体的,所演奏的不是单一创作者的作品”,“生产采取了一种集体创作的形式,没有一张事先制定的蓝图,没有商业化”。在这种关系中,“音乐变为多余的(superfluous)、未完成的、关系的。它甚至不再是一种可以与其作者分割的产品”。[1]301-302
作曲状态有三个要点值得关注。其一,这种理想状态是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主、客体统一,也即劳动者与其产品之间的同一性、自反性关系,音乐与创作者不再彼此割裂。
其二,这种理想状态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变化,这是一种深刻的本体性变化。这种状态打破了重复社会中音乐的私人性、个体性,使之重回集体。这种演奏既是“为他人”的、经由他人才可能的,也正“是他人”的,鲜明地显示出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痕迹,即在社会性劳动中人对人的生产。[9]并且在这里,没有一个权力中心在指挥、掌控一切,演奏者们处于自由状态。无独有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探索个人与社会的理想关系时,也关注到了爵士乐,更准确地说就是这种自由爵士。伊格尔顿发现乐手们“所形成的复合的和谐状态,并非源于演奏一段共同的乐谱,而是源于在他人自由表达的基础上,每位乐手都用音乐自由地表达。每位乐手的演奏越有表现力,其他乐手就会从中得到灵感,被激励而达到更精彩的效果”[10]。爵士乐在形式上的确为社会组织提供了绝佳的启示性案例。此外,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对室内乐(chamber music)的分析也体现了相同的趋向。[11]
其三,这种理想状态体现出反商业化的诉求,“预示了对使用事物的工具取向的否定”[1]302。在这里,生产和消费—享乐重新统一。其背后还蕴含着深刻的时间重构:它“解放了时间,使之可以是活生生的经验,而非囤积之物”[1]311。阿达利将这种状态描述为“非功效/无用”(désœuvrement)。中译本将其译作“游手好闲”的本义,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样就遮蔽了与法国理论的对话关系。这个概念来自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南希(Jean-Luc Nancy)等人也常使用,大致描述的是一种反对完成、封闭又不断遭受中断、破碎和悬搁的状态。但南希等人连“作品”也一并反对[12],而阿达利远没有他们那般激进,他仍是在“作品”概念的框架下运思的。在作曲状态下,乐手们“身体与身体之间的交换——经由作品(œuvre),而不是经由物品(objet)”[1]307。这种“作品”是集体的产物,摆脱了“物品”的商业性和客体性。
很明显,阿达利所谓“作曲”也并非仅限于音乐领域,而是“预示了一个结构性的变迁,更深远地说是一种全新的劳动意义、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与商品关系的出现”[1]290。那么如何实现作曲状态?阿达利不但试图为其提供一些观念层面的支持,还试图探索另外的经济组织体系和政治机构形式。同时,阿达利看到了从重复的困局到作曲的突破,已经存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也即一种新的权力状态。“重复所含括的权力模式,与再现者不同,没有确切的定位;权力被稀释,伪装而匿名”[1]191,阿达利将其命名为权力的“离域”(delocalization)。这种权力状态增强了个体的主体性,每个人都有权“谱写自己的生命之歌”并“发展从噪音创造秩序的能力”[1]284,以使自己的声音真正被听到。
从根本上说,阿达利提出的解决之道是马克思主义的,其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感官的解放路径是一致的——将感官解放置于社会解放的宏观背景中。正如杰姆逊所论,阿达利试图从一个独特角度“描述从旧的资本主义形式(市场阶段,垄断阶段)到一种新形式的过渡”[2]xii,他借由作曲试图展望、描摹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四、《噪音》的模式、图式、范式及相关启发
《噪音》对音乐的历史描摹和理论建构有其洞见,以下拟通过对其模式、图式、范式的探析得出相关启示。本书采用了三阶段的模式(model),将音乐的发展概括为牺牲、再现和重复三个阶段。但阿达利认为音乐“不是以线性的模式演进,而是陷于历史变迁的复杂性和循环性中”[1]27。三个阶段不是前后取代、完全割裂的关系,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导倾向,并且它们也相互提供活力,形成了所谓的共时性(simultaneity)关系。比如,在重复阶段亦有再现的舞台,只不过“重复在开始时是再现的副产品。而现在,再现已经成为重复的辅助者”[1]186。再比如贯穿全书的“牺牲”,在早期阶段,“牺牲”如其本意地被理解为暴力的消弭、秩序的生成;而当集体操演的牺牲被压抑后,重复阶段的音乐便“成为牺牲的孤独景观的拟像”[1]82,牺牲变成一种个人化行为。阿达利在牺牲问题上存在一定矛盾:一方面,他承认“过去牺牲仪式过程所遗留下来的记忆,使音乐保存了可以沟通的力量,即使是在独自一人聆听音乐时”[1]260;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陷于商品的音乐不再具有仪式性,仪式的消失摧毁了牺牲的逻辑,音乐预示了暴力复燃的威胁,已经不再能够肯定社会之存在。这种矛盾是阿达利自身理论不够辩证的反映,这第二方面的观点在基底逻辑上存在问题,它过分强调了集体性在场的作用,而没有考虑到听觉、想象等问题,孤独的聆听既可能导致隔绝,也可能连接到更广阔的共同体,而这恰可能生成重复社会的牺牲形态。
三阶段的模式居于历史性和建构性之间,其中还隐藏着别样的历史观点,即不强调历史的线性,而强调个中的循环性、共时性,过去的存在以某种形态内化入当下的现实中,不断在历史中重现。并且,当阿达利关注录音技术对音乐产生的意外影响时,他已经具备了以媒介为中心进行考察的意识,从而与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等的媒介理论形成呼应。事实上,本书与媒介考古学在超越线性历史的观点上是不谋而合的。
就图式(schema)来看,《噪音》既是寓言式的,也是象征式的。寓言(allegory)的本质是从具体性存在中提炼出整体性、宏观性、普遍性存在。音乐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阿达利用音乐的变化以小见大地展现时代的变迁,勾勒了由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到“重复”的资本主义时代,最后到超越资本主义的“作曲”时代的图景。而象征(symbol)的特点是两个异质性存在(往往一个具体一个抽象)在某方面具有共性,且两者不一定存在包含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阿达利关注音乐与社会的同构关系,不同音乐形态构成了不同权力形态的隐喻,而“作曲”的理想状态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乌托邦对应物。
《噪音》中的音乐身兼两职,并且从这两个不同图式来评价“作曲”的效能,其结果也不同。从象征图式看,虽然作曲存在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但仍有其理想价值。从寓言图式看,则其效能大幅削减。其一,虽然自由爵士将爵士乐推向了一个高超的艺术和思想境界,但最终也只能成为专业人士探讨的对象而难以普及,这就容易陷入对精英艺术的执着。其二,音乐是否商业化构成了阿达利理论的一个矛盾,在音乐的纯粹享乐和经济运行之间存在对立。就现实层面看,后者可视为对前者的保障;但能否实现这种商业化以抗拒现行资本秩序对音乐的收编和控制,则尚需艰难探索。其三,阿达利最终认识到“作曲所属的政治经济学是难以概念化的”[1]310,且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他在现行体制下难以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力方案。
更为重要的是范式(paradigm)问题。本书采用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学科路径,借用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包括符号价值理论)等理论方法对音乐进行了分析。与正统的音乐分析关注曲式、和声、对位、调性、音色等不同,阿达利更关注音乐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的互动。就本书的接受情况来看,音乐界的学者对其基本不予理会,而一些文化研究的学者则认可其在音乐社会学方面的价值。其实这是一种普遍现象,许多音乐家都对持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视角的音乐研究持批评态度,如美国钢琴家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就对提亚·德诺拉(Tia DeNora)音乐研究中的新社会史方法大加批判。[13]这种分歧体现了两种范式之间的区别乃至对立。
两相比对就会发现,阿达利在音乐的本体分析方面虽有涉及,但总体是欠缺的。比如,书中提到半音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这“不会是偶然的”[1]27,但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则很难说。再比如,阿达利认为再现阶段音乐的根本特点是和谐,其主要成就是和声,这样简单地将音乐中的和声与社会层面对和谐的诉求联系起来,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正如布列逊(Norman Bryson)对绘画的阐释,“尽管绘画领域内的技术体系与该社会构成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领域具有直接联系,但它却并非直接衍生自后者”[14]26,“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并不一定,也并不自动地就发生在符号的过程中”[14]178。其实,很多音乐问题要从其自身发展来理解,不能忽视这种相对的自律性。比如,肖邦的“等音转调”艺术就是基于巴赫以平均律调音的键盘才变得可能。[15]154阿达利对音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将音乐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的接触缩减为商品交换的单一路线”[14]184的风险。
虽然阿达利意识到音乐“不是经济基础架构的机械式指标”[1]16,有明确反对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但总体而言,他未能实现音乐的形式—本体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的有机结合。但这两种范式并非决然隔断,杰姆逊认为“较为拙劣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往往会在处理社会主题和处理形式、意识形态主题之间造成断裂。但从原则上讲,把社会历史领域同审美——意识形态领域熔于一炉应该是更令人兴趣盎然的事情”[16]。
如何能达到这种统一?梅纽因(Yehudi Menuhin)、戴维斯(Curtis Davis)对瓦格纳的分析或可提供范例。瓦格纳的音乐有明显的民族立场,力图捍卫纯粹的日耳曼文化。在和声方面,他深受肖邦影响。肖邦的音乐能“从一个延留和弦向另一个延留和弦转调,同时又避免固定在任何一个明确调性上”。两人认为这种技巧在瓦格纳手里“成为把性欲之冲动、狂喜高潮之延长、非现实之梦幻、神秘之幽灵及想象之境界进行美学发挥与升华的重要手段”[15]161。这正是将形式—本体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有机结合的典范。从更深的层面看,在自律与他律之间能否找到一个确切的纽结点,实现形式—本体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的交互阐释,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注释
[1][法]贾克·阿达利.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M].宋素凤,翁桂堂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中译本的翻译略有瑕疵:其一,术语不统一;其二,部分翻译没有采用学界通行的译法,如将distinctive cultures 译为“殊化文化”,将differentiation 译为“异化”等。当中译本翻译存疑时,则引用英译本。
[2]Jacques Attali.Noise:ThePolitical EconomyofMusic.Brian Massumi(tr.).Minneapolis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5.
[3]Réne Girard.ViolenceandtheSacred.Patrick Gregory(tr.).Baltimore and London:The JohnsHopkinsUniversity Press,1977:8-1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0-143.
[5]周志强.声音的政治——从阿达利到中国好声音[J].中国图书评论,2012(12):32-35.
[6][德]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51-57.
[7][英]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悲剧集[M].朱生豪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588.
[8]The Other’s Language:Jacques Derrida Interviews Ornette Coleman,23 June 1997.T.S.Murphy.(tr.)Genre,2004,37(2):319-329.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7.
[10][英]特里·伊格尔顿.人生的意义[M].朱新伟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98.
[11][巴西]弗卢塞尔.技术图像的宇宙[M].李一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119.
[12][法]让-吕克·南希.无用的共通体[M].郭建玲,张建华等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73-74.
[13]Charles Rosen.CriticalEntertainment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105-123.
[14][英]诺曼·布列逊.视阈与绘画[M].谷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
[15][美]耶胡迪·梅纽因,柯蒂斯·W.戴维斯.人类的音乐[M].冷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6][美]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