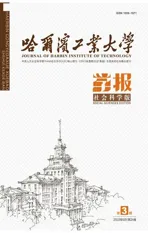士大夫身份与王充征引文书的文化意味
2022-11-25倪晓明
倪晓明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贵阳 550001)
《论衡》是一部用“论”体编撰而成的子书,该书是作者王充在其人生不同阶段所撰文章的合集。 与秦汉子书相似,《论衡》探讨问题较多,头绪繁杂。 学界对该书思想、哲学、文学、文献学层面的解读已堪称鸿富,然而对文本与作者身份关系的探讨则略显薄弱。 目力所及,对于王充的身份问题,有《论汉代“文人”的复合性》[1]以及《德与力:王充文人身份认同及理论意义》[2]98-103等数篇文章。 然而,王充身份的准确定义是什么? 王充身份与《论衡》文本间存在何种联系? 文本主题的转向与身份转型间是否存在关联性? 王充征引文书又有哪些意义? 这些内容仍需进一步探究,也是本文试图解决的问题。
一、独特的文本形态:从《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谈起
文本与作者身份关联紧密,欲探作者身份,当从文本切入。 《验符》篇在《论衡》中显得较为另类,原因在于《验符》篇与《论衡》惯常的开篇模式有鲜明差异。 该篇以叙事的方式开篇:
永平十一年,庐江皖侯国际有湖。 皖民小男曰陈爵、陈挺,年皆十岁以上,相与钓于湖涯。 挺先钓,爵后往。 爵问挺曰:“钓宁得乎?”挺曰:“得!”爵即归取竿纶。 去挺四十步所,见湖涯有酒罇,色正黄,没水中。 爵以为铜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举。 挺望见,号曰:“何取?”爵曰:“是有铜,不能举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罇顿衍更为盟盘,动行入深渊中,复不见。 挺、爵留顾,见如钱等,正黄,数百千枝,即共掇摝,各得满手,走,归示其家。 爵父国,故免吏,字君贤,惊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状。 君贤曰:“此黄金也!”即驰与爵俱往。 到金处,水中尚多。 贤自涉水掇取。 爵、挺邻伍并闻,俱竞采之,合得十余斤。[3]838
《验符》开篇讲述了庐江郡两少年捡到黄金的故事。 这种叙事手法与《论衡》常用的说理模式形成鲜明差异。 总体来讲,《论衡》有两种常用的导入模式:其一为点题模式,其二为驳论模式。点题模式即在篇头点明总论点,随后层层深入,以“总—分—总”模式展开论说。 如《逢遇》开篇:“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3]1《命禄》开篇:“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3]20《薄葬》开篇:“圣贤之业,皆以薄葬省用为务。”[3]961这种模式是《论衡》的典型模式。 驳论模式通过反驳其他论点以确立自身的立论之基,如《物势》开篇:“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3]144《论死》开篇:“世谓人死为鬼,有知,能害人。 试以物类验之,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3]871章学诚将其归入“问难”之类,其言“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4]。 若用今天的术语概括,驳论模式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
《论衡》的谋篇布局大都属于这两种议论模式。 如此一来,《验符》篇的“叙事模式”便显得有些突兀。 简单来说,《论衡》大多数篇章是在讲道理,而《验符》开篇是在讲故事。 文体层面的差异是独特文本形态的首要表征。
除却文体,《验符》篇主题也引发广泛关注。早在明清时期,便有学者对《验符》主题的“反常”提出质疑。 明人谢肇淛《文海披沙》言:“《论衡》一书,掊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至《验符》一篇,历言瑞应奇异,黄金先为酒尊,后为盟盘,动行入渊;黄龙大于马,举头顾望;凤皇芝草,皆以为实。 前后之言,自相悖舛。”[3]1330谢氏认为,《论衡》以批判谶纬俗说为旨归,《验符》却通篇侈谈祥瑞,显然自相矛盾。 此后,有学者怀疑《验符》篇为伪作。 熊伯龙《无何集》载:“余友疑伪作之篇,不但《问孔》《刺孟》《吉验》《骨相》《宣汉》《恢国》《验符》诸篇,以及《订鬼》后四段之言,恐皆属伪作。”[5]刘盼遂则指出《验符》篇确为王充所作,但写作时身不由己:“充著《验符》等篇,以颂东汉,佛家所谓顺世论也。 岂著三增、九虚之人,而信任此等事乎?”[3]1330可见,学术史对《验符》篇已有较多关注,但关注焦点相对集中在该篇主题,并且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
如果将文体视为文本的外观形式,主题视为文本的内在核心,那么素材便是构成文本的微观元素。 显然,以往对《验符》篇的探究忽略了文本的素材。 按照罗兰·巴特的理论,文本(text)是编织物(tissue),“在不停地编织之中,文被制就,被加工出来;主体隐没于这织物”[6]。 若接着罗兰·巴特的话头讲,素材是用于编织的纺线,作者是编织活动的发出者。 在某种程度上,线的颜色、粗细、质地等元素,甚至决定了编织物的素质。
回到《验符》篇,在学术史执着于该篇主题又众说纷纭的形势下,在文章体式迥异于常又难以索解的情况下,考察该篇的文本形态,似应转向更为微观的素材。 然而,该篇的素材来源为何,它的性质又是什么呢?
二、以文书为素材:《验符》篇素材来源探赜
《论衡》素材颇为多源。 岳宗伟的《〈论衡〉引书研究》对王充的知识系统做了“解码式”处理,据岳氏研究,经书与传书均为王充立论时的重要素材[7]。 然岳氏“因书究学”的理路,是仅就常见书展开的讨论,但王充的知识视野,并不局限于经传为主体的常见书。
“俗言俗议”也是王充驳论的重要内容。 《论衡》时常援引“世俗之议”“世俗传言”“世俗之语”“世谓”“俗语”之类的内容,王充自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3]1190。 可见,世俗之议促使王充不断深化思考,探求真相。据此,他的知识系统至少包括“世书”与“俗说”两部分内容,而以往对《论衡》的引文引书研究,本质上都属于常见书层面的研究。①除岳宗伟博士论文《〈论衡〉引书研究》以外,又有吴从祥,智延娜等人的专著对《论衡》引书与引文展开分析,从素材角度论,其所论列均属于常见书,未包括稀见书。 参见吴从祥:《王充经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智延娜、苏国伟:《〈论衡〉文献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其实仅就“世书”来讲,经传之书也不是王充知识系统的全部。 与经传相比,官府封存的文书属于稀见之书, 这与汉代文书管理制度有关[8]216-232。 尽管文书稀见,但对王充却有重要意义。
秦汉时代,文书可指代普通书籍,②兹以《论衡》为例,其中以“文书”泛指图书的实例有两个:《语增》:“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订鬼》:“言出文成,故世有文书之怪。”但更多的是特指政府公文。 《独断》列举的公文包含八种文体。 上行类文体包括章、表、奏、驳议四种,下行类文体包括策、制、诏、戒四种文体。 作为制度的文书,是统治的利器。 《论衡·别通》载:“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3]591又《文心雕龙·章表》载:“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9]
《验符》篇所运用的素材正是汉代的文书,该篇载:
贤自言于相,相言太守。 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程躬奉献,具言得金状。 诏书曰:“如章则可。 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诏书,归示太守。 太守以下,思省诏书,以为疑隐,言之不实,苟饰美也,即复因却上得黄金实状如前章。 事寝。 十二年,贤等上书曰:“贤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献,讫今不得直。”诏书下庐江,上不畀贤等金直状。 郡上:“贤等所采金,自官湖水,非贤等私渎,故不与直。”十二年,诏书曰:“视时金价,畀贤等金直。”汉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独纪之。[3]839
陈君贤将黄金呈献庐江太守,太守便命令文吏起草文书,并将黄金呈献给汉明帝。 从文本记载来看,明帝对此十分怀疑。 庐江太守又上一章,明帝未予理会,“事寝”。 随后,在陈君贤、庐江太守、汉明帝之间,上书与诏书多次往还。 这段记载对汉代地方上报祥瑞的流程做了详细还原。
《验符》所载明帝诏书言:“如章则可。 不如章,有正法。”据此可知,庐江太守所上为“章”。《独断》言:“章者需头,称‘稽首上书’,‘谢恩’、‘陈事诣阙’,通者也。”[10]“陈事”作为章体的应有之义,也与此处相合。
王充不仅对此事甚为知晓,更是直接征引其文,如陈君贤所言:“贤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献,讫今不得直。”太守辩解:“贤等所采金,自官湖水,非贤等私渎,故不与直。”明帝下诏:“视时金价,畀贤等金直。”这些文字显然不是王充杜撰的,而是对公文的删减节录,也有研究将这种对文本的创造性处理称之为“钞”[11]。
王充在征引文书的同时,也基本保留了文书的原始形态,这是《验符》以叙事开篇的原因。 文书本身的叙事性决定了《验符》文本的叙事性。这可从图书目录分类角度寻得学理依据。 《四库全书总目·诏令奏议类序》言:
王言所敷,惟诏令耳。 《唐志·史部》,初立此门。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于集部,次于别集。 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于是可稽。 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 抑居词赋,于理为亵。 《尚书》誓、诰,经有明徵。 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 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 今亦并改隶,俾易与纪传互考焉。[12]
尽管历代官私目录对“诏令”“奏议”为代表的文书归类有分歧,但总体仍倾向于将文书纳入史部之下。 张舜徽先生言之甚明:“秦汉以来诏令、奏议,录入史传,诏令多在本纪,奏议例归列传,故正史艺文、经籍志,初无诏令奏议一门。”[13]可见,文书原本便存于史书纪传之中,其叙事性便不难理解。
问题在于王充为何能够征引文书,这要从汉代文书的管理制度以及王充的身份层面探求原因。 汉代地方吏民所上之书大都秘藏在兰台、石室之中。 《后汉书·百官志》载:“兰台令史,六百石。 本注曰:掌奏及印工文书。”[14]3600此外,像石渠阁、天禄阁、辟雍、东观、宣明、鸿都等汉代重要的藏书处,既包括天下所献书籍,也有公文档案。 如蔡邕《戍边上章》言:“触冒死罪,披散愚情,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15]奏章、玺书俱为公文档案,可知东观也藏有汉代文书。 上行文书藏于秘府,下行文书也有专门储藏之处,都要复制存档并有专人管理[8]216-232。
王充曾担任基层文官,是其能够阅读节录文书的前提。 根据《须颂》《齐世》等篇的记载,《验符》篇应作于章帝朝。 《自纪》篇言:“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为从事。”[3]1189《后汉书·百官志》云:“有功曹史,主选署功劳。”[14]3621可知功曹是以选举为主的基层文官。 在功曹之后,王充在章帝朝曾出任过治中一职。 《后汉书》本传称其“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14]1630。 在章帝元和、章和年间,王充由会稽郡一路向西,辗转丹阳郡、九江郡、庐江郡,最终在时任扬州刺史董勤征辟之下,成为董勤幕府中的一员佐吏(“从事”),随后又升迁为刺史极为倚重的副手(“治中”)。 对于“治中”,《通典·职官》载:“治中从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众曹文书,汉制也。”[16]据此,治中掌管“众曹文书”。 身为治中的王充既有掌管众曹文书的职责,那么自然有权利审阅官府公文档案。
至此,可以作出如下判断:
第一,《验符》篇“庐江湖水出金事件”展示的是一个独特的文本形态。 它的独特性在于一改《论衡》以论辩开篇的常态,以叙事代议论,用叙事的方式编纂成文,而这与文本自身的叙事属性密不可分。 王充是将这一文本进行了节录与转写,但基本保留了文本的原貌。
第二,“庐江湖水出金事件”是以文书为基础形成的衍生文献,是王充编辑处理后的二手文献。尽管是二手文献,但却能够借此窥见汉代文书的原本样态。 这种判断的依据是文本中保留了大量文书原文。
第三,因为汉代文书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唯有掌管文书档案的官员才能够审阅文书,由此,王充的官吏身份便应得到重视。 然而以往研究大多对王充官吏身份略而不谈。 这是《验符》篇被视为伪篇的原因。 可见,身份层面的偏颇可能会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
三、宣汉:王充征引文书的动因
对学者来讲,引文既是其知识结构的表征,也是其学术理想、文化心态的窗口。
王充征引文书,与匡正当时的是古非今论调有关。 《超奇》篇载:“俗好高古而称所闻,前人之业,菜果甘甜,后人新造,蜜酪辛苦。”[3]615《齐世》篇载:“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3]809《案书》:“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3]1173在王充看来,这种厚古薄今的论调,固然与“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3]811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儒家经典占据思想界正统地位的原因。
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经传之书,无论从素材层面,还是立意角度,皆以上古三代为准绳。 与之相比,汉家之事反倒被视为小道。 《须颂》篇载:“世见五帝、三王为经书,汉事不载,则谓五、三优于汉矣。”[3]851《谢短》篇言:“二尺四寸,圣人文语,朝夕讲习,义类所及,故可务知。 汉事未载于经,名为尺藉短书,比于小道。”[3]557-558《齐世》篇载:“世俗之性,好褒古而毁今,少所见而多所闻,又见经传增贤圣之美,孔子尤大尧、舜之功,又闻尧、禹禅而相让,汤、武伐而相夺,则谓古圣优于今,功化渥于后矣。”[3]812为此,王充主张“经传汉事”,并对“宣汉”之人甚为推崇:“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 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今上上至高祖,皆为圣帝矣。 观杜抚、班固等所上《汉颂》,颂功德符瑞,汪濊深广,滂沛无量,逾唐、虞,入皇域。”[3]821-822
王充征引文书正是出于宣汉的考虑。 与儒家经典相比,文书有着鲜明的宣汉意味。 从主题来讲,文书都以汉代社会的政治议题、现实事件为着眼点。 具体而言,有美政、经济、立嗣、战争、祭祀、灾异、风俗、祥瑞、官吏任免、文化事业等多个范畴,但它有一旨归,即围绕汉事展开论述。 从素材来看,王充征引节录的文书大都以汉事为主。
《验符》篇以外,《论衡》全书对文书有多次征引。 《宣汉》篇载:
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凤皇集于太山,后又集于新平。 四年,神雀集于长乐宫,或集于上林,九真献麟。 神雀二年,凤皇、甘露降集京师。 四年,凤皇下杜陵及上林。 五凤三年,帝祭南郊,神光并见,或兴于谷,烛耀斋宫,十有余刻。 明年,祭后土,灵光复至,至如南郊之时。 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 其年三月,鸾凤集长乐宫东门中树上。 甘露元年,黄龙至,见于新丰,醴泉滂流。 彼凤皇虽五六至,或时一鸟而数来,或时异鸟而各至,麒麟、神雀、黄龙、鸾鸟、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时,神光灵耀,可谓繁盛累积矣。[3]820
宣帝朝多祥瑞。 上文是对宣帝朝祥瑞的一次集中书写。 因为文中论及的都是祥瑞之事,其素材源于官府文书当无疑。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多处记载与《汉书》有出入。 其一,《宣汉》篇言:“孝宣皇帝元康二年,凤皇集于太山,后又集于新平。”对此,《汉书·宣帝纪》载:“(元康二年)三月,以凤皇甘露降集,赐天下吏爵二级,民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鳏寡孤独高年帛。”[17]255《汉书》未言凤凰集于何处,只是笼统地说“降集”。然《汉书》载元康元年宣帝所下诏书中却有“乃者凤皇集泰山、陈留,甘露降未央宫”[17]253之语。 由于《汉书·宣帝纪》未明言元康二年凤凰究竟所集何处,故不能准确判定王充记叙是否有误,但二书文字出入却显而易见。 其二,《宣汉》言:“明年,祭后土,灵光复至,至如南郊之时。 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 其年三月,鸾凤集长乐宫东门中树上。”据上下文,此处应指五凤四年事,然《汉书·宣帝纪》五凤四年未载甘露神雀降集延寿万岁宫之事。 至于“鸾凤集长乐宫东门树上”,《宣帝纪》记为五凤三年之事。 《汉书》载宣帝五凤三年诏书云:“甘露降,神爵集。 已诏有司告祠上帝、宗庙。 三月辛丑,鸾凤又集长乐宫东阙中树上,飞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余刻,吏民并观。”[17]266-267据此,首先可证实《论衡·宣汉》等篇章涉及祥瑞的内容源于文书,从《论衡》与《汉书》所引诏书文字高度重合性上得以印证,王充是对诏书文本进行剪裁后纳入自己的文章之中。其次,王充对某些时间的记载与班固有差异。“鸾凤集长乐宫东门树上”一事,《论衡》系于五凤四年,《班固》记为五凤三年,便是明显的例子。
对于《论衡》与《汉书》的差异,黄晖在校释《论衡》时已经有所揭示:“仲任述《汉事》,多不同《汉书》。 班作《汉书》,与王作《论衡》同时,仲任不得据以为文。”[3]749如此看来,《论衡》与《汉书》记载时存在的具体差异,也可归结为素材来源不同的原因。 这意味着,不仅对当朝事件,对于前汉史事的记载,王充也有自己独特的材料来源。 同时,尽管王、班二人记载祥瑞时间有出入,但王充所依据的素材为官府文书则可以确定。
为纠正俗儒厚古薄今的思想,王充征引文书时常与前代作比较。 具体而言,王充擅长运用对比的方法,将经传之事与汉事熔裁为一体,从而实现其宣汉的旨归。 例如《恢国》篇载祥瑞之事:
黄帝、尧、舜,凤皇一至。 凡诸众瑞,重至者希。 汉文帝黄龙、玉杯。 武帝黄龙、麒麟、连木。 宣帝凤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黄龙、神光。 平帝白雉、黑雉。 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连木、嘉禾,与宣帝同,奇有神鼎、黄金之怪。 一代之瑞,累仍不绝,此则汉德丰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间,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 四年,甘露降五县。五年,芝复生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 前世龙见不双,芝生无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龙并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县,德惠盛炽,故瑞繁夥也。 自古帝王,孰能致斯?[3]830-831
祥瑞是盛世的象征,也是君臣合演的一出政治戏码。 清人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两汉多凤凰”条中指出:“按宣帝当武帝用兵劳扰之后,昭帝以来与民休息,天下和乐;章帝承明帝之吏治肃清,太平日久,故宜皆有此瑞。 然抑何凤凰之多耶? ……得无二帝本喜符瑞,而臣下遂附会其事耶?”[18]赵氏已经意识到,宣帝、章帝的喜好,是二人任期内祥瑞层出不穷的原因。 辛德勇进一步指出:“所谓降祥效灵之天人感应,本来都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所做牵强附会。”[19]值得一提的是,《恢国》篇对祥瑞的列举,无论从数量还是种类层面,汉代都远胜前朝,从而得出汉德丰雍、德惠盛炽的结论。
在王充笔下,汉事大有反客为主之势。 他将经书与文书进行剪裁成文时,有着明确的指导思想:宣汉。 在宣汉理路的指引下,经书成为陪衬,汉事成为主体,这与当时学界通行的厚古薄今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王充要凸显汉代的主体性,便需要挖掘素材中的宣汉意味,其征引文书也是着眼于此。 其将当代素材用于文章写作,不仅是素材层面的创新,更是写作理念的“革命”。 此举致力于匡正儒生文必称三代、语必及五帝的复古观念,是从素材到理念的全面纠偏。
四、士大夫:王充身份重估
王充的基层文官身份使其能够掌握文书,这是化公文为素材的前提与基础。 尤其考虑到,“庐江湖水出金事件”是“永平十一年”“庐江郡”进献祥瑞之事,永平十一年至元和三年,时隔近20年,庐江郡隶属扬州部。 若不是担任扬州刺史的治中,王充很难有机会审阅这批年代久远的公文。
作为掌管文书的技术性官僚,王充能够审阅、熟悉、掌握公文档案,其社会身份有着鲜明的“吏”的属性。 然而,以往的《论衡》研究对此却不够重视。 学者们大都先入为主地将王充视为“文人”。 结果就是,作为“文人”的王充得到关注,作为官吏的“王充”却几无涉及。 实际上,王充既是文人又是官吏,两种身份是融合统一的。 如果忽略官吏只谈文人,便意味着研究视角的偏颇。 比如有学者指出,王充“重视有助于世事、教化的实用文体,轻忽文学的审美趣味,使得王充眼中的文人偏离了我们熟知的文人概念”[2]103。 对此,笔者认为大致有三点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一,从社会身份角度来讲,王充首先是基层官吏,其次才是文人。 最典型的例证是《谢短》篇中王充对文吏的三十问,“三十问”都是具体而微的实际问题,这表明王充对吏道已颇为纯熟。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王充多次表达对文吏的不满与对“鸿儒”的向往,但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文吏,其所面对的也是基层小吏所要应付的琐碎的日常事务。
其实不止王充,汉代文人的身份普遍带有复合性的特征。 阎步克将“文人”与“官员”融合的文士称为“士大夫”,他指出汉代“亦儒亦吏”“一身二任”的学者型官僚是政坛的主导[20]21。 这一观点的精当之处在于对汉代文士“官吏”“文人”双重身份的揭橥与重视。 而王充之所以注重实用性文体,正是因为他的官吏身份。 《对作》篇言:“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3]1183王充把《论衡》《政务》二书与唐林、谷永所上的章奏视为同一性质的文章,都以直面现实为特色,以辅政安民为旨归。 王充将其概括为“陈得失,奏便宜,言应经传,文如星月”[3]607。 据此,王充是将自己所撰之书视为对汉代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的结集,而其选取的显然也是与谷、唐二人相同的官吏视角。 官吏视角与辅政义务,意味着王充所拥有的是士大夫的立场[20]10。 也就是说,美善教化、移风易俗是王充的本职工作与分内之事,明乎此便不难理解其对实用文体的崇尚。
第二,具体到“文人”概念,尽管“文人”的名称没有变化,但王充视野中的“文人”与后世意义上的“文人”之内涵外延已有天壤之别。 冯天瑜将概念演变史的研究称为“历史文化语义学”[21]。为此,梳理《论衡》中的“文人”概念便显得尤为重要。 观察《论衡》文本,我们能够发现王充对“文人”有着较多论述,但总体可分为狭义的“文书之人”与广义的“文章之人”二类。 先看文书之人。《超奇》篇载:“故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3]607此处的“文人”便特指“文书之人”。 他对这类文士的定义是“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则传书是其撰写文书的素材,上书奏记才是其目的所在。 文书立足于当代的社会问题,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即“州郡有忧,能治章上奏,解理结烦,使州郡连事”。 由此可知,狭义的“文人”指的就是撰写“文书之人”。广义的“文人”是指“文章之人”。 《案书》篇载:
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 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 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 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3]1174
在《案书》篇中,王充所列举的文士既包括谷永、唐林、周长生等“文书之人”,也涵盖刘向、扬雄、班固等汉代的文章大家。 尤为重要的是,在提到班固、杨终、傅毅等人时,王充指出他们撰写的赋颂,可比美屈原、宋玉;他们撰写的记奏,可匹敌唐林、谷永。 这是“广义文人”即“文章之人”的有力证据。 “文章”的含义广阔宽泛,既可以指代实用性的文书,也包括审美属性更强的赋颂。 王充将偏审美的赋颂与偏实用的记奏混为一谈,就意味着他所理解的“文章”兼容两种类别,相应的,“广义文人”便是能够撰写多种文章的文士。 王充并没有将“文人”与审美文本相联系。
第三,身份与作品密切相关。 王充的身份由“儒生”而“士大夫”,创作题材则由“疾虚妄”转为“颂汉德”。 从王充对待祥瑞态度的转变也能看出,王充的创作主题已经由“疾虚”转为“颂汉”。 尽管其自称《论衡》为“疾虚妄”之书,但不可否认的是“颂汉”主题的作品在书中占有很大比重。 从创作时间来看,“颂汉”类文章大都作于中年以后。 可以说,创作主题的改变,与其年龄的增长有关,也与身份的转变有关。 王充作品中的自我矛盾,是其身份由“儒”到“吏”的反映。 随着时间的延伸,王充对基层文官的身份已经由排斥转为认同。
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潜移默化。 尽管王充对“文吏”颇多非议,但他已经逐渐成为一名纯熟的“儒吏”、一名士大夫,而文本主题早年“疾虚妄”、晚年“颂汉德”,正是这种转化的反映。
王充“工具意识”的凸显,既有外界塑造的痕迹,也有其自我工具化的原因。 前人研究的问题首先是对这一身份转型的忽视,其次是将《论衡》视为封闭的、静态的文本。 实际上,《论衡》成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其个人的心灵史。 只有意识到《论衡》是思考的过程,才有可能免于成见的障蔽。
结语
对公文的征引说明王充的身份具有复合性。他不仅是后世学者视野中的“文人”,更是东汉王朝的一名基层文官。 官吏的身份在给予王充相应职责的同时,也赋予其审阅公文、查阅档案的权利,这是王充将公文化为素材的前提与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王充身份更贴切的表述,应当是融“文人”与“官吏”于一身的“士大夫”。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汉代文士身份较为复杂,这是以往研究中容易忽略的部分,也是秦汉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