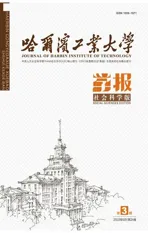从“孔颜乐处”看儒家解决圆善的独特思路及伦理性质
2022-11-25王春梅
王春梅
(长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64)
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难题。 康德否定了伊壁鸠鲁、斯多亚学派对圆善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以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圆善问题[1]134-136。 牟宗三认为康德未能真正解决圆善问题,他提出了以传统儒释道三家的圆教模式解决圆善问题[2]263-274。 杨泽波认为牟宗三也没有真正解决圆善问题,他甚至认为在儒家这里德福不一是常态,圆善问题根本无解[3]53。 至此,圆善问题陷入了难以解决的困境之中。 然而回到孔子,孔子并没有认为德福不一,相反,他提出了德福兼备的“孔颜乐处”,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伊壁鸠鲁、斯多亚学派、康德等人解决圆善问题的方式。
一、当代圆善问题的引入及其面临的困境
牟宗三的《圆善论》将圆善问题引入了中国学界。 在《圆善论》,牟宗三认为康德以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并不能真正解决圆善问题,在他看来,上帝既没有对与德相配的自然进行重新调整,也没有对其进行重新的创造,与德相配的那个“自然”还是那个“自然”,只是靠引入上帝就使它们相谐和,这让人难解[2]240。 牟宗三依据中国儒释道三教圆教智慧提出了解决圆善问题的方案,这一方案从两个方面解决圆善问题:一方面是以无限智心保证成德,当然,无限智心不仅可以保证成德的一面,也是确保德福一致的根基[2]263;另一方面是由无限智心进至圆教保障成福的一面[2]265,即以“诡谲的即”确保德福一致[2]274。 对于牟宗三来说,无论是佛道两家的圆教还是儒家的圆教,解决圆善问题都需要两个步骤:一是依靠“无限智心”成其德,二是依靠“诡谲的即”成其福,德福相即达成圆善。 儒释道三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无限智心”与所成的德。 佛家的“无限智心”是般若智、如来藏自性清净心,所成的德是般若、法身、解脱三德。 道家的“无限智心”是玄智、道心,所成之德乃玄德。 儒家的“无限智心”是仁心、纯粹理性的心,所成之德乃道德。 就儒释道三家而言,牟宗三更为重视儒家之圆教,因为儒家有“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的道德宗骨。 虽然如此,但总的来说,牟宗三认为儒释道三家以圆教解决圆善问题的路径基本一致,他们的区别在于解决圆善问题的第一步即成德的方式不同,儒家是“纵贯纵讲”,讲德之创生,对一切德之存在有一根源性的说明,而佛道两家是“纵贯横讲”,不讲德之创生,只是说明一切德之存在。 无论是“纵贯纵讲”创生的存在,还是“纵贯横讲”说明的存在,都是关于德之存在,只解决圆善成德之一面。 真正解决圆善问题还必须进至“诡谲的即”,涉及自然存在,由此解决福之一面。①自然存在,牟宗三又称其为“法之存在”。 牟宗三在《圆善论》中说“般若之智德是就三千世间法而为智德,解脱之断德(断烦恼而清净为解脱,此亦曰福德,有清净之福)是就三千世间法而为断德,涅槃法身德是就三千世间法而为法身德(佛法身即九法界而成佛法身),主观面之德与客观面法之存在根本未曾须臾离,而幸福即属于‘法之存在’者(存在得很如意即幸福)。 在此圆修下,生命之德(神圣的生命)呈现,存在面之福即随之(此福必须就存在言,与解脱之福德之福不同,福德仍属于德,是分析的,由解脱而即分析出清净之福)。”在这里,牟宗三认为幸福属于“法之存在”,说明这一幸福是与自然存在相关的物质幸福。 此外,牟宗三认为“此福必须就存在言”,说明这一存在也是指自然存在,因为如果这一存在指道德存在,那么,这一福也可以由德分析出,是福德之福,牟宗三明确指出此福不是福德之福,因此这一存在也是自然存在,福是与自然存在相关的物质幸福。
牟宗三提出以“无限智心”和“诡谲的即”解决圆善问题,对于这一方案,杨泽波却认为牟宗三是以“诡谲的即”“纵贯纵讲”解决康德的圆善问题[4]22。在杨泽波看来,无论是“诡谲的即”,还是“纵贯纵讲”,所成的幸福都是道德幸福,并不是康德圆善所保证的物质幸福[3]47。 也就是说,杨泽波认为康德提出的圆善是道德与物质幸福的一致,而牟宗三所建构的圆善则是道德与道德幸福的一致,牟宗三以道德幸福代替康德的物质幸福并没有真正解决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杨泽波不仅否认牟宗三对圆善问题的解决,而且认为圆善问题根本无解[3]55,一定意义上杨先生彻底否定了圆善解决的可能性,使圆善问题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杨泽波之所以得出圆善无解这一结论,主要在于他认为儒家承认德福不一。 因此,儒家有没有承认德福不一就成了圆善能否解决的关键所在。
二、儒家承认的是德福不一还是德物不一?
杨泽波认为,在传统儒家看来,“有德之人未必有福,德福不一是一种常态”[3]48。 杨先生认为儒家所承认的是德福不一,但是,从杨泽波论证的几方面内容来看,他论证的儒家所承认的德福不一其实是德物不一。②本文尽管不完全同意杨泽波对物质、物质幸福的相关论述,但是为了讨论的方便,仍沿用杨泽波的物质、物质幸福这一说法。 杨先生使用的物质这个概念是宋明理学理气之分的气,是康德讲的自然,其物质幸福是与“气”相关的幸福,是与自然相关的幸福,正如他在《贡献与终结:牟宗三儒学思想研究》中所说的,“我使用‘物质’这个概念一般与‘幸福’相连,特指一种与精神幸福相对的幸福,即‘属于气的’(牟宗三语)那种幸福。”“我将康德这种由自然而来的物质生活愿望的满足所达成的幸福称为‘物质幸福’。”杨先生使用物质指的是气、自然,物质幸福指的是与气、自然相关的幸福,与这样的物质、物质幸福相对的是道德、道德幸福,本文正是在杨先生此义上使用物质、物质幸福。 但杨先生又将这样的物质、物质幸福与精神、精神幸福相对,如此就会产生一定的问题,众所周知,朱子的心、情属于理气之分的气,这样的物质可以说与理相对,包括康德讲的自然,可以说与自由、道德相对,但并不是说与精神相对。 杨先生如此讲易产生概念的混乱,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学术纠纷,如杨虎博士驳杨泽波的《论康德与牟宗三圆善论的幸福指向》,以及曾海龙博士的《论康德与牟宗三圆善论的幸福指向》都与此相关。
首先,从杨泽波论证儒家承认德福不一的依据来看,儒家其实承认的是德物不一。 杨泽波论证儒家主张德福不一的依据在于孟子的“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在杨泽波看来,“求在我者”讲的是道德的根据在“我”,如果求就可以得到,如果放弃就会失去;而“求在外者”讲的则是人爵一类的幸福,即使也去求了,但能不能得到却是由命决定的,这种求并不能保证必然能够得到[4]166。孟子讲的“求在外者”的确是人爵一类的名利,从杨泽波认为物质幸福是物质需要的满足来看[3]51,名利属于物质,与物质幸福相关,但还不宜直接等同于物质幸福。 孟子这段话实际表达的是道德与名利的根据不同,一个在内,一个在外。道德的根据在“我”,只要努力求德就可以得到它,而如果选择放弃,那就会丢失它,因此,求德必然能够成德。 而对于人爵等一些名利的东西,其根据在外而不在“我”,即使“我”依据道去求它,但能否得到,依然取决于命运的安排,因此,追求人爵等一些名利的东西并不必然保证能够获得它们。 也就是说,孟子在这里所表达的其实是德与名利不一,以杨泽波所言的物质、物质幸福来看,应该是德物不一,而不是德福不一。
其次,从杨泽波指出儒家承认德福不一的情景来看,儒家承认的也是德物不一,而不是德福不一。 杨泽波认为儒家“承认有德之人未必有福,德福不一是一种常态”[3]48,因为儒家认识到人类社会存在“圣人不能遇世”[3]48“有德之人会穷居”[3]48的情景。 就圣人不遇世而言,涉及的是圣人能不能实现自己人生价值、人生理想的问题,圣遇世,如尧舜禹,成就一番事业,相反,圣不遇世,如孔子、颜回、孟子,虽圣亦不能改变世道昏乱。 圣人遇世不遇世其相关内容的确与幸福相关,但若因圣人不遇世,由此就认为他们未能获得幸福,则是将物质等同于幸福了。 就有德之人穷居而言,涉及的是有德之人得到怎样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活条件的确关乎物质幸福,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物质幸福,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而已。
最后,杨泽波认为儒家“将德福不一的情况归于命”[3]48,其实,儒家“归于命”的也是德物不一,而不是德福不一。 在杨泽波看来,“归于命”的是“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的“命”,此“命是指‘非人之所能为’,也就是不由人的主观努力所能决定的情况”[3]49。 物质幸福是物质需要的满足,满足与否离不开人的主观愿望,亦即幸福多少与人的主观需要有关,因此,这里“不由人的主观努力所能决定的”只能是外在的、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不是与人主观需要相关的物质幸福。 杨泽波进一步认为对于这样的“命”,儒家主张“修身以俟之”[3]51,这里所“俟”的其实也是人爵等一类外在的、客观的名利,而不是与主体相关的幸福。 由于名利这类东西是外在的、客观的,“不由人的主观努力所能决定”,是求之在外的,故这类东西只能“修身以俟之”。 而幸福多少与人的主观需要有关,不能仅仅归于外在的东西而去“俟之”。
由于杨泽波对物质与物质幸福不分,结果将儒家承认的德物不一说成是德福不一。 也就是说,杨泽波得出儒家承认的是德福不一,其实是由于他将物质等同于物质幸福、将德物关系等同于德福关系的结果。 那么,物质究竟是否等同于物质幸福? 如果等同,那么,杨泽波由儒家承认德物不一,进而得出儒家承认德福不一就是合理的,以及由此否定圆善的可能性也是合理的。 而如果不等同,那么,儒家关于德福关系的思想就需要重新审视。
杨泽波认为物质幸福“是因物质需要得到满足所致”[3]51,依据他对物质幸福的这一看法,说明物质幸福不仅与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关,亦与人主观意愿相关,物质幸福不宜简单地等同于物质。 但是,杨泽波并没有对这样的物质幸福与物质进行严格区分,以至于将物质幸福从属于物质、等同于物质。 “与康德圆善相关的幸福属于物理自然方面的事,用理学家的话说是属于‘气’的,换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属于物质的。”[4]187按照杨泽波前面的论述,与德相配的物质幸福是物质需要的满足,但在这里,杨泽波却认为与德相配的物质幸福是属于物质的。 杨泽波对物质幸福论述的前后转变,说明他并没有严格区分物质幸福与物质,导致他前后论述的物质幸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在前一论述中,物质幸福是物质需要满足,物质仅仅是物质幸福的组成部分,物质幸福能否达成还与主体是否满足相关,而在后一论述中,物质幸福则从属于物质、完全由物质决定,物质幸福与主体意愿的相关性被消解了。
杨泽波一方面认为与德相配的幸福是对自然生活或物质需要的满足,另一方面却将与德相配的幸福等同于自然、从属于物质。 在前一种语境下物质幸福与物质并不相同,而在后一种语境下物质幸福则从属于物质、物质幸福等同于物质,正是在后一种语境下,杨泽波将儒家承认德物不一转换成了儒家承认德福不一。
新时期高等教育改革,必须是追求更高质量的教育,并以更高质量为核心,深化教育改革创新。高校要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和人人成才观念,着力创新教育教学方法,重视拔尖人才培养,以全面提高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
其实,对幸福的论述前后不一问题,早在康德论述德福一致的时候就存在了。 康德认为与德相配的“幸福是尘世中一个理性存在者的状态,对这个理性存在者来说,就他的实存的整体而言一切都按照愿望和意志进行,因而所依据的是自然与他的整个目的,此外与他的意志的本质性规定根据的协调一致”[1]132。 在这里,康德首先论述幸福是人满足于自身的实存状态,或者说是人对自然生活的满意。 这一论述说明幸福不仅与自然相关,也与人自身的愿望有关。 但他随后论述德福一致时,并没有论述幸福与道德的协调一致,而是论述自然与道德的协调一致。 也就是说,康德并没有严格遵守他自己对幸福的论述,而是以自然代替了幸福(对自然的满足)。 事实上,幸福虽与自然相关,但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对自然的满足。 幸福的要义在于对自然的满足,如果将幸福等同于自然,以自然代幸福,幸福的要义就丧失了。
康德这种以自然代幸福的做法,将本来是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转变成了德与自然一致的圆善问题。 那么,谁又能保证自然与德相配? 唯有上帝。 于是,康德不得不依靠基督教传统的最高存在者上帝来保证德与自然的一致[1]136。 由自然代幸福使得康德不得不寻求上帝存在以保证德福一致。 也就是说,康德在解决德福一致问题时,将德福关系转换为德与自然的关系,将德福一致转变为德与自然的一致,这一转变使康德不得不借助基督教传统,依靠上帝存在解决德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因此,对于康德来说,与其说基督教宗教背景决定了他依靠上帝解决圆善之福的达成,还不如说,康德将德福一致转变为德与自然一致造成他不得不依据基督教传统的上帝存在解决德与自然的一致。 实际上,即使康德依靠上帝存在解决了德与自然的一致,但从幸福是对自然生活的满足来看,康德仍然未能真正解决德与幸福的一致,毕竟还未确定人们对此自然是否满足。 因此,只有保证人对自然的满足,才是达成幸福的不二法门。
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却认识到有德未必有名有利,认为德与名利不一,认识到德与自然物无法一致。 当然,儒家也期盼德与自然物一致,但他们不是追求德与自然物的一致,而是坦然承认德与自然物不一是常态,儒家的这一认识彰显了儒家独特的人文特质。 杨泽波认为儒家承认德福不一,在一定意义上揭示了儒家这一独特的人文特质,只不过杨泽波是顺着康德以自然代幸福的思路,并没有区分自然物质与物质幸福的不同,结果他将儒家承认德物不一而具有的人文特质变成了儒家承认德福不一而具有的人文特质。
总之,康德未区分自然与幸福的不同,他将德福一致的圆善问题转变成了德与自然和谐一致的问题,最终依靠上帝保证德与自然和谐一致而走向了道德的神学。 杨泽波也未区分自然物质与物质幸福,结果将儒家否定德与自然物一致的可能性转变成了儒家否定德与幸福一致的可能性,最终否定了圆善解决的可能性。 将自然物质与幸福等同,前者为了圆善的达成而走向了道德神学,后者则彻底否定了圆善的可能性。 因此,圆善问题之所以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关键在于人们将幸福等同于其对象自然物。 也就是说,圆善能不能得到合理解决的关键不在于德之一面,而在于福之一面。 德虽然在现实中极难达成,但成德毕竟是自律、由己,付出努力总可以达成。 而福之一面则与客观的物质生活条件相关,如何保障达成福之一面的确存在诸多难题,以至于时至今日,仍然未能在理论上真正解决幸福的达成问题。
三、“孔颜乐处”:儒家式的德福兼备
康德以自然代幸福追求德福一致,使圆善问题的解决走上了不归路。 杨泽波以物质代幸福,彻底否定了圆善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传统儒家并没有将幸福等同于外在的自然物质,他们虽然承认德与自然物不一,但并没有否认德与幸福的统一,相反,他们认为德福可以兼备,这就是“孔颜乐处”: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从上述材料来看,德如孔子、颜回,他们并没有得到美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而是处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的贫困之中,针对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德物不一,但却不能说德福不一,因为只有当孔子、颜回不满足于这样的物质生活条件,才能说德福不一。 然而长期以来,人们简单地将幸福等同于美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没有认识到幸福与物质生活条件之间的不同,没有认识到幸福不仅受客观物质生活条件的影响,更受人的主观物质生活态度的影响,从而认为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孔颜二人得到的只能是苦,结果将孔颜二人在这里所获得的乐解释为伦理幸福[5]19或道德幸福[4]175,并认为这样的伦理幸福或道德幸福是他们二人超越[5]19或辩证地转化[4]64了物质生活之苦获得的。 可见,传统上之所以将“孔颜乐处”解释为道德与物质幸福不一,其关键在于将“孔颜乐处”之道德与物质生活条件的不一等同于道德与物质幸福不一,并进一步将“孔颜之乐”解释为道德幸福或伦理幸福。 因此,一旦将自然物质等同于物质幸福,将德福关系等同于德物关系,就会误解“孔颜乐处”,使圆善问题无解。
从杨泽波认为物质幸福是对物质需要的满足来看,物质幸福不仅仅与物质生活条件有关,更与主体意愿有关,主体欲望强烈,山珍美味都不幸福,主体清心寡欲,粗茶淡饭亦在幸福之中。 回到“孔颜乐处”上述文本之中,对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物质生活条件,孔子乐在其中;对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不堪其忧”,而颜回“不改其乐”,也乐在其中,孔颜二人满足于他们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获得物质幸福[6]67。
面对在别人看来是苦的物质生活条件,孔颜二人却能满足于此而获得幸福,原因何在? 这是因为孔颜二人能够做到“知足而无欲”“让而有礼”,由此达到“贫而如富,贱而如贵”、贫贱富贵如一的人生境界,这样的人生境界能使他们面对一切物质生活条件均能获得物质幸福[6]68-69。也许有人会问,孔颜二人为什么能够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 在濂溪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就在于他们体会到了德性的价值,从而达到内心的安泰,由内心安泰而达“知足而无欲”,满足于一切物质生活条件,从而将富贵与贫贱化齐[7]33。 有德的人不仅可以满足于富贵而获得幸福,也可以满足于贫贱而获得幸福。 “孔颜乐处”正是说明有德的人能够满足于贫贱而获得幸福。
“孔颜乐处”,孔颜二人的德性使他们能够在贫贱中依然获得幸福,更何况富贵乎? 故儒家由“孔颜乐处”的道德修养完全可以实现既有德又有福,从而达成圆善。 不过,儒家以“孔颜乐处”所达成的这种圆善与康德依靠灵魂不朽、上帝存在所达成的圆善在内容与方式上并不相同,表现在:
首先,儒家圆善与康德圆善成德的方式不同。康德设定灵魂不朽以成德,而儒家通过道德修养以成德。 康德认为人受感性自然的影响,是有限的存在者,不可能在今生今世达到德的完备,故设定灵魂不朽以趋近。 而在儒家看来,通过道德修养可以达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进而做到坚守道义而“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以至于“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而成德。
其次,儒家圆善与康德圆善成福的方式不同。康德设定上帝存在保障幸福的获得,儒家通过道德修养保障幸福的获得。 康德所追求的幸福是外在自然生活条件的美好,这种幸福依靠道德修养是无法解决的,故康德不得不设定上帝存在,依靠上帝的力量,达到自然与道德的和谐一致。 儒家则清醒地认识到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不由己,故他们不再通过追求外在美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成其福,而是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通过道德修养提升人生境界从而转变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态度,化贫贱富贵为一,满足于一切物质生活条件成其福。
最后,儒家圆善与康德圆善的内容不同。 康德圆善的内容是德福一致的圆善,而儒家圆善的内容是德福兼备的圆善。 康德认识到道德与幸福属于不同领域、不同性质,他以自然代幸福,自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客观的,可以准确量度,在康德看来,德是对客观的道德法则准确无误的遵守,也是可以准确量度的,所以,康德所言的圆善是道德与幸福按比例的分配,也就是道德与自然的准确一致。 而儒家所言的圆善则是既有德又有福、是德福兼备的圆善。 虽然儒家致力于道德修养以成德,也有客观的一面,认为德性亦有分定,“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孟子·尽心上》),可以量度,但是儒家并没有说量度幸福,因为幸福主要取决于一个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满足程度,这是无法客观量度的,故儒家只是加强道德修养,在德的作用下转变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不是片面地追求外在的物质生活条件成其福,而是就当下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满足于此而获得幸福。 因此,儒家不再追求道德与幸福准确地相配,而是追求既有德又有福的德福兼备。
上述康德与儒家圆善思想的不同是在自然物质与物质幸福区分的基础上得出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儒家独特的伦理性质。
四、从“孔颜乐处”看儒家的伦理性质
与康德设定灵魂不朽、上帝存在所保证的圆善相比,儒家以“孔颜乐处”所开辟的圆善进路有其独特之处。 对于一个人来说,虽然达成儒家这样的圆善也异常艰难,但毕竟儒家为每个人提供了一条通过道德修养达成圆善这样完全可行的路径,由此彰显出儒家独具特色的伦理性质。
(一)务实而圆熟
康德通过设定上帝存在保障自然与道德的和谐一致,而儒家则清晰地认识到德在内,物在外,求德由己,求物不由己,故不强求德物一致,坦然承认德物不一是常态。 虽然儒家也希望邦有道、社会走上正道,期盼有德的人富且贵、过上美好的物质生活,“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福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 但儒家终究没有追求德与自然存在的一致,表现出儒家伦理思想客观、务实的一面。
孔颜二人有德而生活在“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箪食、瓢饮、陋巷”的条件下,使儒家认识到有德的人未必会有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德物不一是常态。 但儒家并没有因为德物不一就放弃对德福兼备的追求,他们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在德性的作用下不再苛责具体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满足于德之所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从中享受到幸福,达到德福兼备。 儒家达成圆善的方式与康德有着明显的不同,康德是将幸福等同于自然,依靠上帝存在保证德与自然和谐一致,从而达到德福一致。 儒家在认识到德物不一的情况下,不是简单地将幸福等同于物质,而是将物质与幸福区分对待,在物质条件差的情况下能够转变对待物质生活条件的态度,满足于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从而获得幸福,达成德福兼备的圆善,彰显出儒家伦理思想圆熟的一面。
儒家的伦理思想之所以能够显现出圆熟的一面,就在于其独特的幸福观。 与康德将幸福等同于外在自然的幸福观不同,儒家的幸福观返回到人自身,着重于解决人自身的满足,主体满足即幸福。 霍华德·金森博士二十多年前通过调查研究得出:“那些具有达观生活态度的人却能获得持久的幸福,他们不管面对怎样的物质生活条件,都能泰然处之而获得幸福。”[6]66这正是儒家两千多年前“孔颜乐处”所体会到的幸福,由此可见儒家对幸福理解早熟的一面。
(二)实践的证知而非理论的辨知
儒家由“孔颜乐处”达成圆善,显示出其伦理思想圆熟的一面,这种圆熟是以实践的证知达到,而不是以理论的辨知达到的。 由实践的证知体会到德福兼备的“孔颜乐处”,需要亲身的实践体验,也就是说,没有相应的实践体验,很难理解到“孔颜乐处”是德福兼备的圆善。 因此,对于“孔颜乐处”的误解,一方面从理论分析来看,固然是人们未能将自然物质与物质幸福区分开来,将德福关系等同于德物关系所致;另一方面则与“孔颜乐处”本身属于实践的证知有关。 “孔颜乐处”既不是像康德一样从理论上阐释清楚此“乐”是什么以及此“乐”如何达成,也不是像霍华德·金森一样通过调查研究在理论上证明一个人只有达观的生活态度才可以获得长久的幸福,它只是一种实践的证知,后人只有达到这样的实践,才能体会到“孔颜乐处”这种满足于其所处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乐”,如濂溪、明道达到了这样的实践,故濂溪有“乐乎贫”的证知语,明道有“贫贱乐”的证知语。 如果没有达到这样的实践,即使面对濂溪的“乐乎贫”[7]33、明道的“贫贱乐”[8]证知语,人们也会质疑这种“乐”是否是对贫贱的“乐”,毕竟在他们看来,贫贱是苦的,无法获得乐。 这样,仅仅从实践体证“孔颜乐处”,一旦达不到这一实践,就既不能体会到这种乐,也不能认识到这种乐的存在。
因此,对于“孔颜乐处”这样实践的证知,完全有必要补上理论辨析的环节,使其不仅能够保持实践证知的圆熟性,而且同时兼具理论辨知的明晰性。 为“孔颜乐处”补上理论的辨知,关键是辨明德、乐、物(物质生活条件)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孔颜乐处”中,首先辨明德与物的关系,明确德与物是相互独立的,德是德,物是物。 其次辨明乐与物的关系,明确乐与物相互联系,物是乐的对象,乐指向物,而不是超越的、辩证的转换物。 最后辨明德与乐的关系,明确德与乐也是相互联系的,德是乐形成的原因,德转变了人对物质生活的态度,使人能够满足于一切物质生活条件得其乐,达成德福兼备。
(三)理想的人生境界而非完备的理论体系
儒家“孔颜乐处”的圆善与康德依靠灵魂不朽、上帝存在而保证的圆善不仅在达成的内容与方式上有所不同,而且达成的方法与路径也有所不同。 “孔颜乐处”达成圆善的方法与路径是实践的证知,而康德依靠灵魂不朽、上帝存在达成圆善的方法与路径则是理论的辨知。 儒家与康德达成圆善的方法与途径的不同,决定了彼此所形成的圆善形态亦有所不同,“孔颜乐处”形成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式的圆善,而康德依靠灵魂不朽、上帝存在所形成的则是一种完备的理论体系式的圆善。
尽管康德依靠灵魂不朽、上帝存在所达成的圆善存在不无讨论的地方,而以这种理论方式所形成的圆善对现实的人生实践亦缺乏指导意义,但其在理论辨析方面的确比较完备。 儒家通过道德实践能够体会到“孔颜乐处”这一理想的人生境界,其对现实人生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其理论辨析不够,存在让人难以把握的一面,即使有往圣先贤体证与合理的解释,只要人们对其缺乏真实的实践,仍然很难得其正解,其现实的指导意义也因此而大打折扣。 对此,固然存在因实践不够而误解往圣先贤的思想,但反过来,如果“孔颜乐处”不仅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亦由此能够建构出完备的理论体系,这种误解即使存在,但至少会少得很多,甚至会没有。
因此,对于理想人生境界的“孔颜乐处”,有必要在其基础上建构完备的理论体系,通过系统的理论辨析,辨析清楚“孔颜乐处”达成圆善的内在理路,使人们即使在无法证知“孔颜乐处”的情况下,也能理解“孔颜乐处”这种圆善的存在,从而指引人们向“孔颜乐处”这种圆善前进。 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人类文明相互融合发展的一种趋向,也是中华文明走向世界的一种选择,亦是当代学人义不容辞的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