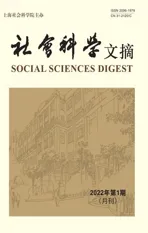顾明栋“摹仿论”诗学问疑
2022-10-26庄焕明刘毅青
文/庄焕明 刘毅青
“摹仿论”是西方诗学最重要的理论之一,不仅对西方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成为中国学界重点关注的理论。学界一般认为,中国诗学不存在西方诗学严格意义上的“摹仿论”。但旅美华裔学者顾明栋对此并不认同。为了论证中国诗学存在“摹仿论”,顾明栋在《中西文化差异与文艺摹仿论的普遍意义》中指陈学界关于西方“摹仿论”的研究只限于简单的二分法,认为西方“摹仿论”具有普遍性。其论证逻辑如下:首先,顾明栋重新解构了西方诗学“摹仿论”的定义,将摹仿归结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他认为西方诗学“摹仿论”不是建立在超验性与内在性分离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模型与复制之间的二元性上;其次,在承认中西诗学差异性的基础上,顾明栋强调“摹仿论”在中国传统诗学里不占中心位置,但肯定中国传统诗学中模型和复制模式的存在,与西方诗学柏拉图“摹仿论”在本质上并无差异。随后,顾明栋又在《中国美学思想中的摹仿论》中详细论述了中国“摹仿论”的特征:阐释了“穷形尽相”是中国诗学的意象摹仿,“离形得似”是中国摹仿论的审美理想,中国摹仿论经历了一个从意象性摹仿到叙事性再现的发展过程。可以讲,《中国美学思想中的摹仿论》是对《中西文化差异与文艺摹仿论的普遍意义》的深化,从实证的角度建构了既与西方“摹仿论”具有可比性又体现中国传统特色的“摹仿论”。但是,顾明栋的论证忽视了两点:第一,中西方观物方式的差异;第二,中西方诗学真实观的差异。我们认为,正是基于这两点,使得中国诗学没有往“摹形”方向发展“摹仿论”,而脱离了形式的摹仿并不是西方诗学意义上的“摹仿论”,即中国诗学中并不存在着西方诗学意义上的“摹仿论”。
中国传统的观物方式
“模仿”的本能或行为是早期人类文化所共同具有,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顾明栋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亦不例外。他举《周易》为例,认为《周易》的“观物取象”是圣人对天地万物的模仿结果:“‘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在该陈述里,譬如‘拟’(模仿)、‘形’(形状)、‘容’(外貌)和‘象’(再现,字面意义即画一个意象),这些词都是‘模仿’概念的变体。《系辞传》还进一步证实了‘爻’象的线条意象(虚线或实线)也起源于模仿:‘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象此者也。’”然而,顾明栋从西方观物方式的角度切入,忽视了中国传统的观物方式之特点,对《周易》的“观物取象”的理解亦有失偏颇。
《周易》的观物方式是观物之主要特征,而成其象。譬如《周易·文言》“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便是根据天地万事万物的主要特征分门别类,以六十四卦囊括天地万事万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易》卦象是作为一种抽象符号,以一对多,而不是西方诗学意义上的一对一“摹形”。
顾明栋对《周易》观物方式的片面理解,也影响了他对中国诗歌“比兴手法”的认知,误把“比兴手法”理解为摹仿手法。顾明栋认为中国诗歌是对自然界自发的回应,同时诗歌也是对所观察世界的模仿,两种思想并存,即诗歌除了是自发外,也是顾式“摹仿论”的模型复制模式,并引用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的一段话(“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以资证明。顾明栋是这样解释的:“刘勰的诗歌创作理论是以二元的移情表现论和摹仿再现论为基础。模仿包涵两种相关的意义,首先是对激发诗人灵感的自然界的模仿,其次是对在声音和语气相对应的语言层面的自然世界的模仿。”顾明栋之所以认为《文心雕龙·物色》是对摹仿的理论阐述,主要是因为其在讲情景关系时,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认为人的感情因景物而变,文辞因感情而生,并强调如何恰当地描写景物。
《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在延伸到中国诗学“诗言志”的过程中,“观”由观物之主要特征发展到观物之伦理,即儒家赋予了“观”以新内涵,由自然层面转移到伦理层面。在中国哲学里,“观”,不单有“眼观”,也有“心观”“静观”“反观”等丰富内涵。“观物取象”是观的方式影响下的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对其后的中国艺术构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自然在中国古代之“观”下,形成了两种解读,一种是表面的山水自然风格之美,一种是背面所隐含的内在规律。古人往往更看重后者,《易经》中的“立象以尽意”即是。因此,在中国古代,“观物取象”已超越了眼之所“观”,对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进入到“心观”“静观”“反观”等层次。
中国古代的“观物取象”之“观”,之所以有如此丰富的内涵,原因在于其主要建立在主客相融的基础上,而西方“摹仿论”则主要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中国哲学则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观”的目的在于把握天道规则,以人道合天道。因此,中国的“观物取象”重在主体的参与,主体除了仔细观察对象外,还必须注入自身的生命意志,即“心观”“静观”“反观”等主动行为,以达到提挈天地、把握阴阳的境界。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观物取象”实非西方“摹仿论”所追求之真实现状所能统摄。
中国诗学之真实观
西方诗学“摹仿论”有两大理论支柱:真实性和二元性。顾明栋已深入讨论过二元论,在此不赘叙。我们通常所讨论的“摹仿论”,主要是指柏拉图从本体论意义上阐发的摹仿概念。柏拉图认为艺术摹仿现实客体,现实客体只是理念世界的不完美的形象而已,真实与艺术是双倍隔断的、无法互动的、静滞的。亚里士多德则改造了柏拉图的摹仿论概念(没有彻底颠覆理式论),认为诗的真实性是存在的,诗人可以表现可能之真实,不一定是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承认艺术的本体论地位。即是讲,西方诗学“摹仿论”对真实性的定义,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顾明栋并未言及西方诗学“摹仿论”对真实性的不同定义,认为中国“摹仿论”大体上更接近柏拉图的思想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其理由在于,“首先,中国摹仿论起源于对意象和绘画的研究,并且绘画理论对文学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在古代,抒情诗一直是主要的文学形式,集中表达情感、印象、感知,而不是关注现实世界。第三,像柏拉图一样,中国的理论家们把文学、艺术领域的摹仿视为最终是对道(恒常的宇宙规则)的摹仿”。如按柏拉图的思想观念,中国诗学的艺术摹仿则丧失了内在合法性,因为它无法体现“道”的真实性。
事实上,中国诗学的“道”既是超验的又是内在的,个体可以通过艺术手段体现“道”的真实性,与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相似——诗人可以表现可能之真实。顾明栋为了解决如何把“中国诗学概念与柏拉图理念和亚里士多德艺术理想相联系”,他以艾布拉姆斯的摹仿论为参考,提出“与中国形而上学的首要原则具有的超验性和内在性本质相一致,道作为中国文学的艺术理想,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新古典主义理想一样,既是经验主义的也是超验主义的”。这种对中西“摹仿论”真实性的论述出现了悖论:一方面认为中国摹仿论更接近柏拉图摹仿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结合亚里士多德摹仿论观念,以契合中国摹仿论中的道的特征——既是超验的又是内在的。顾明栋也没阐明中国诗学对“道”的体认(中国诗学摹仿论的真实性),有别于西方摹仿论的真实性(真理)具有的理性主义倾向(对事物的精确认知),它是生命的感悟。
同时,顾明栋也没弄清楚宇文所安等人指出的中国诗学的“真实性”含义,中国诗学的“真实性”并不是顾明栋所认为的西方模仿再现之意。实质上,宇文所安等人指出中国诗歌的“真实性”,主要是从“诗歌是如何被接受”的角度提出的:西方诗歌一般被认为是虚构,不能涉及现实,一旦涉及现实,如时间和地点的介入,读者很难从诗歌获取一些隐秘的、更丰富和更令人满意的诗意;反之,中国诗歌一般被认为是非虚构,即使有虚构的可能性,中国读者也会视为是真实的。中西诗歌被接受过程中的差异,说明中西社会对诗歌“真实性”存在不同的理解。
此外,摹仿不是中国诗学的重点,只是起点,它不为中国古代学者所重视。中国诗人和画家,想要表达的往往不在诗画的具象中,而是诗画没有体现的地方——诗外意、画外音。这些都不是靠模仿就能获得,须重视诗人的存在、感悟和生发性。
由上可知,中国诗学存在摹仿的行为或观点,但摹仿与“摹仿论”是不同的两个维度:前者有借鉴的涵义,是初级的学习阶段;后者有理论体系支撑,并以此为准则。顾明栋试图论证中国诗学存在“摹仿论”,不过,从顾式“摹仿论”的推论来看,中国诗学中的摹仿观与西方诗学理论上的“摹仿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摹仿在中国诗学里只是起点,终究要被超越的,因此摹仿只能作为一种依附存在,无法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顾明栋把中国诗学摹仿观与“摹仿论”的理论架构一一对应,混淆了摹仿与“摹仿论”的区别。
重思比较诗学的逻辑起点
顾明栋之所以提出普遍意义的“摹仿论”之说,主要是响应了21世纪诗学的发展趋势并试图打破中西诗学中文化相对主义的藩篱。但实际上,中西文化在本质上是截然不同的。对此,叶维廉曾以蛙鱼人寓言说明不同文化的区别如同不同的模子。顾明栋认为,叶维廉模子论在这一系列的二分法中隐藏着的文化相对主义,并未能达成中西二分法比较的初衷——改变中国文论在西方所受的偏见和边缘化的局面。于是,顾明栋“希望详细分析诸多二分法中尚未被质疑的一个(这或许是文学和美学研究中最为基本的一个),那就是西方的模仿论与中国的非模仿论之间的对立”。由此可见,顾明栋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摹仿论”,是有意而为之。按他的说法,试图从中西诗学中广受认可的认知入手,解构看似牢不可破的定义,寻找一条中西共同诗学乃至世界诗学的基本规律。在此之前,不乏有学者有类似想法。顾明栋的步子迈得更大,直接跳出中西方二元论的框架,借用西方文论固有的能指,对其所指进行概念改造,拒绝承认“摹仿论”为西方文化独有之文化创新,否认“摹仿论”取决于超验性和内在性的分离,否认“摹仿论”取决于创世神的存在。因此,“摹仿论”在顾明栋的理论构建中,成为无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的全新的文化普遍主义,一种“世界诗学”的乌托邦构想。他想以此破除西方看待中国的惯有方式(无知、傲慢以及幻想)和非西方人民的自我殖民化问题。
另一面,顾明栋建构的普遍意义的“摹仿论”,也是为了纠正中国学者认识论的惰性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学思想中丰富的摹仿思想之所以没有获得学界的认可,主要是概念性和方法论方面的盲区造成的:“从观念上说,存在着中西传统、思维的二元对立这样一种先入为主之见。这种先入之见很容易导致在理解中西文学起源上的二元对立,即中国文学是自然产生的,而西方文学则具有模仿源头。从方法论上看,部分学者把中国文学思想看成铁板一块的整体,既缺少变化,也没有任何潜在思潮和逆动思潮。由于学者们假定存在一种主流的中国文学思想,他们收集资料时也往往有选择性的,以适应他们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从而排除了其他的想法和思想倾向。”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顾明栋的“摹仿论”是建立在解构西方诗学“摹仿论”真正涵义和片面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的,他想以这种理论统摄中西不同文化具体规律的尝试并不成功。在当下,他的这种尝试也不能解决中国古代诗学转向以及中国现代诗学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诸多危机:首先是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转向危机;其次是现代诗学建构的现代性危机;最后是后现代的解构危机。
尽管顾明栋可能知道中国古代诗学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转向危机和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现代性危机,但他仍从西方诗学概念名称出发提出“摹仿论”是具有普遍性的共同诗学。在笔者看来,顾明栋先预设了西方“摹仿论”具有普遍性,把中国古代诗学归附于西方诗学理论,再从中国古代诗学中寻觅相关材料,依此认为中国诗学中的“观物取象”就是西方的“摹仿论”。究其实质,是对中国文论缺乏自信。他觉得西方文论里有摹仿论,中国也应该有摹仿论,只是中国的摹仿论不同于西方的摹仿论,中国有观物的模仿,而西方有外在的模仿。由此,顾明栋对观物取象的内涵进行了曲解,导致观物取象的真正内涵被西方理论所填充,也就遮蔽了其自身的理路内涵,以及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如此,中国古代诗学不免遭遇“削足适履”之痛。
真正的会通比较要建立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以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西方的理论,不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诗学。异同都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比较加深对彼此的认识,走向对话诗学,促进诗学的交流。以西方为标准的比较,难以促进交流,中国诗学最终难免成为西方理论霸权下的强制阐释。因此,中西诗学的对话,在探寻一致性、同一性和普遍性的同时,应以不抹杀中西文化差异性为前提,不应为了探寻普遍性而刻意追求普遍性。21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也不能一味迎合西方的理念和价值判断,应建构中国本土的话语权和理论体系,以抵抗西方文化普遍主义所滋生的中心主义。中西诗学的研究,其趋势必然也是在多元文化的比较中互参有无,在差异性中探寻文化发展的本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