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异性社会中的文化赋值与数字劳动
2022-08-26罗小茗
□罗小茗
随着数字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渗透,围绕“数字劳动”展开的讨论和研究——无论是大厂青年们的“996福报”,是数据标注员或网络博主们的日常生活,还是外卖小哥被层层外包的“自由劳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这些讨论和研究不仅揭示出数字劳动对当代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也促使人们不断逼近一个问题:从社会整体性文化的角度,究竟如何看待膨胀兴盛中的数字劳动?如果说当前的讨论往往被放置在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或传播学的既有路径之中,那么本文的任务便是尝试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出发,整理与之相关的一部分理论思考,探索展开理解的可能方向。
一、文化研究视角下的数字劳动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从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出发讨论数字劳动,这一出发点究竟有何特殊之处?众所周知,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其重要源头之一是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文化研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文化研究1983:一部理论史》里,一开篇便指出,英国当时出现的文化研究,实际上是要对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问题进行回答:“在经济富足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发生了什么变化?”为此,他特别强调:“文化研究的诞生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计划,是一种分析战后发达资本主义文化的分析方式。”[1]23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则进一步明确,正是“消费者身份与工人和公民的身份之间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构成了文化研究蓬勃发展的契机;当“原有的公民身份和公民责任因消费主义的魅力和自我实现的承诺而迅速黯然失色”之时,文化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试图回应这一重大的社会转型。[2]此后,消费主义开始了它的全球扩张,文化研究也随之散播到世界各地。这个当年在英国社会中急需回应的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中生根发芽,虽有所变化,但类似的责任和焦虑并未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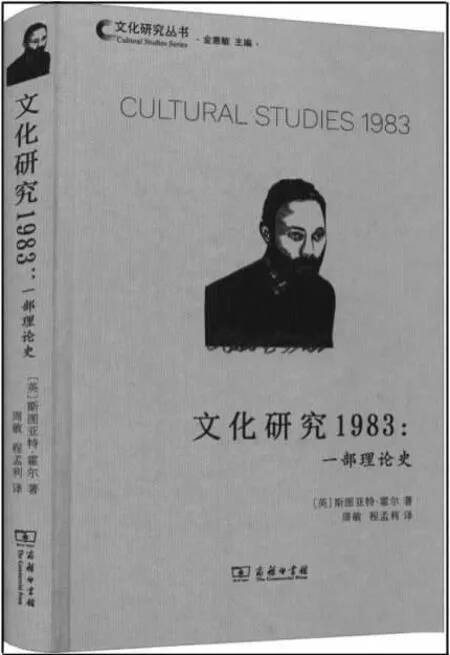
对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来说,也是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的兴盛与公民身份的构建,在中国社会中并不构成英国式的对立与紧张。相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消费者的崛起和公民身份的发生不仅同步,而且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相互配合、彼此助力的关系。[3]正如王晓明指出的那样,经由20世纪80年代末和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国内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三个子系统组合而成的新的社会制度/结构。这三个子系统分别是,以“维稳”为首要目标的国家政治系统、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系统和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统。[4]如果说前一个系统势必形成一种新的公民身份的话,那么后两者则都致力于消费者身份的日益巩固。在这样一种彼此配合实现社会再生产的新的制度/结构中,不仅很难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的抵抗模板,直接套用到中国青年文化的研究之上,也同样无法依样画葫芦,在不探究生产、消费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真正有效的文化批判。这使得那些针对文化研究的长期批评,既永远正确,又往往失焦。[5]因为真正的问题,从来也不是将“阶级”或“劳动”问题放回文化研究的版图了事。而是必须回答,在中国社会形成的这一组政治/经济/文化的配套关系中,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身份之间形成互动与更新的可能。换言之,当英国文化研究以一种特殊的历史方式,将生产者、消费者和公民身份这三者的关系凝结在“工人阶级”“消费文化”和“抵抗”之中时,后来者是否有能力将其重新打开,放置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语境中加以辨认与思考。
在这一意义上说,伴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退潮,围绕数字劳动的相关讨论与研究,实际上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相当宝贵的重新打开这三者关系的契机。特别是,当中国社会促成上述配套关系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业已告一段落,看似和谐的关系出现了松动,乃至势必有所调整之时,更是如此。显然,在短短几年之间,当曾经的“小确幸”和“佛系”,在疫情之后迅速升级为“内卷”和“躺平”的时候,这一变动的趋势正日益明显。文化研究对“数字劳动”的关注与思考也由此出发,特别注重其重新打开生产、消费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并由此重塑社会整体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二、数字劳动的“泛滥”,或独异性社会的困境
在这一思路中打量数字劳动,便会发现,“数字劳动”在冲击和改写生产、消费与社会再生产之间的既有关系的同时,也正变得越来越庞杂含混,无所不包。在梳理了相关的理论演进后,姚建华老师在《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一书中指出,数字劳动从一开始被用来突显信息传播产业对互联网用户无偿劳动的占有与剥削,到越出这一范围,将网络零工、主妇式的服务型劳动、制造业或软件业劳动,以及社会媒体上的产销合一的劳动囊括其中。[6]亚历桑德罗·甘迪尼(Alessandro Gandini)则发出了“数字劳动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吗?”的质疑,认为数字技术和劳动的结合,已经成为当前展开大多数劳动时的一个基本条件,过于泛泛地讨论“数字劳动”,只会模糊“劳动”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中内含的批判性。[7]夏冰青在《再思数字劳动》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据此期待更多的学科加入到对数字劳动的研讨中。[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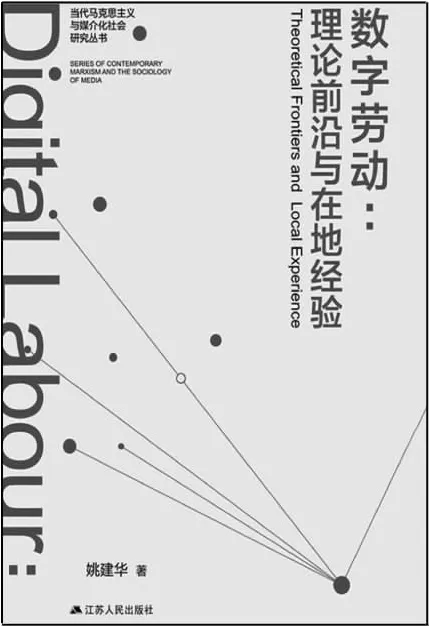
因过于宽泛而变得含义不清,并非“数字劳动”带给劳动议题的新状况。在此之前,安德烈·高兹(AndréGorz)便有过类似的担忧。不过,他所忧心的并非批判性的丧失,而是泛滥地使用“劳动”,将导致“独一无二的个体”消失。援引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和罗尔夫·海因策(Rolf Heinze)的劳动观——“在任何地方,当(一项活动的)用途对于从事它的人而言比其他人更大时,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劳动,否则便是对劳动的滥用”,他据此强调劳动与私人领域之确立之间的关系:
在不滥用的前提下,我们不能把私人领域(如家务活动领域)为自己所从事的“自我劳动”简单地等同于劳动,因为这类劳动专门服务于我自己及和我一起组成一个生活共同体的其他成员,服务于这些人的自我生产与维护。这类活动只有在下列前提之下才能保持其本真意义:不以社会用途来衡量;不是为了纳入社会劳动进程,也不是为了再造或巩固社会关系体系。私人领域的真实意义在于,为个人提供一个生存空间,其中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无须将自己的生活和目标置于社会目标之下。[9]
此处,无意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内部不同的劳动观,只想突出和之后的讨论有关的两点。首先,高兹提醒人们注意,区分是为社会还是为自我展开劳动的标准,并不是在于劳动的主体或其服务的对象,而是劳动的目标及其被评价的标准。其次,自我劳动形成私人领域的目的,在于呵护与保存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换言之,在这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劳动类型。一种是为了社会目标而展开,可以从效率和收益角度加以评判,也因此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往往伴随着剥削与占有。而另一种则是为了自我的生产和维护而展开的劳动,它的意义恰恰在于不受制于现有的社会目标和框架,既在“个体”与“社会”之间形成必要的张力,也与“将一切都视为可占有的和可计算的”这一种观点保持距离。[10]表面上看来,这两者自然有相当大的重合——越是充斥着计算和占有的社会,越是如此,却不能完全混为一谈。[11]
显然,高兹试图做出的这一区分,在网络时代遭遇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无论是“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的观念,还是在背后支撑这种独一无二的自我劳动与私人领域的关系,都遭到了数字技术更为猛烈的冲击与全方位的加持。当以利润为目标的种种行为,经由媒介技术大规模且迅速渗透在人们的日常交往、娱乐休闲、身心活动这些过往为形成个体而展开的行为处事之中时,“独一无二的个体”也由此展开了它的变形。
对于这一渗透与变形,德国社会学家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Andreas Reckwitz)有着独到的观察。他指出,既区别于与普遍性发生关联的特殊,也区别于无法被归类、比较与衡量的独特,一种位于这两者之间的“独异性”正在成为主导社会的核心逻辑。这种独异性,既处于社会规则秩序之内,又不限于被普适性逻辑再塑造的那些。它们往往在社会实践中被理解为“特别的”,并据此被制造和对待——“独异性就是在社会文化中被制造出来的‘与众不同’”[12]36。显然,要在社会实践中指认出“特别”,这本身是一个选取意义系统和重新展开意义链接的相对而言的文化过程。这一文化过程并不新颖,但要变得如此规模巨大且速率惊人,则是计算机算法、媒体形式的数字化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社会网络这三者相互作用、彼此配合的结果。[12]167莱克维茨进一步认为,当独异性作为一种社会的整体逻辑发挥它的作用时,“人们会越来越向自认为独异的人、物、图、地点和事件看齐,并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这样具有独异性的人和事物”。如此一来,时间、空间、客体、主体和集体,都可以通过获得/失去“内在的自复杂性”,完成其被文化赋值/去值的过程。
“独异性社会”的命名,不仅捕捉到了新一轮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而且提供了一个把数字劳动与“独一无二的个体”关联起来加以考察的文化视角。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对人成为有个性的个体这一点一直有着强烈的要求,但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帮助个体形成有个性的主体,协调其所遭遇的个性化和社会化之间的矛盾的手段并不相同。就拿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处的时代来说,当他用时尚来解析个性化和社会化的这对矛盾时,可以拿来标记个性或独特性的物品仍极为有限。人们不仅可以仰仗时尚潮流彰显或隐匿自己的个性,且在此之外,留给个人思考和理解自身的领域,仍颇为广大。[13]而现在,在数字技术极度扩张的社会中,标记出个性化差异的方式无疑是大大丰富了,而留给个人揣摩和思考自身经验的时空条件,则随之急速缩水。这是因为,在有相对积极和主动的思考之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行为举动,业已以数据化的方式被记录在案。从出行轨迹、心理动态到个人喜好,当这些都可以被瞬间捕捉存档的时候,从中挖掘所谓的个体之间的差别,也就变得易如反掌。当这样的差别,通过算法而非个人的自主意识,被迅速归类、计算并推送的时候,其作为“差异”被确认和巩固的速度,也随之提升。正如莱克维茨所言:“大量的数据,即大数据可以借助通过算法得知每个用户独有的特征,甚而有可能得知每个人独有的特征。”[12]180但在这里,他没有指出的是,在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体”时,所谓的独特特征是由数据和算法得以确认,还是由作为主体的个体主动辨析,这两者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特别是,当人人都在不自觉之中仰赖于算法而非自身的辨析,来取舍个性之时,个人所必须承受的个性化欲求与社会化倾向之间的张力,势必进一步增强。于是,在这一片由数字技术所孕育的近乎吞噬一切的差异之海中,人们必然越来越倚重于文化对数据的解释力和组合能力,以便牢牢地抱住所谓的“个性”的浮木。如此一来,整个社会也就被改造成了一架通过制造独异性来维持乃至加速资本流动的巨型文化机器。
这一改造意味着,一方面,独异性逻辑的顺利运行且逐渐占据主导性地位,势必使得各种不同目的和种类的数字劳动围绕这一逻辑,被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劳动的种种组合,又将夯实独异性的社会逻辑继续壮大、蔓延与渗透的物质基础。于是,无论是网红博主们的兴衰、网红景观的制造与推送,是日益兴盛的数字化出版和订阅,是每个人经营自己的朋友圈视频号,是数字加密艺术的兴起,是层出不穷的APP的开发与使用,还是让所有这些经营得以实现的隐身的程序员和审核员,都围绕独异性的社会逻辑被高效且加速度地组织起来。在此之外的种种——平台、客服、物流、商家、教育、媒体,甚至于垃圾回收等,也往往围绕着人们对独异性文化品的生产、流通、消费与弃置而进行。[14]
可以说,正是经由文化的赋值与去值而生成的独异性逻辑,构成了当前不断关联和组织起“数字技术”与“劳动”的核心动力。而这一切又离不开人们对于“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假定、理解与追求。如果说,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Adorno)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提出的“文化工业”,是对植根于福特制时期的文化生产的有力批判,那么,独异性社会则提供了一个它在互联网时代的升级版本。在“文化工业”中,文化有着它的标准化属性。根据这一标准,人们成为沙发上的土豆和第二天里精神饱满的合格劳动力。而在独异性社会中,当文化的标准被改写为“特别”之时,沙发上不再有安静的土豆;人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世界,被放逐在一个由数字劳动构建起来的以“吉尼斯世界大全”式的假定存有和膨胀的时空之中。在这个升级版本中,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消费社会的描述,也得到了它的新补丁。那就是,在此,消费主义允诺的不再是假想中的平等与丰裕,而是假想中的“独一无二”。正是出于对独异性的饥渴,使得人们不辞劳苦地组织起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并据此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
令人遗憾的是,莱克维茨虽极为敏锐地捕捉到了“独异性的社会逻辑”,让人们意识到独异性的渴求与数字劳动之间的强关联性,但他的讨论没有真正触及这一关联中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按“独异性的社会逻辑”而展开的数字劳动,最终创造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个体?此类个体对独一无二性的追求和由此发展出来的种种数字劳动,足以支撑它们所根植的这一社会/市场类型持续不断地运作下去吗?
较之于莱克维茨对于由市场带来文化的赋值与去值的近乎盲目的乐观[15],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对“技术体外化”和个性化经验形成之间关系的分析,为上述问题提供了更为深入的解释。在斯蒂格勒看来,尽管自人类有文明的传承演进以来,技术的体外化便构成了这一演进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文字、图像、影像、存储、网络等技术的升级换代,得以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体”的技术手段和时空条件发生了巨变。曾经一度有助于形成个性化的经验乃至个体意识的持留机制(语言、书籍、教育系统……),如今被持续更新且任意折叠时间流的持留机制(网络、微信微博、短视频、弹幕、后台数据、表情包……)所取代。而一旦被信息流不断冲刷成为个人形成自身经验时的常态,个性化的意识过程就严重受阻。[16]这意味着,在数字技术近乎覆盖一切的时空条件下,各式各样的独异性产品不仅无法真正解决个性的问题,反而构成了个人展开真正的个性化时的巨大障碍,导致围绕自己和共同体展开自我劳动的能力进一步萎缩。在一个没有“我”的时代,自然不会有所谓的“我们”,社会的更新也随之受阻。于是,一个近乎“悖论式”的困境就此出现。一方面,越是需要通过文化的赋值过程制造差异,形成资本流动的社会文化系统,就越是难以弃置个体与共同体,因为正是他们对独特的渴求构成了差异的来源;另一方面,这一由数字技术所加持和加速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又势必损害甚至捣毁了形成个体与共同体所需要的时空条件。
正是在这里,斯蒂格勒指出了空前强大的技术体外化带来“独一无二的个体”的危机,而这一强大的技术体外化恰恰是由数字劳动构建而来。[17]依靠数字劳动所实现的体外化过程越是顺滑迅猛,其对个体的形成过程所造成的损害,也就越是巨大且无可挽回。而越是无力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体,个体也就越需要依赖于数字劳动,去设定、订制、购买和使用市场上所提供的替代品——独异性产品。这一大规模的设定、订制、购买、使用和评价的过程,又将进一步推进数字劳动的发展,加速其对个人意识的规制与渗透。当越来越多的人试图借助独异性商品让自己变得“独一无二”之时,其核心的驱动力,既非市场本身,也非文化的独特价值,而是由这一过程所导致乃至不断加剧的个体的内在贫困。最终,这一对矛盾导致的是:“由于没有了独特性,他们便借助市场所提供的人造物努力使自己独特化。市场就是要开发利用消费所特有的这种贫困,让自恋达到过度和劳而无功,众多个体将体验他们的失败,最终失去他们的形象……”[18]显然,在这一不断加剧的矛盾中,由独异性的社会逻辑所勾连起来的追求独一无二的个体与数字劳动,最终导致的将是个体和社会的全军覆没。
三、文化赋值中的新常识与新迷思
至此,让我们回到高兹的担忧与甘迪尼的批评。不难发现,如果将“数字劳动”放置在“独异性社会”这一概括中加以把握的话,那么“数字劳动”的“滥用”,与其说是界定不清、使用不当使然,不如说是两类社会实践过程同步展开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在算法、媒体形式的数字化和基于互联网的社会网络这三者彼此加持的过程中,与个体形成“独一无二”密切相关的事关自我的劳动,既越来越多地以体外化的数字技术为媒介,也由此被持续地扭曲、侵占和渗透。另一方面,尽管如此,身处经济目标之外的自我维持的努力并未消失,而是持续存在。无论是个人爱好的萌生、旨趣的迸发,还是规模各异的共同体的合作与行事,都甚至于,对“独一无二”的渴望,因上述的扭曲、侵占与渗透,变得越发强烈。正是在这两类社会实践持续同步的过程中,数字劳动的范围不断扩张,近乎吞噬一切;人们对“独一无二”的渴求,也因其内在的匮乏越发强烈,以至于不惜一切去记录和演算那最后一点点可供回味的经验和情感,实现新一轮的文化赋值。
面对这一双向且彼此加强的社会实践过程,无论是立足于劳动剥削理论,还是立足于文化抵抗,都只能是片面的。因为在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在这一赋值过程中正在形成的一连串不连贯的新“常识”。
显然,“数字技术+劳动”的新模式,已经明确打破了过去人们理解生活和自我时所依赖的基本路径,因为后者是由八小时工作制、由与之配套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所确立的。如果说在最初发生这一转变时,人们尚对此议论纷纷的话,那么现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界限的融合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常识,虽未经充分解释,却已逐渐稳定下来。
其次,这个新模式不仅冲击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固有观念,比如,公共与私人、工作与休闲、专业与爱好、个体与社会等,更是大大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导位置的劳动和价值的观念。这不光是因为微信的存在,让体制内外的中国人都失去了上班和下班的界限,变为随时待命的劳动者[19],也因为网红主播一小时的带货收入和数字加密艺术的拍卖价格,同样侵蚀着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关系。
再次,在此过程中,个体对于“独一无二”的渴求日益强烈,但要实现这一渴求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一方面,人们日益明显地感觉到网络技术、算法和媒介的数字化对于这一渴求的重重威胁——在一个数据崇拜的时代,算法和数据往往比个人有更大的发言权;另一方面,又往往试图继续运用新的数字技术的手段,去驱赶或破解这样的威胁。概而言之,在这一部分的常识中,对困境的意识已经形成,即在工业化时代,可以用来追寻/保存/隐匿个性的手段/方式失效了。但究竟如何理解这一困境,尚未被明确下来,以至于人们被本能中对“独一无二”的渴求所驱使,反而更容易被独异性的生产与消费逻辑所吸纳。
最后,人们对于劳动的理解,虽遭到挑战,却迟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工作之外的娱乐休闲被归入以“城市式居家”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系统之中。在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这一部分立足于消费者身份的社会意识,往往被社会媒体和平台电商所承包,也更容易被其时时更新与重塑。劳动的观念则不然。它往往受制于既有的市场观念、薪酬制度、法律法规,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对于“不劳而获”或“多劳多得”的社会意识。同时,在一个充分市场化的社会中,人们受到的剥夺越是厉害,往往越加深了将劳动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加以理解的意愿。因为不如此,便不足以在既有制度中找到抗争的依据。由此引发的一个后果却是,越是如此理解劳动,也就越倾向于取消自我劳动的存在,进而失去与既有的社会制度保持距离的能力。于是,尽管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并非彻底商品化了的那一部分自我劳动,却往往被视而不见。这样的视而不见,反过来又进一步巩固了旧有的劳动观念,使之无法在独异性的社会逻辑中随着价值、生产和消费、公与私等观念的变动,一并变化。
可以看到,在上面这一系列彼此相关的新“常识”中,一方面是数字劳动对社会意识展开了大规模全方位的改造,但另一方面,身处结构性变动中的人们,对于这一改造做出的往往是本能的、彼此不连贯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说,独异性的社会逻辑,也是各种力量——从政府到资本,再到个人——试图收拾这一剧烈变动中的局面,努力将现有因素顺利“结合”起来的一种努力。然而,一旦突出了数字劳动和独异性的文化赋值之间的关联,那么就标示出了这一“结合”内在的困境:既无法实现劳动观念的变革,形成劳动和价值之间的新关系,也无力真正形成“独一无二的个体”,完成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更新。这不仅意味着,迫于个人内在的贫困,其文化赋值和去值的系统运作势必遭遇运转不灵的时刻,更是指在这一过程中,它将一次又一次使人错失正视变动中的常识,对它们展开整合与重新想象的机会。
要捕捉这一机会,正视这一系列变动中的新常识,需要分析在上述变动过程中,什么正在被再度神秘化,成为新的迷思?这一迷思可能将人们引向何处?
不得不说,在这里,首先面临新一轮神秘化的是“独一无二的个体”。[20]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与个体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中被要求成为具有个性的个体,一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催生且倚重的重要观念,但区别在于,在独异性社会中,构成“独一无二的个体”神秘化来源的,是数字技术对于个体状态事无巨细的记录与计算。这使得个体在对自身展开劳动,形成个性化经验时,不得不面临一整套全新的取舍过程。特别是,当这些被数据标记下来的行为,有些是自己有所了解和可以支配的,有些却是无意识的结果之时,如何面对如此巨大的数据记录及其被计算的结果?如何看待算法推送和自身喜好之间的距离?如何理解那些由无意识所导致的数据?对于自我的理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数据监控的干扰与介入?拒绝数据的指导,又在多大程度上助益或阻碍真正的自我劳动的展开?数据的记录和计算,最终与自我劳动将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在当前社会中试图展开自我劳动时需要考虑的线索。它们的存在,不仅大大增加了个体展开自我劳动的难度,更是进一步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新问题。[21]这些问题包括:首先,当彰显差别的个人数据分属于不同的平台和APP之时,大规模留存于各处的数据和形成整体的自我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22]特别是在中国社会中,往往是政府和平台掌握着决定性的数据,而个人所能得到的数据有限且往往具有明确导向性的情况下,个人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数据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其次,如果这一部分的理解实际上构成了新一轮个体在展开自我劳动时所必需的技艺,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教育过程为这一技艺的养成提供条件?或者说,什么是这一新的自我技艺得以养成的社会条件?最后,当个体展开社会劳动,特别是被数字技术组织起来的文化赋值与去值过程时,这一部分的劳动是在不断改善展开自己和社会中的大多数人展开自我劳动的社会条件,增加自我技艺养成的可能性,还是反其道而行之?显然,当这些新问题在日益堆积的独异品的掩饰下,无法真正地被澄清之时,势必使得“独一无二的个体”趋向于进一步的神秘化。而当这些新问题被提出,且得到更积极的思考之时,便有助于去神秘化的发生。
这一决策的提出,是依托当前信息技术时代“互联网+教育”的时代背景,对于教研工作的突破性创新,它能够克服时间、空间等不利条件的约束,利用网络技术,把小学数学教研工作落到实处。这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要强化技术培训和相关网络知识的学习,能够使工作坊学员逐渐熟练工作坊研修操作平台,阅读研修须知,明确研修任务。当学员们掌握了平台使用和操作的基本技术之后,鼓励学员联系自己的数学教学实践积极地参加主题研讨、教学诊断、课例分享等研修活动,这样才能够保证研修活动的有效开展。
至此,可以说,由数字劳动大规模重组的生产、消费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在为过去的观念松绑的同时,也开辟出一片新的有待争夺的社会实践意识的领域。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所言,在所有不连贯的“常识”之中,包含的恰是“石器时代的要素,较发达的科学原理,来自历史上所有阶段的偏见……以及未来哲学的直觉”[1]233。这意味着,对文化研究而言,从含义不清的数字劳动出发,需要重申的不仅是一个新的劳动观念,更是要通过重新审视由独异性的社会逻辑所中介起来的数字劳动和渴求独一无二未遂的个体,识别出其中正在成形的不连贯但有趣的新常识,分析其被神秘化和去神秘化的可能方向,以摆脱由当前这一套生产制度所规定的种种贫困为目标,探索当代生活的新方式。
注释
[1][英]霍尔.文化研究1983:一部理论史[M].周敏,程孟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2][英]默多克.序二[A].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9.
[3]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冲突,而是着重指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它们在中国社会中的和谐共生、共同壮大。
[4]王晓明.什么是今天中国的“住房问题”[A].王晓明等.1990年以来上海都市青年的“居家生活”[M].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探索与争鸣》编辑部,2016:173.
[5]比如,认为文化研究一味注重对符号表达和抗争层面的分析,而忽略对产业政策和经济形态的思考,并呼吁文化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的转向。自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大陆以来,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便不绝于耳。
[7]Gandini,Alessandro.Digital Labour:An Empty Signifier?[J].Media,Culture&Society,2021,43(2):369-380.在文章中,作者绘制了一张表格,以区分受众劳动、数字劳动和平台劳动,指出其主体、劳动行为、被剥削的方式和所运用的媒介完全不同。
[8]Xia,Bingqing.Rethinking Digital Labour:A Renewed Critique Moving beyond the Exploitation Paradigm[J].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2021,32(3):311-321.
[9][法]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M].彭姝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75-76.
[10]正如麦克佛森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中指出的那样,将占有性与个人关联起来,视这一结合为一种自然,进而转化为以霍布斯的“利维坦”为代表的政治理论,这本身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过程所导致的结果,而非必然。对于“可计算”如何与资本主义历史相交织且变得日益突出,韦伯则有过详细的说明。[加]麦克佛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M].张传玺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德]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康乐,简惠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11]比如,我正在写文章这件事。从学院评价体系和KPI考核的角度,它不过是努力挣工分的社会劳动。但显然它对我的意义,不止于此。除却生存的考量,它也是试图整合自身的思考,与他人展开对话和交流,共同推进某一个想法的努力。一个糟糕的学术制度,往往是持续剥夺这两者共存与平衡的可能,迫使人不得不为了前者而彻底放弃或搁置后者。张力或平衡感的破坏与社会劳动彻底驱逐自我劳动,这两者互为因果,相互加强。
[12][德]莱克维茨.独异性社会: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M].巩婕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13]齐美尔认为,只有当其他领域无法达成人们对个性的追求的时候,时尚业才会如此兴盛,而非必然如此。[德]齐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14]就此而言,无论是去年令人咋舌的“倒牛奶事件”,还是引发人们热议的“盲盒经济”,这些在“消费社会”中看起来颇为诡异的消费行为,将在“独异性社会”中得到有效的解释。
[15]受限于本文的议题,在此无法对莱克维茨实际上将市场等同于社会这一理解范式展开梳理与批评。只是简单地说明一下观点,即正是这一近乎无意识的“等同”,最终导致“独异性社会”这一概念的有效性和批判力大大降低。
[16][法]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17]当然,斯蒂格勒的讨论侧重于强调个体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个体经验的形成与工具使用过程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并不必然是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它们又总是被归类为劳动。
[18][法]斯蒂格勒.蚁穴的寓意:超工业时代个体化的丧失[A].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97.由此,斯蒂格勒指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它既急需一种新的个人形象来自我维续,但这一维续的实际过程又是以不断损伤破坏乃至捣毁个体化的过程为代价。
[19]2021年12月,网上曝出了证券公司员工晚上9点在家敷面膜被公司处罚的新闻。近年来,类似的新闻频频爆出。五矿证券员工晚上在家敷面膜被罚,因“过早休息,耽误加班”.澎湃政务[EB/OL].https://m.thepaper.cn/baijiahao_15952023,2022年3月19日访问。另一个更为普遍的例子是,疫情之后,虽各单位公司已恢复正常上班,但由疫情带来的随时网络开会的习惯顺理成章地保存了下来。
[20]限于篇幅原因,本文只讨论“独一无二的个体”的神秘化问题。实际上,还有“价值”和“创造”两项面临着新一轮的神秘化,值得予以分析。
[21]雷蒙·威廉斯曾敏锐地指出,个体和社会分别被抽象化,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生而出现的社会思想的转型。那么现在,无论是个体还是社会,其抽象的性质并未改变,但呈现这一抽象属性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个体的抽象属性恰恰是由海量的数据来标示时,据此展开计算和监控的社会,其与个体之间形成张力的关系,也必然随之变化。[英]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倪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87.
[22]Sefton-Green,Julian and Luci Pangrazio.The Death of the Educative Subject?The Limits of Criticality under Datafication[J].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202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