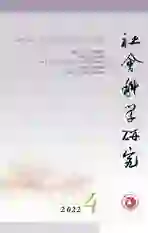倾听与缄默:“不可信言说者”格吕克的生存之维
2022-07-23生安锋郑春晓
生安锋 郑春晓
〔摘要〕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对倾听与缄默这两个长久以来被忽视的生存论议题给予特殊关注,并在生存论的高度强调它们对此在追求存在的本真状态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而202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露易丝·格吕克正是通过倾听音乐和歌声来领悟在世存在的意义、体会此在向死而在的境界,在缄默中聆听良知的召唤、追求澄明无蔽、源始自在的生活状态。以往对格吕克的作品分析鲜有从此角度入手进行研究,在这个“世界成为图像”的现代社会,倾听本真的声音和道说对寻求此在的生存意义和存在价值的必要性也愈加凸显。
〔关键词〕露易丝·格吕克;倾听;缄默;生存
〔中图分类号〕I71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22)04-0085-07
近年来,文学批评界从声音入手对作品进行的分析和讨论呈现逐渐增长的势态。国内学者耿幼壮在论及法国文学家和思想家布朗肖的声音诗学时曾分析道:“对于布朗肖来说,近现代文学的演变可以说是一个‘书写到声音’的过程。” ①英国文学批评家安吉拉·莱顿(Angela Leighton)的新书《聆听:文学作品中的声音》(Hearing Things: The Work of Sound in Literature)也将关注点重新聚焦于聽觉这一长时间被文学界冷落的理解形式。②在传统西方哲学和文学批评理论中,“看”似乎比“听”占有更加关键和主要的位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就曾说过:“眼睛是比耳朵更为确实的依据”。③德国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却认为,倾听是此在最本己的存在特征,此在只有在倾听的时候,与其“听”到的世界才是相互融合的、同处共在的,此在的生存活动和生存方式才是一种“在世存在”(InderWeltsein)。这是因为,语言的本质是“道说”,“‘道说’(Sagan)意谓着:显示、让显现、让看和听”。④在海德格尔这里,人与语言的关系颠倒了,不是人在用语言道说,而是语言在向人道说,人倾听着语言的道说,“沉默应和于那居有着——显示着的道说的无声的寂静之音(Gelut der Stille)。”⑤缄默并不是什么都不说,相反,缄默是语言之道说开始的另一种本质可能性。海德格尔将倾听和沉默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强调终有一死者要在沉默中倾听此在先行具有的领会、追问在世存在的意义。
美国诗人露易丝·格吕克(Louise Glück)获得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其获奖理由是“因为她无可挑剔的诗意之声,以朴素的美感使个体的生存普遍化。”格吕克在诗歌创作中利用倾听和缄默阐述内心遭受的创伤和疼痛,将家庭经历、个人经验与在世生存之道紧密结合。“由是,她的诗歌主体既不完全自由地无所依傍,又不受个体细微感觉的羁绊:既不浮言其苦乐之无可比拟,又不丧失其存在与世界的关联。”殷晓芳:《“反对诚实”:格里克抒情诗歌的实用主义》,《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第27—28页。作为一名后自白派诗人,格吕克将处世哲学和生存诗学建构在倾听和沉默的基础之上,为读者理解其内心世界及诗学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认知形式和审美范式。
一、“不可信言说者”之缘起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否定了希腊人将人的本质规定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这一说法,认为“人表现为有所言谈的存在者。”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34页。语言使此在成为此在,并构成了此在存在的生存方式。当此在被剥夺了语言功能这一人类与生俱来的用来交流、倾听的工具时,此在就丧失了存在的本质,等同于原始的动物。格吕克童年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其失去了表达真实自我的机会,“就像那个家庭的大部分成员一样,我也有强烈的想要表达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却经常难以施展:我说的句子都被打断,彻底改变了——意思变了,而不是被改写了。”Louise Glück, Proofs &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New Jersey: Ecco Press,1994, p.5.唯有词语才赋予在场、赋予此在的存在,不能真实表达内心想法、阐述自我的格吕克内心支离破碎,本应澄明、自在的此在被暂时遮蔽起来,想得到家人全部的爱意和关怀而又不能够实现的矛盾使得诗人变成了一个“跛子”和“说谎者”。
格吕克在诗作中大量融入了自身的家庭经验和人生经历,家庭关系在格吕克的诗作中占有了极其特别的位置,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格吕克和姐妹的关系。格吕克曾有一个出生不到几天就不幸夭折的姐姐,母亲对这个死去的孩子抱有一种极其特殊的情感。在《失去的爱》(“Lost Love”)这首诗中,格吕克将夭折的姐姐比作一块有魔力的强力磁铁,“当姐姐柳向阳将本首诗里的sister译为“妹妹”,笔者认为颇有不妥,英语中的“sister”既可指妹妹,又可指姐姐,但“进入大地”的应是格吕克死去的姐姐才合情理,所以笔者在此将译作中的“妹妹”改为“姐姐”。死去,/妈妈的心变得/很冷,很硬,/像一块极小的铁坠。/后来我觉得姐姐的身体/是一块磁铁。我能感到它吸着/妈妈的心进入大地,/这样它才会生长。”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44—345页。母亲对死去女儿的思念和眷恋像磁铁相吸的引力一样将母亲冰冷坚硬的心吸引到地下,格吕克无法得到母亲全部的爱意和关怀,这给她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创伤。“《不可信言说者》(‘the Untrustworthy Speaker’)承认,在《失去的爱》中她将自己描述成一个悲剧情节的无辜受害者,这让她个体身份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被遮蔽而非显现。”Daniel Morris,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Columbia and London: U of Missouri P, 2006, pp.113-114.的确,格吕克在《不可信言说者》中将伤痕累累的自我视为一个满口谎言、不可信的说话者:
不要听我说:我的心已碎。/我看什么都不客观。……当我说得激情四溢,/那是我最不可信的时候。……当我安静,那才是真实显现之时。……如果你想知道真实,你必须禁止自己/接近大女儿,把她挡住:/当一个生命被如此伤害/在它最深的运转中,/所有功能都被改变。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348—349页。
诗中的“大女儿”指的就是格吕克的姐姐,姐姐的隐形在场夺去了父母大部分的爱,诗人被爱而不得的心理创伤所裹挟,被迫成为了一个“不可信言说者”。邦尼·科斯特洛(Bonnie Costello)评论这首诗歌时认为,“正是因为诗人知道她自己的变形,而且正因为艺术有序的扭曲揭示了规范所隐藏的东西,我们才倾听和信服。”Bonnie Costello, “Meadowlands: Trustworthy Speakers,” in Joanne Feit Diehl ed., On Louise Glück: Change What You See,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2005, p.48.
与姐妹的手足之争、父亲角色在家庭生活中的缺失、对亲情的渴望等童年经历和家庭问题共同参与塑造了诗人的个性。相比起已经死去的姐姐,格吕克与妹妹之间的矛盾和争斗更为外显。格吕克和妹妹都觉得对方挤压了各自的生存空间,二人对彼此分享母亲的爱都颇有不满,“我们两个都觉得/两个人太多/无法生存”。Louise Glück, Poems:1962-201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p.226.此诗未被收录到中译诗集中,故此处为笔者自译。格吕克认为妹妹的出生就是为了“让我缄默”,夺走了本属于诗人的亲情和话语权,使得自己在家庭中成为一个可有可无、默默无言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你被生下:让我缄默。/母亲和父亲的细胞,轮到了你/成为关键,成为杰作。/我即兴而作;我从未记起。/如今轮到你被驱赶;/你要求知晓:/我为什么受苦?为什么无知?/巨大黑暗中的细胞。/某个机器制造了我们;/轮到了你对它讲话,继续问/我是为何?我是为何?”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9页。诗人感觉自己不过是一段即兴而作的小段子,在妹妹这个父母精心制作的得意之作面前相形见绌。在这首诗中,诗人将世界、家庭、母亲分别指称为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世界机器”“家庭机器”和“母亲机器”,这更是在无形中体现了诗人内心深处隐含的冷漠和疏离。除此之外,格吕克与父亲的情感交流和沟通也并不顺畅,父亲和女儿之间经常不知道怎么进行正常的谈话,“交谈对我们来说总是一成不变。/他说上几句。我回上几句。/就这么回事。……父亲避免和我单独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怎么接上话,怎么随意聊天”。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359页。语言缺失、沟通断裂,她在艾略特(T.S. Eliot)笔下的人物自白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此与其中的人物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艾略特独白的目的是交流。可问题是,交流的对象无法找到,又或者根本没有人注意。……艾略特的叙事者要么说不出来,要么听不见;……我第一次读这首诗是在青少年时期。我马上就明白了,我感觉到了和它的联系。”Louise Glück, Proofs &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pp.21-22.
实际上,与其说格吕克是“不可信言说者”,不如说她是个遭受严重心理创伤的“受害者”。由于从小在家庭生活中得不到足够的话语权,格吕克期望通过诗歌来展现自身的存在,在诗歌中以存在者的本质现身,以诗性之思实现灵魂的救赎,追寻现此在的去遮蔽和存在的澄明、涌现。格吕克曾说,尽管“我的一生中有过痛苦的沉默期”,但写作的部分冲动在于,她“希望人们听到”作为她个人“存在的有力证据”。Daniel Morris,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p.142.而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比起成为一名“不可信言说者”,格吕克更倾向于通过倾听和沉默的隐形互动来构建独特的“倾听诗学”和生存维度,以彰显自己对生命和死亡的思考以及爱而不得的缺憾和挣扎。
二、倾听格吕克的倾听
倾听和沉默对于生存的生存论结构具有组建作用,倾听在格吕克的诗歌创造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这也正能说明为什么对于格吕克来说,诗歌的受众不是读者,而是听众。格吕克在“诗人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Poet”)一文中说:“从一开始,我就偏爱那些需要或渴望聽众在场的诗歌。”Louise Glück, Proofs &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p.9.在安·道格拉斯(Ann Douglas)组织的一场文学访谈中,格吕克亦曾明确表达过诗歌与听众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认为一首诗歌就是一条传达给听众的消息,他们是诗歌的发现者和接受者。如果你理解得足够精确,总会有合适的耳朵听到。” Ann Douglas and Louise Glück, “Descending Figure: An Interview with Louise Glück,” Columbia: A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Art, no.6 (April 1981), p.124.唯有倾听,方能作诗;唯有倾听,方能懂诗。传统意义上的读者用眼读诗,而阅读格吕克的诗歌则需要读者用耳去倾听、思考其中蕴含的深层意义。我们作为格吕克的倾听者倾听着格吕克的倾听和道说,而在此过程中我们被召唤成为她。
格吕克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声音效果和机制,巧妙地利用声音作为表达情感个性和传递审美经验的纽带和桥梁。丹尼尔·莫瑞斯(Daniel Morris)认为,格吕克在诗歌写作中“注重声音胜于形象”Daniel Morris,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p.38.,并“实现了格罗斯曼要求当代作家用声音来塑造‘人物’的号召”。Daniel Morris,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A Thematic Introduction, p.127.正是通过倾听,诗人才得以对本真的向死存在的生存论筹划,领悟此在的整体性。在另外一首名为《圣女贞德》(“Saint Joan”)的诗中,幼年的格吕克想象自己死亡时的情景,“我清醒地躺着,倾听。/五十年前,在我儿时。/当然还有现在。/那是什么,正在对我说话?对死亡的/恐惧,对丧失的恐惧;/害怕疾病穿着新娘的白裙——/七岁的时候,我相信我将要死去:/只是日期是错误的。”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第413页。对丧失和死亡的恐惧一直以来占据着诗人的心灵,它倾听了作者年幼时关于若干年后自己将死于小儿麻痹症的诉说,诗人也倾听着心中的“恐惧”五十年如一日的喃喃低语,“我听到/一个黑暗的预示/在我自己的体内升起。/我给了你机会。/我倾听你的诉说,我信任你。/我再不会让你拥有我。”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第413—414页。琼尼·菲特·迪尔(Joanne Feit Diehl)认为,“这里所说的‘你’指的就是‘恐惧’”Joanne Feit Diehl, “‘From One World to Another’:Voice in Vita Nova,” in Joanne Feit Diehl ed., On Louise Glück: Change What You See, p.175.,这个“黑暗的预示”告诉诗人,恐惧以后不会再给诗人“机会”让诗人拥有它,亦即意味着诗人不会再受死亡和丧失的恐惧所支配,诗人从而可以实现最本己的此在。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作诗意谓:跟随着道说,也即跟随者道说那孤寂之精神向诗人说出的悦耳之声。在成为表达(Aussprechen)意义上的道说之前,在极漫长的时间内,作诗只不过是一种倾听。”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第70页。
乐器和音乐在格吕克的诗歌创作中具有非常特殊的作用,它们在格吕克的诗作中频繁地以中心意象的身份出现。“根据格吕克的说法,乐器的哀叹大概是某种不确定的存在焦虑和渴望的表达,而这种焦虑和渴望是自我存在本身所固有的”。Piotr Zazula, “‘To Love Silence and Darkness’:Uneasy Transcendence in Louise Glücks Poems,” Brno Studies in English, vol.38, no.1 (January 2012), p.169.在诗歌《村居生活》(“Village Life”)中格吕克记录了自己倾听乐器奏乐的经历:“有时我会听到有些乐器的音乐,/尽管它们锁在盒子里。/我还是一只鸟的时候,我相信自己将会变成人。/那是长笛。而圆号应和,/当我还是人的时候,我哭喊着要变成鸟。/然后音乐消失。它对我倾吐的秘密/也随之消失。”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244—245页。人、鸟、乐器这三方在“被锁在盒子里”的乐器所奏出的音符和旋律中交汇存在,作者在倾听中领会此在“在之中”的生存状态,于生存的罅隙中短暂地挣脱出来,思考个人身份的迷乱和自我认知的缺失。当音乐消失、倾听被迫停止时,对生存本质的思考和醒悟也就终止了,意即“我听故我在”。
格吕克不仅通过乐器和音乐传达内心情感、领会此在存在的本真意义,更是通过倾听歌声来领会死亡、战胜此在对死亡的“畏”,从而通达“向死而在”的本真存在状态。格吕克一生中先后承受了姐姐和父亲的死亡带给她的无尽痛苦和焦虑,这就使得她对死亡有一种近乎痴狂的迷恋,她的诗作中几乎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但是在“新生”(“Vita Nova”)一诗中,欧律狄刻在通往死亡的路上听到丈夫俄耳甫斯的歌声之时,她对死亡的恐惧和执念似乎悄而淡去了,“你怎么能渴望死亡/当俄耳甫斯还在歌唱?/长久的死亡;去地狱的一路上/我听到他的歌唱。……去地狱的一路上/我听到我丈夫在歌唱,/很像你现在听到我一样。/也许那样好一些,/我的爱在我头脑里生气勃勃/即便在死亡的那一刻。”露易丝·格丽克:《月光的合金》,柳向阳译,第281—282页。诗人借欧律狄刻之口诉说着歌声对自己的拯救,欧律狄刻在通往地狱的路上听到俄耳甫斯的歌声,这一意象帮助诗人战胜了“恐惧”,在聆听俄耳甫斯的歌声中追问现世存在和生活的意义及价值,并让她把头脑中的爱作为“最后的应答”。即便是在死亡的前一刻,诗人的心也是充满了“生气勃勃”的爱和温暖,正如诗集名字《新生》(Vita Nova)所暗示的那样,死亡便是新生。
T.S.艾略特将艺术范畴的听觉反应称为“听觉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我所谓的听觉想象力是对音乐和节奏的感觉。这种感觉深入到有意识的思想感情之下,使每一个词语充满活力:深入最原始、最彻底遗忘的底层,回归到源头,取回一些东西,追求起点和终点。”Thomas Sterns Eliot, The Use of Poetry and the Use of Criticism: Studies in the Relation of Criticism to Poetry in Engl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11.格吕克在创作过程中十分倾向于这种“听觉想象力”的运用,将内心的情感进行外在化、声音化、个性化编码处理,试图抵御视觉对其他感官的压迫和统治,而读者则由传统意义上依靠眼睛和目光阅读的读诗者变身成为以耳代目的“聽诗者”,“聆察”(auscultation)代替了“观察”(focalization)。譬如,格吕克将内心感受到的疼痛和创伤的来源比作竖琴,本应弹奏美好乐曲的乐器在诗人的口中却变成了伤人最深的凶器,就像诗人“不见天光”的童年,本应是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美好时光却造成了诗人日后永久的心理创伤。“后来我受伤了。那张弓/此时就成了竖琴,它的弦/深深切入我的手掌。在梦中/它既制造了伤口又缝合了伤口。……然后我的灵魂出现了。它说/正如没有人能看到我,也没有人/能看到那血。而且:/没有人能看到那竖琴。”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70—73页。诗人摒弃了人类视觉受光线限制的局限性,竖琴之所以不可见,是因为“在目光凝视的地方以外的一切都被遮蔽起来,本来处于整体性联系中的事物就在这种遮蔽中成为孤立、静止的原子式的实体”。王珉:《从注视到倾听——关于西方哲学演变的一个思考》,《学术月刊》1998年第3期,第44页。从视觉到声音的机制转换使得倾听成为了此时可以通达作者灵魂深处的唯一媒介,只有当诗人弹奏竖琴,音乐响起时,视觉对此在存在的遮蔽才得以消解,诗人的存在才能在场。“唯有所领会者能聆听”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233页。,只有领会作者意图的听众才能够通过倾听诗人于琴上弹奏的哀歌来感受其灵魂所经受的疼痛和对生存意义本真的思忖,这就是我国知名叙事学研究者傅修延教授所说的“我被听故我在”。关于听觉叙事学可具体参见傅修延:《释“听”——关于“我听故我在”与“我被听故我在”》,《天津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17—133页;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
三、缄默与此在的本真生存
格吕克所经历的家庭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精神创伤使她内心产生了无法言说的孤寂,正是这种不可言说的孤寂造就了日后格吕克的“独一之诗”,而“沉默,应合于那种作为他的独一之诗的位置的孤寂。”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第78页。在格吕克看来,“沉默,除了是抵御他人侵略或入侵的保护面具,也可以是抵御肮脏语言陷阱的防御手段”。Suzanne Matson, “Without Relation: Family and Freedom in the Poetry of Louise Glück,” MidAmerican Review, vol.14, no.2(Spring 1994), p.90.诗人在缄默中追求此在存在的本真形态,倾听良知沉默的呼唤,将此在最本己的能在(abilitytobe)召唤上前。
海德格尔将此在的存在样态分为非本真形态(inauthentic existence)与本真形态(authentic existence),闲言(idle talk)、好奇(curiosity)和两可(ambiguity)构成了常人消散于世的非本真形态的存在方式。“闲言这种话语不以分成环节的领会来保持在世的敞开状态,而是锁闭了在世,掩盖了世内存在者”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239页。,它作为一种奠基于平均领会的起封闭作用的话语形式,在本质上显示出引诱、安定、异化等特性。在《橄榄树》(‘Olive Trees’)中,格吕克描绘了此在的非本真状态及试图挣脱沉沦此在的愿望,“我抱怨这里,/我的声音有人听到——别人的声音也有人听到。/于是有争论,也有愤怒。/凡是人都会互相诉说,一如我妻子和我。/意见不一也会说话,哪怕其中一人只是装装样子。”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220页。小镇上的每个人都在随意地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做生意的老板们讲着蹩脚的笑话,大家都跟着哈哈大笑;妻子在叙事者耳边喋喋不休地谈论村镇、母亲、青春的故事以及腌制橄榄的具体做法。被抛入日常生活的此在消弭在公众的“闲言”中,此在的非本真在常人的“闲言”中绽露出来,遮蔽了此在最本己能在的可能性。所以叙事者意识到,“假若你不能很快走出去,/你就会死,似乎这种美正在扼紧你,令你无法呼吸。”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220页。从非本真的存在状态到本真的存在状态需要经历从闲言到缄默的过程,无根基的话语只在下定决心的缄默中被揭露和收回。“在另一个人生,你的绝望直接化为沉默。/ 太阳消失在西山之后——/它再回来时,丝毫不提你受过的苦。/你的声音越发微弱。你不再着力,不仅对太阳如此,/对人也是一样。曾经令你快乐的小事,不再能够触动你。”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220—221页。在缄默中,此在作为被抛沉沦的此在向自身呼唤最本己能在的可能性,在呼声中被唤醒的此在告别沉沦于世的常人,不再人云亦云,不再以虚伪的安定和肤浅的娱乐为麻醉剂,而是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返回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和本真的生存状态中。
缄默意味着不求助于任何外力,是一种独立的透明存在。“我们人的说话在听从未被说者之际应和于语言之被道说者,所以,就连沉默也已然是一种应和(Entsprechen)。”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第264页。缄默并不是什么都不说,相反的,缄默是语言之道说开始的另一种本质可能性。在这一点上,萨特(JeanPaul Satre)和海德格尔持相同观点,“他的沉默是主观的、先于语言的,这是没有字句的空白,是灵感的浑沌一体的、只可意会的沉默,然后才由语言使之特殊化。”参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7页。只有对所说之物有了足够本真的了解和领会,此在才能对所说之物表示缄默。在《蝙蝠》(“Bats”)一诗中,常人正是由于对死亡的本质没有足够的了解才在闲言中消磨自身,“关于死亡,人们可能发现,/有权发言者都保持了沉默:/其他人强行出头,一路走进死胡同/或舞台中央……但人类对死亡/一无所知。”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231页。英文原文此处为pulpit,译者译为“死胡同”,笔者认为略有不妥,遂在此改为“讲坛”。那些在公众场合滔滔不绝谈论自己对死亡及生命感想的人们,实际上很可能并不如那些沉默的人更本真地形成对死亡的领会,“漫无边际的清谈起着遮盖作用,把已有所领会和理解的东西带入虚假的澄清境界,也就是说,带入琐琐碎碎不可理解之中。”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233页。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每个人都可以对死亡侃侃而谈,都洞悉了生命和死亡的本质,殊不知死亡的本质恰恰又是在人们熙熙攘攘的清谈中被遮盖了。因此,诗人在本首诗的最后引用马格里斯(Margulies)的话说:“死亡吓得我们全都沉默”,告诫人们只有在缄默中才能更本真地“领会”对此在的终结存在的畏惧,缄默作为生存的本质可能性指出了向死而生之路径。
格吕克曾在《断裂,迟疑和缄默》(“Disruption, Hesitation, Silence”)一文中强调缄默在诗歌写作与境域想象中的重要作用:“吸引我的是省略,是未说出的,是暗示,是意味深长,是有意的沉默。那未说出的,对我而言,具有强大的力量:经常地,我渴望整首诗都能以这种词汇制作而成……暗示另一个时代,暗示一个世界,让它们置于其中就变得完整或复归完整。”Louise Glück, Proofs &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p.73.此在应该倾听良知的呼唤,而这呼唤是缄默无声的,“以这种方式呼唤着而令人有所领会的东西即是良知”。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374页。这呼声呼唤的对象是谁?是此在本身。“它非但不因此丧失其可知觉的性质,而且逼迫那被召唤、被唤起的此在进入其本身的缄默之中。”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377页。在诗集《阿弗尔诺》(Averno)的《回声》(“Echoes”)一诗中,良知的呼声以沉默的方式召唤诗人此在的本我生存,“几年的顺畅,此后/长期的沉默,像山谷里的沉寂/在群山送回你自己的/已经变成大自然的声音之前。/这沉默如今是我的同伴。/我问:我的灵魂因何而死?/那沉默回答说/如果你的灵魂已死,那么/你正活着的是谁的生命?你什么時候变成了那个人?”露易丝·格丽克:《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柳向阳、范静晔译,第65页。从生存论角度来看,这“沉默”的呼声将诗人从灵魂的死亡之渊中解救出来,让诗人意识到“我”活着正在活着的“那个人”的生命,实现了对主体意识的自我救赎和对死亡的本真领会。由此,格吕克超感性和超理性的精神维度和生存论境域通过缄默的呼声得以彰显。
埃塞克·科瑞特(Isaac Crates)在评论格吕克诗歌时曾说:“自《头生子》(1968)起,格吕克的作品开始娴熟地掌握了使用缄默的方法,她利用一些技巧在90年代的书中不断将其进行扩展和发展”。Isaac Cates, “Louise Glück: Interstices and Silences,”Literary Imagination, vol.5, no.3(November 2003), p.469.伊丽莎白·道得(Elizabeth Dodd)在评论格吕克的诗集时也提到:“她继续在诗歌中寻找个人的表达方式,尽管如此,她仍然依赖于沉默和省略,并避免极端的陈述或仅仅是私人的披露”。Elizabeth Dodd, The Veiled Mirror and the Woman Poet: H. D., Louise Bogan, Elizabeth Bishop, and Louise Glück, Columbia: U of Missouri P, 1992, p.149.但是在格吕克的生存诗学体系构建的过程中,缄默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修辞手法和表现方式,更在其中蕴含了诗人对生命本真存在意义的追寻和思考。瑞塔·佩帕斯(Rita Pappas)在评论格吕克最新出版的诗集《忠诚良善的夜》(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时说道:“她最后得出结论,生命中最令人难以忘怀、最神秘的时刻,不是通过言语,而是通过缄默的持久力量来理解的,这是她自己的过去给她的教训。” Rita SignorelliPappas, “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World Literature Today, vol.89, no.2(April 2015), p.68.被剥去了栖所和遮蔽的自身通过呼声被带回其自身,领会源始本真的生存状态。诗人在寂静中倾听良知沉默的召唤和指引,体悟到此在作为能在在根源处所具有的一种“无”性或“不”(Nichtigkeit)性。而这呼唤不付诸于任何音声,“唯欲归者闻之”。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374页。
四、结语
尽管格吕克倾向于以倾听和缄默的状态来面对世间众生,她也一直在用作诗这种纯粹的方式向我们道说着,这是因为“听和沉默这两种可能性属于话语的道说。”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第230页。她将自己的经历和领悟用语言在诗歌中诗化地表现出来,进入一种敞开的领域自行道说。在论文集《证据与理论》(Proofs & Theories)中她坦言诗歌对人类的普遍性作用:“诗歌不是作为一个个物品,而是作为一次次出席(presences)流传人间。每次当你读到一段值得记忆的文字,你就解放了一个同类的声音,将一个人类伙伴的灵魂再次释放到人间。我读诗就是为了听到那个声音。我写诗是为了向我听到的人倾诉。”Louise Glück, Proofs & Theories: Essays on Poetry, p.128.作为一名后自白派诗人,格吕克摆脱了自白派诗人独自揽镜、孤芳自赏的创作局限,将整个人类共同体面临的情感纠结和生存困境放在主要位置,建构生成了一种独特的声音美学和生存诗学。她的诗歌“逐渐抽离于心理学意义的内省而更为关注当下文化逻辑中的主体存在策略” 殷晓芳:《断裂与反讽——格里克神话诗歌的游牧路线》,《国外文学》2017年第2期,第87页。,为现代社会中挣扎求存、沉沦于世的人们指出了一条通过倾听和缄默通达人类诗意栖居的新途径,指引人们追求一种澄明无蔽的、源始自在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格吕克希望自己的诗作可以成为一种“范式”的原因之一吧!
〔作者简介〕生安锋,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郑春晓,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族裔文学中的文化共同体思想研究”(21&ZD281);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殖民主义、世界主义与中国文学的世界性研究”(18WXA002)
①耿幼壮:《文学的沉默——论布朗肖的文学思想》,《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5期,第76页。
②关于莱顿新书的具体分析和批评可参见张逸旻:《批评的“重置”——评莱顿的〈听物:文学中的声音机能〉》,《外国文学》2020年第5期,第173—182页。
③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著作残篇》,罗宾森英譯,楚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④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51页。
⑤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第2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