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阮咸起源问题
——基于丝绸之路上琉特琴乐器图像新证的思考
2022-05-09王雅婕
王雅婕
(上海开放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琵琶”一词在中国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指代并不相同,早期其不单单特指某样乐器,而是“琉特琴”类乐器的统称,主要包括曲项四弦琵琶、直项五弦琵琶及阮咸等。长达近一个世纪以来,学界一般认为:曲项四弦琵琶源自波斯,直项五弦琵琶源自印度,而阮咸为华夏旧器。然而,这种论断也存在一定的争议,比较突出的矛盾焦点集中在阮咸琵琶起源是外来还是本土上。一些日本学者和少数中国学者赞同阮咸由西域传来的外来说,而大部分中国学者则支持本土起源说。不同起源说的缘由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样来看待呢?
一、阮咸起源说
关于阮咸的起源问题,现有学说基本可以分为“乌孙公主”说、“弦鼗改制”说、“西域传入”说和“波斯起源”说四种,即中原、西域、波斯三个层面。其中,“乌孙公主”说和“弦鼗改制”说可视为中原起源说的代表,其主要依据是中国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原起源说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认可。
(一)阮咸起源的中原说
中国最早出现的琵琶类乐器应为秦汉子(秦琵琶),即后来的阮咸。目前,国内大量的音乐教材、研究著作,以及学术论文等,都对阮咸的起源持中原说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牛龙菲《敦煌壁画乐史资料总录与研究》,以及郑祖襄《汉代琵琶起源的史料及其分析考证》等。甚至一些辞典、工具书等皆广泛采用此说,影响深远。如《中国音乐辞典》载:
阮,弹拨乐器,据东汉傅玄《琵琶赋》序载,是当时人参照琴、筝、筑、箜篌等乐器创制而成。
中原说的依据主要为晋代傅玄《琵琶赋》中的史料:
《世本》不载作者。闻之故老云: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知音者裁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之乐。今观其器,中虚外实,天地之象也;盘圆柄直,阴阳之序也;柱十有二,配律吕也;四弦,法四时也。以方语目之,故云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杜挚以为嬴秦之末,盖苦长城之役,百姓弦鼗而鼓之。二者各有所据,以意断之,乌孙近焉。
这段史料描述了阮咸琵琶在当时的具体形制,表述了傅玄本人对阮咸起源的看法。此处作者同时列出“乌孙公主”说和“弦鼗改制”说,而认为“乌孙公主”说更有可能。这实际上也正表现出傅玄本人对于阮咸起源的问题并没有确切的判断,只是如同今天的研究者一样,推断一种更可靠的说法。然而,就是这种推测,成为中国历代史籍记载的参照。《宋书》卷十九《乐志》载:
琵琶,傅玄《琵琶赋》曰:“汉遣乌孙公主嫁昆弥,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筝、筑,为马上之乐。欲从方俗语,故名曰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风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为名。”杜挚云:“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并未评孰实,其器不列四厢。
《初学记》卷十六《乐部下》载:
释智匠《古今乐录》曰:“琵琶出自弦鼗。”
《旧唐书》卷二十九《乐志》载:
琵琶,四弦,汉乐也。初,秦长城之役,有弦鼗而鼓之。乃汉武帝嫁宗女于乌孙,乃裁筝、筑为马上乐,以慰其乡国之思,推而远之曰琵,引而近之曰琶,言其便于事也。
后世史籍不断对其加以转述和引用,造成了此类观点的延续。
因此,千百年来,阮咸是中国乐器的说法根深蒂固。但是,史料文献当中对阮咸的来源只有简要的猜测式记载,加之历史上记写史料的官员大都非音乐专业人士,在记写之时也并没有条件和可能进行相关考证和调查。即便傅玄本身精通音律,但他对于古代音乐交流的事项等可能并不了解和敏感,故他的表述只是猜测,而后世的史官却照单全收,使猜测成为流传千古的“事实”。
由于中国史籍对于音乐内容的记录存在一定的精简化、边缘化、承袭化等客观问题,在我们今天的研究中,应当带着批判性眼光来看待。笔者首先对傅玄有关阮咸起源问题提出的两种可能进行初浅分析。其一,“乌孙公主”说,原文中有“故老云”三字,故其更像是一个传说故事。冯文慈教授也因此认为其更像一种“魏晋时期奇说异谈流行的结果”。而更重要的是,在《汉书》、《新唐书》等正史中,虽然也曾对乌孙公主远嫁这一事件有过明确且相对详细的记载,却不曾提及制造新乐器一事。
其二,“弦鼗改制”说,后世史料也多有雷同。如《通典》卷一四四载:
今《清乐》奏琵琶,俗谓之“秦汉子”,圆体修颈而小,疑是弦鼗之遗制。傅玄云:“体圆柄直,柱有十二。”
首先,“圆体修颈而小”的形制,完全符合古代西亚地区长颈琉特琴的特征,公元前2000年就存在的美索不达米亚长颈琉特琴即为此类造型(后文详述)。第二,从柄上“有柱十二”可见,只有柄足够长,才有可能排开十二个柱子,而在一个细柄身上的品柱,则应该是与琵琶一样的通品,不然则无法排放。但通品类的乐器并不是中原乐器的特征,而具有鲜明的西域特性,这与西亚的长颈琉特琴也完全一致。
符合“圆体修颈而小”特征的似乎还有中国的“弦鼗”一器。弦鼗亦可称为“弦鞉”,史籍中并无对其的详细描述。而仅就“鼗”来看,其作为一种鼓,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东周和秦代(公元前770—前206年),汉代滕州龙阳店乐舞百戏画像石(图1)中,就保留了鼗鼓的形制造像。其鼓身为较小的圆形,双面蒙皮可敲击,鼓身下装把手,鼓面两侧系球,使用者通过摇晃把手使得两球击打鼓面而发声,形制和发声原理都很像现在小孩玩的拨浪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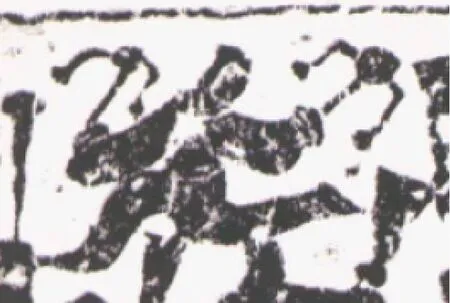
图1 山东滕州龙阳店乐舞百戏画像石中的鼗鼓①图片出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山东卷》,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76页。
由鼗演变成弦鼗的经过,中国学界的看法大致如《琵琶沿革图解》一文所述:
约在公元前214年,中国人民由鼗鼓去丸加轸、弦,创造出直柄、圆形音箱,两面蒙皮、用手弹拨的乐器,叫弦鼗,又名琵琶,因流行于秦地,故也谓之秦汉子。
这种说法也有一些可疑之处。首先,鼗是一个鼓,其跨越成弦乐器,比起西亚长颈圆共鸣箱的琉特琴的演变,似乎更难以理解。且历史上对此问题的记述几乎都是猜测的态度,望“形”生义。而且弦鼗既然是中国乐器演变而来的, 怎么会在历史上没有确切记载,没有流传,甚至无人认识呢?《通典》载:
阮咸亦秦琵琶也……武太后时,蜀人蒯朗于古墓中得之。晋竹林七贤图阮咸所弹与此类同,因谓之阮咸。
《新唐书·元行冲传》亦云:
有人破古冢,得铜器似琵琶,身正圆,人莫能辨。行冲曰,此阮咸所作器也,命易以木,弦之,其声亮雅,乐家遂谓之阮咸。
从这两则文献中笔者不禁生疑:在为阮咸定名的官员元行冲(652—729年)任太常少卿时的唐睿宗景云年间(710—712年),对于以产生于周秦,自汉代以来都有图像描绘的中国固有乐器弦鼗为原型,并由西晋(265—317年)阮咸加工而创的琵琶类乐器——秦汉子,竟然没有人知道吗?这或许正从侧面证实了此器为外来之物,在中原少有人能够辨识,后便借用了出土图像中的弹奏者阮咸的名字沿袭下来。
这就又产生出另一个疑问,即竹林七贤中阮咸所弹乐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笔者遍寻中国史籍也未找到答案,而在日本平安时代承平年间(约931—938年)的百科全书《和名类聚抄》中找到了一则解释:
阮咸,今案云:乐器中无此器名。晋竹林七贤中有阮咸,字仲容,疑仲容因琵琶体所造欤?
记载者以问句结束,则其也不能自信定论。而此处的琵琶,是否即是从西方传来的琉特乐器?关于“弦鼗改制”说,除了上述鼗鼓起源说,还有王耀华在《三弦艺术论》中提出的三弦弦鼗起源说:三弦是“由弦鼗经秦汉子并吸收多种外来因素改造而来的无品、无柱类弹拨乐器”。造成弦鼗是“万能”之器的根源,或许在于中国文献记载和文化研究判断的一种习惯性方法,表现为一味追求“远”“古”,而忽略了对其他文明流动的观照。古人难免望图生义,阮咸源于弦鼗的观点,大概也是一种只知其形而未解其质的判断。试想,“盘圆柄直”类乐器在中原曾有过弦鼗、秦汉子、秦琵琶、汉琵琶、阮咸等多种名称,而琵琶一词是早期外来琉特乐器在中原的统称,那么,一个在中原萌芽并发展起来的乐器又怎会用一个外来名称来指代,并且名称的变化如此频繁呢?这是否正反映出丝绸之路上的长颈琉特乐器经过西晋、南朝,再到唐朝,向着后世中原阮咸类乐器变迁的轨迹呢?
(二)阮咸起源的外来说
在前辈学者中,也有少部分提出了阮咸琵琶为传来之器的可能。其中一部分认为阮咸起源于与中国相邻的西域和中亚,而也有学者提出了其与西亚存在联系的可能性。
首先,西域起源说较有代表性的论断有朱谦之曾提出的在传入中国的琵琶中,“圆体、修颈有四弦十二柱的一种……传入中国,早在汉武帝之时,在西域当时为马上之乐器”。岸边成雄也曾指出:“阮咸在中国文献中,记述为秦始皇时代的鼗鼓发展而成,但在西域却有相同形态的鲁特(琉特)琴。我以为这才是真正使阮咸形成过程受到影响的因素。”他在随后的《日本正仓院乐器的起源》一文中,从实物考古着手,提出新疆龟兹壁画上发现的阮咸与中亚花剌子模一幅壁画上的乐器在形制上很相像,推断它们之间应有渊源。
另外,日本学者田边尚雄在《中国音乐史》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之弓形哈铺,张以羊皮于胴,变化而为三弦之形,入于埃及,乃有羊皮胴之那尔夫。此之种类,波斯大流士王以后,盛行于波斯,纪元以前,胴作圆形,张以兽皮,附以细长之柄,张弦数条。(波斯多用三条)当亚历山大帝国时,由波斯传入西域,流行各地。秦之百姓于长城之役,见其简单形状而模仿之;于平面鼓上插以棒,宛如鼗形,张弦用之,依所象形,名为弦鼓。行于秦末汉初,故又称秦汉子。……汉武帝时,由西域输入琵琶,弦鼓为之压倒;至改其胴如琵琶而以木制之,则为前汉末季事。及唐则天武后时,蜀人蒯朗,从古墓中得此乐器,见与晋竹林七贤图中阮咸所奏之乐器同,遂呼之为阮咸。”
沈知白在《中国音乐史纲要》中也提出:“琵琶这类拨弦乐器有长颈、短颈两种,前者有更悠久的历史。这类乐器最早约公元前两千年已见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小塑像襟上装饰的金属片和印章上。琴身小、颈长而有品,二弦,而无轸,以拨鼓弦;这乐器从巴比伦先后传至埃及和希腊(公元前1000年)……在汉代,从西域传入中国的是波斯的长颈琵琶;……长颈琵琶传中国后,必经改造而成中国的乐器,称秦汉、秦汉子、阮咸等,以区别于短颈琵琶。”
比较田边尚雄与沈知白的结论,他们对最初琴体形制的追溯有很大不同,并且在具体传播的时间节点上也有一定出入。但二者对于阮咸从西到东的传播路径的论述却基本一致,即由美索不达米亚到埃及、波斯,又经西域传至中原。
然而,上述观点大都空有结论,而没有具体的史料或考古图像资料证明,这就难免令人怀疑其中传承演变的逻辑和真实性。要想证明传播说可信,仍需对丝路所经各地长颈琉特乐器进行细致研究。因此,引入别国新的史料、例证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
二、丝绸之路上的“盘圆柄直”类琉特乐器考辨
要重新审视和梳理阮咸的起源问题,无非有两个突破口,即新史料和新的考古图像资料。史料方面,可以说前人几乎已经穷尽,加之东方世界除中国外,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习惯,故难以有新的有力证据。而在考古图像方面,东方世界反映逝者生前状态的墓葬、壁画众多,加之丝绸之路视角下的研究方法,为阮咸起源这一论题带来了新的研究契机。
(一)美索不达米亚的琉特琴
西亚的琉特类乐器主要为长颈的类型,而不见短颈的例证。在其起源问题的讨论上,威廉·施陶德所引证年代最为古老的例子出自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两河流域,伊拉克学者拉辛德同样认同美索不达米亚一带是琉特琴乐器的发祥地,并指出此类乐器现存最早的证据来源自阿卡德人统治时期。笔者所见现存最早的琉特琴图像(图2)出现在阿卡德时期(约公元前2350—前2170年)的轮状印章上,即弓形竖琴和里拉琴出现后的约一千年。图像表现的是与宗教有关的场景,画面中的琉特琴具有长长的琴柄且共鸣箱形制较小,弹琉特琴的乐师坐在画面中间偏左侧的凳子上,正在为前面就坐的神灵们表演。琉特琴乐师的体型比神灵小,暗示其身份地位低贱。

图2 阿卡德时期轮状印章上的琉特琴1②图片出处:《图片音乐史·美索不达米亚卷》,(德国)莱比锡音乐出版社,1984年,第63页。图3—7均出自本书,分别在第63、93、105、145、147页。
阿卡德时期的另外一个轮状印章上也刻画了类似的图景(图3),图中的琉特琴乐师在画面最左边的角落里跪坐着为前面的蝎子神及手拿拂尘坐着的神灵等表演,其身体同样要比诸神小很多。可见在形成之初的阿卡德时期,琉特琴主要使用在宗教场合,由专门的乐师进行演奏。但这里的琉特琴共鸣箱刻画并不非常清晰,我们只能推断其为长颈和小型共鸣箱的样式。

图3 阿卡德时期轮状印章上的琉特琴2
随后,长颈琉特琴在世俗场合也同样得到了流传和体现。首先,其中一部分是有关放牧的场景,比如古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1950—前153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赤陶浮雕(图4),刻画了牧羊人在放牧途中坐在岩石上演奏长颈琉特琴的情景,他身后有羊群,前方的牧犬正转过身来聚精会神地聆听。该长颈琉特琴的共鸣箱较圆,有笔直的长颈,横抱演奏。

图4 古巴比伦时期牧羊人演奏长颈琉特琴赤陶浮雕
类似的放牧场景再如麦莉斯胡(Meli-Sihu)王时期(约公元前1186—前1172年)的石碑浮雕(图5),画面中间的长颈琉特琴演奏者正边走边奏。

图5 麦莉斯胡王时期石碑
在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曾出现的居民中,如闪米特等族群属于游牧民族,大都过着游牧或者半游牧半定居的生活。因此,这些游牧人的长颈琉特琴演奏场面,应该也是美索不达米亚早期琉特琴在世俗场合使用的再现。长柄的样式较短颈琉特琴更适于游牧人在行走、骑行等环境中抱持使用,故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很少能够见到短颈琉特琴的类型。而琉特类乐器体型小巧,通过左手按弦,改变弦震动的长度,就可以产生更多的音高,表现更丰富的音色,较之于早期的里拉琴、竖琴乐器都更为先进和方便。从这些层面来讲,琉特琴的产生完全符合弦鸣乐器的发展规律,是弦鸣乐器在早期西亚环境之下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随着这种乐器的普及,我们能够见到其在塞琉古时期(约公元前323—前140年)与不同乐器的合奏及为歌舞伴奏等,在宴飨俗乐中大量运用。
在抱琴方式上,站姿或者在行进中的演奏,一般为琴颈朝斜上方的样式;而在坐姿演奏中也有横抱的方式(如图4),这可能是由于坐姿演奏时演奏者的身体更为放松,上身也没有持琴压力。但总体来说,从长颈琉特琴发源之初的阿卡德时期,后经巴比伦时期,直到喀西特王朝时期(公元前14世纪),我们所看到的长颈琉特琴的抱持方法基本上是琴杆朝上斜抱。而到塞琉古时期,这种现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时期的长颈琉特琴虽然仍为圆形或者是椭圆形的小共鸣箱加长颈的样式,但在笔者所掌握十余幅此时期的长颈琉特琴图像中,不论是独奏还是与其他乐器合奏的长颈琉特琴,均为向下斜抱的持琴方法。比如塞琉古时期演奏长颈琉特琴与吹双管乐器的合奏双陶人女乐师俑(图6)中,左侧持长颈琉特琴乐师为右手拨弦、左手按弦、琴头朝下的持琴方式。

图6 塞琉古时期双陶人女乐师俑
此外,其他塞琉古时期美索不达米亚长颈琉特琴的图像都证明了这种持琴方式的转变。比如塞琉古时期长颈琉特琴女乐师俑(图7)也充分显示了这一特点。
琴头朝下的演奏方式,由于眼睛比较难看到左手的按弦位置,演奏难度应该更大,对演奏者的技术要求也相应更高。琉特琴发展到塞琉古时期,形制和演奏方法都应该已经逐渐成熟和定型了,这一时期的图像大都表现的是乐师等专业演奏人员,其技艺应该较牧羊人更成熟,或者说炫技的成分也更多了,因此产生了大量向斜下方持琴的演奏方式也合情合理。在弦数方面,此时期也开始有了较为明确的表现,如图7有两条弦的划痕,应为二弦的形制。从更多的早期图像来看,我们仍无法准确断定其琴弦的具体数量,但因此类长颈琉特琴的琴杆通常比较细,我们也可推测其所张弦数应该不会太多。笔者认为其应该在三四根琴弦以内,而最常出现的应为二弦样式。

图7 塞琉古时期长颈琉特琴女乐师俑
综上,美索不达米亚的琉特琴几乎全部为小的圆形共鸣箱加长颈的样式,这是游牧民族乐器的典型特征。它们出现于公元前2350年左右的阿卡德时期,并在随后的两千多年里流传和演变。其形制特征符合我国典籍当中对于阮咸乐器“盘圆柄直”的描述。
(二)古埃及的琉特琴
以现有证据分析,埃及的琉特琴应出现在新王国时期,且以新王国的第一个朝代——第十八王朝(约公元前1575—前1308年)最为突出。其从形制,特别是共鸣箱的形状上来划分,有两种不同的规格。第一种是细长的椭圆形小型共鸣箱的样式,如出自特巴尼大墓地一个哈特谢普苏特女王时代(约公元前1520—前1484年)的音乐家墓室中的木质椭圆形共鸣箱长颈琉特琴(图8),出土时其琴颈上还带有琴轴和残弦的痕迹。

图8 埃及椭圆形共鸣箱长颈琉特琴实物③图片出处:《图片音乐史·埃及卷》,(德国)莱比锡音乐出版社,1961年,第131页。图9、10均出自本书,分别在第131、69页。
而另外一种长颈琉特琴的共鸣箱为更小的圆形样式,如出自德尔·艾尔·麦迪纳赫第1389号新王国时代第十八王朝特巴尼墓室的舞女用圆形共鸣箱长颈琉特琴(图9)。其琴杆细长,共鸣箱较小,似乎也可以用中国典籍当中形容阮咸的“盘圆柄直”来描述。

图9 埃及圆形共鸣箱长颈琉特琴实物
且如埃及第十八王朝的特巴尼大墓中宴会场景的壁画(图10)等图像所示,上述两种类型的琉特琴多同时使用。图10中,最左边的女乐师手持椭圆形共鸣箱长颈琉特琴,紧挨着她的女乐师则横抱圆形共鸣箱长颈琉特琴演奏。圆形形制琉特琴的弦轴处垂下两根穗子装饰,表明其为二弦的形制。

图10 埃及音乐宴会场景壁画中的长颈琉特琴演奏
此两种小型共鸣箱形制的长颈琉特琴与美索不达米亚的类型基本一致,但埃及将其表现得更为固定和明确。从这些实物和图像当中不难看出,埃及长颈琉特琴的琴杆是一直插入到共鸣箱接近底端的位置。那么,埃及长颈琉特琴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连接琴杆和共鸣箱的呢?学者赵克礼认为埃及的长颈琉特琴与当时典型的美索不达米亚长颈琉特琴的琴杆与共鸣体的固定方法是不同的:美索不达米亚琉特琴的琴杆“一直延伸到表面板的尾端,然后在其稍微突出的尾端固定住。而典型的埃及鲁特琴,棹柄也在表面板的上端,然而,它在中途就结束了延伸,表面板上面有明显的皮质物,缝绑着棹柄”。从图10等图像上,我们似乎看到了这种缝绑共鸣箱体与琴杆的皮质物,且从出土实物和一些图像所显示的此类乐器共鸣箱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其有三到四组成对的音孔,因此在两孔之间缝皮质物以固定的推测是合理的。另外,图10还向我们展示出埃及长颈琉特琴的细长琴杆上,多平均分布着一些似用线绳类物品缠绕的品格,其作用类似于后世乐器的品、柱,以方便演奏者按弦。此形制结构也表明了埃及的长颈琉特类乐器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音律特征。而从一些图像和实物资料中表现出的琴轴,或者缠弦在琴杆后留下的穗子装饰等,我们也可以看出埃及长颈琉特琴的弦数一般为两到三根,而以两根为主(如图8、图10均为两根)。
可见,埃及的长颈琉特琴乐器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此类乐器除了连接琴杆和共鸣箱的方法有所不同之外,其他如形制、弦数、演奏方法等都显示出一定的血缘关系。这一乐器出现在埃及对外经济贸易、军事往来及文化交流频繁的新王朝之时,较美索不达米亚的此类乐器晚了五百年至一千年,故应为一种受到西亚,特别是美索不达米亚影响,由其传入埃及并发展起来的乐器形式。
(三)古代波斯的琉特琴
相比较而言,波斯短颈琉特琴是琉特乐器的巨大发展,但由于其主要对后世的琵琶产生影响,故这里不对波斯短颈琉特琴展开论述,而主要讨论波斯长颈琉特的形制和特征。
与大多数西亚国家一样,波斯的长颈琉特琴也出现得比较早。据《新格鲁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论述,伊朗西部的古代埃兰(Elam)王国首都苏萨遗址出土过一些用赤陶土块刻画的弹琉特琴的形象,演奏者大多是裸体的女人和奇形怪状的男人们,这可能是当时音乐家在社会中的地位比较低的缘故。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琉特琴的尺寸开始逐渐增大,到公元前9—10世纪的伊朗青铜高脚杯上刻画的琉特琴已经有140厘米长了。例如,埃兰阿见(Arjan)地区一个公元前650年左右的银碗,展现出了一幅热闹的景象。这个银碗的装饰从内向外围绕着圆心的一朵小花,一共分为五层,热闹的音乐舞蹈场面在第二层(图11)。画面从左到右分别是打手鼓,歌唱,舞蹈,演奏里拉琴、角型竖琴、双管乐器、长颈琉特琴和踩高跷、杂技表演的艺人,以及正在准备食物及饮料,或递送酒杯和陶盆的仆人们,王室贵族正坐在高椅上,欣赏着这个盛大的乐队合奏和技艺表演。这完全是一个世俗场景的描绘,并且向我们展示了早期伊朗所使用乐器的类型,它们大致是与美索不达米亚一脉相承的。

图11-1 埃兰公元前650年银碗⑤图11(1、2)出处:Stanley Sadie,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XII),p527。

图11-2 埃兰公元前650年银碗上的音乐宴会图案线描图
从大量的图像中我们能够看到,自公元前1000年左右以后,波斯长颈琉特琴在伊朗的艺术表现中变得越来越少,甚至逐渐消失了。但此乐器在后伊斯兰时代的一些波斯细密画中仍频频出现,并在现代社会中广泛使用着,演变成为二弦的都塔尔(Dutar)、三弦的塞塔尔(Setar)、四弦的卡塔尔(Cartar)等等。由此可见,长颈琉特琴是一直存在于伊朗及整个西亚和伊斯兰世界的,其艺术表现上的空白期,应主要是由于失宠于宫廷精英阶层。事实上,长颈琉特琴作为伊斯兰世界重要的民间弹拨乐器,在各种不同的民间音乐场合获得了更大的发展,这一点从后世伊斯兰世界长颈琉特类乐器的繁荣就不难推断出。而伴随着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及波斯帝国的建立和扩张要求,作为文化事项,长颈琉特琴也完全具备着向东流传至中亚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动能,从而继续向东影响中亚乃至中原一带。
综合以上西亚地区琉特乐器的情况,笔者认为,西亚地区的长颈琉特琴符合由美索不达米亚起源,并且向着埃及和波斯传播的流传过程,其形制特征也完全符合“盘圆柄直”的描述。与后世阮咸相比,二者间的不同主要在于阮咸共鸣箱的增大,以及琴颈的变短和加宽。那么这种变化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又是发生在什么地区呢?
(四)中亚的琉特琴
中亚琉特琴的类型很丰富。这其中包括西亚长颈琉特琴类乐器,中亚西部的花剌子模文化中也有大量此类乐器。如图12的①—⑤全部为公元1—3世纪中亚的手持琉特乐器陶俑。其中,②—④为椭圆形共鸣箱类型,而①和⑤则为圆形共鸣箱类型。其持琴演奏的方式,除了图12—③是完全横抱之外,其余均为琴头向下倾斜的样式,与美索不达米亚琉特琴在塞琉古时期的抱持方法一致。我们虽然不能从图像中准确判断每一只琴的弦数,但从刻画相对较为清晰的图12—③中,可见共鸣箱体上明显刻画了两条弦的痕迹,并且其琴杆、琴弦与共鸣箱的连接方式也与西亚琉特琴相同。特别引人注意的应该是图12—⑤,其“盘圆柄直”的形态,与阮咸几乎完全相同。

图12 中亚花剌子模文化公元1—3世纪长颈琉特琴⑥图片出处: 《图片音乐史·中亚卷》,(德国)莱比锡音乐出版社,1987年,第58页。图13—15均出自本书,分别在第93、75、95页。
可见中亚长颈琉特琴与西亚此类乐器有着明显的共性和渊源关系,但也存在一些细小的不同。早期西亚长颈琉特琴的琴杆长度至少要有共鸣箱长度的三到四倍,而中亚此类乐器的琴柄长度往往只有共鸣箱的一到两倍。即中亚长颈琉特琴的琴颈开始变短,且有了加粗的迹象。另外,共鸣箱变大、变圆似乎也成为中亚琉特琴的一种趋势和特点。如中亚加卡巴格地区卡什卡达加绿洲帕查尔城遗址的公元1—3世纪手持琉特琴陶土小人像(图13),该造像属于索格地亚文化,人像所持琴器除了琴柄较之前的长颈琉特琴短之外,仍旧是“盘圆柄直”的特征,而共鸣箱也较西亚圆形共鸣箱的长颈琉特琴来说更圆、更大。造像还刻画出了清晰的四条弦,持拨演奏,这些特征都与中原的阮咸非常接近。另外,出土于特尔姆斯市,表现巴克特里亚文化的公元1—3世纪手持琉特琴陶土小人像手中所持琉特琴类乐器(图14),亦表现出短柄而共鸣箱为正圆形的特征,而其五根弦的刻画较为夸张。

图13 中亚帕查尔公元1—3世纪陶土琉特琴俑像

图14 巴克特里亚公元1—3世纪陶土琉特琴俑像
此外,中亚地区带有强烈希腊—罗马影响痕迹的阿夫拉西阿卜城址等地,还出土了大量公元1—3世纪的9—10厘米高手持琉特类乐器的陶土小人像(图15)。从这些琉特乐器的轮廓和痕迹上看,它们大多为圆形共鸣箱加一根不太长的琴柄,从共鸣箱上的画弦痕迹来看,也大多为三到四根弦的样式。此类乐器的大量出土,证明了其在中亚地区的出现绝非偶然,而是在经过了一定的发展后基本定型的结果。

图15 中亚阿夫拉西阿卜城址的公元1—3世纪手持琉特类乐器的陶土小人像
从上述证据看,中原阮咸类乐器的形制首先可以追溯到公元1—3世纪的中亚。由西亚传入的长颈琉特琴类乐器在中亚的环境当中,椭圆形共鸣箱的样式逐渐变少,而以圆形共鸣箱的样式为主流,并且尺寸逐渐加大;琴颈缩短,琴杆一定程度上加宽。而自此,此类乐器称为“盘圆柄直”的琉特琴乐器,似乎比称长颈琉特琴类乐器更为合适了。
四、结论
综上,笔者认为在前丝绸之路时代的整个东方,长颈琉特琴乐器已经进行了充分的东传实践。在这其中,西亚所扮演的角色是起源和第一阶段的传播。琉特乐器首先发源于公元前2000多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此类乐器与游牧民族阿卡德人的生活方式相适应,是典型的马背民族的乐器,且形制以小型共鸣箱加长颈的样式为典型,便于牧民在行走和游牧时携带和演奏。
在大约七八百年后,由于整个西亚北非社会、文化大融和、大碰撞,此类乐器传至新王国时代的埃及,并逐步定型为圆形和椭圆形两种不同的共鸣箱形制,琴弦较少,一般为二到四弦,有持拨子演奏的情况,而也有一部分是用手拨奏的。在此时的图像中已可见音品的部件,证明其可以通过简单的品格按弦来表现更宽广的音域和丰富的音色,这是琉特乐器在西亚本土取代竖琴类乐器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音品增多而乐器体积变小所带来的音色丰富性和便携性,琉特乐器得到了进一步的广泛传播。
波斯地区早期的埃兰和米底文化都留存了小型共鸣箱的西亚长颈琉特类乐器,而自波斯帝国成立及后世逐步进入伊斯兰时代,长颈琉特琴也开始出现在一些器物的装饰、细密画中,并应用到具体的音乐表现之中,这与埃及的传播影响应该关系不大,而主要由于与美索不达米亚早期和波斯西部的埃兰文化相互影响,以及错综复杂的历史、文化关联。在两河流域的长颈琉特琴发展成熟后,同样影响了后世的波斯。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阮咸乐器起源的外来说,尽管诸位学者对于阮咸传入的经过各有不同意见,但对于其过程中波斯的琉特乐器传至中亚这一点,却是统一的。笔者也认可这一点,原因有二。首先,波斯东部与中亚接壤,历史上军事、政治、文化联系非常频繁。第二,亚历山大的东征。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希腊、埃及、波斯之后,继而在中亚建立起了希腊化的国家。其军事征服的背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琉特乐器的交流也自然位列其中。
中亚可以说是琉特乐器东传过程中的转折点,特别就“盘圆柄直”的阮咸乐器而言,中亚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首先,中亚在文化上被称为“贫瘠”之地,指中亚本身没有自己辉煌的历史及文化积淀,其文化特色主要表现为吸收和融合。东西交流为中亚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宝藏,两河流域、埃及、波斯的文化在这里汇总和交融,产生着奇妙的“化学”变化。因此,我们也在中亚地区看到了阮咸琵琶的最初样貌。它从西亚地区较小的圆形和椭圆形两种共鸣箱加细长琴颈的样式,发展出以圆形共鸣箱为主的多样性形制,并且琴柄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变短,共鸣箱逐步增大。其作为琉特琴的一种却并不能够再明确地划分为短颈或长颈类型,而应被定性为“盘圆柄直”的样式。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对阮咸类乐器在丝绸之路的传播过程的论述中,并没有涉及印度和早期新疆地区的情况,是由于在印度的资料中基本不曾见到西亚系长颈琉特琴和任何“盘圆柄直”类乐器的图像和记载。新疆地区以龟兹石窟、壁画为主,的确出现了大量“盘圆柄直”类阮咸乐器的图像,它们主要有近似于现今形式的阮和龟兹固有形式的阮两种形式,从传播的角度看时间和样式不符,而分别更像后世中原影响的产物及龟兹地区独立发展的结果。故西亚传来的长颈琉特乐器经西域传播至中原,西域则主要受中亚的直接影响,而并没有经过新疆地区的中转。回溯史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中原与西亚、中亚等地在早期曾有过直接交流和沟通的印迹。比如波斯在安息王朝时代(约公元前248—前227年)即与中国发生了频繁的交通关系,汉武帝时即令张骞出使西域,曾到达地处阿富汗北部一带的大夏国,打开丝绸之路这一东西方互通之路,使得波斯、中亚等地的商人往来络绎不绝。因此,“至武帝时,大征西域而服属之,新乐佣、散乐之类,盛传中国,因之中国音乐之组织根本上起变化”。这些都是西亚长颈琉特乐器经中亚传至中原的背景要素。
当长颈琉特乐器完成了其在丝绸之路的前端、中段——西亚、中亚等地的传播后,又恰逢汉代这一国力强盛、内外通达的历史时代,此时的客观条件及社会环境都为其传入中原奠定了基石。关于阮咸类乐器在中原出现的时间,学界一般认为是在汉代,相关史料中,如东汉末年刘熙《释名》和应劭《风俗通义》,以及稍晚一些的晋代傅玄《琵琶赋》等,都是公元3世纪前后,或更晚一些的史料。而与史籍相一致的,在浙江绍兴一带下窑陈村出土的阮咸乐器形象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阮咸造像。此文物下方刻有非常关键的“永安三年(260年)”字样,揭示了其为三国孙吴时期之物。这也把中原阮咸类乐器图像的可见时间框定在了公元3世纪前后。从图16中,我们可清晰看到该乐器为圆形共鸣箱、长颈、宽指板、多柱,指板上有通品的形制,演奏形式为一手按弦一手拨奏。

图16 青釉仓罐及阮咸局部图⑦图片出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
由上可知,中亚的长颈琉特琴及“盘圆柄直”类乐器从公元1世纪开始出现,公元3世纪时数量众多,汉末传至中原并在史籍和图像资料中有所体现。
笔者认为,阮咸类乐器应为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长颈琉特琴逐步流传至埃及、波斯、中亚,后进而逐渐传入河西走廊并进入中原的。这一过程体现出中国音乐文化,乃至整个东方文化的形成,都是在交流当中前行的。如仅从中原阮咸史料、形制及在中原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而不去考虑丝绸之路上琉特乐器、“盘圆柄直”类乐器的整体发展和变迁的话,是很难对其源头、流变过程进行准确判断的。我们应当首先认清,任何一种器物都是特定环境下催生的,琉特乐器是适应于马背民族的产物,在汉代甚至更早的时候进入了中原,引起了中原人的强烈兴趣,并对其加以不断吸收和改良,而朝本土化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同时承认的是,文化的变迁是双向作用的结果,应充分肯定中原对于阮咸琵琶的改造。中原在阮咸乐器演变发展过程中,并不是无所作为地对琉特乐器全盘接受,而是以积极的姿态及符合自我文化积淀的诉求,参与了这一改造过程。经过这一变迁历程,中原的阮咸乐器已经较原来西亚的长颈琉特琴产生了很大的改变,其在形制上逐步定型为“盘圆柄直”、共鸣箱较大的现代阮咸琵琶样式。这种改制和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在原因,就是中原农耕民族的生活环境并不需要较小的共鸣箱的便携性,以及较长琴杆在行走或骑马演奏时抱持的稳定性,而是需要一种适应农耕民族坐奏的样式。到西魏以后,随着音乐性要求的提高,阮咸品位的数量逐渐增多,至唐定型为四弦、十二柱的样式。演奏方式从单人独奏、双人合奏不断发展至中、晚唐时期频繁用于乐队的演奏。拨弦方式则为指弹、拨弹兼而有之。同时,受中国佛教石窟及中原艺术的影响,在乐器样式方面也体现出了明显的多样性,有直颈、曲颈、长颈、短颈、凤首等不同类型,以及圆形、花边形、多边形等多种共鸣箱类型,这些形制都凸显出中国风格的造型艺术和审美特色。在今天,阮咸已经彻头彻尾地变身为中华民族的代表性乐器,也使得人们逐渐忘却和忽略了其远在西亚的长颈琉特琴胞兄,以及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渊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