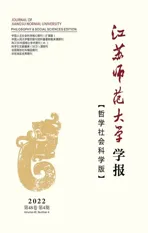中韩笔谈文献中的衣冠问题新探
——兼谈东亚笔谈的研究方法
2022-03-18张伯伟
张伯伟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一
东亚地区在二十世纪以前,都处于以汉文化为核心的文化圈中。虽然语言不通,但一般接受过教育的人,都能识得汉字,因而在彼此相见的场合,他们就能够“以笔代舌”,通过大家都能理解的汉字来进行交流,故谓之“笔谈”(Sinitic brushtalk)。传世文献很多,主要集中在中朝、中日、中越以及朝日之间(1)也有中国人与西洋人的笔谈,如张德彝于同治五年(1866)随斌椿出使欧洲,著《航海述奇》,其中《法国日记》曾记载拜访“姓茹名良者”,“并不交谈,以笔书之,可通其意”。所谓“茹良”,当指Stanislas Julien,今通译作“儒莲”,是当时欧洲最优秀的汉学家。但此类文献数量极为有限,故暂不涉及。。绝大多数的笔谈文献,都有特定的时间、地点、人物、情境,其所保存的记录新鲜而生动,它一方面可以让我们直接接触到一幕幕真切的历史场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谈话内容皆真实可信),但如果使用不当,也很容易陷入“以偏概全”或掉进“碎片化”的陷阱。因此,在面对这一类文献的时候,使用“长时段”的研究方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和必要。
“长时段”(longue durée)一词,明眼人立刻知道它是来自于法国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史学的概念,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时段”和“短时段”。布罗代尔指出:“传统历史学关心的是短时段、个人和事件,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那种急匆匆的、戏剧性的、短促的叙述节奏。”(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Écrits sur l'Histoire),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在这里,“传统”完全不同于汉语语境中带有权威而不容置疑的意味,相反是一个贬义词。较为高明的是一种“对局势的描述”,即中时段式的研究,“这种描述考察的是历史时间的大段落,以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为一段进行研究”(3)[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Écrits sur l'Histoire),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在他看来,“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4)[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Écrits sur l'Histoire),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而中时段尽管“理所当然应该直接引出长时段的概念”,但实际情形非特不是如此,“还发生着返回到短时段的现象”(5)[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Écrits sur l'Histoire),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因此,布罗代尔史学中最重要的概念就是“长时段”,尽管他必然也会在自身的研究中使用“短时段”或“中时段”。他认为,“从短时段转向较长的时段,然后转向深远的视域(只要它存在,它肯定是智者的时段),这时就可以重新思考一切,重新建构周围的一切。历史学家怎么会不被这种前景所吸引”(6)[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Écrits sur l'Histoire),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所谓“长时段”,大致是从一个世纪到几个世纪,其最大的长处在于,可能较准确地发现一个缓慢的、层积的历史结构的“断裂点”,“是相互矛盾的压力所造成的它们或快或慢的损坏”(7)[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Écrits sur l'Histoire),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9页。。布罗代尔秉持这样的史学观念,完成了两部代表性巨著,即《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以往人们利用笔谈文献从事研究之际,大多采用了短时段的方法,将两个人或一群人在某一时刻的笔谈作为研究对象,属于一种“个人和事件”的研究。有些研究能够超越此范围,可以达到“中时段”。我想说的是,即便考察文献的跨度超越了五十年,但受到目光局限,仍是一个无法超越中时段的“对局势的描述”。若干年前我在《名称·文献·方法——关于“燕行录”研究的若干问题》中曾经提倡运用“长时段”的方法研究东亚行纪(8)原载《南国学术》2015年第1期,后经修改收入张伯伟著《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第七章,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09-233页。另外,张伯伟在《“燕行录”研究论集》“前言”中也强调了“长时段”的研究,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第3-5页。,笔谈资料大多集中在东亚行纪之中,所以,其研究方法也应该是可以贯通的。我想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尽管布罗代尔对“三个时段”有明显的轩轾,但在历史研究中,不同时段的考察方法不是也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没有“短时段”的锱铢累积,我们会失去历史的丰富性;没有“中时段”的趋势变动,我们可能无视历史的阶段性;但如果没有“长时段”的眼光,我们可能会迷失在历史之树的树叶上,同时也无法捕捉到历史阶段的转折点。本文拟截取十七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段,具体研究的是中韩之间的笔谈。之所以选择中韩笔谈文献,原因一是存世文献的丰富,二是观念变化的曲折,基于这两点原因,于是就有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这些文献在东亚笔谈的研究中具备了某种典型性。就研究方法而言,对于中韩笔谈的剖析,似乎也足以代表东亚笔谈。
这里说的“十七世纪中叶”,准确地说,是从代表明清鼎革的崇祯十七年(朝鲜仁祖二十二年),也就是顺治元年(1644)开始的。在中国历史上,这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权更迭,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取代汉族政权的更迭。所以,不仅在政治上有许多变化,而且在风俗上(比如服装、薙发、婚葬等)也与明朝有显著区别。对于朝鲜半岛的君臣上下而言,明朝对于他们有“再造之恩”,在其心目中,也一直视明朝为“天朝”,因而那时的使行记录一般都冠以“朝天录”、“朝天日记”等名,彼时自称的“小中华”,是相对于“大中华”而言的。其心理状态如果不说是崇拜,至少也应该说是谦逊的。但在明清鼎革之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首先是由“朝天”改称为“燕行”,这一方面代表了朝鲜士大夫在政治上对清朝“含忍而又事之”(9)语出洪敬谟《燕槎汇苑总叙》,文中亦将朝鲜朝对明清易代的感受作了对比:“我本朝与皇明并立……皇朝,中华也,吾初受命之上国也……崇祯甲申,清人入主中国,我以畏天之故,含忍而又事之如皇明。”(《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13册,韩国古典翻译院,2011年版,第336页)的无奈(如蔡济恭将其行纪命名为《含忍录》),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他们在文化上对清朝的鄙视,认为这个政权属“夷”因而也不配“天朝”之称。其次是心理状态的变化,此时的“小中华”面对的是“腥膻毡裘”的“胡夷”,“华夷”的身份至此发生了转变,朝鲜人进入中国,犹如从文明之地进入蛮夷之邦,总是自觉地带着与身俱来的骄傲和自豪,特别是拥有“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身份的人。也许正是有见于此,一些学者就得出了“明朝后无中国”(或曰“十七世纪以后无中国”)的结论(10)参见葛兆光《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华书局,2014年版。作者在该书中多处、反复阐述了这一核心观点。,把以中国为核心的汉文化圈的崩坏追溯到四百年前。这个结论可以得到部分文献的支撑是显而易见的,如果用“短时段”甚至“中时段”的方法考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然而,“人们不无理由地说,短时段是所有时段中最变化莫测、最具欺骗性的”(11)[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在布罗代尔的忠告面前,我们实在应该对依据个别人物、事件而导致的结论保持必要的警惕。
本文拟以“长时段”为研究方法,但也不废“短时段”和“中时段”的呈现。所以在写作上,我试图通过几个集中的片段,呈现短时段的历史图景;这些以时间顺序展现的历史图景,构成了作为中时段的趋势变动;通过联缀起来的不同的趋势变动,不仅可以看到在一个长时段中丰富而又变化着(或大或小)的历史图景,也能够理解和把握东亚汉文化圈的“断裂点”,同时也能呈现其外部压力和内部挣扎的多重力量,是如何造成了这一文化圈的“或快或慢的损坏”。我要讨论的有三个问题,即“衣冠服饰”、“华夷变迁”和“中州人物”,每一个问题都是一幅历史图景的长卷,而透过三幅长卷的迭加,可以让我们发现在“断裂点”上的惊人相似。本文是对“衣冠”问题的讨论。
二
儒家对于服饰是非常重视的,因而有“衣冠文物”之说。中国之所以有“华夏”之名,就与衣冠密不可分,所以孔颖达在《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下《疏》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12)《十三经注疏》下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年版,第2148页。直到明代的虞守随也说:“服饰在人其事若小,而所系甚大……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也。”(13)《明实录·武宗实录》卷一七〇,正德十四年正月乙卯,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3285页。但在明清鼎革之后,薙发易服,对于汉族人而言,当然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和痛苦,所以,当朝鲜使臣来到中国,由于他们的服饰还是“明制”,汉人因从中看到“汉官威仪”而感慨,朝鲜人则既是自傲也是为了探测汉人心理,便常常以服饰衣冠为话题。
顺治三年(1646),郭弘址以书状官身份出使中国,宿抚宁县汉人王运恒家,与之笔谈,问曰:“今日吾行,秀才以为如何?”王答:“尚存父母遗体,贤于我辈万万。”所谓“遗体”,即指以往的衣冠发式,王氏还手指郭氏头戴之网巾云:“此乃我太祖颁制之物也。”且表情“愀然久之”(14)郭弘址:《丙戌燕行日记》,林基中编《燕行录续集》第107册,韩国尚书院,2008年版,第457页。。
康熙元年(1662),郑太和以正使身份入中国,在永平府曾与魏际瑞(伯子)笔谈,伯子回家后对其子世杰回忆十年前(1652)往事云:“高丽使者裹网巾、著纱帽,朱袍方袖,束带坐马上入朝,都人叹为汉官威仪。”(15)郑太和:《阳坡相公己壬燕行录》,《燕行录续集》第108册,第268页。李东溟为此行书状官,与姜君弼、君辅兄弟笔谈时,也故意询问“天下衣冠尽变否”(16)《(壬寅)进贺兼陈奏行书状官李东溟闻见事件》,《同文汇考》补编卷一,第11册,台北珪庭出版社,1980年版,第390页。?
康熙二年(1663),李曼以副使身份入中国,宿秀才刘舜脉家,与之笔谈,“问以近年兴亡事迹及民生休咎”,舜脉父年七十余,躲在后舍,愧对译官云:“吾欲见东国使臣,而奈此头无冠何?”直到晚上,李曼使人招之,则自言老监生,“剃发以来,愧见外人”(17)《(癸卯)进贺兼谢恩行副使李曼闻见事件》,同上注,第391-392页。。
康熙五年(1666),正使许积、副使南龙翼、书状官孟胄瑞入中国,在野鸡坉与赵妍笔谈,问曰:“大明子孙尚有余存者乎?衣冠亦思旧时乎?”赵以诗答之,有“汉仪常思想,何时变中华”(18)佚名《燕中闻见》,林基中编《燕行录全集》第95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版,第56页。之句,也被他们记载下来。
康熙八年(1669),闵鼎重以正使身份入中国,在玉田县宿王秀才家,与之笔谈,他故意发问:“明朝士人冠服带履之制可得一一见示耶?”(19)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22册,第379页。在广宁卫与知县颜凤姿笔谈时,又再次询问:“旧典太学生、州县生材、秀才及举人巾服带鞋之制,可得闻乎?”(20)闵鼎重:《老峰燕行记》,《燕行录全集》第22册,第389页。其所谓“旧典”,亦即“明制”。
尽管我们常常将笔谈的内容看成是真实场景的记录,但实际上,发问者、回答者有身份、地域等差别,辑录成文时也同样是有所选择的。上述记录的发问者,其身份基本上属于“三使”之一,在明清鼎革之后来中国,负有了解当下中国国情并向朝鲜国王报告的职责。而他们内心的期待,大多是希望汉人不忘故国、有报雠复明之心。编入《同文汇考》“补编”中的“使行别单”有六卷之多,起于仁祖十七年(崇祯四年,1639),讫于正祖九年(乾隆五十年,1785),本来就是藏在王室的档案,是使臣回国后上呈的大大小小的“闻见事件”,而具有“三使”身份的“燕行录”作者,其记录也同样要上报国王。即便在这样的文献中,有的使臣也还是会比较诚实地指出,有些记录可能是“不实”的。比如朴世堂于康熙七年(1668)以书状官身份入中国,写作《西溪燕录》,其中就特别写到:“臣所与问答者如此,其人亦似稍愿,故随闻以记。但见此流居路傍,多阅东使,故习于酬酢,视人意向顺口便说,显有抑扬之色,所言未必尽信。”(21)朴世堂:《西溪燕录》,《燕行录全集》第23册,第365页。
我们不妨以后来的一个例子略作参照,康熙五十一年(1712)二月,闵镇远以副使身份入中国,在蓟州停留时,傍晚有一老人来访,自称姓朱名言,闵问“或是皇明后裔否”,朱答云“神宗亲皇子四王毅然之第四子思诚即吾祖也,吾父名伦也”,鼎革后,改名易姓为“丁含章”隐匿于此,曰:“见老爷所著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闵镇远深受震撼,赠之以诗云:“倾盖泽如旧,含愤却不言。百感徒填臆,临分拭泪痕。”(22)闵镇远:《燕行录》,《燕行录全集》第34册,第391-392页。以闵氏感动之强烈,回国后必定大肆宣传了一番,所以同年十一月,金昌业以军官弟子员身份随使团入中国,到蓟州时特别提及数月前闵氏曾在此遇到“皇明后裔”丁含章,要求访其所居,馈赠礼物,央求翻译张远翼“往见其人,从容盘问”,张氏却以“朱太子宁有子孙至今保存也,此必奸细之徒图骗赂遗,假冒其名,此何待验问而知其伪”为由,认为“访问自是危道,不如已之为稳”(23)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2册,第530-531页。,婉拒其请。于是金昌业自行前往暗访丁含章,对众人循循善诱,最终得知其祖先实为当地“大富家”,这才恍然大悟,丁氏“乃是世居此处人,其变姓名隐居之说,已归虚套矣”(24)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2册,第534-535页。。金昌业乃白衣文士,不负有任何政治使命,对他而言,了解事实真相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他的记录中,多有“更正”之辞。在大凌河与秀才王俊公笔谈,王举动诡秘,“方其书也,频频回视外面,似恐人来者然”,而其真实目的在索物,“译辈言此人颇虚疏,所言不足信。曾前使行到此,每呈如此之言,因求某物而去”(25)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2册,第435-436页。;到北京,与序班潘德舆往来,从而得知“我国欲知此中阴事,则因序班求知,故此属太半为伪文书而赚译辈”(26)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3册,第33页。。
实则到了康熙五十一年,距离清朝立国已近七十年,汉人对于服饰衣冠的想法已经发生了变化。仍以金昌业的记载为例,在小黑山,金氏问一少年:“尔见俺衣冠,好笑否?”少年答曰“不好矣”(27)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2册,第423页。;在十三山与十五岁少年张奇谟笔谈,问:“你祖先衣冠,其制如何?”答:“生在晩不知。”问:“俺们衣冠,你见如何?好笑否?”答:“不敢笑。”“实说无妨。”答曰:“衣冠乃是礼也,有何笑乎?”又问:“剃头,尔意乐乎?何不存发如我们?”答:“剃是风俗,不剃是礼。”(28)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2册,第432-433页。在榆关与荣琮笔谈,问:“我们衣冠与大国异制,可骇不骇?”答:“老爷们衣冠甚可爱,我明朝衣冠是这样。”问:“然则公辈即今衣冠非旧制否?”答:“我们此时衣冠是满州。”(29)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2册,第489页。到了此时,无论是汉人还是朝鲜人,谈论上述问题的态度已趋“平常心”。即便有的汉人仍不免民族心理,而朝鲜人的“自豪”已在逐渐淡化。康熙五十九年(1720),李器之以军官子弟身份随使团入中国,在凤凰城与秀才觉罗明德笔谈,明德曰:“贵国之衣冠人物,晚见之甚有愧心焉。”李问曰:“我们衣冠稀见眼生,得无惊怪乎?”明德曰:“贵国衣冠乃汉官威仪,何怪之有?慕之不暇而已。”李答曰:“我们衣冠是礼服,贵所服乃时王之制。人生情志相通则形骸可外,何有于衣冠之异同乎?”(30)李器之:《一庵燕记》,《燕行录续集》第110册,第387-388页。李器之的身份也是白衣文士,故与中国人交往没有太多负担,能坦诚相待。而身份不同,记载就会很不一样。同是这一年,李宜显以正使身份入中国,在其《庚子燕行杂识》中写道:“路中所谓秀才,绝未有能文可语者,椎陋无识,甚于我国遐乡常汉之类……中州文物,尽入毡裘,故自尔至此耶?良可慨也。”(31)李宜显:《庚子燕行杂识下》,《燕行录全集》第35册,第462页。这显然是一种偏见过甚之辞。
三
乾隆朝开始发生较大改变,尤其是到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无论是哪一方(中方或朝方),也无论其身份是汉人或满人,是官员或布衣,谈到衣冠服饰的差异时,不过是前朝往事、各秉面目而已。我们不妨撷取几个事件来看:
乾隆二年(1737),李喆辅以书状官身份入中国,在甜水店与满人赵鹤岭有如下笔谈,李问:“即今天下太平,民皆乐业否?”赵答:“新皇帝圣明,民皆安乐矣。”问:“尔们男女衣服无异同,男不带,女无裳,是何制度?”答:“吾俗固然,不须问也。”问:“吾辈衣服制度,视尔们何如?”答:“子之骇我亦犹我之骇子,制度各异,善恶何论?”(32)李喆辅:《丁巳燕行日记》,《燕行录全集》第37册,第442页。“骇”为惊讶之意,你看我惊讶一如我看你惊讶,彼此风俗、制度不同,无优劣可论,恰是一番堂堂正正的忠言谠论。
乾隆二十五年(1760),李商凤以军官子弟身份随团入中国,在丰润县与秀才谷庆元等人笔谈,问曰:“尔们衣裳之制,较吾们孰胜?”答曰:“贵国袭前明之服,吾们遵时王之制,不可可否。”(33)李商凤:《北辕录》,林荧泽编《燕行录选集补遗》上册,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东亚细亚学术院,2008年版,第797页。在三河县与教谕薛文儒笔谈,李示以幅巾问曰:“尊知此制否?”答曰:“不知。”李自豪地说:“此朱文公之服也。”但薛坦然回答说:“只知本朝衣冠耳。”(34)李商凤:《北辕录》,林荧泽编《燕行录选集补遗》上册,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东亚细亚学术院,2008年版,第810页。到北京,与举人胡少逸笔谈,李故意挑起话题说:“衣冠文物,焕乎可述,幅圆大小,何须论也?红兜黑袜,令人可悲。”胡答曰:“红兜仍西僧之制,若贵邦之制,喜今日犹见汉官。”李进而曰:“衣者,身之章,亦不可少之也,今若脱却西僧之服,穿洪武之制,此非可乐事耶?”胡的反应是“笑而无语”(35)李商凤:《北辕录》,林荧泽编《燕行录选集补遗》上册,成均馆大学大东文化研究院东亚细亚学术院,2008年版,第897页。。
乾隆三十年(1765),洪大容以军官子弟员身份入中国,在北京遇到“杭州三士”严诚、潘庭筠、陆飞,结下深厚情谊,他观察副使金善行与潘庭筠之间的笔谈,“语及衣冠及前朝事,副使故为迫问,多犯时讳,难于应酬,而(潘)言言赞扬本朝,间以戏笑,无半点亏漏,而言外之意自不可掩”(36)洪大容《湛轩燕记》,《燕行录全集》第43册,第28-29页。案:关于洪大容与杭州三士的“干净笔谭”,现有夫马进日语译注本两册,可参考,日本平凡社2016、2017年版。。洪大容本人也就衣冠服饰说了一番貌似“痛切”的话:“中国衣冠之变,已百余年矣。今天下惟吾东方略存旧制,而其入中国也,无识之辈莫不笑之。呜呼!其忘本也。见帽带则谓之类场戏,见头发则谓之类妇人,见大袖衣则谓之类和尚。”然而从谈话气氛来看,显然并无沉痛之感,故严诚笑曰:“类僧诚然,帽带亦类僧,赖有发耳。”(37)《湛轩燕记》,《燕行录全集》第43册,第130-131页。盖谓不仅大袖衣类僧人,帽带亦类僧人,只是因为有了“类妇人”的头发,所以尽管有帽带,也就不类僧人了。洪大容不喜佛教,故严诚特以“类僧”打趣,在谈衣冠问题时,竟然还牵扯了另一个敏感话题——头发。清人入关伊始,即下“剃发令”、“易服令”(38)据郑天挺考证,“剃发”原为满洲习俗,清太祖天命四年(1619)以后,“凡其他部族投降加入满洲集团的,无论汉人朝鲜人,全以剃头为唯一表示”(《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收入其《清史探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与儒家强调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39)《孝经》语,《十三经注疏》下册,第3545页。的观念相抵触。江南人奋起反抗,其祸至惨,乃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口号。但是百余年后,当洪大容与江南人谈起“剃头”,却成为一种玩笑的语料。洪氏就记录了与潘庭筠的一番“戏言”:“兰公又戏云:‘剃头甚有妙处,无梳髻之烦、爬痒之苦,科头者想不识此味,故为此语也。’余曰:‘不敢毁伤之语,以今观之,曾子乃不解事人也。’两生皆大笑。兰公曰:‘真个不解事。’又笑不止。”(40)《湛轩燕记》,《燕行录全集》第43册,第75-76页。甚至对于“明制”衣冠,也不免私下议论其非。试以“网巾”为例,这本来是明太祖时的创制,乃根据道士的头巾而来,所谓“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故“颁令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且“永为定制”(41)郎瑛《七修类稿》卷十四“国事类·平头巾网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前面述及顺治三年郭弘址入中国,与王运恒笔谈,王即手指网巾,怀念前明,并愀然久之。但到了洪大容的时代,他却说“网巾虽是前明之制,实在不好”,理由居然是“头戴马尾,岂非冠屦倒置乎”?之所以“不去之”,也只是“安于古常,且不忍忘明制耳”(42)《湛轩燕记》,《燕行录全集》第43册,第76页。。到了乾隆四十五年(1780)朴趾源以军官子弟随团入中国,在热河与王鹄汀笔谈时,“网巾”已被中国人看成是与裹脚之“足厄”、吸烟之“口厄”相提并论的“头厄”,总称“三厄”(43)朴趾源:《热河日记》,《燕行录全集》第54册,第176-178页。。这段话还被朴思浩抄录到自己的“燕行录”中(44)朴思浩:《燕蓟纪程》,《燕行录全集》第85册,第514页。。
衣冠服饰本来只是人生日用之物,但经过儒家观念的过滤,就被附加上了文化意涵,在明清鼎革之后,其附载的意义又从服饰的华夷之辨上升到政治的反清思明。这样的观念延续了约七十年,在十八世纪前期渐渐开始淡化,到中期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先是去政治化,然后是文化意涵的减弱,最后就以一种风俗习惯视之。至此,中朝之间的人员交往,在涉及衣冠问题时,更多的是将它看成一种既在的现实。就算偶尔触发一些故国之思、满汉之别,也大都显得风轻云淡。更多的场合下,汉人欣赏朝鲜衣冠,朝鲜人也乐为“服装秀”,基本上都是一种礼貌行为。嘉庆二十三年(1818)崔斗灿漂流到浙江,衣冠弊坏,在杭州无可著者,乃于箧中得宕巾,华人爱之曰:“冠亦明制衣,先生一身浑是明制。”在其笔下,有中国人孙颢元“乞暂借,余许之,孙乃着之,顾影徘徊,似有喜色而已,在座皆以次轮着”(45)崔斗灿:《乘槎录》,《燕行录全集》第68册,第495页。,仿佛是在举行一场小型的“汉服秀”。咸丰三年(1853),姜时永以正使身份入中国,在北京与边钟鄂笔谈,亦涉衣冠。姜曰:“身上所著纱帽团领,即中华旧制,欲令先生一见,故衣此而来。”边曰:“家藏七世祖莱芜知县公遗像,即前明衣制,故曾所仰认。今又奉览盛仪,尊意可感。”(46)姜时永:《輶轩三录》,《燕行录全集》第73册,第484-485页。明代服装是“中华旧制”,清朝服装也就是“中华今制”,仅仅就衣冠而言,已经不能据其差异而作“华夷”之辨了。同治十三年(1874),沈履泽以副使身份入中国,在小黑山与房主盛永福笔谈,盛云:“吾之落发为二百余年,每见贵们之冠衣,则多愧多愧。”沈笑答曰:“俗尚也,何足为愧也?”(47)沈履泽:《燕行录》,《燕行录续集》第144册,第170页。甚者有人为了学术研究之需而关注朝鲜衣冠,光绪十一年(1885),南廷哲以副使身份入中国,在北京与海关道道台周馥山笔谈,周云:“中国衣制之变已久矣,惟贵国独见汉官威仪。弟平时读书,阅古衣制图,欲深究其曲折,而不身亲见之。贵国朝服一袭,可为我购致否?欲留之以资博古,价银当自办。”南氏答:“敝邦衣制虽古,他事皆不如故,可叹。不必论价,回国后,当以一袭得呈耳。”(48)《乙酉正月北洋大臣衙门笔谈》,成均馆大学藏书阁藏本。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氛围中,如果有朝鲜人偶尔就衣冠问题稍做文章,就可能招致严厉的驳斥。嘉庆六年(1801),吴载绍以副使身份入中国,在北京与众多文人笔谈,其中记载了一段译官与王金华的对话:“译官刘运吉尝指王金华之衣而笑曰:‘此服好耶?’金华蹙然曰:‘但遵国制,宁问好不好,运吉之问太逼矣。若华夏全盛时,运吉辈何敢挟东夷制度侮南京士大夫乎?’”(49)吴载绍:《燕行日记》,《燕行录续集》第121册,第397-398页。此时的王金华,虽然所穿服饰是“满制”,但毫无愧色地以“华夏”自命,而谓身着明制衣冠的刘运吉是“挟东夷制度侮南京士大夫”。此时的译官或作者对王金华的此番言论也未能有任何回应,只是悄悄地在自身的文字记录中发了一点牢骚,以弥补内心的缺憾。总之,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到过中国的朝鲜知识分子,对清朝的感受已经全然不同于其燕行前辈或国内闭目塞听的守旧之徒。在其中的很多人看来,清朝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所以朝鲜应该“北学于中国”。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子弟军官身份随团赴京的朴趾源就说出他眼中的清朝形象,是“三代以降圣帝明主、汉唐宋明之良法美制,固不变也”(50)《热河日记》,《燕行录全集》第53册,第453页。。正祖八年(1784),李鼎运在上呈国王的“闻见事件”中,描写乾隆朝的“辟雍”场景云:“多士青衿仿上衣下裳之制,有中华遗风。”(51)《(甲辰)谢恩行书状官李鼎运闻见事件》,《同文汇考》补编卷六,第12册,第900页。这与清初的场景判然为二。
下一个“趋势变动”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衣冠问题上引起中、朝人共同反感的,是日本随着明治维新运动而来的向西方学习,在服饰上规定了“制服”,也就是充满了“西国”色彩的“洋服”(ヨウフク)。光绪八年(1882),金允植作为领选使入中国,曾在天津与器机局总办刘含芳笔谈,刘曰:“日王之可鄙者,是在变洋太过……不改衣冠正朔,亦可。”金曰:“日本之人善变化,其国与敝邦庆尚道相邻,其人文之开,由我峤南儒林之风;嗣后购买中华经籍,彬彬多文学之士;及闻洋夷之风,又突然尽变,可谓下乔木而入幽谷者也。”刘曰:“日本内地之民未变者尚多,将来日王之失,亦在此也。”金曰:“非徒法制,衣冠正朔之改,并扫文字。”刘曰:“西国之有识者,皆称日人曰猴。盖猴之性,见人为亦为之,而莫知其所以耳。”金曰:“日人之善学人为,诚如西人所云,然若不变其衣冠正朔,何至自取侮辱乎?日人之纳侮,亦东洋之耻也。”(52)金允植《天津谈草》,《燕行录全集》第93册,第288—289页。案:金允植在对话中使用的“下乔木而入幽谷者”一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1页)以言日本的行为是弃明(即乔木,喻中华文化)从暗(即幽谷,喻西洋文化)。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势力向东亚大举突进,东亚各国所面临者,乃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东亚汉文化圈之彻底崩坏,一方面是晚清政府之黑暗腐败,却沉浸在自身构筑的“天朝”美梦中自我膨胀;一方面又有外来势力的强行进入,以坚船利炮为前驱摧毁了中国经济、文化的优势。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积极向西方学习,逐渐成为东亚的先进国,并且在甲午战争前后,以“东洋之英国自负,蔑视支那、朝鲜”(53)原田藤一郎《亚细亚大陆旅行日志并清韩露三国评论》,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十二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版,第248页。。一切皆由于国势之积贫积弱,故汉文化也渐渐不为人所重,即便在中国国内,也被种种的“革命”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根除,以至于后来一批知识分子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如何使中国文化获得重建和复兴,直到今天也还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1914年李承熙在北京,曾与众多中国人笔谈,李氏强调文化的重要,主张“纲常道德果得正,则亦何患不富强耶”?袁峻质疑道:“今何西之富强而中华之反不富强也?”李氏则以 “孟子曰五谷之不熟,不如稊稗之有秋”(54)《杂著·袁峻笔话》,《大溪集》卷二十八,韩国文集编纂委员会编《韩国历代文集丛书》第1058册,韩国景仁文化社,1999年版,第438页。案:李承熙引用孟子言论为说,实际上对其重心有所修正。《孟子告子上》云:“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四书章句集注》,第336页)孟子强调即便是“美种”,也要努力培养使之成熟方有意义。李氏的意思是,正因为其属“种之美者”(喻中华文化),成之不易,所以比不上“稊稗”(喻西洋文化)之能“疯长”。为说。在李氏眼中,辛亥革命废弃了“中华旧章”,根本无“光复”之可言:“以道理言,则满犹尊崇孔教,其伦理犹不大悖。辛亥民国肇建,遂尽灭纲常,废弃尧舜孔孟之道,直使神圣种族化作西欧之民而已,何有光复?”(55)《杂著·李南彬笔话》,《大溪集》卷二十八,第460页。在其心目中的“华夷之辨”,也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认识,而持一种反对“排满”、反对“种族主义”、反对“西俗”的态度:“使民国而永不复先圣制度,直从西俗而已,则政孔子所谓中国而入于夷狄则夷狄之者也……所谓种族主义,本亦狭隘。况中国之族,亦非尽一人之种,稍广之,则满洲亦一黄种,本非相绝者乎?”(56)《杂著·李南彬笔话》,《大溪集》卷二十八,第461页。只是这个问题,已远远轶出了“衣冠”的范围,我将在讨论“华夷变迁”的问题时再作展开。
四
本文强调了“长时段”研究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一个具体问题的展开,对历史研究的“三个时间段”皆有所触及。最近三十年间,在欧美史学界最为风光的要数“新文化史”研究,他们抛弃了年鉴派史学宏大叙事的方式,注重研究历史之树的“树叶”,往往导致历史研究的“碎片化”(57)参见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多斯(François Dosse)《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年鉴〉到“新史学”》(L' histoire en miettes: Des Annales à la "nouvelle histoire"),马胜利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而“碎片化”的研究必然是“短时段”的。2014年,乔·古尔迪(Jo Guldi)和戴维·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合著的《历史学宣言》首先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网页上公开发布(其后才付梓印行),这部充满激情和挑战的著作(某些地方摹仿了《共产党宣言》的笔法)立刻引起欧美史学界的轰动。整部著作的核心观念,就是呼唤“长时段”史学的回归。因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间,短期主义成了学术追求的时尚”(58)乔·古尔迪、戴维·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孙岳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所以本书的开篇即云:“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59)乔·古尔迪、戴维·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孙岳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而在全书之末,作者呼吁道:“全世界历史学家,联合起来!你们会赢得一个世界,现在还为时不晚。”(60)乔·古尔迪、戴维·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孙岳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5页。虽然作为一种历史技艺的概念,“长时段”在六十年前由布罗代尔提出,但回归后的“长时段”是一种“新的长时段”,“在概念上可能源自过去,但其指归却是朝向未来的”(61)乔·古尔迪、戴维·阿米蒂奇:《历史学宣言》(The History Manifesto),孙岳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9页。。本文也希望通过一则个案研究,对这一史学呼唤作出哪怕是很微弱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