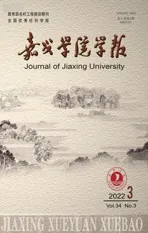论李富孙《七经异文释》的撰述缘由和旨趣
2022-03-17付虎
付 虎
(吉林大学 考古学院,吉林长春 130000)
李富孙(1764-1844),字既方,别字芗沚,(1)关于李富孙的字,多处史料记载并不相同,吴辛丑、曹小燕的《论李富孙〈易经异文释〉的训诂价值与当代意义》(《周易研究》,2021年,第1期,第28-34页)则进行了细致的辨析,此处不再赘述。号校经叟,浙江嘉兴人,是当地的文化世家李氏之后。[1]李富孙一生著作等身,《七经异文释》便是其著作之一,是一部广泛搜辑和考订经学异文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共五十卷,其中包括《易经异文释》六卷、《尚书异文释》八卷、《诗经异文释》十六卷、《春秋三传异文释》十二卷、《礼记异文释》八卷。冯登府称赞该书“详该奥博,足补陆元朗氏(陆德明)之所未逮”[2]。曾镛也说:“况广为搜辑,复有以曲通其义,类观所自叙,知有功于经学不少。”[3]451可见该书的经学成就之高,然而,学界对于该书却少有关注,(2)为数不多的研究《七经异文释》的成果有林忠军、张沛、赵中国等人所著的《清代易学史》(济南:齐鲁书社,2018年,第618-631页),整体论述了李富孙的易学成就;吴辛丑、曹小燕的《论李富孙〈易经异文释〉的训诂价值与当代意义》(《周易研究》,2021年,第1期,第28-34页)则专门研究了《易经异文释》的训诂价值;高婷婷的硕士学位论文《嘉庆时期〈诗经〉文献研究》(沈阳师范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简述了《诗经异文释》的体例和阐释特点。另有林佳楠、安忠义的《李富孙生平及其作品考述》(《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4卷,第2期,第52-56页),仅对《七经异文释》的成书过程进行了简单介绍。
关于李富孙撰述《七经异文释》的缘由和旨趣更无人论及。本文则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学术背景,以及《七经异文释》中各部分内容的自序来进行探析。
李富孙所著《七经异文释》,除《易经异文释》外,于其他六经各有序,另外又给《七经异文释》全书作了总序,所以《七经异文释》的序文包括:《七经异文释自序》(3)天津图书馆藏校经庼臧版《七经异文释》第一册,写作“七经异文释自叙”;《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所收《校经庼文稿》,作“七经异文释自序”。本文皆作“七经异文释自序”。《尚书异文释自序》《诗经异文释自序》(4)天津图书馆藏校经庼臧版《七经异文释》第七册,写作“诗异文释自叙”;《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所收《校经庼文稿》,作“毛诗异文释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75册,收录李富孙所著《诗经异文释》无自序。本文遵循《续修四库全书》第75册收录的《诗经异文释》的书名,皆作“诗经异文释自序”。《春秋三传异文释自叙》(5)《续修四库全书》第1489册所收《校经庼文稿》,写作“春秋三传异文释自叙”;《续修四库全书》第114册所收《春秋三传异文释》,也作“春秋三传异文释自叙”。本文亦同。与《礼记异文释自序》。
《七经异文释自序》置于全书之首,总括七经在流传过程中经文古义的流失,描述了经学异文产生的诸多原因,感慨前人针对异文现象,未能广为搜辑,且偏离圣人要旨,最后阐明了其撰述该书的宗旨和理想。其他各书自序,又详细论述了具体经书的流传得失,俨然是一部经学学术史。《七经异文释》全书各个序文之间协调统一,基本上揭示了李氏撰写该书的原因和旨趣。
一、李富孙撰述《七经异文释》的缘由
李富孙《七经异文释》的成书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学术背景分不开的。首先,清朝建立之后,统治者为巩固政权而实行高压的统治政策,如大兴文字狱以加强对人们思想的控制,同时提倡稽古右文,重视古代典籍的编纂以转移人们的反清视线。其次,清代康雍乾时期,出现了史称的“康乾盛世”,一方面中国迎来了一百多年和平安定的政治局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6)此处仅从清廷的高压政策和康乾盛世这两个角度(或者说是从当时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这两个因素)来论述乾嘉考据学的形成,但是除此之外,其形成仍然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具体可参看赵永春《近十年来乾嘉学派讨论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8期,第17-21页),亦可参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81页)一书。[4]
学者们纷纷埋头于故纸堆中,进行繁琐的训诂考据工作,以求还原经文原貌,追寻古义,经学异文便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一学术风潮于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史称“乾嘉考据学”(又称之为“乾嘉学术”“考据学”“朴学”“汉学”等)。李富孙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无疑会受到该学风的影响,张舜徽就称李富孙为“朴学之士”[5]。《七经异文释》便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
但这仅是李富孙撰述《七经异文释》的外部原因,想要全面且深刻地认识其撰述缘由,则不得不从李富孙为该书所作的自序入手,探析其内部原因。
第一,经文古义难以传承,诸儒又抱残守缺,各守师承,说法不一。经文遭秦焚毁之后,其传承过程异常艰辛,一方面是因为经文古义的流失,另一方面是受到师承之间经文传抄讹误的影响。李富孙认为“经自秦燔后,往圣之微言奥旨澌灭无存”[3]451(《七经异文释自序》)。经文遭受秦代焚毁之后,经文古义几至不存。到了汉代,只得依靠屋壁所藏和民间所献的古文经以及老儒所口授的今文经来阐发经学要旨,但又残缺不全。同时,李富孙在《礼记异文释自序》中又说:“自汉以来,诸儒皆承师说,多有异同,兼简册递写,传者不无讹误。”[3]454各家说法本就不同,而传承过程中又出现传抄讹误的现象,其间,会产生多少异文更不得而知,经学传承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
儒生们抱残守缺,固守师说,致使说法不一,异文频生。李富孙在《七经异文释自序》中总括了《易》《书》《诗》《礼》《春秋》的流传与师承关系,在《尚书异文释自序》《诗经异文释自序》等其他自序中均进行了详细论述。进而提出“弟子各守师说,人殊其谊,亦经异其文”[3]451的观点:弟子都遵守各自老师的说法,致使对经文的解读各不相同,异文也就产生了。《诗经异文释》亦言:“诸儒各以家法教授,师承既异,而文字训诂亦多不同。”[3]453同时,李氏也对于诸儒各执己说表示了理解,他说:“兹非有意乖违,其家法授受然也。”[3]451儒生们并非有意背离古义,只是其家法传授便是如此。
第二,诸儒对于经传的异文或真伪,不加分辨或说明,直接称引。李富孙认为:“许叔重(许慎)《说文解字》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春秋》左氏,然颇杂采诸家,故所引经文,一字间有互异。郑康成(郑玄)、范宁、何休、郭璞辈所注,其引诸经亦有不同。”[3]451许慎称引经文时,各家说法兼容并取,且许慎所处时代,去古未远,得以看到时代更早的经文文献,使《说文解字》引用的经文文字与后世文献中的经文多有不同。像郑玄、范宁、何休、郭璞等人,他们称引经文的依据又各不相同,由此,异文便又增加了。
李富孙所生活的时代,为清朝乾嘉时期,正处于清学的全盛期,以“专经为尚”,“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6],而当时研究《说文解字》引经而产生异文问题的学者更不在少数,如钱大昕亦有相同的看法:“今世所行《九经》,乃汉魏晋儒一家之学,叔重(许慎)生于东京全盛之日,诸儒讲授,师承各别,悉能通贯,故于经师异文,采摭尤备。”[7]
李富孙又在《尚书异文释自序》中论及《伪古文尚书》时说:“迨陆德明作音义,孔颖达等成义疏,越唐及汴宋,莫有轻为拟议,惟朱子始疑之。”[3]452自唐至宋,像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孔颖达等人作经文义疏,称引经文传注时,均未辨明《尚书》真伪,仅朱熹开始怀疑《尚书》中部分篇章的真伪。可见前人称引经文时,对于经文的真伪和异文,未加仔细分辨,李富孙亦遗憾于此。
第三,后人不通古义,妄为臆改,训诂之书又不能广泛采集异文。李富孙在《七经异文释自序》中提到:“盖汉人去古未远,六书为小学,说字解经,罔弗洞究根原,传经者率本六书意谊,或从古文,或从假借,或以声近,或用省文,加以南北语殊,轻重差别,故有字随读变,义因文异。”[3]451意即汉时离古不远,儒生尚通小学,解读六书文字时为遵循古义,用假借字、声近字或省文等各种方法。汉朝时人或能明白其中原委,通古人圣言,而后世则不然,后人则去古久矣,“不知古训,妄为臆改,而古人之经谊几不可通矣”[3]451。为了辨析异文,疏通古义,后世虽有训诂专书,但李富孙却憾其未能达到会通古义的效果,所参考的经籍文献也很有限。如唐陆德明著有《经典释文》,李富孙谓其“诸家异同,采摭略备,然第及诸经训诂之说,未尝于经典外广为搜辑”[3]451,《春秋三传异文释自叙》也说:“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仅采诸家之文字音切,而未尽会通其谊。”[3]454
总之,李富孙撰写《七经异文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乾嘉学术风潮的影响之外,还十分关注经文古义的传承问题。但是经文的焚毁和经学异文的大量产生,使人们对经文的理解偏离了古人原有之意,这也是其撰述该书的主要原因。
二、李富孙撰述《七经异文释》的旨趣
李富孙在治经过程中深刻感到经学异文给人们的研习带来的巨大障碍,为此付出了许多努力,这也是《七经异文释》的旨趣所在。
第一,不专主一家,兼采诸儒之说,广搜异文。李富孙十分赞赏汉代广立经文、不专于一家的做法,他说:“刘歆尝谓汉时广立经文,义虽相反,犹并置之,则穷经之士,不专为一师之学者。”[3]451李氏自己面对诸家说法的态度亦是如此,即“兼采后儒之说”[3]451“并为搜辑”[3]454,在读书之暇,广泛搜集异文。在撰写《诗经异文释》时,“见有与今《毛诗》异者,罔弗搜罗荟萃,绎其义”[3]453,一旦发现有与今本《毛诗》文字不同的地方,就全部收入,而后再理其端绪。《清史稿》在论及李富孙的《七经异文释》时也说:“前儒之论说,并为搜辑。”[8]
第二,征而有据,详考异文,正其讹谬,或可探寻圣人要旨,以供后世所采。李富孙的工作并非止于简单地搜集异文,而是广泛搜集异文之后详加考订。“兹复详为训诂,非如诸家之弟存其文”[3]453。在疏证异文时,李氏皆有根据,并非凭空臆说,在《诗经异文释自序》中直言:“皆根据经传,非骰冯虚臆说。”[3]453在撰写《尚书异文释》时,抛弃《伪古文尚书》,仅释被人们认为是较为可靠的《尚书》二十八篇。海昌蒋光煦为《春秋三传异文释》作跋,赞其“考核俱精审,辨异同而定得失,实可羽翼经传而不谬”[9]。可见李富孙实事求是,征而有据的治学态度。
李富孙会通各种方法考订异文,即“旁通曲证”[3]451。且不怕繁琐,对于异文皆一一考据,详加训诂,以期“正其讹谬,辨其得失,折衷以求一是”[3]454,《礼记异文释自序》亦言:“校其殊异,考其谬误,皆为旁通曲证,参究详审,别是非而订得失。”[3]454李富孙在《七经异文释自序》《诗经异文释自序》《春秋三传异文释自叙》及《礼记异文释自序》的最后均表达了他的理想,意即不囿于一家之见,详细考证异文,或可探寻圣人古义,后世学人在治经的过程中,至少能够参看此书。
第三,李富孙视野广阔,博览群书,其搜集异文所参考的文献,涉及经传笺注、子史金石等,期望弥补陆德明“未尝于经典外广为搜辑”[3]451的遗憾。如《七经异文释自序》所言:“富孙少而不学,长稍涉《六经》,见汉、晋诸儒之解诂各有师承,其与经文异者,不仅《释文》所载,自经传笺注及子史金石所引,往往与今文不同。循诵之暇,悉为缀缉。”[3]451可见李富孙视野广阔,眼光独到,其参考内容不仅限于传世的经文,对于金石文字也囊括其中。如《诗经异文释》“鐘鼓乐之”条:
《韩诗外传》(五)作“鼓鐘”(《楚茨》“鼓鐘送尸”,《疏》亦本作“鐘鼓”,《宋书·礼志四》同段氏曰:“鐘鼓送尸”,与上“鐘鼓既戒”一例。)
《唐石经》“鐘”作“鍾”。(《鼓钟》《楚茨》《宾之初筵》《白华》《执竞》《山有枢》《鼓钟序》并作“鍾”。)
案:《说文》“鐘”、“鍾”二字文义皆异。《五经文字》云:“今经典,或通用‘鍾’为乐器。”盖古多有以“鍾”为“鐘”者,而“鐘”则不可为“鍾”也。《韩诗外传》作“鼓鐘”,义亦通。[10]
此处,李富孙除了参考《毛诗》《韩诗外传》《说文解字》《宋书》等传统文献来搜集和考证异文之外,还参考了唐代碑刻文字。正如《诗经异文释自序》所说:“浏览经史,以及《说文》传注、诸子百家、汉唐石刻,不弟三家之文。”[3]453可以说,李富孙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李富孙虽然受制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条件,不能同现代人一样看到更多更新的出土文献材料,但是作为传统的儒士,在考证异文之时,尽可能地于经学之外寻求突破,这在今天看来十分难得。
总之,李富孙不怕工作的繁琐性和复杂性,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在厘清经学异文上做了许多工作。他一方面博览群书,广泛搜集经学异文,兼采各家说法;另一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考订,辨别异文正误,努力探寻古人要旨。经学文献自秦传至于今,内容多有流失,其间又产生了大量的异文,由此为后人的传习带来诸多困难。李富孙生活于朴学盛行的乾嘉时期,对于经学异文十分关注,为减少异文给人们带来的困扰,而作有《七经异文释》,且秉持着“文辞谨饬,不尚空谈,笃实无欺”[4]的治学风格,对经学异文进行了大量的搜集和细致的考订,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期望能为后世学人所采用。本文仅在探究李富孙撰述《七经异文释》的缘由和旨趣方面做了一些微小的工作,希望能使学界对于该书的价值有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