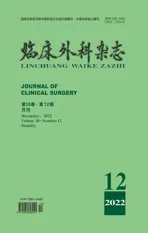病理性瘢痕研究中的困惑和突破
2022-02-24徐若清黄昕李青峰昝涛
徐若清 黄昕 李青峰 昝涛
病理性瘢痕是一类创面异常愈合所致的纤维化性皮肤疾病,主要包括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创伤后增生性瘢痕的总体发病率高达40%~70%,瘢痕疙瘩在有色人种中发病率为4%~16%[1]。病理性瘢痕引起外观毁损,还常伴随难以忍受的痛痒、挛缩畸形、功能障碍等,影响病人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围绕病理性瘢痕,前期已有大量基础和临床相关研究报道。目前,对于病理性瘢痕发生发展的确切机制仍不明确。对于病理性瘢痕的临床诊断、分型、治疗决策和随访评估也有待深入探讨。
一、基础研究现状与相关进展
病理性瘢痕的形成受到遗传因素、全身因素(如血压、激素)以及局部因素(感染和炎症等)的共同影响。成纤维细胞作为主要的效应细胞,其功能的激活,尤其是胶原分泌功能的亢进,最终造成了病理性瘢痕过度的基质沉积。同时,成纤维细胞在激活的过程中,与多种细胞存在互作关系,但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多组学、多色流式细胞分选及谱系追踪技术的兴起,使人们得以从单细胞角度对瘢痕中的成纤维细胞及其所处的微环境进行解析,并对特定亚型的细胞进行分选和功能验证,进而取得了系列具有启发性和临床转化潜力的发现。
1.成纤维细胞亚型:Rinkevich等[2]利用谱系追踪技术发现,小鼠在宫内发育过程中产生一群介导瘢痕形成的关键成纤维细胞亚型,其特征是表达Engrailed-1,故定义为En-1阳性成纤维细胞(EPFs);经过流式筛选,约94%EPFs特异性高表达CD26(即DPP4),据此认为,CD26可以作为EPFs的表面标志物。另一研究采用单细胞转录组测序,筛选出增生性瘢痕特异的成纤维细胞亚群,差异表达基因分析显示,该亚群上调表达DPP4,故DPP4也是人瘢痕形成的关键因子[3]。DPP4的小分子抑制剂,在体外能够抑制成纤维细胞的基质分泌功能,在动物体内具有改善瘢痕胶原排列、减少胶原沉积的效应。格列汀类药物作为DPP4抑制剂,已被临床应用于糖尿病治疗,是预防或改善瘢痕的潜在选择[2-3]。
从愈合方式上看,EPFs大量存在于小鼠皮肤的筋膜层,能够引导筋膜周围嵌入的血管、神经等成分向创面聚集,在伤口表面形成临时基质,进而介导创面愈合与瘢痕的形成[4]。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械张力信号转导通过驱动YAP入核,刺激位于真皮网状层的En-1阴性成纤维细胞亚型(ENFs)表达En-1,转化为介导瘢痕形成的EPFs。机械力诱导的小鼠瘢痕模型中,体内运用YAP抑制剂能够减轻机械张力的影响,显著降低创面YAP和α-SMA的表达及EPFs的激活水平,并恢复皮肤附属器的生长、实现无瘢痕愈合[5]。目前,以维替泊芬为代表的YAP抑制剂已经在猪的病理性瘢痕模型中开展进一步的临床前实验。
此外,我们团队运用多色细胞流式技术筛选出增生性瘢痕中细胞比例显著上调的CD39+成纤维细胞亚型,该亚型通过高分泌促纤维化因子IL-11,辅助激活成纤维细胞的基质分泌能力,诱导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化。应用小分子药物POM-1阻断CD39,在体外能够抑制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分化过程,在体内减轻胶原沉积、减小瘢痕面积。该研究提示不同亚型的成纤维细胞之间存在密切互作关系,如何精准靶向这些关键的细胞亚型并进行干预,值得进一步研究[6]。
2.成纤维细胞与其他细胞的互作关系:单细胞细胞互作分析技术能够高通量描绘细胞互作关系,有利于复杂细胞互作体系的解析。有研究发现,皮肤成纤维细胞是一群形态和功能异质的细胞,这些成纤维细胞之间,以及与其他类型细胞间,存在广泛互作效应。Deng等[7]研究提示,瘢痕疙瘩组织内间充质成纤维细胞亚群比例显著增加,并上调表达与胶原组织、创面愈合、成骨分化等相关的基因。经过这群细胞的培养液上清液刺激后,其他成纤维细胞的Ⅰ型和Ⅲ型胶原表达增高,并且该效应可被POSTN中和抗体阻断,故这群细胞可能通过POSTN促进其他成纤维细胞的胶原蛋白合成。Liu等[8]指出,在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KFB)和血管内皮细胞(VEC)之间存在丰富的细胞互作,其中TGF-β和Eph-ephrin通路较为关键,分别参与了成纤维细胞转录状态和血管生成过程的调控。Shim等[9]通过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联合分析发现,瘢痕疙瘩特异的成纤维细胞亚群在真皮深层富集,且主要位于血管结构周围;同时,瘢痕疙瘩内VEC也体现出高表达POSTN,FN1等的间充质激活特征。空间转录组的受体-配体共表达分析发现,VEC通过与间充质激活相关的配体调控KFB,二者之间存在的TGFB3-TGFBR2互作网络,可以促进VEC增殖和迁移。
巨噬细胞被认为是瘢痕中成纤维细胞激活的关键免疫细胞,尤其是M1和M2的表型转化过程[10]。Shook等对病理性瘢痕小鼠创面愈合过程中的巨噬细胞亚群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解析,发现巨噬细胞可以调节肌成纤维细胞的异质性,表达CD301b的巨噬细胞亚群通过IGF1和PDGFC激活促纤维化亚型,即脂肪前体细胞,并促进成纤维细胞的增殖。Feng等[11]指出,瘢痕疙瘩与邻近正常皮肤组织在免疫谱表达上存在差异,尤其是单核-巨噬细胞系统;巨噬细胞可能通过TGFβ及CCL2受体-配体结合与成纤维细胞相互作用[11]。除此以外,Direder等[12-13]的研究还说明,瘢痕疙瘩内施万细胞与巨噬细胞间也存在互作关系。瘢痕疙瘩存在特异且保守的施万细胞亚群,它们表达前体标志物,呈现不包绕轴突的修复型特征;巨噬细胞通过GAS6等调节修复型施万细胞动态分化,同时施万细胞通过CCN3等募集并促进巨噬细胞向M2型极化,并抑制其MMP9蛋白表达与基质降解,从而促进和维持瘢痕的病理表型。施万细胞与角质形成细胞、平滑肌/周细胞之间通过PTN-NCL的相互作用可能参与瘢痕疙瘩的肿瘤样生长。
二、临床诊疗现状与相关进展
临床实践中,由于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的高度相似性,二者的诊断和鉴别依赖于经验判断,缺乏诊断“金标准”和有效评估工具是临床工作面临的困境。目前,病理性瘢痕的主流治疗手段仍聚焦于手术、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细胞毒性药物、光电治疗和放疗等。现有的治疗手段复发率较高,单独手术切除的复发率高达70%~100%、糖皮质激素类药物复发率约为50%、放疗复发率在15%~23%左右[14]。一旦发生耐药或复发,只能重复治疗或选择手术切除辅助放疗,不断复发和尝试新治疗的过程往往给病人带来痛苦。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病理性瘢痕的临床诊治中也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中、日及欧美等更新了瘢痕管理的临床指南,进一步规范了病理性瘢痕的诊断和治疗。同时,新药研发、光电放疗等技术的更迭,及对传统治疗手段的优化都为病人带来了新的希望。
1.诊断与鉴别:增生性瘢痕和瘢痕疙瘩的诊断与鉴别通常依赖于二者的临床表现及病理学特征。通常认为,增生性瘢痕生长较为局限,而瘢痕疙瘩生长呈浸润性,表现出一定的类肿瘤生长特性。组织学上,尽管二者的α-SMA表达情况、真皮结节和粗大胶原纤维束的排列形态有一定鉴别意义,但这些指标的判读都较为主观,区别二者的生物标志物仍不明确。Limandjaja等[15]提出,病理性瘢痕真皮区表现出未成熟瘢痕的特质(CD34-/αSMA+),且高表达p16。瘢痕疙瘩真皮中p16和表皮中involucrin的表达要显著高于增生性瘢痕。这些发现能够一定程度对二者进行鉴别。此外,Syndecan-1在瘢痕疙瘩中富集表达,而在正常皮肤和增生性瘢痕中几乎不表达,是瘢痕疙瘩潜在的分子诊断标志物[16]。然而,上述分子的鉴别意义有待大样本的临床验证。
传统的病理活检具有侵入性,可能引起不适甚至加剧瘢痕增生,因此无创筛检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液体活检”是检测和分析局部病灶释放到血液中的循环细胞、DNA和外泌体,可以作为理想的早期筛查和预后标志,指导临床早期干预和治疗决策。Xu等[17]基于单细胞测序技术鉴定了可以作为瘢痕疙瘩诊断和预后标志物的可溶性人白细胞抗原E(sHLA-E),经过队列研究验证,该标志物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达到83.69%和92.16%。Yeo等[18]运用透皮纳米探针NanoFlares可视化检测活细胞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的mRNA水平,通过动物和人瘢痕组织离体模型验证发现该技术可以实现病理性瘢痕的快速诊断和量化评估。这些无创检测手段的有效性还需要后续多中心的临床试验进行验证。。
量表是病理性瘢痕鉴别和随访评估的重要工具,较为常用的有温哥华量表(VSS)、病人与观察者瘢痕评估量表(POSAS);近期学界提出的针对病理性瘢痕的评估工具有日本瘢痕研讨会瘢痕量表(JSWSS)[19]、底特律瘢痕疙瘩量表(DKS)及瘢痕疙瘩面积和严重程度指数(KASI)。这些量表各有侧重和局限性,目前缺乏全面有效的评估工具。我们认为,应该从诊断、治疗(必要性评估和决策选择)及随访等实际应用出发,多维度综合评价,从而鉴别和区分不同的瘢痕亚型,建立对应的治疗方案。此外,一些影像学手段如激光斑点对比成像(LSCI)和多模态光声/超声同样可以被用于评估瘢痕生长状态并监测瘢痕复发[20]。Rutkowski等[14]使用激光散斑成像系统(FLPI),并辅以分光光度法量化胶原和黑色素,综合组织学上表皮厚度和糖胺聚糖表达水平,评估瘢痕对治疗的反应性。这些新的评估手段还需要进一步临床实践的验证。
2.治疗新方法:目前指南的治疗推荐多为经验性总结,缺乏大样本的RCT研究和循证医学支持。糖皮质激素和细胞毒性药物是目前最常用的瘢痕治疗药物,主要通过靶向炎症反应及成纤维细胞的增殖分化,从而抑制胶原沉积、调节基质重塑。A型肉毒素(BTA)是整形外科的常用药物,广泛应用于面部年轻化、治疗肌肉痉挛等。有研究发现,它同样具有抑制成纤维细胞增殖和向肌成纤维细胞分化过程,故被尝试用于瘢痕形成的防治。Huang等[21]在一项RCT研究中提出术,后早期运用A型肉毒素可以改善内眦赘皮矫正术后瘢痕的VSS评分,预防增生性瘢痕形成。高儿茶酚胺血症是病理性瘢痕形成的全身性因素之一,Ei等[22]提出,普萘洛尔作为一种非选择性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可以拮抗儿茶酚胺带来的应激效应,从而减轻瘢痕形成。同一团队的RCT研究对大面积烧伤儿童给予普萘洛尔联合氧雄龙治疗,结果显示,联合治疗能显著改善患儿增生性瘢痕的形成,并获得较好的长期社会心理效应[23]。Jun是组织纤维化病理过程的中枢分子介质,Griffin等[24]揭示了Jun上调网状成纤维细胞的纤维化信号通路及脂质成纤维细胞中的PPARγ信号传导,从而促进小鼠形成增生性瘢痕;同时Jun在人的增生性瘢痕成纤维细胞中高表达。CD36是细胞表面潜在的Jun下游靶点,其小分子拮抗剂丹酚酸B(SAB)能够调控成纤维细胞亚型、下调TGFβ1基因表达和分泌功能。SAB目前已经被用于临床提升脂肪移植存活率,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其在病理性瘢痕中的临床意义有待后续的临床研究[24]。这些老药新用的形式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加速了转化应用,值得借鉴。尽管如此,这些临床药物对病理性瘢痕的具体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有待进一步的基础研究予以探索。
此外,研究者们还在积极地对传统治疗改进与创新。例如,Dhurat等[25]提出,运用“pop”法进行瘢痕内注射,利用活检针进行多点穿刺,并通过形成的孔道病灶内注射曲安奈德。该方法在对瘢痕疙瘩减瘤减张的同时,让病灶内注射更为简便,并且药物浸润更加均匀,最终达到更优的治疗效果。传统的瘢痕疙瘩病灶内射频消融术中,能量通过尖端向各个方向传递。Taneja等[26]运用静脉导管对射频探针进行改良,能量通过套管下表面的孔传递,解决了消融过程中能量向上扩散、损伤表皮的问题。
三、展望
近年,通过对细胞群体的微观解析,加深了人们对于病理性瘢痕的形成过程中细胞成分、互作关系、分子调节的认识。但是,表型稳定且具有代表性的病理性瘢痕模型的缺乏,阻碍着该领域相关基础和转化研究。常用的啮齿类模式动物的皮肤厚度、张力和愈合方式与人类相差较大,难以形成与人体类似的病理性瘢痕组织;目前仅能通过机械牵张,药物(如博来霉素)注射和放射线损伤等方式诱导形成的皮肤纤维化模型作为替代。也有学者利用组织种植模型或体外组织培养进行研究,然而均存在稳定性较差且难以模拟免疫环境等问题。未来,需要研究者们从基因编辑、人源化小鼠及构建皮肤类器官等角度进行尝试,构建出更符合人病理性瘢痕特征的研究模型。
我们认为,在临床诊疗方面,亟待建立完善的分子诊断和分级标准、提出系统的随访评估工具,以实现对病理性瘢痕的准确诊断和分型分类。面对棘手的耐药与复发问题,可以利用多组学技术探究耐药靶点,并通过高通量药物筛选手段研发新的靶向药物。另外,与新兴的材料科学进行医工联合,有望设计高效的靶向性药物递送系统,从而实现更为精准治疗。对于新的诊疗手段及药物,需要深入的机制挖掘,也需要更多大样本、多中心的高质量临床实验验证,从而转化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