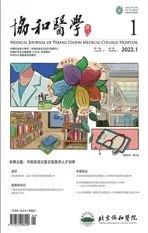阿扎胞苷联合GemOx方案治疗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一例
2022-02-16陈晓君刘彦权胡晓梅黄素蓉沈建箴
陈晓君,刘彦权,胡晓梅,黄素蓉,沈建箴
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1血液科 福建省血液病研究所 国家血液病学重点实验室 3病理科,福州 3500012赣南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肿瘤科,江西赣州 341000
1 病例资料
患者女性,27岁,以“进行性鼻塞3个月余”于2021年1月1日收住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血液科。
患者于2020年9月无明显诱因出现鼻塞伴流涕,偶有鼻腔出血,伴全身皮肤散在包块,呈暗紫色,颜面部显著,最大处约4 cm×4 cm,外院鼻腔(鼻咽部、右侧鼻底)肿物活检结果:小细胞恶性肿瘤;免疫组化示CD4(+)、CD123(+)、CD56(+),淋巴造血系统不能排除髓性病变可能;(右侧中鼻甲)黏膜慢性炎症伴息肉形成;免疫组化示CD3散在(+)、CD20(-)、CD21(-)、Ki- 67指数(50%+)、CD56(+)、CD4(+)、CD123(+)、突触素(-)、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原位杂交示EBER(-);IGH-IGK基因重排(-)。2020年12月自觉鼻腔肿物、颈部及腹股沟淋巴结均逐渐增大,为进一步治疗就诊我院。
入院查体:全身可见多发皮损,以颜面部显著,额头处3 cm×3 cm、右脸颊处5 cm×5 cm、左脸颊处3 cm×7.5 cm暗紫色肿块,质韧、边界清楚(图1A);躯干(图1B)及双下肢多发皮疹,最大处约2 cm×3.5 cm,鼻腔周围可见黑色肿块,双侧颈部及腹股沟可触及多发肿大淋巴结,最大者约5 cm×6 cm,心肺查体无异常,肝脾未触及肿大,双下肢无水肿。

图 1 患者初入院时全身多发皮损A.颜面部;B.躯干
入院后血常规示白细胞4.36×109/L,血红蛋白73 g/L,血小板102×109/L;血生化示乳酸脱氢酶3174 μmol/(S·L),余未见异常;凝血示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43.9 s,凝血酶原时间13.2 s,D-二聚体1.77 mg/L。骨髓涂片:有核细胞增生极度活跃,粒系细胞占3.0%,红系细胞占7.0%,粒∶红=0.4∶1,粒系、红系细胞均增生受抑;原幼淋巴细胞占82.5%,胞体中等大小,圆形或不规则,胞质的量中等,淡蓝色,有空泡,胞核圆形或不规则,染色质疏松,核仁1~3个;单核细胞分类未见;全片见巨核细胞>500个,血小板散在常见(图2A)。细胞化学染色(图2B~D):POX染色(-)、PAS染色(+)、AS-DCE染色(-),骨髓象结合细胞化学染色提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cute lymphocytic leukemia,ALL)。
骨髓(髂后)活检病理结果:HE及PSA染色镜下示骨髓增生极度活跃,骨髓间质可见一类核不规则细胞弥漫成片分布,胞体小至中等大小,核略不规则,染色质细腻,可见1至多个小核仁,MF- 0级;免疫组化:CD20(±)、PAX5(±)、CD3(±)、CD34(-)、CD117(-)、Lysozyme(±)、CD56(+++)、CD123(弱++)、CD4(+++)、TDT(+)、CD7(+++)、Desmin(-)、myodl(-),提示为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肿瘤(blastic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 neoplasm,BPDCN)可能;流式免疫分型:CD4(+++)、CD56(+++)、CD123(弱++),提示为BPDCN(图3)。
鼻腔肿物活检免疫组化结果:CD4(+)、CD56(+)、CD123(+)、Ki- 67指数(50%+)(图4)。病理会诊:确诊BPDCN。PET/CT检查:鼻腔、鼻咽部、双扁桃体多发软组织增厚伴代谢增高,双颈部、纵膈、双锁骨上区、左乳腺区、双侧腋窝、腹腔、腹膜后、双侧腹股沟区多发高代谢肿大淋巴结(最大约5.5 cm×4.3 cm),脾大伴代谢增高,头皮、颜面部、双上臂、左大腿皮下软组织增厚伴代谢增高,全身骨髓代谢增高,考虑淋巴瘤浸润;左附件区代谢增高,考虑浸润不除外。
患者明确诊断为BPDCN,治疗上予强的松预处理,阿扎胞苷联合GemOx方案(d1~d7:阿扎胞苷100 mg/d, d2:吉西他滨1 g/m2+奥沙利铂100 mg/m2)化疗。化疗1个疗程后,患者面部肿块变平减小(图5A),双侧颈部及腹股沟肿大淋巴结、鼻腔肿物较前缩小,鼻塞症状缓解。患者返院复查相关指标示白细胞 2.55×109/L,血红蛋白71 g/L,血小板887×109/L,乳酸脱氢酶3109 μmol/(S·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43.6 s,凝血酶原时间13.0 s,D-二聚体1.43 mg/L;骨髓涂片:有核细胞增生明显活跃,粒系细胞占31.5%,红系细胞占62.0%,粒∶红=0.5∶1,粒系细胞增生减低,红系细胞增生明显,中晚幼红细胞比例增高;淋巴细胞比例减低;单核细胞大致正常;全片见巨核细胞298个,血小板可见成堆分布(图5B)。骨髓(髂后)活检病理结果:HE及PAS染色镜下显示少量破碎骨髓,增生程度无法估计;粒红系造血细胞少见,未见原始细胞;未见巨核细胞;淋巴细胞、浆细胞、组织细胞少量散在;MF- 0级;免疫组化:CD4(-)、CD56(-)。

图 2 患者化疗前骨髓涂片及细胞化学染色结果(×1000)

图 3 患者化疗前骨髓免疫组化(多聚螯合物酶法En Vision,×200)及常规病理染色(HE,×200)结果

图 4 鼻腔肿物活检免疫组化染色结果(多聚螯合物酶法En Vision,×200)及常规病理染色(HE,×200)结果
患者以阿扎胞苷联合GemOx方案化疗4个疗程后,鼻腔肿物消失,皮损较前大部分消退,仅残留少许色素沉着(图5C)。骨髓涂片:有核细胞增生活跃,粒系细胞占比56.5%,红系细胞占比24.0%,粒∶红=2.35∶1;粒系细胞增生,各阶段细胞形态及比例大致正常;红系细胞增生,以中晚幼红细胞为主;淋巴细胞比例减低;单核细胞比例增高;全片见巨核细胞143个,血小板常见(图5D)。肿瘤流式细胞微小残留病变检测未见白血病相关表型细胞,全身浅表淋巴结彩色多普勒超声示双侧腋窝、腹股沟淋巴结肿大(最大约1.3 cm×0.7 cm),较化疗前数量明显减少,大小明显减小,随访至发稿前患者一般情况尚可。
2 讨论
BPDCN是一种罕见的侵袭性血液系统恶性肿瘤,见,极易误诊、漏诊,使BPDCN患者错过最佳治疗时机。该病最初被称为粒状CD4+自然杀伤(natural killer,NK)细胞白血病,直至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提出BPDCN这一名称,2016年,该病被单独列为一类血液系统肿瘤[1]。BPDCN的确切发病率尚未知,相关研究表明,BPDCN约占所有血液系统肿瘤的0.5%,中位发病年龄为53~70岁,男女比例为(2.0~3.3)∶1[2-3]。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儿童BPDCN更为罕见,但目前国外已有报道,BPDCN的发病呈现双峰分布,即第一高峰出现于20岁以下患者,第二高峰出现于60岁以上患者[3]。Kim等[4]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比较了BPDCN儿童患者和成年患者的预后,结果证明年龄是其独立预后因素,即儿童患者的恶性程度较成人低,通常预后尚可[5],成人患者尽管大多数对各种化疗方案都有反应,但极易复发,且复发后治疗效果较差,其中位总生存期为1年[6]。本例患者目前未复发,但由于随访时间尚短,长期疗效仍需观察。

图 5 患者阿扎胞苷联合GemOx方案化疗1个疗程(A、B)及4个疗程(C、D)后,面部肿块逐渐变平、缩小,仅残留少许色素沉着,骨髓涂片逐渐接近正常
从细胞遗传学和生物学角度,60%的BPDCN患者可出现染色体复杂核型,常见的重现性染色体异常包括5q、6q、12p、13q、15q、9号单体[1],亦有研究证实该病的发生与MYB家族基因和MYC的基因组重排有关[7],BPDCN除侵犯骨髓和皮肤外,还可有许多髓外病变,包括中枢神经系统、胸膜、鼻腔、睾丸、扁桃体、肺和眼睛等,此例患者为鼻腔及皮肤受累,BPDCN诊断除需依据临床表现、影像学、形态学、分子生物学外,还需检测免疫表型,BPDCN细胞表达CD4、CD43(SPN)、CD45RA和CD56(NCAM1),以及浆细胞样树突状细胞相关抗原CD123(IL3RA)、BDCA- 2(CD303,CLEC4E)、TCL1和CTLA1(GZMB)[8]。BPDCN的特异性免疫表型包括CD4、CD56、CD123、TCL1和CD303,通过上述特异性免疫表型基本可诊断该病。本例患者首次就诊时骨髓病理免疫组化示CD4(+++)、CD123(弱++)、CD56(+++),符合该病的诊断标准。BPDCN患者初次就医时应尽可能完善相关检查,包括完整的影像学资料(如增强CT或PET/CT)以及骨髓常规、病理和流式细胞术免疫分型等[9]。BPDCN多首发于皮肤,且表现缺乏特异性,极易与原发性皮肤病相混淆[10],此外,该病亦可被误诊为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acute myelogenous leukemia,AML)皮肤受累,当病灶数目较少时,还可能会被误诊为创伤性紫癜。一项研究90例BPDCN患者临床表现的回顾性分析中,73%表现为1个或多个结节,14%带有弥散性斑块,12%带有瘀伤样斑块,但皮损的严重程度似乎与生存无关[11]。此外,BPDCN易被误诊为髓样肉瘤和结外NK / T细胞淋巴瘤,需要详尽的免疫组化检查加以区分[12]。
CD56是神经细胞黏附分子,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家族成员,其在NK细胞以及CD4+和CD8+T淋巴细胞上表达,被认为是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和间变性大细胞淋巴瘤患者预后不良的指标,CD56与各种肿瘤的进展和转移密切相关,目前被广泛用作多种恶性肿瘤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的生物标志物[13]。在血液恶性肿瘤中,CD56是NK /T细胞淋巴瘤的特异性标志物,见于浆细胞瘤和微绒毛淋巴瘤。 Sobas等[14]和Rai等[15]研究均认为CD56是AML不良预后的独立指标。本例患者治疗前骨髓病理免疫组化示CD56(+++),提示其预后较差,考虑本例患者为年轻女性,本中心采用阿扎胞苷联合GemOx方案化疗,仅1个疗程后,患者骨髓病理免疫组化即显示CD56(-),且皮损较前大范围好转,双侧颈部及腹股沟肿大淋巴结、鼻腔肿物均缩小,有较高的治疗应答率;4个疗程后鼻腔肿物消失,皮损仅残留少许色素沉着,各项检测均提示病情明显缓解,且随访4个月时患者一般情况尚可,表明此化疗方案效果可观,三药联合治疗在效果上和起效速度上均明显优于单药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鉴于BPDCN的发病率低,且不易诊断,该病目前尚无标准治疗方案,临床常用治疗手段大致分为化学治疗、造血干细胞移植、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现已证明BPDCN的发病机理为表观遗传修饰基因突变和转录甲基化信号异常过表达,因此,表观遗传学及基因靶向治疗很可能是一种极具潜力的治疗策略,低甲基化剂、阿扎胞苷和地西他滨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6]。美国一项跨度13年的大型回顾性研究中,将化疗方案分为采用AML标准诱导方案、ALL标准诱导方案、CHOP样方案、大剂量甲氨蝶呤联合天冬酰胺酶(Aspa-MTX)化疗以及其他治疗5组,该项研究结果表明,接受AML及ALL标准诱导方案或Aspa-MTX化疗的患者,其生存期长于接受CHOP样方案或其他方案者。值得注意的是,BPDCN易侵犯中枢神经系统,若化疗方案未覆盖中枢神经系统,则需加强中枢浸润预防[8],推荐预防性鞘内注射化疗药,或使用其他可透过血脑屏障的药物如塞替派等。目前国际上推荐的低强度化疗药有地西他滨[17]、吉西他滨联合多西他赛和苯达莫司汀[1]。除小儿BPDCN病例外,单靠化疗产生持续缓解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造血干细胞移植在患者获得首次完全缓解后维持长期生存显得尤为关键,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各种血液系统肿瘤的潜在疗法,在首次完全缓解时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可提高总生存率[6]。对于不适用高强度诱导化疗以及造血干细胞移植方案的老年患者,除采用低强度化疗外,靶向药物为BPDCN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Tagraxofusp是近几年开始用于BPDCN的一种CD123靶向治疗药,安全性尚可,且其副作用总体上可被接受,已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18]。部分BPDCN可转化为AML或合并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且在BPDCN患者中也检测到 DNA甲基化基因TET2突变,去甲基化药物阿扎胞苷已被批准用于中高危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和AML,由于BPDCN也是一种髓样恶性肿瘤,因此也被用于该病的治疗。另有研究评估了3例使用阿扎胞苷化疗的BPDCN患者的预后情况,结果表明患者的皮肤病变均得到改善,但仅1例达到持久缓解,所有患者耐受性均较好,但3例患者的中位生存期仅为17个月[19]。Bcl- 2抑制剂是近几年开始应用于临床的一种靶向治疗药物,也可用于BPDCN患者的治疗。编码抗凋亡细胞存活蛋白的Bcl- 2基因在BPDCN中过表达,有研究发现,BPDCN原始细胞对Bcl- 2抑制剂Venetoclax均敏感,国外文献报道了2例复发/难治性BPDCN的患者在接受Venetoclax治疗后效果可观,因此推荐Venetoclax或其他Bcl- 2抑制剂单独或联合其他疗法用于BPDCN患者的治疗[20]。嵌合抗原受体修饰T细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modified T cells,CAR-T)疗法是近年来新兴的免疫疗法,在多种肿瘤疾病的治疗中效果显著。CD123在BPDCN中高表达,此CD123 CAR具有特定的单链抗体(scFV)和较高的亲和力,可特异性识别CD123,与BPDCN患者的原始细胞相结合,而不与血液或骨髓正常细胞结合,从而达到精准杀灭BPDCN肿瘤细胞的作用。CAR-T治疗最常导致的不良反应为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但研究表明CD123 CAR-T细胞可能会减少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的发生[21]。如上所述,BPDCN的治疗方案有多种,本例BPDCN患者表现为CD4、CD56强阳性,故本中心采用了阿扎胞苷联合GemOx方案,阿扎胞苷作为经典表观遗传学抗肿瘤药,其可抑制肿瘤组织中DNA甲基化水平,从而可逆转被过度甲基化的抑癌基因恢复正常功能。GemOx方案中的吉西他滨属于抗代谢类抗肿瘤药物,通过作用于细胞S期,抑制细胞DNA合成,从而促进细胞凋亡;奥沙利铂是三代铂类抗癌药物,通过抑制DNA合成,从而显著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增殖。GemOx方案具有用药简单、高效抗癌和低毒性等特点,因此在多种恶性肿瘤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2020版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淋巴瘤诊疗指南提到,GemOx方案对NK/T细胞淋巴瘤、外周T细胞淋巴瘤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该方案首次被使用,患者治疗效果较好,这将为BPDCN的临床治疗方案提供更多选择。
3 小结
BPDCN在临床上较为罕见,且往往恶性程度较高,预后差,确诊后应尽快治疗以改善预后。此例BPDCN患者鼻腔及皮肤同时受累,临床更为罕见,且由于国内外目前对BPDCN报道较少,本中心采用的阿扎胞苷联合GemOx(d1~d7:阿扎胞苷100 mg/d, d2:吉西他滨1 g/m2+奥沙利铂100 mg/m2)方案对患者的长期预后意义,需要通过更长时间的随访结果以及更多病例的应用经验加以验证。
作者贡献:陈晓君负责收集资料、查阅文献和论文撰写;刘彦权负责论文修改和校对;胡晓梅、黄素蓉负责患者图片收集和整理;沈建箴负责论文审核。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注:本文发表已获得患者知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