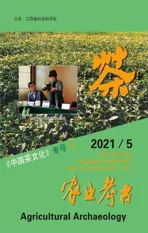全面抗战时期徽州地区的茶农生计*
2021-12-15张绪
张 绪
1937年7月7日,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僻处皖南山区的徽州虽然少有战火之苦,但是由于战时环境影响,当地的经济与民生却深陷困境。茶业作为当时徽州地方经济结构的主体,它的衰疲直接影响到当地茶农的日常生计以及皖南后方社会的稳定。
一、战时徽州地区茶业经济的衰疲
徽州一域僻处皖南山区,由于山多地少,田亩不足,所以当地农民多恃山林产业为生,而茶叶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生计资源。据记载,在全面抗战之前,“徽属各县农民大多恃产茶之收入为一年之总开支”[1],“徽茶之盛衰与民生关系至为密切”[2]。在著名的“祁红”“婺绿”产地——祁门和婺源(今属江西省),更是如此。如祁门县,境内“山丘地占80%,一般农家多以植茶为主,杂粮为次”[3],“茶农的一年生活所系全靠茶市的收入,不像别的地方,茶叶不过是副业而已”[4]。在“山多田少”的婺源县,“出产以茶叶为大宗”[5],产茶区域几乎“无处无之”[6],“茶农一年生计全赖于茶”[7],“茶叶一项占茶农总收入百分之五十以上”[8]。茶叶种植在近代徽州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中占据着明显优势,茶叶资源对当地社会民生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近代,徽州出产的茶叶主要用于外销,对外部市场有着很高的依赖度。在全面抗战开始后,作为国内重要产茶区的徽州因为受到战事影响,茶叶对外贸易路线严重受阻,地方茶业经济随之陷入困境。据称,1938年以后,“徽州茶叶市场日渐萧条,精制‘屯绿’茶号因外销滞落,竟由原来287家骤减至12家”[9](P6)。茶号数量从287家减少至12家,缩减比率约为95.82%,茶业市场的衰疲程度可见一斑。伴随着茶号数量的急剧减少,当地的茶叶产销量也呈现出明显的颓势。如婺源出产的绿茶在最盛时期每年产毛茶4万担,“抗战后外销逐暂呆滞,生产因之日减。至三十二年(注:1943年),只有毛茶1万担矣”[5]。昔日在茶界颇有名气的“祁红”“屯绿”,其销量则一路下滑。据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调查,1936年祁红销售数额为84000余市担,1938年为46000余市担,下滑幅度接近50%。当时就有去过祁门的人谈及:“现在采办祁红,只有‘陷区’上海茶商时来零星问津,其他内地销售为数甚微。”而且在他们看来,因为受到“抗战滞销之影响”,这种“长期趋势的惨跌”无可挽回[10](P120)。与“祁红”境遇类似,“屯绿”的销量也较战前有了大幅度下滑,“屯绿在战前外销颇畅,大部运销欧美各国,战时亦与祁红遭同样之命运。民廿二年(注:1933年)产额,据估计为13万余市担;民二十六年(注:1937年),贸委会收购为7万余市担;近年来则更江河日下,同时因销路不良,农村经济危机日趋严重,于是有许多茶农因感于生计迫切,不得已多将茶树砍伐,改种杂粮,以致往昔绿黝黝的可爱茶林一变而为牛山濯濯矣。祁红固已不‘红’,屯绿而今也不‘绿’(乐)了。”[10](P121)“祁红”“屯绿”的严重滞销反映出战时徽州地区茶业经济的不景气,当地茶农的家庭生计深受影响。
二、战时徽州地区茶农生活的窘迫
随着茶业经济的衰落,不少茶农开始面临严重的行业危机,其经济处境愈发艰难,生活变得穷苦不堪。如在婺源茶区,自抗战伊始,当地茶农便遭遇茶叶滞销与茶价低落的困境,“春茶开始东奔西走,告贷无门。迨初制完竣,毛茶无人过问,即曩昔贩买贩卖而从中渔利之茶贩亦裹足不前,欲以低价脱售而不可得,况有利之高盘乎?结果,山价造成□(注:原文缺字)六元之极低纪录,惨极人寰(此系指婺源茶区而言,该年扯价约二五元,至其他茶区或因别种关系而有不同,然不景气则一律也)”[11]。对以茶为生的茶农而言,毛茶的滞销意味着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断绝,在此情形下,茶农的生活只会变得更加艰难。在位于歙县东部的茶产区,茶农的生活也因茶叶滞销而变得相当困苦。据当时人描述:该地茶农“吃的是‘苞萝’,今年的收成不好,因为秋日久旱,只有四成收入,每天能有一餐白米饭吃的都很稀少。没有水田,米都是从绩溪、旌德等地挑来的,每元六升半、六升、五升半,渐渐高涨。他们愁着冬腊的食粮,更有明年呢?所有的希望都是寄托在茶叶上面,毛茶价的高低成了生死存亡的关键。他们深受高利贷、捐税以及物价侵蚀的重压,喘不过气来。生活一天天地痛苦,意志也就更消沉、麻醉,看不到前途的光明”[12]。茶业经济的衰疲让当地的茶农备受煎熬,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温饱都难以维系。其实,这种情形在当时的皖南茶区相当普遍,甚至出现茶农吃草根树皮以及饿死的悲惨现象[13]。
在抗战期间,除茶叶滞销外,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的匮乏以及物价的飞涨也让徽州茶农的生活雪上加霜。众所周知,徽州地处山区,受地理环境限制,当地的粮食产量一向比较低,经常需要到周边余粮地区进行调运和接济。据1935年2月7日出版的《申报(上海版)》记载:“皖南徽属各县僻处山丛,可耕田少……产粮向不敷民食,大半仰给于芜湖、太平、宣城、景德、饶州各埠。”[14]缺粮成为困扰徽州地方社会民生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全面抗战发生后,这一问题更加凸显。当时的徽州正好处于东南战场的后方,又为皖南行署所在地,环境相对安全,大量沦陷区的难民纷纷涌入,进而造成当地人口数量激增,对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的需求也变得极为旺盛。在此情形下,缺粮问题自然也就更趋严重。如在婺源县东北乡,“所产米粮只足三个月之用,玉蜀黍只足两个月之用。祁门缺粮约如婺源。两县穷民现均挖食树根疗饥”[15]。不仅缺粮如此,而且粮价飞涨,这也让徽州地区的茶农苦不堪言。在战时,因为有限的粮食供给难以满足众多人口的消费需求,加上不法粮商趁机操纵市场,囤积居奇,所以徽州等地的粮价一路飞涨,这对于以种植茶叶作为主要经济收入来源的茶农而言,无疑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让他们本已艰难的生活更加不堪。以祁门县为例,据《祁门茶情》记载:“盖今年祁中粮食甚缺,价格奇昂,米每石一二百元,茶农自无福消受,赖以为生者唯有杂粮,以食玉米(俗称包芦)为最普通。但玉米一石亦须百元,近已腾至百二三十元左右,以一人日食一升、每家四口计,则每日所食已需五元左右。及观今年茶农毛茶售与茶号之价格,不特未曾提高,且有不及去年之价格者……今年茶号所收毛茶平均扯价,每担(大秤)只三十余元(如以市秤计,则不出二十元),是则售茶一担只足购玉米二斗,不及一家五口之粮。普通茶农所产茶叶极有限,其不免于饥馑者几希!”[3]一方面是茶价的低迷,另一方面是粮价的高涨,由此形成了一种价格剪刀差,祁门县茶农靠出售茶叶所得的经济收益变得十分有限,无力承担价格快速上涨所带来的较高粮食消费成本,生活过得颇为艰难。在其他产茶地区,茶农的生活状况也基本如此。时人原颂周在考察东南四省茶区(包括祁门、浮梁、屯溪、婺源、淳遂区、武夷山)之后做了这样的描述:“茶区都是山岳地带,居河流之上游,绿山青山,茶农卜宅其中,洵得清福,有《乘桴由祁门下平里》一诗为证。可是月不常圆,昔之养尊处优者,今则茹苦含辛,莫知死所。原因是茶山类皆缺粮,向持卖茶之资购进粮食,今粮贵茶贱,生活立受打击。”[15]关于当地茶农的真实生活,从原颂周所写的几首写实性诗作[15]也可看出。为便于了解,现将这几首诗作转录如下:
《宿婺源塔坑有感》
飘飘寒雨似梅天,路入荒山马不前。
一宿探知穷苦在,有茶无米复无钱。
《祁门即事》
茶园处处满蘼芜,四月晴和草木疏。
旧日当炉夸富有,如今采叶赚钱无。
千官忙为功名计,万户愁将庚癸呼。
救死怜贫应及早,忍令老弱坐泥涂。
《采薇》
茶事萧条敲野葛,远荒无米且如薇。
山民品尽凄凉味,性命如悬肠不肥。
由这三首诗作可以看出,在祁门、浮梁、屯溪、婺源、淳遂区、武夷山等东南四省茶区,因为受到战时环境影响,物资运销困难,所以当地的茶业经济变得十分萧条,粮食短缺问题也更为严重,有茶无钱、粮贵茶贱成为困扰当地茶农生产与生活的两大现实难题。如在婺源塔坑,“村中便有老农饿死之事”。在该县第三区,亦“有因穷自杀之事……在不远的村庄,以无力用实物完粮、情急自尽者亦有两起。其他茶农亦皆疾首蹙额,以卖物完粮为苦事”[15]。茶农的艰辛和无奈显而易见。
迫于生存压力,徽州地区的一些茶农纷纷开始砍伐茶树,改茶种粮,试图通过调整产业方向,来化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正如时人所言:“皖南的祁红、屯绿尤为外销茶叶的巨宗。战后因国际交通路线翦断,堆积的茶叶无法外运,以致资金呆滞不灵。政府既无法大量收购,茶商也无力继续周转经营,而茶农乃不得不除去茶树,改种杂粮以资糊口。”[16](P122)在婺源县,自抗战爆发后,因为粮食购买困难,“人民多数砍伐茶树,改种杂粮,藉维目前生计”[5]。改茶种粮的现象在该县东北乡尤为普遍,“能种杂粮之茶园,业经砍去茶树十之四,其可以改种水稻之地方,均已挖除根株”[15]。在祁门县,虽然“尚无大量砍茶情事”,但是茶农改茶种粮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杂粮的种植面积渐呈扩大之势。据统计,到1941年,该县“种植玉蜀黍之面积已倍蓰于前”[15]。其实,这种改茶种粮的现象在当时整个皖南茶产区相当普遍,有的则是任由茶园荒芜,不再进行生产投入。据记载,自抗战发生后,“各港口相继沦陷,致失出口之路,销场为之一蹶不振。农村既少收入,生活又复日高,迫不获已,将植茶地区之茶树砍去,改种高粱、玉米,以资糊口。高岗之茶虽未砍去,因无销路,不去芟草施肥,亦多枯萎”[17]。在销路受阻、市场萎缩的情况下,茶农们束手无策,只好将原本就不适宜于种粮的茶地改为粮田,以图自救。可以说,改茶种粮或弃茶不种是当时徽州茶农在茶叶滞销、粮食短缺的现实生存困境下所做出的一种无奈选择。
三、战时徽州地区茶农经济的救济与扶持
在抗战时期,茶叶不仅与徽州地方经济与社会民生有着密切关系,而且具有可观的贸易价值,是中国换取外汇的一大物产资源,关乎中国抗战之大局。时人有言:“盖自抗战以来,茶叶出口年值数千万,其对于抗战之贡献实非浅鲜。”[18]鉴于此因,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地方茶业经济也比较重视,并采取了一些救济和扶持措施,以解决茶叶生产和茶农生活的困境。徽州作为当时国内的一个重要产茶区,又是皖南国统区的核心地区,茶业经济自然会受到较多关注。
在战时,为改善和发展茶农经济,徽州地区相继成立了茶叶生产运销合作社,其目的是希望“采用合作制度,以合作社方式把散漫的茶农组织起来……使茶农自产毛茶,以集体的力量自己加工精制,联合运销,缩短生产者与消费者中间的转折过程,取消中间商人种种无理剥削,更进而改进茶树栽培,建立现代化的茶园茶场”[19]。1939年5月,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成立,并“于‘屯绿’茶区的休、歙两县”成立茶叶生产运销合作组织,“依据省会合约,设合作指导团,专负休、歙、祁、至四县茶合事业推进之责”[20]。至1940年8月,安徽省茶叶管理处又“根据省建设厅订定之调整办法,将合作指导团改组为合作室”[20]。在该机构的指导和推动下,徽州地区的茶叶生产运销合作社数量有了一定的规模。据统计资料显示,至1941年7月,皖南各县有茶合组织133社,社员人数为9984人,各项贷款总额为92835700元。其中,休宁的茶合组织有31社,社员人数为3225人,各项贷款总额为11326300元;歙县的茶合组织有15社,社员人数为2005人,各项贷款总额为6997400元;祁门的茶合组织有61社,社员人数为2674人,各项贷款总额为54000000元[21]。三县的茶合组织数共计107社,社员人数为7904人,各项贷款合计为72323700元,这三项指数在皖南茶合组织总指数中所占的比例依次为80.45%、79.17%、77.91%。可见,在战时皖南地区,徽州地区的茶叶合作社在组织数量、社员人数以及贷款数额方面都占据着明显优势。这些先后成立的茶叶生产运销合作社有助于降低茶农制茶与销茶成本,较大程度地避免了中间商人的克扣盘剥,有利于保护茶农的自身经济利益。如在休宁县西边的回流乡,该地盛产茶叶和桐油。至抗战发生后,因销路不畅,产品滞销,加上旱灾影响,当地“居民十室九空,以大麦、玉蜀黍和菜而食,尚不得饱,灾情至为严重”。但是,得益于“茶合社之组织,社员得有贷款换粮度日,得以不死,而其所产茶叶亦免压价或不能出售之损失”。该县鹤城乡亦是“田地甚少,物产以茶、桐、竹、木为大宗”。该地茶农生活更加艰苦,在毛茶滞销的情况下,“未参加茶合社者只得不惜血本忍痛出售,但社员则无此种损失”[22]。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茶叶合作社组织尚不完善,“惟因进展过速,难免粗制滥造,忽视了质的健全”[20],其实际运行效果还不尽如人意。比如在贷款方面,原先预计在1939年冬季“贷款与茶农,作中耕施肥等生产上用途,终犹豫不决,临渴掘井,茶农需款急得万分,才来设法筹放,茶农直到年关腊月底才借到款,但已失了时效”[19]。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会给茶叶合作社带来声誉上的损害,而且不利于茶叶合作社开展和推进后续工作。
在抗战时期,茶叶作为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资源,与桐油一样均被国民政府纳入管制范围。为促进茶叶经济发展,充实抗战经济实力,国民政府在对茶业经济进行实际管制的过程中,也会适当考虑茶农和茶商的利益,以便提高他们的从业积极性。战时安徽的茶叶管制除涉及贷款、收购、运储等环节外,对毛茶价格也有具体的限定,即“为保障茶农利益,以求茶业交易之合理,由茶管处于茶汛开始之期,派员分赴各茶区调查毛茶产制成本,依照成本调查之数加上农民正当利润,规定毛茶山价,使农商遵此价额交易,俾利益均沾”[23]。对于茶农而言,毛茶价格直接关乎其经济利益,政府通过定价管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茶农的经济利益。另外,安徽省茶叶管理处作为战时安徽省茶叶资源管理的专门机构,对茶农利益之保护也有其明确职责,这在《安徽省茶叶管理处管理规则》中有所体现。如《管理规则》第一条即提出要“维护从业者之正当利益”。《管理规则》第四、五、六、七条则主要强调在毛茶交易过程中对茶农利益的保护。在毛茶价格方面,第四条规定:“毛茶价格不得低于生产成本,亦不得故意操纵,妨害产量与推销。凡收购毛茶者应就所在地议定最低价格,悬牌公告,并须呈报本处备案。”在对茶农的经济补偿方面,第五条规定:“凡经营制茶之公司厂号合作社(以下简称制茶者)均须提出纯利至少百分之十补偿茶农”,以作“办理农村福利事宜之用”。在毛茶交易款项方面,第六条规定:“毛茶交易以兑付现款为原则,遇有特殊情形,如运现困难时,其迟延付款时期亦不得超过一个月。”关于毛茶交易的公平性原则,第七条规定:“收购毛茶不得克扣斤两,并须应用市秤。”[24]这些《管理规则》条款对保护茶农的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此外,在抗战期间,安徽省国民政府还利用安徽地方银行发放茶贷,以扶持茶农经济,促进地方茶业经济的发展。安徽地方银行于1936年1月16日在芜湖正式成立,并在安庆、蚌埠、屯溪设有分行,各县设办事处。后来受抗战形势变化影响,至1938年夏,遂“以长江为界,在屯溪设总行临时办事处,总行及总金库则设于战时省会之立煌县城,分区管理大江南北行处业务”[25]。作为战时安徽的一个重要金融机构,安徽地方银行的经营业务范围较广,除开展存款、汇兑、信托等业务外,对生产事业以及社会事业亦积极扶持,时常开展放款业务,其中就包括茶叶贷款一项。如在1939年,该行“于皖南与中央搭放二成,计一百二十万元,皖西搭放三十万元;在1941年,“因中央停止茶贷,该行单独在皖南贷放二百四十万元,在皖西贷放三十万元”[26],遂“使当时动荡不安之产茶区域顿趋稳定”[25]。茶叶贷款的发放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茶农在生产经营方面的资金压力,有助于改善已经衰疲不堪的徽州茶业经济,也在客观上保障了后方社会的稳定。
四、结语
总之,茶业作为近代徽州地方经济的一大支柱性产业,其兴衰既关乎国计,又牵涉民生,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进入抗战时期,这种关系依然存在,甚至比战前更为凸显。在战时,因为军事侵扰和经济封锁的影响,徽州出产的茶叶无法外运,茶叶外销路线严重受阻,茶业经济遂呈现出衰疲之势,且濒临崩溃。在种茶收益锐减、物价不断攀升的情况下,徽州茶农的经济生活深受影响,日益艰窘,在他们中间,食不果腹者多见,因贫自杀者有之。面对茶叶滞销、粮食短缺等艰难困境,改茶种粮或弃茶不种成为许多徽州茶农的无奈选择。为改善和扶持茶农经济,充实抗战经济力量,安徽省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举措,不仅成立了专门的茶叶管理机构即安徽省茶叶管理处,来加强对该省茶叶经济的管制,而且还在徽州地区积极推行茶叶生产运销合作社,以保障茶农之利益,并在抗战初期利用安徽地方银行发放茶贷,来缓解茶农在生产经营方面的资金压力。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战时徽州地区的茶业经济以及茶农生计,也保障了后方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