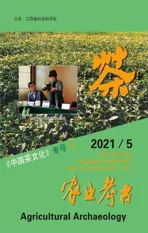礼法融合:古代宫廷茶文化及其延伸*
2021-12-15卢欣
卢 欣
中华茶文化起源于“神农尝百草”的先民时代,从“南方之嘉木”到“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茶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从单一的物质文化向组织制度文化和精神生活文化等不同层次的全面深化过程,最终使得茶成为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国饮。总体来看,茶兴于唐而盛于宋,得益于统治阶层的认可和接纳,是在政治统摄之下“政治、文化双重共同体互构认同”[1]的结果。因此,从贡茶、赐茶、茶税、茶法到茶宴、茶诗、茶俗、茶礼,茶作为天地灵物由“野”入“朝”,继而又由庙堂到江湖,被注入了丰富的政治文化意涵。在古代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宫廷茶文化由于统治阶层所特有的政治核心地位,在中华茶文化体系的整体发展方向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对茶文化的民间大众化流行也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在我国古代传统国家治理体系中,一直有着“礼”“法”之争,即以“礼”治国与以“法”治国的优先性问题,两者分别以儒家礼治和法家法治为典型代表。尽管自汉代以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统治者的官方认定,但实际上在历代王朝统治中,始终存在着“外儒内法”“阳儒阴法”的纠缠,而宫廷茶文化向民间大众茶文化的延伸,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统治阶层融合“礼”与“法”的有效载体,成为古代圣王之道在现实社会走进“百姓日用”的可能实践路径。由此,对宫廷茶文化的多重面相进行细致梳理,探究宫廷茶文化及其延伸的象征意义与隐喻意涵,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全面了解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对当前推进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一、祭与贡:从野到朝的礼制兴起
一般认为,茶叶最初进入人类先民视野是基于其药用价值,据传已散佚的《神农本草》中记载:“神农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2](P2)。然而,此时之茶尽管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药用价值,但毕竟是野生之物,尚未进入到统治阶层的权力象征之域。由现存文献考证,茶进入古代宫廷王室的视野可以追溯至周代,《周礼·地官司徒》记载“掌荼,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二十人”[3](P142)、“掌荼:掌以时聚荼,以共丧事”[3](P249);在《尚书·顾命》中,也有“王三宿,三祭,三咤”[4](P407)的记载。在周代,王室祭祀是十分重要的政教合一仪式,在权力最高位者需要以“绝地天通”的唯一性来捍卫自身执政的合法性、标榜权力的天命神授,而祭祀之中出现茶的身影,甚至是出现司掌茶事的专职人员,表明茶这一天地自然灵物实现了从“野”到“朝”的转变,被赋予了神圣符号象征之义,成为周代礼乐制度体系建构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可以说,作为礼治天下之茶此时便已初现端倪。
如果说宫廷祭祀之茶尚且是在世之人对已逝祖先、在地之人对在天神灵的敬畏和祷告的话,那么“贡茶”的出现,则是宫廷茶被赋予礼制等级隐喻的关键一步。据《华阳国志·巴志》载,早在周朝时巴蜀便把茶作为向周天子敬献的贡品之一,“茶、蜜、灵龟……皆纳贡之”;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从野生茶树向种植茶树的转变,“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葵”[5](P2)。周王室在得到巴蜀地区的“贡茶”之后,则投桃报李“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通过联姻的方式让宗室女子嫁到巴蜀之地,使得巴蜀之地的统治者在与周王室联姻之下成为周天子的宗族血亲,具备了天命在兹的分封合法性。在这一过程中,贡茶无疑是联结政治权力、血缘宗亲、神人关系的桥梁纽带,而贡之以茶、祭之以茶也成为构建封建礼制体系的重要象征符号。
巴蜀进贡周王室之茶或许还只是偶然为之,真正常态化、制度化的“贡茶”则始于唐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代宫廷贡茶区有怀州、峡州、归州、夔州、金州、兴元府、寿州、庐州、蕲州、常州、湖州、睦州、福州、饶州、溪州、雅州等“八道十一州”[6](P97),各地进贡茶叶数量不等,专供宫廷皇亲国戚和权贵大臣饮用。为进一步加大贡茶常态化、制度化监造,大历元年(766)和大历五年(770),唐朝统治者分别在江苏义兴(今江苏宜兴市)和顾渚(今浙江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顾渚山一带)设置了贡茶院,这也标志着贡茶制度的真正确立。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顾山,在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7](卷第二五《江南道一》P606),而宋人钱易《南部新书》也记载“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谓之‘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8](P66)。由此可见,唐代贡茶数量已经十分庞大,对于贡茶区地方而言,也是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满足宫廷茶的消费需求。这一方面使得茶作为上流社会饮用之物进一步被赋予高贵、神圣的象征意义,推动了茶叶消费的时尚;另一方面也使得茶叶等级品次与人本身的地位紧密关联,成为“尊尊”“亲亲”儒家礼制文化的重要符号。以特定地区、特定批次贡茶专供宫廷贵胄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在儒家礼治天下的“尊卑”“名分”“差序”脉络之下也使得以茶治国、开展茶政成为可能。
随着贡茶制度的深入,民间饮茶也不断普及,到宋代时,统治者为了在宫廷饮茶上彰显自身的高贵地位,除了在产地上进行贡茶区划分,还在茶叶品质、采摘批次、外观形式等方面进一步提升“礼”的标准化,开始监造著名的龙凤团茶。宋人熊蕃在《宣和北苑贡茶录》中记载:“太平兴国初,特置龙凤模,遣使即北苑造团茶,以别庶饮,龙凤茶盖始于此。”[9](P133)由此可见龙凤团茶最初的目的就是在于“以别庶饮”,突显宫廷茶与民间茶的“尊卑有别”。除了对宫廷茶整体高贵性的彰显之外,在龙凤团茶系列中,也有尊卑高低之分,对应统治阶层内部的礼制规范。比如,通过大小团茶来区分品次,据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龙、凤团茶最为上品,一斤八饼。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运使,始造小团以充岁贡,一斤二十饼,所谓上品龙茶者也……”[10](卷八《事志》,P99)北宋杨忆《谈苑》则对龙凤团茶等级进行了详细记载,列出了“龙茶、凤茶、京挺、的乳、石乳、白乳、头金、蜡面、头骨、次骨”十个等级,“龙茶以供乘舆及赐执政、亲王、长主,其馀皇族、学士、将帅皆得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白乳”[11](P115)。除了严格按照君臣、父子、长幼、夫妇等儒家礼制要求发放不同的茶品之外,连发放的先后也有明确的规定,“号为头纲,玉芽以下,即先后以次发”[11](P119)。宋代是儒家文化发展的又一高峰期,礼治天下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司马光就曾在《资治通鉴》中直言:“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而朱熹更是主张“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12](卷一四《戊申延和奏劄一》,P657)。由于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注入浓重的礼治内涵,宫廷贡茶作为统治阶层饮食日用之物自然也不例外。
此外,在宫廷茶文化中,以帝王之尊对臣子、使节甚至百姓赐茶,也是其茶政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宋史·礼志》载,“凡宰相、枢密、执政、使相、节度、外国使见辞及来朝,皆赐宴内殿或都亭驿,或赐茶酒并如仪”[13](卷一一九《宾礼四》,P2282)。在宋之后的明代、清代,宫廷茶文化中也都有各种赐茶活动出现,进一步使得高贵之茶成为君礼臣忠的褒奖恩赐、象征邦交友好的礼物符号、彰显爱民恩泽的仁政隐喻。
二、税与榷:利出一孔的塞私充公
在儒家文化传统中,“大公无私”“重义轻利”是个体公私观、义利观的基本伦理价值取向。相应的,在国家治理层面上也提倡“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圣王治国之道。在封建王朝的公私观中,长期秉持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固有认知,“公”的含义也大多直接是指封建王侯与国君,即“天下”“国”与“公”系于国君一人,国君作为“天子”与百姓的关系被视为是一种公私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直接写照,比如《诗·周颂》就有“嗟嗟臣工,敬尔在公”[14](P323)之句。由此,在古代国家治理实践中,维护统治者、忠君尽职也成为忠义礼智信的首善标准、天下“大公”的检验标准。尽管随着儒家文化自身的发展,其公私观中也逐渐注意到“天子”与“天下”的区别,但是“在传统血缘宗法的等级社会中,儒家无法在制度上找到区分二者的保障”[15](P102)。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儒家早期公私观中对天子国君的尊崇,成为了法家公私观和国家治理观的源头。法家代表人物韩非,便认为“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把国君之利视为“公利”,臣民之利视为“私便”,认为应该“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对人们利己本性加以明确的法度规范以实现真正的 “公利”[16](《八说》,P425)。正是在这样的礼法之争背景下,阳儒阴法、外儒内法成为历代统治者国家治理的重要实践路径。随着饮茶全民化、茶叶经济的繁荣,宫廷茶与民间茶成为折射“公私”关系的新兴样态,制定茶法、征收茶税、榷茶专营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统治阶层“塞私便”以充“公利”的重要选择之一。
实际上,由于得到统治阶层的认可以及宫廷茶文化的带动引领,民间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也突飞猛进。唐代陆羽《茶经》的问世推动民间大众茶文化的进一步普及,自此“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17](卷六《饮茶》,P51)。安史之乱后,唐朝廷国库日益空虚,军费匮乏,如何短时间内迅速增加财政收入成为统治者急需解决的燃眉之急,而与此同时,民间茶业的发展却不断呈现上升趋势。诗人岑参《郡斋平望江山》提及当时茶叶种植的普遍性,“庭树纯栽桔,园畦半种茶”[18](P2089);孙樵《书何易于》中记录了民间茶经济发展状况,“益昌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19](P9651);《册府元龟》记载,唐代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20](P510)“伏以江南百姓营生, 多以种茶为业”[20](P494);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洗宗礼状》中描写当时四川泸州一带茶叶种植,更提到“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21](P8048)。由此可见,南方的茶叶种植在唐代时已经十分普遍,由于其经济收益高,甚至成为百姓农业种植的根本作物,地位高于秀麦等其他粮食作物。一方面唐王朝国库空虚、急需用钱,另一方面南方茶叶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成为农业重要支柱,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宗建中三年(782),采纳户部侍郎赵赞的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之一,以为常平钱”[22](卷八四《杂税》,P1545)。这次征税只是临时性的赈灾救急,不久即停征,而直到793年盐铁使张滂奏立税茶法重新开征,“伏请出茶州县若山及商人要路,以三等定估,十税其一”[23](P1435),由此茶税成为独立税种进行常态化课税。事实上,茶税的出台是统治阶层面临政权稳定现实需求而做出的必然选择。《商君书》有云:“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孔,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24](P150)茶税的产生正是宫廷茶通过茶税之法来扩展茶的政治社会功能的结果,是以宫廷茶统摄民间茶,以国君之“公利”对百姓之“私利”的“塞私充公”。唐代农业税赋一般为三十取一,而茶税十取一可见征收之重,亦可见当时唐朝统治者对于茶税提升国库收入的重视。据《旧唐书》记载,德宗贞元九年(793)国家财政全年收入为40万贯,整个开成年间(836—840年)朝廷的矿冶税“每年也不过收入7万余缗,甚至还抵不上一县的茶税”[25](P253)。大量的茶税收入则使得唐王朝得以迅速增加国库收入,以至于“大中初,天下税茶增倍贞元”[20](P510)。
此外,除了在茶税上间接助力“利出一孔”外,唐朝统治者还进一步出台“榷茶”法,加大对茶业的宫廷垄断。所谓“榷者,禁他家,独王家得为之”[26](卷五九《五宗世家》,P2547),也就是说茶叶种植、采摘、制造和贸易销售全由国家垄断,私人一律不得经营。大和九年(835)唐文宗采纳郑注建议,“以江湖间百姓茶园,官自造作,量给直分,命使者主之”[23](P2996),由诸道盐铁使王涯兼任榷茶使,“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22](P1889)。在如此严苛的榷茶法之下,私人茶园被毁坏或充公,茶农茶户成为专为政府生产茶叶的雇工,一切涉茶经贸都牢牢被抓在官府手中。客观而言,这样的茶法使得茶农苦不堪言,原有茶业经济受到较大冲击,而茶商也“鬻茶之资不能当所榷之多”[20](P6115)。 榷茶法加剧了唐王朝的社会矛盾,茶叶走私和官商冲突也屡禁不绝。为此,唐王朝一方面加大对违犯茶法的刑罚力度,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行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27](P1382);另一方面给官茶批发商颁发“陈首帖子”作为茶叶贸易运输中的通行证,规定各级地方不得巧立名目对官办茶批发商再征税赋,提高茶业官商的积极性,确保朝廷中央能够不断获取榷茶之利。
唐代以降,作为宫廷茶文化的延伸,各类茶税茶法继续深入发展,使得茶业经营与宫廷之内的中央政权进一步关联。比如,宋朝有“三税法”“贴射法”“通商法”,而后又颁发“引票”规定茶商定额特许经营[28](P44-46);元朝则实行“卖引法”,“长引每引计茶120斤,收钞五钱四分二厘八毫;短引计茶120斤,收钞四钱二分八毫”[29](P43-46),而后废长引单剩短引,制定“茶由”等名目官营;明清之际,茶法更为严苛,甚至明太祖朱元璋女婿也因“数遣私人贩茶出境”[30](P107-115)贩卖私茶之罪而被诛杀。总的来说,茶税、榷茶等一系列茶业法度的出现,在本质上是宫廷礼制之茶在法治上的客观手段延伸,是统治阶层为维护政权稳定而开展“塞私充公”的茶政治理,使得茶作为重要的“公利”地位得到巩固确认,也为中华茶文化体系的整体发展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三、宴与文:庙堂江湖的人文化成
在古代国家治理中,统治阶层逐渐形成了德法并举、礼法并用的实践模式,而《唐律疏议》更明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也”[31](《名例》,P3)的治国之道。由于政治对文化的统摄主导,茶文化在历史长河中被注入丰富的政治文化象征与隐喻意涵,以宫廷茶文化为引领,不管是直接彰显宗法礼制的祭茶、贡茶、赐茶,还是以国家社会“公私”之争出现的茶税、榷茶、茶引等宫廷茶文化延伸,都对茶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茶作为饮食之物,真正要融入百姓日用之中成为全民国饮,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强个体体验、形成社会记忆。回顾古代宫廷茶文化的发展,统治阶层开展礼制之茶与法治之茶的融合、推动宫廷高雅之茶成为民间大众之茶的努力,也是在“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实现的,而其中最具代表性便是茶宴和茶诗词在民间的流行和日常化。
所谓“茶宴”也称为茶筵、茶会、茗宴等,陈文华指出,“茶会就是用茶点招待宾客的社交性集会”,“用茶叶和各种原料配合制成的茶菜举行的宴会,就叫做茶宴”[32](P160)。简而言之,茶宴就是用茶来招待客人的社交聚会。据《三国志·吴书》记载,“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33](卷六五《吴书·韦曜传》,P1462),可见在三国时期,茶就已经出现在宫廷宴会的舞台上,但显然当时之茶尚且不是宴会主角。实际上,一直到唐代,茶宴才成为宫廷茶文化的重要茶事活动,李郢《茶山贡焙歌》便是对皇宫之中一年一度清明茶宴的生动描写:“蒸之馥之香胜梅,研膏架动声如雷。茶成拜表贡天子,万人争啖春山摧。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34](P39)如此盛大的清明宴,劳民劳力,给地方和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但在对上流社会生活的推崇追捧之下,宫廷茶宴活动也逐渐被普通百姓所认知和接纳,并为民间效仿迅速流行。比如,据《吴兴记》载,自南北朝起吴兴(今浙江湖州市)、毗陵(今江苏常州市)两郡太守每年在采茶季都会在顾渚山附近举办茶宴,祭祀天地、祈祷地方风调雨顺[1](P15),文人士大夫群体更是常通过举办各类茶宴雅集,舞文弄墨、诗词唱和、高谈阔论。宋代时,茶宴活动更加频繁,宫廷茶宴、寺院茶宴和文人茶宴成为主要的形式,并滋生出许多茶事活动中的茶礼、茶仪。比如,在宫廷茶事中,在酒席前后必有茶宴,或赋诗填词以劝茶,或举行烹茶、分茶、品茶等雅集活动,实际上 “茶宴俨然成了宴饮的标准程序之一”[35](P69)。据宋人王明清《挥麈录》记载,贵为帝王之尊的宋徽宗,甚至亲自在茶宴上为大家点茶,“赐茶全真殿,上亲御击注汤,出乳花盈面”[36](《餘话卷之一》,P216)。统治者的宫廷茶雅好第一时间在文人士大夫群体中引起效仿,并逐渐形成斗茶之风,宋人唐庚《斗茶记》载:“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予为取龙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为上,某次之。”[9](P122)由此可见,从王室祭祀、宫廷贡茶和王公茶宴到文人茶会、百姓斗茶,茶文化实现了从庙堂到江湖的大众化。
除了在日常饮食之中推动宫廷茶文化的大众化之外,以茶赋、茶诗词、茶论为代表的茶文创作也使得文字传播深入到帝国的各个角落。自唐代陆羽创作《茶经》之后,针对茶主题的文字创作日益频繁,或从个体感官赞美茶的滋味口感,或以茶的高洁品性来自况,或以茶交友唱和怡情,使得茶这一自然灵物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比如,唐代王敷《茶酒论》就在为茶辩护时指出“百草之首,万木之花”[37](P267)、“我之茗草,万木之心,或白如玉,或似黄金”[37](P268),对茶的推崇跃然纸上。此外,文人茶诗词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现。以唐代为例,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34](P23)、白居易《山泉煎茶有怀》[34](P23)、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34](P17)以及皮日休《茶中杂咏·煮茶》[34](P44)和陆龟蒙 《奉和袭美茶中十咏》[34](P46)等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据考证,《全唐诗》中茶诗作者总计156人,占全唐诗作者总数的4.8%;茶诗516首约占整个唐诗总数的1%。内容涉及煎茶、饮茶、茶具、采茶、造茶、茶园等各个方面[38]。至宋代,各类茶诗词、茶录、茶论更是层出不穷,如宋庠《自宝应逾岭至潜溪临水煎茶》[34](P72)、文彦博《和公仪湖上烹蒙顶新茶》[34](P88)、 蔡襄 《即惠山煮茶》[34](P93)、黄裳《茶苑》[34](P127)、杨万里《酌惠山泉瀹茶》[34](P203),不光写出了饮茶之个体感受,更涉及种茶、制茶、煮茶各个环节的风雅乐趣。为推动宫廷茶文化的大众化,甚至连宋徽宗都按捺不住,亲自撰写了《大观茶论》[39],参与到这场茶文化大众化运动的盛会之中。总的来说,以文人士大夫精英阶层为主体而创作的茶诗词,无疑对茶文化走进街头巷尾、深入百姓人心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随着茶文化大众化的深入,历代文人还不断交流茶种植、制造、品鉴、饮茶方法等茶事经验和知识。比如,刘贞亮《茶十德》、许次纾《茶疏》、张又新《煎茶水记》、温庭筠《采茶录》、毛文锡《茶谱》、欧阳修《大明水记》、蔡襄《茶录》、沈括《本朝茶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丁谓《北苑茶录》、朱权《茶谱》等[40],将饮茶与君子人格、人生哲学、识人交友、礼仪社交、社会治理等各个方面关联起来。与此同时,民间茶俗、茶礼、茶仪也越来越健全完善,“宾主设礼,非茶不交”[41](卷四《榷茶》)、“至则啜茶,去则啜汤”[42](《茶汤俗》,P2288)已经成为百姓日用的基本礼仪,真正完成了宫廷茶文化的民间大众化,中华茶文化的发展也实现了从“野”到“朝”而又再次反哺于“野”的“大化天下”闭环征程。
四、结语
总而言之,在儒法合流的传统社会治理体系中,宫廷茶被注入了丰富的纲常伦理象征和隐喻意涵,并在礼法融合的现实选择下,成为统治阶层“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有效载体之一。在古代茶文化体系中,凭借政治威权的先天优势,宫廷茶文化的社会行动取向和载体选择成为理所当然的主导因素,直接影响到民间大众茶文化的联动发展。因此,受到礼法融合国家治理观引领的大众茶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作宫廷茶文化的社会化延伸。事实上,不管是与宫廷特权阶层直接关联的贡茶赐茶,还是在国家治理观照中自上而下发起的茶税、榷茶、茶引,以及以文人士大夫群体发起的茶诗词、茶论创作等,都融合了国家治理、礼法教化、社会整合的丰富意涵,推动着茶文化在物质、组织制度、精神生活等不同文化层次上不断变迁发展,为中华茶文化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