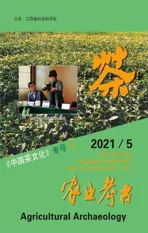清末民初北京茶馆与市民日常生活探析
2021-12-15杨贺
杨 贺
近代北京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演进过程,从封建王朝的帝都到北洋政府的国都,再到国民政府的故都,一系列复杂的角色转变让这座古城饱经风雨,经历了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座中国城市的演变轨迹。而北京的茶馆就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中跌宕起伏,演绎了一部活生生的人间话剧,描绘了一幅鲜活的北京市民日常生活画卷,映射着整个近代北京社会的时代变迁和人文个性。
一、多样的茶馆
旧时北京有句谚语:“早茶晚酒饭后烟。”而且人们见面的问候语也是“喝茶啦?”[1]可见茶在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所谓“北京中等以下的人最喜欢上茶馆”[2](P71),“中国人喜好喝茶、北平人尤甚”[1],“北平人的吃茶是很有名的”[3]等等,相关记述不胜枚举,所以清代以来的北京,茶馆林立,种类繁多,而各种史料所记大都以营业性质与经营范围来作为划分茶馆的标准,经过归类汇总,主要可分为大茶馆、清茶馆、书茶馆、野茶馆等四种。
(一)大茶馆
大茶馆在清代绝对称得上盛极一时,这根源于清王朝对旗人多方面的特殊政策,旗人“生则入档,壮则充兵,巩卫本根,未便离远”[3],他们不能从事商业、农业等其他谋生活动,主要靠清王朝发放的钱粮来维持生活,其政策本意是免除八旗子弟的后顾之忧,使其专心骑射,以保持八旗兵原有的军事素质;但是事与愿违,却逐渐滋生出一大批所谓的“有闲阶级”,也就是闲人,比如老舍先生在茶馆中塑造的“松二爷”和“常四爷”的形象就是典型的闲人:“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绉绉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4](P4-5)这段文字把“闲人”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
同时,清王朝旗、民分治,内城为旗人居住。为防止旗人耽于享乐,所以限制戏园等商业性休闲娱乐场所的建立,而且不允许旗人赴戏园看戏,“凡旗员赴戏园看戏者,照违制律,杖一百”[5](P10)。所以茶馆这种公共休闲空间便成为了两全其美的选择。既不会如戏园般容易使人耽于享乐,又能为旗人提供一个放松身心的场所,所以大茶馆的兴旺是必然的,是整个旗人社会兴旺的伴生体。
大茶馆以“大”为名是有道理的,首先是格局大,“大茶馆局面广阔,门面自三间到五间不等,后面房屋常是六七进,前设柜台和大灶,中为罩棚,后为过厅(俗称‘腰栓’),再后为后堂,两旁侧房的单间,叫做雅座”[6](P13),金受申也对大茶馆的格局有过描述:“大茶馆入门为头柜,管外卖及条桌帐目。过条桌为二柜,管腰栓帐目。最后为后柜,管后堂及雅座帐目,各有地界。后堂有连于腰栓的,如东四北六条天利轩;有中隔一院的,如东四牌楼西天宝轩;有后堂就是后院,只做夏日买卖和雅座生意的,如朝阳门外荣盛轩,各有一种风趣。”[7](P15)可以看到,大茶馆虽然布局各异,但是整体来说,占地面积都是非常大的,难怪时人感叹:“请想是得多大的房子?多大的调费?前前后后共是得多少人?”[2](P72)大茶馆根据设施及所销售食品的不同又可分为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二荤铺四种[7](P16)。
红炉馆,顾名思义,即有“红炉”之馆。“红炉”就是一种制作饽饽的工具,大茶馆里边的红炉要比专门饽饽铺中的小,但是能制作的种类也是比较多的,比如大八件、小八件等。著名的天汇轩大茶馆就属于红炉馆[7](P16);而窝窝馆,同理,以江米艾窝窝得名,《北平风俗类征》中记载的“燕都小食品杂咏·艾窝窝”云:“白粘江米入蒸锅,什锦馅儿粉面搓。浑似汤圆不待煮,清真唤作艾窝窝。”[8](P225)说明艾窝窝本是回族食品,也是旧时北京著名的小吃之一。搬壶馆,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茶馆,“亦焦焖炉烧饼、烧排叉二三种,或代以肉丁馒头”[7](P16)。
有学者认为以上三种实际上是难以区分的[9](P35),但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只卖茶水和京味糕点等特色食品,而不供应饭菜;而第四种大茶馆二荤铺,却具有鲜明的特点,即既卖茶又卖酒饭,所以又叫茶饭馆。这种与饭馆是有区别的:“本来饭馆都预备茶,以备客人饭前之用,恰如瓜子点心之类一样,但不专卖茶。在茶饭馆里,你可以专喝茶不吃饭,这是茶饭馆与一般饭馆不同的地方”[1],“二荤”并非是两种肉食,而是客人自己带的食材是“一荤”,茶馆提供的佐料是“一荤”[7](P16),1929年的《北平指南》有记载:“二荤铺以便饭为主,菜以猪羊肉为多,因单卖清茶,故又名茶馆。饼面饭菜,价格均极公道。菜码更较他处丰富,饼面亦可论斤计算。而尤以肉馒头为最普通之点心,每十枚一碟,仅价一角耳。亦有卖八分五分者,小费亦随意。”[10](P59)结合夏仁虎所说二荤铺为“平民果腹之地”[11](P127),可见这种茶馆颇受下层人士的欢迎。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约1938年前后,“现在硕果仅存的二荤铺,已经改了饭馆,二荤变为一荤,不炒来菜儿了”[7](P16)。
(二)清茶馆
大茶馆没落后,北京出现了很多比较有特色的茶馆,清茶馆就是其中之一。清茶馆一个“清”字指明了这种茶馆只卖茶水,没有其他点心和饭菜。这种茶馆没有大茶馆的规模和气派,但服务却更加灵活,而且价格低廉,功能也相对多样,所以数量迅速增加。《燕市积弊》中即载“清茶馆儿遍街”[2](P72)。面向的顾客群体也比较多样,《民生周刊》载:“所谓清茶馆者,意思是仅供清茶之谓,此类茶馆,专供一般比较斯文者流,猜壁子、吟诗、下棋,以名士自居;其次则为提笼架鸟者,清晨啼鸟后,来此集聚,其鸟叫声优良者,互相携鸟追随。以求托鸟(鸟初学啸,向老鸟学腔之意),每日差钱总有同好代付,茶馆掌柜对于这人也特别殷勤,盖因鸟及人以资号召也。”[12](P15-16)
以上所说的第一类斯文者流是比较常见的,“围棋国手崔云趾君,曾在什刹海二吉子茶馆,象棋国手那健庭君,曾在隆福寺二友轩,全是清茶馆的韵事”[13](P9)。而第二种提笼架鸟者也非常普遍,这些人通常都有早起遛弯的习惯,“遛鸟的人在这里把鸟笼挂到茶馆房屋前,群鸟争唱,人们聊着天、喝着茶、听着鸟叫,眼珠子不动地界儿的盯着鸟笼子。相互品评着、议论着、交流着。会做生意的茶馆掌柜为兜揽生意,就邀请养有好鸟的老主顾前来‘赛会’,挣个脸面荣光,同时以此吸引其他的养同类鸟的人来喝茶。这些‘慕鸣’而来的养鸟人,其本意并不在喝茶,而是来听鸟哨。有的带着自己的鸟,是为了‘串套’——把人家叫得好的地方学过来,押在自己的鸟口上”[14](P48)。除了以上两种人,很多清茶馆也承担着劳动市场和交易中心的角色,一般在上午的人流退去后,中午以后,就会换一类顾客,很多茶馆往往会成为某一行当的聚会场所。“凡找某行手艺人的,便到某行久站的茶馆去找”[13](P9)。还有其他如拉房纤儿的、放高利贷的等,都会把清茶馆当作聚集地。清茶馆中比较有名的是窑台茶馆,天桥的劈柴陈、六合楼、西华轩、同乐轩、合顺轩、爽心园、荣乐园等茶馆[15](P200)。其中窑台茶馆就颇受梨园弟子的喜爱:“每晨富连成班生荟集于此,品茗喊嗓,票友来此亦多。”[16](P19)
“遍街儿”[2](P72)的清茶馆实际就是“大茶馆的”缩小和简化,有学者认为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实际就反映了从大茶馆逐步转化为清茶馆的沦落过程[9](P49)。清茶馆形式简单,一杯清茶即可成馆,所以介入门槛和可塑性就比较强,在招揽顾客的驱动下,自然而然就会加入其他服务项目,也间接促成了书茶馆、棋茶馆等特色茶馆的诞生,这一承“大茶馆”之后,启“书茶馆、棋茶馆等”之前实际也是清末民初北京社会变迁的缩影。
(三)书茶馆
书茶馆,即既卖茶,又可听评书的茶馆。名为茶馆,实际到这里的顾客大部分都是为听评书而来:“去的人专为听说书、这说评书者却变成了主要的营业、而卖茶反是附属的”[1]。书茶馆讲究“开书不卖清茶”,所谓清茶,就是只喝茶,不听书[6](P145)。评书开讲之后是不可以的。开书时间有三个,下午一时至三时,叫“说早儿”,三四时至六七时为“白天”,七八时至十一二时叫“灯晚”,上午一般是不开书的。而“说早儿”一般都是无名角色才肯说,有名的角色都是轮流来说白天和灯晚。
而书茶馆也是分档次的,主要的标准有两个:一是茶馆的规模,二是名角的分量。二者本身也是相辅相成的:“说书先生,必于午后三时以后,始施施然来。与相识者拱手寒暄,喑哑之嗓音,如筛破锣。于时苦朋友已多陆续发去,座上茶客,尝有着獭皮领大氅,戴貂冠之阔家子弟,两大枚一碟之大花生与哈德门香烟之销数,因之激增。……迨暮色苍茫,万家灯火时,客始相继离去,书亦停止,如带灯晚,其开场又恒在下午八九时以后矣!”[12](P15-16)这段话提到过双厚坪,极富盛名,有“评书大王”的美誉,而欣蚨来和广华轩(即广庆轩)也是可以容纳数百人的大型书茶馆。这种书茶馆一般的劳苦大众是听不起的,只能是上文提到的“着獭皮领大氅,戴貂冠之阔家子弟”才能消费得起。这类书茶馆一般以两个月为“一转”,到期换人演出。不过也有例外,比如天桥的福海轩(也名福海居),俗称“王八茶馆”,“不挂常客,所以任何说书的都能由福海轩挣出钱来”[18](P16)。
最初书茶馆只讲评书,后来逐渐增加了大鼓书、相声、二簧清音等多种曲艺形式,尤其是天桥的书茶馆更是如此,兼容并包,种类多样。书茶馆本身也是中国古代小说和传统文化的传播阵地,很多著名的明清小说都是通过说书艺人的生动表演,才广为传播。
(四)野茶馆
野茶馆,闻名知意,就是郊野之茶馆。前清时期北京城内多皇家禁苑,除了陶然亭、窑台之外,是没有游憩地方的[13](P9)。所以很多人要享受自然风光,只能远走城外。野茶馆便在景色优美、风光旖旎、人流相对较多的郊外之地应运而生。野茶馆一般流行于盛夏,“屋外搭天棚,以砖坯砌土台,设备简陋,茶叶则甚讲究,喜喝野茶者多因贪其凉爽,赤臂坐棚下,或聚茶友斗纸牌;日色平西,有烧饼驴肉可充点心,晚风拂暑,循路返家”[12](P15-16)。而有的人又偏爱秋冬到野茶馆,体验另一种风味:“这种野茶馆最好在秋冬去闲坐。秋天里,微风一吹,白杨萧萧作响,振声四野。远远可以看到一叶叶的红叶,松柏依然是碧绿不退,秋虫儿藏在荒草里,悲叹他的暮景……冬天里最好踏雪去闲坐,小茅屋里温暖异常,案上的酒向人喷着香气,有酒癖的,这时不得不来几盅地地道道的烧刀子。”[19](P14)可见野茶馆虽大都简陋,但回归自然的感觉却让人陶醉。
著名的野茶馆有以土炕得名的六铺炕茶馆,以垂柳闻名的绿柳轩茶馆,以百架葡萄闻名的葡萄园茶馆等等。这些茶馆由于大都风景优美,所以往往能吸引较多茶客,而且常常举办各种活动。比如葡萄园茶馆:“葡萄园在东直、朝阳两门中间,西面临河,南面东面临菱角坑的荷塘,北面葡萄百架,老树参天,短篱余绕,是野茶馆中首屈一指所在。夏日有谜社、棋会、诗会、酒会,可称是冠盖如云。”[13](P9)
除了以上几种之外,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茶馆,但或因规模较小,数量不多,如棋茶馆、茶酒馆;或因其临时性,如茶棚;或因是否为纯粹意义之茶馆存在争议,如茶园、茶楼、茶社等。其中所涉如茶园,因于戏园紧密相连,茶社与公园相伴生,都不在此处叙述。而事实上,各种类型的茶馆划分并非绝对,比如:清茶馆也可能会有棋案成为棋茶馆,野茶馆也有评书等曲艺活动成为书茶馆,而冬季很多野茶馆不再营业,又具有了茶棚的临时性。所以这种细分的主要意义不在分类本身,而在于说明一个事实:虽然大茶馆不断走向衰落,但是北京的茶文化并没有就此消亡,而是化整为零,以另一种形式融汇于各色各样的中小茶馆之中,不断传承发展,成为了京味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茶馆与市民日常生活
茶馆名为饮茶之地,但实际上其功能远远超出了饮茶止渴的范畴。不管是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都“辄喜来此,坐半日光阴之消磨”[17]。正如王笛所说,茶馆是一个“自由世界”[20](P62),而对自由的渴望是不分阶级阶层的,不同的人会赋予茶馆不同的内涵,而茶馆也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各种不同的角色。
(一)信息与社交中心
茶馆是天然的信息交流平台,扮演着社区中信息中心的角色。“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像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4](P1)。很多茶馆内都会粘贴 “莫谈国事”的标语,有人认为这既是一种限制,但是也是一种方便:“国事者是也,张三谈它,李四论它,混淆听闻,免不了捉将官里去,便惹得大家麻烦了。”[21](P191)但是往往这种标语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屋子里充满着烟,谈笑声。虽然在贴上用红纸写着‘莫谈国事’的标语,但人们仍然是谈着、讲着。由国家大事,讲到张大嫂怎的,讲到谁谁怎样,简直说无所不谈,无所不讲了。”[22]
茶馆也是交朋好友的好地方,是一个社交中心。有共同爱好的人往往会凑到一起交流心得,如提笼遛鸟者品评下画眉、百灵、黄雀等的鸣腔;爱观棋、下棋的三五成群,摆棋对弈;爱听评书的每天到固定的茶馆听段评书,久而久之就互相熟识,成了书友。如靳麟先生“七七事变”前经常到后门的广庆轩听书,就结识了很多书友[23](P360)。即使是陌生人也照样可以很快成为朋友,胡天海地的闲侃一番:“茶馆里是不寂寞的,陌生人很快地便会成为朋友;即使是从未有过一面之缘的,面对面,茶壶对着茶壶,我替你斟一杯,你替我斟一杯,这样便会交谈起来,谈到生活,谈到社会新闻;有时也骂,这个捐那个捐都在被骂之列……他们的谈话似乎是没有什么隔膜的,天气怎么样,贵姓府上,这些很少管到;彼此都诚朴,都豪迈,什么都可以谈。完了各人都走各人的路,像熟识,而实际却连姓名都没有通。北方人的性情从这里是可以看到的。”[24]
(二)交易与雇佣中心
茶馆不仅是信息传递、交朋待客的场所,同时也是商品交易和劳动力雇佣的媒介和平台:“茶馆常常是街谈巷议的交换之所,但交换的不一定完全是这些新闻,此外还有人谈买卖,和其他的事也常在茶馆交易、接洽、磋商。”[1]比如旧时北京的房地产中介,俗称“拉房纤的”或“纤手”“跑纤的”,他们没有固定的营业场所,每日都会出入大小茶馆之间专门打听是否有人出售、出租或者购买、租赁房屋,然后代为奔走,从中撮合,还有媒人及其他“不生产的寄生生活的事业”也会选择茶馆作为交易场所:“在北平有一些没有固定的职业的人,他们常作买卖或租赁房屋的介绍人、借贷的中人、媒人和其他不生产的寄生生活的事业,希图得到佣钱、回扣或报酬。他们的交换意见的地方就是茶馆,有时将茶馆就当作机关。”[1]除了以上这些“中人”,还有诸如“打鼓儿的”(专门收购旧货物的商贩),大中商号中“跑外的”等都在茶馆进行商品交易。
茶馆同时也是类似“劳动力市场”的雇佣中心,是“劳动届找工作的地方”[25]。旧时北京的木厂子和营造厂,棚铺、杠房还有各种手工作坊,大都不雇佣长期工人[26](P165),他们揽到活儿后,都是临时到茶馆找手艺人来干,同时那些手艺人也相应地会在茶馆等候被雇佣:“等工作的人要占茶馆座客的多数,像抬杠夫、抬轿夫、吹鼓手的、打执的头儿、泥瓦匠、拉排子车的都是,每天清早便到茶馆喝茶,杠房或喜轿铺遇着有买卖了,便到茶馆去找人。”[25]这种由各行手艺人占据的聚集地称为“口儿”或“攒儿”。如上所述,茶馆经常是这类聚集地的首选,“各行各街巷皆有其聚之茶馆,如前门外之万德馆、天汇轩等等皆是”[27](P4-5)。
作为“口子”的茶馆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社区服务中心,为以售卖人力而非货物的中下层民众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公共空间,在这里,雇主、雇工、茶馆老板各取所需,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态系统,各个区域,各个街口一般都会有自己固定的活动范围,轻易不会越界,所以这种生态系统往往非常稳固,轻易不会被打破。
(三)调解中心
茶馆常常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场所,扮演着调解中心的角色。比如老舍先生笔下的《茶馆》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来,往后院去。”[4](P3)之后出场的黄胖子就充当着调停人的角色。因为砂眼看不清楚,一进门就嚷嚷着“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4](P18)这种到茶馆解决纠纷的方式叫做“吃讲茶”或“茶馆讲理”。王笛认为,“吃讲茶”象征着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力量,也是地方精英建立权威的良好机会[20](P345)。而这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国家、社会与市民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茶馆在北京市民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形形色色的人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都把泡茶馆当作每日必做的功课。很多人也因此注意到了茶馆教化的作用,有人认为平民教育要到“茶馆里讲故事”,要“投其所好”,因为商人、店员等职业白天都要做事,到晚上才有闲散时间,所以“茶馆是施行平民教育顶合适的地方:利用别人闲散,教常识或识字,没有比茶馆更好的了。茶馆里不是有弹词说书的人吗?何以大家肯出了钱去听?因为讲的人唱的人能投人所好的”[28](P2)。齐如山也认为去茶馆听书的人要比去戏馆听戏的“多百倍”,“倘国家、地方或社会团体加以注意,详订章程,亦施行社会教育一极好之方法也”[27](P5)。
三、茶馆里的表演与游戏
茶馆除了具有交流信息、社会交往、交易空间等较强实用性的功能外,实际上其最大的作用还是休闲娱乐,是名副其实的社区公共休闲空间。不同的茶馆通常会提供不同的文娱活动,市民既可以观看评书、戏曲等曲艺表演,又可以参与斗蟋蟀、下棋、猜谜等多样的游戏活动。
(一)表演
正如齐如山所说,到茶馆听书的,要比去戏馆看戏的多百倍。所以茶馆中第一表演当属评书[27](P5)。北京是评书的发源地,一些评书名角,大半由北京训练出来的[18](P16)。可谓是“群星璀璨”,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有评书大王双厚坪(擅长多书)、田岚云(说《东汉演义》和《明英烈》)、潘诚立(说《精忠传》《明英烈》《清烈传》)、陈士和(说《聊斋志异》)、张少兰(说《聊斋志异》《精忠传》)、王杰魁(说《包公案》)、品正三(说《隋唐传》)、袁英杰(说《施公案》)、群福庆(说《施公案》《盗马金枪传》)、连阔如(说《东汉演义》)、杨云清(说《水浒传》《济公传》)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绝活,比如双厚坪,正书说的不多,但是在正书之外,能穿插很多逸闻趣事。所谓“插科打诨、信手拈来,亦庄亦谐,极有风趣”[29](P225-229)。
当时有评书表演的茶馆非常多,东西南北城都有。比较著名的有:天桥之福海轩,正阳门外之德泉馆,崇文门外之魁元馆,宣武门外之胜友轩、如云轩,阜成门内之三义轩、西义轩,西直门内之华乐轩,安定门内之朝阳轩,东安门外之东悦轩,地安门外之通河轩,东四牌楼之蓬莱轩,西四牌楼之欣蚨来,北新桥之天泰轩,新街口之兴记书馆[30](P21)。天 桥 上 的 书 茶 馆 尤 其 有 名。张 次 溪 在《人民首都的天桥》曾记载天桥上的书茶馆,写道:“门面并不讲究,就是房檐上挂着几个半尺来长的小牌子,……此外再用窗户板,刷上一张报子,悬在门口上,写某月初几日(旧用农历)特聘张某某李某某准演某书某传。他们所演的书,与我们看的小说虽然名字相同,可是内容就不大一样了。如《水浒传》《施公案》《三国志》等书,他们都有秘本,确与众不同,轻不外传。”[31](P151)
除了评书之外,茶馆中还有大鼓、单弦、莲花落、相声、京剧、昆曲、梆子等多种曲艺形式。大鼓书有多种,如京韵大鼓、唐山大鼓、乐亭大鼓、梅花大鼓、东北大鼓等。说唱最多的还要数京韵大鼓。和说评书有点不同,大鼓演员中多有女角。莲花落这种北京特有的演唱形式也常可在茶馆见到,莲花落高手白玉山,就曾在西安市场欣蚨来茶馆以演连续剧目叫座[32](P239)。而欣蚨来茶馆同时也是一处清唱茶馆,是西城京剧票友日常演出的场所,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京剧票友经常在此清唱:“欣蚨来茶馆的地方不大,设备简单,几张茶桌,几把椅子,没有戏台,更谈不上什么布景。票友们约集三五同好,来此消遣清唱,每天午后游人行经此处,丝竹之声,悠扬悦耳。翁偶虹先生工于花脸戏,当年常是这里的座上客。”[33](P218)
总之,茶馆通过多种多样的经营活动,既满足了各类茶客的个性需求,同时也扩展了经营范围,增加了收入,大大丰富了茶馆的文化内涵。正如习五一所说:“最能体现老北京茶馆文化的地方,一个是书茶馆,一个是戏茶馆”[32](P239)。
(二)游戏
茶馆中除了观看表演外,还有很多可以亲身参与其中的游戏项目。下棋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项。茶馆中每每有摆棋的,或象棋或围棋,两个人对局一声不响,只听见棋子声,四面围观的人也不说话,下象棋的最多,最普通,因为会的人多,棋子方便,时间又不太久。下围棋的则较少,而且较大的、整洁清净的茶馆才有,所以要想学习围棋必须下茶馆,茶馆自然“造就出不少围棋的人才”:“凡是能手想同人较量,以增益本领,定自己的高下的,没有不下茶馆的,有好多大茶馆以摆棋著名,像海丰轩至今还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旅居日本的中国少年围棋国手吴清源,也在这里摆过棋。”[25]
虫鸟也是茶馆最常见的游戏项目。“溯自满清入关而后,王公贵族,八旗子弟,坐享厚禄与饷银,无所事事,多流连于禽鸟之玩好。或调鹰于臂,或饲鸟于笼,相习成风”[34](P162)。清末北京志也记载:“北京人颇好养鸟养虫,养鸟有笼内养及架上养两种。每日清晨,许多人手提鸟笼漫步街头,或手举鸟架逍遥自得。笼内养鸟多为欣赏鸟鸣,架上养鸟多为观赏其艺。例如,红靛咳儿、蓝靛咳儿、白翎等鸟,专以其鸣声供人欣赏,而老西儿、燕雀却以其艺供人观赏。”[35](P535)很多茶馆针对顾客的爱好会举办一些以鸟为主题的活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串套”:“清茶馆主人为了招徕主顾,扩大营业,在春夏秋三季还举行‘串套’活动(即听鸟鸣)。对养有好鸟的知名老人发出请帖,请他于某月某日携鸟光临。请帖很讲究,花笺红封,浓墨端字。同时还在街头巷尾,张贴黄条。届时养鸟的老少人士都慕‘鸣’而来,门庭若市。这样,茶馆不但生意兴隆,利市百倍,而且因此名噪九城。如崇外大街路西万乐园,曾多次举行这种活动。”[6](P15)
猜谜也是茶馆中常见的娱乐方式。在什刹海有一个叫“二吉子”的茶馆,晚间经常有灯谜爱好者在这里“挂壁子(把灯谜条子挂在墙灯上)”[36](P294),署名仇曾升的作者曾经撰文回忆父亲经常到二吉子茶馆①中以谜会友:“北平猜谜很讲究,晚上把谜条顺序贴在灯上,叫打灯虎、猜灯谜。白天把谜条放在‘壁子’里,挂在墙上,故又叫壁虎。‘壁子’打开像个折子,谜条夹在每格间,每格可重叠放十几条,一个壁子有十几格。他(作者父亲)每上茶馆至少带两个壁子。”[37](P336)
茶馆也会不定期举办灯谜会,当时北京著名的谜社射虎社、隐秀社、咏霓社等经常到茶馆中设谜悬挂。谜家大多富有学识,比如20世纪30年代最有名的射虎社就是在京的文人隐士、遗老遗少及旅居京都的知识分子组成[38](P180),制谜也大都出自典籍,谜面用词高雅,或猜古籍名、词牌名、京剧名,或猜古今人名、食品、用具、中草药等,猜中后常令人感叹制谜之巧妙有趣,也是当时茶馆的一大乐事[39](P149)。
四、“新”与“旧”的熔融与冲突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转型最激烈的阶段之一,传统与现代的交织缠绕是其中永恒不变的主题。而当这一主题落到古城北京,其表现出的景象往往变得复杂。首先在北京这座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力量异乎寻常的强大,800余年的帝都史带来了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赋予了北京沉重的传统的力量,所以在由帝都向现代化城市的转型过程中,本应摧枯拉朽的新的力量往往表现的不是那么强大,“任你有跳舞场,她仍保存茶馆;任你有球场,她仍保存鸟市;任你有百货公司,她仍保存庙会”[40](P20)。新与旧会发生的冲突很多时候也并不适用于北京,戏院中可以同时上演戏曲、话剧和电影而并不会出现什么问题。这一切无不体现出独具“北京特色”的现代化城市转型,而茶馆作为传统休闲空间的典型代表,其自身也演绎着一系列熔融与冲突。
(一)熔融
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茶馆并没有像辫子、跪拜礼等迅速走向消亡,而是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或融入、或被融入到现代化的洪流之中。
一方面,社会精英利用茶馆集聚人气的特点,使之成为社会教化和改良的场所,传统的茶馆中被注入了很多现代化元素。比如在茶馆中开设讲报处,先是一名叫卜广海的医生开设了“第一讲报处”:“有卜广海者,在东四牌楼六条胡同口外会友堂药铺行医多年,间壁置有棚屋一处,向赁为茶馆说书之用,兹因街上贴有京话日报,顿发感情,谓说书不如说报之有益,遂将此茶馆改为讲报处。”[41]之后有人效仿又开设了“第二讲报处”:“现有李星五、陈乐园二君,在东直门外关厢地方借用申家茶馆,照东四牌楼会友堂办法开设第二讲报处,每日从一点钟起五点钟止讲说京话日报,从此愚民之被其开通者当又不少矣。”[42]
另一方面,在公园等现代化休闲空间中,茶馆以崭新的姿态“茶座”获得了新生,很多茶座成为士绅、政要、知识分子等名流荟萃之所。中山公园和北京公园的茶座当时就非常有名,比如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是很多文化名人的常客。著名文学家萧乾每次回北京,都会到来今雨轩举行茶会,“一九三五年七月,我去天津《大公报》编刊物了。每月我都到北平来,在来今雨轩举行个二三十人的茶会,一半为了组稿,一半也为了听取《文艺副刊》支持者们的意见”[43](P279)。著名才女林徽因也是每会必到,每次都会发表自己独特而犀利的见解。而这一时期也成为林徽因女士文学创作的巅峰期,被人称作“来今雨轩时期”[44](P201)。来今雨轩还经常举办各种聚会:“京师各界,召集会议,率多赴中央公园来今雨轩,轩以是而名。”[45]可见,茶馆在时代变迁下并没有被淘汰,而是吐故纳新,获得全新的发展。
(二)冲突
并非所有的茶馆都能“熔融”于新事物之中,茶馆中大茶馆的没落,清茶馆、书茶馆等特色茶馆的崛起,就是新旧冲突的一个具体表现。大茶馆是旗人社会繁盛的产物,也必然会伴随着旗人社会的解体而消亡。老舍《茶馆》中描写的裕泰大茶馆就是最好的缩影。从庚子前的高朋满座,到庚子后逐步萧条,继而到军阀割据时期的“硕果仅存”,而且为了避免淘汰,“它已改变了样子与作风。现在,它的前部仍然卖茶,后部却改成了公寓”[6](P31)。实际上除了旗人群体经济状况的每日愈下,也还有业内竞争的加剧,饭馆、清茶馆“遍街”[2](P72),尤其是清茶馆的急剧扩张,使时人没必要舍近求远,专去大茶馆消费。当然,大茶馆虽然被历史无情地淘汰,但是其代表的北京品茶文化却没有消失,在庚子之后众多其他类型茶馆中传承下来。
茶馆中信息传播速度极快,这样的特点也引起了地方政府的重视,政治权利与民间话语的冲突无法避免。很多茶馆都会悬挂“莫谈国事”的标语,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故我常看见茶馆酒肆里头,墻上总是有四个字,写着莫谈国事,不知道这个规矩创于何年,这岂不是拿国家当了一个私物,不准别人干预么?你们想世上的事,若要不是偏私邪僻的,那有怕人说的呢,拿着堂堂正大的一个国家,岂有不准人说话的理么?”[46]茶馆中同样充满了很多带有封建色彩的不良社会现象,比如贩卖人口、赌博等。这些必然与政府机构以及社会舆论发生剧烈的冲突,有一些“士大夫之流”表示永不进茶馆,他们认为茶馆是下流社会人们的场所了[1]。有人还评价茶馆中所讲评书得内容稍显陈旧,“至于新小说作为说本的还没有过,于此可以看出这些人的思想观念还未变更;而小说的形式,新的没有旧的能深入民众中”[1]。为此,社会精英们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如“拟先召集平市各艺人、给奖举行技艺竞赛,以选拔一部分技术较高人才”,想通过改编旧有评书唱本、训练说书艺人的方式来达到“普遍提高民众知识,增进民众之社会生活力量”的目的[47]。
五、结语
北京的茶馆是一个微缩世界,茶馆的变迁体现着时代的更迭。清末民初,北京茶馆种类繁多且各具特色。除了最基本的饮茶止渴外,通常还兼有信息与社交中心、交易空间与雇佣中心、调解中心等多种职能,是社区市民的活动中心。而为了招揽顾客,还提供多种多样的曲艺表演和各种赛会等。在历史变革的大背景下,北京茶馆也无法幸免。面对猛烈的“欧风美雨”,其自身演绎了一系列熔融与冲突的历史图景,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兴衰浮沉。
在历史的长河中,北京茶馆一度消亡,但是其自身蕴含的文化因子却成为了“京味”文化的一部分而保存了下来。林语堂说:“朝代兴替,江山易主, 可北京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如故。”[48](P3-4)这种“生活”是抽象的,是“难以用语言去表达”,是“许多世纪以来形成的不可名状的魅力”[48](P12)。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老北京”文化或者“京味”文化,而其中作为“老北京”文化因子的一部分——茶馆,是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追寻的。
注释:
①原文作者并未直接提及此茶馆为二吉子茶馆,但该茶馆位于什刹海东边烟袋胡同,而且“从早到晚备有‘手谈’和‘笔谈’之地”。这与二吉子茶馆的基本信息是一致的,所以可以判断此茶馆就是二吉子茶馆。参见仇曾升所作《晚年忆童趣》(北京燕山出版社编《旧京人物与风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