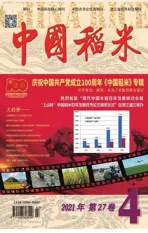稻米: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
2021-12-07曾雄生
曾雄生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100190;作者:zeng@ihns.ac.cn)
1 稻米与国计民生
1910 年(清宣统二年)4 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日子,湖南长沙城中以卖水为生的贫民黄贵荪一家四口因为无法买到米而跳井自杀,激起民愤,引发了抢米风潮。参与抢米的人数超过两万人,并波及周边多个城市。湖南巡抚岑春蓂对长沙人民严厉镇压,导致事态进一步恶化。1911 年,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了满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大清帝国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与长沙抢米风潮没有直接联系,但其根源就出在米上。
一万年以前,生活在中国长江中下游的远古先民将采集到的普通野生稻试着加以人工种植,于是一场革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相较于畜牧业和其他旱粮作物,水稻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但稻米的高产和其所含的特殊营养物质如精氨酸等,也能够繁殖和养活更多的人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也是水稻生产最多的地方。公元一千年前后的宋朝,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亿人大关,其中半数以上的人口靠大米来养活。而据明末宋应星的估计,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0%。今天,世界上近一半人口以稻米为主食。现今,在亚洲,就有20 亿人从大米及大米产品中摄取60%~70%的热量和20%的蛋白质。中国、印度总人口中约有65%是以稻米为主食。
稻米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首先应归功于其优良的生物学特性。水稻是一种稳产高产作物。晋傅玄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1]”。水稻稳产高产的特性,使得天然适宜其生长的中国东南地区成为国家的粮食供应基地,维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自隋朝(581—618)连接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开通以后,南方生产的稻米就源源不断输往北方。唐贞元八年,权德舆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2]”。稻米构成了国家财赋的基础,唐朝时国家十分之九的财政收入来自产稻的江淮地区,江淮地区因而为“国命”所系[3]。唐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得不到给养的禁军士兵酝酿哗变,朝野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历时4 年的李希烈之乱被平定后,江南漕米及时运到陕州,保障了皇室和卫士的粮食供应,一触即发的禁军哗变事件得以缓解。唐德宗高兴的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4]”。
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在不断扩大水稻领地。唐、宋、明、清时期(618—1911),有识之士,如宋初何承矩,元代虞集,明代徐贞明、汪应蛟、徐光启,清代蓝理、朱轼、林则徐、李鸿章、周盛传等,均建议在北方具备条件的地方种植水稻,以减少对南方稻米的过度依赖,有的还采取了相应的行动。清雍正年间,京东地区就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治水营田种稻运动。历史上,山西晋祠、北京京西、天津小站都曾是北方地区重要的水稻产地。经过数千年的努力,水稻突破其自然界限,越过淮河,跨过黄河,到达长城以北。但100 年以前,中国北方的稻米产量仍有限。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稻米的主产区。宋、明时期先后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显示这一地区所产稻米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对稻米的依赖愈大,因稻米产生的问题也愈大,由于稻米缺乏而引起的饥荒一直严重困扰着中国人民,不仅威胁着百姓的肚子,更动摇着统治者的位子。
如何解决稻米缺乏引起的吃饭问题,牵动着历朝历代统治者和普通大众的心,都在为提高水稻产量做着自己的努力。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宋真宗赵恒以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莳之。同时将种植方法张榜告示民众。与中国内地原有的水稻品种相比,占城稻穗较长、无芒、粒型偏小,其最大的优势在于“不择地而生”[5]。宋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南方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占城稻这一特性适应了“旱改水”及梯田开发的种植需要。它的引进推广使得长江中下游地区在原有一季晚稻的基础上,增加了一季早籼,为明清时期南方双季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清康熙皇帝则希望通过采用南方水稻生产技术和选育新品种来提高水稻的产量。康熙三十二年(1693)六月二十八,他在南巡途中,了解到福建一些地方用猪毛、鸡毛作为冷水田的肥料,施用后的水稻能获得丰产,并提早成熟,便将这种方法用于京西玉泉山稻田的水稻种植上,水稻果然早熟并丰收[7]。康熙皇帝还留心于水稻品种的选育,并且成功育出品种“御稻米”。这个品种农历六月便熟,米色微红而粒长,气香而味腴。以其生自苑田,故名“御稻米”[8]。御稻米育成之后,康熙帝本着“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的宏愿,积极致力于该品种的试种和推广。他首先在热河行宫避暑山庄试种成功,结束了长城以北不种水稻的历史。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就康熙对御稻米的培育和推广给予了高度评价,“由于这是能够在长城以北生长的唯一品种,因此成为有价值的了[9]”。康熙更希望将御稻米推广到南方,以促进南方双季稻的发展,并亲自指导了李煦等人在苏州等地试种。
帝王之外,普通百姓也在想方设法提高水稻产量。南宋理学家陆九渊一家试图通过“深耕易耨”的整地方式来提高水稻的抗旱能力和产量。他介绍经验说:“吾家治田,每用长大镢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以他处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已。以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余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10]。至陆九渊生活的南宋时代,中国传统稻作技术在历经数千年的改进之后已趋于成熟,其特征是在耕、耙、耖等深耕易耨的整地基础上,通过育秧移栽和耘田烤田等技术,极大限度提高水稻单位面积产量。与此同时,人们还通过选用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水稻品种,扩大水稻种植面积,促进稻作边缘地带的开发,致力提高水稻总产量。于是就有适宜在高仰之地种植耐旱的占城稻,有适宜湖田、低地种植的耐涝的黄穋稻,还有适宜滨海和内陆盐碱地种植的咸水允稻等。
稻作技术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随着水稻产量的提高,中国人口在宋代首次突破1 亿大关,至清康乾时期已2 亿,到清道光年间更是达到了4 亿。这虽然不全是稻米的功劳,明代中后期从美洲新大陆传入的玉米、番薯、马铃薯等也功不可没,但可以肯定的是水稻的贡献最大。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长,新的问题又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现,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生活资源增长的速度,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源只能按算术级数增长。这个问题早在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唐朝便已出现。当时的诗人就发现,“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但饿死人的事不仅仅是因为粮食生产的不足,更是因为财富分配的不公。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旧中国,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仅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20%~30%,而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可耕地面积的70%~80%。他们利用所占有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导致贫富严重分化和社会对立。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天下为公”的口号,把解决吃饭问题的办法放在生产稻米的土地上,提出“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以实现“民生之义”。
2 “吃饭问题最大”
在湖南长沙因为粮价上涨引发抢米风潮的那年,毛泽东17 岁,他从粮商那里听到了这件事。穷人没有饭吃,自然要求富裕的人接济,甚至发生了“吃大户”的运动。他从事米粮生意的父亲也有一船米被穷人劫去。毛泽东直接感受到“粮荒”。1919 年7 月14 日,毛泽东发出这样的呼声:“我们关在洞庭湖大门里的青年,实在是饿极了!我们的肚子固然是饿,我们的脑筋尤饿!替我们办理食物的厨师们,太没本钱。我们无法!我们惟有起而自办!这是我们饿极了的哀声!千万不要看错![11]”。意思是如果社会不能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只好自己起来解决。此前两年的1917 年7 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文章,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2]。”
解决吃饭问题一直是毛泽东参加革命的动力及领导革命的主轴。1927 年,毛泽东等革命领袖选择秋收时节发动起义,就是看到了粮食的重要性。次年的砻市会师,也极富深意。砻,就是一种加工稻谷的工具,稻谷过砻脱壳之后就成了稻米。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武装斗争的第一个根据地。1941 年和1942 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把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1959 年4 月29 日,他在《党内通信》中都还写道:“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13]。”
毛泽东也试图从土地上去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根据地建立之后,随即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把从地主处没收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新中国成立之时,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已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之后在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等新近解放的地区继续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些地区所涉农业人口数和土地面积占到了全国总数的2/3 以上。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得到的土地占总耕地面积的95%,基本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随后又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由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实现了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制,以体现公有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然而经过30 多年的摸索,发现人民公社体制也存在“吃大锅饭”等问题,一定程度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自1978 年开始,在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2016 年,党中央又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实行“三权分立”,以优化土地资源配制,实现土地最大价值。
但近百年来的地权改革只是手段和步骤,真正的目标是让土地长出尽可能多的粮食来,才能最终解决不断增长人口的吃饭问题。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在提倡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提出了“精耕细作”的号召[14]。之后,“精耕细作”也就成了毛泽东认定的解决中国吃饭问题的法宝。1957 年10 月9 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提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同一讲话中两次提到“精耕细作”,可见对精耕细作的重视。紧接着在1958 年,毛泽东提出农业八项增产技术措施,将精耕细作的内容具体化为: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规划)、肥(合理施肥)、水(兴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种(培育和推广良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防治病虫害)、管(田间管理)、工(工具改革)八个方面,即农业“八字宪法”。
从上世纪50 年代开始,我国为了提高粮食产量,采取了许多办法,其中也包括传统的农具改进、技术创新和品种改良。如“大跃进”期间推广的由水稻丰产专家陈永康总结的水稻“三黑三黄”看苗诊断技术,其实就是对明清以来在江南稻区广泛使用的看苗追肥经验的一次总结。清代在今江苏南通地区使用的插秧辅助工具“莳梧”即为当代水稻插秧机的前身[15]。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影响不止体现在一些具体的技术上,而是渗透于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16]。
3 稻作科技的进步
然而,当我们将最近100 年跟1 000 年,甚至10 000 年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稻米所养活的人口,还是水稻产量都有了显著进步。以养活的人口来看,1921 年,中国人口总数约 44 338 万人,而 2021 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已超过140 000 万人,增长了近10 亿人口,稻米是作了重要贡献的。从稻米的产量来看,1961—2019 年,世界稻米产量从21 564.66 万t 增长到75 547.38 万t,增长了2.50 倍,年均增长率为2.19%;水稻占世界谷物产量的比重也有所上升,从1961 年的24.59%上升到2019 年的25.36%。同一时期,中国大陆稻谷产量从5 364.00 万t 增长到20 961.40 万t,增长了2.91 倍,年均增长率为2.38%,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水稻在世界水稻中所占比重从1961 年的24.87%上升到2019 年的27.75%;最显著的还要数单产的提高,中国大陆单季水稻产量从1961 年的2.04 t/hm2提高到 2020 年的 7.04 t/hm2。
水稻产量的提高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2008 年由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过去几十年的世界农业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市场改革和对农业投入的增加;特别是在中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科技进步在提高农业生产力、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便宜食物和减少贫困人口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业科技已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科技进步更是中国农业生产力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或者说是第一推动力[17]。
近一百年来,中国稻作生产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积极依靠科学技术,促进粮食增产和农业发展。其中,最为耀眼的就是水稻育种的成就。1893 年日本最早开展了现代水稻品种选育工作。中国则始于1906 年,然而直到1919 年中国才开始用严格的育种方法进行系统的、比较有针对性的育种,至1949 年30 年间育成水稻品种约100 个。1949 年以后,中国的水稻品种选育开始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相继出现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出现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至70 年代初,以选育矮秆高产品种为主,并于60 年代后期基本普及了矮秆良种。第二次突破是从20 世纪70 年代初至80年代初,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的“三系配套”和推广。由于杂交稻强优势组合的育成和种子生产体系的建立,使水稻的杂种优势在世界上首次得到应用。矮秆水稻和杂交水稻生产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使中国的绿色革命处于世界先进水平。1987 年,我国科研人员又成功地将光敏核不育特性转移到其他水稻品种中,实现了“两系”杂交育种,培育出了更加高产优质的水稻品种。20世纪80 年代末至90 年代,中国科学家在建立了“三系”“两系”杂交水稻理论与技术基础上,又提出了“以单蘖生物产量优势为基础,茎蘖顶端优势、粒间顶端优势和根系顶端优势为中心”的超高产水稻生理模式和“后期功能型”超级稻新理论,超级稻育种研究保持世界领先。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科学家独立完成的水稻(籼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序列图更是被国际著名的Science 杂志评价为“具有最重要意义的里程碑性工作”,对“新世纪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永远改变了我们对植物学的研究”,是“中国对科学与人类的里程碑性的贡献”。除此之外,水稻分子生物学更是突飞猛进。在水稻组学、逆境生物学、功能基因的克隆和调控网络的解析方面已经引领世界水稻乃至作物科学研究,获得了一系列原始创新成果和新突破,如水稻广谱抗病遗传基础及机制、杂种优势的分子遗传机制、水稻感知和耐受冷害热害机制、调控植物生长代谢平衡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分子机理、自私基因维持植物基因组稳定性的分子机制和大规模种质资源的全基因组变异的解析等[18]。科技进步为“藏粮于技”提供了坚实基础。未来人们可以更加随心的根据人们需求设计和改造水稻,稻米也会因而受到更多人的喜爱。
4 稻米的未来
过去的100 年,特别是最近50 年,中国的水稻生产和科技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国用不到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超过世界20%的人口。但粮食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水稻生产和科技依然任重道远。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非农就业人口越来越多,也必将对稻米消费和生产产生重要影响。2018 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9.58%,2020 年,居住城镇人口比率达到63.89%。城镇人口的增加导致纯稻米消费者的数量在增加,对稻米产量和品质会提出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特别是城市及其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占用大量耕地,使原本紧张的耕地资源愈加显得不足,这势必威胁到粮食安全。城市化必将对稻米生产和需求产生冲击。首先是从事水稻生产的劳动力减少,这就意味着要提高水稻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在消费方面,城镇人口对稻米原粮的需求减少,导致稻米价格持续走低,影响农民种稻的积极性。城市化的发展给水稻生产提出许多挑战,但也给水稻生产和科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城市人口在对稻米原粮需求减少的同时,对稻米的种类和品质要求提高,加工专用稻以及高抗性淀粉、低谷蛋白等功能稻米和品质较好的粳米消费将增加。2000—2015 年,中国粳稻人均年占有量从37.0 kg 上升到52.8 kg,提高了15.8 kg。过去水稻育种三次重大突破和水稻栽培制度大的改革,几乎都是以提高产量为主攻目标,而今后水稻育种和栽培的目标将更加注重品质。同时,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环境友好型水稻生产将受到追捧。
如何在进行城市建设的同时,保证农业生产用地,促进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的发展呢?从农业历史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要占用耕地,但也可以促进农业发展和农业技术进步。城市人口的多样化需求,加上城市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实力,使得城市成为农作物种类和品种最丰富、农业人才最集中、农业技术最先进的地方,一些先进农业技术也最先在城市里得到发明和运用。甚至源于西方的近代农学在中国也首先是在城市发展起来。曾经在稻作农业中广泛使用的“区田法”“代田法”最初都是在宫中或是宫殿外的空地上得到试用,而灌溉稻田使用的翻车最初就是用于城市道路的洒水车。20 世纪60 年代广泛推广的水稻塑料薄膜育秧,其使用的温室栽培在2 000年前的秦汉时期就有采用。城市还是水稻品种研发和推广中心。宋真宗引种的占城稻,先是从福建引到开封,经过在皇宫附近的稻田试种之后,再下发给江、淮、两浙三路进行推广。御稻米则是由康熙皇帝本人在中南海丰泽园的稻田中发现,经过单株选育法培育成功,再向全国推广的一个水稻品种。
未来的水稻生产与稻作科技除了受到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亦将受到全球化的挑战。今天所看到的水稻其实就是成千上万年以来全球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稻米丰富了不同地区人类食物的种类,也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起源于中国的水稻经由海路和陆路传入日本之后,促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形成。日本人通过使用水稻作为自己的隐喻来反复地重构自我。犹如‘韩国稻草屋顶’所象征的那样,水稻也是韩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发明和使用的牛耕方式,在大约2 000 年前的东汉时期便传到了现在越南等地。用于稻田耕作的江东犁,自唐朝在江南地区出现之后,也在中国其他地区及东南亚得到广泛使用。17 世纪时荷兰人在印度尼西亚爪哇等处看到当地中国移民使用这种犁,很快将其引入荷兰,后对欧洲近代犁的改进产生了重要影响。用于稻田灌溉的水车,在唐朝的时候已传到了日本,用于稻田灌溉。12—13 世纪日本从中国引进水稻品种大唐米,在日本围海造田中大显身手,成为低温地种植不可缺少的品种。见于宋代的“蒸谷米”这种稻米贮藏加工方式,在今天的印度和孟加拉国仍很普遍。水稻的历史还和近代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兴起纠缠在一起。在过去的4 个世纪,水稻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它的领地,为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和东南亚的采矿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为资本主义殖民地的开拓和获得独立后的新兴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粮食支柱。20 世纪60 年代,位于菲律宾的国际水稻研究所的水稻育种专家,利用中国台湾的水稻种质资源培育出“奇迹稻”(Miracle Rice),为东南亚国家的粮食增产立下了汗马功劳。20 世纪70 年代后,中国杂交水稻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研究推广,解决了世界数千万人的吃饭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也享受到了水稻全球化所带来的成果。中国历史上曾从泰国、越南、朝鲜等国大量进口大米,以弥补自身产量的不足。宋真宗时期引种的占城稻,原产于越南,因其早熟、耐旱、不择地而生,尤其是适合于高仰之地种植等特点,促进了梯田的开发、粮食产量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中国还曾从朝鲜引进过一个名为黄粒稻的品种。中国近代种植的许多优良水稻品种很多来自于日本和朝鲜。1926 年引入的日本品种陆羽132、1932 年引入的青森5 号,及1938 年由朝鲜引进的安东陆稻等,都曾在我国东北地区水稻生产上直接利用[19]。陆羽132,别名陆羽,是日本农林省农事试验场陆羽支场用陆羽20(母本)和龟之尾(父本)杂交育成,引入中国东北后,经熊岳试验站确定为优良品种,在辽宁省南部地区逐渐推广,成为当时该地区推广的最好品种,之后一段时间成为天津及周边地区种植的主要品种,也在北京地区推广种植(故又名北京粳、北京晚稻);解放后,陆羽稻在河北平山、山西太原、陕西汉中、江西余江、海南琼山及上海奉贤、南汇、川沙等地都有种植。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天津,日本人从日本、朝鲜带来银坊、水源52、水源85、陆羽132、金刚等品种在此种植,这些品种一直沿用到20 世纪50 年代[20]。1955—1959 年,从日本引进水稻品种401 个,其中1957 年原农垦部引进58 个粳稻品种。1963 年,中国农业科学院从日本引进水稻品种184 个[21]。1957 年,从日本引进的世界稻(经过鉴定,定名为“农垦58”),推广后种植面积迅速增加,对促进长江流域双季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稻米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虽然有观点认为,稻田排放的气体是全球变暖因子之一。但更多的人相信,作为人工湿地的稻田对维持生态平衡还是有着积极作用。水稻生产具备粮食安全、生态保育、心灵建设、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连接着人类的未来。2004 年,联合国首次设立“国际稻米年”,主题为“稻米就是生命”。为一种作物做出这样的安排,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尚属首次。此前的2002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全球环境基金(GEF)支持下,联合有关国际组织和国家,于2002年发起了被视为关乎未来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的大型项目。到目前为止,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总数达到了60 多个,其中稻作农业文化系统最多。
随着中国人口的城镇化、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未来中国的水稻生产必将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但我们也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这就是“手中有粮心不慌”。作为一个拥有14 亿人口的大国,不可能依靠国外的供应来解决自身的粮食安全问题,中国人自己的饭碗还必须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科技为农业生产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必须依靠科技提高稻米的产量和质量,以满足亿万人口对口粮的需求。可以预见,未来100年,1 000 年,甚至10 000 年,世界上半数以上的人口还必须依靠稻米作为主食,作为水稻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的稻作农人和科技工作者也必将担负起更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