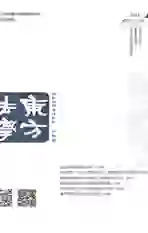论民法典中区块链虚拟代币交易的性质
2021-08-09于程远
于程远
内容摘要: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观察,虚拟代币可分为货币代币、使用代币、投资代币三种基础类型,其法律性质各不相同。货币代币既非物权,又非债权,是一种无实体、非货币的新型财产;使用代币的发行人承诺使用代币的购买人以特定的代币数量购买相应的产品、服务,从而建立起发行人与代币购买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投资代币指向未来的支付、共同管理权或共同表决权,应当受证券法以及相关商事法律的规制。区块链技术的应用本身并不改变虚拟代币的法律性质,虚拟代币交易中,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智能合约只是一种新兴的合同形式,但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起到代替传统民法上公示的作用。
关键词:虚拟代币 数字货币 区块链 比特币 智能合约 代币融资行为
中图分类号:DF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039-(2021)04-0139-151
一、问题的提出
自从2008年中本聪将区块链技术以及基于该技术产生的比特币带入公众视野,全球投资者对于“数字加密货币”这一新兴投资产品的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分布式记账”“不可篡改”的特性 〔1 〕迅速在金融市场上获得投资者的信赖,而比特币总数2100万枚的限制更是加剧了此种投资产品的稀缺性,首次代币发行(ICO,Initial Coin Offering)也就此成为金融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新宠 〔2 〕。一时之间,各类代币融资项目蜂拥而至,为市场监管带来重大难题。而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的特性,更是带来数字加密货币挑战法定货币地位,甚至动摇整个社会经济秩序的担忧 〔3 〕。
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工商总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发布《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称“公告”),将代币融资行为定义为非法行为:“融资主体通过代币的违规发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非法公开融资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这一文件尤其明确地否定了虚拟代币的货币属性:“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4 〕至此,代币发行融资在全国范围内被叫停。
然而,关于虚拟代币交易效力的争议却并未因公告的颁布而止息,尤其在传统民法领域,人们由此得到的问题甚至多于答案:从理论上看,这一公告从金融监管层面对代币融资行为的否定究竟在民法上产生怎样的意义,特别是对于个别的私人交易的效力会产生何种影响,并未明确;在实践当中,大量与虚拟代币相关的“委托投资”“委托交易”纠纷进入民事诉讼领域,给民事审判工作带来分歧与疑难;而与虚拟代币相关的研究一直聚焦虚拟代币发行的监管领域,对虚拟代币交易的民法规制则鲜有关注 〔5 〕。
反观比较法上,对虚拟代币交易的理论与立法探索虽然同样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但总体呈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势 〔6 〕。例如美国 〔7 〕、德国 〔8 〕、法国 〔9 〕、意大利 〔10 〕、奥地利 〔11 〕等国均从政策上对虚拟货币这一新兴事物作出积极应对。2019年,列支敦士登率先针对虚拟代币交易推出代币与可信技术服务商法(TVTG),以单行法的方式为虚拟代币交易的民法规制提供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为全球的虚拟代币立法作出表率 〔12 〕。《代币与可信技术服务商法》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用专门的章节处理了虚拟代币交易的民法规制问题。该法在一般规定部分便开宗明义地指出:“本法旨在为建立在可信技术基础之上的交易系统确立法律规制框架,尤其规制:(a)虚拟代币、通过虚拟代币表达权利以及虚拟代币转让的民法依据。(b)对可信技术服务商的监管以及可信技术服务商的权利与义务。”其立法目的在于:“(a)保护特别是金融以及商业部门电子法律交往中的信赖,保护可信技术系统的使用者;(b)为可信技术服务系统的应用创设积极的、创新友好、技术中立的框架条件。” 〔13 〕
笔者无意讨论虚拟代币的市场监管问题,而是试图从民法的角度入手,分析虚拟代币交易背后的民法意义。正如德国学者温德霍斯特所言,当面对区块链、虛拟货币这样的新兴问题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应当强调,至少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技术应当遵从法律,而非反之” 。〔14 〕尽管虚拟代币依托于区块链技术以“全新”的面貌出现,给传统民法、乃至整个法秩序带来了新挑战,但附着其上的法律问题却未必全新。虚拟货币交易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在传统法律制度之外“重开天地”,而是如何在既有法律制度的领域内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虚拟代币的基础类别
虚拟货币这一概念近年来的再度火爆,得益于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但虚拟代币本身并非一个全新的概念,在这一概念的笼罩之下,相应的交易模式在实践中呈现出的具体形态各不相同。如果单纯地以“虚拟代币”或“虚拟货币”概念本身为基准划定交易合法或违法的界限,则难免会使在理论上本不同质的问题交错混杂,从而造成与之相关的讨论陷入混乱之中。因此有必要对虚拟代币这一概念进行细致观察,以甄别其中可能包含的异质法律问题。
在德国法上,虚拟代币的分类方法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将虚拟代币分为货币代币、使用代币与投资代币三种基础类型,在此三种基础类型之上,还存在各种混合类型以及进一步的分类方法。〔15 〕例如莫伦坎普就将虚拟代币分为本征代币与外围代币两类 〔16 〕。所谓本征代币,指自身具备价值,即仅因其自身存在即可将一定价值归属其上的代币,货币代币即为其典型。所谓外围代币,即代币价值并非源于其自身,而是需要借助与其他商品或服务、或其他本征代币绑定而确定其价值的代币。从这一意义上看,外围代币实质上是某种真实的价值客体的数据化表现。〔17 〕
(一)货币代币
所谓货币代币指的是诸如比特币、以太币等作为一般支付手段投入使用的虚拟货币,其特点在于此类虚拟货币用以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并不与特定的网络交易供应商绑定。〔18 〕关于货币代币法律性质的讨论需要对两个问题进行区分:其一是货币代币之上是否存在某种“权利”,从而使其交易得以适用与该权利性质相对应的法律规范;其二则是货币代币是否属于“金钱”,从而使以其为标的物的债在民法上成立金钱之债。这是两个不同质的问题,货币代币之上是否存在权利,存在何种权利或法律上保护的利益,直接决定了法律对当事人在货币代币上的利益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这是第一层级的问题。而货币代币是否构成金钱以及是否构成金钱之债,则在第二层级上触及民法上与金钱之债相关的特殊规则。
1.货币代币的合法性之疑
尽管公告对代币融资行为作出彻底的否定性评价,但民间投资者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进行投资的热情却依旧高涨,尤其是在“委托投资”纠纷中,因代买代卖比特币等虚拟代币而引发的诉讼依旧大量存在,各种“虚拟货币”的民间交易依旧层出不穷:影视链FTV虚拟货币 〔19 〕、Vpay 〔20 〕、派 〔21 〕、波场币 〔22 〕、马克币 〔23 〕等种类繁多的虚拟代币加大了审判工作的难度。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虚拟代币交易的合法性看法不一,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立场:(1)有效说。这种观点支持虚拟代币交易的效力。该观点从解释论上分析,认为公告的意义仅在于否定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货币”属性,禁止其在金融领域被作为货币使用,但“并未否定上述虚拟货币可以作为一般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虚拟货币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可支配性”的特征,属于民法所保护的“虚拟财产” 〔24 〕。因此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并不因公告之规定而陷于无效 〔25 〕。(2)无效返还说。这种观点对虚拟代币交易的效力持否定态度,认为合同无效,应当按照无效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处理。该观点认为依据公告规定,虚拟代币交易属于合同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情形 〔26 〕,双方应当就已经发生的给付互负返还义务且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分担损失 〔27 〕。(3)不保护说。这种观点则认为法律不对此类交易进行救济,从而在否定合同效力之后继而否定双方当事人的返还义务。其理由在于虚拟代币交易行为不受我国法律保护,其行为造成的后果以及风险应由当事人自行承担。〔28 〕有法院甚至在裁判文书中明确指出:“在买卖比特币过程中产生的损失难以认定系从事的合法交易活动中合法权益受到损失,因此……本案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的受案范围……” 〔29 〕由此,司法实践基于虚拟代币的交易发展出了一种新的“自然之债”的类型,此类交易无论表现为买卖、委托投资抑或其他合同形式,均无法获得效力;而当事人基于此类“合同”而进行的给付,也不能依据真正的“无效合同”的相关规则请求返还——简而言之,法律拒绝对此类交易进行处理,而将其留给当事人“自治”。
七部门联合作出公告的效力折射到民法上意外地形成“有效”“无效”“不保护不返还”三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意见,其根本原因在于虚拟代币的特殊性使得法院在对交易效力进行判断时将不同层面的问题混淆在一起,将“非法集资”层面非法性的判断与交易客体非法性的判断混为一谈。
非法集资行为的认定针对的是当事人集資的行为,而非从根本上禁止针对相关客体的交易。例如常见的非法集资行为包括:“(1)借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等名义非法集资……(4)通过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5)以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与‘快速积分法等方式进行非法集资……(9)以签订商品经销合同等形式进行非法集资……(12)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形式进行非法集资。” 〔30 〕在对上述非法集资行为进行规制时,人们通常不会想要彻底禁止市场上对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无论是“种植、养殖、项目开发、庄园开发、生态环保投资”,还是“商品销售与返租、回购与转让、发展会员、商家加盟”在通常情形下均为合法行为,更遑论“会员卡、会员证、席位证、优惠卡、消费卡”之类充斥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商品服务。
但是,虚拟代币交易却从根本上引发了监管部门乃至全社会关于“客体非法性”的担忧。此种担忧清晰地体现在公告的措辞之中:“代币发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比特币等基于区块链技术产生的虚拟货币以其“去中心化”的特点严重挑战了法定货币的权威,“代码即法律”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被提出, 〔31 〕更是从思想上形成了对既有金融、社会秩序的挑战。从市场监管的角度来看,将虚拟货币融资纳入监管范畴是维护金融、社会秩序的必然之义,然而从传统民法角度观察,立足于“非法集资”或“证券范围”的相关讨论,永远无法真正解决比特币、以太币等虚拟代币交易本身是否合法的问题。是否禁止比特币等虚拟代币的流通与是否禁止发行代币融资应当被区别对待:前者的动因源自对虚拟代币挑战法币地位的隐忧,而后者的动因则更多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不受非法集资行为的损害。唯有深入虚拟代币的具体类型与构造,了解其原理与内在结构,才能将上述本不同质的问题区分开来。
2.货币代币的民法属性:非物非债的财产性权利
对于虚拟代币的法律属性,理论上存在“非货币财产说”“数据说”“证券说”“准货币说”等不同观点 〔32 〕。这些学说从各自的角度对虚拟代币的性质进行了描述性的归类,突出了虚拟代币在某一方面的特质:例如“非货币财产说”关注虚拟代币代表的财产利益,“数据说”关注虚拟代币的技术基础,“证券说”关注虚拟代币的金融属性,“准货币说”则关注虚拟代币在社会实践中的支付功能。上述学说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反而共同构成了对虚拟代币法律属性的完整思考。
从法律属性上看,货币代币构成一种既非物权、也非债权的财产性权利。货币代币之所以不属于物,其根本原因在于货币代币之上无法成立物权法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 〔33 〕,理由有两点:第一,虚拟代币用户对虚拟代币享有的权利并不具有物权意义上的支配性。用户对于虚拟代币通过账户实现的“支配”并非物权意义上的“支配”,因为账户仅能起到确定访问密钥的作用,而无法越过服务器实现对虚拟代币现实的管领力。一旦系统或程序出现问题,用户则无法控制自己账户内的虚拟代币 〔34 〕。第二,货币代币不具有使用价值,不能满足物权法上对所有权的定义。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而货币代币的本质功能在于支付,其作为一种支付手段仅具有交换价值,而不具有使用价值 〔35 〕。因此,如果将货币代币认定为“物”,则会与物权法以所有权为核心构筑的概念体系相悖。在通常的交易中,人们将一定数额的价值归属于单位数量的虚拟代币之中,并且以该虚拟代币为单位进行交易,这并不意味着虚拟代币本身成为了物,物的属性也并非虚拟代币充当交易媒介的必要前提。德国法上虽然拒绝在虚拟代币上使用“所有权人”的概念,而代之以虚拟代币的“拥有者”的表述方式,但也不得不承认,虚拟代币拥有者针对虚拟代币的权利是一种与所有权近似的权利。此类财产虽然不属于物,但其交易与转让可以类推适用民法中关于物的规定 〔36 〕。
货币代币之所以不属于债,原因在于货币代币仅由矿工“挖矿”取得,如“数据说”所主张的,其本质是一段数据 〔37 〕。尤其是在“去中心化”的区块链技术基础上,实际上既不存在货币代币的拥有者基于该货币代币而对他人享有的债权,也不存在一个中心支付机构,即承诺随时兑现虚拟代币的“中间人” 〔38 〕。就此点而言,货币代币与银行存款的性质截然不同,在后者情形下成立银行与储户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39 〕。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货币代币之上存在着被市场广泛认可的财产价值。虚拟代币自身不具有内在价值,其价值完全取决于使用者在何种程度上接受其作为一种支付手段。也正因如此,虚拟代币之上才可以成立一种既不属于物权、也不属于债权、无实体的、非货币的新型财产 〔40 〕。2020年修订的德国金融事业法(KWG)在第1条“概念规定”中增加了关于“虚拟价值”的定义,其中规定:“本法所称虚拟价值,指某种价值的电子形式,该价值不由任何中央银行或公共机构发行或提供保障,不具有货币或金钱的法定地位,但可以基于自然人或法人的约定或事实上的实践而被接受为互易工具、支付工具或为投资目的而发挥作用,并可以通过电子方式转让、储存以及交易。”
在虚拟代币的法律性质问题上,代币与可信技术服务商法并未将虚拟代币统一地定义为物权、债权或其他类型的财产权,而是将虚拟代币定义为“可信技术系统中的一段信息”,其能够代表针对某人的债权或社员权,针对物的权利或其他的绝对权或相对权。在此之外,虚拟代币必须归属于单个或多个可信技术身份 〔41 〕。所谓可信技术身份,则指使得虚拟代币的清晰归属成为可能的身份。对虚拟代币进行转让,则需要所谓的“可信技术密钥”,它使得对虚拟代币的处分成为可能。而可信技术服务商指的则是从事虚拟代币的发行、制造、可信技术密钥保管、可信技术代币保管、可信技术维护、物理验证、代币交易、交易检验、定价、身份识别等业务的人 〔42 〕。从上述对虚拟代币的定义来看,该法直接针对的对象似乎仅限于外围代币,即不包括以比特币为首的本征代币,因为后者本身并不代表任何针对他人的“权利”。但是该法第3条第3款又特别规定:“本法第4条到6条、第9条依其目的适用于不代表任何权利的代币。”依据该款规定,外围代币交易的相关民事规范也可以有选择地适用于本征代币的交易之中 〔43 〕。
承认货币代币的虚拟财产属性,在合同法、税法、继承法、破产法领域均有重要意义 〔44 〕。例如在承认货币代币财产属性的前提下,双方当事人以法定货币交换虚拟代币的约定可构成买卖合同 〔45 〕。但如果双方当事人的约定并非以法定货币交换虚拟代币,而是以虚拟代币作为结算工具,用以“购买”他物,则成立互易合同 〔46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互易合同与买卖合同在构造上的相似性,还是主观上将虚拟代币作为“钱”使用的意愿,均不能构成在法律上将互易合同定性为买卖合同的理由 〔47 〕。
3.货币代币“金钱”性质的否定
从比较法上来看,虚拟代币的货币功能尚未在任何一个国家得到承认 〔48 〕。因为货币制度本质上属于国家主权领域,没有国家主权背书的虚拟代币,不可能如同货币一般成为法定的支付方式。这在民法上意味着,债权人在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形下无义务接受债务人以虚拟代币进行的履行 〔49 〕。因此,货币代币实际上是一种可交易价值的数据呈现,其在内网范围内承担了支付工具的功能,但在外部因不具有法偿性而不成为真正的货币 〔50 〕。
当人们对于虚拟代币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货币”进行争论时,经常被忽略的问题是“金钱”这一法律构造在民法上具有的特殊意义以及“金钱之债”在民法上适用规则的特殊性。如果认为货币代币属于“金钱”,那么在民法上至少会带来以下后果:首先,当事人以“给付金钱”为内容的义务无法适用债法上有关给付不能的相关规则。对此,我国民法典第579条明文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而第580条规定的给付不能的情形仅适用于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錢债务”不符合约定的情况。其次,如果被认定为金钱债务,则虚拟代币的给付与返还也存在计算利息的问题,而该利息需要以同种类的虚拟代币进行支付。最后,金钱给付无法适用瑕疵担保规则。从合同性质上看,一旦虚拟代币被认定为金钱,则以虚拟代币交换其他种类商品的合同就不再是互易合同,而是买卖合同,这在法律适用上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债法上关于瑕疵担保的救济规则无法适用于虚拟代币之上 〔51 〕。
民法上之所以对金钱之债另眼相看,其最核心的原因在于金钱之债仅具备唯一的目的,即一方当事人将抽象的财产价值转移给另一方当事人,但对于金钱本身的价值并不关注——因为该价值就是通过金钱本身加以衡量的 〔52 〕。例如,甲以一万元将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出卖于乙,甲考虑的是以该笔记本电脑获取一万元的抽象财产价值,而乙考虑的是以一万元的抽象财产价值获取该笔记本电脑,而不会再去考量一万元究竟“值多少钱” 〔53 〕。因此,金钱之债根据其意义与目的是一种抽象的、无客体的价值移转之债 〔54 〕。
当货币代币作为一种投资品出现,其价值与现实直接产生交集时,其本身的价值依旧取决于法定货币的定价。换言之,当交易双方当事人使用货币代币进行交易时,双方并非认为“该笔记本电脑价值若干虚拟代币”,而是“该笔记本电脑价值一万元,一万元可以购买若干虚拟代币,所以该笔记本电脑价值若干该虚拟代币”。如此一来,货币代币只不过是在法定货币与终端商品与服务的交换之间增加了一道媒介,而货币代币自身同样具有市场价值,此时其性质并非金钱,而是商品。因此,以货币代币兑换其他现实商品与服务的交易,其本质上属于互易合同,而以货币代币兑换法定货币的交易,其性质属于以法定货币购买货币代币的买卖合同。与之类似的是在外汇买卖中,尽管人们在日常用语中经常使用“兑换”外汇的表达方式,但该交易关系从民法上评价并非互易,而是买卖。其本质上是当事人使用手中的法定货币购买外汇的行为,外汇在此种情形下的性质并非货币,而是商品 〔55 〕。由此可知,尽管货币代币原则上可以作为商品、服务交易中的对待给付发挥生活观念上的“支付”功能,但从法律评价上看,货币代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支付工具,而是一种仍然需要借助法定货币体现其价值的投资产品 〔56 〕。
(二)使用代币
與货币代币不同,使用代币存在确定的发行人,代币的拥有者基于使用代币而对该发行人享有一定权利 〔57 〕。例如委内瑞拉的一种名为“石油币”的虚拟代币,其价值通过将每个支付单位与原油相绑定而获得实现 〔58 〕。与投资代币相比,使用代币的拥有者对发行人享有的权利不应是金融性的,而应当指向特定的产品或服务 〔59 〕。这意味着使用代币的拥有者既不能基于使用代币而进入一个企业之中,也不能凭借使用代币参与利润的分配。根据莫伦坎普的观点,使用代币具有两大重要作用:其一,使用代币具有稳固货币代币价值的作用。因为使用代币在货币代币与现实价值之间建立了桥梁,使得货币代币作为支付手段的特质在现行经济秩序之下得以保障。其二,使用代币简化了对财产客体以及相关权利的处分流程,人们唯需解决如何对简化后的流程在法律上进行评价的问题 〔60 〕。
使用代币与货币代币不同,诸如比特币等货币代币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发行人,因此对于货币代币而言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一级市场。但使用代币是由发行人发行的,因此对于使用代币而言存在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的划分,应当对其发行与交易进行分别观察 〔61 〕。就使用代币的发行而言,发行人承诺使用代币的购买人以特定的代币数量购买相应的产品、服务,这从本质上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习惯的各类购物券、代金券并无不同。使用代币既无股份的性质,又不以未来指向金钱的资本利益为标的,因此并不构成金融法上的有价证券 〔62 〕。在其后的二级市场交易中,因为使用代币本质上属于代币拥有者可以向发行人主张的债权,因此原则上应当适用民法中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 〔63 〕。
使用代币与投资代币不同,对于投资代币,购买者关注的是发行人通过其项目盈利的意愿和能力,对于使用代币而言则不然。使用代币的购买者更为关注于使用代币相关联的商品或服务的性能与使用风险 〔64 〕,即呈现出较强的产品关联性 〔65 〕。当使用代币初次发售时,意味着代币购买方获得了该代币所代表的权利以及财产客体的处分权;当使用代币被再次转让,则意味着其所代表的权利或财产客体也被一并转让 〔66 〕。在法律关系的构成方面,使用代币在区块链上的“移转”本身实际上并不具备独立的意义 〔67 〕。对于合同成立以及生效的判断应当遵循民法上的一般规则,在对构成合同的意思表示进行解释时,也应当依据意思表示解释的相关规范,基于“客观受领人”的立场判断是否能够从代币转让行为中解释出当事人的默示意思表示。
(三)投资代币
投资代币体现的价值是未来的支付、共同管理权或共同表决权 〔68 〕。投资代币中最为著名的实例是“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根据DAO的协议,DAO币的拥有者可以在互联网上通过投票的方式共同作出投资决策 〔69 〕,DAO币的拥有者之间就此成立了一个民事合伙性质的社团 〔70 〕。
投资代币构成有价证券,必须纳入金融市场的监管之中。德国联邦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将此类代币定性为“一种独立类型的有价证券”,并且指明此处其有价证券的属性应仅从监管法的意义上去理解 〔71 〕。与使用代币类似,投资代币同样存在一级二级市场的划分,需要注意的是,在二级市场进行交易时,要区分该投资代币究竟代表了一种单纯关于未来支付的债权,还是也包含一种成员资格 〔72 〕。如果投资代币的具体构造表现为一种企业份额的代币化,则其还需要受到相应商事法律的规制 〔73 〕。
将虚拟代币划分为货币代币、使用代币与投资代币在监管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在瑞士法上,投资代币必然属于证券范畴,从而需要受到相关金融法规的规制;货币代币通常不属于证券范畴,不适用针对证券的规范;对使用代币而言,只要该代币仅针对发行人的产品与服务作出承诺,且其承诺的债权从发行开始便是可以使用的,则不构成证券;然而若使用代币存在预融资阶段,则可能暂时性地构成证券 〔74 〕。在德国法上,货币代币同样自始不属于有价证券的范畴,因为其支付单位的功能天然排除有价证券的性质 〔75 〕,投资代币必然属于证券范畴,而使用代币则需要分情况判断。对使用代币而言,如果其体现的主要风险是债务不履行的风险,即与之关联的产品的使用性能无法实现的风险,则其并非证券而是一般债权。对于此类代币的交易,民法上债权转让的规范、包括消费者保护的相关规范都可得以适用 〔76 〕。然而,如果使用代币的交易是为了获取该产品或服务在未来可能产生的收益,则构成有价证券。尤其是当产品与服务尚未切实存在,与之关联的使用代币却已经开始发售时,该使用代币会被认定为具有融资功能的有价证券 〔77 〕。
三、虚拟代币的转让规则
(一)虚拟代币的处分与智能合约
围绕虚拟代币交易经常使人困扰的问题是:如何在法律上评价虚拟代币在私人主体之间的转让。该问题在既有讨论中经常被人们与区块链技术之下的另一个颇具争议的法律问题相混淆,即智能合约的法律性质问题。
智能合约,指在当事人预先设定的条件成就时自动执行的合同形式 〔78 〕。在智能合约中,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均以数据的方式被预先储存下来。而一旦条件成就,程序会自动完成合同的履行,无须当事人再实施其他履行行为。智能合约本身并非某种独特的缔约方式,其所呈现的合同的缔结依旧遵循“要约/承诺”的基本范式。智能合约属于合同形式的一种——在法律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订立口头合同、书面合同、公证合同,也可以选择通过数据电文订立合同,自然也可以选择通过智能合约的方式订立合同。智能合约不等于合同本身,而只是一段电脑程序,但当事人可以通过智能合约完成从合同的订立到履行等一系列法律上的行为。例如,若将自动售货机视为最原始的智能合约,则该买卖合同从订立阶段便采用了智能合约的方式;在合同的履行阶段,当事人的履行行为可以借助智能程序在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自动执行,完成例如支付、激活账户、发货等一系列操作 〔79 〕。在此意义上,智能合约可以起到预先防范违约的作用。例如当线下的合同发生给付障碍时,当事人可以通过预先设定的智能合约获得损害赔偿,从而避免谈判力量不对等、维权成本过高等情形下求偿不能的风险。对此,工信部《2018年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中指出:“智能合约是由事件驱动的、具有状态的、获得多方承认的、运行在区块链之上的且能够根据预设条件自动处理资产的程序,智能合约最大的优势是利用程序算法替代人为仲裁和执行合同。本质上讲,智能合约是一段程序,且具有数据透明、不可篡改、永久运行等特性。” 〔80 〕
因此,以智能合约订立的合同本身依旧需要遵循民法典关于合同的相关规范,具体到虚拟代币的转让问题中,则需要当事人之间存在关于转让虚拟代币的合意,这一合意可能从当事人设定智能合约的行为中解释得出。当虚拟代币在线上的移转与当事人在线下的实质法律关系状态发生偏离时,缺乏当事人合意的虚拟代币移转不能成立合同 〔81 〕。事实上智能合约的执行未必全都在线上进行,可以完全在线上履行完毕的智能合约主要涉及虚拟货币本身权属的转让,但智能合约的履行也可能需要借助线下的行为,例如寄送特定的货物等。当事人既可以通过智能合约直接订立合同,也可以将在线下订立的合同通过智能合约加以固化,以保障其执行 〔82 〕。
代币与可信技术服务商法对于虚拟代币的处分作出了清晰的定义,其认为虚拟代币处分既包括虚拟代币处分权的转让,也包括以虚拟代币设定担保或用益权。该法第6条规定虚拟代币的转让应当满足以下条件:首先,虚拟代币的转让行为应当根据可信技术系统的规则订立,当事人也可以在不转让虚拟代币的情况下,在虚拟代币上设定限制物权,只要该限制物权的设定对第三人而言是公开的,且该限制物权设定的时间是清晰的。其次,虚拟代币的出让人与受让人做出一致的、转让虚拟代币处分权或设定限制物权的意思表示。最后,虚拟代币的出让人在法律上应当为有权处分,除非存在该法第9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情形。如果虚拟代币的处分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或者法律上的原因嗣后丧失,则应当适用不当得利的相關规则进行返还 〔83 〕。如果某人出于获得虚拟代币处分权或限制物权的目的,善意地受让虚拟代币,那么即便出让人属于无权处分,该受让人也应当受到保护,但受让人知晓或在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之后应当知晓出让人为无权处分的除外 〔84 〕。上述规范确定了法律行为与意思表示规则在虚拟代币交易中的适用可能,虚拟代币的交易绝非纯粹的“代码之治”,对于虚拟代币处分的有效性依然需要考察当事人的合意,而善意取得与不当得利返还的问题同样可能出现在虚拟代币的交易之中。
(二)区块链技术的“登记簿”功能
区块链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数据透明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其天然获得了技术上的公示公信效力。首先,区块链上的数据并非掌握在某个中心化的数据管理机构手中,而是由整个区块链系统中的全部节点对区块链上的信息独立进行记录,只要其中一个节点上的信息未丢失,整个区块链上的信息则都可得以保存 〔85 〕。其次,区块链采用哈希算法加密,极大提高了记录信息的安全性,而且区块链中每条信息的变化都需要经过超过51%的节点确认之后方可生效,使得其中的信息极难被篡改 〔86 〕。最后,区块链技术将每一笔交易向全网络节点广播,形成所有人可见、永久透明的交易记录 〔87 〕。因此,尽管区块链技术的运用从本质上不改变合同在民法上的构造,但其所具备的公示公信功能决定了该技术在民法上的意义并非仅限于一种新兴的合同形式,而是在特定情形下可以起到替代民法上公示制度的作用。
区块链的作用在民法上类似于登记簿,其与地产登记簿、商事登记簿等登记簿的区别在于前者从区块链的技术特性中获取信赖,后者的权威性和效力由法律确定和维持 〔88 〕。例如,在不动产的转让中,民法典第210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登记机构办理。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就不动产的转让而言,民法典第209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区块链的权威性则源自技术本身,货币代币之所以存在并且可以被转让,是因为区块链系统“记录”了它的存在并将其归属于某一用户。这一过程并非基于法律规定,而是纯粹基于运算而产生。货币代币的转让需要先将该笔交易记录到一个区块之中,再将该区块添加到相应的区块链上。例如,甲要将5个比特币转让给乙,则需要先形成一个记录了“甲转让5个比特币给乙”的区块,再将该区块添加到比特币区块链上。这5个比特币之所以在交易完成之后“归属”于乙而非甲,并非基于法律的规定,而仅仅是因为技术上是如此实现的。这并不意味着代码就此取代法律而成为判断财产权益归属的根本性依据。
立足于區块链的公示功能,代币与可信技术服务商法区分了可信技术密钥的持有者所拥有的事实上、技术上的“处分能力”以及民法意义上的“处分权”,并对两者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从技术事实的角度观察,持有可信技术密钥的人拥有事实上处分虚拟代币的能力;而从民法上处分权的角度观察,拥有可信技术密钥的人被推定为享有虚拟代币的处分权,每一个前手的可信技术密钥拥有者都被推定为在其拥有密钥的时间期限内享有虚拟代币的处分权。如果该基于密钥持有状态的推定与事实上的法律状态不符,即可信技术密钥的持有者并未想要同时成为处分权人 〔89 〕,则善意的持有者可以信赖前手处分人为有权处分 〔90 〕。针对外围代币转让过程中其所代表的相关权利所处法律地位,代币与可信技术服务商法明确了两条基本规则。第一,区块链“登记”的公示公信规则。根据该法规定,任何在可信系统中被证明拥有处分权的人均同时被视为虚拟代币所代表的权利的合法拥有者,从而可以向依据该虚拟代币的具体构造承担相应义务的人请求履行该义务。当债务人向在可信系统中被证明拥有处分权的人进行给付之后,其债务得到清偿,除非其明知或在尽到适当注意之后应知对方并非相关权利的合法拥有者 〔91 〕。第二,虚拟代币转让的效力及于该代币所代表的权利。如果虚拟代币处分的法律效果无法直接得以实现,则负有转让虚拟代币义务的人应当采取妥善措施以保障虚拟代币所代表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完成转让。根据代币与可信技术服务商法第7条第3款的规定,在强制执行程序中,虚拟代币的转让同样针对出让人具备法律拘束力,而针对第三人,则仅当诉讼程序开始之前该转让已经启动或虽然在诉讼程序开始当天启动,但受让人可以证明尽管其已经尽到适当的注意义务,但仍然对该诉讼程序的开启不知或不应知情时,该转让才具备法律效力 〔92 〕。
强调区块链的登记簿功能在民法上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将“公示”问题与产权归属问题区分开来:区块链上记载的虚拟代币产权状态并不意味着法律上的最终评价,但基于区块链的技术特征,此种记载可以起到公示的作用。这一区分直接导致对于区块链上是否存在善意取得问题的不同判断。大量观点认为对虚拟代币而言不存在民法上的善意取得问题,其最核心的论据在于虚拟代币无法在区块链以外流通,区块链中记载的归属状态就是其实际状态,因而不存在善意取得中权利外观与归属的背离,也就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93 〕。但此类观点实际上混淆了财产占有事实状态的变化与财产权利转让之间的关系。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区块链技术还是建诸其上的智能合约,相对于法律上的“合同”概念而言,都仅是合同订立或履行的技术手段,而该转让行为在法律上的效力是否能够得到认可,与该行为是否在技术上已经完成无关。作为登记簿,区块链上的信息仅是对当事人行为(特别是意思表示)的记载,并不代表法律评价的最终结果。因此,在区块链上“变更登记”、转移虚拟代币财产归属的行为在德国法上被一致认定为一种事实行为 〔94 〕。若某一交易已经在区块链上完成,但其合同在事后被认定无效或被撤销,则应当依据不当得利法的规则进行返还 〔95 〕。此时返还的客体并非虚拟代币所代表的财产价值,而是为了实施该转让而在区块链上记录的信息,使受让人不再从技术上有权处分相应虚拟代币,而使出让人重新在技术上获得处分相应虚拟代币的权限。该返还关系类似于登记簿登记状态的返还 〔96 〕。如果该返还已经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则应当对其价值进行补偿 〔97 〕。
四、法律属性、处分规则、公示效力的体系整合
基于上述论证可知,虚拟代币的法律属性、虚拟代币的处分规则以及区块链上记载的虚拟代币权属状态实际上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其中,虚拟代币的法律属性位于逻辑的前端,而与虚拟代币的处分规则紧密相连:法律属性决定规范适用。而虚拟代币转让的特性恰恰在于人们通常仅通过区块链上的数据来观察虚拟代币的权属移转,这就使得人们通常将法律上的评价与技术上的“能为”混淆在一起。事实上,区块链技术由于其本身的公开性、安全性,在交易中仅能够起到公示公信的作用,并不直接触及虚拟代币背后的法律关系。虚拟代币在区块链上的移转并非在法律上毫无意义,它可以起到证明其所代表的权益归属的作用,而交易中的第三人可以善意信赖区块链上显示的权属状态。但对于虚拟代币转让背后所代表的权益如何转让,还需要结合虚拟代币的不同类型分别判断。
对于货币代币的转让,可以类推适用动产物权转让的相关规范,在区块链上移转权属,相当于动产的交付;而对于使用代币的转让,则可以适用债权转让的规范。但由于区块链本身具有公示的效力,因此使用代币的转让无须特别通知债务人,任何持有虚拟代币的人均可依据其所持有的虚拟代币直接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原则上不得拒绝,除非对方并非相关权利的合法拥有者;投资代币的转让本身不属于民法问题,而应当依据其具体构造在构成有价证券时适用证券的相关法规范,在其代表企业份额时,还应适用相关商事法律规范。
总而言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虚拟代币确实带来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交易形式,它将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打包在一起,一并冠以“虚拟代币”之名,并依托区块链,在技术上实现统一的“处分”规则。但是当此种经济现实进入法律的视野,法律需要做的恰恰是将此种社会现象反向拆解开来,透视其背后的法律本质。事实上从过往中不难发现,在腾讯QQ红极一时的年代,社会上同样爆发过关于Q币是否能够代替法定货币的疑虑 〔98 〕,然而如今人们似乎已经对各种各样的此类代币司空见惯了。区块链作为一项对社会公众而言难以理解的新兴技术,其带来的变革一如当初。以区块链技术为基础的比特币等数字加密货币引发的质疑与抵制也像是网络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中的又一个轮回。
Abstract: Virtual token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basic types with different legal nature: currency tokens, utility tokens and investment tokens in perspective of legal application. Currency tokens are neither right in rem nor creditor's right, but a new type of non-physical and non-monetary property. The issuer of utility token promises token purchaser to purchase the product or service with a specified amount of tokens so that a credi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suer and the purchaser of the utility tokens is established. The Securities Law and other relevant commercial laws shall govern investment tokens with respect to future payment, joint management right or joint voting right. The application of block chain does not change the legal nature of virtual tokens, the intellect contract is a new type of contract in virtual token transaction, but block chain can play the role of publicity in traditional civil law because of its openness and safety.
Key words: virtual tokens; digital currency; block chain; bitcoin; smart contract; token financing behavi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