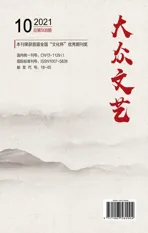《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研究
2021-06-13王雨秋王艺凡肖慧敏
王雨秋 王艺凡 肖慧敏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山海经》作为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的奇书,以山海为经,载述诸多奇植异兽怪人及由此产生的神话与巫术幻想,保留了丰富芜杂的早期神话资料。较西方高度系统的史诗神话,《山海经》也更具原始的洪荒的气息,因而更能以此管窥先民的神话思维形态。
相较于《山海经》中奔走跳跃的活泼的也因其瑰奇神话色彩而更引人注目的动物,《山海经》的草木作为荒诡自由的元初世界之背景,默默不动,更易为人所忽略,但也正因根植于元初世界并与之融为一体,因而也较《山海经》中的动物形象更能体现先民的本来思维,更具原始意味。故此,本文从静态之草木形象着手,从有别于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动物形象研究之角度,一窥先民的原始思维。
一、《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
汉人刘秀《上山海经表》载:“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山川各别,草木不类,水土不一,《山海经》中并没有如希腊神话中有高度权力的神统摄四方役使万物,与山川同在之草木,未有专司之神掌管,而是依山川随水土,为山海之所固有,自由蔓衍,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草木随意分布在山川之中,因而与之遭遇也就具有了偶然性,没有专司之神的束缚,这些草木给人带来的吉凶祸福便也具有了极大的偶然性。草木是随时可遭遇的,草木所带来的吉凶祸福也是不确定的,所以与之遭遇的先民也就对其充满了恐惧感、神秘感和侥幸感。对山川丰饶草木的不可控感也使先民们具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希冀祥瑞的欢愉。
《山海经》中记载的草木极为丰富,有的甚至不乏神话色彩,如《中次七经》中“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丘,服之媚于人”记载䔄草化生的故事,但总的来说,《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基本上还是较为如实地反映了元初时代先民的生存环境。《山海经》中的草木按草本木本分基本可分为两类,为草,为木,未见灌木的分类,也未有更为细致的分类,由此可见,当时的先民对草木种类的认识还是停留在比较简单的层面的。《山海经》中的草木分布也是比较如实的,北方通常为不毛之地,不生草木,而东南多草木,是较为符合中国地理环境的,如此看来,《山海经》虽然是一部“古之巫书”,但是却仍然依托于现实,而草木正是集展现其时真实世界与反映先民神话想象于一身,链接神话想象与真实世界的线索。
《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反映先民神话想象的方式正是先民观照草木的方式。除了记载草木名称外,先民与草木的交互方式主要有“佩”和“食”两种,其他方式也有如“浴之”等,但数量较少,且同“佩之”一样,都是通过肢体接触,故此与“佩”同说。“佩”通过接触,“食”通过体内的吸收,除了“食之”常常为了充饥外,“佩”和“食”主要是为了获取草木的医用价值,保持身心的康健,反映了其时人们的医药知识及医疗水平,掺杂其中的,是许多巫术色彩浓厚的“疗效”,如一种“其状如葵”的叫多条的草,“食之使人不惑”,还有一种果实如枳的树木,“食之宜子孙”。这些显然不是可以普通草木的一般医用疗效,但是可以通过“佩之”和“食之”来达到这种功效,这正是弗雷泽在《金枝》中论及的“交感巫术的另一大分支”,即“接触巫术”,其作用原理是事物通过互相接触而在彼此间形成一种联系。但是这种接触效应非常有限,只及于个人,最多及于家族,并且大部分都是单类药物对于单类病症的一对一疗效,例如“嘉荣服之者不霆”“帝休服之者不怒”等,并没有两种或以上药物的搭配治疗,也没有如“一株”“一段”这类直接说明使用的剂量,说明了当时用药知识还停留在一个较为基础的层面,效应范围则主要反映先民所恐惧和担忧的事件,如部分身体上的疾病、无法解释的梦魇等现象、主要集中于恐惧和迷惑等心理上的问题以及子孙的繁衍。究其原因,在于先民们生产和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有限,对不可知的自然力量感到畏惧,于是转而求助于神秘的巫术,并将其记录下来,作为一种固定的经验,最后成为一种巫术的信仰和仪式,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我们已经知道,在某种危急之时,原始人的知识有限,早期观察和推理的能力亦告束手无策之际,于是所有的本能和情绪,所有的实际活动,把他领入死胡同,动弹不得。人类对此会有自然的突发反应,其时出现一些幼稚的行为方式,并对其效力抱有幼稚的信心。巫术将这些幼稚的信仰和仪式予以固定,并使之标准化,而成为永久的传统方式。”此外,还有一些草木有着特殊的实用价值,如一种叫白䓘的树木,除“食者不饥,可以释劳”外,还可以“血玉”。
《山海经》中部分草木功效如下表所示:

表1 《山海经》中部分草木功能汇总表
二、《山海经》中的动物形象
不同于《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山海经》中的活泼的动物却使初民的心理五味杂陈。一方面,对于这些各式各样的动物,初民们充满了描述这些奇异动物的热情,它们的叫声使这个莽荒的元初世界生气勃勃,尤其是对于一些可以带来祥瑞的动物,初民们无疑是欢迎的,比如“见则其国大穰”的狡。但是另一方面,在初民生存处所的周围,似乎四处潜藏着种种异兽怪禽,带来可怕的征兆,初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瞬间欢乐祥和洗荡净尽,只余下沉重的生存忧患。“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显得十分脆弱和渺小,逐渐产生对自然物和自然力的敬畏感、依赖感和神秘感”,这些怪兽异禽给初民们带来的忧惧主要集中在天灾、人祸与疾病三个方面,它们随时出没,带来大水、大旱、大兵、大疫等征兆,既非人间恶行招致的灾祸,也非如西方神话中诸神的喜怒无常,只有突如其来不可控的惊慌失措,这便是先民们对自然界不可控的灾难的感受。天灾既已不可控,人祸却似乎也无能为力,战争徭役的预兆也时时可见,如“见则县有土功”“见则国有兵”。一切的灾祸祥瑞都取决于与这些带有征兆的异兽怪禽的不期而遇的“见”,这种遇见动物时惴惴不安的忧惧和初民们面对疗救为主的草木时平和的心情完全不同,也就在一片动物的遥遥呼和中更显出《山海经》中草木形象的宁静、包容与疗救。如果说《山海经》中的动物形象过分地反映着初民的生存危机意识,那么《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就是初民们“在某种非自然逻辑的状态中求取自身吉凶安危的保证”。
《山海经》中部分动物征兆功能如下表所示:

表2 《山海经》中部分动物征兆功能汇总表
随时可出没的怪兽异禽带来吉祥与灾异的征兆,初民们喜爱能带来吉祥征兆和抵御凶兆的动物形象也是自然之理。动物形象的祈福御凶功能便是先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动物们征兆吉凶的功能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寄托了初民们美好的愿望。
值得注意的是,具有祈福功能的动物多为鸟类,或如凤凰、鸾鸟是带来祥瑞,或能御火,如丑阳山上“其状如鸟而赤足,可以御火”的飞禽、小华山上“可以御火”的赤㭤。后者这类可以御火的鸟类更为引人注目,它们的名称里要么带有“赤”字,要么就是身体的部位是红色,如“赤足”“赤喙”“赤身”等。这一现象可以从弗雷泽的《金枝》中找到一个可能的答案。弗雷泽指出,这是一种巫术赖以建立的思想原则,即一种根于相似律的“同类相生”或“果必同因”,基于此种原则的法术叫“顺势巫术”或“模拟巫术”。名字带“赤”的鸟或者身体部位为“赤”的鸟和红色的火焰似乎有着某种同出一源的关联,先民们则认为这种关联可以抵御无情大火的侵扰。
《山海经》中部分动物祈福御凶功能如下表所示:

表3 《山海经》中部分动物祈福御凶功能汇总表
《山海经》中的动物形象除了显示征兆的功能外,也具有其作为外物而为先民所用的疗救功效,通常也是通过“食之”与“佩之”两种方式,这一点同《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一样,这些动物形象也因此具有了草木形象的植物性从而使《山海经》中的元初世界变得祥和起来,危险也似乎显得不那么可怕。也由此看出先民们在征服动物方面做出的努力,在危机重重的自然与社会中积极保全自身的厚生养民思想。
《山海经》中部分动物疗效如下表所示:

表4 《山海经》中部分动物疗效汇总表
三、《山海经》中所载的草木神话
《山海经》中关于草木的载述除了前文所述的具有某些特定功能的普通植物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关于草木的神话。
在《山海经》所载的远古岁月里,先民们认为万物有灵,万物生存的根本来源于神灵的依附,如果神灵依附于物,那物就具有了生命,一旦神灵离开,那物也就相应地宣告死亡。而在初民们的植物崇拜中,最高级别的神是树神,《海外东经》中就记载有“东方句芒,鸟面人身,乘两龙”的这样一个名为“句芒”的司木之神。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口数量不多,人类的能力也有限,这样一个弱小的族群,在面对着危机四伏的自然环境并不时遭遇着不可控的天灾人祸时,如何存活下来,以及如何存活得更久是人类所要面临的头等大事,与人类的脆弱单薄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有着旺盛的生殖力和顽强的生命力的草木。“横树之即生,倒树之即生,折树之即生”,《韩非子》中这样论及树木的顽强生命力,树木不仅百折而又生,而且能维持千百年的寿命,这更为初民所关注,庄子《逍遥游》便曾说“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因此,初民们便非常希望能够将草木的这种旺盛的生命力转嫁到自己的身上,从而使人类能够繁衍生息,代代长存。也因此产生了关于草木的不死神话。
最初关于草木的不死神话显然是根于草木本身旺盛生命力的神话,这种草木以“不死”的面目出现,便有了“不死树”的神话。《海内西经》载“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歼琪树、不死树”,不死树在先民看来如此珍贵,以至于在这棵神奇的树附近有只“身大类虎而九首人面”的开明神兽作为它的保护神。《大荒南经》里记载有一个“不死之国”,其国人“甘木是食”,似乎是因为食了这种“甘木”才使此国人有了不死的能力,“甘木”便也是不死树了。既然吃了这种“不死树”便能使人有了不死的能力,那便相当于一种药了,于是便有了“不死药”的神话,应当是不死树的神话发展到后来与方士的长生久视之术结合的产物,《山海经》中便记载有以巫彭为首的几个巫师“皆操不死之药”,不死树便从有神兽看管的神物变成了巫师掌管的不死药了,演变到后来甚至还有后羿上昆仑山向西王母求取不死药的神话传说,不死药进一步变为由神所有之物了。
大概由于不死树不死,根据人们的日常经验,年岁长的树木大概都是极为高大的,所以这种不死之树大概是要直入云霄,在人类不能到达天空的过去里,笔直入云的树便成了人类沟通天地的纽带,因而也自然地带有与神沟通的意味。《海外北经》载“寻木长千里”,长达千里的树似乎在人世间是难寻的,但是以神话的角度看便是顺理成章。先民们对树木更为神奇的想象是扶桑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对于这棵十日可居的神奇大木,《淮南子·天文训》是这样阐述的,“日出于旸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树木成为太阳的居所,且太阳上树成为白昼的开始,树的神性进一步增强。更为出名的是《海内经》的建木,《山海经》中是这样记载的,“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上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这种“百仞无枝”的树显然也具有了某种神性的特质,而且进一步发展,这棵神奇的建木成了大皞攀爬过,且是由黄帝制造的天梯。树至此时,已经从寻常“长千里”的略具神性的大木变成了与日共存的日之居所,再变而成由黄帝制造的天梯,树的神性在不断加强,但树的独立性也在逐步地削弱,神的权力在不断增强,在这种神话的演进与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是现实社会权力的不断集中,神话也就成为管窥其时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
要之,《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既是先民生存环境之反映,也映射出其时初民们的心理状态。面临着最为直接的生存威胁,先民们忧惧着威胁他们的天灾人祸和疾病,也在积极寻求可以禳福避祸的方式。不同于动物可能带来的灾异,《山海经》中的草木形象以其温和静默的疗救功效,集中体现了先民的厚生养民思想。关于其中的草木神话,以表现原始先民们追求健康长寿为底里,既反映了神话发展演进的过程,也表现了社会现实中权力的不断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