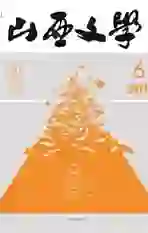光在虚无缥缈间
2021-06-02李壮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渺间。
——白居易《长恨歌》
“麦子店的夜晚是火热的。”这是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事实上,这个用来开头的句子一直没有消散,它如同某种背景音,始终铺垫和弥漫在这个热闹而又充满荒唐色彩的故事背后。在石一枫的笔下,麦子店不仅仅是一个地点,麦子店的夜晚也不仅仅是一个时刻;它是小说主人公的一种执念,而一种执念总是通向另一种执念,最终就会像并联电路一样,把世间那么多的执念统统给联到了一起。就拿这火热的麦子店夜晚来说吧。此时此地发生着的事情,固然只是卑微到充满喜剧感的小人物们的阴差阳错,背后却站着那么多浩大而普遍的困惑:在如此大的世界上,在如此多的同类中间,一个人应如何选择自己站立的姿态与位置?在冷暖善恶希望绝望无休止的撕扯转换中,一个人又到哪里去寻找自己观看、理解、应对这世界的坐标点?一个人的心灵看似是这样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但又有什么地方,能够真正地安放下它们?这么一连串的执念纠结下来,麦子店就不仅仅是麦子店了,而像是接近了宗教故事里的某些地点——例如西奈山顶、或者菩提树下,我们的主人公就站在这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正中心,起劲儿却又无望地思考着人与世界、与同类、与自己的关系问题。
“麦子店”三个字于是成为了某种无法说清道明却注定不能绕过的潜意识,它甚至变成了一枚无形的图钉,扎在各种地圖的隐秘穴位上——纸质的地图,手机上的电子地图,以及秘藏着渴望与耻感的当代个体内心地图。正如同“麦子”与“店”的组合是将农耕文明与商品社会的两种典型意象不由分说地压缩在一起,我面前这个被石一枫安放在麦子店的故事,也是以类似的方式,把喜与悲、冷与热、虚与实、聚与散、信任与背叛、盼望与破灭,都杂糅并置在一连串意味深长的玩笑里面。
因此,首先值得说一说的,就是这个“麦子店”。
1
在直观的层面上,麦子店是一片空间实体,它真实地存在于文本之外的现实世界中。说来惭愧,我本人虽已在北京生活多年,但直到读到这篇小说、直到我被好奇心驱使着打开了手机地图,我才搞清楚北京还真有片地方叫“麦子店”。我吃惊地发现,麦子店离我的日常活动范围并不远:它的南边是团结湖,那里坐落着几家重要的文学报刊社,我经常过去开会;东边是朝阳公园,周末去遛弯的人或许能见到我在球场上飞奔的身影;西南方向是大名鼎鼎的三里屯,去屯里逛个街吃个饭,自然是日常休闲的选项之一。唯独麦子店这片地方被我绕了过去,对我来说,它就像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这是当下都市生活的常态:我们固然生活在某一城市之中,但我们并不见得真正熟悉它,人们熟悉的往往只是与自己的生活发生了关联的那些“点”,以及由这些“点”所建构起来的特定想象:居所是一个“点”,工作地是另一个,最多再加上熟悉的商圈饭馆娱乐地带,连接起这些“点”的是交通图上的地铁线,我们在黑暗的地底管道里肃然静立而后如常抵达,地面上那些被60公里平均时速轻巧掠过的复杂生活景观正如同一个人生命有限性的完美隐喻。
如此,同样一座城市,却常常被切分为不同的空间、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形体和想象;从上帝视角来看,这城市的存在是确凿、稳定、严格遵守着物理学规则的;对生活于其中的人来说,这种“真实存在”却各有各的定义。石一枫在小说里借主人公王亚丽的心思划分过这“复数的北京”:遍布工地与立交桥的五环外是一种,那里的人“早上像打仗一样挤车上班,晚上像逃难一样挤车回家,回了家就把灯一开把门一关,此后与外界隔绝联系”,以一种“仿佛从没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北京”的方式构成了“生活在北京”的特殊典型方式;“燕莎”“凯宾斯基”以及天安门城楼又是一种北京,空间的距离并不远,但“那些北京,就是王亚丽摸不着也想不到的了”。石一枫所选取的麦子店,则代表着北京的另种可能——或许是意味更复杂、诗意空间更深邃的一种。这里的景观是多层次的,“有二十四小时不关门的咖啡馆,有经营各种没用的小玩意儿的文创商店,有上演‘不插电音乐和‘无台词话剧的酒吧书吧”;这里的人也是捉摸不透的,“他们在忙乱之余,似乎又总在琢磨一些别的事儿——不在眼前的事儿,虚无缥缈的事儿。所以半夜有人抽疯大笑,清晨有人痛哭流涕,不分昼夜都有人喝多了躺在马路牙子上晾肚皮”。这些人和事物,似乎在以一种虚无缥缈的方式释放出真实的慰藉与魅力。
这样的麦子店显示出意义与话语谱系的游荡状态,它真实可感又令人费解,既令人感到亲近又不断散发出陌生,仿佛一个空间背后叠加着另一些空间,又仿佛它的真实恰恰就植根于背后硕大无朋的不真实。它刚好适合王亚丽这样的“新北京群体”:在身份认同和自我想象方面,王亚丽们——这些忠贞于半价法棍,而坚定拒绝鸡蛋灌饼的年轻人——与北京、或者说与这个时代最前沿最核心的经验之间,始终处在暧昧、纠缠、若即若离、互释共生的状态之中。
在“复数的北京”里,麦子店这项小小的“单数”,又呈现出自身内部的“复数形态”甚至“余数形态”:固然我们可以指着手机地图上的驾车路线去论证麦子店的真实和具体,生活于此的王亚丽们,却始终尝试着要在确凿与缥缈、亲近与陌生、地面与天穹、安身认命与自由飞翔之间,重新丈量和定义自己在这世界上的位置。在诸多故事的结尾,他们往往像除不尽的余数一样被甩出了时代的运行公式、像结石一般被排出了生活常规的体外。但他们终究是乐此不疲的,仿佛只有通过此种方式,他们才最终得以被真正地整合与消化:“王亚丽的想法是,‘作就‘作吧,人生能有几年‘作。要是不‘作,她就该留在老家结婚生娃奶孩子。她有个初中同学的乳房都能甩到肩膀后面去了。”
也正是在此种意义上,《玫瑰开满了麦子店》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北漂或底层故事:深究起来,王亚丽们并非是在跟全球化时代的大都市现实较劲儿,而是在跟自己较劲儿;牵绊着人物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具体困境(这些具体困境更多只是情节发展的导火索),更是情感与价值的认知认同。
2
就这样,在王亚丽这里,空间的定位变成了空间的想象,实体的麦子店变成了抽象的麦子店。这样的空间,早已不再是柏拉图意义上均匀且同质的容器,而是充分进入了列斐伏尔与福柯意义上的、充满着社会关系与话语权力的、可不断进行自我再生产的空间语境——空间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也在生产和塑造着空间之中的人。
于是,麦子店成为了王亚丽——当然也包括她那位惹上麻烦的男友“果粒橙”——心中的小小执念。她迷恋着面包店里的半价法棍,迷恋着这里各形各色鱼龙混杂的人,她想要留在这里生活,计划着要自力更生开一家房屋中介,地址也早早选定在了麦子店。无他,只是因为这里可以满足她心底最隐秘的愿望、最迫切的需求:用虚无缥缈的事儿来代替实际发生的事儿。然而问题在于,即便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也最终会在具体的现实中留下线头;而这些再真切不过的线头,恰恰是人物接通那虚无缥缈世界的唯一导体。
在王亚丽的故事中,这枚线头就是“钱”。如果不是下定决心要在麦子店实现创业梦想,王亚丽和“果粒橙”不必以自虐般的残暴决心开启存钱计划;如果不必下如此的省钱“狠手”,王亚丽也犯不着去“团契”里蹭饭吃;不用蹭饭省钱,也就不会跟岳晓芬产生交集,纵然同样会发生亲生母亲为钱给自己下套这样的事情,但男朋友那笔来路不明的资金,总归不会交到岳晓芬这样的外人手里;没有王亚丽忽然寄放来的巨款,岳晓芬“活下去”的渴望便不会被意外点燃,之后便不会上演“经不住考验”的吞款求生戏码,这个故事便也不会滑向“仙人跳”和“失手伤人”这样不可收拾的结局。
拉起这根线头,我们发现,小说的故事线索其实是非常清晰的。这场悲喜急转的“故事”,说到底是场错进错出的“事故”,它由一场场或大或小的“欺骗”甚至“诈骗”行为串联起来——这些眼花缭乱的“骗”里,有的情节严重、有的情有可原,有的成功实现、有的却彻底演砸了。这是一场披挂着悬疑(或者说“伪犯罪”)外衣的、细品之下颇感苦涩的黑色喜剧,一系列轻重不同、完成度也不同的欺骗行为,被黑色幽默的火焰焊接在一起,扭成了一只不规则的车轮;它捆绑着故事在北京东三环的柏油路面上以不可预料的轨迹剧烈弹跳,越是想停就越是停不下来。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石一枫小说所惯有的特点:它由某一股强劲的情节动力推动前行,看似单线迅猛的运行轨迹上,迸溅遗留下一连串嬉笑怒骂而又大可玩味的生活细节的铁屑漆皮。
3
同样为石一枫小说惯有的,还有故事背后的话题之“核”。石一枫常常喜欢在小说中设置一个坚硬的命题核心,这个核心就像是史蒂文斯放置在田纳西山巅的那只坛子,它使得凌乱的荒野纷纷向此倒伏。这一枚“核”,在《世间已无陈金芳》里是“人样”,在《地球之眼》里是“道德”,在《心灵外史》里是“信”,在《借命而生》里是“失败”。到了《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则是“亲人”——或者说,是一种情感安放的可能。
“亲人”,这原本是一个不存在疑问的名词,在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亲人”这一概念由血缘宗族关系绑定,在多数时候,它的意涵和边界并不比圆周率或勾股定理更加模糊。而一个不存在疑问的概念,不可能成为小说的核心——参照卢卡奇的逻辑,这样的概念倒是很适合作为史诗的核心。而石一枫之所以能够在这篇小说里将“亲人”作为关键词(它一再重复出现、甚至其规律性的出场往往会成为情节突转的暗示),显然是因为,在麦子店和王亚丽们的语境中,“亲人”这一概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异变、甚至能够成为其自身的反讽。
这种异变和反讽首先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先验的“亲人”,其意义稳定性已经在当代社会的语境中被消解了。故事里并非没有出现传统意义上的亲人,但这些传统亲人形象要么是不光彩的、要么是无能为力的。王亚丽的父亲一早便抛弃妻女跟着粮店的“野女人”跑路,只给原配家庭留下了对馒头大饼的深深恶意。母亲倒是原封未动地守候在老家,可惜已变成了吸血鬼般的形象:平日里索要钱财扔上牌桌不计较也罢,但一来二去把女儿在拆迁房上的名分都算计走,这就有些过分了。对于岳晓芬来说,“亲人”的确从来不曾变为不光彩的角色,然而在先天性心脏病的巨大治疗费用面前,她还是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即便亲人的感情是无价的,但在明码实价的存活成本面前,“无价”几乎就真的变成最字面意义上的“无所价值”了。
“归根结底一句话,王亚丽算是没家了。”更悲凉的是,在这样的结果面前,甚至悲怆也渐渐平息,“取而代之的只是心酸”——在王亚丽的潜意识中,这样的结局似乎是注定的,甚至说,是其实早已完成的事实。于是接下来,王亚丽们只能在变幻不定的陌生人社会中,摸索着寻找新的“亲人”,或者说“亲人”的替代物。这个话题就有些太大了,它几乎涉及到现代性语境下传统社会结构的整体性瓦解及其重构。我们在此就先仅围绕故事本身来讲吧。不得不说,王亚丽的“寻亲之旅”是有所收獲的,即使这些收获来的“亲人”们看起来多少有些奇形怪状:例如把辱骂作为感情表达方式的男友“果粒橙”,以及看起来让人琢磨不清的岳晓芬姐妹。然而,也正是这些被现代意义上的充分理性个体所选中认定的“亲人”,最终把彼此打进了命运的死结:所有的欺骗与伤害,无不是因信任和自以为稳妥的安放而来,假如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人将别人认定为“亲人”,那么这个欺骗套欺骗、事故接事故的故事,根本就不会出现。
有时候王亚丽的脑中也会忽然升起迷惑:“他怎么就成了她的‘亲人?就因为他在出租房的沙发上把她给办了?”
想也是白想,问也是白问。说到底,她和他们,岳晓芬、“果粒橙”,还包括一楼的房东大爷和二楼的团契成员,都需要温暖、需要信任、需要“亲人”、需要找一处地方来安放自己的心灵。为此,王亚丽和她身后那些站在故事里的人,寻遍了麦子店、寻遍了北京、甚至有可能寻遍了他们所能抵达到的世界,答案却是:这样的地方,没有。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阅读《玫瑰开满了麦子店》的时候,会不断地想起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都是关乎某种彻骨的孤独,《一句顶一万句》告诉我们的是“失语”,一个人耗尽一生都找不到自己寻找的那个词、那句话;《玫瑰开满了麦子店》告诉我们的却是“语失”,我们谁都知道那个词、那句话,只是一经说出,它的意义便涣散在了风里。
就像那个“印在画儿上的干瘦的外国男人”。那是他第一次在王亚丽的心中燃起希望的火焰:那一天,王亚丽坐在马桶上,母亲——那已然失效的“亲人”——正从听筒里倾泻出令她心灰意冷的聒噪。这“男人”掉在地下望着她。或许有一瞬间,她以为那是一种新的可能,一个可以安放在胸口的、略带羞涩甚至羞耻的秘密,即便这秘密、这信任、这托付,从一开始就无关宗教,而仅仅关乎食物、照顾以及人与人最简单安全的相处。
这奢求自然破灭了。但在破灭之中,也未尝找不到暖与光明的影子。小说结尾处,关于房东老头形象的兀然反转是否合理,我们暂且不论,照片上的女孩、岳晓芬和王亚丽的瞬间错觉重合,终究是动人的:“本来是不相干的人,却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有了关系……(她们)在错觉之中重合,又在错觉之中分开,从三个人变成了一个,又从一个人分成了三个。”王亚丽,这个倒霉透顶的平凡女孩,此刻竟成为了伟大而甜蜜的幸存者。这是穷途末路之际的奇幻抵达,是一种在坠落中完成的仪式性超越:在生活那恶作剧般的谷底,在头破血流跌折了腿、从肉体感受层面进入了“虚无缥缈”之境的王亚丽,竟然看到了她追寻已久的景象——
“那是她所从未见过的沙仑的玫瑰,开满了麦子店。”
【作者简介】 李壮,青年评论家、青年诗人。1989年12月出生于山东青岛,现居北京,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有文学评论及诗歌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方文坛》《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作品入选多种选本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曾获《诗刊》陈子昂诗歌奖2018年度青年理论家奖、丁玲文学奖、长征文艺奖等。出版诗集《午夜站台》、评论集《亡魂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