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太阳
2021-05-14林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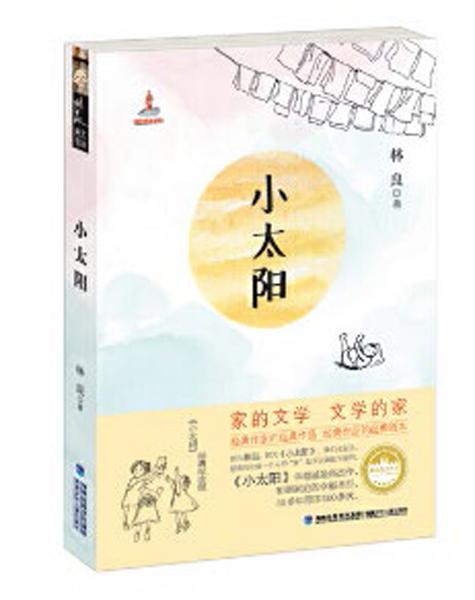
图书簡介:
一对父母、三个女儿和一只狗——一个平凡的家庭,在林良浅白、幽默又充满感性的笔触里,成了风靡台湾文坛数十年、历久弥新的《小太阳》。《小太阳》再现一个平凡家庭十五年的日常生活,从首篇到末篇,相隔十四年。这是一本散文集,也可视为一本散文体小说。全书处处可见令人莞尔的神来之笔,平凡里见真情,淡泊中有深意,是读者心目中永远温暖的光源所在。
一间房的家
窗户外面是世界,窗户里面是家,我们的家只有一个房间。我们的房间有两道墙。第一道是板墙,上面裱着一层淡红色的花纸,那是特为我们的洞房花烛夜布置的。这一层墙纸虽然已经褪了色,但是它曾经映过花烛的金光,使房间比独身时代显得温暖。第二道墙是家具排列成的圆形阵地:床、衣架、缝衣机、茶几、藤椅、柜子、书桌。房间的中央是我们的广场,二尺见方。我们不能每天在家里老站着或者老坐着,我们要走走,走动的时候就专靠这一片二尺见方的广场。
下班以后,我们从街上走回来,我们走过一座一座的建筑物,然后拿钥匙,开了锁,推门一看,每次我们都觉得家这么小!我们站在广场的中央,面面相觑,广场已经满了。
我们费过很多心血来布置这个房间,对待这个房间好像对待一个孤儿,既然它在这个世界上是这么凄苦可怜,那么就只好用我们的一点热情来补救它一切的缺憾。我们在窗户格子上添一层绿油漆,窗玻璃上贴着雪白的窗纸,多多买镜框,挂几张颜色鲜艳的生活杂志插图。我们花三百多块钱给它钉一个全新的天花板。总之,我们尽我们的力,尽我们的钱,呕出我们的心血来装扮它。我们像贫寒家庭的父母,因为不能供给自己的儿女享受童年应有的衣饰和欢乐,就竭诚献出他们所能有的爱!
我们并肩环顾这个五光十色的小房间,觉得它装扮得过分,但是值得怜爱。就只有这么一间了,能多疼它一点就多疼它一点吧,溺爱也不再算是过分了。
新婚之夜,我们听到邻居在炒菜,胡同里两部三轮车在争路,宿舍里的同事在谈论电影、宴会、牌局和人生。我们惨淡地笑一笑,知道房子太小,环境太闹,此后将永远不能获得我们梦寐中祈求的家的温馨和宁静,但是我们没有怨恨。即使它只是一个小小的薄纸盒子,我们两个人总算能够在一起了。
我们要做饭,就在公共宿舍的篱笆旁边搭了一个更小的厨房,像路边卖馄饨的小摊子。我们在那边做饭,端到卧室来吃,这样就解决了生活问题。我们有钱的时候,买两根腊肠,几块钱叉烧,在煤油炉上热一热,就放在书桌上相对细嚼。我们在闹声里找到只有我们两个人感觉得到的宁静,我们的耳朵也学会了关门。
下雨天,她到厨房去的时候,我心里有送她出远门的感觉。我打开窗户,可以看到她淋雨冲进厨房,孤独地在那里生火做饭。雨水沿着窗户格子往下滴,我的视线也模糊了。我想过去陪陪她,但是厨房太小,容不下我进去切菜。我在屋里写稿,等着等着,等她端着菜盘冒雨回到我们的家。她的衣服湿了,脸上挂着雨珠。总有一天,我们会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房子的,那时候她就不会再淋雨了。这个日子也许还很远,但是我看见她擦去脸上的雨珠,仍然在微笑,我就有耐心去等候那个日子。
我们的房间在宿舍的大门边,隔着板墙是公家的厕所,窗下又是别人的过道。我们夜里常常被重重的门声惊醒,有时也为头上频繁的脚步而不能合眼,但是我们一想到我们的誓言:即使过一生贫贱的日子也不气馁。于是我们把手握在一起,不让哪一个人发出一声叹息。
最感激的是朋友们并没有把我们忘记,常常到这个小房间来探望。他们虽然只能贴墙挤在一把藤椅子里坐着,但是都有了对我们这个家的尊重。朋友们高兴我们已经建立了家,没有人计较它建立在多大的房子里。我们换衣服的时候,把朋友留在门外。我们有一个人午睡的时候,把朋友请在厨房里坐。但是我们一样邀朋友度周末,虽然吃饭的时候四方桌在小房间里堵住我们的胸口,拥挤得像一口小锅里炖四只鸭,我们仍然不肯让快乐从我们中间溜走。
我们夜里看到万家灯火,看到一个一个发出光明的窗户。我们把它比作地上的星星。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家,夜里也有灯光,我们的窗户也会发出光明,成为星群里的一个。这对我们是一种无上的鼓舞!
我们既然不和生命的长流分离,我们就已经满足。我们既然不能有一个像家的房子,就让我们尽心尽性爱这个只有一个房间的家吧!
小太阳
2月的雨,3月的雨,使我家的墙角长出白色的小菌,皮箱发霉,天花板积水,地上盖满一层访客的友谊的泥脚印。和平西路二段多了几个临时池沼,汽车过去,带着喇喇的溅水声。湿衣服像一排排垂手而立的老人,躲在屋檐下避难。自来水畅通了,因为上天所赐的水已经过多。湿淋淋的路人,像一条条的鱼,严肃沉默地从篱笆墙外游过去。
这是台北的雨季,是一年中最缺少欢笑的日子,但是我们的孩子却在这样的日子里出世。她已经在这潮湿的地球上度过十五个整天。她那乌黑晶莹的小眼睛,却还没见过灿烂的太阳、明媚的月亮。她会不会就此觉得这世界并不美?
我回忆那天,孤独坐在台大医院分娩室外黑暗的长巷里,耳朵敏感到可以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我看到长凳上那些坐着等候生男生女消息的丈夫们,我觉得他们是乐观而强壮的。他们用不着分担太太的阵痛,他们享受这种上帝赐给男人的福分,并且还要挑剔,希望女孩子都诞生在别人的家里。跟他们比较起来,我是悲观而软弱的。虽然美丽的护士劝我离开占用了一整天的长凳出去吃一顿晚餐,但是我匆匆去来,似乎花钱吃了一肚子干涩的旧报纸。我在祈祷,偷偷画着十字。我想到夏娃把智慧之果放到亚当嘴里,上帝怎么诅咒那个爱丈夫胜过畏惧上帝的妇人:“我必多多增加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我多么害怕。
于是,我回想我们恋爱时候怎么试图瞒过一些多年的朋友,偷偷安排每一次的约会。我又想到婚后那种宁静的日子,我在写稿,她轻轻从背后递过来一杯热茶,宽容地给我一根她最讨厌的香烟。我想起我们吵嘴的时候,我紧皱的眉,她脸上的泪。我又想起我们欢笑的日子,在书桌上开菠萝罐头,用稿纸抹桌子。她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我也成了她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分娩室的门把我们隔开了。
我听到分娩室里有许多痛号声,我把每一阵心碎的呼号都承担下来,当作是她的。每一个新生婴儿的啼哭,我都希望是她脱离痛苦的信号。长凳上只剩我一个人了,我在恐惧里期待着。最后,护士推过来一张轮床,从我身边经过。她宁静地躺在床上微笑着,告诉我:“是一个女的,你不生气吧?”我背过脸去,热泪涌了上来。
我们的孩子就这样来到世上。她有她母亲的圆脸,我的清瘦,但是在我们心里,她已经很美啦,我们不敢要求更多。我们在雨声中把她从医院接回我们的家,一个潮湿狭窄的小房间。这个小小的第三者似乎一生下来就得到父母的钟爱,在她撅着小嘴唇甜蜜睡觉的时候,在她睁开乌黑的眼睛凝视灯光的时候,在我们发现她脸上有颗小黑痣的时候……那种生活的温馨!
但是她也给我们带来现实的生活问题。她的小被窝里好像有一部小印刷机,印出一份一份浅黄深黄潮湿温和的尿布。我们一份一份接下来,往脸盆里扔。因此,阿钏的眉头皱了,阿钏的胳臂酸了,阿钏的脾气坏了。她的印刷機使我们的临时佣人吃不消了。
我们的卧室开始有钉锤的响声,铁丝安装起来了,一道,两道,三道,四道,五道,六道。她的尿布像一面一面雨中的军旗,声势浩大地挂满一屋。我们在尿布底下弯腰走路。邻居的小女孩来拜访新妹妹,一抬头瞧见那空中的迷魂阵,就高兴得忘了来我家的目的。书桌的领空也让出去了,我这近视的写稿人,常常一个标点点在水上,那就是头上尿布的成绩。
一切都在改变,而且改变得那么快。我们从前那种两部车子出门、两部车子回家的公务员生活乐趣被破坏了,但是我们却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补偿。我们可以捏捏婴儿的小手,像跟童话里的仙子寒暄,可以抚摸她细柔漆黑的发丝,可以看她在澡盆里踩水像一只小青蛙,可以在她身上闻到婴儿所专有的奶香味儿。在她那一张甜美的小脸蛋儿前面,谁还去回忆从前的旧乐趣?
这小婴儿会打鼾,小嗓子眼儿里咕噜咕噜响。她吃足了奶会打嗝,会伸个懒腰打呵欠,还会打喷嚏。我们放在床头的育婴书上说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享受她给我们的一切声音,这声音使我们的房间格外温暖。我们偷看她安静时候脸上的表情,这表情没有一丝愁苦的样子。
她占用我们的半张床,但是我们多么愿意退让。她使我们半夜失眠,日间疲惫不堪。我们却觉得这是人间最快乐的痛苦、最甜蜜的折磨,但愿不分昼夜,永远紧紧拥她在怀里!
窗外冷风凄凄,雨声淅沥,世界是这么潮湿阴冷,我们曾经苦苦地盼望着太阳。但是现在,我们忘了窗外的世界,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小太阳了。小太阳不怕天上云朵的遮掩,小太阳能透过雨丝,透过尿布的迷魂阵,透过愁苦灵魂坚硬的外壳,暖烘烘照射着我们的心。
我多么愿意这么说:我们的小太阳不是我们生活的负担,她是我们人生途中第一个最惹人喜爱的友伴!
寂寞的球
对她来说,两个姐姐几乎等于是“上一代”。年龄跟她比较接近的二姐,比她大两千一百九十多天。大姐是她眼中的“彭祖”,比她大了两千九百二十多天!玮玮觉得寂寞,是必然的。
她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台上玩那四只嵌磁铁的小“亲嘴狗”,全神贯注,一声不响。有时候我走过她的身边,她会抬起头来,很客气地跟我笑一笑:“我在玩儿它们。”
“好玩不好玩?”我忙着别的事,但是也不能不像“柴油特快”勉强在小站停车那样,站住,跟她寒暄一句。
“不好玩。”她很老实地回答,“你现在有没有时间?”
“没有。”我用有急事待办的神气回答。
“再见。”她说,又低头去玩那四只“亲嘴狗”,摆个南北向的一字长蛇阵,然后拆散,改排东西向的一字长蛇阵,然后拆散,又摆了个南北向的一字长蛇阵……
在感觉上,我和太太总认为樱、琪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同伴,四个人共同经历过种种人生的“新境”,四个人在一起“话旧”“话新”的时候,情绪都相当热烈。这种情形,对玮玮形成一种精神威胁,使她有“参加不进去”的感觉,因此她从小学会了一个真理:攻击就是“存在”。
在联合国里,小国的代表必须不停地发表尖锐苛刻的言论,要大量运用“蛮不讲理”或“强词夺理”的技巧,然后大国才会把他“当作一回事”。玮玮为了使人把她“当作一回事”,也有这种“攻击倾向”。
在她落寞、沉默的时候,大家心里的想法是:“她多么正常啊,多么上轨道哇,多么有秩序呀!”大家心里都非常“庆幸”,认为玮玮是一个好孩子——一个无声无息、等于“不存在”的好孩子。大家对玮玮的期望早就是这样:不要打搅任何人。
可是玮玮也是“人”,并不是一个矮凳子,或者一座台灯。她也需要别人的关心。如果人人都认为不跟她接触就是一种最值得维持的关系,她怎么能忍受!当然,她只有攻击。
常常在我专心写稿的时候,她忽然出现了。
“给我两张纸!”她说。
“去跟妈妈要去。”
“我不要,我要跟你要!”
“你没看到我没工夫?”
“给我两张纸!”
“你到客厅去玩好不好?”
“给我两张纸!”
“你到底想干什么?”
“给我两张纸!”她说。
我不得不打开抽屉,很不耐烦地递给她两张白纸:“好,现在回到你的书桌上去画去。”
“我不要,我要在你这里画。”多使人气恼。
“好。”我说,“你在这儿画。我到你的书桌上去写。”
“你到哪里,我也要跟到哪里。”她说。
“你快惹我生气了。”我警告她。
“那么你要跟我玩!”
“我怎么会有工夫跟你玩?”
“那么我就要在你这里画。”
就在两代的感情开始恶化的时候,妈妈来解围了。妈妈把这“寂寞的球”接了过去,安置在厨房里——仅仅是安置,因为妈妈正在那儿当“炒菜的机器”。果然再过不久,那部“机器”怒吼了:“鱼还没剖肚怎么就扔进锅里?走开走开,快走开!”
过了不久,“机器”又怒吼了:“别拿,那是豆腐。你看,完了不是?一块豆腐完了!”
隔室有椅子向后推的声音,樱樱站起来了,她到厨房去接“寂寞的球”。她很像老师招呼小朋友:“玮玮乖,到樱樱这边来,看樱樱在这儿做功课。”玮玮一向喊大姐樱樱,大姐对她也自称樱樱。樱樱很失策地把“寂寞的球”安置在书桌边。
“樱樱!”
“哎。”
“樱樱!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哎。”
“你知道我梦到什么了吗?”
“哎。”
“你猜。”
“哎。”
“我梦见一张纸。”
“哎。”
“樱樱。”
“哎。”
一边看课本、一边不停地“哎”,从学习的观点看,我对樱樱的分心觉得有点儿不安。玮玮从“得不到关心”的事实来看,对樱樱的“分心”有点儿愤怒。
隔壁房間里有一种不祥的寂静。
“玮玮!”樱樱拍案哭喊。
“什么事?”我像防盗铃那么迅速地“反应”起来。
“她她她,我的大字本完了!”樱樱悲声回答。
像警车那么快的,我走进樱樱的卧室。她的书桌上有墨水汇聚成的小池塘。樱樱含泪。玮玮像西部的快枪手那样,在闹事以后,摆出“这纯粹是为了自卫”的神气,冷静地看着我。
家庭里有惯例,我把玮玮带到客厅,让她“静坐思过”。不过近来她对“静坐思过”已经有反感,认为那是对她最大的侮辱。只要我一走开,她马上就到处漫游,并且毫不思过。我也不敢太坚持,因为她一切的“过”,实在都是“父之过”。
果然,不久,她因为三处无法容身,就大胆闯入虎穴——二姐的房间。一个人如果不是寂寞到极点,是不会去找仇人下棋的。
玮玮被琪琪“规定”不许喊琪琪“琪琪”。琪琪因为在六岁失去“老幺”的权杖,四年来一直力图“恢复”。现在家里形成一种“有两个老幺”的局面,一个大老幺,一个小老幺。小老幺一定得喊大老幺“二姐”,不许喊“琪琪”。
“二姐!”我听到玮玮像在办公室门口喊“报告”那样谨慎地说。
“干什么?”这是二姐的“优势的口气”。
“我想进来。”玮玮试探地、小心地说。
“进来就进来吧,我又不是猫。”
“小老鼠”迈着轻快的脚步,跑进二姐用功的房间。
“二姐,我来告诉你!”受到了鼓励的“老鼠”,挨到“猫”身边,“我昨天梦见一张纸。”
“没有意思。”
“我不跟你玩儿了。”
“你最好别跟我玩儿。”
“我要去告诉爸爸,说你欺负我。”
“不许走,给我站在这里!”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玮玮逃出了虎穴。这就是她有名的“落荒而逃”,跟她的“静坐思过”齐名。
玮玮在最需要人陪伴的年龄,偏偏遇上家里的大建设时代,个个只顾埋头努力,无法分心。对玮玮来说,这真是她童年的“冰河期”。她的“家”是由一个“在书堆里露出鼻尖和笔尖的爸爸”、一个“忙个不停的八臂妈妈”、一个“端书凝神念念有词的樱樱”、一个“不声不响拿钢笔在纸上刻字的二姐”,还有她自己,共同组成的。她努力,想破坏这个局面,因此天天有小“冲突”发生。
也许她是对的。因为她是刚从天国来的,她知道亚当、夏娃所住过的伊甸园并不像家里这样紧张。
同样是“偷”,为什么“第一对夫妇”偏偷智慧之果?偷“时间之果”不是更好吗?大概玮玮所抗议的,也是这件“无法挽回的往事”吧。
停电五十小时
那天因为艾尔西台风扯断电线,这个城里许多地方都停电。住在城市里的现代人,都知道停电有一种美趣。烛光代替了俗气的电灯。一家人在烛光下,因为它的照明圈有限,所以更容易紧紧挨在一起,格外亲热。一个人有事要离开烛光的照明半径,一家人就用送行的眼光目送他走入黑暗中。听到脚步声响,大家都忍不住抬头睁眼,在黑暗中搜索。忽然眼前一亮,一张亲人的脸,迎着烛光,又回来了,大家让出位置,邀“回家”的亲人入座,亲切地探问烛光外黑暗世界中的情况。
“七姐妹怎么样?”
“我把鸟笼提到洗澡间去了。”
“刚刚听到哗啦一声,那是什么?”
“大概是邻家的窗玻璃破了。”
“除了那一块洋铁片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落到咱们院子里来了?”
“吹来一个大纸盒!”
大家安详地笑,轻轻地谈。房子成为“外面的世界”,真正的“家”却在烛光里。
家总有家事。要铺床,烛光到床边,一家人也到床边。烛光到第二张床边,一家人到第二张床边。第三张。第四张。
洗碗,烛光到厨房,一家人也到厨房。龙头滴着水,这是停水的预告。没有瀑布,也没有河流,只是水滴。第二天会是一个“很干”的日子,不过没有人去担忧。很难得有这样的日子:爸爸秉烛,妈妈洗碗,三个孩子看。
一家人乘一艘发光的小船,在黑海里航行。烛光是很美的,烛光是很温暖的。
小船上的乘客,一个一个离船登岸,到“床岛”去睡。我,小船的水手高举蜡烛,孤孤单单,摇着空船,回到自己的无人岛。我跳上床,对准烛光,噗!烛灭了,全家都在黑暗里。
铜鼓手在屋瓦上不停地敲鼓点子,节奏很快。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大风,像懂得气功的少林寺大和尚,对院子里的圣诞红发出一掌,再发出一掌,圣诞红的骨头断裂。
我在黑暗中静听屋外的“破坏”,静听那个穿着袈裟的大和尚,呼呼呼,来回走动。
这真是最奇特的一夜,跟我的“夜的定义”完全不相符的一夜:没有那一杯茶,没有那一支笔,没有那一叠稿纸,没有那几本书。
我第一次练习不看书睡觉。那是很难的。不过我并不担心失眠,因为我对睡眠,债台高筑,只要落在它手里,它是不会放过我的。完全的黑暗是很可怕的,它使我对睡眠失去抗拒力。
一个喜欢想的人,正好可以利用宁静的黑暗,享受常人所忽略的一种享受:恢复对人间的真正的陌生,恢复一个人的真正的孤独,然后用感激的心去品味人间的无法否认的温暖、朋友的无法否认的温情。
我跟任何人实际上是完全不相干的。人在本质上本来就是完全孤独的个体。可是我所得到的早就超过了一个“陌生人”所应得的,甚至连这个应该是孤独的人感冒了,都有人眼中露出诚恳的金光,为我介绍一种永远不灵的特效药。
我又想到另外一种不幸的人,怕承认个体本来就是孤独的。在心理上,他是一个暴君。他要求别人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他不管别人需要不需要,全凭自己的需要去拥抱人。他告诉那个被拥抱的人:“在你被拥抱的时候,你心中应该充满感激。”然后又说:“现在,你应该拥抱我,作为报答。”
他发现许多被拥抱的人都不回报,体会到另外一种意味的孤独,带着恨意的。
一个人应该对别人好,也应该感激别人对他好,但是不管他费多少心机,尽多少力,他无权要求别人应该对他好。
爱是个体发出的金光,爱是不需要回报的。爱不是交易,不是生意。需要回报的爱,附有借据,别人不照付利息,或者过期不还,就会由爱转恨。
爱像百万富翁在直升机上撒钞票,谁捡到就是谁的。如果这些钞票都是要归还的,他何必多此一举?他有什么权力折腾人?
有许多妄谈爱的人,其实都是心胸狭窄的放高利贷者。这是我们应该留心的。
“充满感激的孤独”,这是我所想的。
我不能想更多,因为睡魔捉住了我。
这是第一夜。
第二天,还是风,还是雨。上班的时候并不觉得有异,玻璃楼的光线不会使人看不清稿纸的格子。回家,总觉得眉毛像屋檐,遮住光,看什么东西都有光线不足的感觉。家里没有灯。
初次感觉到夜进屋子里来。从前,夜是只到窗外、只到门口的。家里有灯。
都市人在黄黄的烛光下做事,因为原始的官能已经退化,身体容易失去平衡感,心情容易烦躁紧张。玮玮吃饭的时候,把一个调羹碰落地上。“岁岁平安!”
家的“舆论”开始尖锐化。
“今天晚上做功课怎么办?”樱樱说。
“今天晚上写周记怎么办?”琪琪说。
“我是小班,我没有功课。”玮玮说。她又说:“今天晚上看电视怎么办?”
烛光把每个人的鼻尖都照亮了。这些金鼻人看烛光都觉得可恨。
太太用炒菜锅煮饭。大同电饭锅在架子上赋闲。冰箱成为制造腐败食物的白盒子。电视机和电唱机,真正成为客厅的摆设。熨斗在玮玮的皱围裙旁边打瞌睡。电铃不响。斯诺,我们的已经长成“少年”的白狐狸狗,担任电铃的职务。
最使人心烦的是没有灯光。樱樱、琪琪坚持一定要做功课,“不然的话”,老师就会怎么样怎么样,她们说。
我走进风雨中,又买回来许多蜡烛。不久,每个“读书人”的书桌上都点上五六支,每个人的书桌都成了生日蛋糕。
我想起物理学的“烛光”(不是诗的“烛光”)。我想起“六十烛”“一百烛”。我想起如果真那么做,书桌上的场面一定很惊人。
我想起两千多年前的匡衡,他当宰相的时候,恐怕已经很“近视”了。
果然,太太反对孩子在几支蜡烛下查字典做功课。她认为那是一种最大的“不卫生”。可是孩子都表示不满。功课不许做,电视不能看,到底要她们做什么?她们说。
“在客厅里坐坐,或者站起来走走。”太太说。
孩子都到客厅去,坐着,然后站起来走走,然后坐下,然后又站起来走走。我知道这是一种抗议,白宫门前举牌子游行的那种抗议。
但是我没办法,都怪电。我也有自己的烦恼,晚上一定得赶完一篇稿子。我向太太声明,我写的一个字有字典注释的十六个字大,而且我是“早已经很近视”的了,所以她不反对,只是不断地给我添蜡烛。我在“十二烛光”下满头大汗写完我的稿子,鼻子也熏黑了。
从开始停电的那一个小时算起,到第三天晚上全屋雪亮的那个小时为止,我家恰好停电五十小时。在电灯下写这篇追记,记忆有些模糊。如果改用烛光,成绩也许会好一点。
金色的团聚
每天的黄昏是家里的黄金时刻。想到夕阳的光辉所给人的金色的幻觉,每天黄昏一家人的团聚,真是“金色的团聚”。
在朝阳升起的时候,老大和老二从她们的双层床爬出来。老大住楼上,老二住楼下,孩子们是这么“称呼”她们的小鸟窝的。那张双层床,是家里的小公寓。虽然夜里都点过眼药水,但是小孩子像小鸟,每天早晨睁眼是一件重大的事。两个孩子在还没走到洗澡间以前,总是睁不开睡眼。正像老三所形容的:“她们的眼睛有点儿瞎。”
两个瞎人把双手当触须,摸进了洗澡间,“牙脸”(刷牙洗脸)了以后,眼睛亮了,三腳两步回到卧室,换上了老三所说的“学校的衣服”,像举重一样地把书包搬到饭厅。妈妈给她们预备的稀饭早已经晾在饭桌上了。一向喜欢静观、然后发表“文学的观感”的老三,说她们的“赶吃”是“把许多东西一下子装进肚子”。
就在姐妹俩忙着往肚子里装东西的时候,妈妈的双手像鼓霸乐队的鼓手一样忙,忙着给两个偏食的孩子装饭盒。
时钟的长针一走到表示“动身”的罗马数字上,孩子们都像挨了一鞭,跳起来,抓起饭桌上的“抹嘴毛巾”,在嘴上由左到右,由右到左,意到笔不到地各写了一个草书的“一”字,然后像童子军露营似的,背起“三百斤”重的书包,提起妈妈苦心经营的饭盒,夹着讲义夹子,抓起“防变天”的薄夹克,两个样子很笨重的小瘦子,头也不回地往门外冲。
“连‘下午见都不说了?”
“下午见!”
每天早晨分手的时候,两个小都市人总算没忘了跟父母道一声“告别的招呼”,虽是被动,却值得原谅,她们也是“赶时间的人”。现代人虽然有电话那样方便的“说话工具”,但是都忙得没有时间说话。两个小现代人当然也不能例外。
孩子们走了以后,接着,孩子们的妈妈的“紧张戏”又上演了。她一方面要忙自己的梳洗和早餐,一方面要招呼“不知光阴似箭”的老三慢吞吞地吃早点,一方面要催我这个“坚决反对每分钟心跳超过六十九下”的新哲人快拿报纸进厕所,一方面还要去市场买“怎么今天又吃这个”的菜。一共有四方面,四方面一夹攻,心理卫生学者所说的那些“风凉话”,都成了“废话”。她的脾气表现得稍微有点儿急躁,她的内心可能已是十万分地急躁。跟时钟的长针赛跑,长针总是赢的。
我对钟从来没有好感,也不承认发明钟的人对人类有什么真正的贡献。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发明另外一种“比它更能造福人类的代替品”以前,只好暂时由它胡闹。胡闹是胡闹,也不能完全不加以控制。我的方法是分解它,对它实行“科学管理”,例如在每天早晨上班以前仅有的四十八分钟里,我规定了该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最慢时间”:刷牙一分半钟,洗脸两分钟,刮脸四分半钟,梳头一分半钟,在“化学便盆”上看报二十五分钟,吃早点十三分钟,穿皮鞋半分钟。事实上,每一个项目都还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因此我能在钟的控制下获得休息。我控制了控制我的东西。唯一的遗憾是我为了这样做,不得不不停地看表。看表使我紧张。
夫妇两个,饱受时间折磨以后,好歹总算出了门,上班去了,到另外一个“更使人紧张的地方”去工作去了。这时候,所谓“家”只是一个两岁半的老三和一个阿兰罢了。
每天早上,“家”就是这样被时间拆散了。如果有人偏找这个时间给“家”下定義,家就是孤儿院。
有聚有散,这是悲观人的看法。如果我们从相反的方向看过来,旧聚散了,新聚又形成,散不尽,聚不完,人生总是那样热热闹闹的。看懂这个道理的人,都明白宇宙生生不已,想寻觅一点“凄凉感”,也并不很简单,例如每天黄昏那一次金色的团聚,就是很好的例子。
夕阳把出墙的树梢染上赤金色,屋檐、屋脊都滚上一道灿烂的金边。傍晚的风来摇屋角的铁马。阿兰出来浇花。老大、老二,也背着“三百斤”重的书包回家了。书包也很可能照到夕阳的光。那么,用现代诗人那种“跳接得很厉害”的描写法:两个小仙子背着金色包袱踏上了归途。
寂寞得以自言自语来排遣日子的小老三,总算下了“独语”课,上前去致欢迎辞:“你们这两个小家伙回来干什么!”上前去扯她们的衣服;上前去接她们的饭盒;上前去抱她们的书包,“重”得跟书包一起坐在地上。三个孩子像三只小狗撒欢儿,也会笑了,也会闹了,也有力气斗嘴打架了。时间暂时释放了她们。
不久,妈妈也回来了,尽管一天的劳碌很可能已经在她脸上刻上了一道皱纹,但是现在她用那道皱纹来笑。每一个孩子都想把这“最长的一日”的日记用嘴写出来给妈妈听。三个孩子有三大篇,加上妈妈自己的一篇,用孩子的数量词来形容,真是“四长的一日”!
最后回家的是一家之主,因为回家最晚,所以不是冠军,不是亚军,算是“末军”,孩子们说的。父亲争夺战就在这个时候揭幕。我的耳朵已经习惯同时听三个(有时候是四个)人同时说话,同时知道三个(有时候是四个)人的话的内容;回答第一个人的问题,一手抚摸第二个人的头发,一手抱起第三个小人,眼睛跟第四个人笑。
厨房里传来饭香。大家把早晨所受的罪忘得一干二净,对于明天早上要受的罪也没工夫去多想。夕阳无限好,黄昏一刻值千金,这就是我说的“金色的团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