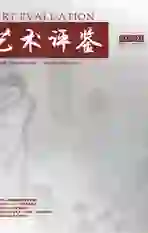浅谈中国新诗与现代歌词的审美差异
2021-04-02张咏民
张咏民
摘要:20世纪初,中国新诗与现代歌词相继出现。作为中国诗歌在新时期发展中的两种产物,他们有着许多相似点和共同性。然而,随着文学性和音乐性的对立的强化,新诗与现代歌词的差异变得日益显著,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审美特征,成为中国艺术百花园中两株光彩夺目、奇异芬芳的艺术奇葩。
关键词:中国新诗 现代歌词 审美差异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21)04-0039-03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往今来,在悠久深厚的华夏文明的润泽下,诗歌的发展犹如绵延不断的大河,奔流不息,源远流长。从先秦的诗经楚辞,到魏晋的乐府古诗,再到唐诗、宋词、元曲,历代杰出的诗词名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这些作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中国大地上盛传不衰,历久弥新,成为我们丰富灿烂的文化遗产。可以说,中华诗词不仅是中国文明史的积淀,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自豪与象征。
一般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诗歌。进入20世纪,随着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变革,中国文学开始了从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过渡,诞生了以自由为特点的新诗。与此同时,学堂乐歌的出现也开启了现代歌词的萌生与发展。分析两者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在某些时期他们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态。然而,由于新诗过多地强调它的文学性,而现代歌词突出表现它的音乐性,致使两者的距离逐渐拉大,其审美差异也变得更为清晰明朗。总的说来,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创作的目的上,新诗越来越倾向于为抒发诗人“自我”情感所写,而现代歌词则更多地表现在为某一社会群体而歌。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界“创作自由”口号的提出,诗人不仅在“选择题材、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上有了“充分自由”,而且在“抒发自己的感情和激情和表达自己的思想”方面也享有了“充分自由”。因此,在经过巨大变化后的新诗,其主流也逐渐开始走向“个人化写作状态”。诗人用自己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将新诗的写作放置在自身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发出完全属于自己的声音。翻看这一时期的新诗作品,我们会清楚地感觉到它主流的群体意识在日益淡化,相反其主体意识与个性化特色却变得突出、显著起来。如我们常见诗中《致XXX》一类的作品,多以抒发诗人个人情感为主。一般来说,诗人并不过多地考虑接受者,他们面向的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他所努力实现的是用怎样的方式来达到最大的表现“自我”的能力。
现代歌词作为面向大众的文学,始终以社会群体为主要服务对象,成为一群人或一类人的代言。歌词作者站在某类人的立场上观察世界,写的感情和体验不仅是每个词人个别的感受与独特的情感,还概括、表现了群体的、大众的情感,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审美形象中的交融与统一。试看《让世界充满爱》唱出了全世界乃至全人类的美好向往;《咱们工人有力量》展示了工人阶级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表达了战士心中深切的怀乡之情和崇高的责任感;《长大后我就成了你》饱含了人们对辛勤园丁的赞美与崇敬之情,等等。这样有着相同地位或相同经验的听众,就会深有同感,在歌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即而产生共鸣,自然,也会在那群人中间流传开来。这大概也就是为何现代歌词的受众者较新诗多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语言机制上,新诗主张一种新异独特、曲折雅致的陌生化,而现代歌词则追求一种雅俗共赏、明白晓畅的通俗美。
高兰曾在《漫谈诗的朗诵》一文中指出,“诗,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的艺术,而同时又是一种艺术的语言。因此,这不仅必须靠语言来表现,而且还需要用非常艺术的语言才能完美地表现出它自己包含的全部涵义,只是用一般的普通的语言那是不够的。”其实,在这一点上,新诗的读者更是深有感触。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在接受新诗的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同样的认知,即认为现在的新诗就阅读而言,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语言障碍,抑或有人干脆则说,现在的新诗根本就读不懂。透過这种直觉式的感受,我们不难发现,新诗作为纯粹的语言艺术,是以语言形象来诉诸于人的视觉的,读者可在“仰而思,俯而读”的反复过程中,逐步理解、深化、直至领悟其中的内涵。因此,面对新诗作品,就要求读者要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相当的艺术修养。
现代歌词隶属于音乐文学的范畴,它是通过乐曲的演唱方式,来诉诸于人的听觉。它不可能像诗那样可以反复吟诵,用较长的时间来领会其内涵,它要使听众在较短的时间内,入耳消融,一听就懂,所以,歌词的语言有别于那些深奥难懂、曲折艰涩的诗家语,它必须是我们生活中经常听到的大众语言,要做到精炼质朴、通俗晓畅。如:《篱笆墙的影子》(张藜词)、《常回家看看》(车行词)、《同桌的你》(高晓松词)等。试想,如果歌词语言没有了这个基础,那么写出的歌词就会书卷气太浓,书画腔太重,不易于接受、传唱。罗大佑在谈到自己的歌词创作时指出:“我宁可牺牲文学的深度,而要达到歌词清楚、明了,使观众一听就印入记忆,以后再听就会有响应。中国的文学已经抑扬顿挫得难以入歌了,如不注意口语化,过分堆砌词句,那简直是开观念的玩笑。”如此设身处地地为大众着想,必然会得到大众的回报,他的《是否》《童年》《真心英雄》等就是成功的例子。当然,追求歌词语言的通俗美,并不意味着要把作品写成大白话,顺口溜,让人感到平淡无奇,一览无余,要使歌词既容易让人听懂又很有韵味、很有琢磨头,像乔羽先生提出的那样,“寓深刻于浅显,寓隐约于明朗,寓曲折于直白,寓文于野,寓雅于俗”。这是所有词作者倾注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
因此,新诗与现代歌词语言机制的不同,也就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把歌词当诗来读的时候会觉得肤浅、无趣,而把诗谱成曲后演唱会感到别扭、臃肿。试看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的两首诗:一首是《白玉苦瓜》,写对故国的情思,其中有这样几句:“似醒非醒,缓缓的柔光里/似悠悠醒目千年的大寐/一只瓜从从容容在成熟/一只苦瓜,不再是涩苦/日磨月磋琢出深孕的清莹……”诗人用一只白玉雕成的苦瓜,来象征整个中国的文化和传统,然而,对这一主旨的领悟,却需经过一番反复体味、琢磨才能理解诗意,尤其像“大寐”、“深孕”这样的词语,很容易让听众产生误解,故而不宜谱曲演唱;而另外一首《乡愁》,用“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矮矮的坟墓”和“浅浅的海峡”四个新颖的比喻来抒发思乡的愁绪,取代了深奥难懂的语言,明白如话,一听即懂,具备了歌词所要求的通俗美,当然就会被作曲家谱曲而广为传唱。
再次,在作品的合乐性上,新诗的创作采取的是一种自律、消极的态度,而现代歌词的创作则表现出一种它律、积极的行为。
音乐性原是诗歌语言的一种审美特性,诗的可诵性、可歌性,都要求音乐性。正如明代谢榛指出的那样:“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其实,我们知道,在诗歌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早期的诗与歌词是同一的,都是可读能唱的。但是,在新时期以来的巨变中,新诗已不再能唱了,它创作的真正使命就是为了供读者读或口头朗诵,因此,新诗的创作遂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思想内蕴的深化和文字语言的讲究上,往往为了照顾文学性而削弱了音乐性,表现在内在结构,可以不受音乐的束缚,任自己的情感无拘无束的自由抒发,而表现在外在形式,可以不必押韵,可以毫无节制与规律地建行分节,甚至不加任何标点,再加上自由的体式和结构,使之缺乏一种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音韵回旋的韵律美,看来不顺眼,读来不悦耳,堵塞了新诗通向音乐美的道路。
相对于新诗而言,现代歌词是一种歌唱性的文学,它要为谱曲演唱提供最初的文本。苏珊格朗曾说过:“衡量一首好词的尺度,就是它转化为音乐的能力。”因此,作为音乐文学,现代歌词必须兼具文学性和音乐性。正如曾宪瑞先生所说:“一首好的歌词,应当带有音乐特色的文学美和闪耀文学光彩的音乐美,集文学美与音乐美于一身,使之谱曲能唱,离曲能赏。”这就是说,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要求歌词灵活运用写作技巧和修辞手法,增加其文学内涵;而从音乐的角度来讲,则要求歌词在创作中要時时、处处为音乐着想,不论内在结构,还是外部形式,都要体现一种不可或缺的音乐素质,如我们常说的押韵、节奏、声调等因素。由此,我们也可以解释,为何像《祖国啊,亲爱的祖国》(舒婷作)、《海的思念》(刘登翰作)、《阳光中的向日葵》(芒克作)等这些优秀的新诗如此感情充沛、意境深远,但不适于谱曲,而像《我爱你,中国》(瞿琮词)、《大海啊,故乡》(王立平词)、《月光下的凤尾竹》(倪维德词)等歌词虽然结构简单,语言通俗,却适于谱曲演唱,同时,也不失为一首好诗。人们常说,“好诗未必是好词,好词一定是好诗”,也许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歌词的音乐性与文学性在某些方面是有抵触的,如歌词的重复、反复与再现对于乐曲来说是必要的,但同诗家语的凝炼精警是矛盾的。因此,词作者在创作过程中,要清楚的歌词与新诗的差异,均衡处理好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关系,以使它们取长补短,达到和谐、自然。
最后,在题材的选择上,新诗越来越追求一种严肃性与深刻性,而现代歌词则呈现出一种多样性与时效性。
从新时期以来的不少新诗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往反映、歌颂时代与社会的作品有所减少,用正面的态度去写一些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品也不多见,当然,像那些卿卿我我的爱情之作和那些琐屑的小题材也不是诗人所钟爱的,而过多地着眼于一些宏大的题材,运用刚性的话语和深邃的思维方式,使作品产生某种新异的冲击力。如《我是铜像》(张毅伟作),“我是无名的铜像/我站在这里/袒露我的一切/面对太阳/面对辽阔的世界/表达我的真诚……”作品以铜像为象征的载体,紧扣铜像的象征意义,循序渐进,先抑后扬地阐述历史,发表见解。特别是最后一段诗人以充满信心的口吻坚定地表白:“决不轻率地说/我已经死去”,而要“在我最后的姿态里/还留着我执着的向往/因此,我活着/我站在这里”。由此,让读者在感受“铜像”精神的同时,坚定了信念,赋予了强烈的历史感、使命感和希望。类似地,《我们是一双眼睛》(牛波作)赋予了“眼睛”以深刻地人生意蕴:这是一双共创世界的眼睛,“景物分给我们一人一半/合起来才能组成完整的世界”。这是一双生命相结的眼睛,“一只眼睛陷入黑暗/另一只就要寻找两倍的光明”。这是一双灵犀相通的眼睛,“虽然我们永不相望/但却无时不在远方碰撞”。诗人在这双灵动的眼睛中,召唤着读者的伦理性关注和人格性感悟。
然而,新诗所弃的题材,正是现代歌词所坚守的。从对时代、祖国的深情颂歌,到对大好河山的激情讴歌,从雄壮的军旅歌,到缠绵的相思调,从豪迈的进行曲,到生活的小插曲,现代歌词的题材灵活多样,各领风骚。殊不知,随着传媒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现代歌词经谱曲演唱后,通过网络、广播、电视、唱片、音乐会等方式,已潮涌般地沁入我们生活中的各个角落,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各种不同题材的作品:像《爱我中华》《同一首歌》《爱的奉献》《好日子》《家和万事兴》《时间都去哪儿了》《从头再来》《十五的月亮》《当兵的人》《你笑起来真好看》等,都深受人们的喜爱。其中,数量最多的当数爱情题材的歌曲,如《月亮代表我的心》《涛声依旧》《最浪漫的事》等等,都被反复歌唱,即使让人感到有些泛滥,也还是乐此不疲。同样,现代歌词的题材在选择上还带有很强的时代色彩,例如《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江山》《不忘初心》等主旋律的作品正是在特定的时期“应运而生”。在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也会出现大量与之相吻合的纪念和庆祝歌词,如《党啊,亲爱的妈妈》《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相约九八》《为了谁》《雾里看花》《西部放歌》《天路》《生死不离》《脱贫宣言》《再一次出发》等,更是家喻户晓,久唱不衰。
总的来说,作为现代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产物,新诗与现代歌词虽然有着相似之处,但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构筑了各自不同的审美特征。它们就像艺术百花园里两株并肩生长而又花色迥异的艺术奇葩,以其鲜活的魅力和醉人的艺术芬芳,永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美的享受。
参考文献:
[1]苗菁.现代歌词文体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34-46.
[2]许自强.歌词创作美学[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