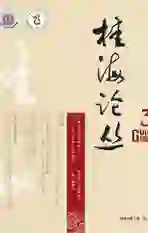百年红船的由来、本来与未来
2021-01-02肖纯柏
肖纯柏
摘要: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嘉兴红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把红船精神概括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之源和党的先进性之源。红船精神承载了中国共产党青春建党、志向建党、民主建党的文化基因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新时代“中国号”巨轮需要舵手领航,坚持党的领导,坚定共产主义航向,勇于自我革命,既往开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红船;初心使命;未来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1)03-0032-06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研究”(20JJD710008)。
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在世界政党发展史上,只有一个政党是在一条小船上诞生的,这就是1921年在嘉兴南湖红船起航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孕育形成的红船精神推动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乘风破浪,行稳致远。红船承载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昭示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只有不忘为民初心,牢记强国使命,中国共产党才能继续创造辉煌和奇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国共产党革命红船的由来
嘉兴南湖,以湖得名,以船盛名。南湖的色彩缤纷,由来已久。嘉兴南湖的绿林亭舍最早建于吴越时期,南宋始建烟雨楼。宋代以后,嘉兴南湖与杭州西湖、南京玄武湖并称江南三大名湖。近代,南湖渡船,碧水蓝天,自然与人文,一体而多色,既属风景名胜,亦为革命文化遗迹,是浙江和上海辛亥志士的重要活动基地。红船文化继承了辛亥革命精神,又发展了近代革命文化。何谓“革命”?革命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生生不息;革命是“革其旧制,催生新命”,革故鼎新。1905年和1907年,光复志士秋瑾两次到嘉兴南湖放鹤洲,与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褚辅成筹商革命大计。嘉兴有62人参加了光复会、同盟会,其中敖嘉熊1904年春在嘉兴东门外建立了浙江省第一个秘密革命活动基地“温台处会馆”,被陶成章称为推动浙江革命的第一人。龚宝铨与蔡元培、陶成章一道创立了光复会,是民国元老之一。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余孟庭等24人,都在嘉兴进行过革命活动。1912年10月,孙中山在南湖同有关人士畅叙后在烟雨楼前留影。1932年,韩国独立运动领导人金九来嘉兴避难,在南湖游船上召开韩国临时政府国务会议,商议抗日复国大计。
作为铭刻革命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印记的南湖游船,最引人瞩目、格外耀眼的景致,当属1921年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悄然闭幕,中国共产党由此诞生,这条小船因此有了一个响亮而永载史册的名字——红船,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源头象征。不仅其他政治力量沒有想到这条小船在短短二十八年后,会成为中国巨轮,即使当时的与会代表也未曾料到,开天辟地建立共产党,短短28年后会翻天覆地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惊天动地改革开放,感天动地老百姓跟党走、扬帆领航新时代。
毛泽东同志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就没有改变中国、造福人民、影响世界的中国共产党。南湖红船与俄国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渊源与共,同色湖天。1917年11月7日,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揭开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序幕,全球首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阿芙乐尔”号舰船因此被称为“苏俄红船”。
中共革命红船是在北京酝酿的。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最早在北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接触。中共革命红船其实是在上海“打造”的。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此后各地组织相继建立。1921年7月23日,13位中共一大代表和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在上海法租界李书城的寓所开会,中共一大开幕,张国焘为大会主席,主持了一大开幕会和闭幕会。中共革命红船最后是在嘉兴起航的。中共一大在1921年7月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法国租界巡捕程子卿带领警察搜查了会场,中共一大被迫休会。最早有人提议在上海换到其他地方继续开会,也有人建议去杭州开会。后来在李达夫人王会悟和邵力子(浙江绍兴人)的建议下,中共一大转移到嘉兴续会。嘉兴位于上海与杭州之间,上海到嘉兴的距离比到杭州更近,不到100公里,交通便捷。嘉兴毗邻上海而得风气之先,工商业也发达,同时小城不易引人注目,隐蔽安全。嘉兴是王会悟的家乡,由于王会悟是嘉兴桐乡乌镇人,如遇突发事件可通过熟人网络快速应对,应急能力强。值得一提的是,党的二大就是在李达、王会悟家里召开的,他们为了建党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九死一生,是党的一大、二大卫士。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从北京到上海再到嘉兴,风雨兼程。
为了减少风险,一大代表没有同日同时抵达嘉兴,而是由王会悟带领董必武、陈潭秋等人乘火车第一批到达嘉兴,提前做好闭幕会的准备工作。第二天,李达带领其他代表作为第二批与会人员乘火车到达嘉兴。王会悟去火车站接到代表们后,未进当时的嘉兴城,而是直接前往南湖的狮子汇渡口。大家先乘摆渡船到了湖心岛,登上南湖的烟雨楼,察看周边环境以防不测,然后通过拖梢小船,登上事先租好、后来被称为“红船”的游船。游船是一条单夹弄丝网船,雅称画舫。船身长约16米,宽3米,内有前舱,舱内有凉棚;中舱有方桌,桌有茶具,四周放置凳椅;房舱设有床榻,供休息用;后舱可做饭,小拖梢船可进城购物接人。一大代表在船中开会,备有麻将,如遇搜查危险,坐在船头放哨的王会悟以敲击舱门的方式提醒大家佯打麻将作掩护。
南湖红船上开会的一大代表共10人,即张国焘、董必武、李达、毛泽东、刘仁静、包惠僧、王尽美、周佛海、陈潭秋、邓恩铭,这10名代表于1921年8月3日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参加了一大闭幕会,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党的一大南湖会议。就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选举了第一个中共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第一个工作决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因此,红船也被亲切地称为“母亲船”。
二、中国共产党革命红船的本来
红船具有文化意象意义,象征舟水关系的革命航船,承载了中国共产党艰辛曲折的建党历史。以红船命名的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蕴含了丰富的党内政治文化。
一是南湖红船留下了青春建党的印记。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年纪轻轻就干大事,有些代表年纪轻轻就献出生命。参会代表中年龄最大者何叔衡是45岁,年龄最小的是刘仁静,为19岁,13位代表平均年龄为28岁。1921年建立中国共产党,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好历经28年,可谓青春建党、青年改变中国,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二是南湖红船留下了志向建党的足迹。13位一大代表全部都是知识分子,没有一个是工人和农民,也没有一个商人。1921年全国58名中共党员当中,有4名是工人,其他均为知识分子。当初他们都有很好的初心,视名利如浮云,使命高于生命,以忘我精神入无我之境,把中国共产党定位为“群众党”,而不是定位为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和狭隘的小圈子。他们在行动上是“先锋队”,胸怀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并脚踏实地、忠诚为民,不惧风雨,不怕惊涛骇浪,舍小家、顾大家、为国家,舍身忘我,扬帆远航。三是南湖红船还留下了民主建党的胎记。中共一大代表是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出来的。党的一大会议的最后一天,代表们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党主张。会议还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选举他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会议中,大家发扬君子之道和同志之道,党内互相称同志,不以职务论英雄,不以当官为荣耀,而以做事奉献为己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民主集中制为原则,以依靠群众、联系群众为依托,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民主性政党的伟大开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
南湖红船起航后,历经波折,从黄浦江到南湖,从井冈山到长江,从长江到黄河,再到鸭绿江,五湖四海的舟水文化涵养了中国共产党。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历史转折关头,情不自禁回望了党的起点:“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水上开的。”[2]1958年毛泽东到杭州时,专列经过南湖,他急令停车,没有让任何人陪同,独自走下火车,站在南湖东北侧,面向红船方向,深情凝思良久。近半个小时后,他才缓缓登上列车离去。毛泽东在沉思什么呢?面对中国共产党从当年的区域性政党转变为全国性的政党,从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艰辛奋斗的群众性政党,转变为掌握全国政权并要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毛泽东想到了建党的不易、执政的挑战和对未来的信心。是什么让1920年58名最早的共产党员走到一起,壮志凌云,救国救民?是什么让1921年13位党的一大代表在上海开群英会,相聚建党,开天辟地?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力量纷纷登台亮相,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是书生论政,意气方遒,又凭什么超过当时资格老、人数多、基础厚、影响大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实现惊天逆袭?更让人惊叹的是,中国共产党南湖启航后,一路遭遇暴风骤雨、黑云欲摧,队伍内部也出现迷茫、迷失,早退、掉队甚至背离,靠什么化险为夷、化危为机,获得持续发展的力量,积小胜为大胜,取得最后胜利?是“红船精神”让中国共产党如虎添翼,实现凤凰涅槃。
红船具有浓厚的象征文化意义,体现了从实物之船到意象的革命航船,再到抽象的红船精神的意象之美、奋进之美。从历史维度看,红船启航是党的建设的红色起点。“红船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是发展方向,是奋进明灯,是铸就在中华儿女心中的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3]此前,中国近代以来的政党政治一直未能实现人民解放和民族解放的崇高使命。中国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古国,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文明中断的大国,积淀了深厚的治国智慧和政治文明。但是到了近代,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由于缺乏先进的政治力量引领,未能吸收人类最先进的文明成果,因而逐渐落伍、僵化,最终落后挨打。红船精神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首先在于为中华民族提供了顺应时代潮流、勇立时代潮头的先进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与无产阶级运动过程的整体利益保持一致,“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作为崭新、先进的政治力量,与过去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以及其他政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和民族复兴为目标、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严格的纪律为行动准则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其理论的先进性、组织的严密性、政治理想的崇高性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崭新领导力量。这是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立党根基。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族复兴便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其一,“红船精神”蕴含的“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给中国政治道路增添了巨大的创造力,改变了过去保守落后的政治氛围。早期建党先驱和骨干人员,绝大多数是青年,敢闯且勇于革新,充满朝气活力,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尊重、对人民的深情,形成了既严肃又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二,中国共产党人在红船起航后,以超乎常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扑下身子走向基層,百折不挠克服难关,改变了中国过去一盘散沙的局面,把群众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在中华民族繁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创了政党骨干与群众长期保持血肉联系之先河,这是中国全新的政治面貌。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和坚强领导,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政党。孙中山领导的政党因为内耗不断、地方各自为政、军阀连年混战而无法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因而无法解决政治力量四分五裂的千古难题。同时,近代中国早期其他政党的党建工作不力,党内涣散,缺乏凝聚力,也缺乏生机活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最先进的政治力量,也是国家最高政治力量,党领导的以南湖为起点的革命之路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是实现共产主义和民族复兴历史使命的必由之路。由此,红船起航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红色起点,红船精神第一次把民族复兴的思想力量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之上,把领导力量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之上、把依靠力量建立在广大群众之上。历史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只能是空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上海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是党的全部历史的逻辑起点和中国政治道路的新起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力量、走向执政的红色起点。
小小红船,承载千钧,开启了跨世纪的航程。南昌起义失败后,周恩来乘小木船前往香港,转道播撒革命星火。红军长征,革命“红船”从江西于都河的渡口出发,此后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在大渡河脱险,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多次乘木船过黄河,与长江一带的新四军顽强抗击日军。1948年,毛泽东乘木船离开生活和战斗了十三个春秋的陕北,前往西柏坡,迎接新曙光。1949年,解放军将士以简陋的帆船,“百万雄师过大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迎来“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跨过鸭绿江,奋力抗美援朝,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强保障,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整整10周年,社会主义中国焕然一新,让人想起1921年共产党的“开天辟地”、1949年新中国的改天换地。当年诞生中国共产党的南湖红船已毁于抗日战火,荡然无存。为了还原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追根溯源,不忘走过的路,重建南湖红船工作摆上了重要日程。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委会在大量采访老船工、老渔民和老游客的基础上,仿制了大号双夹弄丝网船模型。经王会悟验看和中央审定,确认纪念船为中型单夹弄丝网船。据此,嘉兴有关船厂制作了中共一大纪念船,并绘制图纸存档。1959年10月1日,党的一大纪念红船正式下水,停泊于湖心岛烟雨楼畔。
红船之“红”,红在喜庆,红在本色,与红星、红军、红帽、红旗、红墙一道构成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图谱。作为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亲历者,董必武对红船有着特殊的感情。1964年,他登上重建的南湖游船赋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1985年初秋,邓小平欣然题写了“南湖革命纪念馆”的馆名。1986年1月,胡耀邦题写了“中共一大会址”。1986年4月,杨尚昆为南湖题写匾额“访踪亭”。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或瞻仰红船,或亲笔题词“沿着南湖红船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3],以“红船”与“航道”的象征语言,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绵绵初心。
2002年10月,成长于革命家庭、长期受红色文化熏陶的习近平同志,调任浙江后仅仅十天,就专程到嘉兴南湖瞻仰红船,并提出南湖是全国的南湖,红船是全国的红船,甚至应成为国外友好人士研究我们党史的基地。2005年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习近平同志率领浙江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来到南湖瞻仰红船,举行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专题学习会,提到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从祖国各地来到南湖,看一次展览,听一次党课,学一次党章,观一次专题片,瞻仰一次红船,重温一次入党誓词[3]。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从理论上第一次公开提炼和阐释了“红船精神”的丰富内涵,阐述了“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和党的先进性之源。他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3]这一论述填补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到上井冈山这段时期的精神空白,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共产党精神链条和谱系。“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精神和不忘初心的最早表达,同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艰辛历程,成为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宝贵精神财富。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他饱含深情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5]294“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5]294
三、中国共产党革命红船的未来
南湖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是文化概念;红船不只是一条物体的船,而且是一艘寻求民族复兴的船,是一艘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航船,也是拥有九千多万党员、承载十四亿多中国人民希望、未来要驶向胜利彼岸的“世界巨轮”。瞻仰南湖红船既是对慎终追远、寻根祭祖的文化继承,又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固本培元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更是对未来创造新辉煌和更大奇迹的豪情与信念。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南湖红船好比攻坚克难、吃苦在前的冲锋之舟,也是寻求民族独立、为民造福的普渡之舟,更是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造福人类的“诺亚”方舟。党在船上,船在水上,觅渡远航。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走得越远,初心不可渐行渐远;越是往前走,越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越要抓住不变的东西。一个党也好,一个党员也好,其前途命运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面对初心。面向21世纪,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治不忘乱、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时刻提醒自己不可“翻船”和“脚踏两只船”。船行万里,方向第一。大海航行要有护航手,更要靠舵手。无论遇到狂风骤雨,还是激流险滩,坚定正确的航向,顺應潮流并勇立潮头,不走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走适合自己又推动人类进步的中国道路。“船到中流浪更急”,只要保持定力,锚定崇高的理想目标,就会“乘风破浪会有时”“轻舟已过万重山”,最后“直挂云帆济沧海”“唯见长江天际流”。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当年的小小红船,如今已经成为拥有九千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未来还要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政党。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是一项极其艰辛的事业。今天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推进新时代的社会革命,努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新一轮的艰苦创业,也是新的万里长征,需要“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情怀,进行新的开天辟地。为此,党的“复兴号”巨轮需要依水行舟,风雨同舟,防范覆舟。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政治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红船启航是中华民族寻求站起来的政治转折点,从此民族复兴建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的政治基点上。中华民族将要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从有没有、饱不饱转向好不好,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关键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应对复杂挑战和不确定风险。为此,要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善于从“红船精神”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红船精神”是革命精神,也是自我革命精神。今天我们弘扬以“红船精神”为龙头的革命精神,要发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自我革命精神”,把握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以刀刃向内、自我纠错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担当祛邪治病、强筋健骨。这种自我革命精神是对红船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