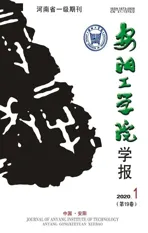豫剧《朝阳沟》的隐含话语
2020-12-26皇甫风平
皇甫风平
(河南工业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郑州450001)
《朝阳沟》是一部豫剧现代戏,初创于20世纪50年代末,以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主题,经舞台演出和修改完善之后,于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成戏曲艺术片。《朝阳沟》的创作年代正值文艺创作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这出戏的创作初衷,主要是配合并歌颂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作品刚一问世就好评如潮,当时的戏曲界权威报刊《戏剧报》发文指出:“这是一出充满了革命热情,紧密配合当前任务的好戏。它以知识青年参加农业劳动,进行思想改造的故事为主线,迅速及时地反映了我们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派崭新景象。”[1]这正是以政治标准对这出戏做出的评价。在当时,这类以演绎政治政策、歌颂新生活为目的的应景作品比比皆是,包括戏曲、电影及其他艺术形式。时过境迁,这类应景作品大都被人遗忘,而豫剧《朝阳沟》一直传唱至今,受到广泛好评,创造了戏曲现代戏历经60年仍盛演不衰的奇迹[2]。甚至,这出戏俨然已成为一种文化表征,当人们提及豫剧时,除了《花木兰》《红娘》《穆桂英》等古装戏,就是现代戏《朝阳沟》。
《朝阳沟》的成功,因素固然不止一种。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作品对“乡土情怀的拓展与提升”[3]、“主题积极向上、人物鲜活生动、故事平中见曲、讴歌时代精神”[4],等等,均是这出戏成功基本因素。但是,仅仅停留于此还远远不够,本文要分析的就是这出戏成功的深层原因。
一、《朝阳沟》与“仙女下凡”的故事原型
“仙女下凡”故事原型是豫剧《朝阳沟》若干隐形结构之一。
《朝阳沟》剧情相对简单,全剧共8场,中心线索是银环下乡。高中毕业生王银环到她的同学拴保的家乡朝阳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开始,银环对下乡一腔热情,但很快就遇到了一连串困难,尤其是母亲的阻拦,思想上发生动摇。后来,在村支书和群众的帮助下,在农村生产劳动过程中,银环对土地、乡村和朝阳沟产生了深情,认识到农村是知识青年贡献力量的广阔天地,并最终在朝阳沟扎下根来。无论是创作初衷,还是读者对作品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解,《朝阳沟》都是在表现新旧观念的尖锐冲突,是在展示社会主义新农民新的精神风貌,是在宣传与歌颂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政治主题。也就是说,《朝阳沟》的核心话语是政治,是政治教育。但是,如果脱去故事表层的外衣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部戏在政治话语外壳之下深藏着某种民间艺术话语,暗合了某种特定的民间审美心理。实际上,这部戏以民间熟悉的生活化语言,在讲述一个现代版的、现实版的“仙女下凡”的故事。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本质。同时,《朝阳沟》叙事巧妙地融合了政治话语与艺术话语,并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平衡点。毕竟《朝阳沟》是以政治说教为初衷的一出戏,政治话语贯穿始终。幸运的是,政治话语并不“过载”,而是巧妙地融入了一个民间易于接受的故事原型之中。
一个地地道道的知青下乡故事,为什么可以将其理解为“仙女下凡”的故事?原因很简单,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政治说教,将空洞的政治说教镶嵌在了某种大众能接受、又易于接受的艺术叙事之中。如果说主角王银环就是“七仙女”,栓保就是那个招来“七仙女”的穷小子董永。当然,《朝阳沟》故事不是神话传说,更不是把王银环等同于现实版的“七仙女”,而是说银环在与栓保的人物关系上具备了“仙女下凡”的叙事特征,这里指的是叙事学上的等同意义。《朝阳沟》被广泛接受也间接证明了这一判断。《朝阳沟》的主要听众是农民。而农民听戏,首先想得到某种审美享受。“仙女下凡”的故事通俗易懂,又最容易浮想联翩,已经深刻地植入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正如研究者徐冰所指出的那样:“银环的形象多少像是‘董永行孝型’故事中七仙女的现实版。城市女高中生虽然与农村的生活环境有距离,但还不至于高不可攀。”[5]
首先是空间关系上,银环所生活的大城市省会郑州与栓保所生活的小山村朝阳沟,有着明显的“等级”关系。其次是银环和栓宝所出生和成长的社会背景之间有较大差距。实际上,上述两点正是这出戏所竭力描写和证明的。作品通过“落后人物”银环妈之口,反复强调“城里”和“乡下”,并把二者作为对立关系。再次,作为高中同学,银环和栓保是平等或平行关系,但在下乡问题上,表现出二人的不平等的关系。很明显,二人关系中银环有“俯就”之势,而栓保多为“仰视”。正如银环所唱:“栓保你为留我,又批评又鼓励明讲暗求。”也正因为此,听说银环要来朝阳沟而没有来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景象”:“自从你们写信要下乡,朝阳沟这几天忙了又忙,老支书大会宣传小会讲,二大娘把红绿标语贴满墙,小妹妹一天村头接几趟,我的娘睡不着只嫌夜长,我的爹逢人就说有了希望。”如果这出戏像创作初衷所要表达的那样,仅仅为了迎接一个下乡青年,又怎样理解栓宝全家乃至朝阳沟全村轰动式的热烈景象呢?朝阳沟对即将到来的银环的反应已经远远超出合理限度,看上去也不太正常。更重要的是,银环的到来,已经不再是银环自己个人的事情,也不再是银环母女和栓保一家人的事情,而是整个朝阳沟的事情。
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作品依赖接受主体的积极介入,它只存在于读者的审美观照和感受中,受接受主体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结构的左右[6]。也就是说,接受者有权并且必然会对审美对象进行筛选、加工、过滤、扭曲等等。这也就是所谓的对艺术作品的“误读”,既包括有意识的误读,也包括无意识的误读。正是这种误读创造了“朝阳沟”。我们看到,这出戏所要表达的政治话语在听众那里已经被过滤得所剩无几,有些政治话语被过滤,更多的政治话语被加工、扭曲并最后误读成为一个易于听众接受的传统故事,即“仙女下凡”的故事。
《朝阳沟》已经传唱几十年,政治话语环境早已发生巨变,当年所刻意宣传的政治话语已经不为当下听众所熟知,或者说,当今的许多听众对“上山下乡”的理解已经非常模糊,可是,《朝阳沟》的魅力不减。显然,听众并不是想从中接受什么“上山下乡”运动的观念,而是想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当年的创作者也许不会承认这一点,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管创作者承认不承认,也不管创作者意识到没有意识到,都不妨碍豫剧《朝阳沟》在叙事学上和美学上符合这一点。
二、日常生活叙事与政治话语的“分裂叙事”
日常生活叙事与政治话语的“分裂叙事”是豫剧《朝阳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隐形结构。
《朝阳沟》创作于1958年,一场由工农业战线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迅速波及各个领域。文化部召开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工作会议,发出戏剧工作大跃进的号召,戏剧战线的“跃进”就此拉开序幕[7]。诞生于这个特殊时期的《朝阳沟》自然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正如当时评论者沈峣所说:“《朝阳沟》抓住了现实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青年知识分子劳动化、与劳动群众结合的问题。”[8]但是,如果豫剧《朝阳沟》只是一味地演绎某一政治理论甚至某一政策方针,那么它就不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朝阳沟》。如前所述,豫剧《朝阳沟》是一出很独特的戏,之所以成功,深层原因之一就是暗合了中国传统审美特征。这里所说的独特,意思是作者初衷要宣传“上山下乡”这一主题,而听众只管“误听”出一个“仙女下凡”的故事,出现了“你说你的,我听我的”的戏剧性分裂。这就是文学理论上所谓的作家的主观愿望和作品的客观效果并不总是吻合,甚至背道而驰。
正因为此,戏中出现了许多独特现象。比如,政治话语对日常生活的威胁,这尤其表现在剧中人物争辩时、意见不合时、劝导对方接受自己意见或想法时。究其原因是,政治话语“效果好”“见效快”,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不可争辩性。这是当时的特殊语境所造成的,只是《朝阳沟》中的政治话语相对要温和得多。下面举几个这样的例子。
银环下乡有些犹豫,栓保劝她,本来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因为两人毕竟是“恋爱关系”。而栓宝说的全是政治话语:“两条道路愿从哪条走,任你挑任你选我不强求。”“两条道路”在这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两种选择,也不是个人意志的选择,更不是银环是否愿意嫁给一个乡下人的选择。很显然,这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的选择:一条道路是响应号召,去农村接受教育,另一条则是贪图享受,留在城里。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话语,比我们现在所能理解的要严重得多。
银环“先斩后奏”,偷偷下乡,银环妈追到朝阳沟,要把女儿拖回家,拖回城里。银环妈进门先是遇到了栓保娘,后又来了二大娘。亲家相见立刻争吵起来,你来我往,不可开交,最后二大娘对银环妈说:“县长、省长、毛主席还看得起我们呢,你有啥了不起啊?”银环妈便无可辩驳,争吵立刻结束。这是整出戏政治意味最足的几句。下乡不久,银环思想动摇,栓宝眼看留不住她,就用其惯用伎俩:“你说过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你说的话讲的话,你一字一句全忘完,想想烈士比比咱,有什么苦来怕什么难。”银环深知其中的政治意义,当然不可以直面辩驳,只能巧妙地借用日常话语予以消解:“少给我来这套。”
银环动摇,借机自己母亲有病要离开朝阳沟。作为婆婆的栓宝娘挽留银环时,说出的却是这番话:“再大的能耐,也不能把脖子扎上。”这句话和她之前所说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没有农民来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遥相呼应。这些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话语与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老年农村妇女的身份并不相符。
即使银环母女之间,在关系紧张时,也会使用政治话语进行政治威胁,虽然比较温柔,却很有威力。银环下乡朝阳沟,银环妈追来,强求银环回城,母女二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银环唱的是:“在城里你也曾参加开会,听读报听宣传不断学习,全国人民都知道农业重要,为农业大发展谁不积极?”这不仅让银环妈有政治上落后的嫌疑,也让银环妈无法用正常话语辩驳,因为,政治话语是不可辩驳的。
硬的不行,银环妈就来软的。银环妈给银环写信,谎称自己有病,打算以此骗银环回家。收到来信,银环信以为真,回到城里的家。刚见到母亲,就发现了母亲的用意,于是母女二人就因下乡问题开始争论。开始的争论无非是些亲情和日常伦理,但是,亲情和伦理很快转变成政治话语。银环说:“没有农民来种地,全国人民吃什么,没有农业大发展,社会主义怎建设。”银环妈感觉到这些话的政治威胁和压力,马上退步说:“又算你妈我说错,光咱娘俩偷偷地说。你干农业我拥护!可是就是母女俩分割。”她力图把话题引到日常伦理上来,引到母女亲情这一话题上来。银环妈那句“光咱娘俩偷偷地说”是很有意味的,背后透出的是谈虎变色的心理,而她所说的“你干农业我拥护”正是在政治话语压力下违心所说,同时也是对自己“说错”的政治语言的纠正,是对政治话语压力的一种心理缓解。尽管并没有其他见证人在场,尽管争吵是在居室内进行,政治话语的威力依然没有褪色。
大团圆结局是具有中华民族文化色彩的叙事方式,也非常符合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朝阳沟》毫无疑问地采用了这一叙事方式。最后一出场戏“亲家母你坐下”是《朝阳沟》的“大团圆”结局。非常有意味的是,这场戏不仅有草草收场之意味,更重要的是在这场戏中,最应该是主角的银环竟然由主角变成了“旁观者”,成为可有可无的配角。银环只能在旁边静听三个“亲家母”对唱,完全失去了“话语权”。这一看上去不符合逻辑与常识的场景,恰恰流露出日常生活叙事与政治话语叙事的某种矛盾与分裂。在最后这一场戏中,人物矛盾和戏剧冲突已经得到和谐、圆满的解决,所以政治话语的中心自然不一定再是戏剧核心人物银环,而是剧中相对离政治话语中心较远的人物才更有利于创造出和谐轻松的气氛。在《朝阳沟》整个剧情中,也似乎只有这一段戏,其政治话语似乎荡然无存。
三、婚姻故事镶嵌到政治话语之中
豫剧《朝阳沟》的第三个隐形结构就是将婚姻故事巧妙地镶嵌到政治话语之中。
现在,我们一般将这出戏理解为栓保和银环的一段爱情与婚姻戏。实际上,将二者当成恋爱关系,只是我们对这出戏的再加工、再创造并渗入了听众审美感受的结果。如前所述,这是听众的一种误读。在1963年戏曲艺术片《朝阳沟》及其之前的《朝阳沟》并没有明确指明栓保和银环是恋爱关系。这出戏之所以成为豫剧现代戏的经典之作,很大程度是由于这种误读。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读?原因是这出戏采用了特定的叙事手段,那就是,将婚姻故事镶嵌到政治话语之中。
首先,《朝阳沟》并不是一个恋爱故事。《朝阳沟》讲的是城市姑娘银环和高中同学拴保高中毕业后同赴栓保家乡朝阳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故事自始至终都没有交代过二者有恋爱关系或婚约关系,也没有明示或暗示二者在三年同学期间有超出同学之情的其他关系。正面描写二者关系的唯一一段唱词是栓保所唱的《我坚决在农村干他一百年》。这段唱词这样描述二者关系:“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无话不谈,我难忘你叫我看董存瑞,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从这段话看,二者的关系并没有超出革命友谊的层面。而二者相约下乡,也正如栓保所唱:“咱俩个抱定了共同志愿,要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你说过党叫干啥就干啥,决不能挑肥拣瘦讲价钱。”下乡是听党的话,是为了做一个“有志青年”,无关恋爱婚姻。
其次,人物关系。银环下乡到朝阳沟,便与朝阳沟的人建立了特定的关系,尤其是和栓保一家人的特定关系。银环仅仅是栓保的高中同学,既然不是栓保的恋人,自然就不是栓保家的儿媳或未来儿媳。但银环在朝阳沟的身份又是什么,她为什么偏偏下乡到朝阳沟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作品并没有明确交代,也许是不便明确交代或不能明确交代。更重要的是,她下乡到朝阳沟后,为什么自然而然地住在栓保家,而不是别的什么地方,对于这种异常,剧情也没有给出交代。但是,对于这些异常情节、异常剧情,听众也能够自然而然地接受,甚至能听之任之,并不感觉到有什么突兀。究其原因,这一切都是由于银环“特殊身份”造成的。叙事者虽然并没有指明银环和栓保是恋爱关系,但透过故事,透过故事繁杂的外衣,听众或接受者已经将二者想象成恋人关系或婚姻关系。所以,当银环看上去无缘无故地住在栓保家时,也就不会感觉有什么不合逻辑之处。同样,当银环随栓保喊栓保爹娘为爹娘时,听众也觉得完全在情理之中。但是,毕竟故事并没有明确二者的特定恋爱关系,相反,二者特定的恋爱关系总是被政治话语稀释和操纵。比如,村支书在谈到银环的时候,也是从响应号召、建设新农村等政治话语角度,只是在最后才委婉地说“再说还有这层亲戚”。“再说还有这层亲戚”只是委婉地表明银环和栓保一家人的特定关系,并不仅仅限定为和栓保一人的特定关系,是“间接”的间接表述。另外,二大娘等人对银环的态度,也表现出对二者特定关系的若隐若现的特殊理解。
第三。称呼。对周围人的称呼很能直接地反映人物之间的特定关系或微妙关系,并隐藏着特定的人物心理。这出戏里的称呼略显混乱,这是由于略微混乱的叙事逻辑所造成的,更是由于银环特定而微妙的身份造成的。银环下乡表面理由并不是由于和栓保的特殊“恋爱关系”,而是积极响应当时的政策号召。银环称呼栓保爹娘为爹娘,称呼二大娘为二大娘,这并不表明银环与栓保的特定关系,也不包含有特定人物关系的意义,而是银环作为栓保的同龄人、同学,也作为晚辈对长辈一般意义上的称呼。如果有特定的关系的含意,也是间接的。只有栓保的妹妹巧珍略显例外,开始巧珍一直称呼银环嫂子,银环是默认的。考虑到银环并没有和任何人结婚,也没有和任何人定下婚约,听任或默认这种称呼是非常令人意外的。但是,当银环对朝阳沟开始动摇的时候,她立刻阻止巧珍这样称呼自己,所以,巧珍加重语气喊她“银环同志”。还有,一旦涉及相对严肃的政治话题,人物关系及其称呼就会非常明确。仔细听就会发现,凡是银环犹豫或与他人关系相对紧张时,都很容易被称为“同志”——巧珍这样称呼银环,二大娘这样称呼银环,栓保也这样称呼银环。这一称谓本身是以极具张力的话语形式将人物关系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用以掩饰日常生活下人物的真实而微妙的关系,同时,也有缓解和释放政治话语压力的作用。
如前所述,随着戏剧矛盾的高潮与解决,大家似乎也放松了政治警觉性,这就有了脍炙人口的“亲家母你坐下”唱段。在这里,无论是栓保娘、二大娘,还是银环妈,都自然而然地称呼对方为“亲家母”。“亲家母”的称谓最多也只能理解为间接地暗示了栓保和银环的恋爱关系,依然是对二者关系的间接表述而非正面表述。在不同的场合,“亲家母”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和完全不同的意义。所以,只能说是“放松”了警觉性,并不是说完全忘记。尽管如此,“亲家母”已经是整个剧情中对银环栓保二人关系的最明确的间接表达了。